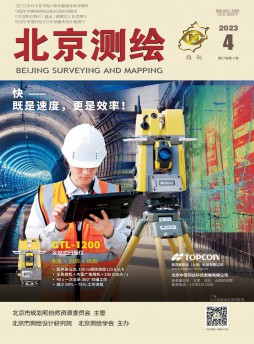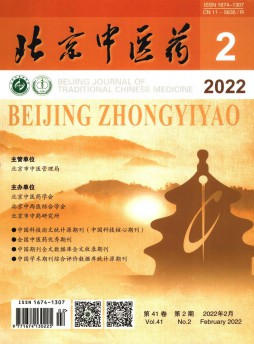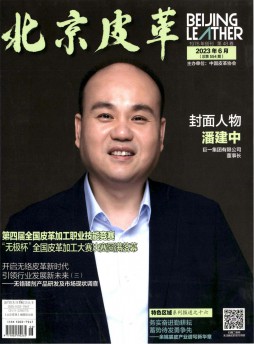論北京佛教文化的政治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北京佛教文化的政治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由于金朝對佛教從制度上加強整頓和管理,對寺廟修建屢作嚴格限制,故金中都金代修建的寺廟多為官寺。大定十四年(1174年)金世宗詔渝:“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1]112。金中都內大圣安寺、大覺寺、大永安寺、慶壽寺等皆為官辦佛寺。金朝對云居寺的石經刻造工程亦不予支持,故金代云居寺刻經規摸亦無法與遼代的刻經規模相比。元朝統一全國后,北京成為多民族統一的國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后雖歷經明、清朝代更迭,始終是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未再發生變動。元代中央一級的佛教組織都設在大都,先后有釋教總統所、總制院、宣政院等機構,使大都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隨著元朝的建立,藏傳佛教傳入元大都。元代諸帝皆對佛教大力扶植、優禮有加,遂為大都佛教之興盛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全國造寺日盛,遂出現了“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蘭勝觀,棟宇相望”的狀況。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圣壽萬安寺是大都首屈一指的藏傳佛教寺廟,寺內白塔如今已成為北京城標志性建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所造的壽安山寺,需開山鑿石,工程浩大,當時詔令“治銅五十萬斤,做壽安山寺佛像”(今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其所鑄佛像之巨大,又創下一個空前絕后的記錄。
云居寺石經續刻得到元朝政府的支持。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高麗僧人慧月,修葺了石經山華嚴堂,并補刻了堂內殘損的五塊經版。在元朝諸帝中以抄寫金字佛經最為盛行。當時著名書法家鄧文原、吳澄和班惟志等都應詔到元大都參加了書寫金書佛經的工作。僅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為書寫金字《藏經》就用了黃金3244兩。時人有詩為證:“朝廷年年寫佛經,千人萬人集佛庭”。元大都佛教文化的發展與元朝政府尊崇佛教的政策是分不開的。明成祖遷都后,使北京繼元朝后再度成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明朝歷276年,16位皇帝中除世宗崇道外,大多尊崇佛教,王室對佛教的崇信及其建造的佛教寺院,對朝野上下崇佛造寺起到了引領風氣之先的導向作用。據《大明會典》統計,自太祖立國,至憲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僅京城內外敕賜寺觀己至639所,后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絕。明朝京城各大寺院中,幾乎都有明代諸帝所賜的大藏經。明成祖朱棣還以超度戰死的將士亡靈為名,下令鑄造了著名的永樂大鐘。該鐘于明永樂年間在鑄鐘廠鑄造,鐘體通高6.75米,直徑3.3米,重46.5噸,內外壁鑄有《法華經》等17種佛教經咒,共計22.7萬余字,鑄成后先置于漢經廠,明萬歷時移至萬壽寺。由于明代帝王對佛教的扶植,使北京佛教發展很快。
北京作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對于全國各民族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佛教作為清王朝進行思想和精神統治的支柱之一,始終處于清王朝的掌控之下,北京佛教也隨著國運的興盛而發展。清朝京城不僅漢傳佛教寺廟林立,而且喇嘛廟在京城亦隨處可見。北京西黃寺是順治皇帝為迎請五世達賴而敕建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廟也是出于清朝統治者信仰和利用喇嘛教“安藏定邊”的政治需要。至今仍然矗立在雍和宮里的那塊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書寫的喇嘛說碑文非常清楚地講述了乾隆改雍親王府為喇嘛廟的初衷。正如乾隆所言:“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清朝在京城修建喇嘛廟,正是“建一寺勝派十萬兵”的政治體現。自元、明、清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來,封建的政治機構、官吏都集中在北京,管理全國佛教事務的機構都設置在京城,從這里的每一道有關佛教內容的皇帝諭旨,不僅影響著北京佛教與文化的發展,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佛教的發展。出于政治與信仰的需要,歷朝帝王多出資修廟,使高僧云集京城。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為佛教文化中心創造了前提,北京佛教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又依靠政治中心的影響得以高度發展。
一、北京皇宮御苑內的佛教文化
由于對佛教的崇奉,明清二朝在皇宮御苑內多建有佛寺與佛堂,數量相當可觀。皇宮中的佛堂在建筑形制上,為了與皇宮宮殿建筑環境相匹配,因而比皇宮外建造的佛教寺廟更為雍容華貴和氣派,更具皇家風采,為北京佛教文化一大特質。皇宮里的佛教殿堂,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寺院,但具備佛寺的基本功能,何孝榮先生將其界定為準佛寺。紫禁城內的佛教建筑主要分布在宮殿中軸線的西路,且多以佛堂的形式出現。紫禁城西路,佛教殿堂相對集中在宮殿的后部區域。中正殿佛堂區,是皇宮佛教活動的中心區域。除此之外還有寧壽宮佛堂區,慈寧宮佛堂區,慈寧花園佛堂區,福宮花園佛堂區和御花園佛堂區,以及養心殿東、西配殿和養心殿西暖閣為代表的各處殿堂暖閣內設立的小佛堂。這些佛堂,有的是專供皇帝進行佛事活動使用的,有的是專供皇太后、皇后以及嬪妃們、皇子們進行佛事活動使用的。從紫禁城內佛堂的建造、布局以及陳設來看,是按照皇帝對佛教教義的理解來設置的。北京佛教寺廟建造是古老的北京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特別是那高大的紅墻,金碧輝煌的殿堂,縱貫全寺的中軸線,幽雅恬謐的庭院建筑,與皇宮禁城的建筑渾然一體,從而達到功能與藝術的統一,給人一種撼人心魄的東方特有之美感。
(一)中正殿
紫禁城設有專門管理藏傳佛教活動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簡稱“中正殿”,這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佛堂。中正殿佛堂,原名元極寶殿,又名隆德殿,為明清兩朝皇帝禮佛的場所,也是皇宮佛教活動的中心。《酌中志》載:“萬歷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圣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須于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2]118-119明朝藏傳佛教跳布札的佛事活動曾經在此舉行,到了清朝不僅皇帝在此禮佛,而且還請著名喇嘛在此誦經,定期舉行藏傳佛教佛事活動。如嘉慶《大清會典事例》載:“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奉旨:中正殿供奉佛像,著喇嘛念經,交與札薩克達喇嘛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中正殿念經處,外旗蒙古鋪排頭目二名,內府鋪排頭目一名,俱授為八品筆帖式。其余鋪排等,俱更名為蘇拉筆帖式。”①中正殿是明清兩朝皇帝在紫禁城內進行佛事的中心。
(二)雨花閣
雨花閣為紫禁城內典型的藏式佛殿,最初是乾隆皇帝禮佛修持的壇城,也是清朝政府安藏定邊策略的重大舉措。乾隆皇帝說:“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與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故數十年可得乎?”[3]乾隆皇帝在紫禁城內修建雨花閣,實則是“以黃教柔訓蒙古”政策的體現。雨花閣完全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唪經定例而建,借鑒了西藏著名的阿里古格托林寺黃金神殿的建筑風格。雨花閣分為四層為金剛塔式布局,按藏傳佛教密宗理念設有三座壇城,三座紫檀木壇城均坐落在漢白石座上。自乾隆皇帝始,清朝歷代皇帝亦按例供佛朝拜,此制一直延續至宣統年間。[4]
(三)皇家御苑中佛教文化
皇家御苑中佛教殿堂和佛塔的建造要比紫禁城中佛教殿堂更為豐富多彩,有的小巧玲瓏,有的高大雄偉,除了佛教殿堂外,還有高大的佛塔,這是紫禁城內佛教建筑所不及的。另外,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在建筑布局上也獨具特色。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建筑大多因地形地貌而建造,且與御苑中的山水相依,與皇宮中佛堂相比其規模要略小。北京現存的皇家園林有位于城內的西苑三海即中海、南海和北海,還有頤和園(即清漪園)、玉泉山園林(即靜明園)、香山園林(即靜宜園),圓明園、暢春園和南苑。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有北海中的永安寺、闡福寺、西天梵境、小西天等,永安寺內的白塔,靜宜園的昭廟,暢春園的恩佑寺等。皇家御苑中佛教殿堂最典型最具特色當屬頤和園的佛香閣,還有頤和園的智慧海,以及圓明園的日天琳宇。乾隆十五年(1750)為慶賀崇德皇太后六十壽辰在清漪園(頤和園)建大報恩延壽寺,并將甕山改稱為萬壽山。頤和園除了佛香閣和智慧海佛堂外,還建有轉輪藏、五方閣、寶云閣、四大部洲、香巖宗印之閣、善現寺、云會寺等,這些佛教建筑基本上都坐落在萬壽山的前山和后山。另外靜明園里的楞伽洞、華嚴洞、觀音洞也獨具特色。這些佛教殿堂不僅僅是皇家禮佛的殿堂,而且是皇家御苑中靚麗的景觀,是北京佛教文化的組成部分。
二、北京佛教寺廟是文物藝術的寶庫
北京佛教寺院是北京佛教文化的物質載體,賦予了北京極其豐富的佛教文物遺存,較好地保留了建筑、雕塑、繪畫、經典、碑刻等豐富的佛教文化資源,有的佛寺本身就是文物,或者是珍藏有罕見文物的藝術寶庫,具有傳播和承載北京傳統文化的功能。北京佛教寺院是供奉佛教諸佛與菩薩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侶進行宗教儀式、修習和居住的場所。它不僅是一種宗教建筑,同時也是佛教藝術薈萃之地,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如北京八大處靈光寺的佛牙舍利、云居寺的石經、廣濟寺的指畫、法海寺的壁畫、雍和宮里的大佛、智化寺的佛樂清音等等,無不是深藏于佛教寺院中的稀世珍寶。
(一)云居寺的石經
北京最珍貴的佛教文化遺產,當屬云居寺的石經。云居寺收藏的已逾千年的一萬五千余塊石經,全部經版鐫刻的佛教經典達千萬字以上,使云居寺成為世界佛教典籍的石書庫。而且石經上匯集了千百年來無數雕刻家和書法家的字跡,石經上鐫刻的字體風格各異,結構嚴整,蔚然壯觀,是書法藝術中的精品,是歷史留給人類的稀世珍寶。學界一致認為:房山石經是以歷代佛經善本為依據刊刻,不啻一座巨大的善本佛典寶庫,特別是其中保存有五十余卷我國現已佚失的佛教典籍,在佛教思想和歷史研究方面彌足珍貴,而且對于存世佛經的校勘有著重要價值。附在房山石經經文后總計達6800余條的題記,是研究我國北方地區中世紀政治、經濟結構、社會風俗,以及官職、手工業、工商業發展狀況的珍貴資料,云居寺石經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云居寺石經雕刻字跡端莊秀麗,技法純熟流暢,薈萃十一代書法家之大成,對于書法藝術、雕刻藝術和文字演變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趙樸初先生稱房山石經為“國之重寶”,云居寺為“北京的敦煌”,被譽為世界七大石窟之一。云居寺石經的發現,被認為是繼陜西秦始皇兵馬傭之后的又一世界奇觀。云居寺除石經外,還珍藏著“國家一級文物”、國之重寶———木板經。木板經即乾隆版大藏經,又稱清藏或龍藏,是清代由皇室下令刊刻出版的一部佛教典籍叢書,因其所用的經版為木質雕版,俗稱“木版經”。龍藏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確定,它不但是我國的一宗珍貴文物,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受各信奉佛教國家的關心和重視。1981年11月27日在云居寺雷音洞內發現的貯藏千年的“佛舍利”更是世界珍寶。云居寺不愧為藝術寶藏。
(二)靈光寺佛牙舍利
北京靈光寺佛牙舍利塔供奉著佛祖釋迦牟尼佛牙。釋迦牟尼佛有兩顆佛牙存世,一顆在中國北京;一顆傳到錫蘭(今斯里蘭卡)。北京僧眾為保護這顆佛牙歷盡艱辛,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對此處進行狂轟濫炸,招仙塔連同其他殿宇均化為廢墟,佛牙舍利亦下落不明。多年后,僧人圣安率眾修復寺院,在清理招仙塔基瓦礫時,發現一石函,內裝一只沉香木匣,上刻“釋迦牟尼佛靈牙舍利,天會七年四月廿三日記,普慧書”的墨字題記和梵文經咒。天會是五代時期北漢政權的年號,善慧為北漢僧人,宋太祖曾賜其“宣秘大師”稱號。在圣安的主持下沉香木匣被開啟,果見佛牙一顆,遂將其供奉于禪堂內。1964年6月,在靈光寺內重新修建了佛牙塔,并將釋迦牟尼佛牙供奉在舍利塔堂內。自此,靈光寺就成為中外佛教團體和信眾朝拜的圣地。靈光寺佛牙塔內珍藏的佛牙,云居寺內珍藏的兩顆佛祖舍利和西安法門寺珍藏的佛骨指舍利,并稱為佛事海內三寶。
(三)法海寺壁畫
壁畫是繪制在建筑物墻壁上的藝術品,是繪畫藝術和建筑藝術的完美結合。佛教壁畫可分為寺院壁畫和石窟壁畫兩部分,北京地區佛教壁畫以寺院壁畫為主,其中法海寺壁畫堪為佛教藝術瑰寶。法海寺以大雄寶殿內保存完好的《帝釋梵天圖》十鋪明代壁畫而聞名中外,這些被稱為國寶的壁畫距今已有560年的歷史。法海寺壁畫具有構圖嚴謹、筆法細膩、技巧純熟、用色考究等特點,因其采用“瀝粉貼金”的手法,故壁畫達金碧輝煌的效果,實為現存古代壁畫中的極品。徐悲鴻、侯仁之等專家一致認為:“法海寺壁畫的藝術水平、繪制工藝、制作工藝及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為我國明代壁畫之最,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最高水平,是我國元、明、清以來現存少有的由宮廷畫師所作的精美壁畫,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在壁畫方面的杰出代表,與敦煌、永樂宮壁畫各有千秋,并可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相媲美。”[5]80-81法海寺壁畫是中國壁畫藝術水平極高的杰作,堪與宋元壁畫相媲美,在中國繪畫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北京地區現存歷史最久和最完整的壁畫。
(四)大型佛教繪畫———指畫之冠《勝果妙因圖》
北京廣濟寺大雄寶殿佛像影背后面,裱貼有一幅描繪釋迦牟尼佛在靈山說法的巨幅繪畫,這就是清代著名畫家傅雯奉乾隆皇帝諭旨為皇太后祝壽所作的指畫《勝果妙音圖》。這幅繪畫采用中國傳統畫法中的指畫技法繪制而成,故名指畫。《勝果妙音圖》高6米、寬1.3米,紙本、水墨淡設色。全圖場面宏大,人物眾多,形象傳神生動。畫面的中央是釋迦牟尼佛端座在蓮花寶座上,笑容可掬地向信徒講經說法,空中有騰云駕霧的四大天王護法,佛的左右分別為騎著獅子的文殊菩薩和騎著白象的普賢菩薩;佛祖寶座前是善財童子以及大鵬鳥和迦陵頻伽鳥,均為人頭羽翼,冉冉飛行;周圍一百多位弟子神態各異,無一雷同,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其中還有中國的布袋和尚以及三國時期的關羽、關平和周倉,雖與此畫背景不甚相宜,卻也符合畫家所處時代三教合一的國情。在《勝果妙音圖》畫幅的右下角有作者署款:“勝果妙音圖,乾隆甲子九年清和月八日,奉敕沐指畫墨恭摹尊像,臣傅雯□□”,從署款中得知此畫繪于清乾隆甲子九年(1744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據《讀畫輯略》記載:傅雯“善指頭畫,得高且園之傳,尤長于盈丈佛像。乾隆甲子,供奉內廷,尋以旗員補用。武職通世,故善詼諧。詩畫皆敏捷,俄頃間,可得數十幅。題識亦不作尋常語。尤好從僧游,故其得意之作,僧寮中多有之。”①在中國畫史上只有傅雯一人能夠繪制如此巨幅的指畫。廣濟寺大雄寶殿內珍藏的這幅《勝果妙音圖》指畫,是目前國內外所存最為巨大的指畫珍品,具有極高的欣賞價值和文物價值。
(五)智化寺“京音樂”
智化寺的“京音樂”是北京佛教音樂的典型代表,屬漢傳佛教的廟堂音樂。明成祖朱棣曾搜集唐、宋、元以來流行于南北地區的佛教音樂曲調四百多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問世,權傾朝野的宦官王振將深藏宮中的佛教古樂譜據為私有,使宮廷音樂流入智化寺內,今日所見智化寺所用的古譜曲牌,大部分與此曲集中的名稱相同。正統十一年(1446年),該寺成為北京地區佛教音樂的傳播中心,素有“京音樂”之稱。五百多年來,智化寺“京音樂”傳承未斷,至今該寺樂僧已傳至26代。智化寺“京音樂”在演奏技巧與方法上,至今保持著歷史原貌,被稱為廟堂音樂的活化石。現演奏的曲目主要為第15代樂僧永乾,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整理的《音樂腔譜》,共載有48首佛曲,其中有唐代教坊曲《望江南》《千秋歲》《感皇恩》《后庭花》等;有與宋代詞牌相同的《一剪梅》《醉春風》《梅花引》《粉蝶兒》等;還有與唐代法曲同名的《獻仙音》等;最多的還是傳統的贊唄樂曲如《三寶贊》《金字經》《華嚴燈贊》《普庵咒》《楚江秋》《五團花》《焚化贊》《大華嚴》和《小華嚴》等。此譜為工尺譜,但與民間工尺譜的記載符號和點板方式不盡相同,頗具唐、宋遺韻。智化寺設有專門的樂僧,演奏的曲牌分為只曲和套曲兩種。單獨演奏的曲牌為只曲,若干首曲牌連綴演奏的為套曲。《音樂腔譜》中記載了41首套曲,其中“中堂曲”5首,多在白天作法事時演奏,晚上舉行超度餓鬼“放焰口”時通常演奏有14首曲牌組成的套曲“料峭曲”。白天和晚上演奏的兩個套曲風格迥異,前者恢弘、堂皇,富有佛家正大光明的氣度;后者則委婉、沉郁,頗具佛家悲天憫人的柔情。演奏時使用的樂器有鼓、鐺子、小鈸、大鈸、鐃、木魚、笛子、十七簧笙、九孔管、云鑼等。演奏時,九孔管處于領奏地位,笙用來表現樂曲的節奏,笛子則自由活潑地穿插于旋律之中,這種既發揮各種樂器的特點、又和諧統一的演奏風格,一直延續至今。當今的智化寺佛教音樂,已由北京佛教協會組建的佛教音樂團繼承下來,除演奏傳統佛樂曲牌外,又在吸收民間曲調的基礎上,創作出更為豐富多彩的佛教音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北京佛教音樂團出訪西歐、新加坡;1996年出訪德國,并且參加了國際宗教音樂的交流。他們演奏的《五方佛》《行道章》《倒提鎦金燈》《金鎖套十番》等樂曲,已成為享譽世界佛壇的音樂。另外,在智化寺內發現的“以血為墨”書寫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等,不但令人驚嘆!而且是世間極為罕見的珍品。
(六)雍和宮里的珍品
北京的雍和宮不僅是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佛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機構。雍和宮的喇嘛除從事佛事活動外,還要從事經文、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的研究,清朝宮廷里用的歷書就是雍和宮喇嘛編寫的。雍和宮喇嘛編寫的歷書除供清宮廷里使用外,還供西藏、青海、內蒙古地區使用。雍和宮里珍藏的藏傳佛教文物,可以和布達拉宮的文物相媲美。雍和宮萬福閣里的白檀木大彌勒佛是“世界獨木大佛之最”。這尊獨木大佛從地面到頂部高達18米有余,埋在地下的還有8米。大佛佛身面寬8米,另人驚詫的是這尊大佛通體由一整棵白檀木雕制而成。佛像面部端莊慈祥,神態雍容爾雅,體態雄偉,全身貼金,鑲嵌著各種各樣的珠寶。抬頭仰目觀望著佛首,真有落冠之勢。據說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到雍和宮參觀訪問時驚訝地贊嘆道:“它給了我美的享受……”。雍和宮里的大佛不但堪稱北京宗教精華之最,而且是“世界獨木大佛之最”。雍和宮照佛樓里的金絲楠木佛龕供奉的那尊黃銅制的照佛是件稀世的藝術珍品。照佛的佛龕以及火焰背光,全用金絲楠木雕刻而成。雍和宮法輪殿內高大的五百羅漢山是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藝術精品,雕刻雖然細膩,其造型卻又顯得粗獷。獨木大佛、金絲楠木佛龕和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五百羅漢山,堪稱木雕制品的三絕。雍和宮永佑殿珍藏的唐卡———綠度母補繡像,是乾隆皇帝的母親孝圣憲皇后用了七千多塊色澤不一,大小不等的緞子親手補繡而成的。這幅唐卡中的度母神態栩栩如生,色彩艷麗,堪稱唐卡中的精品。如今這幅巨大精美的補繡像成為永佑殿內最珍貴的文物。雍和宮里的佛像、唐卡、三光毯、喇嘛碑和億萬年前的風眼香等等,件件都是難得的藝術珍品,雍和宮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宗教博物館。北京佛教文物遺存數量之多、藝術之精湛、保存之完美、文化內涵之豐富,是任何一座城市都無法比擬的。北京佛教寺院就是一座珍藏文物與藝術珍品的寶庫。
三、北京藏傳佛教文化的政治作用
藏傳佛教是流行于我國藏、蒙、土家、納西等民族地區的佛教宗派。藏傳佛教經西域傳入蒙古地區,受到蒙古貴族的崇信,并隨著蒙古政權不斷向南擴張,而進入中原漢族地區。元代統治者原本信仰薩滿教,隨著蒙古民族對外軍事的征服,使他們開始接觸到藏傳佛教。“藏族高僧深厚的宗教修養吸引著他們皈依沙門”[6]701。元朝統治者大力扶植喇嘛教,其最初用意是把它當作安藏定邊的策略,另外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也有意使喇嘛教成為控制漢民族的手段。出于對鞏固西藏統治政策的需要,元代尊藏傳佛教為國教,封薩迦派高僧八思巴為國師,并賜玉印,使其成為統領全國佛教的領袖。元朝政府在元大都設置宣政院,管理全國的佛教和西藏等地的軍政事務。由于元世祖忽必烈與藏傳佛教薩迦派教高僧八思巴的政治結緣,不僅使接受藏傳佛教后的蒙古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與藏民族連為一體,而且使藏傳佛教傳入京城。自此,元大都的藏族僧人不斷增多,藏式寺廟也陸續營建,獨具特色的藏族文化亦以藏傳佛教為載體而傳入北京地區。因此,元大都內的藏傳佛教寺廟不僅是禮佛的殿堂,而且是元朝政府與邊疆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平臺。
藏傳佛教文化從遙遠的青藏高原來到元朝的政治中心,并融入元大都文化之中,藏族文化以藏傳佛教文化的姿態在元大都綻放。如:由藏僧八思巴帶到京城來的尼泊爾著名工匠阿尼哥主持建造大圣壽萬安寺中的白塔帶有鮮明的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白塔的建造,就是藏傳佛教傳入北京城的標志性建筑,它代表藏族文化在北京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元大都內喇嘛廟中的佛像雕塑藝術也獨具鮮明的藏族文化特色,“金剛護法”的雕塑令人生畏,力量無比,與漢傳佛教中護法像反差極大。藏族文化正是通過藏傳佛教文化的方式在元大都傳承下來的。明代延襲元代以藏傳佛教治理西藏的政策,從明永樂開始,對藏傳佛教實行了“多封眾建”的政策,即對各教派領袖人物都加以封賜,改變了元代獨尊薩迦的政策。明成祖曾多次遣使入藏,迎請格魯派首領宗喀巴進京說法,并請噶舉派首領哈立麻入京主持法會,致使藏傳佛教再度東來。明成祖還特意在京城修建了藏式的寺廟———“真覺寺”,以供來京城的西藏喇嘛居住。因真覺寺內的藏式佛塔與中原之塔建造迥然不同,所以京城百姓稱之為“五塔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新修建的大隆善護國寺,是明朝主管全國佛教事務的中央機關———僧錄司所在地。明朝來京的大智法王班丹札釋、西天大喇嘛桑渴巴辣、西天佛子大國師張公(藏名“桑節朵而只”)、灌頂大國師班卓兒藏卜、大覺法王著肖藏卜、西天佛子著乩領占朵多只巴、妙濟禪師綽巴札釋等高僧都錫駐于此寺。明朝北京城內的大隆善護國寺與大慈恩寺、大能仁寺是京師著名的三大藏傳佛教寺廟,是明代西藏僧人居京修持之地。從明成祖對西藏高僧“多封眾建”政策的實施,以及朝貢制度和茶馬互市政策的確立,不僅確立了明朝政府與西藏地區的隸屬關系,加強了對西藏地區的統治,而且也促進了北京藏傳佛教文化的發展。
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后,為了進一步強化對蒙藏地區的直接管轄,特別看中喇嘛教對蒙古的作用。清代設置理藩院,在繼承元代宗教政策的基礎上,又有所補充和完善,“以黃教柔訓蒙古”正是清政府安藏定邊的基本國策。從順治到康熙,清朝中央政府冊封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皇帝賜五世達賴金冊、金印,賜封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喇怛喇達賴喇嘛”。從此,達賴喇嘛的封號正式確立,藏傳佛教格魯派歷世達賴喇嘛轉世都必須經中央政府冊封始成為定制。清政府對喇嘛教各宗派首領都具有封贈和廢黜權。康熙皇帝曾多次對蒙藏上層人士和喇嘛教首領說:“本朝為護法之主”。為加強對喇嘛教的管理,清王朝采取“眾建而分其力”的政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大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并賜金冊金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為“灌頂惠普廣慈大國師”。自此形成了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統,使他們具有同等權力與地位。這一舉措進一步加強了清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統一管轄,從而也分散和削弱了達賴為首的神權勢力及對蒙古地區的控制。清朝中央政府為了防止在活佛轉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弊端,避免蒙古王公貴族利用喇嘛教,并與宗教領袖人物互相勾結,集政教權勢于一身,以形成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不利局面,乾隆皇帝對活佛轉世制度進行了改革,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分別在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宮設立“金奔巴”(奔巴,藏語“瓶”)制度。北京雍和宮的“金奔巴”決定北京地區和內蒙古地區活佛喇嘛的轉世。西藏大昭寺的“金奔巴”決定達賴與班禪的轉世。自此清朝中央政府將轉世靈童的確立權掌握在清王朝的手中。
“金瓶掣簽”的實行,也是中央政府對西藏、蒙古地區行使主權的一種體現。這一制度的確立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清王朝對藏傳佛教的管理,而且也防止了蒙藏貴族對宗教權力和財產的染指。金瓶掣簽制度已經成為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傳承文化。清統治者為加強蒙古地區和藏族地區的統治,積極強化藏傳佛教這一文化紐帶,在北京多處修建喇嘛廟,供養蒙古和藏族高僧。為迎請五世達賴喇嘛的到來,順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門外鑲黃旗教場北(今德勝門外西黃寺大街)專門修建了喇嘛寺廟西黃寺,作為欽待五世達賴在北京期間的駐錫之所。康熙在北京建造了不少藏傳佛教的寺廟,如康熙四年(1665年),將太液池西南岸的明朝清馥殿改建為宏仁寺喇嘛廟;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南苑建造了永慕寺;三十三年(1694年)在皇城內建造了瑪哈噶喇廟(普度寺),寺中供奉藏傳佛教瑪哈噶喇神像。康熙五十年(1711年)為章嘉呼圖克圖修建了嵩祝寺等等。康熙在位時重修的喇嘛廟也很多,如妙應寺(俗稱白塔寺),崇國寺(即大隆善護國寺)等,并親自為重修廟宇撰寫碑文,為寺廟題寫的匾額更是多不勝數。雍正元年(1723年)修建了福佑寺,重修隆福寺,在安定門外修建了達賴喇嘛廟。乾隆九年(1744年)將雍親王府改建為喇嘛廟,即雍和宮。此后又在皇宮園囿、三山五園內修建了大量的藏傳佛教寺院。清代北京藏傳佛教寺廟的修建,不僅為在京的藏、蒙僧眾舉行佛事活動提供了宗教活動的場所,為漢、藏、蒙等民族進行文化交流搭建了平臺,為藏傳佛教文化日益民俗化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加強了民族團結、維護了祖國的統一,使獨具民族特色的北京藏傳佛教文化日益繁榮起來。隨著北京藏傳佛教文化的發展,藏傳佛教獨特的金剛驅魔神舞、大威德金剛壇城法會、打鬼(跳布扎)等藏族的佛教舞蹈逐漸演變成北京民眾喜愛的民俗活動。
四、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重要的標志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舉世聞名的千年古都,匯聚著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承,形成了多元文化體系。北京不但擁有三千多年的建城歷史,是遼、金、元、明、清五個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很早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是多種宗教和諧共存的所在。北京是帝王北京、百姓北京、宗教北京。美國城市社會學家R•E•帕克曾經說:“城市是一種心理,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也就是說,體現一個古老名城的標志,不僅僅與其傳統文化有關,而且也與其宗教載體密切相關,[7]從城市學的角度來看:宗教文化是城市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北京佛教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是北京城市文化和歷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擁有的古剎,居全國都市之首。據《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統計:1928年北京登記在冊的寺廟為1631個。另據1947年北平市政府統計:當時全市城區和郊區的寺廟為1920座。在北京城形形色色的寺廟中,佛教寺廟幾乎占去了半壁江山,近一千多座。佛教自東晉十六國時傳入北京地區,至今已有1600年的歷史。民國年間,佛教寺廟坐落在北京內城的大約有400多座,均勻地分布在東西南北四個城區,但是坐落在外城東南郊的寺廟僅有100余座,而北京外城西北郊的佛教寺廟卻多達500多座。因此,北京有“西山五百寺”之說。
“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是燕趙地區婦孺皆知的諺語。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趙樸初先生曾寫“氣攝太行半,地辟幽州先”之聯,來贊揚潭柘寺殊勝的地理位置與其悠久的歷史。雖然這一說法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據,但從北京周邊地區佛教的傳入,以及《魏書》的記載來看,潭柘寺的建立是極有可能的。潭柘寺、戒臺寺、云居寺、法源寺、靈光寺、臥佛寺等都有一千年以上的寺院發展史,與千年古都北京城一起經歷了風風雨雨,共度滄桑,見證了千年古都北京城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北京云居寺珍藏的一萬五千余塊石經,更是北京城發展過程中的精彩篇章,每一塊石經都見證了北京城發展的歷程。北京佛教文化具有歷史發展完整的脈絡,北京佛教寺院是佛教現實化、物質化的載體。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北京的重要標志之一。(本文作者:佟洵單位: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 上一篇: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建議范文
- 下一篇:塔吉克族語言發展對策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