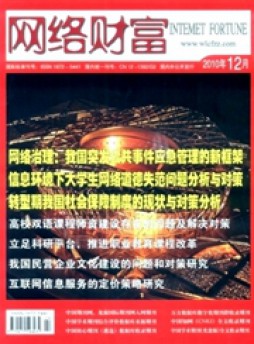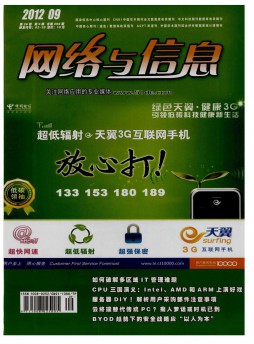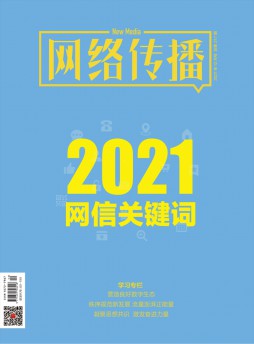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可能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可能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網絡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崛起,尤其是公民以個體形式,直接通過微博進行實名舉報的迅速發(fā)展并非偶然。一方面,目前體制內監(jiān)督因主客觀原因的多重影響,現狀并不樂觀,這就需要網絡輿論監(jiān)督作為一種“非體制內”的監(jiān)督手段的出場,其構成了網絡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除了其作為媒體與生俱來的“監(jiān)督權”之外,網絡媒體作為輿論監(jiān)督的一個特殊的平臺和手段,具有其特殊的優(yōu)勢,而此優(yōu)勢構成了網絡輿論監(jiān)督存在的必然性。
(一)網絡媒體監(jiān)督平臺在我國,傳統(tǒng)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作為對權力的一種監(jiān)督形式,由于受到種種因素制約其發(fā)揮作用并不理想。而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橫空出現有效規(guī)避了傳統(tǒng)媒體受到的限制,使輿論監(jiān)督得到補充,從而得到實現。一方面,在我國,受體制因素制約,“對權力者的監(jiān)督歷來十分困難”[2]。同級媒體不能監(jiān)督同級黨委,這種體制下的媒體就成了政府管理社會的工具,從而極易忽視作為輿論監(jiān)督信息來源的民意基礎,更無法有效地發(fā)揮對反腐倡廉的監(jiān)督作用。另外,市場經濟影響下的地方傳統(tǒng)媒體極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團的制約和限制,包括政府、企業(yè)、大型社會組織等。因此受制于地方本位主義的障礙,當傳統(tǒng)媒體對貪官污吏展開披露時,媒體輿論監(jiān)督就會被視為影響地方形象的手段,地方政府和有關官員很可能利用權力對媒體實行打壓和恐嚇,使輿論監(jiān)督無法有效進行。而網絡媒體則很少受相關體制上和地方本位主義的制約與限制。首先,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相當強的開放性。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準入門檻的降低,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主體可以是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此時的主體只代表個體本身,不涉及任何組織的利益,因此幾乎不受任何組織制約和管控;二是網絡媒體超出了同級媒體不能監(jiān)督同級黨委所規(guī)定的媒體范圍,因此輿論監(jiān)督主體可利用網絡這一新媒體平臺,對各級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員進行無惡意的曝光,從而使網絡輿論監(jiān)督有效實現。另外,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傳統(tǒng)媒體輿論監(jiān)督所擁有的寬容性:目前國內的受眾已能熟練地對被審查過的媒體文本進行顛覆性解讀,發(fā)掘出其中深奧的信號,受眾開始能夠避開意識形態(tài)部門對言論的管控對權力部門及權力人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同時,基于這一變化,越來越多的受眾開始對傳統(tǒng)媒體提出質疑,這一質疑使受眾對網絡媒體的信任度愈發(fā)提高,原因在于,網絡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更值得信任、更加安全且有效的平臺,使受眾能夠“在國內或跨越國界來討論政治性的敏感問題”。網絡輿論監(jiān)督由此展開。比如,2013年年初“山西房媳案”中,爆料人高勤榮就選擇了微博作為其爆料的首發(fā)平臺,一則由于其出獄后失去了原有的報紙,二則,他認為自媒體時代的到來,“我感覺互聯網比以前的平臺還好”。另一方面,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還指出,“中國媒體在市場化和商業(yè)化的過程中正在獲得相對的自主權……中國的媒體市場既受到管控,又受到激發(fā)”[1](P33)。相對獨立的公民記者和獨立監(jiān)督人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這一改變。具有一定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公民記者獨立出原有受到管控的傳統(tǒng)媒體,利用在傳統(tǒng)媒體積累的優(yōu)勢資源,在網絡平臺上對信息進行和曝光。同時,具有獨立性的公民記者在話語領域也進行著從媒體話語向社會話語的轉變:媒體話語決定了新聞從業(yè)者在新聞報道中必須遵守體制內的“游戲規(guī)則”,對官員腐敗的新聞有所取舍,而當新聞從業(yè)者的身份發(fā)生轉變,其話語形態(tài)也隨之發(fā)生了轉變,進入了社會話語領域,作為公民的他們,可以在網絡這一平臺上,暢所欲言,隨之對權力的監(jiān)督也更加暢通和不受限制。
(二)作為一種監(jiān)督手段的網絡媒體監(jiān)督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3]。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jiān)督、人大監(jiān)督、政府內部監(jiān)督、政協民主監(jiān)督、司法監(jiān)督、公民監(jiān)督和輿論監(jiān)督組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監(jiān)督體系。但是,就我國對權力監(jiān)督與制衡的現狀來看,除了輿論監(jiān)督外的上述其他監(jiān)督程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內官員權力進行了監(jiān)督與制衡,但從某種程度上講,依然屬于一種“臨近失效”的狀態(tài):全國范圍內的政治表達流暢度較弱、相關行政過程開放度較低、司法機關處理相關案件的能力也有待提高。這些相對滯后的因素成為制約“體制內”監(jiān)督的重要因素。因此,從輿論監(jiān)督的原始理論出發(fā),我國的媒體輿論監(jiān)督已逐漸成為彌補上述體制內監(jiān)督缺陷的、對權力進行監(jiān)督和制衡的“第二權力”。一方面,市場化體制催生下的眾多媒體已經“斷奶”于相關體制,基于生存的本能,媒體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曝光包括官員腐敗在內的社會黑暗面以爭取更多的受眾;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新聞從業(yè)人員和公民記者,開始將“揭黑”作為維護包括自身在內的公民的有效權益的表現。在此大背景下,網絡媒體輿論監(jiān)督應運而生。與上述“臨近失效”狀態(tài)的監(jiān)督手段相比,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內容公開性、手段獨立自由性、過程迅速性和全面廣泛性。首先,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曝光內容公開性的優(yōu)勢。這一優(yōu)勢也是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其優(yōu)勢的根基所在。究其原因,官員腐敗案件的披露只有在完全公開透明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才能真正做到標本兼治。仍以“山西房媳案”為例,爆料人對“房媳”的揭露并沒有止于2013年1月22日的一條爆料微博,而是繼續(xù)跟進,連續(xù)發(fā)表了321條相關微博。前期(爆料后當日到山西三部門攜手調查)集中在對“房媳”的相關涉案問題的進一步爆料,如舉家造假問題、戶口問題、失業(yè)證問題、家屬(主要為“房媳”公公孫太平和丈夫孫紅軍)腐敗問題、超生問題等的揭黑;中期(調查開始至孫紅軍落馬)集中在對案件查辦的敦促以及進一步爆料,此時爆料的聚焦點開始集中在“房媳”丈夫,時任夏縣公安局局長孫紅軍身上,如艷照門問題、非法攜帶槍支彈藥問題、房產問題等。由于案件目前止步于孫紅軍的落馬,因此現階段微博主要集中在對孫太平貪腐行為的揭露和對案件進一步調查的敦促上。由此觀之,相比于傳統(tǒng)的官方監(jiān)督手段,網絡輿論監(jiān)督能夠更加全面、系統(tǒng)地將整個案件完整地還原,使相關材料更加豐富和完善地呈現在公眾眼前。一方面,官方監(jiān)督手段客觀上存在缺陷:首先,政府的信息公開雖比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前有所進步,但是其開放程度依然相對較低———需要公開時沉默、有所保留公開等;其次,政府信息公開更多地偏向于單向度輸出信息,忽略了公眾對信息的關注與反饋,由此造成了整個信息公開過程的不平等。而網絡輿論監(jiān)督恰恰規(guī)避了官方監(jiān)督模式下的弊端,其更少的限制和更簡單的利益鏈條使最終呈現出的爆料信息更加完善;另外,在整個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中,公開在網絡上的爆料信息也隨時接受著社會的監(jiān)督———虛假信息被淘汰、真實信息被建構、更多的信息從反饋中得到,在這種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的更加完善的流程中,使信息具有了公信力,從而也更加真實,更加全面。其次,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優(yōu)勢還有監(jiān)督手段的獨立自由性。在應對腐敗的過程中,確保監(jiān)督機構和反腐機構的獨立性是能否取得反腐成效的關鍵因素[4]。目前,在黨中央已經開始注重強化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的前提下,上述體制內監(jiān)督手段在實施過程中已經具備相對的獨立性,但仍存在干擾性因素對獨立性的制約,“紀檢部門應該沖鋒在前,有線索就查,有腐敗就懲,但總感覺是遲緩、滯后”:法律層面,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制度欠缺,制度層面,相關部門利益的牽制與糾葛,而網絡輿論監(jiān)督則更少地受到這兩方面因素的制約,從而能夠獨立自由地表達意見。網民作為獨立的個體在網絡,特別是微博上的信息一般情況下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網民只對自己負責、就事論事,因此其發(fā)表的言論也就相對具有獨立性。再者,網絡上往往會形成針對某一事件的討論,在公開而獨立的爭辯中,使文本中所呈現的事實越來越接近本質的真實。這一獨立自由公開討論的機制是體制內權力監(jiān)督手段所無法觸及的。因此,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獨立性又確保了其內容的公開性和全面性。在“山西房媳案”中,爆料人就是借助了微博這一平臺,規(guī)避了傳統(tǒng)的上訪制度下的復雜環(huán)節(jié),直接將信息通過140字在微博平臺曝光,并在相對自由平等的媒介環(huán)境下,基本不受牽制地對事件進行跟蹤爆料。在獨立爆料過程中,爆料人就從多方面收集來自不同地區(qū)網民提供的新的信息,充實了爆料的內容。但是網絡媒體監(jiān)督的獨立自由性并不表示爆料過程中不會受到上述原因的牽制。以本案為例,爆料人高勤榮在爆料期間曾多次受到騷擾和威脅,并且受到來自外部的施壓。因此從這一層面上講,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獨立自由性從本質上依然不是絕對的。第三,網絡輿論監(jiān)督,特別是以微博實名舉報為手段的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迅速性的優(yōu)勢。這一迅速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爆料人獲得材料到材料通過網絡媒體呈現在受眾面前的時間迅速性;二是從形成網絡輿論到傳統(tǒng)媒體介入,再到有關部門著手調查的過程具有迅速性。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迅速性優(yōu)勢是由網絡媒體自身的性質決定的。網絡自身就具有操作簡易、上傳快捷、跟帖及時的特點,而反腐案件一直以來都能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種背景下,網絡迅速性特點在實名反腐過程中被無限放大。最后,全面廣泛性是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又一優(yōu)勢。全面廣泛性指通過網絡媒體,誰都可以監(jiān)督權力機關和個人,誰都可能被監(jiān)督,任何內容都可能成為監(jiān)督的文本,監(jiān)督的內容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信息等。而官方監(jiān)督由于受部門職責“管理權限”人財物等條件制約,其監(jiān)督面要小得多[5]。上述理論架構和對實際案例分析表明,網絡輿論監(jiān)督作為一種監(jiān)督手段,是對“體制內”監(jiān)督手段在獨立性、廣泛性等方面的延展;作為一種輿論監(jiān)督手段,是對傳統(tǒng)媒體輿論監(jiān)督在體制上和監(jiān)督主體上的補充。
二、新媒體反腐的邊界和局限
由于在制度層面和法律層面缺少相應的制約機制,網絡輿論監(jiān)督在客觀上發(fā)揮作用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成為網絡輿論監(jiān)督、獨立監(jiān)督網站、獨立監(jiān)督人一直以來仍受人詬病的不可忽視的短板。
(一)隱私權與名譽權對實名舉報的制約網絡輿論監(jiān)督目前面臨的最大的困境就是網絡侵權問題。特別是對于素質參差不齊的實名舉報主體即普通公眾而言,實名舉報和網絡侵權的界限并不明晰。因此,目前網絡實名舉報極易觸及法律對某些組織和個人、某些權利的限定,包括網絡輿論監(jiān)督權和名譽權等的沖突、網絡監(jiān)督權和隱私權的沖突、網絡輿論監(jiān)督和保守國家秘密的沖突和網絡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權的沖突等[6]。在這里,僅討論網絡輿論監(jiān)督權與名譽權、隱私權的沖突。網絡輿論監(jiān)督侵權問題一般集中在隱私權、名譽權對網絡輿論監(jiān)督權利的制約上,若公眾在進行實名舉報過程中沒有把握好“度”,極易侵犯相關人員的個人權利。這里的“度”包括實名舉報的消息來源是否明確,消息內容是否真實,在傳播過程中是否經過人為渲染和夸張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網絡輿論本身具有的極端性特點,二是舉報主體對客體合法權益保護意識的缺乏。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關聯性。關于網絡輿論本身具有極端性的特點在網絡實名舉報中一般體現在實名舉報主體舉報完成后(此處回避了實名舉報主體實際惡意的原因),舉報內容在網絡上被無限轉載。由于網民對官員腐敗現象有好奇仇恨心理,因此極易引發(fā)網民大規(guī)模地使用網絡話語暴力、無節(jié)制地對被舉報者的“人肉搜索”等,造成超前于司法審判的道德審判,而這些行為已經侵犯了被舉報者的隱私權和名譽權,并超出了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范疇。舉報主體對客體合法權益缺乏保護意識則體現在舉報后迅速形成的“某官員人人喊打”的輿論氛圍。實名舉報的主體以及網民往往會忽略對還未進入司法檢察程序的官員的合法權益的維護。但是,若在此背景下刻板地遵循單向維護被舉報官員的相關個人權利,又會導致網民進一步、不加節(jié)制的調查,形成惡性循環(huán)。至此,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作為公眾人物的政府官員的名譽權問題。在我國,作為媒體的網絡在面對名譽權的侵權案例中,有針對“公眾人物”的抗辯事由。公眾人物在面對自身名譽權問題的司法案件中普遍遵循“輕微損害原則”(或稱“微罪不舉原則”)。“輕微損害原則”認為,公眾人物包括政府官員在內,其地位和社會評價來源于公眾,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的法律原則,一方面,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另一方面,對于公眾人物,公眾有知情權;媒體包括網絡媒體在內,為了維護公眾的合法權益和利益有權行使對公眾人物的監(jiān)督權,只要沒有實際惡意,公眾人物就應該尊重法律賦予的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對其進行“寬容和理解”。因此,依此原則思路,網絡實名舉報主體只要在舉報過程中本著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還原事實本真,并且不帶有主觀惡意,對所舉報的官員都不構成侵權。由此看來,在上述博弈中,網絡實名舉報與公民有關權利的界限依然較模糊:一方面,遵循“輕微損害原則”,公眾可以對政府官員進行舉報和披露,但是在舉報和披露過程中,失去了法律和制度的約束,又很容易以主觀的、非理性的語言、行為、情感等觸及到“輕微損害原則”所不包含的領域,如其住宅居所、通信秘密等,造成對被舉報人產生權利的損害。
(二)實名舉報難以從偶然性走到必然性當前,網絡實名舉報官員腐敗最終獲得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但其無一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爆料人獲取材料的偶然性、曝光過程的偶然性等。在沒有相關制度規(guī)約前提下,網絡實名舉報的偶然性問題也成為制約網絡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瓶頸。就“山西房媳案”而言,實名舉報人高勤榮獲取舉報材料的行為對普通公眾來說就極具偶然。而從另一角度切入,除了上述材料來源的偶然性因素,偶然性的網絡實名舉報給官員形成了一種“示范”效應,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建構一種完美的公眾形象,但這種公眾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擬的;同時由于舉報的偶然性,官員又存在一種僥幸心理,用公眾形象的“假面具”避免偶然性的網絡實名舉報。這兩方面原因導致能夠被公眾注意到的并作為舉報材料的真實信息被解構,然后利用公眾形象被重構,使相關材料越來越少,實名舉報就越具有偶然性,由此形成惡性循環(huán)。另外,我國目前仍未形成有效的、直接的與網絡輿論監(jiān)督相關的制度。在制度空白的背景下,網絡輿論監(jiān)督從根本上就具有自發(fā)性和偶然性,且監(jiān)督不規(guī)范,也未形成規(guī)模。上述因素使網絡輿論監(jiān)督難以從目前的偶然性和自發(fā)性過渡到必然性,并使網絡輿論監(jiān)督具有規(guī)范的制度制約,并形成規(guī)模。
(三)網絡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公正的博弈在我國,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監(jiān)督作為對權力部門及個人的監(jiān)督手段長期并存。只是無論是傳統(tǒng)媒體,還是現代微博,都可以參與某些公共事務,可以實現對政治權力領域的某種監(jiān)督,卻從不可能具有超越公權威信的力量[7]。媒體代表公眾執(zhí)行的監(jiān)督權利與司法公正之間的博弈也是長期以來存在的棘手問題,網絡輿論監(jiān)督作為一種新型的輿論監(jiān)督的手段,其自身的特點使其與司法公正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網絡媒體與司法制度均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社會的公正和公平,二者具有同等的價值觀。網絡媒體通過對社會不公正行為的揭露促使公眾對不公正現象的關注,從而促使社會公平正義得到伸張;而在司法層面,公檢法部門通過法律對不公正行為進行約束和懲治。但是,二者追求的所謂“公正”內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追求道德上的公正與公平,往往帶有主觀性;而后者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與公平,帶有嚴格而理性的客觀性。理論上,“輿論監(jiān)督只是一種精神的力量”,但在我國由于媒體具有的“輿論引導”的屬性,“它多少是一種黨政權力的延伸和補充”,因此媒體權力部門和個人的揭露與舉報,“盡管不應該是一種輿論審判,但是實際效果多少變成了一種輿論審判(實為傳媒審判)過大的監(jiān)督效果”[8]。另一方面,司法機關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目前也屬于網絡輿論監(jiān)督關注的重點。網絡輿論監(jiān)督對司法部門進行有效監(jiān)督是促進我國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但是公眾在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同時很容易就忽略了一個事實———司法部門需要有其公信力。雖然司法部門在運作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網絡輿論監(jiān)督過程中,監(jiān)督主體易忽略爆料可能帶來的嚴重社會影響;公眾不可避免地會“以偏概全”對司法部門言語攻擊、渲染和夸張,這成為司法部門公信力難以為繼的制約因素。因此,在缺少制度和法律規(guī)約下網絡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公正存在的博弈也成為制約網絡輿論監(jiān)督的重要因素。
三、結語
“一個社會對批評之聲有多大容忍限度,往往標志著這個社會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對人民如此,對新聞界依然。”[9](P19)當下,隨著媒介社會的發(fā)展和彌散,以傳統(tǒng)媒體為主導力量、網絡媒體為新生力量、實名舉報為自由力量的輿論監(jiān)督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輿論監(jiān)督作為一種制約公權力有力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是釋放社會情緒的有力渠道。但是網絡輿論監(jiān)督依然面臨制度上的欠缺,發(fā)展并不完善。如何在制度和法律空白的社會環(huán)境中發(fā)展網絡輿論監(jiān)督,特別是規(guī)范實名舉報,依然是未來學界探討和研究的重點。
作者:劉立剛張巖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 上一篇:自媒體時代下網絡輿論論文范文
- 下一篇:刑事審判的網絡輿論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