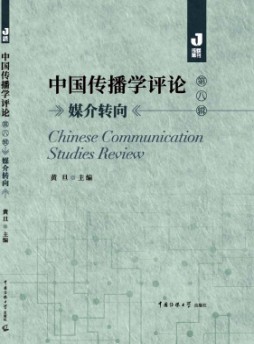傳播學(xué)視角的譯者主體性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傳播學(xué)視角的譯者主體性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譯者的主體作用和角色
(一)譯者的主體作用———跨文化使者譯者的主體作用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跨文化傳播作用;二是使異域國讀者接觸到不同文化的作品,體驗不同文化的藝術(shù)魅力,開拓視野。縱觀中西翻譯史,每一次重要作品的譯介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目的語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發(fā)展。唐代的佛經(jīng)翻譯使佛教文化在中國廣泛傳播,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人生哲學(xué);西方圣經(jīng)的翻譯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影響比佛經(jīng)翻譯的影響作用更大,可以說圣經(jīng)的內(nèi)容在文學(xué)藝術(shù)、道德倫理、處世哲學(xué)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皆有深刻影響。在中國歷次文化思潮中,翻譯都起著開啟民智、傳播異域科學(xué)和人文思想的作用。譯者具有會通中西的語言文化修養(yǎng),他們精選外國著述中的經(jīng)典,譯介到國內(nèi),開拓了國人的視野,使國人思想得到解放,逐漸意識到若要富國強民,非“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可。徐光啟、李之藻等清朝士大夫們先后組織翻譯了涉及幾何、算學(xué)、測量、農(nóng)業(yè)、機械、哲學(xué)等理工農(nóng)醫(yī)各學(xué)科幾千冊西方書籍,對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文化大師梁啟超倡導(dǎo)應(yīng)把翻譯作為教育民眾、宣教啟蒙、改變政治價值觀的工具;翻譯家嚴復(fù)先后翻譯了《天演論》《原富》《法意》《物種起源》等經(jīng)典著作,向國人介紹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和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制度等最新西方思想,引發(fā)了社會思考,對近代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產(chǎn)生了一定沖擊;胡適通過譯詩欲改變中國封建文化傳統(tǒng),推進社會的發(fā)展;一些重要作家、詩人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冰心,都親自從事翻譯工作,在政治改革與文化運動中產(chǎn)生了空前影響。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桂冠的莫言借鑒了拉美文學(xué)作品譯本中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手法,獲得了諾獎評委的青睞;莫言作品的英譯作者———美國漢學(xué)家葛浩文把目的語讀者的接受性作為首要考慮因素,創(chuàng)造性地再現(xiàn)了莫言作品的獨特藝術(shù)魅力,深得異域普通讀者和專業(yè)讀者的歡迎,這也是莫言獲獎的關(guān)鍵之一。
(二)譯者的主體角色———創(chuàng)造性操縱者傳統(tǒng)譯論強調(diào)譯文的忠實性和譯者在譯作中的隱身,譯者漸漸成為一個邊緣人,在翻譯活動中處于屈從地位。傳統(tǒng)譯論認為忠實于原文是翻譯的最高宗旨,旨在探討靜態(tài)文本的語言層面轉(zhuǎn)換問題,卻忽視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主觀能動性。而隨著譯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譯者的角色越來越受到重視,作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中心地位漸漸被削弱。譯者同作者一樣被看成了創(chuàng)作主體,開始轉(zhuǎn)變成為創(chuàng)作者的角色。譯者在內(nèi)外因素制約范圍之內(nèi)可以自由地操縱擺弄文本,甚至可以采用抵抗式翻譯策略,如:刪除簡化、意象替換、中西文化觀念會通。譯者作為譯入語第一讀者也由此獲得了空前的自由,不必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趨,他們賦予了原著一個新的“來世”[3]。謝天振在《譯介學(xué)》中提出譯者為“創(chuàng)造性叛逆”角色,肯定譯作中融入了譯者自己的視域空間、主觀感受性和目的性。書中提到,“說翻譯是叛逆,他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yù)料到的參照體系中(指目的語);說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的,是因為它賦予了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xué)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4]137。
二、葛浩文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
(一)文體選擇和翻譯策略自從20世紀(jì)90年代“文化轉(zhuǎn)向”之后,譯學(xué)界開始注意譯者在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譯者主觀上的各種因素包括譯者的興趣、知識面、審美標(biāo)準(zhǔn)、翻譯目的、翻譯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作者對翻譯作品和翻譯策略的選擇取舍。基于目的語讀者的審美取向和接受性以及盡可能使源語文化融入目的語文化的考量,葛浩文在翻譯莫言作品《生死疲勞》時主要采用了照顧目的語的歸化翻譯策略,具體使用了刪除、添加、改寫和添注的翻譯手段,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主體性作用的發(fā)揮。葛浩文認為,“一個做翻譯的,責(zé)任可大了,要對得起作者,對得起文本,對得起讀者”[5]。他深知要對得起讀者,而不是作者。作為一名翻譯實戰(zhàn)經(jīng)驗豐富的譯者,深知英美國家讀者的期待,在翻譯策略方面他嫻熟地使了用歸化翻譯策略,使翻譯文本盡可能地接近讀者的期待。把“硬漢子”譯成“ironman”,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可以聯(lián)想到好萊塢電影《鋼鐵俠》中的人物角色,減少了讀者的理解障礙。例2我掙開眼睛,看到自己渾身沾著黏液,躺在一頭母驢的腚后。天哪想不到讀過私塾、識字解文、堂堂的鄉(xiāng)紳西門鬧,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驢子。[6]8“私塾”“鄉(xiāng)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著特殊的含義,直譯不免冗余啰嗦,且讀者理解起來較困難,無法獲得良好的閱讀體驗。葛浩文以目的語讀者為服務(wù)對象,運用歸化翻譯手段盡量使原作作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實際上葛氏在翻譯莫言作品《生死疲勞》中,除了主要采用歸化翻譯策略,適當(dāng)?shù)臅r候為了保留異域文化特色,讓目的語讀者身處異域文化氛圍中,也靈活地采用了異化翻譯策略,且翻譯手段多樣,包括了增添、刪除、添注等手段。例3后來我們還與一支踩高燒的隊伍相遇,他們扮演著唐僧取經(jīng)的故事,扮孫猴子、豬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6]7“唐僧取經(jīng)”的故事出自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孫猴子”“豬八戒”就是書中的主要角色,這顯然與目的語讀者的文化差異很大,但是譯者并沒有給予過多的詳細添注,增加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負擔(dān)。這正契合了葛氏的翻譯觀點,認為任何任意的刪減或者過分的添加注釋的學(xué)術(shù)性翻譯,不利于被讀者接受,必要時應(yīng)該采用保留源語文化意象或者添加少量注釋的翻譯手段。在翻譯中同樣存在著內(nèi)因與外因交織的辯證統(tǒng)一關(guān)系。葛氏翻譯的成功內(nèi)因主要在于其深知讀者的閱讀趣味,自身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對中國文學(xué)和文學(xué)翻譯事業(yè)的熱愛,在準(zhǔn)確定位讀者的基礎(chǔ)上,靈活地采用了恰當(dāng)?shù)姆g策略;而在多種外因的作用下,如:編輯和出版商的動機,文化的不平衡性,西方文化強于中國文化,譯文中對原文進行了刪節(jié)、改動甚至編譯,這種“連譯帶改”的翻譯策略看似不忠實,實際是在對原作翻譯產(chǎn)生影響的內(nèi)外因素綜合作用下的更好的忠實。例6想不到她竟然有一條那樣好的嗓子,想不到她竟然能演唱那么多的樣板戲片段。她唱阿慶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鐵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他們兩人真是珠聯(lián)璧合,一對金童玉女。例6、例7中,原文蘊含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例8中葛氏考慮到民謠內(nèi)容與后文重復(fù),一則出于目的語讀者認知語境和閱讀反映考慮,刪除了多余的缺乏語境支撐的文化因素;二則考慮到出版社和編輯的客觀要求,刪除了重復(fù)內(nèi)容。但不管出于何種因素考量,葛氏都踐行了自己翻譯的忠實思想,實現(xiàn)了原文和譯文的語義對等,滿足了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葛氏也曾坦言,“不能讓美國讀者認為這是個不懂寫作的人寫的書”,可見他何其重視讀者的閱讀體驗。通過上述有限的具有代表性的譯文個案分析,可見譯者葛浩文的翻譯手段靈活,不過度拘泥于原文,這恰好是譯者主觀能動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體現(xiàn)。
(二)譯者主體性模式分析葛浩文有著扎實的漢語功底以及較高的翻譯素養(yǎng),始終在翻譯過程中以忠實于作者為準(zhǔn)繩,同時兼顧目的語讀者的接受性。他先后翻譯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30多位作家的40多部文學(xué)著作,大量的翻譯實踐使他的翻譯能力和譯作質(zhì)量不斷得到提高,漸漸得到了學(xué)術(shù)批評界和普通讀者受眾的認可。他的博士論文《蕭紅傳》奠定了其漢學(xué)家的身份,他與莫言之間的融洽的私人關(guān)系,也是他成功解讀莫言作品,成功向英語國家譯介其作品的關(guān)鍵原因。在翻譯方法的選擇上,葛浩文也是比較靈活的,采用過“增譯”“編譯”“適當(dāng)刪截”“異化策略”“簡化翻譯”等靈活的翻譯技巧,旨在綜合考量作品的題材、內(nèi)容、翻譯目的、翻譯作品的接受效果、政治意識形態(tài)、詩學(xué)傳統(tǒng)、贊助商要求、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譯作的產(chǎn)生是各種因素不斷制衡,各種利益群體妥協(xié)的結(jié)果,最終目的就是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和價值。葛氏成功地譯介莫言作品,并在譯入語國家得到了有效傳播,可見以國外漢學(xué)家為翻譯主體,同時以熟悉中國文化和作品內(nèi)涵的原作者為翻譯顧問的翻譯主體模式能夠更好地譯介中國文學(xué)和文化。
三、結(jié)語
葛浩文是被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公認為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首席翻譯家,其流暢的筆法,對原作的精確理解,以在譯入語讀者中的傳播效果為翻譯標(biāo)準(zhǔn),靈活調(diào)整自己的翻譯手段,體現(xiàn)出其作為譯者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但譯者作為一個外國人,沒有真正身臨其境地感受過中國博大精深之文化,譯文中對文化負載詞的誤解現(xiàn)象也不少見。對于葛氏翻譯活動中各種復(fù)雜因素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如:譯者責(zé)任、翻譯忠實性標(biāo)準(zhǔn)、譯者翻譯觀念,文化地位的差異和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等因素對譯者主體性發(fā)揮的影響。葛氏這種連譯帶改的翻譯方法,證明是中國文學(xué)對外譯介的最合理的譯介模式。葛氏個人的人生經(jīng)歷和學(xué)術(shù)背景,以及在翻譯上的成就,對培養(yǎng)高端漢英翻譯人才,在政府制定翻譯政策方面都值得借鑒。
作者:查道虎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