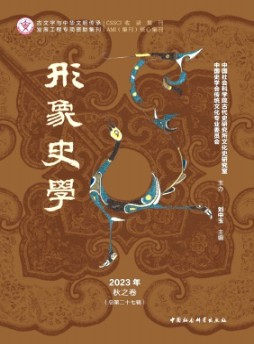史學起源的社會條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史學起源的社會條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史學集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文明的階段性特征是定位歷史現(xiàn)象的一種參照,而文明之間的聯(lián)系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為宏大的時空背景。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之間的交往、沖突、融合頻繁而深入。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幸記錄了一些文明間的互相評價,能夠為某些文化現(xiàn)象的起源和發(fā)展提供證據(jù)。希羅多德在《歷史》中就曾經(jīng)批駁了一些希臘人①把埃及人的靈魂不滅、轉(zhuǎn)世輪回的學說納入自己名下的做法。②歷史意識從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非常漫長,史學的產(chǎn)生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獨立于其他文化因素。希臘和中國是史學的兩大發(fā)源地,同時,埃及、兩河流域、赫梯、波斯、猶太等文明遺留了大量的歷史記錄,這些歷史記錄卻從來沒有達到史學的高度。這樣,即便沒有直接聯(lián)系的文明也可以為史學起源的問題提供或多或少的證據(jù)。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古代文明的各種歷史記錄形式從而得出史學產(chǎn)生的一般脈絡(luò)的思維并不嚴謹,不過,在一種長時段的文明比較語境當中可以更為精準地定位史學產(chǎn)生的初始環(huán)境,同時,也更容易對不同文明的“歷史”評價其優(yōu)劣得失。
埃及是古代世界神權(quán)政治的代表,隨著國家管理機構(gòu)的形成和強化,以軍事強權(quán)為支柱并輔之以宗教權(quán)威的王權(quán)符號體系逐漸產(chǎn)生了一套相對固定的“歷史”表述模式,其中包括王權(quán)的象征符號體系、可視的文字藝術(shù)以及編年形式的歷史記錄等。以埃及敘事成就最高的《圖特摩斯三世年代記》為例,其中共記載對亞洲的戰(zhàn)役17次,但是無一次涉及雙方交戰(zhàn)的具體細節(jié)。除了第一次戰(zhàn)役(米吉多戰(zhàn)役)的背景介紹較為詳盡之外,其他戰(zhàn)役都很簡略,而且對于法老所得戰(zhàn)利品的記述比例遠遠超過記載戰(zhàn)役本身。當然,我們不應(yīng)該輕易否定其中所體現(xiàn)出的歷史意識的進步,在第四次戰(zhàn)役中提到:殿下命令將此次殿下之父所賜之勝利鐫刻于神廟的石墻之上。③雖然這種歷史記錄的動機是出于王權(quán)和神意,但畢竟是一種對記錄本身的自覺的強調(diào)。另外在第三次戰(zhàn)役結(jié)尾的敘述中,殿下說道:“我發(fā)誓,如同拉神鐘愛我,我父阿蒙青睞我一樣,所有上述之事都是真實的……所有發(fā)生在朕身上的事情都是真的,我沒有虛構(gòu)”。④雖然這種強調(diào)真實的意圖并非史學意義上的去偽存真,其目的只是在于證明:和其他可能偽造的記錄相比,文中強調(diào),法老代表諸神真實地履行了開疆擴土、維持秩序的職責,但是此處也在王權(quán)與神權(quán)的權(quán)威之下突出了“真實”的重要意義。埃及社會的政治模式是王權(quán)與神權(quán)的嚴密契合,法老秉承神的血統(tǒng),擁有神的頭銜,具備神的屬性,凡戰(zhàn)爭、政務(wù)、建筑、外交、商業(yè)等等都冠以神圣的名義,如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科普托斯政令、拉美西斯二世與赫梯所簽訂的合約等,都充斥著濃厚的神意。古代埃及的歷史記述證明了一個處于宗教的嚴格束縛的社會是不會有史學產(chǎn)生的。古代的猶太、印度以及一些較為原始的民族的情況與此類似,他們可以有各種記錄,甚至不乏歷史記錄和歷史反思,只是由于宗教的禁錮而沒有產(chǎn)生史學。⑤兩河流域的早期城邦體制與古代埃及的神權(quán)政治存在區(qū)別。兩河流域的城邦也存在神化王權(quán)的情況,但是通常來講,國王是以人類的身份統(tǒng)治國家的。而且城邦保留了原始的共和制傳統(tǒng),王權(quán)受到長老會和民眾大會限制。蘇美爾早期城邦的一些歷史記述和埃及同時期的歷史記錄相較,顯得更為周詳。以能代表這一時期歷史意識最高點的烏魯卡基那改革的泥錐銘文為例,這篇文獻非常重視烏魯卡基那上臺執(zhí)政和前任國王盧伽爾安達政治劣跡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了對事件原因的重視。
①整體來講,兩河流域一直處于戰(zhàn)爭頻繁、歷史劇變的時代,所以兩河流域的政權(quán)都注重城邦的霸權(quán)和帝王的偉業(yè)。然而,也正是由于戰(zhàn)爭頻仍,中期亞述之前的諸多歷史記錄所存甚少。亞述的王室年代記當中,不乏敘事精細者,但是其中所述諸王戰(zhàn)事,全以炫耀武力和威望為特征。比如辛那赫里布八次戰(zhàn)役銘文,第一次戰(zhàn)役的開篇寫道:(我是)辛那赫里布,偉大的王、威武之王、世界之王,睿智的牧羊人……。②在第八次戰(zhàn)役的敘述中,國王的英武和威力達到極致:我砍斷他們的脖子如同(砍)獻祭的羔羊。我割斷他們的脖子如同割斷一條線,我讓他們的血如同雨季的大洪水流淌在廣闊的地面上……,③亞述的年代記讀之唯感血腥之氣,還不如早期蘇美爾城邦的個別銘文具有一定的歷史判斷力。整體來講,兩河流域的歷史記錄基本是一種政治工具。我們通常不知道歷史記述的記載者為何人,也看不到他們對事實真假的區(qū)分,偶有對前朝興衰的反思,卻又走向神意。比如阿卡德王國的納拉姆辛便是失敗的國王的代表,但是按文獻所載他葬送了邦國是因為違背了神意。④兩河流域文明的宗教信仰并沒有達到像埃及宗教那樣禁錮民眾心智的程度,但是政治權(quán)力對歷史記述的控制,致使歷史記述行為完全淪為政治動機的附庸。赫梯和波斯的歷史記錄與兩河流域的情況比較接近。波斯具有良好的檔案保存以及歷史編寫制度,但是編年記錄被王權(quán)所控制的情況從《以斯帖記》第六章第一節(jié)當中所記載的故事可知一二:國王亞哈隨魯睡不著覺之時,就吩咐人去取編年記事來讀。即便是比埃及和兩河流域更為成熟的社會,如果政治體制對于個體自由的禁錮過度,一樣不會產(chǎn)生自由的學術(shù),包括史學,古希臘的斯巴達城邦便是一例,這個城邦從來沒有產(chǎn)生一位古希臘的出名學者。這樣,中國史學和希臘史學起源的優(yōu)越條件便顯而易見了,那就是政治環(huán)境和宗教信仰對歷史記述來講沒有形成絕對禁錮,社會思想文化的基礎(chǔ)相對理性。不過,中國和希臘的史學初始化環(huán)境差別很大,包括宗教信仰、政治體制、知識學科體系等。近年來一直致力于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研究的臺灣學者杜維運先生,在“中西古代史學的比較”一文中特別強調(diào)了中西史學起源的比較問題,其中認為古希臘重哲思輕歷史,其史學地位低微,所以如果和中國史學起源相比,西方根本不會有令人興奮的發(fā)現(xiàn)。⑤因為此處杜先生已經(jīng)提出了史學的學科地位問題,尤其是史學和哲學的比較,所以本文也就此問題略作探討。首先,應(yīng)該承認從整體來講,古希臘的哲學和歷史處于一種矛盾狀態(tài),“特殊性”和“普遍性”意義上的分歧,是歷史和哲學一直面臨的基本沖突的根源。其次,古典時代哲學和歷史學體現(xiàn)在各類著作中的交織是有限的,而且這種有限的交織牽扯到很多層面的復(fù)雜問題。
不過縱觀西方史學的發(fā)展,最初也是最為重要的對史學的推動力就是米利都學派奠定的哲學思維,這種思維開始對外部世界進行一種本原推究,而這種思維用之于對社會和人生問題認識的時候,便產(chǎn)生了對事件原因的追溯。很明顯,希羅多德的“歷史動力”概念就是沿襲了由愛奧尼亞哲學家發(fā)展出來的“宇宙動力”的概念。①哲學意味著理性和科學地對待自然和社會的各種現(xiàn)象,這對于史學來說最大的益處就是促使植根于趨于普遍理性和科學的社會土壤當中的自覺歷史意識的產(chǎn)生。希臘人在認知世界方面確實是幸運的,他們有機會向埃及人和巴比倫人學習先進知識。不過這種幸運更多地來源于希臘人自己的求知與創(chuàng)新,從現(xiàn)在的研究來看,埃及人確實有眾多方面的實用知識,而他們的知識并沒有達到一種抽象的層面,比如數(shù)學一直局限于土地測量和實物分配這些和政府管理相配合的實用層面。巴比倫人也有日食和月食的記錄,但是這種記錄多用于占卜,而他們關(guān)于行星的運動、二分二至之說常常和神話與傳說聯(lián)系起來,他們的歷法也很難說是科學嚴密。真正對這些知識進行總結(jié)升華并創(chuàng)立學科體系的,是希臘人自己。雖然古希臘人欠下近東民族很多文化和精神的債務(wù),但是在目的論和方法論上,古希臘人找到了與近東民族不同的答案。與古希臘哲學的求知愛智相適應(yīng),希臘歷史學的重要目的便是真實地記錄歷史,而不受任何權(quán)利的支配,希臘的史學也講求經(jīng)世致用,但是為官方和統(tǒng)治提供借鑒的意圖和中國史學比較起來則非常薄弱。②古希臘哲學是幾乎所有知識學科的母體,從其中孕育出天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文學、生物學等,而歷史學和醫(yī)學被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但是從古典史家的作品中很容易判斷,歷史是和政治、軍事、地理、修辭等等知識聯(lián)系起來的,所以歷史很難被完全排除到知識體系之外。古希臘很多歷史學家都受過哲學的熏陶,色諾芬本身就是哲學家,不過他們并沒有受到來自所謂哲學層面的“貶低”的影響。相反,在闡述政體問題的時候,波里比阿認為哲學對普通人來說太晦澀,他寧愿以歷史學家的身份來具體簡潔地闡述問題。③而且,希臘的歷史記載難以印證哲學思維下的循環(huán)史觀之類的“歷史觀點”。從黑格爾到柯林伍德的關(guān)于古希臘“非歷史”的哲學角度的判定,需要謹慎考察。誠如以研究古典史學聞名的意大利學者莫米格里亞諾所評論:非要說柏拉圖比希羅多德更能代表希臘文明只是一種主觀臆斷。④每一種文明在給予歷史記錄的自由空間和知識土壤方面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區(qū)別。古希臘和中國雖然都產(chǎn)生了史學,但是其社會背景和知識底蘊區(qū)別很大,很多情況需要進一步從文獻中鉤沉。不過,如果在沒有對文獻進行全面考察的情況下,非要說古代中國史學優(yōu)于希臘史學也是一種猜想。同時,通過這種對比,我們應(yīng)該明確史學處在怎樣的環(huán)境下才能更為健康地發(fā)展,這種比較對于當今的史學的健康發(fā)展也具有基本的參考意義。
作者:史海波 單位:吉林大學 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