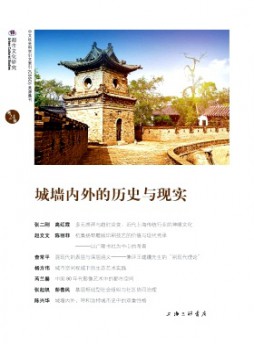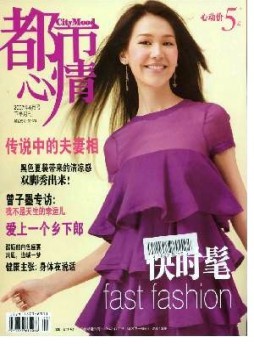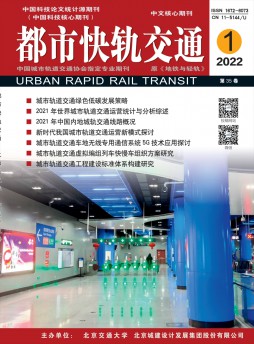都市社會學(xué)的現(xiàn)代化理念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都市社會學(xué)的現(xiàn)代化理念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邏輯起點:“第四種國家”
第一類國家工業(yè)發(fā)達(dá),農(nóng)產(chǎn)品大都不能維持本國人生活,以工業(yè)產(chǎn)品銷售利潤從他國購進(jìn)糧食。第二類國家從事農(nóng)業(yè)者雖少,但農(nóng)產(chǎn)品不僅可以自給,且有盈余可供出售,其生活方式令人羨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都采用機器,農(nóng)場面積很大,生產(chǎn)效率極高。譬如美國,從事農(nóng)業(yè)者1000萬人左右,但1926年所產(chǎn)小麥占世界小麥總量的22.8%,玉米占60.9%,棉花占62.2%。吳景超認(rèn)為,沒有哪個國家的生活程度可與美國相頡頏媲美,一是因為美國人—地比例適中,二是因其職業(yè)中構(gòu)成“甚為得法”,故而能夠做到農(nóng)業(yè)既足自給,工業(yè)也很發(fā)達(dá)。各業(yè)民眾彼此交易貨品與服務(wù),生活程度因而得到普遍提高。在他看來,俄國存在的問題不在于人—地比例之不當(dāng),而在職業(yè)構(gòu)成不合理,也就是農(nóng)民太多,尤其是在“五年計劃”以前,俄國農(nóng)業(yè)與美國的最大差別在于機械化水平太低。貧窮系第四類國家之共同特點,“他們主要的謀生方法,既然是農(nóng)業(yè),但以國內(nèi)人口繁密的緣故,所以每家分得的農(nóng)場平均便不很大。他們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勞力,在農(nóng)場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溫飽兩字。一遇兇年及災(zāi)亂,便有凍餒之憂。他們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卻衣食住的消費之外,便沒有別種享用可言。他們終年碌碌,所為何來,無非為自己要吃飯,一家人要吃飯而已。吃飯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國家,雖然也占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他們除去吃飯之外,還有別種享樂。”在吳景超看來,第二類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yè)構(gòu)成堪稱典范,第一類國家人口密度和第三類國家職業(yè)構(gòu)成需要努力改進(jìn),第四類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yè)構(gòu)成均需改良。中國既然屬于第四類國家,所以中國問題最難應(yīng)對,對于改良工作亦當(dāng)特別努力。吳景超曾將其單篇論文結(jié)集出版,以首篇論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作為書名。他在該書“自序”中聲稱,“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是“全書的要義”,其他內(nèi)容“不過發(fā)揮這些要義”。因此,中國人口密度與職業(yè)構(gòu)成,顯然系其現(xiàn)代化思想的邏輯起點和歷史基點。
二、路徑選擇: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和都市化
(一)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制度、技術(shù)、人口
人口密度高,農(nóng)民比例亦較高,中國現(xiàn)代化自當(dāng)關(guān)注農(nóng)業(yè)。據(jù)吳景超分析,中國農(nóng)民之所以生計困難,要因不外六端,即:農(nóng)場太小、生產(chǎn)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業(yè)衰落以及遭受奸商剝削和子女剝削。針對農(nóng)村普遍破產(chǎn)的歷史境況,他認(rèn)為實現(xiàn)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需從制度、技術(shù)和人口三大維度切入。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必須進(jìn)行土地制度改革,將大量佃農(nóng)轉(zhuǎn)變?yōu)樽愿r(nóng),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由于中國佃農(nóng)過于貧困,無力依靠自身力量變?yōu)樽愿r(nóng)身份,政府必須設(shè)法相助,具體而言,效法丹麥,政府幫助農(nóng)民購地,使佃農(nóng)轉(zhuǎn)為自耕農(nóng);效法愛爾蘭進(jìn)行減租,促使地主出售土地;借鑒東歐各國辦法,由政府公平規(guī)定土地價格,避免地主囤地居奇。在他看來,此一方案既借鑒了歐洲國家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成功經(jīng)驗,又考慮到了本國國情。其次是建構(gòu)公平的分配制度。吳景超認(rèn)為,所謂公平分配,亦即承認(rèn)各人收入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能太過懸殊。公平分配的實現(xiàn)有賴于政府采用稅收手段,如所得稅、遺產(chǎn)稅等。他從邊際效用視角出發(fā),認(rèn)為運用稅則手段實行財富轉(zhuǎn)移,雖可導(dǎo)致富人奢侈生活受損,但政府利用稅收興辦教育衛(wèi)生娛樂等社會事業(yè),民眾生活卻可普遍性提高,故而此種辦法,對于少數(shù)人有損,而對于大多數(shù)人卻有利。就技術(shù)層面而言,必須大力推行農(nóng)業(yè)機械化。
吳景超認(rèn)為,美國農(nóng)民耕種所得,除交稅和滿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以資教育、衛(wèi)生、娛樂、旅行和交際之用,而中國農(nóng)民耕種所得卻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美中兩國農(nóng)民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巨大差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前者普遍采用機器耕作,而后者反之。因此他斷言:我國農(nóng)民如想步美國農(nóng)民后塵,享受他們那種愉快生活,非擴大農(nóng)場利用機器進(jìn)行生產(chǎn)不可。換言之,要使鄉(xiāng)村復(fù)興并最終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必須改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使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漸轉(zhuǎn)向西式機械化生產(chǎn)。變革生產(chǎn)制度與提升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可以擴充經(jīng)濟增量,改良分配制度,則能夠?qū)崿F(xiàn)經(jīng)濟存量的優(yōu)化配置,但尚需控制人口數(shù)量,避免經(jīng)濟增量為新增人口所吞噬。作為一名職業(yè)社會學(xué)家,吳景超對中國人口問題有著清醒認(rèn)識,一直將人口眾多視為農(nóng)村破產(chǎn)的重要原因,極力鼓吹實行節(jié)育政策。他強調(diào)指出,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業(yè)已成為社會各界之共同訴求,欲圖實現(xiàn)此一目標(biāo),“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節(jié)制人口”,“如不立行節(jié)制政策,將來一定要產(chǎn)生較現(xiàn)在還要嚴(yán)重的局面”,因此,節(jié)育政策乃系“各種救國事業(yè)之中一種最重要的事業(yè),是建造新中國的各種辦法中一個最有效的辦法。”
(二)工業(yè)化:“歧路”與“活路”
20世紀(jì)的世界,工業(yè)化潮流彌漫到全球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chǎn)階級的生產(chǎn)方式。”吳景超在美留學(xué)長達(dá)6年,親眼目睹美國工業(yè)化的巨大成就和迷人魅力,深刻體會到工業(yè)美國與農(nóng)業(yè)中國之間的深刻反差,認(rèn)為“對于人民福利上的貢獻(xiàn),無論從哪一方面著眼,都不如機械的方法”,美國與中國恰好站在兩個極端,前者人均可以驅(qū)使13.38馬力的生產(chǎn)力量,而后者則僅0.45馬力,他認(rèn)為這是美國富而中國窮的主要原因。基于此種理解,他強調(diào),中國要想圖存,舍工業(yè)化之外別無他途,因為“惟有一個工業(yè)化的國家才能在現(xiàn)代的世界上生存,惟有一個工業(yè)化的國家才能使人民的生活優(yōu)美繁榮。”
20世紀(jì)20年代以降的中國,以農(nóng)立國論此起彼伏,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風(fēng)生水起,但以工立國論與之頡頏相抗,亦不落下風(fēng)。吳景超是以工立國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疾聲呼吁:“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們只有努力走上工業(yè)化的路,才可以圖存,我們只有一條路是活路,雖然這條活路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所謂活路,即工業(yè)化道路,而所謂歧路,亦即種種反對工業(yè)化的論調(diào)。吳景超將工業(yè)化之反對者分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廢食派和畏難退縮派,逐一予以駁斥。夸大派認(rèn)為中國文化每一方面均比西方文化高明,“都是好的,都是應(yīng)當(dāng)保守的”,故而“不必學(xué)別人,還是以農(nóng)立國為佳”,同時常用籠統(tǒng)名詞來指稱農(nóng)業(yè)國家的優(yōu)點和工業(yè)國家的缺點,“以自圓其說,以滿足其夸大的欲望”。吳景超運用最新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指出民眾收入與工業(yè)化水平恰恰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農(nóng)業(yè)國家缺乏財富積累,人民生活必然窮苦,因無法接受教育而愚笨,因無力講究衛(wèi)生而短命。中國人之窮、愚及短命,“是一件可憐的事,沒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禁欲派強調(diào)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雖然不能滿足人類衣食住行等基本欲求,但解決方法不在于增加生產(chǎn),而是節(jié)制欲望。
吳景超斥責(zé)此種主張是懶漢態(tài)度,認(rèn)為人類追求物質(zhì)享受之量多質(zhì)好與花樣新鮮,恰恰是社會進(jìn)步的主要動力,采集經(jīng)濟時代信奉禁欲主義,決不會產(chǎn)生漁獵或畜牧經(jīng)濟,漁獵或畜牧經(jīng)濟時代信奉禁欲主義,也決不會產(chǎn)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因噎廢食派在一定程度上認(rèn)識到工業(yè)化帶來的利益,對于英美工業(yè)文明持鑒賞態(tài)度,但是歐美經(jīng)濟大蕭條導(dǎo)致的大規(guī)模失業(yè)、勞資間沖突尖銳化等現(xiàn)象,促使他們對工業(yè)化本身產(chǎn)生懷疑和恐懼,認(rèn)為中國“還是不走上工業(yè)化的路為妙”。在吳景超看來,與工業(yè)社會中的失業(yè)等問題相比,農(nóng)業(yè)國家的災(zāi)荒等社會問題有過之無不及,性質(zhì)更加嚴(yán)重,危害更加巨大,“每隔若干年必來光顧一次。光顧的結(jié)果,是農(nóng)民暴動,是內(nèi)亂發(fā)生,是死于饑饉者若干萬人或數(shù)十萬人,是人相食。”況且,工業(yè)化與失業(yè)并不具有因果關(guān)系,工業(yè)化也不必然導(dǎo)致勞資沖突。
畏難退縮派高呼中國工業(yè)化之路走不通,認(rèn)為“工業(yè)已經(jīng)給帝國主義包辦,市場已為帝國主義壟斷,關(guān)稅已受帝國主義支配,在這種種的壓迫之下,本國的工業(yè),實無發(fā)展的余地。假如要走這一條路,前途真是艱險萬狀,不如回轉(zhuǎn)頭來,整理我們的農(nóng)村,過我們固有的農(nóng)民生活。”吳景超則強調(diào),新工業(yè)國遭受老工業(yè)國之壓迫,乃系世界例,美、德兩國并不因有英國這一勁敵,便放棄工業(yè)化企圖,日本也不因市場上已有英美各國貨物而退縮,蘇俄也并不因為四周已有許多工業(yè)國便取消五年計劃。吳景超將上述諸種反工業(yè)化主張視為“經(jīng)濟上的復(fù)古論”,明確宣稱“對于一切的復(fù)古運動,都不能表示同情,對于這種經(jīng)濟上的復(fù)古論,尤其反對。”
(三)都市化:“更深的都市化”與“都市意識”
都市化乃是現(xiàn)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重大差異之一。吳景超認(rèn)為,都市化至少包含兩層意義,從人口空間分布來看,鄉(xiāng)村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而都市人口卻逐漸增加;就人口職業(yè)構(gòu)成而言,從事農(nóng)業(yè)者逐漸減少,而在其他實業(yè)中謀生者則逐漸增加。19世紀(jì)以降,世界都市化進(jìn)程迅速推進(jìn),他認(rèn)為其中原因大致有三,即農(nóng)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和商業(yè)革命。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機器化,剩余勞動力逼迫轉(zhuǎn)移到都市謀生,導(dǎo)致都市人口膨脹。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科學(xué)化,可以不擴大耕地面積而增加產(chǎn)量,從而為都市提供食糧。都市化也是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物。現(xiàn)代新式工業(yè)之所以集中于都市,主要在于都市交通方便、金融機構(gòu)完備,同時因為大量工人聚集,都市也是消費品的大好市場。近代商業(yè)的發(fā)展,使商人大大增加,而商人和商業(yè)又多集中于都市。根據(jù)英美兩國都市化的歷史進(jìn)程,吳景超得出結(jié)論:唯有鄉(xiāng)村與都市的人口比例適當(dāng),國家方能富強,民眾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反觀中國。吳景超援引1933年的統(tǒng)計,中國雖有上海、天津和北京3個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120個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但都市人口僅占總?cè)丝诘?.4%。英國超過10萬人口的都市為42個,但都市人口卻占總?cè)丝诘?4.2%。美國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為93個,都市人口亦占總?cè)丝诘?9.6%。不僅如此。中國都市之組織很不完備,不能充分行使都市應(yīng)盡職務(wù),即使是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在國內(nèi)雖可稱雄,但與倫敦、紐約相比則明顯幼稚,離“成年”尚遠(yuǎn)。因此,他強調(diào),將中國與發(fā)達(dá)國家相比,中國鄉(xiāng)村人口顯然太多,而都市人口則太少,“中國的窮,中國人的貧與弱,這種不合適的人口分配,要負(fù)一大部分的責(zé)任。”因此,中國必須“更深的都市化”,而“欲達(dá)到此點,并無別條新奇的路,只有步先進(jìn)國的后塵。”
“農(nóng)村破產(chǎn)”乃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諸多有識之士秉持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思想理念,認(rèn)為都市對農(nóng)村不但毫無貢獻(xiàn),反而加劇農(nóng)村破產(chǎn)。吳景超則極力呼吁“發(fā)展都市以救濟農(nóng)村”,強調(diào)欲真正救濟與復(fù)興農(nóng)村,唯有發(fā)展都市這一途徑。在他看來,通過“興辦都市工業(yè)”、“發(fā)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guān)”等辦法,則可實現(xiàn)救濟農(nóng)村之目標(biāo)。興辦都市工業(yè)可以吸收都市附近剩余勞動力,解決鄉(xiāng)村人口生計問題,用他的話來說,“中國農(nóng)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眾,是農(nóng)村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農(nóng)業(yè)中已無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國的都市,從發(fā)展工業(yè)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農(nóng)民,遷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因爭食者減少,生活也可略為舒適一點了。”發(fā)展交通則能溝通城鄉(xiāng),便利農(nóng)產(chǎn)品流通,“都市交通發(fā)達(dá),就是市場”,而擴充金融機關(guān)、廣設(shè)支行或分處于內(nèi)地農(nóng)村,既能吸收內(nèi)地資金以便發(fā)展都市生產(chǎn)事業(yè),又可放款于內(nèi)地,減輕農(nóng)民利息負(fù)擔(dān),資助農(nóng)民購買機器設(shè)備,從而推動農(nóng)村工業(yè)化。吳景超強調(diào),建立在工業(yè)化基礎(chǔ)上的都市化,方系“解決中國經(jīng)濟破產(chǎn)問題的一劑起死回生的妙藥”。要想提高中國的都市化程度,都市精英必須樹立“都市意識”。吳景超認(rèn)為,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各界精英亦集中于都市,但他們似乎缺乏“都市意識”。在其都市社會學(xué)理論中,存在都市與都市附庸兩大區(qū)域,兩者之間共生共榮。都市商界精英不能正確劃分該市“勢力范圍”,亦無法全力經(jīng)營它,都市與附庸便無法共存共榮。在他看來,假如都市精英均有此種都市意識,那么即使經(jīng)濟蕭條和農(nóng)村破產(chǎn),將來終有繁榮之日。
三、根本依歸:富民與強國
按照美國比較現(xiàn)代化研究者布萊爾之洞見,現(xiàn)代化乃是人類社會最具革命性的歷史變遷。人類現(xiàn)代化的追求,根本依歸在于增進(jìn)每一個體之福祉。吳景超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化根本依歸的認(rèn)識,以盧溝橋事變?yōu)榻琰c,前后稍有不同。此前,他著重強調(diào)富民,而后則聲稱“先強而后言富”。吳景超認(rèn)為,中國民眾追求衣食住行四大欲望的滿足,“乃是做人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即便是追求教育、娛樂、交際、衛(wèi)生和旅行等方面的享受,也不能被視為逾矩過分,故而他大聲呼吁改良生產(chǎn)方法,極力提倡工業(yè)化。同時,忽視大眾福利,也是他批駁禁欲派的重要理由。他說,禁欲派反對發(fā)展工商,“未免太忽視了大眾的福利。中國的大眾,并不是縱欲的。他們終日孜孜,并非在那兒想過奢侈的生活,想得逾分的享受,乃是在那兒設(shè)法,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還時刻的感到力不能濟,時刻的受凍餓的苦痛。”改善民生,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實際上成為吳景超現(xiàn)代化思想的基本指向和根本依歸。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一文中,他指出,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各種派別的共識,“我們整天整月的忙,目的雖然不只一端,但有一點是大多數(shù)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們現(xiàn)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豐富一點。”
農(nóng)民無疑是吳景超眼中的社會大眾之主體。在《農(nóng)民生計與農(nóng)村運動》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國農(nóng)民生計困難和農(nóng)村破產(chǎn)的主要原因,指出“救窮”實為各種農(nóng)村運動的主要目標(biāo),但在他看來,農(nóng)村運動對于農(nóng)民生計問題雖然不無改善,但肯定不能根本解決,因為中國農(nóng)民數(shù)量龐大,受惠于農(nóng)村運動者為數(shù)甚少,而且對于兵匪、地權(quán)、交通和苛捐雜稅等問題,私人團體根本無力解決。因此他強調(diào),農(nóng)民生計問題乃是經(jīng)濟建設(shè)這一大問題的一部分,不能單獨解決,只能與工業(yè)、礦業(yè)、運輸業(yè)、交通業(yè)、商業(yè)等問題一同解決。在《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程度與農(nóng)場》一文中,吳景超運用恩格爾系數(shù),指出中美農(nóng)民生活程度差距巨大。單個家庭的零用支出一般包括食品、衣服、房租、燃料、雜項等費用,收入越高,前4項花費所占比例愈低,雜項花費則愈高。提高中國農(nóng)民的雜項費用,亦即改善其生活水平,成為吳景超農(nóng)業(yè)改良主張的基本初衷。在《多福多壽多男子》一文中,吳景超對國人的傳統(tǒng)人生觀進(jìn)行詮釋,認(rèn)為民眾多福多壽的追求并未實現(xiàn),唯有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和國防鞏固,才有幸福生活的基礎(chǔ),而“有了幸福生活的基礎(chǔ),還要在上面蓋起幸福生活的建筑,然后幸福的生活,才可實現(xiàn)。”他將“幸福生活的建筑”明確視為“物質(zhì)文化”,認(rèn)為“衣食住行等等根本的欲望,如不能滿足,人生便無幸福可言”,“如欲中國的大眾,都能滿足以上的根本欲望,只有采用先進(jìn)國的機械生產(chǎn)方法,來開發(fā)中國各地的富源,才能辦到。等到物質(zhì)的文化,已經(jīng)開花,結(jié)下的果子,自然是精神文化。在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都發(fā)達(dá)的國內(nèi)過日子的人,自然是多福的。”近代以降,各種救國主張此起彼伏,其核心無不指向中國現(xiàn)代化這一根本問題,或者說,均關(guān)涉如何實現(xiàn)中國之富強問題。1938年,吳景超明確指出中國工業(yè)化具有雙重目標(biāo),“中國如何可以由貧弱到富強,乃是過去百余年來,多少志士仁人日夜籌思的一個大問題。”他強調(diào),工業(yè)化是實現(xiàn)中國由貧弱到富強的必由之路。由貧弱而富強,實則意味著工業(yè)化必須實現(xiàn)兩重目標(biāo),即富與強。
富,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強,便是增強國防力量。他宣稱,只有努力實現(xiàn)工業(yè)化,“人民的生活程度才可提高,國防的力量才可增進(jìn)。中國的人民,如不愿老過窮苦的生活,老受敵人的壓迫,非急起直追,設(shè)法使中國于最短期內(nèi)工業(yè)化不可。”對于中國工業(yè)化的兩大目標(biāo),不少人主張“兼籌并顧、不分輕重”。吳景超對此并不贊同。他認(rèn)為,如果中國工業(yè)化所需的的財力與人力都很充裕,那么民生工業(yè)與國防工業(yè)當(dāng)然可以同時進(jìn)行,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工業(yè)化資源非常缺乏,民生工業(yè)“多花一分財力,一分人力,國防工業(yè)便要吃一分的虧”,故而對于富與強這兩大目標(biāo),實有必要權(quán)衡輕重和區(qū)分先后緩急。在他看來,在外患嚴(yán)重的抗戰(zhàn)時期,如何使中國由弱而強,遠(yuǎn)比如何使中國由貧而富重要。身處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國防需要高于一切,必須優(yōu)先發(fā)展國防工業(yè),應(yīng)當(dāng)多設(shè)煉鋼廠、煉銅廠、機器廠、飛機廠、槍炮廠、彈藥廠、汽車廠、汽油廠等等可以供給國防軍需的工廠,以便增加國防力量。而提高生活程度之民生目標(biāo),無疑必須置于次要地位。吳景超強調(diào),“如把這個根本態(tài)度決定之后,就得準(zhǔn)備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內(nèi)吃苦。都要立志在國防還沒有鞏固之前,不預(yù)備提高生活程度。提高生活程度是一個很好的目標(biāo),但在目前還有更急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提高生活程度一事,退遲一二十年,再去設(shè)法實現(xiàn)。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內(nèi),人民的生活程度,自然要設(shè)法維持,使其不要下降,最好還要使現(xiàn)在呻吟于貧窮線以下的人,能略為提高生活的水準(zhǔn)。但除此以外,不要另存奢望。只要工業(yè)化真的開始了,美滿的生活,是終可以實現(xiàn)的,但實現(xiàn)的時期,無妨使他展遲,使他稍緩,以便全國人民的精力,都可集中在國防工業(yè)上面。”眾所周知,在抗日戰(zhàn)爭戰(zhàn)略防御階段,中國喪師失地,大半個中國淪陷。吳景超甚至認(rèn)為,武器不如人,乃是抗戰(zhàn)不能勝利的主要原因。與敵人比較,中國并不缺乏勇敢、紀(jì)律,也不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而是缺乏飛機、大炮、坦克及一切機械化設(shè)備。中國之所以缺乏機械化武器,原因在于沒有實現(xiàn)工業(yè)化,而日本工業(yè)化的啟動比我國早數(shù)十年,制造武器的能力比我國強大得多。
因此,他強調(diào),抗戰(zhàn)初期敵強我弱的態(tài)勢,顯然與中國此前的工業(yè)化目標(biāo)密切相關(guān)。抗戰(zhàn)之前,我國沿海大都市的工業(yè)大部分是民生工業(yè),而非國防工業(yè),也就是此前工業(yè)化“傾向于富的目標(biāo),而忽略了強的目標(biāo)”,但是“辛辛苦苦創(chuàng)造出來的事業(yè),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大部分化為灰塵。”吳景超從中得到的教訓(xùn)是:“一國的財富,如不是建筑在強的基礎(chǔ)上,那種財富,是沒有保障的。”因此他認(rèn)為,“以前談富強,總是把富字?jǐn)[在強字前面,以后我們應(yīng)當(dāng)矯正這種錯誤,應(yīng)當(dāng)先強而后言富。我們應(yīng)當(dāng)把國防工業(yè),看得比民生工業(yè)更為重要。我們的財力人力,當(dāng)應(yīng)大部分放在國防工業(yè)上面。”抗戰(zhàn)的需要,無疑是吳景超思想發(fā)生重大轉(zhuǎn)向的重要緣由,而蘇、德兩國“后發(fā)型”工業(yè)化的成功經(jīng)驗,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子。他自己承認(rèn),自己此前的學(xué)術(shù)著眼點主要在于工業(yè)化與民眾生活程度之關(guān)系,但1937年“在歐洲游歷了半年,走了許多國家,其中德國與蘇聯(lián),給我的印象最深。”據(jù)他觀察,蘇德兩國工業(yè)化目標(biāo)并不是提高民眾的生活程度,而是為了增進(jìn)國防力量,“因而回顧中國目前的處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雖然是重要的,但增進(jìn)國防的力量,則尤為迫切。盧溝橋事變的發(fā)生,使我覺得這種態(tài)度,有提倡的必要。中國現(xiàn)在需要工業(yè)化,還是不易的真理,但我們目前所急待建設(shè)的工業(yè),應(yīng)為國防工業(yè)及與國防工業(yè)有直接關(guān)系之重工業(yè)。民生工業(yè)的建設(shè),應(yīng)居于次要的地位。”
四、結(jié)語
從一定程度上看,一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也就是一部中國現(xiàn)代化史。現(xiàn)代化追求、探索與實踐,成為貫穿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基本紅線之一。吳景超對當(dāng)時中國國情的判斷,也就是對中國現(xiàn)代化基點的認(rèn)知,無疑是客觀和精準(zhǔn)的。現(xiàn)代化追求的本旨在于提高民眾福祉,現(xiàn)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此種認(rèn)識對于正確區(qū)分發(fā)展和增長,避免陷入經(jīng)濟主義陷阱,至今仍有重要的價值。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路徑,近人大多偏執(zhí)一端,或主張以農(nóng)立國,或強調(diào)以工立國,而吳景超雖有所偏重,但顯然主張一種整體化的路徑,反對偏廢一端,誠如他所言:“對于發(fā)展中國的實業(yè),改良生產(chǎn)的技術(shù),是主張各方面同時并進(jìn)的。農(nóng)業(yè)固然重要,工業(yè)也不可忽視。鄉(xiāng)村固然要復(fù)興,都市也應(yīng)當(dāng)發(fā)展……喜歡注重農(nóng)業(yè)而忽視工業(yè),贊美鄉(xiāng)村而咒詛都市……是一種危險的傾向……都市與工業(yè)的畸形發(fā)展,固然是不足取……應(yīng)當(dāng)歡迎有志人士來創(chuàng)造新工業(yè),創(chuàng)造新都市,為鄉(xiāng)下的過剩農(nóng)民,另辟一條生路……不但農(nóng)業(yè)的技術(shù)要改良,別種實業(yè)的技術(shù)也要改良,不但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要趕上歐美;就是工業(yè)、礦業(yè)、商業(yè)、交通運輸?shù)鹊葘崢I(yè),都要設(shè)法去趕上歐美。要各方面的生產(chǎn)技術(shù)都有進(jìn)步,然后中國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作者:楊棉月周石峰單位:貴州師范大學(xué)檔案館貴州師范大學(xué)歷史與政治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