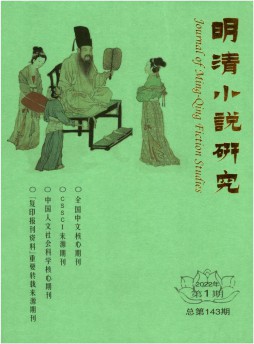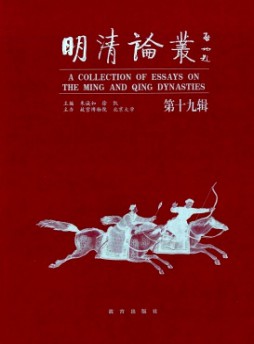明清時期果樹商品化趨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明清時期果樹商品化趨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明清文學與文獻》2016年第0期
摘要:明朝“永不起科”政策的推行,為關中陜北陜南土地開墾特別是果樹種植面積擴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陜西果樹商品化在明清時期繼續得到發展,與良好的農業政策、優越的自然條件、豐富的技術經驗積淀有關,與果品銷售市場密不可分。然而,海外殖民采略嚴重制約了明清陜西果樹商品化進程。
1明清時期陜西果樹較為集中形成商品化的基礎
陜西地域狹長,跨越緯度近9°,境內地形起伏多變,北有干旱少雨的黃土溝壑區,南有溫暖濕潤的秦巴山地,被司馬遷稱為“天府之國”的關中盆地位居正中。地形、緯度的多樣化為陜西果樹大集中、小分散栽培狀態奠定了良好的自然條件。現據雍正《陜西通志》及各府縣州志,對明清時期陜西果樹栽培大集中小分散狀況加以分析:
1.1關中以梨、李、石榴、柿、核桃、桃等6種為主
其中梨涌現了許多優勢產區和優良品種。如耀州梨在明代已有一定的名氣,被李時珍錄進《本草綱目》。渭南縣的“香水梨”則顯然是一個香氣撲鼻、鮮美多汁的品種。朝邑縣王謙村梨的產量高、名氣大,是清代少數以某種物產聞名的鄉村;盩厔縣出單果在0.5kg的大梨,但難以貯藏。為解決梨產量高、生產季節性強的問題,邠州人發明出秘密的貯藏辦法,能夠將梨保鮮至翌年2月。李以咸陽縣、渭南縣、邠州3地的名氣較大。渭南有“御黃李”良種,邠州則“李異他處,供用頗多”,為李的名優產地。石榴的優勢產地有禮泉昭陵、渭南、盩厔等地,按種子的顏色已分為紅、白2種,《渭南縣志》載“子軟而色淡者佳”。柿子廣泛分布于咸寧縣、三原縣、渭南縣、華州,主要用于加工柿餅后出售或貯藏備荒,華州多在土壤磽薄、山石嶙峋的南部山地種柿子樹,充分利用土地,增加收入。核桃主要分布于關中南北沿山地帶,如渭南縣、咸寧縣、麟游縣都是核桃產地。清前期,陜西桃樹整體屬于庭院樹種,較少有專門果園生產,文獻中僅見三原縣張村桃果產量品質較佳。此外,木瓜、棗、櫻桃、杏、柰、松子、無花果、枳椇(拐棗)、葡萄、銀杏在關中也有稀疏分布。
1.2陜北以棗、郁李、文冠果等3種為主
陜北與晉西北同屬狹義的黃土高原,以“安邑千樹棗”而著名于《史記》。明清時期黃河、延河流域的清澗、佳縣、吳堡、延川都是棗的盛產地,當地甚至出現了種植、經營的專業戶。郁李的果仁在明清時期是陜北的重要貢品,明初以同官所產最為有名,中期后供品范圍逐漸擴展到甘泉、鄜州、洛川、宜君等地,雖“每年額供二十斤送司解部”,卻是一種宮廷必備的中藥材。文冠果在陜北至今還以半栽培管理為主,當地人沒有采食的習慣,一般都用其種子榨油。此外,受人口遷徙及臨近關中果區的影響,桃、李、梨、柿也偶有發展。綏德的玉黃李,延安的木瓜、櫻桃,延長的林檎都有一定的名氣。另有分布較為廣泛的野葡萄,作為景觀樹種被引進庭院栽培。
1.3陜南以柑桔、栗、核桃果樹為主,相對栽培體系更復雜
根據栽培果樹的種類不同分為2個亞區:其一是漢中中南部的常綠果樹區。其二是秦巴山地的板栗核桃區。常綠果樹區柑子、桔子、柚子、橙子等蕓香科果樹都有分布。明清時期,因城固柑子相比附近各縣品質更好而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沔縣的柑子味苦,便轉向桔柚一類的種植,另外,還培育出一種“金色而肥甘”的優質枇杷。明清時期秦巴山地的移民依據來自不同的地區,栽培習慣也有所區別。因而秦巴山地的板栗、核桃分布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如明代后期,商洛原本是綿蘋果的優勢產區,《山陽縣志》更是冠以“極佳”的評語,可惜李自成起義軍入關以來,頻頻征集此物,百姓紛紛伐樹逃避貢賦,令其幾乎絕種。鎮安縣十分重視利用野生或半野生狀態下栭栗、毛栗、油栗等,既撿來鮮食,也曬干后用來煮食備荒。洛南縣則重視核桃的利用,整個商州的核桃及木材幾乎全部來自此縣,“果之最盛者無如核桃”,吃不完賣不掉的部分甚至用來榨油點燈,令人咋舌。山陽縣則重視石榴的種植,每村每戶都種,春來繁花似錦,秋日碩果累累。陜南地區由移民栽培習慣發展起來的果樹還有:桃、梅、杏、柿、棗、葡萄、木瓜、枇杷、梨、櫻桃、銀杏。野生獼猴桃(《洋縣志》為“羊桃”)當時仍沒有受到重視,致使陜西人再次與“水果之王”擦肩而過。明清時期寺觀廟宇等場所栽植著具有宗教象征意義的果樹,也保存了不少古代果樹。據《陜西省古樹名木信息網》的查詢[2]:(1)銀杏。共11株。主要分布于關中的西安、咸陽(樹齡800年以上)和陜南的安康、漢中(清末栽培居多)4個地區。(2)杜梨。吳起縣2株,栽于清末。銅川印臺區1株,栽于清中期。(3)文冠果。清澗縣1株,栽于北宋。米脂縣2株,栽于清中期。(4)酸棗。子洲縣1株,栽于西漢。橫山縣2株,栽于明初。(5)核桃楸。商洛商州區1株,栽于清末。(6)栓皮櫟。洛南縣1株,栽于明初。(7)棗。吳堡縣2株,韓城市1株,均栽于清初。此外,明清時期的野生果樹也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種植財富。據張亮成先生等人1983~1987年的調查,陜西秦巴山區的野生果樹有20科151種[2]。另據白崗栓等1999~2001年的調查,渭北黃土高原溝壑區有野生果樹113種,隸屬25科48屬[2]。因為野生果樹相對栽培果樹體系具有更高的穩定性,由此可見,明清時期陜西野生果樹種植資源的豐富和寶貴。
2明清時期陜西果樹生產經營的商品化趨勢
明清時期,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陜北的棗。綜合清澗、佳縣、吳堡、延川等地及臨境山西、河南各地方志來看,黃河沿岸分布著一個狹長彎曲的產棗勝地。清道光《延川縣志》記載:“紅棗……沿黃河一帶,百里成林,肉厚核小,與靈寶棗符。成裝販運,資以為食”實際調研與這些記載相吻合。這個優勢棗產區的形成有溫差大、雨量適宜、干棗耐儲存儲運輸等因素,而明清時期水上運輸的便捷和低廉是其交通原因。關中商品化程度較高的果樹有梨、綿蘋果、李、石榴等,通常布局于“附郭之地”的城郊,以便靠近肥源和消費場所。至于桃、葡萄、杏、柿、山楂等,大概由于好種易活,系農家庭院的常見栽培果樹,其商品化程度反而較低。陜南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只有柑桔,枇杷偶見優良品種的售賣。其它如洛南的核桃用來榨油燃燈,各種野生半野生的栗子曬干救荒,說明商品化程度極低。綜上不難看出,影響陜西果樹商品化的主要因素是交通條件,如洛南山高路險,許多地方飛鳥難過,當時核桃很難販運。在陜北黃河沿岸,關中、漢中各地城郊分布著較多精心經營的果樹區。商洛、安康等地則受人口、交通等條件的局限,果樹商品化程度較低,管理也較粗放。一般來說,商品化程度越高的果樹越費功力,其生產管理也就越精細。但對于明清時期陜北的棗來說,因其管理相對簡單[2],如育苗時分株即可(《齊民要術》《農政全書》《豳風廣義》3部農書均沒有提及棗的嫁接);只需除草、開甲,無需水肥管理(《齊民要術》甚至指出棗適合種植在高阜干燥水肥不能運達的地方,后出農書均贊同賈氏學說);采后只需干制揀選即可販運。可能是棗這種“用力少而著功多”的特點,才使其配合明清“永不起科”的政策,成為當地的農業經濟支柱之一。關中的果園是一個極為完整的系統,其精細程度較之今日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豳風廣義》記載,建造果園大致可以分為選址、作墻、備水儲肥、果樹配植等環節。
果園選址于城市近郊,以便靠近肥源與消費場所。選址近郊,民風不似偏遠村落淳樸,因此要作圍墻防盜。明清時期關中最常見的圍墻是土墻,西北方略高,以抵御冬日強勁的寒風。約7000㎡以上的大型果園則采用酸棗編織的籬墻,冬季稠種為三壟,約合0.5m,春來生苗后,每隔約合0.25m留1株端正旺盛者,三壟相錯如“M”形,歷經2年就能編織出嚴密的籬墻,可防盜,也可防野獸破壞。此外,柘樹(Cudraniatricuspidata(Carr.)Bur.exLavallee)和枸橘(Poncirustrifoliata(L.)Raf)與酸棗擁有類似的柔枝和尖銳的枝刺,也被用來制作籬墻。由于關中氣候干旱,果樹對水的耗費量又十分巨大,營建的果園都有備水抗旱的習慣。果園里大多挖有很深的旱井,缺水的生長旺季便用水車汲取澆灌。每逢冬季大雪,即掃雪堆在果樹根下,起到水肥兼施的效果。果園中蓄積大量的人畜糞尿,拌土腐化,避免生糞傷根以及引來害蟲。榨油后的菜籽餅在當時也是受歡迎的果園肥料。從多種地方志中的風俗記載來看,明清時期陜西還有一種澆冷卻煮肉湯汁的施肥方法。《豳風廣義》稱這種方法“澆肥一次,可旺數年”。明清時期關中果園“極盡地利”,其果樹配植十分精細,可以用“二圈一心”來概括。“二圈”的外圈是籬墻,在發揮防盜的基本功能之余,還兼具經濟利用價值。如柘樹葉可用來養蠶;枸橘所結的枳實供入藥,也能用糖腌制成蜜餞果子;酸棗仁可入藥,且產量和價格都很高,按7000m2果園的規模計算,能收酸棗仁約合70.8kg,所得收入在繳納田畝稅賦后,還能用于雇傭園丁的開支。“二圈”的內圈是桑樹,修剪成傘蓋形,用于飼蠶收絲。果園中心以梨為主,中國綿蘋果(蘋果、檳子)次之,二者間作。中國綿蘋果口感不如梨,但對干旱及蟲害等的抗逆性較強,當梨樹歉收時能夠止損,也能替補因蟲害死亡或產量不豐的梨樹。在果園尚未郁閉成林時,可以種十幾架葡萄,將味美但易爛的吐魯番品種和口味稍遜便于儲藏的山西品種混種。紅果、白果(可能是中國綿蘋果類群中2個原始的品種)也被種來防止其它果樹災年歉收。
從上述果樹配植的防災止損意識來看,明清時期陜西病蟲害防治的鮮明特點:首先通過構建多元樹種組成的復雜生態系統來培育高質量的果品。對于關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梨,還采取了很多精心的防治措施。如對付天牛等在樹身上蛀孔的害蟲,可以用鐵絲勾出蟲體,灌入桐油悶殺,還可以利用中藥百部的毒性殺滅。除這種手段外,很多地方志和專門農書還記載了冬季采取用火把燎烤果樹枝椏,殺死蟲卵的預防措施。《豳風廣義》中特別強調,春季的清明時節,害蟲開始活躍,此時用火把烘殺幼蟲,效果更好。由于火把烘殺蟲卵和幼蟲只能對付淺表害蟲,陜西先民又在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出冬季用鐮刀刮去老樹粗皮的做法。刮皮與燎烤相結合,起到了比二者分別單獨使用更好的防治效果。如果出現果實遭受金龜子等蟲害,為防止其傳播,則通常摘除有蟲的梨果,挖坑深埋。鳥雀有啄食破壞果實的天性,為降低損害,每到即將成熟的季節,果園設有驅逐鳥雀的園丁或童子。此外,打死1只高掛樹梢,也是先民摸索出來的一種防治鳥雀危害的辦法。明清時期陜西商品化程度較高的果樹有陜北的棗、關中的梨和葡萄,因此,其貯藏和加工受到的重視程度較高。在貯藏和加工方面受到重視的另一部分果樹是含水分少糖量高的柿、板栗等古代常見的“救荒果樹”。陜北以加工、貯藏、運輸干棗為主,其方法自《齊民要術》以來,古今并無太大改變,都包括曝曬、翻攪、攤晾、揀去爛果等基本環節。關中以梨為“百果之宗”,因此十分重視,采摘時遵循成熟程度次序采摘,對于高枝采摘不變,則制成“捕蝶網”樣式的采摘工具,在割斷果柄時使梨果墜入其中而不傷外皮。梨的鮮貯與《農政全書》里棗的鮮貯十分相似,但更加精細,采取1層麥麩(或米糠)1層鮮果的方式,為防止腐爛雜菌傳播,還采取5~6d翻開查看,梨上一旦生出斑點就立即售賣。為保濕保鮮,還發明出用白蘿卜皮包裹的辦法,據說可以將梨貯藏到翌年的4~5月。葡萄則已吸收新疆、山西等地窖藏越冬的經驗,并創新性地砍來粗大柳枝,鉆孔后插入葡萄蒂。柿子多在采收后旋去外皮,制成柿餅。也有釀成柿子醋,以備飲食添加。渭南、富平等地街頭,成熟后3~5個月內,有一種以柿子果醬與面粉攪拌后油炸而成的點心,稱為“柿子餅”,至今仍是深受當地人喜愛的一種風味食品。
3海外殖民采略抑制明清陜西果樹商品化發展
明清陜西果樹如果按照上述商品化發展,可以發展到東南沿海,壯大規模,和江南水果爭高低,與嶺南水果決雌雄,直至暢銷世界。然而,這時正是海外殖民瘋狂擴張的時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等殖民主義者紛紛來到我國采集各種植物,有些借植物采集刺探軍事經濟情報。中國這一時期有數以萬計的植物包括果樹資源流失海外,陜西也不例外[2]。可以說,新航路開辟后海外殖民者對包括陜西在內的中國各省區果樹資源進行了瘋狂采略,造成包括陜西在內的中國果樹長達400多年的浩劫。16世紀初期,葡萄牙征服了馬來亞后,葡萄牙人便逐步在我國開始貿易和商業活動,將中國的柑桔引入葡萄牙并傳播至整個歐洲。直到清初,即17世紀中葉,歐洲國家基本依靠天主教神父傳教及考察活動,搜集、掌握中國各地植物資源狀況,期間或有一些商人、游人來中國旅游考察。將中國的荔枝、龍眼,陜西的桃樹、柿子、杏樹、葡萄等果樹采集并帶到歐洲。大約于1520年,葡萄牙人由中國將甜橙引入歐洲,又從歐洲轉引至美洲、北非和澳大利亞[2]。17世紀中葉到鴉片戰爭前,歐洲諸國掀起了前往中國采集植物的高潮,先后來中國采集植物的不僅有神父、商人、旅行者,還有植物學家、園藝學家、博物學者、外交官、間諜、特務、學生、醫生、船長、軍人、職員、工人等,這些植物采集者的身后一般都有政府的支助。鴉片戰爭前30年,英國人更加肆無忌憚地采掠中國植物,成為西方的領頭羊。將中國的香蕉、枸杞、油茶、海桑、枇芭、柚子,陜西的木瓜、榛子、梨、文冠果、核桃、梨、栗子等掠奪回國。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趁火打卻,變本加厲,更加瘋狂地盜掠中國植物資源。直到解放前,從沿海到邊疆,從農區到草原,陜南陜北,八百里秦川,所到之處的中國植物資源都遭到殖民者踐踏蹂躪,瘋狂盜竊,果樹包括金桔、海棠、金絲桃、番櫻桃、獼猴桃、芭蕉等,幾乎竭澤而漁,所剩無幾[3]。
綜上論之,明清“永不起科”政策的推行,為關中陜北陜南土地開墾特別是果樹種植面積擴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礎[3]。而陜西果樹商品化在明清時期繼續得到發展,與良好的農業政策、優越的自然條件、豐富的技術經驗積淀有關,與果品銷售市場密不可分。然而,海外殖民采略嚴重制約了明清陜西果樹商品化進程。400多年的殖民瘋狂采略,中國流失了數以千種的珍貴果樹,陜西流失了幾乎全部果樹品種資源,嚴重擾亂了陜西果樹發展的市場秩序,阻斷了陜西果樹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成為陜西果區萎縮,果業長期滯后的根本原因。
作者:郭風平1;劉得騰2;郭新榮1;安魯1 單位: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渭南市非遺保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