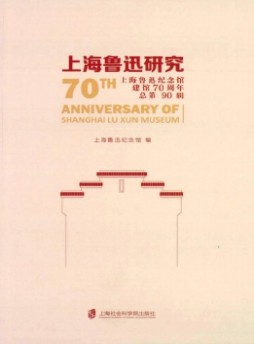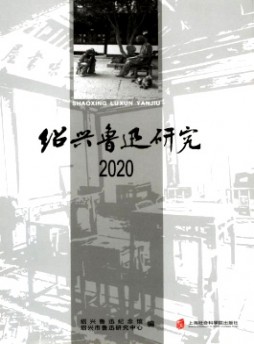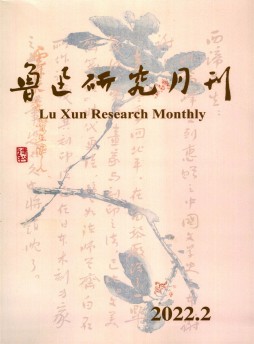北岡正子的魯迅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北岡正子的魯迅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魯迅研究月刊雜志》2015年第九期
北岡正子的魯迅研究,是1950年代在日本魯迅研究會(huì)成立之初發(fā)軔的。剛剛進(jìn)入魯迅研究會(huì)時(shí),她還是御茶水女子大學(xué)的二年級(jí)學(xué)生。當(dāng)時(shí),日本戰(zhàn)敗后讀中學(xué)和大學(xué)的一代青年人正在成為學(xué)術(shù)界的生力軍,這些人雖然在政治、文化立場(chǎng)上差別頗大,甚至相互對(duì)立,但是他們的學(xué)術(shù)實(shí)踐都同樣有著很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尤其是在美軍占領(lǐng)和冷戰(zhàn)的語境下研究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學(xué)者們,往往是以一種“戰(zhàn)斗”的心境進(jìn)行研究和言說的。當(dāng)然,他們的“戰(zhàn)斗”并不是那種高舉魯迅的“旗幟”、滿紙魯迅“語錄”的方式。恰恰相反,他們有意識(shí)地將“不依靠魯迅的話語”作為自己的原則之一。所謂“不依靠魯迅的話語”,實(shí)質(zhì)上就是要避免膚淺地、形式化地接受魯迅,避免將魯迅化為新的偶像。
這是因?yàn)椋麄冸m然著文與竹內(nèi)好進(jìn)行辯論、試圖突破竹內(nèi)好《魯迅》的框架,但至少都從竹內(nèi)好的《魯迅》中學(xué)到了一個(gè)根本的思想:魯迅是拒絕偶像崇拜、抵抗外來權(quán)威的。這一點(diǎn)一致被魯迅研究會(huì)的成員們認(rèn)作是魯迅的“姿態(tài)”。但是,在紛繁復(fù)雜的文化、歷史與現(xiàn)實(shí)中,怎樣具體理解這一“姿態(tài)”,以及更為重要的———應(yīng)該以怎樣的“姿態(tài)”去迫近魯迅?圍繞這些問題,魯迅研究會(huì)內(nèi)部產(chǎn)生了很嚴(yán)重的分歧,而北岡正子就是在這樣的眾聲喧嘩之中,開始自己閱讀魯迅、研究魯迅之路的。她在數(shù)十年之后回憶道:“在這個(gè)對(duì)自身的人生態(tài)度窮追不舍的研究會(huì)中,我還不明白要怎樣調(diào)整自己的‘姿態(tài)’才好,總是像一個(gè)不懂事的小孩子,跟在學(xué)長們的后頭努力奔跑。”①可見,“姿態(tài)”作為一個(gè)宏大而又切身的話語,是北岡正子從她還在學(xué)術(shù)道路的起點(diǎn)時(shí),就不得不正視的一個(gè)根本性問題,而她最初面對(duì)這個(gè)問題時(shí),感到惶惑、無所適從,卻又滿懷著熱情去主動(dòng)地努力追趕。應(yīng)該說,“史實(shí)還原”特別是“材源考證”的研究道路,是她在尋求自身迫近魯迅的“姿態(tài)”這種艱難的努力中所獲得的。
引導(dǎo)北岡正子走上這個(gè)研究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丸山昇。丸山昇針對(duì)日本魯迅研究中“感悟式批評(píng)”的泛濫之勢(shì),以細(xì)致研讀中國陸續(xù)出版的魯迅?jìng)饔浳墨I(xiàn)來構(gòu)筑自己學(xué)問的根基,而作為學(xué)妹的北岡正子當(dāng)時(shí)正是與丸山昇一起研讀這些文獻(xiàn)的同伴。這段珍貴的學(xué)習(xí)經(jīng)歷顯然影響到了北岡正子對(duì)“姿態(tài)”的理解方式,她在復(fù)雜的立場(chǎng)之爭中接受了“姿態(tài)必須以堅(jiān)實(shí)的文獻(xiàn)依據(jù)為支撐”這種最樸素的立場(chǎng)。事后看來最樸素的東西,在“歷史現(xiàn)場(chǎng)”卻往往是最難捕捉到的。當(dāng)爭論者糾結(jié)于究竟誰的“姿態(tài)”更能夠改造日本社會(huì)、誰的“姿態(tài)”更能夠回應(yīng)社會(huì)中苦難者的呼告時(shí),恰恰容易忘了自己何以有資格取這樣的“姿態(tài)”。當(dāng)時(shí)的北岡正子作為一個(gè)年輕的女學(xué)者,在諸多耀眼的、義正辭嚴(yán)的“姿態(tài)論”中立定了自己的腳跟,這是她學(xué)術(shù)生命中至關(guān)重要的一次選擇。北岡正子雖然從研讀中國出版的魯迅?jìng)饔浳墨I(xiàn)而走上研究魯迅的道路,可是卻并沒有以這些文獻(xiàn)作為自己主要的研究對(duì)象或研究工具。這其中當(dāng)然有學(xué)術(shù)分工的原因:針對(duì)這些傳記文獻(xiàn)的工作,丸山昇已經(jīng)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另一方面,北岡正子能夠另辟蹊徑,也體現(xiàn)了她學(xué)術(shù)思維的敏銳度。她在認(rèn)真閱讀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傳記文獻(xiàn)并從中受益之余,開始從事發(fā)掘存在于日本的、以日語書寫的魯迅?jìng)饔涃Y料這一工作。魯迅青年時(shí)代的一多半都是在日本度過的,關(guān)于他的這段歲月,除了許壽裳、周作人等當(dāng)時(shí)也在日本的親友能夠提供一些一手材料之外,大量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并不在中國。魯迅在日本時(shí)的檔案材料、當(dāng)時(shí)魯迅閱讀的書刊報(bào)章,以及與魯迅留學(xué)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政府規(guī)定、學(xué)校政策等文件,都只有日本學(xué)者才方便查找、閱讀、整理和分析,這也是日本學(xué)界可以為魯迅研究做出巨大貢獻(xiàn)的獨(dú)特領(lǐng)域之一。特別是魯迅仙臺(tái)時(shí)期的生活,當(dāng)時(shí)他身邊一個(gè)中國人都沒有,所以連許壽裳和周作人所知道的的都僅僅是來自魯迅的講述,可以說全部的一手傳記資料都有賴于日文文獻(xiàn)的發(fā)掘整理。當(dāng)然,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這里所說的“傳記”一詞都是廣義的,即不只是人生經(jīng)歷,還包括圍繞著傳主的社會(huì)、人文、人際等諸類環(huán)境。可以說,對(duì)于作家來說,其作品背后的東西都是廣義傳記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正如發(fā)明家一生各項(xiàng)發(fā)明成就背后的東西皆是科學(xué)史中傳記研究的對(duì)象一樣。北岡正子的研究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個(gè)部分。第一個(gè)部分是從魯迅在日本時(shí)期所遭遇的種種事件來研究魯迅思想走向成熟的線索,而關(guān)于這些大小事件,北岡正子主要都是以大量日文文獻(xiàn)為依據(jù)求其真相,發(fā)現(xiàn)并力求解決漢語回憶文章(包括魯迅本人回憶文章)中的疑點(diǎn)。第二個(gè)部分,也可以說是在學(xué)界口碑中構(gòu)成了“北岡形象”的部分,就是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
關(guān)于寫作《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的命意,北岡正子曾這樣自述:魯迅離開仙臺(tái)醫(yī)專后所提倡的“文藝運(yùn)動(dòng)”情況如何呢?……可以說《摩羅詩力說》最充分地體現(xiàn)出魯迅的文學(xué)觀。……這篇在人類精神發(fā)展中求得救國救民方策的詩論,是魯迅文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摩羅詩力說》由總論(第一、二、三節(jié))、分論(第四、五、六、七、八、九節(jié))、結(jié)論(第九節(jié)后半)組成。周作人的回憶錄早就指出,分論的一部分(第七、八節(jié))有材料來源。但近幾年來查明,不僅這一部分,幾乎分論的所有部分都有材料來源,…………這說明《摩羅詩力說》是在魯迅的某種意圖支配下,根據(jù)當(dāng)時(shí)找得到的材料來源寫成的。將材料來源的文章脈絡(luò)和魯迅的文章脈絡(luò)加以比較檢查,弄清魯迅文章的構(gòu)成情況,就可以從中領(lǐng)會(huì)魯迅的意圖。如果僅把《摩羅詩力說》看作魯迅的獨(dú)創(chuàng),那就不能發(fā)現(xiàn)。②很顯然,北岡正子的研究目的是領(lǐng)會(huì)魯迅《摩羅詩力說》的寫作意圖,她認(rèn)為只有清楚了這篇文章的所有材料來源并以這些材料來源對(duì)照魯迅的文章,才能發(fā)現(xiàn)魯迅真正的意圖。就此而言,可以說,北岡正子領(lǐng)會(huì)《摩羅詩力說》寫作意圖的方式是還原其寫作過程。對(duì)此我們可以質(zhì)疑:為何一篇文章的寫作意圖不能從最終文本中領(lǐng)會(huì),而要從寫作過程中領(lǐng)會(huì)?這是否意味著這篇文章事實(shí)上沒有成功地呈現(xiàn)其意圖呢?當(dāng)然不是這樣。
聯(lián)系全書,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北岡正子是將“材源”看作了《摩羅詩力說》的一種“注釋”。因此,她所說的通過文本與材源的比較檢查而領(lǐng)會(huì)意圖,當(dāng)是意為領(lǐng)會(huì)魯迅每一次取舍增刪的具體“意圖”,同時(shí),也是以這種方式繼承魯迅當(dāng)年的“意圖”。從在比較中看到魯迅的取舍增刪這一方面來說,“材源考”事實(shí)上可以起到凸顯《摩羅詩力說》中一些詞句的作用,這些詞句之所以得以凸顯,正是建立在《摩羅詩力說》中存在著大量與其材源文意、語序全然相同的段落這一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一個(gè)不知道或沒有細(xì)致了解這些材源的人,閱讀《摩羅詩力說》的一般方式當(dāng)然是逐句閱讀,對(duì)于文中每一處敘事和議論,都以相同的重視程度進(jìn)行接受。但是在北岡將《摩羅詩力說》中的語句與材源進(jìn)行了全面、清晰的對(duì)比之后,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分辨文中的哪些敘事與材源完全一致,哪些敘事是對(duì)材源中一個(gè)更長段落的縮寫,哪些敘事是對(duì)材源中散見于多處的內(nèi)容所做的歸納概括,哪些議論是對(duì)材源作者議論的復(fù)述,哪些議論是魯迅領(lǐng)會(huì)了材源作者的思想而以自己的語言加以表達(dá),以及哪些議論是魯迅自己閱讀、譯介材源文本時(shí)萌生的思考與感慨。另一方面,材源中哪些敘事在魯迅的講述中被略去,哪些議論沒有在《摩羅詩力說》中介紹,北岡正子也都在她的論著中一一標(biāo)明。在此僅舉一例,以見北岡正子的材源考具有凸顯《摩羅詩力說》中體現(xiàn)魯迅獨(dú)特“意圖”的詞句之作用。《摩羅詩力說》的第六節(jié),是對(duì)雪萊的介紹,經(jīng)北岡正子考證,這一部分的材源是濱田佳澄的《雪萊》。在一一比對(duì)了《摩羅詩力說》中與《雪萊》一致的段落并發(fā)現(xiàn)了一處材源不明但不甚重要的敘事之后,北岡正子強(qiáng)調(diào)了魯迅與濱田對(duì)于相同史實(shí)的不同態(tài)度,她寫道:濱田接著描寫雪萊的極端失望情緒,連期望能夠認(rèn)識(shí)這些詩歌真實(shí)價(jià)值的少數(shù)讀者都背離了他,這使他十分沮喪,甚至不想和當(dāng)時(shí)馳名遠(yuǎn)近的友人拜倫在一起。魯迅的論述中心卻放在詩人與偽俗尖銳對(duì)立的關(guān)系上,指出詩人為對(duì)抗社會(huì)偽俗弊習(xí)而寫的詩歌受到這種偽俗弊習(xí)的壓制。對(duì)于雪萊詩歌所面臨的社會(huì)評(píng)價(jià)的這種不同態(tài)度,表現(xiàn)為如何看待雪萊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用濱田的話來說即其“革命性”的差異。魯迅認(rèn)定詩歌必須沖擊世俗,使其驚慌失措,從而革新人生。因之,雪萊的詩恰恰體現(xiàn)出魯迅“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的觀點(diǎn)。魯迅對(duì)于雪萊詩歌的這種看法,后來也曾表露過,例如他不是曾把給敵人以不愉快作為自己文章存在的理由嗎?
與此相反,著意于描繪雪萊的沮喪、失望的濱田,卻未能看透以夭折告終的雪萊詩歌的社會(huì)作用。③也就是說,魯迅舍棄了材源中表現(xiàn)雪萊沮喪失望情緒的內(nèi)容,而對(duì)于雪萊詩作遭到的冷遇,則做出了與材源截然不同的議論。在材源的作者看來,詩作遭到冷遇無論如何是一種失敗,而在魯迅看來,遭到冷遇正說明了雪萊的詩作是有價(jià)值的,甚至遭到冷遇這件事本身就是文學(xué)的一種社會(huì)價(jià)值。如果沒有這么細(xì)致的材源考,我們讀到《摩羅詩力說》的這個(gè)段落當(dāng)然也能看得到魯迅這種文學(xué)觀的表達(dá),但卻不會(huì)意識(shí)到這種表達(dá)的特殊性,即含有和材源作者相辯論的意味。從繼承魯迅的意圖這一方面來說,魯迅當(dāng)年寫《摩羅詩力說》是要在中國人中特別是留日中國青年中宣示摩羅文學(xué)的精神,這種精神對(duì)于以尊卑秩序?yàn)楣怼⒁浴皽亓脊€讓”為風(fēng)尚的中國和日本來說,都是異質(zhì)的,即使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動(dòng)蕩的歷史,這種精神依然有加以宣示的必要。也就是說,這種摩羅精神仍然是魯迅的文化遺產(chǎn)中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部分之一。北岡正子將魯迅當(dāng)年依據(jù)的材料一一找到,加以引用和介紹,正是重申這種精神的一個(gè)行動(dòng)。伴隨著魯迅去世后在中日兩國被“經(jīng)典作家”化的過程,他的異質(zhì)性面臨著模糊化的可能,許多人將魯迅納入既成的文化秩序之中并以魯迅為文化秩序“保駕”。竹內(nèi)好和日本魯迅研究會(huì)的一些青年人分別與這種傾向進(jìn)行過正面的搏斗,而北岡的“材源考”則是采取了一種看起來溫和得多的方式對(duì)抗那種抹殺魯迅異質(zhì)性的力量。她在文章中大篇幅地將曾經(jīng)感動(dòng)青年魯迅的讀物再一次呈現(xiàn)出來。這些讀物帶著那個(gè)思想解放時(shí)代特有的氣息,大張旗鼓地張揚(yáng)反體制、反傳統(tǒng)、反“良風(fēng)美俗”的“大魔王”精神,毫無日本式“禮貌”、服從、忠君、敬上的色彩,因而在日本很快就被強(qiáng)大的主流意識(shí)湮沒了,郭沫若等人留日時(shí)接觸到的“浪漫主義”就不再是這樣的精神。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北岡正子迫近魯迅的姿態(tài)就是重讀魯迅讀過并曾熱情介紹給人們的書,而且重新將這些書介紹給這個(gè)時(shí)代的人們。
通過北岡正子的研究,我們對(duì)于魯迅《摩羅詩力說》的體裁也可以有一個(gè)更明確的認(rèn)識(shí)。總的來說,《摩羅詩力說》并不是魯迅閱讀了大量外國作家的作品和傳記資料后在一些問題上提出自己新見解、新觀點(diǎn)的“論文”,而是將外語資料摘譯、概括、編輯而成的“介紹文”。魯迅在童年時(shí)代完整地接受過“四書”的教育,對(duì)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句語錄當(dāng)然十分熟悉。當(dāng)他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樹立了新的文化信念之后,這種中國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思想傳統(tǒng)以新的形式繼續(xù)影響著他的文化活動(dòng),縱觀魯迅數(shù)十年的文字生涯,他用于搜集、校對(duì)、整理、翻譯、編輯等“述”一類工作的精力和時(shí)間,大于他用于“作”的精力和時(shí)間,而且“述”的工作絕大多數(shù)都是他積極主動(dòng)去做的,很少看到他在談到這一類工作時(shí)用到他談?wù)搫?chuàng)作時(shí)常用的“擠”等詞。《三閑集》卷末的自編《魯迅譯著書目》,是作為對(duì)自己“成績”的總結(jié)而整理的,其中不但“譯”和“著”并列,而且還特別列了“譯著之外,又有所校勘者,為:……所纂輯者:為:———所編輯者,為:……所選定,校字者,為:……所校訂,校字者,為:……所校訂者,為:……所印行者,為:……”④的一大篇,可見他對(duì)自己這部分工作的特別看重。這是魯迅的“文化性格”中很值得注意的一個(gè)方面。而北岡正子細(xì)致考證《摩羅詩力說》的材源,匡正了學(xué)界對(duì)于《摩羅詩力說》體裁的認(rèn)識(shí),由此明確了《摩羅詩力說》主要是屬于“述”的范疇,“作”的成分是補(bǔ)充性的、點(diǎn)綴性的、技術(shù)性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種出色的編譯工作。編輯《墳》時(shí),魯迅可能對(duì)十多年前做這篇文章的詳情已記憶模糊,正像《墳》的《題記》中說的:“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如果當(dāng)時(shí)魯迅能記起這篇文章是編譯而成的,大概也依然會(huì)將其印入文集再次發(fā)表,因?yàn)?“其中所說的幾個(gè)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gè)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后,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xiàn)在他們竟又時(shí)時(shí)在我的眼前出現(xiàn)。”
如果說北岡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承載了注解文本、繼承精神、辨析文體三重意義的話,那么她考證魯迅日本留學(xué)時(shí)期史實(shí)的著作,則可以說是聚焦于在日本的魯迅如何成長這一個(gè)問題,而她試圖解答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盡量詳細(xì)地復(fù)述當(dāng)時(shí)發(fā)生在魯迅身邊的事情。北岡這方面的著作,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是《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從弘文學(xué)院的入學(xué)到退學(xué)事件》(關(guān)西大學(xué)出版部2001年第1版),這本書的內(nèi)容,圍繞著魯迅日本留學(xué)的早期經(jīng)歷,廣泛地講述了清朝派遣留日學(xué)生政策的制定、弘文學(xué)院成立的背景、當(dāng)時(shí)的水陸交通、魯迅在學(xué)期間弘文學(xué)院的重大事件和規(guī)章沿革等等,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北岡正子的研究視角是平和的、客觀的,近百年前弘文學(xué)院的是是非非,對(duì)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都已經(jīng)成為歷史,重要的不是在彼時(shí)彼地的歷史中誰對(duì)誰錯(cuò),而是理解魯迅怎樣在日本“異文化”的環(huán)境中作為一個(gè)青年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問題意識(shí)。因此,北岡正子的這個(gè)研究,是“設(shè)身處地”的研究,她的思路,就是盡最大努力還原魯迅的經(jīng)歷與見聞,以文字的形式構(gòu)成一個(gè)與當(dāng)年魯迅所處的歷史時(shí)空高度相似的模擬時(shí)空,由此讓自己和讀者都能夠深入地、細(xì)致地體會(huì)魯迅的成長之路。在這個(gè)過程當(dāng)中,北岡正子也為許多重要學(xué)術(shù)問題的多角度研究做出了貢獻(xiàn),比如許壽裳回憶中說魯迅與他討論中國國民性時(shí)圍繞的是“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這樣三個(gè)問題,而兩人當(dāng)時(shí)所做出的回答,核心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而“癥結(jié),當(dāng)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于異族,認(rèn)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惟一的救濟(jì)方法是革命。”⑥這則材料常常被魯迅研究者們所引用,可以說已經(jīng)進(jìn)入了魯迅研究的“核心材料”之列。而北岡正子在關(guān)于弘文學(xué)院校史的文獻(xiàn)中看到了與許壽裳的回憶可以構(gòu)成互文性的材料,即弘文學(xué)院校長嘉納治五郎與楊度的討論紀(jì)錄。這場(chǎng)討論是由嘉納治五郎1902年考察中國教育之后對(duì)學(xué)生發(fā)表的訓(xùn)話引起的,當(dāng)時(shí)28歲的楊度是弘文學(xué)院的旁聽生。北岡正子在介紹了她從1902-1903年的《新民叢報(bào)》讀到的這批討論記錄之后,與許壽裳對(duì)他和魯迅如何討論國民性的回憶做了比較,認(rèn)為:魯迅與許壽裳的討論,在這奴隸性的由來和如何救濟(jì)為著眼點(diǎn)的方面與楊度的思考有共同之處。還有將被異民族征服的狀態(tài)看作是臣仆(奴隸)的觀點(diǎn),可以說是同樣植根于漢民族主義之中的吧。
像這樣的魯迅與許壽裳的所謂國民性的討論,應(yīng)該看作是受嘉納與楊度討論的直接波動(dòng)。這一討論不該一般性地納入視野。嘉納與楊度的討論引起留學(xué)生的關(guān)心,即使在中國也可讀到《支那教育問題》,想到這些,與魯迅和許壽裳的討論相似的問題或許還存在,不過魯迅未曾留下記錄,即如今日所知。⑦在閱讀大量史料之后,作這樣簡短的結(jié)論,可以說是許多日本學(xué)者的一種風(fēng)格,他們看重的是將自己的見解自然地體現(xiàn)與史料之中。北岡對(duì)這一論題結(jié)論的表述,其實(shí)只說了最基礎(chǔ)也最不容易引發(fā)爭議的三個(gè)觀點(diǎn):一、魯迅與許壽裳關(guān)于國民性的討論,是在嘉納治五郎與楊度關(guān)于中國教育的討論影響下進(jìn)行的,理解魯許的討論應(yīng)考慮到這一影響;二、魯迅與許壽裳關(guān)于中國國民性的討論中,奴隸性的由來與救濟(jì)方法的問題意識(shí)與楊度有共同之處;三、魯、許與楊度認(rèn)識(shí)當(dāng)時(shí)漢族與滿洲關(guān)系的意識(shí)形態(tài)根基是一樣的,都是漢民族主義。如果比較的結(jié)論僅此三點(diǎn),那么這一比較的學(xué)術(shù)意義恐怕也不過如此而已了,但是我們認(rèn)真閱讀了北岡正子的對(duì)嘉納治五郎與楊度的討論進(jìn)行的歸納介紹之后,就會(huì)意識(shí)到她的這番發(fā)現(xiàn)有比上述三點(diǎn)結(jié)論更大的意義。筆者曾在2002年將《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中的這一部分以《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由來》為題漢譯發(fā)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期望引起學(xué)界的關(guān)注與討論。在此,就這一北岡正子以文獻(xiàn)發(fā)掘提出的問題探討如下:首先,還是從北岡的三個(gè)結(jié)論談起。上文雖然說這三個(gè)結(jié)論是“最基礎(chǔ)也最不容易引發(fā)爭議的”,但若較真起來,其第一個(gè)結(jié)論就并非不容置疑。許壽裳和魯迅當(dāng)年在日本討論的情形,我們今天只能看到許壽裳的回憶,魯迅的作品中未見記述;而無論是魯迅還是許壽裳,都沒有在著作中提到過嘉納治五郎和楊度的討論。北岡書中給的全部證據(jù),也都只能證明魯許討論受到兩位前輩討論影響的可能性,而證明不了其必然性。邏輯上更加穩(wěn)健的說法可能是,兩個(gè)討論在議題、思路上的相似性,恰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關(guān)心中國時(shí)局、熱心探求救國之路的人們有著共同的關(guān)注點(diǎn),而其中的一部分年輕人(楊度、魯迅、許壽裳正是那個(gè)年代的“70后”“80后”)對(duì)于這些關(guān)注點(diǎn)做出了相似的思考,得出了相近的觀點(diǎn)。這也對(duì)應(yīng)了北岡的第二個(gè)結(jié)論,即魯迅、許壽裳的討論與楊度的言論存在共同之處。
第三個(gè)結(jié)論其實(shí)也可以作如是觀,所謂“漢民族主義”是當(dāng)時(shí)民間志士共同的看法,其根源還是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所以魯迅、許壽裳在這一點(diǎn)上和楊度一致,似乎也不必看做特別的事情。在兩個(gè)討論的對(duì)照中更應(yīng)該注目的,是其中體現(xiàn)的時(shí)代思想風(fēng)潮以及魯迅、許壽裳在這樣的風(fēng)潮中所持的思想立場(chǎng)。從嘉納治五郎和楊度的討論來看,兩人都期待著中國發(fā)生變化,而且,兩人期待的變化都同時(shí)包括著社會(huì)的變化與國民精神的變化。期待變化,也正是魯迅和許壽裳進(jìn)行討論的出發(fā)點(diǎn)。從更大的背景來看,當(dāng)時(shí)“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zhàn),也是將期待中國發(fā)生變化作為默認(rèn)前提的。“人心思變”,就是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思想風(fēng)潮。然而,中國社會(huì)的變化與中國國民精神的變化如何實(shí)現(xiàn)?變化的目的何在?這些問題卻在共同的時(shí)代思想風(fēng)潮之內(nèi)有著種種不同的回答。在這個(gè)意義上,將嘉納治五郎和楊度的討論作為理解魯迅、許壽裳的討論以及理解魯迅思想的一個(gè)參照,是很有價(jià)值的。嘉納治五郎和楊度爭論的焦點(diǎn),在于對(duì)中國國民精神的培養(yǎng)中是否應(yīng)當(dāng)包含著鮮明的反抗意識(shí)。雙方的討論正是由于楊度認(rèn)為嘉納演講中傳達(dá)的公民教育理念中缺乏反抗意識(shí)的教育而引發(fā)的。在討論的過程中,嘉納先后提出了一些理由為自己的理念辯護(hù),這些理由可以大體歸納為兩個(gè)方面:反抗意識(shí)進(jìn)入教育,將導(dǎo)致清政府終止包括留學(xué)在內(nèi)的新式教育,并整體排斥學(xué)習(xí)社會(huì)科學(xué)的新知識(shí)青年;反抗意識(shí)會(huì)導(dǎo)致中國陷入騷亂,黃色人種自相殘殺,而給白色人種可乘之機(jī)。
對(duì)于第一方面的理由,楊度沒有進(jìn)行正面批駁,只是說不能因此就任由國民教育墮落為與專制者同流合污的地步,而對(duì)于第二方面的理由,楊度則明確表示,若不盡快培養(yǎng)反抗意識(shí),包括滿族在內(nèi)的中國人只能繼續(xù)處于蒙昧之中,做白色人種的奴才,毫無益于黃色人種的崛起,甚且導(dǎo)致黃色人種陷入萬劫不復(fù)的境地。這種以“人種利益”為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當(dāng)然體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思想的偏差與局限性,但嘉納與楊度在這樣的討論中體現(xiàn)的思路,卻有著超越這種局限性的意義。無論所尋求實(shí)現(xiàn)者是“人種利益”也罷、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也罷,楊度其實(shí)講的是一個(gè)根本性的政治哲學(xué)問題,那就是能夠在專制體制和奴役關(guān)系下實(shí)現(xiàn)這樣的利益嗎?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雖然“騷亂”可能會(huì)一時(shí)損害這樣的利益,但卻是不得不走的一步,否則虛假的“一團(tuán)和氣”“上下同心”只能導(dǎo)致整體利益的持續(xù)流失。在討論的后期,嘉納對(duì)楊度這樣的政治理念表示了認(rèn)同,并將自己的觀點(diǎn)重新概括為國民教育的宗旨在于“不可服從于強(qiáng)力”和“不可不服從于公理”,“公理者,能以公德追求‘一群’(集團(tuán)、社會(huì))之利益,不惜一身之害,以圖集團(tuán)之利,集團(tuán)利固而一國之本立設(shè),反之,人人謀利己而‘公眾’(公民)則不保,個(gè)人也無以立。事實(shí)是必以‘公眾’相保而人人獲利為目的,作為教育問題,則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群’獲利為目的,是為公德。”⑧楊度對(duì)嘉納的公理主義教育觀表示欽佩,認(rèn)為正是當(dāng)時(shí)中國教育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原則。至此,討論雙方在言詞上達(dá)到了一致。縱觀這場(chǎng)討論,其開端的確是包含著一些誤會(huì)的成分,嘉納演講中的主張以柔和、平衡的方式曲線推動(dòng)中國國民意識(shí)的更新,以求代價(jià)最小而成效最大,只是因?yàn)樗诒磉_(dá)中始終強(qiáng)調(diào)柔和、平衡,才激起楊度當(dāng)場(chǎng)發(fā)表異議。嘉納治五郎在主持弘文學(xué)院的中國留學(xué)生教育之外,其實(shí)有一個(gè)更為人所知的身份,那就是日本現(xiàn)代柔道之父。因此,也可以說他是將柔道的平衡思想和以柔克剛的智慧運(yùn)用到了中國國民教育的問題上,而楊度是在討論的過程中才逐漸意識(shí)到這一本質(zhì)的。
另一種可能是,楊度其實(shí)并未誤解嘉納的本意,乃是故意發(fā)難,以“擠”嘉納更清楚地對(duì)中國問題表態(tài),讓聽演講的中國留學(xué)生不至于錯(cuò)誤接受嘉納的國民教育理念。無論如何,討論最終收獲了不可服從于強(qiáng)力而當(dāng)服從于公理的點(diǎn)題之論。這完全可以看成是嘉納和楊度共同認(rèn)可的政治哲學(xué)與國民教育理念。但是,討論終止之時(shí),兩人就真的沒有分歧了嗎?我們發(fā)現(xiàn),楊度在認(rèn)同嘉納之言的同時(shí),還講了這樣一番話:“‘奴隸性’重,惟知仰人以自存,不謀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作為人的獨(dú)立),一變而為‘損人利己’之心。”⑨嘉納言“公理”的重心,在于“公”與“私”之辨,主張教育中國人將“群體”看得比“個(gè)人”為重。這話就未免是異國人的隔靴搔癢了。因?yàn)樵谥袊幕星∏∈菑膩頉]有“個(gè)人”的地位,而“群體”一直是強(qiáng)大的“霸權(quán)話語”。當(dāng)時(shí)中國社會(huì)廣泛存在的“損人利己”問題,不是因?yàn)槿藗冄壑袥]有“群體”,而是因?yàn)槿藗冄壑袥]有“個(gè)人”———無論對(duì)于自己還是對(duì)于他人,都既沒有對(duì)個(gè)人尊嚴(yán)的珍重,也沒有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敬畏。相比起來,楊度的話就實(shí)在得多:“奴隸”文化的本質(zhì)就在于依賴“恩德”(法外開恩)而不是憑自己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創(chuàng)造來自立,因此對(duì)于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看得越來越重要,“獨(dú)立個(gè)人”的意識(shí)則不知不覺地漸漸淡漠了,這才導(dǎo)致了道德的墮落。可見,在國民道德教育的具體實(shí)踐問題上,楊度直到討論的最后,堅(jiān)持的仍然是培養(yǎng)“個(gè)人”意識(shí)為先。或者說,在不可服從強(qiáng)權(quán)而當(dāng)服從公理這句話中,嘉納強(qiáng)調(diào)的是當(dāng)服從公理,而楊度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不可服從強(qiáng)權(quán)。
現(xiàn)在在回過頭來看魯迅與許壽裳的討論。顯然,他們也和嘉納治五郎、楊度有著相同的基本政治哲學(xué),即專制體制和奴役關(guān)系只能毒害人群。而他們對(duì)于國民性的見解與嘉納的觀點(diǎn)很遠(yuǎn)而與楊度的觀點(diǎn)相似,他們所說的“誠”與“愛”都是人與他人之間的關(guān)系而非人與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但是,他們比楊度走得更遠(yuǎn),這體現(xiàn)在他們更強(qiáng)調(diào)奴隸身份對(duì)于天然人性的扭曲。在楊度說許多中國人奴隸根性太重,以至于只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時(shí)候,魯迅和許壽裳說的卻是:做了奴隸的人,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所以,這兩個(gè)年輕人實(shí)際上達(dá)到了這樣的一個(gè)邏輯節(jié)點(diǎn)———若不根本否定專制體制與奴役關(guān)系,任何國民教育的效力都是脆弱的,真正的國民教育必須與革命成為一體。由此,在嘉納治五郎和楊度的雙重映襯下,魯迅與許壽裳當(dāng)時(shí)國民性思想的徹底性和激進(jìn)性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了。總之,無論是材源考,還是傳記研究,北岡正子都以辛勤踏實(shí)的勞作為我們呈現(xiàn)了魯迅文學(xué)的真實(shí)“背景”,魯迅文學(xué)存在于這樣的背景之上,也應(yīng)在這樣的背景上加以觀察,只有我們能夠從背景中看到魯迅,也就是說,能夠?qū)Ⅳ斞钢糜诒尘岸植讳螞]于背景時(shí),我們才離魯迅真的近了一步。
作者:李明暉 靳叢林 單位:武漢美術(shù)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