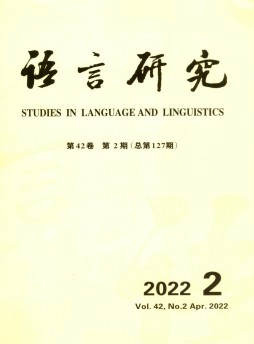語(yǔ)言因素在脫貧攻堅(jiān)中的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語(yǔ)言因素在脫貧攻堅(jiān)中的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在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大背景下,在“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大方略的落實(shí)中,語(yǔ)言因素是很重要的一個(gè)方面,更是一個(gè)基礎(chǔ)性因素。國(guó)家扶貧政策中有許多與語(yǔ)言文字相關(guān)的表述,國(guó)家語(yǔ)委、國(guó)家民委也出臺(tái)了圍繞脫貧攻堅(jiān)的語(yǔ)言文字政策。從語(yǔ)言地理上來(lái)說(shuō),14個(g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的語(yǔ)言/方言特征都較為復(fù)雜。語(yǔ)言作為資本,可以在改觀教育劣勢(shì)上發(fā)揮重要作用,并進(jìn)而有助于改觀就業(yè)和經(jīng)濟(jì)劣勢(shì),以達(dá)到扶貧脫貧的目的。統(tǒng)一的語(yǔ)言無(wú)論是從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是大勢(shì)所趨,所以有必要在貧困地區(qū)加大普通話推廣力度、實(shí)施語(yǔ)言文字精準(zhǔn)扶貧的策略。與此同時(shí),要注重語(yǔ)言/方言多樣性的保持,構(gòu)建和諧雙語(yǔ)雙言社會(huì);而貧困地區(qū)的干部也有必要學(xué)會(huì)一些當(dāng)?shù)氐纳贁?shù)民族語(yǔ)言或方言。重視語(yǔ)言因素的基礎(chǔ)性作用,做好語(yǔ)言扶貧工作,將有助于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實(shí)現(xiàn)“真脫貧”和“脫真貧”的目標(biāo)。
關(guān)鍵詞:脫貧攻堅(jiān);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普通話;語(yǔ)言資本;語(yǔ)言扶貧
一、引言
貧困,是人類面對(duì)的共同問(wèn)題。扶貧、脫貧、減貧,是聯(lián)合國(guó)《新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的主要工作之一。消除貧困、改善民生,也是執(zhí)政黨治國(guó)理政的重要使命。中國(guó)政府歷來(lái)重視扶貧—脫貧工作,從1986年國(guó)務(wù)院貧困地區(qū)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領(lǐng)導(dǎo)小組的成立到1994年的《國(guó)家八七扶貧攻堅(jiān)計(jì)劃》和2011年的《中國(guó)農(nóng)村扶貧開(kāi)發(fā)綱要(2011—2020年)》,再到2016年的《“十三五”脫貧攻堅(jiān)規(guī)劃》的出臺(tái),三十年間,中央扶貧政策幾經(jīng)調(diào)整:從“救濟(jì)式扶貧”到“開(kāi)發(fā)式扶貧”;從“區(qū)域性扶貧”到瞄準(zhǔn)貧困縣、“整村推進(jìn)”再到“扶貧入戶”,而“精準(zhǔn)扶貧”則成為當(dāng)下的最新方向標(biāo)。幾十年來(lái)我國(guó)取得的扶貧—脫貧成就是巨大的,也為世界的消除貧困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根據(jù)世界銀行的標(biāo)準(zhǔn)和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1981年世界平均貧困率是42.15%,而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貧困率是88.32%;到2013年,世界平均貧困率是10.68%,而中國(guó)的貧困率則下降到了1.85%。
二、國(guó)家政策中的語(yǔ)言扶貧措施
⑤我國(guó)的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式扶貧應(yīng)該可以追溯到1986年國(guó)務(wù)院貧困地區(qū)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領(lǐng)導(dǎo)小組⑥的成立。但在各類政策文件中,一直到了2011年的《中國(guó)農(nóng)村扶貧開(kāi)發(fā)綱要(2011—2020年)》才首次提到了語(yǔ)言因素,即“五、行業(yè)扶貧(二十三)”中提到的“在民族地區(qū)全面推廣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到了2016年的《“十三五”脫貧攻堅(jiān)規(guī)劃》,與語(yǔ)言因素相關(guān)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現(xiàn),從而將語(yǔ)言因素在扶貧—脫貧方略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具體的政策比如“建立健全雙語(yǔ)教學(xué)體系”和“加大雙語(yǔ)教師培養(yǎng)力度,加強(qiáng)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教學(xué)”(第五章“教育扶貧”第一節(jié)“提升基礎(chǔ)教育水平”);“加強(qiáng)民族聚居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特困群體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培訓(xùn)(第五章“教育扶貧”第三節(jié)加快發(fā)展職業(yè)教育)等。201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貧困村駐村工作隊(duì)選派管理工作的指導(dǎo)意見(jiàn)》,將“積極推廣普及普通話,幫助提高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應(yīng)用能力”明確為駐村工作隊(duì)的主要任務(wù)之一。除了上述扶貧—脫貧政策中的表述,在2016年8月教育部、國(guó)家語(yǔ)委的《國(guó)家語(yǔ)言文字事業(yè)“十三五”發(fā)展規(guī)劃》中,“三、主要任務(wù),(一)普及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2.加快民族地區(qū)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中指出“結(jié)合國(guó)家實(shí)施的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方略,以提升教師、基層干部和青壯年農(nóng)牧民語(yǔ)言文字應(yīng)用能力為重點(diǎn),加快提高民族地區(qū)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率”;在“四、重點(diǎn)工程,(一)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攻堅(jiān)工程”中又提到“與國(guó)家扶貧攻堅(jiān)等工程相銜接,在農(nóng)村和民族地區(qū)開(kāi)展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攻堅(jiān)”。2017年4月教育部、國(guó)家語(yǔ)委又了《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攻堅(jiān)工程實(shí)施方案》,在“一、總體要求,(二)”中提到,“雖然我國(guó)的普通話平均普及率已超過(guò)70%,但東西部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發(fā)展很不平衡,西部與東部有20個(gè)百分點(diǎn)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過(guò)90%,而很多農(nóng)村地區(qū)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區(qū)則更低。中西部地區(qū)還有很多青壯年農(nóng)民、牧民無(wú)法用普通話進(jìn)行基本的溝通交流,這已經(jīng)成為阻礙個(gè)人脫貧致富、影響地方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制約國(guó)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甚至影響民族團(tuán)結(jié)和諧的重要因素。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yīng)先通語(yǔ)”。在“一、總體要求,(三)”中又說(shuō),“要結(jié)合國(guó)家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基本方略……制定普通話普及攻堅(jiān)具體實(shí)施方案,大力提高普通話的普及率,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提供新動(dòng)力,為文化建設(shè)提供強(qiáng)助力,為打贏全面小康攻堅(jiān)戰(zhàn)奠定良好基礎(chǔ)”。2018年1月,教育部、國(guó)務(wù)院扶貧辦、國(guó)家語(yǔ)委三部委聯(lián)合制定了《推普脫貧攻堅(jiān)行動(dòng)計(jì)劃(2018—2020年)》。計(jì)劃的制定宗旨就是要充分發(fā)揮普通話在提高勞動(dòng)力基本素質(zhì)、促進(jìn)職業(yè)技能提升、增強(qiáng)就業(yè)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準(zhǔn)的舉措、更加有力的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奠定良好基礎(chǔ)。計(jì)劃提出了一個(gè)“目標(biāo)定位”、四個(gè)“基本原則”和九大“具體措施”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計(jì)劃將普通話普及率的提升明確納入地方扶貧部門、教育部門扶貧工作績(jī)效考核,列入駐村干部和駐村第一書(shū)記的主要工作任務(wù),力求實(shí)效。綜合人口、經(jīng)濟(jì)、教育、語(yǔ)言等基礎(chǔ)因素和條件保障,聚焦普通話普及率低的地區(qū)和青壯年勞動(dòng)力人口,將普通話學(xué)習(xí)掌握情況記入貧困人口檔案卡,消除因語(yǔ)言不通而無(wú)法脫貧的情況,切實(shí)發(fā)揮語(yǔ)言文字在教育脫貧攻堅(jiān)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顯然,提升貧困農(nóng)村和民族地區(qū)群眾的普通話能力和水平是實(shí)現(xiàn)知識(shí)學(xué)習(xí)和其他技能提升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此基礎(chǔ)上貧困群眾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真正的脫貧。上述文件和政策,必將會(huì)為國(guó)家扶貧—脫貧方略的實(shí)施提供切實(shí)的語(yǔ)言層面的保障。
三、特困地區(qū)的語(yǔ)言使用現(xiàn)狀
《中國(guó)農(nóng)村扶貧開(kāi)發(fā)綱要(2011—2020年)》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遴選出了14個(g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作為扶貧—脫貧工作的重點(diǎn)。它們基本都屬于老(革命老區(qū))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邊(邊疆地區(qū))窮(瘠苦地區(qū))地區(qū),貧困程度較深,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普通話普及率不高、水平較低。本節(jié)就嘗試從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區(qū)和漢語(yǔ)方言區(qū)這兩個(gè)層面來(lái)簡(jiǎn)略描畫(huà)一下這些地區(qū)的語(yǔ)言使用現(xiàn)狀。在這14個(gè)特困地區(qū)中,有11個(gè)地區(qū)是涵蓋少數(shù)民族居住區(qū)的⑧。具體說(shuō)來(lái),按照少數(shù)民族人口比例依次是⑨:(1)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93%以上⑩,境內(nèi)主要少數(shù)民族有維吾爾族、塔吉克族、回族、哈薩克族、柯?tīng)柨俗巫濉M族、蒙古族、藏族、土家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塔塔爾族等二十多個(gè);(2)西藏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到90%以上,主要是藏族以及回族、納西族、怒族、門巴族、珞巴族等;(3)四省藏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到了73%左右,主要包括藏族、蒙古族、羌族、彝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羌族等少數(shù)民族;(4)滇桂黔石漠化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2129.3萬(wàn)人(62.1%),有壯、苗、布依、瑤、侗等14個(gè)世居少數(shù)民族;(5)武陵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一千一百多萬(wàn)人(47.8%),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三十多個(gè)少數(shù)民族;(6)滇西邊境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831.5萬(wàn)人(47.5%),有彝、傣、白、景頗、傈僳、拉祜、佤、納西、怒、獨(dú)龍等二十多個(gè)世居少數(shù)民族,其中有15個(gè)云南獨(dú)有少數(shù)民族、8個(gè)人口較少民族;(7)烏蒙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總?cè)丝?0.5%,片區(qū)內(nèi)居住著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數(shù)民族,是我國(guó)主要的彝族聚集區(qū);(8)大興安嶺南麓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111.4萬(wàn)人(13.3%),有蒙古族、滿族等6個(gè)世居少數(shù)民族,其中有達(dá)斡爾族、錫伯族、柯?tīng)柨俗巫宓?個(gè)人口較少民族;(9)燕山—太行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146萬(wàn)人(13.3%),有滿族、蒙古族、回族等3個(gè)世居少數(shù)民族;(10)六盤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390.1萬(wàn)人(16.6%),有回族、東鄉(xiāng)族、土族、撒拉族等;(11)秦巴山區(qū)有羌族等少數(shù)民族人口56.3萬(wàn)人(1.5%)。14個(gè)特困地區(qū)都涉及到漢族居住區(qū),從語(yǔ)言地理上來(lái)看:(1)基本上覆蓋了北方、吳、湘、贛、客家、閩、粵等幾大方言區(qū)及其內(nèi)部一些次方言區(qū);(2)有好幾個(gè)處于兩大或幾大方言區(qū)交界的地區(qū),方言使用情形也就更為復(fù)雜,比如燕山—太行山區(qū)、呂梁山區(qū)、六盤山區(qū)、秦巴山區(qū)、大別山區(qū)、烏蒙山區(qū)、羅霄山區(qū)、武陵山區(qū)、滇桂黔石漠化區(qū)、滇西邊境山區(qū)等。從上面的數(shù)據(jù)和分析可以看出,14個(gè)連片特困地區(qū)基本上都呈現(xiàn)出了語(yǔ)言或方言使用較為復(fù)雜的狀態(tài)。
四、語(yǔ)言資本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
(一)語(yǔ)言作為資本在扶貧—脫貧中的作用語(yǔ)言,是一種資本(capital)。語(yǔ)言資本有不同的維度,比如可以歸入文化資本[2-3],也可以歸入人力資本[4-5]。本文取其人力資本屬性,即語(yǔ)言是一種具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知識(shí)和能力。
(二)統(tǒng)一的語(yǔ)言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一直以來(lái),許多不同學(xué)科的學(xué)者(比如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語(yǔ)言學(xué)家等)似乎都認(rèn)同這一觀點(diǎn):語(yǔ)言多樣性程度更高的國(guó)家往往比那些以單一語(yǔ)言為主的國(guó)家更貧窮。與語(yǔ)言以及其他文化因素(比如民族等)的碎片化相關(guān)聯(lián)的,往往是社會(huì)的分化和沖突、低流動(dòng)性、有限的貿(mào)易、不完善的市場(chǎng)以及較貧乏的交流。對(duì)這一論題較為系統(tǒng)和全面的分析可以追溯到Fishman[9]。此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幾份調(diào)查報(bào)告,分析了語(yǔ)言同質(zhì)(統(tǒng)一性)或異質(zhì)(多樣性)與諸種社會(huì)—政治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在總結(jié)部分,作者說(shuō)道:“一般說(shuō)來(lái),比起語(yǔ)言異質(zhì)性,語(yǔ)言同質(zhì)性往往更多地與國(guó)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聯(lián)。語(yǔ)言上同質(zhì)的國(guó)家往往在經(jīng)濟(jì)上更發(fā)達(dá),教育上更先進(jìn),政治上更現(xiàn)代化,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上也更穩(wěn)定和牢固。”又說(shuō):“具有統(tǒng)一語(yǔ)言和多種語(yǔ)言的國(guó)家所表現(xiàn)出的許多差別似乎也體現(xiàn)了富國(guó)與窮國(guó)之間的差別。”幾年之后,Pool(1972)在Fishman(1966)等研究的基礎(chǔ)上,分析了133個(gè)國(guó)家1962年前后人均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和最大本族語(yǔ)社區(qū)人數(sh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并指出:“一個(gè)國(guó)家可以具有任何程度的語(yǔ)言統(tǒng)一或語(yǔ)言分歧而仍然是不發(fā)達(dá)的;一個(gè)全民(或多或少)使用同一種語(yǔ)言的國(guó)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或貧或富。但是,一個(gè)語(yǔ)言極度繁雜的國(guó)家總是不發(fā)達(dá)的或半發(fā)達(dá)的,而一個(gè)高度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總是具有高度的語(yǔ)言統(tǒng)一性。因此,語(yǔ)言統(tǒng)一性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條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語(yǔ)言統(tǒng)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條件(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關(guān)系上的)。”二十多年后,Nettle[10]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費(fèi)舍曼—普爾假說(shuō)”(Fishman-PoolHypothesis),即認(rèn)為語(yǔ)言多樣性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有種逆相關(guān),而語(yǔ)言統(tǒng)一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則是正相關(guān)。Nettle(2000)的研究基本上證實(shí)了這一假說(shuō),但與此同時(shí)Nettle認(rèn)為需要在解釋機(jī)制上有所改進(jìn)。Wang&Steiner[11]從社會(huì)資本的角度發(fā)現(xiàn),一般說(shuō)來(lái)社會(huì)資本越高的國(guó)家越富有,而具有較高社會(huì)資本的國(guó)家在語(yǔ)言上也會(huì)呈現(xiàn)出較高的同質(zhì)性。比如日本、荷蘭、丹麥等就屬于國(guó)內(nèi)語(yǔ)言單一且社會(huì)資本指數(shù)高的國(guó)家,而印度和烏干達(dá)則是完全相反。這也可以看作是對(duì)“費(fèi)舍曼—普爾假說(shuō)”的證明。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國(guó)家間轉(zhuǎn)向國(guó)家內(nèi),從語(yǔ)言間轉(zhuǎn)向語(yǔ)言內(nèi)的方言,這一假說(shu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立的。劉毓蕓等[12]的研究就表明:其他條件不變時(shí),在同一方言大區(qū)內(nèi)部,方言距離每增大1個(gè)層級(jí),勞動(dòng)力跨市流動(dòng)的概率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區(qū)之間,方言距離每增大1個(gè)層級(jí),勞動(dòng)力跨市流動(dòng)的概率降低3%左右;勞動(dòng)力跨方言流動(dòng)的最優(yōu)方言距離是跨方言區(qū)、但不跨方言大區(qū)。Falck等[13]探討了歷史的方言差異給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交流帶來(lái)的影響,跟劉毓蕓等[12]的研究異曲同工。其核心發(fā)現(xiàn)是:德國(guó)當(dāng)代的人口流動(dòng)與方言間的相似度成正相關(guān),這一關(guān)系有重要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效應(yīng),即如果沒(méi)有方言的屏障,德國(guó)的國(guó)內(nèi)人口流動(dòng)會(huì)比現(xiàn)在現(xiàn)實(shí)的情形高20%左右。Lameli等[14]利用相同的方言學(xué)材料,也得出了與之一致的結(jié)論。一個(gè)反面的證據(jù)是瀕危語(yǔ)言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即經(jīng)濟(jì)發(fā)展越好的國(guó)家或區(qū)域,語(yǔ)言瀕危的速度會(huì)更快,換句話說(shuō)語(yǔ)言一致的程度會(huì)更高。當(dāng)然,除了對(duì)假說(shuō)正面的證明,也還有些研究對(duì)這一假說(shuō)持反對(duì)的意見(jiàn)。比如Sreekumar[15]、Gerring[16]等的研究。正如Galbraith&Benitez-Galbraith所說(shuō):“語(yǔ)言多樣性、種族分化與經(jīng)濟(jì)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是復(fù)雜的,其爭(zhēng)論也是開(kāi)放的。”[17]具體到特困地區(qū)來(lái)說(shuō),可以據(jù)此做出如下論斷:不同民族語(yǔ)言區(qū)和不同漢語(yǔ)方言區(qū)的民眾提升普通話這一國(guó)家通用語(yǔ)的水平將有助于特困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下文第五部分的論述也正與這一結(jié)論相合。此外還有三點(diǎn)需要特別指出:一是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一語(yǔ)言的重要性,并不是對(duì)語(yǔ)言多樣性的否定,也不是要抑制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和漢語(yǔ)方言。恰恰相反,從單語(yǔ)主義走向多語(yǔ)主義[18]以及雙語(yǔ)雙言社會(huì)的構(gòu)建[19-21],不僅具有理論和實(shí)踐的雙重價(jià)值,而且可以使通用語(yǔ)的傳播和推廣與語(yǔ)言/方言多樣性這二者和諧共存。二是在提升全民特別是貧困地區(qū)民眾普通話水平的同時(shí),貧困地區(qū)的干部也應(yīng)該學(xué)習(xí)一些當(dāng)?shù)氐纳贁?shù)民族語(yǔ)言或方言。“同說(shuō)方言土語(yǔ),能夠讓扶貧干部和貧困群眾更好地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所以,扶貧干部要用好土話,在用土話和貧困群眾溝通交流的過(guò)程中,拉近與貧困群眾的關(guān)系,贏得群眾的支持和信任。”[22]三是統(tǒng)一的語(yǔ)言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并不是簡(jiǎn)單的線性關(guān)系,而是一種概率性關(guān)系。即較低的通用語(yǔ)言能力并不一定必然導(dǎo)致貧困,否則就無(wú)法解釋有些方言集中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也很發(fā)達(dá)的事實(shí);但是對(duì)于貧困地區(qū)、貧困家庭來(lái)說(shuō),他們的通用語(yǔ)言能力往往是較低或沒(méi)有的,而提升他們的通用語(yǔ)能力則有助于他們走出貧困。
五、提升普通話能力助力脫貧攻堅(jiān)
如果上文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增強(qiáng)貧困地區(qū)的普通話推廣力度、提升貧困地區(qū)人們的普通話水平就是語(yǔ)言扶貧的核心內(nèi)涵,對(duì)于扶貧—脫貧方略的實(shí)現(xiàn)和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就具有著重要作用。
(一)提升普通話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國(guó)還有30%即四億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話交流,尤其是在農(nóng)村、邊遠(yuǎn)地區(qū)和民族地區(qū)。國(guó)務(wù)院扶貧辦黨組書(shū)記、主任劉永富在談到貧困地區(qū)脫貧的難點(diǎn)之時(shí)就指出:“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人不會(huì)說(shuō)普通話,他如果出來(lái)打工,或者是到內(nèi)地做一些什么事情,交流有難度。”顯然這一論斷也是適用于漢語(yǔ)方言區(qū)等其他貧困地區(qū)的。此外,“普通話的推廣有利于降低溝通交流中的不確定性,促進(jìn)知識(shí)和技術(shù)的傳播,容易形成團(tuán)隊(duì)合作,擴(kuò)大創(chuàng)業(yè)者之間的‘學(xué)習(xí)效應(yīng)’,推動(dòng)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23]。大量研究表明:(1)語(yǔ)言上的差異往往會(huì)阻礙勞動(dòng)力在市場(chǎng)中的流動(dòng);(2)在一國(guó)內(nèi)部,會(huì)說(shuō)通用語(yǔ)者比只會(huì)說(shuō)本族語(yǔ)者收入要高;(3)雙語(yǔ)教育與經(jīng)濟(jì)收入之間基本呈正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24-27]。其中,Tang等[27]的一份研究就指出,中外學(xué)者普遍認(rèn)為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滯后是因?yàn)槠浣逃降臏螅亲髡邆兺ㄟ^(guò)《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動(dòng)態(tài)調(diào)查》等大量第一手?jǐn)?shù)據(jù)證明: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維、藏)與漢族的教育水平相差無(wú)幾,而影響少數(shù)民族就業(yè)和收入機(jī)會(huì)的更重要原因是普通話能力的薄弱。因此,改善民族平等的先決條件之一是普通話在少數(shù)民族群體中的推廣與普及。為了促進(jì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應(yīng)當(dāng)強(qiáng)化漢語(yǔ)教學(xué)。許多學(xué)者也都指出,“重視民族語(yǔ)文,抓好雙語(yǔ)教育,在社會(huì)掃盲、普及文化、提高普及義務(wù)教育效果方面十分顯著”[19]。雙語(yǔ)教學(xué)在提高民族地區(qū)的文化水平、促進(jìn)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20]。況且,用普通話扶貧,用扶貧推廣普通話,不僅具有重要的經(jīng)濟(jì)意義,而且具有深遠(yuǎn)的政治意義[28]。因此,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貧困地區(qū)來(lái)說(shuō),提高普通話的普及率,提升當(dāng)?shù)厝藗兊钠胀ㄔ捤剑瑢?shí)施語(yǔ)言文字精準(zhǔn)扶貧的策略,將非常有助于當(dāng)?shù)胤鲐殹撠毠ぷ鞯拈_(kāi)展以及扶貧—脫貧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特別是在奮力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新形勢(shì)下,掌握普通話已經(jīng)成為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一種重要能力,對(duì)于其脫貧致富具有重要意義[29]。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對(duì)于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該施行何種語(yǔ)言教育政策這一議題,筆者更傾向于在綜合考慮當(dāng)?shù)貛熧Y力量、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語(yǔ)言的資源性、語(yǔ)言的身份認(rèn)同性等參項(xiàng)的基礎(chǔ)上,采用分階段教學(xué)的策略,即初級(jí)階段的教學(xué)可以使用少數(shù)民族的母語(yǔ),隨著教學(xué)階段的提升,逐漸過(guò)渡到母語(yǔ)和普通話的雙語(yǔ)教學(xué),而似乎不宜采用所有學(xué)習(xí)階段的教學(xué)語(yǔ)言都是普通話的“一刀切式”策略。構(gòu)建和諧的雙語(yǔ)雙言/多語(yǔ)多言社會(huì),應(yīng)該是理論與實(shí)踐上的指向所在。對(duì)于漢語(yǔ)方言區(qū)的特困地區(qū)來(lái)說(shuō),加大普通話推廣力度,提升當(dāng)?shù)厝说钠胀ㄔ捤酵瑯泳哂谢A(chǔ)性作用。因?yàn)榉窖圆町悤?huì)阻礙勞動(dòng)力的市場(chǎng)流動(dòng),只會(huì)說(shuō)方言者的經(jīng)濟(jì)收入也往往要比會(huì)說(shuō)通用語(yǔ)者要低[12,30-3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說(shuō)一推廣普通話就能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是有個(gè)普及程度的問(wèn)題。比如卞成林等[33]以廣西2011—2015年普通話普及率、人口增長(zhǎng)率、固定資產(chǎn)投資率、貿(mào)易依存度等數(shù)據(jù)為樣本,得出結(jié)論認(rèn)為廣西普通話普及率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之間存在二次曲線關(guān)系,普通話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規(guī)模,且廣西這一最低有效規(guī)模為60%—63.8%。即要使普通話推廣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產(chǎn)生正面效應(yīng),就必須保證普通話普及率大于60%。這一研究具有很強(qiáng)的啟示價(jià)值。多次強(qiáng)調(diào)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jié)合。扶志就是從思想觀念、信心毅力和志氣勇氣方面幫助被幫扶者;扶智就是從文化水平、知識(shí)素養(yǎng)、智慧能力方面幫助被幫扶者。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普及攻堅(jiān)工程實(shí)施方案》中提出的“強(qiáng)國(guó)必先強(qiáng)語(yǔ),強(qiáng)語(yǔ)助力強(qiáng)國(guó)”“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yīng)先通語(yǔ)”的方針策略是必要而恰當(dāng)?shù)摹?/p>
(二)提升普通話能力助力脫貧攻堅(jiān)的實(shí)例在實(shí)際扶貧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就將掌握普通話作為一個(gè)重要的扶貧手段,比如云南瀘西縣白水鎮(zhèn)全鎮(zhèn)已經(jīng)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普通話培訓(xùn)列為精準(zhǔn)扶貧的一大舉措,為暢通語(yǔ)言交流搭建平臺(tái)。由專業(yè)教師長(zhǎng)期擔(dān)任教學(xué)和輔導(dǎo)工作,開(kāi)展各種培訓(xùn)學(xué)習(xí),通過(guò)“走出去,請(qǐng)進(jìn)來(lái)”的方式,讓普通話在少數(shù)民族村寨推廣開(kāi)來(lái),消除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交流障礙,實(shí)現(xiàn)與外界語(yǔ)言、文化、思想的融合,促進(jìn)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發(fā)展,以精準(zhǔn)教育助力脫貧攻堅(jiān)。四川涼山州則通過(guò)教習(xí)普通話,加強(qiáng)技能培訓(xùn),來(lái)幫助貧困群眾增長(zhǎng)見(jiàn)識(shí)、增加知識(shí),掌握脫貧致富的方法與技巧,獲得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能力和勇氣。甘肅省教育廳則圍繞語(yǔ)言文字精準(zhǔn)扶貧,提出了“一抓兩促三支撐”工作思路,以此提升農(nóng)村普通話水平。正如郭龍生所指出的:“將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普通話的推廣程度納入貧困縣脫貧考核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之中,必然會(huì)有效促進(jìn)語(yǔ)言文字的精準(zhǔn)扶貧,也會(huì)有利于盡快提升貧困地區(qū)的社會(huì)文化程度,從而在經(jīng)濟(jì)脫貧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教育脫貧、文化脫貧,達(dá)到最終‘脫真貧’和‘真脫貧’的目標(biāo)。”[34]
(三)提升普通話能力的措施提升貧困地區(qū)人民的普通話水平和能力,可以至少在以下幾個(gè)方面用力[28-29,34-36]:1.在民族地區(qū)實(shí)行“雙語(yǔ)教育”的同時(shí),加強(qiáng)幼兒園、小學(xué)階段的普通話教學(xué),讓普通話成為人們的日常使用語(yǔ)言,同時(shí)增進(jìn)教師的普通話培訓(xùn)和能力水平。2.結(jié)合當(dāng)?shù)禺a(chǎn)業(yè)發(fā)展的需求,在農(nóng)村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體系中增加或強(qiáng)化對(duì)不具備普通話溝通能力的青壯年的專項(xiàng)培訓(xùn)的內(nèi)容。3.外來(lái)務(wù)工人口較多的城市將外來(lái)常住人口納入本地語(yǔ)言文字工作范圍,將普通話培訓(xùn)納入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4.參加扶貧對(duì)口支援工作的省市和企業(yè),將推廣學(xué)習(xí)普通話列入援助計(jì)劃,提高受援地方青壯年與社會(huì)交流、自主就業(yè)的能力。5.廣播電視是人們學(xué)習(xí)普通話的重要途徑,借助廣播電視“戶戶通”推進(jìn)普及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6.開(kāi)發(fā)定向教材,開(kāi)展推普周定向支持。2018年5月,教育部、國(guó)家語(yǔ)委在京2017年中國(guó)語(yǔ)言文字事業(yè)發(fā)展?fàn)顩r,教育部語(yǔ)用司、語(yǔ)信司司長(zhǎng)田立新談及語(yǔ)言扶貧過(guò)程中采取的相關(guān)舉措時(shí)就提到:為了更好地指導(dǎo)農(nóng)村和民族地區(qū)學(xué)習(xí)普通話,6月將出版教材《千句普通話溝通你我心》;將在第21屆推普周活動(dòng)中,在11個(gè)西部省區(qū)對(duì)30個(gè)國(guó)家級(jí)貧困縣給予重要支持。7.開(kāi)發(fā)語(yǔ)言文化資源,抓好重點(diǎn)活動(dòng)。有計(jì)劃地進(jìn)行貧困地區(qū)語(yǔ)言文化資源的整理、整合、轉(zhuǎn)化和利用,開(kāi)發(fā)貧困地區(qū)語(yǔ)言文化產(chǎn)業(yè)以及人文旅游,推動(dòng)貧困地區(qū)語(yǔ)言文化資源的可持續(xù)性價(jià)值轉(zhuǎn)換。開(kāi)展與普通話相關(guān)的重點(diǎn)活動(dòng)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貧困地區(qū)民眾學(xué)習(xí)普通話的熱情,比如定期舉辦經(jīng)典誦讀、演講、講故事等語(yǔ)言活動(dòng)。8.構(gòu)建語(yǔ)言扶貧志愿者服務(wù)制度。可以嘗試有計(jì)劃地組織大學(xué)生和研究生開(kāi)展到村、到戶、到人的跟蹤滾動(dòng)式語(yǔ)言志愿者服務(wù)。同時(shí)依托在線語(yǔ)言服務(wù)平臺(tái),把面對(duì)面服務(wù)和遠(yuǎn)程在線服務(wù)相結(jié)合,形成立體長(zhǎng)效的語(yǔ)言志愿者服務(wù)體系。
六、結(jié)語(yǔ)
貧困問(wèn)題是一個(gè)世界性問(wèn)題,不管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發(fā)展中國(guó)家還是貧窮國(guó)家,都面臨此問(wèn)題。貧困問(wèn)題是一個(gè)涉及到許多方面的系統(tǒng)問(wèn)題,比如收入、食物、教育、醫(yī)療等。貧困問(wèn)題的解決無(wú)疑需要多維路徑、多方努力,而語(yǔ)言就應(yīng)該是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決策中,語(yǔ)言因素往往因其“大隱隱于市”而被人習(xí)焉不察。但是在許多情形下,語(yǔ)言因素卻往往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邊緣性和脆弱性的癥結(jié)之一。就扶貧—脫貧方略來(lái)說(shuō),處理好各種語(yǔ)言問(wèn)題,利用好語(yǔ)言因素的積極作用,以語(yǔ)言文字精準(zhǔn)扶貧為重點(diǎn)提升貧困地區(qū)的普通話水平,無(wú)疑會(huì)幫助相關(guān)部門和組織在實(shí)際項(xiàng)目中減少貧困。語(yǔ)言文字精準(zhǔn)扶貧是“真脫貧”“脫真貧”的核心途徑之一,因?yàn)椤巴ㄕZ(yǔ)是脫貧攻堅(jiān)的治本之策”[37],“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有的貧困勞動(dòng)力進(jìn)行語(yǔ)言扶貧,有助于提高他們戰(zhàn)勝貧困的能力,也有助于培養(yǎng)他們永久脫貧的能力;通過(guò)對(duì)貧困地區(qū)和貧困家庭的中小學(xué)生進(jìn)行語(yǔ)言扶貧,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強(qiáng)的生存和發(fā)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陷入貧困的人文誘因”[35]。語(yǔ)言扶貧必將助力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要發(fā)揮好語(yǔ)言因素的作用,就需要有一些合理而系統(tǒng)的語(yǔ)言規(guī)劃,比如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的進(jìn)一步推廣、合理而有效的雙語(yǔ)教育政策等。一個(gè)好的語(yǔ)言規(guī)劃,對(duì)于貧困的減少甚至消除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38]。對(duì)于貧困地區(qū)來(lái)說(shuō),好的語(yǔ)言規(guī)劃可以在消除絕對(duì)貧困和饑餓、接受基本教育、減少嬰兒夭折、孕婦健康、減少傳染疾病等方面都有積極作用[39]。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考察顯然是初步的、嘗試性的。在“語(yǔ)言與貧困的關(guān)系”這一大議題之下,在國(guó)家“脫貧—扶貧”這一大背景下,還有許多問(wèn)題尚待探討,比如貧困對(duì)于貧困地區(qū)兒童語(yǔ)言能力的影響[40-41],語(yǔ)言因素在教育、醫(yī)療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作用[42],等等。此外,要真正了解和發(fā)揮語(yǔ)言因素在國(guó)家脫貧—扶貧方略中的作用,還需要大量的實(shí)地調(diào)研和考察。這些應(yīng)該就是下一步亟待研究的議題。
作者:王春輝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