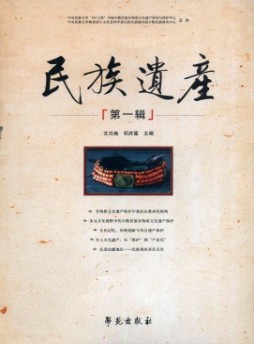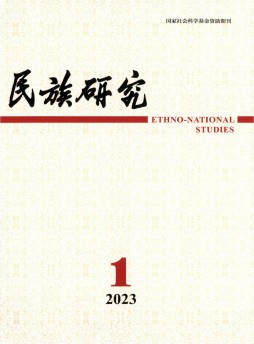民族史研究的反思與重構(gòu)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民族史研究的反思與重構(gòu)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西民族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的微觀視角
由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決定,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方向不僅有宏觀的理論,還有微觀的實(shí)踐。也正是因?yàn)楹暧^與微觀、理論與視角的互相補(bǔ)充,才推進(jìn)了包括當(dāng)代民族史在內(nèi)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發(fā)展。而這些微觀視角又不屬于某一固定學(xué)科,其為眾多學(xué)科所共享。這里主要談及與當(dāng)代民族史相關(guān)的話語—權(quán)力、日常生活史、口述史、過程—事件和民族國家認(rèn)同。
(一)話語-權(quán)力話語-權(quán)力理論源于結(jié)構(gòu)主義以來對(duì)知識(shí)本身的持續(xù)反思,福柯將其發(fā)展成為一套理論體系,并對(duì)“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表達(dá)與實(shí)踐就是在其影響下對(duì)底層社會(huì)領(lǐng)域的拓展和延伸。比如在的研究中,張小軍從土地的象征資本化、劃階級(jí)的象征權(quán)力、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象征資本生產(chǎn)和鄉(xiāng)民階級(jí)習(xí)性四個(gè)角度,探討了“階級(jí)”生產(chǎn)中不同資本之間相互轉(zhuǎn)換和象征資本再生產(chǎn)的邏輯,指出象征資本理論對(duì)理解中國社會(huì)的重要意義。[3]李放春認(rèn)為“革命”與“生產(chǎn)”是有著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的話語和歷史實(shí)踐,其中的關(guān)系并非協(xié)調(diào)一致,而是充滿緊張、錯(cuò)位乃至“斗爭(zhēng)”,這一關(guān)聯(lián)所蘊(yùn)含的結(jié)構(gòu)化張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革命現(xiàn)代性的實(shí)踐形態(tài)。[4]在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同樣可以采用話語—權(quán)力分析。比如在分析民族識(shí)別的過程中,就需要考慮到話語權(quán)力的傾斜性;在研究民主改革的過程中,就需要考察話語權(quán)力的妥協(xié)和讓步;在考察民族救助的過程中,就需要考察話語-權(quán)力的作用。實(shí)際上,目前在鄉(xiāng)村史研究中使用比較廣泛的“國家—社會(huì)”視角就是話語-權(quán)力的發(fā)展和變異。國家權(quán)力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啟動(dòng)和最初運(yùn)轉(zhuǎn)中扮演了指揮、管理的重要角色。國家政策的推行過程,也就是國家權(quán)力從中央到基層得到強(qiáng)化的過程。[5]
(二)日常生活史何為日常生活?雷頤認(rèn)為,“所謂‘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識(shí)’為基礎(chǔ),不過‘常識(shí)’因太平常、普通而常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們往往不顧常識(shí)地要壓制甚至消滅(如有可能)‘日常生活’。”[6]匈牙利哲學(xué)家阿格妮絲•赫勒總結(jié)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即重復(fù)性、自在性、經(jīng)驗(yàn)性和實(shí)用性。[7]而日常生活史就是研究普通民眾的日常消費(fèi)、交往、觀念活動(dòng)。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經(jīng)成為底層社會(huì)重要的研究視角,為多學(xué)科研究者所重視。美國學(xué)者懷特認(rèn)為,“要理解驚人的事件,就必須聯(lián)系日常的生活模式來認(rèn)識(shí)它。”[8]7黃宗智特別強(qiáng)調(diào),到最基本的事實(shí)中去尋找最強(qiáng)有力的分析。[9]孫立平也認(rèn)為,“我們對(duì)日常生活的強(qiáng)調(diào)……不是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個(gè)完全自主的領(lǐng)域,而是看作普通人與國家相遇和互動(dòng)的舞臺(tái)。因此,我們……強(qiáng)調(diào)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的均衡和整合。”[10]在研究當(dāng)代民族史中,需要將此視角應(yīng)用其中,這種視角在考察鄉(xiāng)村社會(huì)時(shí),重視研究對(duì)象的微觀化,采取“目光向下”的觀察角度,它的研究對(duì)象包括吃、穿、住、行等各個(gè)方面,并且強(qiáng)調(diào)在研究的過程中采用“他者”立場(chǎng)。①比如在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民族宗教文化異同的過程中,就需要考察新中國成立前后日常生活變化與宗教文化的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只有通過對(duì)民族地區(qū)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才能從現(xiàn)象的背后尋找到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原有的規(guī)范、限制與約束;研究者也只有關(guān)注“小人物”的生活和事件背后的故事,從“走向民間”、“走向民族”角度,才能細(xì)致地考察民族地區(qū)社會(huì)的基本情況。
(三)新革命史以往革命史的研究取向是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鏈接,不可否認(rèn)這種研究方法所表現(xiàn)的歷史變遷及其研究價(jià)值。不過,歷史所承載的并不僅僅是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它還包含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豐富的內(nèi)容,論者甚至認(rèn)為這種研究方法存在“思維陳舊的簡(jiǎn)單化傾向,即沿襲著革命歷史書寫的傳統(tǒng)革命范式,更準(zhǔn)確地說是黨派史觀的范式。”[12]周錫瑞也認(rèn)為,在革命史的研究中,大陸學(xué)者的“分析術(shù)語和思維方式都和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文獻(xiàn)十分接近。”[13]538在具體書寫過程中,革命史就表現(xiàn)為單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shù)民族上層到北京及內(nèi)地大城市觀光的事件,多數(shù)教科書都表述為中共中央決定出此政策后,少數(shù)民族上層人士就歡欣鼓舞,紛紛表示對(duì)國家和政黨的認(rèn)同。實(shí)際上,其中的過程十分復(fù)雜:首先是民族上層人士的代表人選,不能沒有代表性,也不能是完全的反對(duì)派。很多少數(shù)民族上層人士由于過深的顧慮,不愿意離開他所熟悉的勢(shì)力范圍,這也給邀請(qǐng)他們外出觀光增加了難度。其次是在觀光過程中,接待人員要做細(xì)致的工作,爭(zhēng)取在觀光途中實(shí)現(xiàn)上層人士思想的轉(zhuǎn)變。最后是觀光這種思想教育的效果,隨后進(jìn)行的民主改革就是很好的實(shí)踐證明。詳細(xì)地分析少數(shù)民族的觀光團(tuán),我們發(fā)現(xiàn)歷史的事實(shí)要遠(yuǎn)比“政權(quán)演變、民眾接受、革命積極性提高”這三部曲復(fù)雜得多,傳統(tǒng)的“政策—效果”模式往往掩蓋了歷史事件的復(fù)雜、曲折、艱難與痛苦。從表面上看,這種真實(shí)往往不是完美的,但這種艱苦探索才能襯托出中國革命的光輝,也正因?yàn)槿绱藦?fù)雜的博弈過程,才能彰顯中共政權(quán)力量的強(qiáng)大,這就是“新革命史”。如何來實(shí)現(xiàn)這種“新革命史”的書寫呢?實(shí)際上就是探求歷史原本的復(fù)雜敘事,從原本的靜態(tài)的宏觀和微觀政策分析轉(zhuǎn)變?yōu)閯?dòng)態(tài)的政策實(shí)踐,考察事件背后的邏輯和原有的真實(shí)。在這方面,海外已經(jīng)擁有了諸如《中國鄉(xiāng)村:社會(huì)主義國家》[14]、《地主、農(nóng)民、共產(chǎn)黨:社會(huì)博弈論的分析》[15]等具有相當(dāng)代表性的成果。當(dāng)然,國內(nèi)的郭于華、李金錚、張佩國等也開始在此方面做出探索,甚至一批年輕研究者也涉入其中。相信“新革命史”的研究視角可以在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中嶄露頭角。
(四)過程—事件在底層社會(huì)的研究中,由于受科學(xué)主義為核心思想的結(jié)構(gòu)化文本表述的影響,研究者在展示和還原經(jīng)驗(yàn)的復(fù)雜性時(shí)常遭遇方法論的局限,使得我們還在有意無意地講述“規(guī)范的故事”[16]598。人類學(xué)民族志敘事文本和作為研究立場(chǎng)而凸顯的“地方性知識(shí)”視角的引入,無疑對(duì)結(jié)構(gòu)化方法與田野經(jīng)驗(yàn)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推動(dòng)作用。由此,在對(duì)鄉(xiāng)村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學(xué)界有意識(shí)地將經(jīng)驗(yàn)分析方法由結(jié)構(gòu)分析轉(zhuǎn)向故事敘事。近年,《林村的故事》和《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都是屬于這種類型的故事敘事。孫立平更加注重動(dòng)態(tài)研究,將此類方法總結(jié)為“過程—事件”分析。在這里,過程本身已經(jīng)成為一種獨(dú)立的解釋變項(xiàng)和解釋源泉,也成了對(duì)社會(huì)事實(shí)本身的一種新的假設(shè),即對(duì)作為社會(huì)事實(shí)而存在的動(dòng)態(tài)的過程-事件中去尋找靜態(tài)結(jié)構(gòu)中無法顯現(xiàn)的因素與出人意料的變化,去探求過程本身對(duì)影響事件走向和結(jié)果的不可預(yù)知和把握的作用。因此,要求將研究對(duì)象的呈現(xiàn)由一種結(jié)構(gòu)化表述轉(zhuǎn)化為一種故事文本的敘事,在對(duì)這一故事的本身表述性建構(gòu)中去建立起理解和分析,在動(dòng)態(tài)的、歷時(shí)性的情景呈現(xiàn)中去把握研究對(duì)象之復(fù)雜的、隨機(jī)的和充滿偶然的因果序列。[17]這一點(diǎn)正好也可以嘗試去應(yīng)用到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quán)面對(duì)民族地區(qū)復(fù)雜的局面,所采取的多種政策,雖然目前還未能有細(xì)致的了解,但也可以嘗試去利用“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去還原民族地區(qū)歷史本來的真相。
(五)民族國家認(rèn)同由于社會(huì)成員隸屬于不同的社會(huì)組織和群體,繼而擁有多種身份和角色,由此決定了社會(huì)成員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的差異。在傳統(tǒng)社會(huì),“皇權(quán)不下鄉(xiāng)”,國家權(quán)力對(duì)基層社會(huì)的控制力有限,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還很難產(chǎn)生尖銳的矛盾。而進(jìn)入民族國家時(shí)代后,其特征是“內(nèi)部的行政調(diào)解依賴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監(jiān)控并具有國際行政的條件”。[18]4這樣,社會(huì)成員的心理和行為層面都將發(fā)生顯著變化,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的沖突在所難免。加拿大學(xué)者威爾•金里卡在談到兩者的關(guān)系時(shí)認(rèn)為,少數(shù)群體向國家發(fā)動(dòng)挑戰(zhàn)的背后是國家對(duì)少數(shù)群體的施壓。少數(shù)民族一旦認(rèn)為他們的利益無法在現(xiàn)存國家中得到安排,他們就會(huì)考慮分離,從而威脅到國家的統(tǒng)一,因而國家需要調(diào)適民族文化差異,在協(xié)商之中實(shí)現(xiàn)和諧共生。[19]2,90實(shí)際上,這就是實(shí)踐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的統(tǒng)一。圍繞兩者的關(guān)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rèn)知。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的矛盾和張力成為蘇聯(lián)解體后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興起背景下的一種主要論調(diào),他們認(rèn)為民族的自我意識(shí)及其對(duì)現(xiàn)有國家統(tǒng)治的不認(rèn)同往往會(huì)導(dǎo)致民族獨(dú)立運(yùn)動(dòng),尤其是跨境民族中有些人在國家觀念與民族觀念發(fā)生沖突時(shí),民族觀念往往超過國家觀念。[20][21]9因而周平提出,要淡化族際界限,采取區(qū)域主義的邊疆治理方式來促進(jìn)族際政治整合,加強(qiáng)公民的國家認(rèn)同。[22-23]其實(shí),在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對(duì)立沖突的過程中,也有和諧共生的一面。費(fèi)孝通曾指出,“中華民族是56個(gè)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體,中華民族是高層,56個(gè)民族是基層。高層次的認(rèn)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rèn)同,不同層次的認(rèn)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rèn)同基礎(chǔ)上可以各自發(fā)展原有的特點(diǎn),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24]163當(dāng)代民族關(guān)系就是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相融合的代表,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政權(quán)采取了多項(xiàng)促進(jìn)民族關(guān)系的措施,都可以看作是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實(shí)踐共生的重要路徑。因而民族國家認(rèn)同也可以成為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視角。
二、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的科學(xué)方法
對(duì)于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方法顯得尤為重要,科學(xué)的方法有助于我們認(rèn)識(shí)事物的本質(zhì)。在唯物史觀中,分析、比較、綜合都是較為常用的具體方法。不過,除了這樣的基本方法外,近年來歷史學(xué)界已經(jīng)將自身的研究與社會(huì)學(xué)的調(diào)查訪談、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計(jì)量、心理學(xué)的心態(tài)分析聯(lián)系起來,進(jìn)而產(chǎn)生了自己獨(dú)特的研究方法,這里主要介紹口述史學(xué)、計(jì)量史學(xué)和心態(tài)史學(xué)。
(一)口述史學(xué)對(duì)口述史與微觀村落的考察,已引起了國內(nèi)外學(xué)者的普遍關(guān)注。海外較早訪問革命根據(jù)地或在當(dāng)?shù)厣钸^的海外新聞?dòng)浾吆陀^察家,如韓丁、克魯克夫婦、貝爾登等都有相關(guān)著作傳世。韓丁的《深翻》和《翻身》,以親歷者的角度對(duì)山西張莊的和共產(chǎn)黨的實(shí)踐進(jìn)行了高度評(píng)價(jià)。[25-26]克魯克夫婦的《十里店》(2)是作者作為觀察員采訪河北十里店村復(fù)查和整黨運(yùn)動(dòng)的紀(jì)實(shí)性作品,該書勾畫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復(fù)雜的事件和動(dòng)態(tài)的歷史過程。[27]由此得出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觀點(diǎn)和論調(diào),比如談及租佃制度與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時(shí),珀金斯就認(rèn)為,“土地的再分配就不一定會(huì)提高生產(chǎn)力”[28]140;馬若孟也認(rèn)為,“與其說是促進(jìn)不如說是阻礙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力和產(chǎn)出的增長”。[29]2弗里曼等人也持相同的觀點(diǎn),不但沒有解放農(nóng)民,給貧困農(nóng)民以權(quán)力,而是使“最具報(bào)復(fù)心理的人變成村里新的掌權(quán)者”。[14]376這些結(jié)論的產(chǎn)生大都源于口述史資料的收集。在國內(nèi)學(xué)界,較早關(guān)注口述史和微觀村落的是北京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系,他們對(duì)20世紀(jì)下半期農(nóng)村社會(huì)生活口述資料的收集,主要是陜北的驥村和河北的西村,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李康的《西村十五年》[30],李放春的《歷史、命運(yùn)與分化的心靈》[31]等。目前,雖然民族學(xué)研究已經(jīng)廣泛使用這種口述史與微觀村落的視角,但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還比較欠缺。實(shí)際上,利用口述資料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bǔ)文獻(xiàn)資料的不足,甚至可以改正文獻(xiàn)資料中錯(cuò)誤的部分,尤其是目前在民族地區(qū)普遍使用普通話的前提下,口述資料的收集難度要遠(yuǎn)遠(yuǎn)小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少數(shù)民族社會(huì)歷史調(diào)查。
(二)計(jì)量史學(xué)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折就是計(jì)量史學(xué)的出現(xiàn),從而為歷史學(xué)追求“科學(xué)化的歷史”[32]10發(fā)展注入了一種嶄新的方法。美國歷史學(xué)家貝林曾認(rèn)為,計(jì)量歷史學(xué)研究為隱而不見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shí)開拓了道路,構(gòu)成了對(duì)現(xiàn)代史學(xué)的一大挑戰(zhàn)。[33]386-423巴勒克拉夫更直言道,現(xiàn)代西方史學(xué)的突出特征就是“計(jì)量革命”。[34]131可以說,計(jì)量史學(xué)的出現(xiàn)為歷史學(xué)開辟了新的領(lǐng)域。計(jì)量史學(xué)最初應(yīng)用到經(jīng)濟(jì)史領(lǐng)域中,進(jìn)而形成了新經(jīng)濟(jì)史。隨后,計(jì)量研究引入到政治史研究中,并形成了新政治史,比如大眾選舉問題、政黨體制演變問題、精英問題等。計(jì)量史學(xué)后又引入到社會(huì)史,更所謂的五花八門,從而將家庭、種族群體、職業(yè)團(tuán)體、移民、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轉(zhuǎn)變?yōu)閷W(xué)者的研究重點(diǎn)。由此看來,以計(jì)量研究為標(biāo)準(zhǔn)的史學(xué)研究從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到經(jīng)驗(yàn)分析,再到歷史敘事,計(jì)量史學(xué)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將計(jì)量史學(xué)應(yīng)用到當(dāng)代民族史中。在基層政權(quán)的建設(shè)中,可以利用計(jì)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區(qū)政權(quán)建設(shè)的規(guī)模和績效;在社會(huì)制度的變革中,可以利用計(jì)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區(qū)制度變革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在社會(huì)治理的測(cè)量中,可以利用計(jì)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區(qū)社會(huì)治理的實(shí)際效果。應(yīng)該說,隨著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的進(jìn)一步推進(jìn),會(huì)出現(xiàn)更多的將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信息理論和數(shù)學(xué)應(yīng)用到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通過資料的處理和學(xué)理模型的制作,可以將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引向深入。
(三)心態(tài)史學(xué)心態(tài)史學(xué)也被稱為心態(tài)史,是專門研究歷史上群體心態(tài)結(jié)構(gòu)及其演變過程和趨勢(shì)的新興史學(xué)分支。法國年鑒學(xué)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認(rèn)為,心態(tài)就是集體心理,即“人們,一個(gè)特定的人們集團(tuán)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的方法,后被年鑒學(xué)派廣泛應(yīng)用于歷史研究之中。[35]273目前,心態(tài)史學(xué)已經(jīng)突破了群體的限制,個(gè)體心理研究也被廣泛應(yīng)用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因此,心態(tài)史學(xué)是應(yīng)用現(xiàn)代心理學(xué)和精神分析學(xué)的理論、方法、手段,通過對(duì)歷史人物的個(gè)體和群體的心理活動(dòng)及特征的分析,對(duì)歷史現(xiàn)象做出解釋和研究的方法。心態(tài)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貢獻(xiàn)就是深化和擴(kuò)大了歷史學(xué)家對(duì)歷史的認(rèn)識(shí),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往歷史學(xué)研究“無人歷史”的傾向,使得人的精神活動(dòng)的研究得到了應(yīng)有的重視。在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心態(tài)史學(xué)涉及社會(huì)文化等一系列基本層面的問題,包括民族地區(qū)民眾對(duì)生活、死亡、愛情、性、家庭、宗教、政權(quán)等諸多問題的認(rèn)識(shí),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地區(qū)處于急劇的變動(dòng)和轉(zhuǎn)型階段,這種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就更加明顯,作為研究對(duì)象也就更加有意義。比如在死亡史的研究中,死亡史與民族地區(qū)的宗教史、民族文化史、民俗史、社會(huì)史等形成交叉學(xué)科,從而使得死亡史研究成為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可行對(duì)象。不過,目前中國對(duì)心態(tài)史學(xué)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duì)外學(xué)術(shù)交流的深入,美國的精神分析和法國的心態(tài)史學(xué)的基本方法得以傳入,但正在稱得上具有相當(dāng)學(xué)術(shù)影響力的成果還是西方翻譯過來的學(xué)術(shù)專著,比如美國哈佛大學(xué)孔飛力的《叫魂》,作者在書中研究了200多年前發(fā)生在中國的遍及12個(gè)省份的一場(chǎng)被稱為“叫魂”的妖術(shù)及其帶來的心理動(dòng)蕩,描述了關(guān)于這一事件的三個(gè)不同版本,并且這三個(gè)版本并不孤立,而是從不同的側(cè)面切入到同一個(gè)主體,實(shí)際上研究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權(quán)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制約。[36]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國內(nèi),特別是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就缺乏這種具有相當(dāng)學(xué)術(shù)影響力的心態(tài)史成果。
三、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反思
任何一種理論與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既有其存在的優(yōu)勢(sh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關(guān)鍵在于使用者的駕馭能力。對(duì)于上述的微觀視角和科學(xué)方法在當(dāng)代民族史的應(yīng)用,研究者應(yīng)該去整合以往的知識(shí),避免模式化、囫圇吞棗和極端化等傾向。模式化傾向。在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中,將其他學(xué)科的理論應(yīng)用于具體的問題研究中,可以給研究者提供一個(gè)解讀的視角,但是這種理論的應(yīng)用也容易走向模式化。模式研究,就是試圖通過運(yùn)用某一種理論模式概括當(dāng)代民族史的一般規(guī)律,進(jìn)而解釋普遍的現(xiàn)象,描述事務(wù)發(fā)展的基本進(jìn)程,甚至預(yù)設(shè)必然的發(fā)展方向。[37]顯然,這種模式極端化的弊端非常明顯,容易使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對(duì)象教條化,使復(fù)雜的問題變得簡(jiǎn)單化。比如在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地區(qū)剿匪的過程中,如果使用單線條的“沖擊—回應(yīng)”模式,就會(huì)使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剿匪缺乏復(fù)雜感和真實(shí)感,使得原本包括眾多類型的匪類應(yīng)有不同的價(jià)值取向,變得簡(jiǎn)單化。囫圇吞棗傾向。中國目前的社會(huì)學(xué)、政治學(xué)、生態(tài)學(xué)理論大多是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社會(huì)傳入的結(jié)果,是西方學(xué)者根據(jù)本國的國情總結(jié)出來的解釋框架和建構(gòu)體系,我們將其拿來使用時(shí),要注意其實(shí)用性。比如權(quán)力話語分析的視角,新中國成立前后少數(shù)民族上層在國家的感召下,可能在情感的認(rèn)同上大于利益的認(rèn)同,或者處于某些信仰的問題而放棄利益,這會(huì)使得一些研究者質(zhì)疑情感和利益之間的關(guān)系。實(shí)際上,權(quán)力話語分析視角下情感和利益的關(guān)系十分復(fù)雜,不同的群眾有不同的表現(xiàn),外部的條件和內(nèi)部的因素都可能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應(yīng)具體審視。同時(shí),大量的研究者,尤其是初學(xué)者,容易囫圇吞棗地將理論套用于當(dāng)代民族史的研究對(duì)象之上,并沒有徹底理解,甚至一知半解,容易造成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誤讀。極端化傾向。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始終屬于民族學(xué)和歷史學(xué)范疇,資料的整理與收集、解讀與建構(gòu)始終是史學(xué)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而不能將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過度理論化。上文在談及計(jì)量史學(xué)的應(yīng)用中,就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因?yàn)橛?jì)量的結(jié)果“無法由任何方法來檢驗(yàn),因?yàn)槠滟Y料深埋在私人電腦中,而非暴露在出版的腳注中,無法讓人按圖索驥。無論何如,這些史料往往以數(shù)學(xué)深?yuàn)W的形成表示,對(duì)大多數(shù)的史學(xué)家來說都是無法讀懂的。”[32]10因此,不能將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作為政治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生態(tài)學(xué)的純理論問題來進(jìn)行思考,避免當(dāng)代民族史研究走向理論的極端化。
作者:李飛龍單位: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貴州社會(huì)建設(shè)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