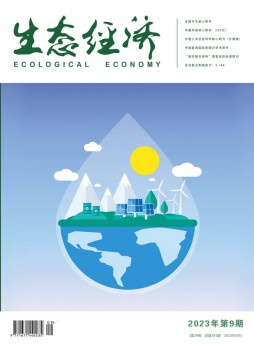生態與美學的交織互動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生態與美學的交織互動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以西方工業化發展進程為背景,探討景觀生態設計思想的發展演變和審美變革。在后工業時代和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之下,風景園林領域生態思想發展和演進所形成的理論和概念逐漸融合了生態和美學、精英藝術和大眾審美的二元對立,并促進了更具生態性和審美價值的創新景觀實踐項目的探索。文章分析評論的生態啟示設計和關注環境的先鋒藝術案例表明,社會需要多學科合作來強調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并通過景觀表現和審美體驗促進公眾的生態意識。文章最后提出,中國風景園林界應該打破學科藩籬,加強多學科合作,建立更具生態意識的景觀審美標準,通過景觀實踐促使公眾成為更具生態意識和知識的環境公民。
關鍵詞:風景園林;生態美學;關注
環境的藝術實踐風景園林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點,包含生態、美學和社會人文要素。從始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麥克哈格注重場址生態要素分析和技術處理的生態設計,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更加多元的設計思潮和實踐,生態和美學的論辯一直貫穿于各時期思潮過程之中。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生態議題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等多學科領域。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使得風景園林師在城市設計工作中起到更加重要和主導的作用。保護生態環境,設計展示場址的生態演進過程,重建和療愈被破壞的生態系統,以及處理更具體的雨水花園、屋頂綠化,等等,成為風景園林領域備受關注的實踐內容。風景園林已不再局限于如畫的景色或者建筑的襯景,它從地理概念延伸到社會、政治和生態相互聯系的系統概念,從強調視覺美感轉變為解決生態技術、強調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等綜合問題的解決。與此同時,一些先鋒藝術家參與到景觀和土地藝術實踐中,表達對于環境問題和人類未來的關注和警示。審美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非確定性、隨機性、混沌散亂等藝術表達形式對古典美學的詩意、秩序、純凈和精英化提出極大的挑戰。由于景觀具有多重含義,文章所涉及的“景觀”一詞,主要指人類能夠真實感知的具體的戶外空間組成。這些組成內容包括氣候、地形、土壤、動植物等自然因素,以及設施、構筑、人類活動及活動痕跡等人文因素[1]。景觀是風景園林實踐的對象,亦是風景園林實踐的結果。
1映射工業發展歷程的景觀生態設計思想演變
19世紀中后期,伴隨技術進步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帝國主義壟斷階段過渡。這一時期的工業文明主要表現在對自然掠奪式開發,對自然的生態價值缺少認識,自然逐漸破碎化。以英美為代表的工業先行發展國家的資本壟斷導致中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大批無地農民涌向城市,城市設施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在此背景之下,奧姆斯特德(Olmsted)、霍華德(Howard)、蓋迪斯(Geddes)、芒福德(Mumford)等從風景園林、田園城市、區域規劃等不同側面試圖解決工業城市的社會和環境問題。這一時期主要的生態設計思想體現在重建人和自然的聯系,并且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理想主義和實驗色彩。奧姆斯特德認為風景優美的公園具有精神激勵作用,同時能夠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具有疏解精神壓力、增加精神穩定的作用,把如畫的自然帶入城市是其設計的主要宗旨。精巧細膩,層次豐富,有如圖畫般的經過提煉的自然美,是奧姆斯特德設計風格的主要特征。霍華德在倫敦附近的萊契沃爾思(Letchworth)建造了第一座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田園城市,蓋迪斯將自己的優托幫(Eutopia)理想付諸在蘇格蘭丹佛姆林(Dunfermline)的規劃實踐之中[2]。這些先驅者們的理論和實踐開創了現代城市規劃的方法論和技術路線,前瞻性地警示工業文明、技術進步和人類福祉之間曲折迂回的關系。而奧姆斯特德的貢獻不僅在于創立了風景園林學科,還在于在這些城市規劃先驅所提倡的人與自然、城市與環境協同發展的生態思想框架之下,奠定了風景園林師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工業發達國家經歷著嚴重的環境問題。人類的生活環境遭到工業廢棄物的嚴重污染和破壞,工業廢水無序排放,殺蟲劑以及日化產品的廣泛應用,使河流湖泊海洋遭到污染。1962年R.卡遜(R.Carson)《寂靜的春天》出版,是戰后開啟世界范圍內環境保護運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該書嚴謹的科學理性精神和人文關懷不僅喚起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也促使各國政府起草出臺環境保護法律。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在公眾中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加。1969年麥克哈格的《設計結合自然》變革性地轉變了風景園林實踐,他提倡從生態科學中借鑒原理和規則并應用到設計項目中。其圖層疊加技術對設計場址的適應性分析為園林規劃和設計提供了科學的數據支持,他宣稱生態是命令而不僅是解釋,科學是園林設計唯一的權威[3]。在生態設計思潮影響下,美國院校一些園林專業更加關注環境管理、自然科學和生態修復技術,而對于視覺藝術、設計理論和歷史重視不夠[4]。麥克哈格大力提倡的生態設計思想具有時代的開拓性,同時也有時代的局限性。當時工業急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不僅資源耗竭,而且工業廢棄物和污染還威脅著人類健康和生存環境。
生態學是20世紀70年代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理論武器,麥克哈格近于專斷地強調生態設計,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作為風景園林師社會責任感的表達。20世紀90年代之后,歐美發達國家基本完成“去工業化”,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發達國家的城市環境得以改善。但全球性的能源危機、溫室效應、海洋污染等環境問題進一步加劇,可持續發展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并逐步付諸實踐。工業時代遺留下的廢棄地和環境問題面臨著更新、改造和利用的問題。20世紀70年查德•哈格(RichardHaag)改造的美國西雅圖煤氣廠公園翻開了后工業時代尊重歷史、反思工業文明、展示多元審美價值、利用生態技術進行景觀更新的新篇章。20世紀90年代彼得•拉茨(PeterLatz)在德國杜伊斯堡北園的設計中采用保留工業機器、進行局部土壤凈化以及運用鄉土樹種重建地方生態系統的方法,使該園成為劃時代的后現代景觀設計的代表作。景觀都市主義把后工業化社會城市重組、改造和更新的實踐提升到理論高度。查爾斯•瓦爾德海姆(CharlesWaldheim)、詹姆斯•科納(JamesCorner)、雷姆•庫哈斯(RemKoolhaas)、阿里克思•魁戈(AlexKrieger)、莫森•莫斯塔法維(MohsenMostafavi)等成為這一理論的先鋒代表人物[5]。在景觀都市主義理論框架中,自然和城市從二元對立轉向互惠共生,從引入自然到全面利用自然和生態系統,城市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具有與森林和河流一樣的‘生態性’”[6]。在過去被認為丑陋的廢棄礦坑、銹跡斑斑的鼓風爐和鐵軌,在后工業時代經過重新詮釋,與修復的生態環境一起喚起記憶,并擴大和改變了對美的定義。
2意識與價值的變革—從無視生態到彰顯生態
19世紀之前的西方國家自然地理條件優越、自然景色優美、環境宜人、土地肥沃、森林蔥郁、水源豐沛,風景園林服務的對象主要為君主和貴族。因此,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護等問題并不在設計師的考慮范圍之內,如凡爾賽宮苑選址在極度缺水的場所,卻以氣勢蓬勃、精致巧妙的水系著稱,足見君主對自然強烈的征服欲望及其賦予風景園林的政治意義。工業革命之后,環境的破壞和生態危機使風景園林師們意識到景觀的生態屬性與人類及環境的生存息息相關。而生態主義思想的影響使風景園林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自然觀均發生了嬗變,風景園林設計的意識與價值由人與自然相互隔離的心理補償和無意識的自然主義傾向轉變為自然獨立審美價值的客觀賦予和含有民主意識的現代文明指向,關注民眾的身心健康、安全與休閑娛樂活動,如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Park)給予城市中或富有或貧寒的人們以公平的景觀享有權[7]。現代主義園林的生態探索和生態學觀點的融入對社會道德和生態意識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并將設計師的樸素生態觀念上升到關注生態環境的層面。從麥克哈格“自上而下”垂直流動的生態規劃方法到卡爾•斯坦尼茲的“自上而下”關注水平作用的多解規劃方法,再到景觀都市主義所提倡的“自下而上涌現”的生態設計手段,風景園林的生態價值逐漸擺脫了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生態認識,轉而成為探索自然過程與城市環境關系的有效途徑、連接生態過程與城市環境的重要紐帶和積極的生態介入手段,如勞倫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在錫蘭奇(SeaRanch)海濱農場住宅區規劃中對自然地理條件、地貌特征和動植物資源的深入調查與思考,喬治•希爾(GeorgeA.Hill)和菲利普•列維斯(PhilipLewis)對自然過程的生態引導,阿德里安•高伊策(AdriaanGeuze)在東斯爾德大壩項目(EasternScheldtSurgeBarrier)中以廢棄貝殼表達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后達爾文主義解析。生態主義思想的發展與成熟賦予了風景園林以嶄新的空間組織模式、動態交互方式、生態關系描述和關鍵性的生態材料與分析技術,甚至新的思維模式,以發揮風景園林之于城市的生態導管和綠色廊道功能。同時,風景園林作為連續的地表結構與多維空間形態的整合也逐漸演變為承載了演替過程、容納了城鄉活動、融合了自然與人文過程的交換媒介。這種意義與價值的變革給予了風景園林以更加積極的社會、生態意義,并成為積極嵌入式的操控與調節策略,使風景園林的生態意識也從對生態環境的忽略、傲慢與無視轉變為對風景園林生態屬性的彰顯、樸素生態觀念的表達和生態主義思想的切實發展與實踐,甚至是對風景園林與人類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城市生態系統倫理關系的深度思考。
3材料與技術的創新—從不可再生到可持續生態主義的興起
使風景園林師開始重新審視人類的設計與建設活動與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并將其使命與人類生存、社會發展和環境存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生態主義思想激發了自然觀和價值觀的轉變及生態材料和可持續性技術的創新,推動了風景園林設計實踐由對生態性的無視和對自然資源的無限制耗費轉變為對自然過程的尊重、對廢棄設施的功能轉換、對可再生物質及能源的循環使用、生態材料的應用、可持續性技術的創新,以實現場地的自我維持和可持續發展。其中,廢棄設施和構筑物功能的轉變不但賦予了場地以新生,使其煥發了新的活力和勃勃生機,也減少了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浪費,保留了場地的歷史和城市發展與革新的文化印記。例如,美國西雅圖煤氣廠公園(GasWorksPark,Seattle)選擇性地保留原有煤氣廠中巨大的工業設備作為雕塑、游戲器械和歷史遺跡,并在已有的廠房基礎上進行再創作,將荒廢的廠房改建、更新為具有展示、餐飲、休息、游樂等功能的配套設施,而屹立在湖畔的高大油塔和被油漆成紅、黃、藍、紫等顏色的破舊機器則卸下了冰冷的面具,成為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兒童攀爬場。同時,依據生態設計原則,設計應盡可能地應用場地原有的可再生材料進行形式和功能的重建,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可再生材料的潛質,減少生產、加工和運輸過程中對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減少施工過程中原有廢棄物移除的資金耗費及新的廢棄物的產生,減少設計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并以此為基礎保留當地的歷史文化特點并增強其自我調節能力[8]。例如,德國海爾布隆市磚瓦廠公園(ZiegeleiPark)中,設計師保留了原磚瓦廠取土遺留的黃黏土陡壁構建自然保護地,并就地取材以充分利用場地原有的廢棄材料,如以拆建后的瓦礫作為道路的基層,或增加土壤中滲水性的添加劑,以殘余的石材砌成擋土墻,以舊的鐵路作為路緣[9]。此外,風景園林設計過程中應用的可持續性技術包括水資源的管理、建筑與可持續景觀的結合、綠色能源的利用、廢棄物和污染物的處理及景觀資源管理等。例如,德國慕尼黑的風中庭院(CourtyardintheWind,MunichGermany),通過建筑塔頂的葉輪獲取風能,并轉化為電能,經由復雜的連接裝置為機械旋轉的平臺提供動力,以帶動地表、基礎設施及人的轉動。風中庭院的設計通過場地自身的自然條件和風能優勢,將綠色能源機械轉化為景觀動力,并將轉化的過程和原理展現給游人,賦予其獨特的景觀體驗,為可再生能源的轉化與利用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4空間與維度的延展—從二維平面到四維時間自然觀的改變
與科學概念的引入使風景園林設計中生態思想的表達以動態性、變化性、不確定性和彈性為特征;而生態主義理念的融入和生態設計技巧的進步、生態材料的應用激發了風景園林設計思維模式的轉變和表現維度的延展。風景園林關注的重點由點、線、面構成的視覺平面轉變為由體積構成的實體空間感受,而生態系統恢復的過程和自然演替進程的漫長又使風景園林設計納入了時間的流變因素。同時,生態規劃方法的完善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風景園林的設計過程發生了由單一結論到多解可能、從線性過程到非線性思維的轉變;而生態設計關注的焦點也從生態因子的垂直流動變為關注水平作用,甚至發展為對由持續演化的線索構成的系統網絡內的相互影響與作用的強調。風景園林的美學特性使早期的設計實踐更多地關注二維平面的視覺效果,而其生態屬性使設計師運用數據信息的采集發展了二維平面疊加的生態分析技術,如卡爾•斯坦尼茲(CarlSteinitz)在弗吉尼亞半島(VirginiaPeninsula)的景觀規劃研究中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獲得土地適宜性評介,以分析其景觀空間格局、景觀的能流和物流的交換途徑以及生物生態學特征的相關性。同時,風景園林的功能性使設計師不得不從實體空間的角度思考長、寬和高形成的體積關系和尺度感受、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循環及生態因子之間立體交織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關系。而空間分析技術在風景園林設計中的應用突破了二維平面疊加的瓶頸,實現了三維空間分析的模型化。風景園林設計由二維平面疊加到三維空間模型的轉化有效地建立了場地與地形之間的拓撲關系,實現了集成數據與三維空間表達之間的有效轉換。此外,第四維時間維度的引入使設計師意識到風景園林中的生態屬性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的,不是由設計師賦予的,而是固有存在的,而包括風景園林在內的城市領域內的所有力量和因素則需被放置在動態的時空平臺上加以思考和研究,并被視為由隨時間而變化的獨立線索交織而成的系統網絡。這種以時間為媒介的表達和感知方式激發了場地分析與設計實踐之間的關聯,使設計對生態過程的無視轉變為尊重和理解。例如,詹姆斯•科納(JamesCorner)及其團隊(FieldOperations)設計的弗萊士河公園(FreshRiverPark)規劃囊括了3個階段,長達30余年的實施計劃,保留了樣地土壤及植物隨環境、時間和自然演替的變化而變化的流動性,提供了建立在自然演替進程和動植物生命周期基礎之上的、靈活的、長期的開放性策略,意在引導景觀形成過程與生態恢復過程的協同。
5趨勢探究生態主義思想影響下的風景園林設計的發展趨勢
殊難預料,但是風景園林學與生態倫理學和美學倫理的融合是可能的發展方向之一。生態主義的哲學貢獻曾經使風景園林由設計走向了科學,也將使風景園林設計領域的自然觀、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發生劇烈的變革,從而由科學走向倫理學的思考。
5.1生態倫理學關注生態主義的自然觀使風景園林師在實踐中重新認識了自然的含義,確定了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準確位置,使設計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由膜拜、歌頌、控制、主宰、對立與征服回歸到自由、平等和公正。生態主義的價值觀強調自然物的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創造性價值和整體系統價值,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極大地推動了風景園林領域新的價值觀的發現與表達。生態主義倫理道德觀賦予了風景園林師以公平、平等、公正的意識,將道德關懷和平等意識拓展到非人的自然物,并突破了狹隘的、短淺的功利主義觀念,將對短期利益的關注擴展到長期的、可持續的整體自然生態尺度。生態主義的哲學貢獻使風景園林發生了生態倫理學向度的轉化。在生態倫理學的語境中,風景園林不再是滿足人們視覺和社會、心理需求的物質實體空間,而是包含了邏輯與非邏輯、理性與非理性的價值評判以及滿足各個階層人群的物質和環境利益的訴求反饋[10],是帶有生態學和倫理學色彩的復雜社會實踐過程。生態倫理學的介入將使風景園林師反思人本主義的初衷,以多學科的融合為基礎,引導新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從而實現從消費設計到生態設計到可持續性設計的轉變,以提高生活質量,獲取精神愉悅和自我實現,對風景園林和生態城市的構建具有現實意義。
5.2美學倫理的轉向風景園林是一門以美學為基礎的學科,美學的哲學基礎及藝術形式的轉變也將影響風景園林領域的審美價值觀的嬗變,而新世紀美學運動的生態化、倫理化的發展趨勢也將促使風景園林的美學導向發生倫理化的轉向。18世紀至今,美學的哲學基礎發生了由人文主義到科學主義和生態主義的轉變,使傳統美學發生了向生態美學和倫理化美學發展的新趨勢,將風景園林設計關注的焦點由美的實體轉變為對人與自然物及無機環境之間關系的探索,削弱了人對自然的駕馭權利,強調人與自然物的平等共生關系,體現了人對自然美的再認識與超越。向倫理化美學的轉向使風景園林設計著意于自然演替的時間連續性和對人類活動的動態過程的描述,關注內在聯系而非外在形態,并使風景園林師的權利和義務受到倫理化的宏觀限定。倫理化美學與風景園林學的融合將使設計體現為對時間和生命周期的把握,風景園林設計將成為由線索編織而成的關聯網絡,且獨立而交織的線索將伴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萌發、生長、成熟、衰退等發展演替過程,且線索與線索之間的深層聯系、結構、對話和溝通將影響風景園林設計的美學生成。
6結語
近些年,我國通過綠道體系、郊野公園、雨水花園、濕地公園以及名目繁多的園林、園藝博覽會等建設了數量可觀的各類公園。這其中有在場址更新、生態修復以及文化和美學等方面表現突出并獲得國際聲譽的項目。但另一方面,我國一些城市園林項目存在表面生態化和非可持續的問題,如:用防滲技術維持濕地公園的景觀而忽視濕地的自然循環和交換過程;以近乎掠奪的方式從鄉村和自然山林中移植大樹進城,達到速成綠化和美化效果,卻干擾和破壞了大樹原初生態環境;等等。此外,學科之間甚至學科內部的壁壘導致學科之間缺少融合交流,園林設計精英化的傾向在激發公民的生態意識、社會參與和創新的教育模式等方面缺少探索和實踐。文章所探討的案例表明園林和環境藝術實踐的民主方式可以鼓勵人們關愛地方生態環境,更深刻地認識和溝通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通過風景園林、先鋒藝術社會實踐以及當代生態理論的互相追隨、互相加入和互相促進,促使公眾成為具備生態意識和知識的環境公民,建立起人和自然相互持續的整體生態—社會系統。
作者:何麗 單位:釜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 上一篇:干旱地區造林技術及管理措施范文
- 下一篇:林業生態文明建設中科技創新支撐作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