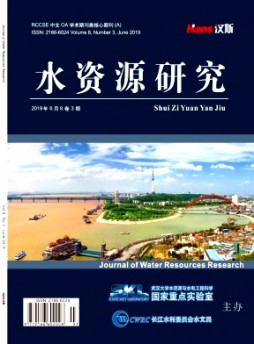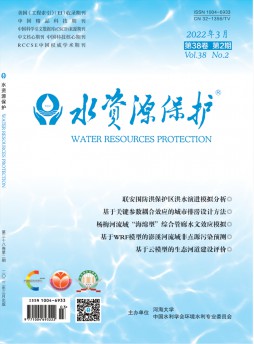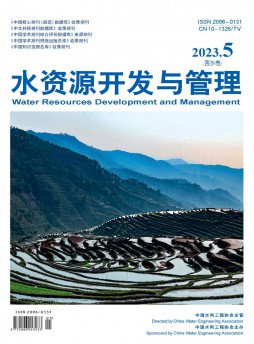談水資源與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治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談水資源與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治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必然性
(一)水資源的多維屬性矛盾導(dǎo)致水資源共享沖突
水資源同時(shí)具有生態(tài)、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的多維屬性,但這些屬性之間存在著矛盾。水資源的共享沖突可能涉及不同利益主體,沖突的原因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第一類是使用過(guò)程的外部性帶來(lái)的,即由于水資源固有的流動(dòng)性使得上下游區(qū)域之間會(huì)因水污染、取水不公等造成沖突和矛盾,這類沖突不直接涉及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可稱為社會(huì)及自然資源共享沖突。第二類是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過(guò)程中水資源在各行業(yè)部門之間的配置引起的共享沖突,即配置過(guò)程中效率過(guò)低或交易成本過(guò)高而引發(fā)部門之間的沖突和矛盾,這類型的沖突是由水資源的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引起的,稱為經(jīng)濟(jì)資源沖突。水資源屬性的多維性導(dǎo)致水資源涉及多重利益主體,相對(duì)于其他公共資源管理而言,更具有復(fù)雜性。我國(guó)的水資源管理,目前仍然是基于行政垂直結(jié)構(gòu)的單一體制,難以協(xié)調(diào)多維屬性間的體制性矛盾。因此,需要改變傳統(tǒng)單一政府為決策主體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將涉及到的多元主體納入水資源管理之中。
(二)生態(tài)考核弱化導(dǎo)致地方政府水資源管理失靈
水資源作為區(qū)域公共資源,應(yīng)是所在行政區(qū)的重要公共管理職能所在。但是,在現(xiàn)實(shí)的治理實(shí)踐中,相對(duì)于其他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而言,資源和水環(huán)境的治理的績(jī)效顯示度低、監(jiān)測(cè)困難、實(shí)施成本高,因而被地方政府忽略。首先,地方政府的行為動(dòng)力主要來(lái)自于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激勵(lì)。在財(cái)政分權(quán)的背景下,我國(guó)地方政府追求本地財(cái)政收入的增長(zhǎng)最大化,從而實(shí)現(xiàn)其預(yù)算需求。另外,也來(lái)自于地區(qū)官員排序的追求,周黎安(2007)在LazearandRosen模型基礎(chǔ)上提出了我國(guó)地方政府的“政治錦標(biāo)賽”模型,該模型解釋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動(dòng)因,在政治錦標(biāo)賽基本行政體制框架下,地方政府通過(guò)競(jìng)爭(zhēng)追求與其他相關(guān)地區(qū)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的排位。中央政府對(duì)地方政府官員進(jìn)行制度性的績(jī)效考核,這種考核以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速度(即GDP增長(zhǎng)速度)為最主要指標(biāo),這使得關(guān)心職位晉升的地方政府官員很強(qiáng)調(diào)增加GDP的激勵(lì)(王哲偉,2012)。因此,地方政府相對(duì)于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而言,生態(tài)環(huán)境改進(jìn)的指標(biāo)往往被淡化。其次,地方政府的水資源治理成果考核存在困境。一是指標(biāo)難以量化。相對(duì)于國(guó)民經(jīng)濟(jì)較為成熟的考核指標(biāo)體系而言,自然環(huán)境治理作為一種政府職能在考核中的指標(biāo)體系,量化工作往往比較困難。由于水資源的多重屬性,很難用一個(gè)簡(jiǎn)單的指標(biāo)進(jìn)行量化考核,而且由于考核體系需要所有參與考核的機(jī)構(gòu)和人員公共認(rèn)可并掌握,因此量化較為困難。二是成果難以被監(jiān)測(cè)。即使水資源治理的考核可以被量化,但是其績(jī)效的歸屬都難以被衡量。因?yàn)樗Y源作為一種自然資源,其巨大的空間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其被改善或惡化,均難以被有效觀察和地方政府本身的行為投入之間的直接關(guān)系,這就使得地方政府進(jìn)行搭便車。最后,對(duì)于人民生活和企業(yè)生產(chǎn)來(lái)說(shuō),水資源和環(huán)境的改變,對(duì)于受眾來(lái)說(shuō)可以直接獲取其改變的效果,但是地方政府獲取這種信息需要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水資源治理的效果假如由地方政府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將面臨巨大的操作成本。
(三)公眾參與的行為受到內(nèi)外環(huán)境的影響制約
基于公眾參與的水資源多元主體治理結(jié)構(gòu)優(yōu)于原有單一垂直式結(jié)構(gòu),然而在現(xiàn)實(shí)中,由于各種障礙,使得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管理難以有效進(jìn)行。
1.我國(guó)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在思想意識(shí)上存在認(rèn)識(shí)不足。
我國(guó)公眾參與的行為往往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傳統(tǒng)的官本位思想在公眾中還是根深蒂固,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眾參與意識(shí)的提高,主動(dòng)積極的參與行為往往很難被公眾接受。“公眾環(huán)保指數(shù)”是刻畫公眾參與生態(tài)保護(hù)程度的指標(biāo),國(guó)家環(huán)保總局和中國(guó)環(huán)境文化促進(jìn)會(huì)于2008年聯(lián)合編制了我國(guó)的“公眾環(huán)保指數(shù)”。調(diào)查編制的結(jié)果揭示了我國(guó)公眾在環(huán)境保護(hù)中的參與程度非常低,知道環(huán)境問(wèn)題免費(fèi)舉報(bào)電話的不到1/5(僅占16%);這當(dāng)中知道并打過(guò)該電話的不到1/2(僅占9.2%)(畢霞、楊慧明、于丹丹,2010)。由此可見(jiàn),我國(guó)的現(xiàn)狀是公眾的環(huán)保知識(shí)欠缺,公眾參與程度低,在實(shí)際發(fā)生環(huán)境或生態(tài)問(wèn)題時(shí),公眾沒(méi)有渠道或者沒(méi)有制度保障來(lái)理性表達(dá)自己的利益訴求,從而也降低了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2.參與權(quán)未明確,抑制了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的動(dòng)力。
由于我國(guó)對(duì)公眾對(duì)水資源及水環(huán)境的使用權(quán)、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等一系列產(chǎn)權(quán)在法律上未做較為明確的界定,公眾在參與水資源管理中難以找到適合的制度保障工具進(jìn)行參與。尤其是對(duì)公民擁有環(huán)境權(quán)未作出明確界定,使得公民難以衡量自身權(quán)利是否遭到破壞,以及損失承擔(dān)歸屬問(wèn)題,缺乏公民參與的制度保障,致使公民參與動(dòng)力不足。
3.公眾進(jìn)行參與水資源治理受到理性選擇影響。
一是搭便車的可能性,即使公眾擁有了明確的環(huán)境權(quán),但是由于對(duì)于公民而言,自然環(huán)境與資源的治理是一種公共產(chǎn)品,其收益具有較強(qiáng)的正外部性,因此公眾可能會(huì)等待其他公眾參與,享有其他公眾參與的成果。二是集體行動(dòng)的成本,即使公眾不選擇搭便車,但是單個(gè)公民參與難以奏效,必須要有集體行動(dòng)的力量做基礎(chǔ),且集體行動(dòng)組織成本較高,這種組織成本便是一種交易成本。按照科斯定理的觀點(diǎn),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共資源的治理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當(dāng)公眾的組織成本大于其可能的潛在收益時(shí),集體行動(dòng)的動(dòng)力將被抑制。三是知識(shí)與信息不足,對(duì)于公眾而言就算解決了共同認(rèn)識(shí),也不能有效地解決共同知識(shí)的問(wèn)題。對(duì)公共資源的治理,知識(shí)信息的傳播是十分重要的,水資源的重要性是不爭(zhēng)的共識(shí),但是有關(guān)水資源保護(hù)與治理的相關(guān)知識(shí)和信息存在嚴(yán)重的不對(duì)稱或者不充分現(xiàn)象。在我國(guó)沒(méi)有獲取有關(guān)水資源知識(shí)信息的權(quán)威途徑、手段和平臺(tái),無(wú)論是公眾還是管理部門對(duì)知識(shí)信息的掌握都是不完備的,彼此之間也很難溝通交流,這就使得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存在較大的信息鴻溝,在遇到水資源治理問(wèn)題時(shí)影響彼此的認(rèn)同程度,從而有進(jìn)一步激化矛盾。信息鴻溝導(dǎo)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不僅降低了跨界水資源沖突的治理效率,更成為公眾參與水資源管理的基礎(chǔ)性障礙。
二、公眾參與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層次與選擇
公眾參與要求管理的組織構(gòu)架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與以“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決策管理模式不同,必須向廣泛公民的決策參與和靈活的管理方式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不僅是組織構(gòu)架的變動(dòng),更是主體權(quán)利限定與相互關(guān)系的深刻變化,網(wǎng)絡(luò)治理的提出便是對(duì)這種變化的深刻闡述。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模式主要是水資源治理過(guò)程中的利益相關(guān)者關(guān)系。“公眾參與”表明網(wǎng)絡(luò)成員是來(lái)自不同領(lǐng)域、不同地理區(qū)域的不同個(gè)體、部門或組織。不同背景的網(wǎng)絡(luò)網(wǎng)絡(luò)成員形成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共同決策多元化的網(wǎng)絡(luò)問(wèn)題,因此網(wǎng)絡(luò)治理模式主要是解決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問(wèn)題。Provan(2007)將“網(wǎng)絡(luò)治理”視為一種機(jī)制對(duì)其進(jìn)行了界定,他指出網(wǎng)絡(luò)是由三個(gè)或多個(gè)自然組織合作建立的一種組織治理架構(gòu),網(wǎng)絡(luò)治理是一種治理機(jī)制和治理方式,網(wǎng)絡(luò)成員的私人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同時(shí),整個(gè)網(wǎng)絡(luò)層次的共同目標(biāo)才是網(wǎng)絡(luò)得以建立的關(guān)鍵。網(wǎng)絡(luò)成員的合作行為是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的前提,這也決定了網(wǎng)絡(luò)成員對(duì)網(wǎng)絡(luò)層次的目標(biāo)負(fù)有責(zé)任,對(duì)治理規(guī)則和程序的遵循都是自愿的,而非利益或權(quán)力使然。水資源作為公共物品,其利益相關(guān)者涉及盈利和非盈利部門、私人和公共部門、NGO等多種組織和個(gè)人。在多元主體中,目前參與度最低的是公眾,這也是參與障礙最大的地方。公眾參與不能僅限于公眾個(gè)體的參與,而應(yīng)包括了個(gè)體、組織及跨區(qū)域在內(nèi)的三個(gè)參與層次。基于此,根據(jù)水資源的屬性,可以界定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三層次框架。
1.個(gè)體層次。
按照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基本界定,當(dāng)以私人部門的身份存在時(shí),每個(gè)個(gè)體都是自利的,經(jīng)濟(jì)利潤(rùn)最大化和個(gè)人效用最大化是理性的行為選擇。顯而易見(jiàn),單一的用水戶從水資源的使用中獲得經(jīng)濟(jì)收益或個(gè)人效用。水資源的經(jīng)濟(jì)屬性帶來(lái)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和收益。在個(gè)體層次上,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建立在市場(chǎng)交易基礎(chǔ)上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可以很好測(cè)度彼此在水資源沖突中的利益得失,因而經(jīng)濟(jì)手段,如補(bǔ)償、水權(quán)交易等常常被認(rèn)為是有效的解決方案。
2.組織層次。
發(fā)生社會(huì)及自然資源的共享沖突時(shí),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有可能失效,建立在個(gè)體層次的治理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需要引入組織層次的治理。建立在組織層次的治理主要是協(xié)調(diào)不同組織,如公眾和政府的利益訴求,此時(shí)的效率標(biāo)準(zhǔn)不再是單一的市場(chǎng)收益,而是問(wèn)題解決的經(jīng)濟(jì)和時(shí)間成本,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效益,如社會(huì)公平、環(huán)境保護(hù)、生態(tài)補(bǔ)償?shù)龋唧w指標(biāo)可能是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也可能是非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
3.跨界層次。
水資源最本能的功能屬性是生態(tài)屬性,即維系人類和自然的和諧與可持續(xù)發(fā)展,而不僅僅是作為生產(chǎn)要素投入到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中,或者作為景觀提供觀賞服務(wù)。因此水資源共享問(wèn)題在人類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之間隱含了更為廣泛和深遠(yuǎn)的沖突和合作契機(jī)。網(wǎng)絡(luò)治理不僅限于在個(gè)體和組織層面實(shí)現(xiàn),還需要在跨越地理邊界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交互關(guān)系也將體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中。同時(shí),時(shí)間序列上,可持續(xù)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不同代際之間的水資源共享與分配,這很難用單一的指標(biāo)來(lái)測(cè)度,也很難判斷代際聯(lián)系的強(qiáng)弱,此時(shí)網(wǎng)絡(luò)治理能夠通過(guò)集成不同的利益述求實(shí)現(xiàn)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而協(xié)調(diào)沖突。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水資源多維屬性之間發(fā)生配置沖突,需要協(xié)調(diào)多元主體的利益關(guān)系時(shí),網(wǎng)絡(luò)治理可以提供有效的合作機(jī)制和平臺(tái),這一平臺(tái)在治理的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中會(huì)不斷增強(qiáng)和推進(jìn)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的建立,從而鞏固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如泛珠“9+2”合作區(qū))。
三、基于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框架與實(shí)現(xiàn)
(一)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于水資源的多維屬性使得政府單一治理會(huì)出現(xiàn)政府失靈,我國(guó)目前體制機(jī)制本身存在的問(wèn)題使得由個(gè)體公眾進(jìn)行參與水資源管理也難以實(shí)現(xiàn)。因此,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式的公眾參與是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基本導(dǎo)向。由公眾參與的基礎(chǔ)分析來(lái)看,對(duì)于公眾參與的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框架的構(gòu)建,應(yīng)該包括三個(gè)部分的內(nèi)容。基于“公眾參與”的區(qū)域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框架
1.公眾參與的層次選擇。
由于水資源具有多維屬性,功能也具有多重性,并非任一的水資源治理功能均適合于所有層次。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的層次取決于水資源的多維屬性,公眾在個(gè)體層次、組織層次以及跨區(qū)域?qū)哟伍g進(jìn)行選擇,又主要決定于所參與的水資源的屬性,以及發(fā)生利益沖突所引發(fā)的是個(gè)人利益、公眾利益還是區(qū)域利益。
2.公眾參與的組織選擇。
對(duì)于公眾進(jìn)行組織形式選擇時(shí),面臨著四重因素的影響。一是考慮理性選擇,公眾參與受到其理性選擇的影響,由于個(gè)體依據(jù)成本收益衡量來(lái)決定自己的行動(dòng),因此要避免搭便車的行為,通過(guò)制度設(shè)計(jì)改變個(gè)人成本收益比,將外生行為轉(zhuǎn)化為內(nèi)生行為。二是考慮組織成本,公眾參與需要通過(guò)集體行動(dòng)來(lái)實(shí)現(xiàn),而集體行動(dòng)需要付出組織協(xié)調(diào)及激勵(lì)的成本。不同緊密程度的組織是網(wǎng)絡(luò)中組織選擇的考慮的關(guān)鍵要素,組織成本將直接影響到公眾選擇組織的緊密程度。三是考慮目標(biāo)一致性,由于參與水資源治理的公眾目標(biāo)不同,其一致性程度也影響到公眾組織結(jié)構(gòu)與組織規(guī)模選擇。在網(wǎng)絡(luò)中通過(guò)溝通與協(xié)商實(shí)現(xiàn)共同認(rèn)知和共同價(jià)值觀,進(jìn)而促進(jìn)目標(biāo)一致的實(shí)現(xiàn)。四是考慮共同知識(shí)與信息,在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中,共同知識(shí)一方面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組織溝通成本,而對(duì)于共同知識(shí)與信息的供給存在外溢性效果,需要資金的投入如果網(wǎng)絡(luò)內(nèi)部動(dòng)力不足的情況下,則會(huì)導(dǎo)致治理成本巨大,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治理失敗。
3.公眾參與的目標(biāo)選擇。
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治理與政府主導(dǎo)的垂直治理的不同也在于更強(qiáng)調(diào)目標(biāo)整合能力,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是網(wǎng)絡(luò)各主體形成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果。公眾參與在水資源的多維屬性上,呈現(xiàn)出目標(biāo)多樣性選擇。由于在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中更強(qiáng)調(diào)多元主體的參與,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組織網(wǎng)絡(luò)集成公眾目標(biāo),通過(guò)組織協(xié)調(diào)集成組織目標(biāo),在目標(biāo)形成的過(guò)程中平等溝通是主要途徑。公眾作為水資源的受眾,在享有作為公共資源的私人收益的同時(shí),也參與到公共目標(biāo)的私人貢獻(xiàn)之中去。溝通途徑的形成,需要強(qiáng)化主體間平等,而不是利益間均衡的協(xié)調(diào)。此時(shí)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應(yīng)該是動(dòng)態(tài)和可持續(xù)的,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目標(biāo)選擇要充分考慮公眾在相互協(xié)調(diào)中對(duì)社會(huì)資本的偏好和對(duì)代際公平的訴求。因此,公眾參與的目標(biāo)選擇具有平等性、動(dòng)態(tài)化、繼承性及可持續(xù)性。
(二)公眾參與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的實(shí)現(xiàn)
1.引入非正式組織與權(quán)威。
傳統(tǒng)的治理結(jié)構(gòu),更多地考慮正式組織的行動(dòng)和正式權(quán)威的作用,這是傳統(tǒng)的對(duì)于公共資源的治理方式。但是由于公民社會(huì)的興起引發(fā)的公眾訴求多元化,公眾內(nèi)部非正式組織以及非正式權(quán)威需要被充分考慮。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治理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勢(shì)在于平等和可持續(xù)性,而傳統(tǒng)的治理更強(qiáng)調(diào)效率。由于公眾之間的關(guān)系作為一種社會(huì)資本,在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形成的非正式組織以及非正式權(quán)威,在具體的治理行動(dòng)中更容易形成目標(biāo)一致的行動(dòng),比如用水者協(xié)會(huì)的創(chuàng)新。在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開(kāi)始,灌溉系統(tǒng)管理制度改革為許多發(fā)展中國(guó)家和部分發(fā)達(dá)國(guó)家所重視,并逐步推行“參與式”灌溉管理,這種管理模式強(qiáng)調(diào)了農(nóng)戶在灌溉管理中有權(quán)直接參與,并為其結(jié)果負(fù)責(zé)。其管理模式的安排是按灌溉渠系的水文邊界劃分區(qū)域,通過(guò)民主方式組建灌區(qū)合作管理組織,即用水者協(xié)會(huì)。隨著全球各國(guó)的探索逐步深入,我國(guó)于20世紀(jì)90年代開(kāi)始,也開(kāi)展了“用水戶參與灌溉管理改革試點(diǎn)”的實(shí)踐,建立了“自主管理灌排區(qū)”。WUA是用水戶與供水戶之間的中間商,既把供水機(jī)構(gòu)的灌溉水作為商品賣給用水戶,又代表用水戶向供水公司購(gòu)買水,費(fèi)用的收取和交納都通過(guò)與農(nóng)戶或供水公司簽訂契約實(shí)現(xiàn)。除此之外,WUA還承擔(dān)了灌溉資產(chǎn)保值增值的責(zé)任,需要負(fù)責(zé)支渠和支渠以下的各級(jí)渠道的運(yùn)行和管理。
2.調(diào)整地方政府激勵(lì)結(jié)構(gòu)與方式。
由于我國(guó)的財(cái)政分權(quán)與“政治錦標(biāo)賽”的基本行政構(gòu)架,使得地方政府對(duì)生態(tài)建設(shè)的關(guān)注與投入難以符合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要求。在區(qū)域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框架的實(shí)現(xiàn)中,公眾的參與決策,需要調(diào)整原有的激勵(lì)結(jié)構(gòu)。一是由“竹竿”式考核向“木桶”式評(píng)價(jià)方式轉(zhuǎn)變:對(duì)于地方政府而言,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較容易出成果,顯示度較高,激勵(lì)的竹竿效應(yīng)明顯,激勵(lì)指標(biāo)的提升會(huì)掩蓋水資源及其他生態(tài)指標(biāo)的不足。可以將地方政府的激勵(lì)轉(zhuǎn)變?yōu)椤澳就靶?yīng)”的考核,地方區(qū)域水資源狀況和沖突治理的狀況如果有下降,則采用懲罰性措施。二是分散并降低考核成本:上級(jí)政府對(duì)于地方政府的激勵(lì)在原有的上下級(jí)之間的激勵(lì)由于依靠下級(jí)水資源管理狀況和改進(jìn)努力的考核,由于信息不對(duì)稱,難以做到激勵(lì)相容。因此,將公民作為觀測(cè)和評(píng)價(jià)水資源使用效果的主體,能夠便于直接觀測(cè)水資源的改善,其觀測(cè)成本更低。三是調(diào)整支持性政策供給結(jié)構(gòu):原有的以政府采購(gòu)為主體的水資源治理的財(cái)政投入體系,可以轉(zhuǎn)變?yōu)閷?duì)公眾參與組織成本(比如NGO組織的運(yùn)行費(fèi)用)、公眾水資源知識(shí)的培訓(xùn)費(fèi)用、對(duì)于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的獎(jiǎng)勵(lì)以及專業(yè)機(jī)構(gòu)參與評(píng)價(jià)的費(fèi)用等等。通過(guò)這樣的調(diào)整,可以有效地促進(jìn)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同時(shí)降低對(duì)于水資源治理質(zhì)量的觀測(cè)和考核成分。
3.創(chuàng)新區(qū)域激勵(lì)約束制度安排。
解決區(qū)域水資源的治理問(wèn)題,實(shí)現(xiàn)公眾參與的網(wǎng)絡(luò)治理,地方可以嘗試區(qū)域制度創(chuàng)新。一是公眾的水權(quán)制度性保障。公眾參與區(qū)域水資源的網(wǎng)絡(luò)治理,前提需要有公民的水權(quán)做保障。對(duì)于自然資源的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在全國(guó)性的相關(guān)制度中還比較模糊,但區(qū)域中可以嘗試自主性設(shè)立。二是明確公民的參與義務(wù)與責(zé)任。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性保障,要實(shí)現(xiàn)網(wǎng)絡(luò)的可持續(xù)目標(biāo),必須將公民的自主理性參與作為基礎(chǔ)。這樣一方面可以嘗試將公眾參與水資源治理作為一種義務(wù),如果不參與則受到相應(yīng)的懲罰;另一方面可以仿照一些國(guó)家中區(qū)域的做法,以公眾參與的水資源治理作為行政處罰的一種方式,如在美國(guó)一些地方如果公民有一些違法行為(例如交通違章),則可以在接受經(jīng)濟(jì)和行政處罰的同時(shí),選擇做義務(wù)勞動(dòng)治理水環(huán)境,也稱“以勞代罰”,從而改變其參與水資源治理的機(jī)會(huì)成本結(jié)構(gòu)。三是通過(guò)政府與公眾互動(dòng)提升信任、公開(kāi)和共同信息。作為區(qū)域的水資源治理,政府與公眾都屬于治理網(wǎng)絡(luò)中的主體,要通過(guò)多種方式來(lái)促進(jìn)網(wǎng)絡(luò)的社會(huì)資本的形成和共同信息的基礎(chǔ)。比如水價(jià)聽(tīng)證會(huì),就是我國(guó)城市水資源治理制度改革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利益公民參與的方式。
四、結(jié)語(yǔ)
總之,公眾參與水資源網(wǎng)絡(luò)治理創(chuàng)新模式,能積極引入非正式組織和非正式權(quán)威的參與,能調(diào)整地方政府的激勵(lì)結(jié)構(gòu),建立地方公眾參與的制度體系。
作者:鎖利銘馬捷單位:電子科技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電子科技大學(xué)經(jīng)濟(jì)與管理學(xué)院
擴(kuò)展閱讀
- 1談水資源問(wèn)題的成因和對(duì)策
- 2談綠色建筑評(píng)價(jià)中的建筑給水排水設(shè)計(jì)
- 3談熱水器內(nèi)膽水壓疲勞試驗(yàn)開(kāi)裂原因
- 4談自來(lái)水供水企業(yè)成本核算與管理
- 5談水產(chǎn)養(yǎng)殖與成本管理的關(guān)聯(lián)
- 6談處理工業(yè)廢水的方法
- 7談分離技術(shù)處理工業(yè)廢水
- 8談航天用鎢滲銅產(chǎn)品水浸超聲檢測(cè)
- 9談暴雨洪水發(fā)生的時(shí)空特征及致災(zāi)因素
- 10談水生態(tài)服務(wù)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評(píng)價(ji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