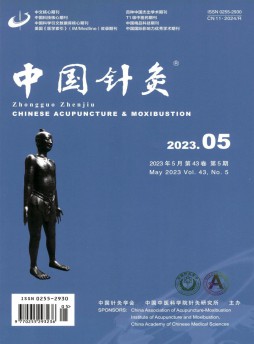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中國現(xiàn)在處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完善的十字路口,不到位的保護和尚有缺失的權(quán)利限制新問題都有待解決,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并非僅有利而無弊。應(yīng)當(dāng)說,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批判探究和策略探究都是不可少的,但有一個重點放在何處的新問題。面對中國目前這種侵權(quán)嚴(yán)重和權(quán)利濫用同樣嚴(yán)重的復(fù)雜狀況,在如何評價我們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這個新問題上,中國法院的觀點似乎比我們許多學(xué)者的觀點更為可取。
[關(guān)鍵字]: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定位
[論文正文]:
近年來在所謂的“經(jīng)濟全球化”中,南北經(jīng)濟發(fā)展越來越失去平衡、南北貿(mào)易發(fā)展也越來越失去平衡,其中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在《和貿(mào)易有關(guān)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議》達成時,尤其是多哈會議后,在國際上顯現(xiàn)的南北失衡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專利對醫(yī)藥的保護和發(fā)展中國家公共健康之間的失衡,等等。這些新問題,引起許多人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進行反思,是必然的。而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注重的,正如一位從事專利工作多年的學(xué)者所說,在探索利益平衡時“一個重要原則是要充分注重發(fā)展是硬道理,盡可能用發(fā)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新問題,而不大可能退回到過去的大鍋飯時代。”在科技領(lǐng)域退回去吃大鍋飯,只會使我們永遠缺少能和外國企業(yè)競爭的核心技術(shù)。在文化領(lǐng)域退回去吃大鍋飯,只會使我們自己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作品越來越少。這種結(jié)果并不符合公眾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費者自肥的侵權(quán)者,雖然號召人們回到過去的大鍋飯時代,并擬出種種名為“最新”的方案引導(dǎo)別人去吃大鍋飯,但他們自己肯定不會加入吃大鍋飯的行列,卻依舊扛著“代表公眾”的旗,走著侵權(quán)致富的路。敢于站出來維權(quán)的作者,在侵權(quán)人以各種手段打壓之下并未屈服,表明了他們并非為私利而是為更多被侵權(quán)作者的利益,為繁榮文化創(chuàng)作而斗爭。侵權(quán)人則無論冠冕堂皇地說些什么,卻始終不敢觸及自己靠侵權(quán)和欺世的“發(fā)家史”,不敢談及非法獲利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區(qū)別。這是人們很輕易注重到的。
把僅僅適合發(fā)達國家(乃至個別發(fā)達國家)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強加給全世界,是發(fā)達國家的一貫做法。發(fā)展中國家的抗?fàn)帲瑥闹贫瓤傮w的層面上,從未奏效過。1967年《伯爾尼公約》修訂的失敗,1985年大多數(shù)國家反對以版權(quán)保護計算機軟件的失敗,Trips協(xié)議談判時,秘魯和巴西等國建議的失敗,都是實例。我們在經(jīng)濟實力尚無法和發(fā)達國家抗衡的今天,是接受對我們確有弊端的制度,然后探究如何趨利避害,還是站出來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領(lǐng)頭羊,再度發(fā)起一次1969年或1985年那樣的戰(zhàn)爭,力促國際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從Trips協(xié)議退回來,退到對發(fā)展中國家較為公平的制度?也是確定我們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戰(zhàn)略時必須考慮的一個重大新問題。
此外,許多人在抱怨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水平“太高”時,經(jīng)常提到美國20世紀(jì)三十年代、日本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和我國目前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相似,而當(dāng)時它們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水平則比我們現(xiàn)在低得多。這種對比用以反詰日、美對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不合理的指責(zé),是可以的。但假如用來支持它們要求降低我國目前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立法的水平,或批評我國不應(yīng)依照世界貿(mào)易組織的要求提高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水平,則屬于沒有歷史地看新問題。20世紀(jì)七十年代之前,國際上經(jīng)濟一體化的進程基本沒有開始。我們假如在今天堅持按照我們認(rèn)為合理的水平保護知識產(chǎn)權(quán),而不愿考慮經(jīng)濟一體化的要求以及相應(yīng)國際條約的要求,那么在一國的小范圍內(nèi)看,這種堅持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國際競爭的大環(huán)境中看,其惟一的結(jié)果只可能是我們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我國達到現(xiàn)在這種備受許多國內(nèi)學(xué)者指責(zé)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法律水平,的確是只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身居最高層者才能作出的決斷。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在世界科技的最高端,必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使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有利的一面不斷得到發(fā)揮,不利的一面不斷受到遏制,除了靠立法之外,就主要靠執(zhí)法了。而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中,法院的功能永遠是在首位的。因為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這種私權(quán),行政執(zhí)法的功能,在國外、在中國均是逐步讓位于司法的。由于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行文總的講尚未完全擺脫傳統(tǒng)立法“宜粗不宜細”之弊,故法官對法的解釋、法官的酌處權(quán),進而中國法官的素質(zhì)、中國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結(jié)構(gòu)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對于偶然的、僅僅因過失的侵權(quán),和反復(fù)的、故意的侵權(quán)不加區(qū)分,同樣處理,既是許多人認(rèn)為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過度的主要原因,也是許多人認(rèn)為保護不力的主要原因。解決這個新問題既要有更加細化的法律,也要有更合理的司法解釋和更高的法官素質(zhì)。假如大家注重到,面對中國目前這種侵權(quán)嚴(yán)重和權(quán)利濫用同樣嚴(yán)重的復(fù)雜狀況,在如何評價我們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這個新問題上,中國法院的觀點似乎比我們許多學(xué)者的觀點更為可取。
在立法之外的策略方面,國際組織(包括歐盟之類地區(qū)性國際組織)的立法及探究結(jié)果對我們的影響,外國(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等)立法及國家學(xué)說對我們的影響,我們均應(yīng)探究。此外,假如多個外國聯(lián)手將對我們產(chǎn)生何種影響,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探究。例如,對于我們發(fā)明專利的短項“商業(yè)方法專利”,國家專利局固然可以通過把緊專利審批關(guān),為國內(nèi)企業(yè)贏得時間。但那終究不是長遠之計。試想,美、日、歐等在傳統(tǒng)技術(shù)專利方面“標(biāo)準(zhǔn)化”發(fā)展,曾給并正給我們的產(chǎn)品出口帶來不利,假如美、日(或再加上幾個其他發(fā)達國家)在商業(yè)方法專利上也向“標(biāo)準(zhǔn)化”發(fā)展,即假如實施“金融方法專利化、專利標(biāo)準(zhǔn)化、標(biāo)準(zhǔn)許可化”,那么會給我國銀行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何種影響,會不會把我們擠出國際金融市場?這就不僅僅是專利局把緊專利審批關(guān)能夠解決的新問題了。在這些方面作出較深入的探究,有助于我們拿出策略,“趨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