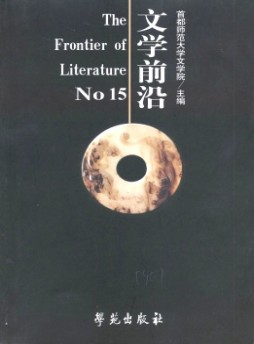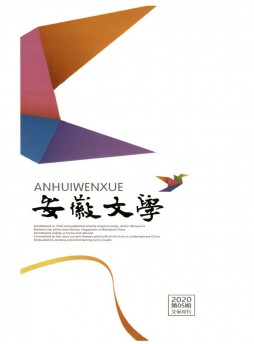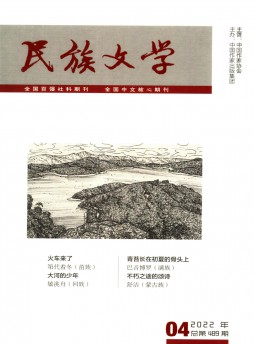文學倫理學下的生態文學書寫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倫理學下的生態文學書寫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科學理性的過度膨脹與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人類不能只在科技理性中安身立命,以資本邏輯為代表的理性瓦解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共同體,讓人的心靈無法得到安頓,因此,感性世界的建構將成為心靈港灣的需求。在生態世界的建構中,感性世界對“本心”的滋養是關鍵,而感性世界的建構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完成,一是生態文學作品傳統,即經典的生態文學作品,二是創作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生態文學作品可以發揮文學倫理的作用,完成感性倫理世界建構的使命,從而創建人與人、人與物和諧相處的生態世界。
生態文學最初指再現了自然生態被破壞的文學作品,其目的是為了告誡人類自然生態被破壞后的災難性后果,從而起到警示性作用。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生態破壞現象不僅存在于自然世界,還擴展到人類社會,即生態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文學倫理學認為,文學起源于人的倫理需要,其存在目的首先在于倫理教誨,而審美是為倫理原則服務的。[1](P9)人之所以為人,最本質的是人具有倫理選擇,離開了這個選擇,人就會滑向“非人”的深淵,觸犯某種倫理禁忌,從而受到懲罰。本文以文學倫理學為視角,擇取相關生態文學作品,展現生態文學作品發揮倫理功能的過程,并燭照生態文學作品所具有的獨特倫理價值。
一、生態文學的根源
生態文學起源于生態危機,是生態危機在文學作品中的顯現。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進步強制”,其發展邏輯表現為“不進步”就不是現代社會。這種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大都市正在集聚,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大都市“甚至以更加爆炸性的速度增長”[2](P37)。英國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創始人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認為,現代社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工業的蓬勃發展成為一個國家的決定性力量,而工業持續膨脹的結果是,人類世界在生態方面最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3](P252)在加拿大小說家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小說《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中,核工業污染所形成的放射性物質彌漫在空氣、河流等自然環境中,使得有生育重任的女性身體“骯臟得就像進了油的河灘……說不定連兀鷹吃了她們的尸體都會斃命”[4](P181)。核工業的發展原本是為人類提供能源,但畸形的核工業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小說中寫到,核工業病毒侵入人體后,在身體內存活的時間比人的壽命還長,人的生命終結并不意味著病毒的死亡,可能還會繼續侵害其他的有機體。這種科技理性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在西方的生態文學作品中大量出現,既有具象性的描寫,又有關于人類文化命運的反思。反思的結果大都將這種生態災難歸結為人類數千年理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僅是核工業,即使是對人類生命起到治療作用的生物克隆、器官移植技術,也可能會帶來災難性后果。阿特伍德的《羚羊與秧雞》(OryxandCrake)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小說以倒敘的方式,首先展現了人類被毀滅后的悲慘場景:在一片廢墟上,遍地是生物工程制品——雞肉球、器官豬和秧雞人。雞肉球只長出雞胸脯和雞腿肉,人類飲食不需要的部位一概沒有;器官豬長出供人類移植的器官,如腎和大腦皮層;秧雞人是一種“人造人”,以生物工程精英“秧雞”的名字命名,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制造出任何體貌、性情的“人”,這種“人”幾乎不需要消費,“只吃樹葉、草、根以及一兩種漿果”,但卻美麗溫順,可以為人類提供隨心所欲的服務。[5](P315-316)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秧雞將一種災難性病毒植入進一種常用的維生素膠囊,并準備在病毒發作時出售疫苗,從而大發橫財。不幸的是,秧雞突然死亡,并且在死亡前毀掉了只有他自己能控制的疫苗,從而帶來了整個人類的毀滅。由于技術主義的盛行,人類的生存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技術化,從而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這種技術化要求能夠控制外部世界,包括作為特定主體的人。個體被作為物而受到控制,造成了人的物化,從而改變人與世界原初的生態關系,不可避免地帶來生態危機。那么,這種技術至上是否可以靠道德來約束呢?換言之,科技理性可否邏輯地推斷出道德,而用這種道德對理性自身進行約束呢?康德曾經想建立道德的理性基礎,他認為人的行為應由理性規范,只有這一行為對其他所有人有普遍立法的意義才是道德的。[6](P39)這是無條件的,康德稱之為“絕對命令”。他以絕對命令的形式,為人類社會的道德做出理性的論證。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實際上難以靠抽象的理性思考來做出道德決定。每一次道德的善舉均來自于正義情感的驅動,而這種情感的決斷往往與生態文學作品及其他藝術作品所具有的情感沖擊和藝術感染力息息相關。
二、生態文學傳統與生態文學創作
在當代,建構感性世界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大眾傳媒,如赫爾曼(EdwardHerman)和喬姆斯基(NoamChomsky)所言,大眾傳媒向人提供娛樂和信息,“灌輸特定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準則,以便其融入社會整體”[7](P1)。但這種價值準則往往帶有強迫性,人出于本能地進行排斥,即不能心悅誠服地領會到價值觀的真理性。因此,建構價值觀需要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心靈滋養之源泉來自于這些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生態文學作品并非僅只是對現實的摹仿,而是更多地指向未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文學比歷史更真實,因為歷史只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實,文學是講述還沒有發生、但按著某種內在規律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事。[8](P1451-1452)生態文學作品指向未來,人類社會的生態原則在生態文學作品中獲得感性的顯現,由此,讀者才能通過進入作品領會到生態原則的真理性。如果現實行為違背生態原則,讀者就會自覺地進行調整。因此,生態文學就是由于人類應用先進技術控制并攫取自然,從而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后,文學作品所進行的回應。[9](P137)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中,工業文明將文質彬彬的工廠主克里夫變成了殘疾,而護林工梅勒斯雖沒有文化,卻充滿活力,從而導致康妮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克里夫,投身梅勒斯的懷抱。按照生態文學的觀點,這其實是投身大自然的一種隱喻,喻指人類逃離惡劣的生態環境,回歸大自然。有些生態文學作品是對神話、傳說的改編。何成洲認為:“北歐的山妖神話在最近二三十年中被挪用和再創作,編制出風格迥異但又深具生態關懷的重要作品。”[10]同時,有些中國生態文學作品的創作也受西方作品啟發,二者有一定的淵源關系。阿狄生(JosephAddison)的隨筆《倫敦的叫賣聲》(OntheCriesofLondon)與劉炳善的《開封的叫賣聲》就存在淵源關系。前者借狂想客的書信講述了倫敦嘈雜的生存環境,里面充滿著對城市噪音的不滿,有的噪音還嚴重威脅到人的棲居,如一位脾胃不好的紳士出錢讓叫賣小販遠離他家的院落。最后,這位狂想客只好請求政府授命,自己對噪音進行一番整治。劉炳善譯完這篇隨筆后感慨萬千,內心涌動起豐富的生命情感,使其聯想到自己所處的生存環境,于是寫下了《開封的叫賣聲》。不同的是,他對中國傳統的叫賣聲稱贊有加,深為各行各業精致的叫賣聲所感動,但也展示了現代推銷手段的糾纏和對民眾正常生活的干擾。劉炳善在作品中對這種糾纏和干擾并未作道德評價,而是讓讀者進入作品去領會和反省。讀者在作品所開啟的世界中意識到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生存環境,領會到人會在未來的生活中有所抉擇,這是生態行為自發性的前提。生態文學作品通過其所建立的感性世界滋養人的心靈,而這一世界需要兩種方式來完成。第一是生態文學傳統,即經典的生態文學作品,如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約翰•鄧恩的詩歌、約翰•彌爾頓的詩歌、哈代的小說、加里•斯奈德的詩歌、托妮•莫里森的小說、阿特伍德的小說,等等。這些作品蘊含著豐富的生命情感,讀者一旦領會就會進入作品所建立的場域,從而獲得精神寄托。當人內心充滿生命情感時,就會產生表達的欲望,但有時又限于自身所掌握的語詞和形式的局限,不能徹底表達或完全不能表達出來,導致自己不能認清這份情感,這是痛苦的根源。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易對外部世界產生消極和否定的不良情緒,這種情緒對生活的生態化極為不利,這時需要借助經典作品。中外歷史上積淀的生態文學作品豐富燦爛,幾乎承載了人類所有的生命情感,這些作品幫助人看清自己的生命情感,能有效幫助人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第二是適合的生態文學創作,即創作出能體現當代人生存命運、容易產生共鳴,讓人獲得自我對生命情感認同的生態文學作品。世界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付出了沉重代價,社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不是某些特定的人使然,而是當代的文化病癥。這種文化病癥與經濟全球化不無關聯,資本的邏輯要求不斷增值,這一本性促使資本征服整個世界,侵襲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如波蘭尼(KarlPo-lanyi)所說,這種資本所形成的市場體系,到達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現有居民,還是尚未出生的后代,……這種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已經在全球展開”[11](P137)。當今的經濟、教育、醫療、房產等領域均已走向市場化,這一進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生態原則的迷失。民眾在現代性進程中往往隨波逐流,最后終于疲于應付資本的邏輯,感到無所適從,由此產生海德格爾所言的“無家可歸”之感。優秀的生態文學創作就是要以感性的方式建構起當代人當下的生存場域,顯現民眾的生命情感,使民眾“有家可歸”。這種生態文學作品適合性的標志就是能否承載起民眾當下的生存情感。
三、生態文學的倫理建構過程
生態文學作品是對倫理禁忌即生態危機的表達,目的是為了讓讀者引以為戒,從而選擇合乎人本性的生存方式。如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的《俄底普斯王》以神諭的方式展現了殺父娶母的倫理禁忌。這是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倫理原則。這種倫理原則以生態文學作品的形式顯現出來,讀者通過進入作品打開文本世界,領會這一倫理原則的真理性,從而在未來的生活中按感性真理的指引有所抉擇,自覺遵守倫理禁忌。在這種倫理禁忌和倫理原則的規約下,人以屬人的方式存在著,對于倫理秩序的混亂,深切領悟到危害性,并盡力阻止。這樣就容易形成人與人、人與物倫理關系的生態化。因為倫理關系不僅涉及人與人的關系,還涉及到人與物的關系,人與物不是統治與被統治、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而是一種生態的依存關系。最初,人懷有對自然的天然敬畏,認為自然世界體現了神的意志。隨著理性主義的興起,人不斷獲得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越來越多的認識,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逐漸非神化,在這個祛魅的過程中,理性處于統治地位,原來的神性由于被認為是迷信與荒謬而被排斥到邊緣的位置。人依靠理性,控制和改造著自然界。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過度發展,人的社會交往變得越來越艱難,人與人之間共同的社會時間秩序被打亂了。[12](P75-76)理性的過度膨脹造成生態危機,出現了資源枯竭、人際關系冷漠、道德淪喪等一系列問題。因為人常常以趨利避害的理性邏輯對待周圍的事物,萬事以自己的利害得失為考量原則,這就形成了人對外界索取的本性,一切以“利益優先”成為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這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表現,是生態批評反對的主要內容。埃克曼(KerstinEkman)的小說《天溝森林中的綠林好漢》(TheForestofHours)“從歷史的角度批評和質疑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尤其是那些支撐文明大廈的基礎概念,比如,主體、客體、自然、文化以及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建構的規范和制度”[10]。王諾、喬納森•萊文(JonathanLevin)等學者認為,生態危機主要的根源性問題還是在人,是人的思想與文化決定了人在這個世界中的生存方式[13](P4),而生態文學作品就是在以感性的方式培育生態的倫理關系。生態文學作品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一點,當然有其內在原因。政府制定的生態文明規則往往在社會公共領域發揮作用,而在私人領域卻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為人并沒有在內心深處領會到生態原則的真理性。生態文學作品卻能直達人的心靈,通過其語詞改變著人的言說方式,形塑著人的價值觀念,讓人在作品所打開的感性世界中領會到何為生態,何為反生態。這種感性領會與邏輯范疇的理性解讀完全不同,人在理性上能夠理解邏輯范疇,但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決定往往不是人的理性做出的,而是由人的感性力量來進行決斷。生態文學作品通過感性的方式培育著接受者的生態觀。毋庸置疑,生態文學作品在構建人類的生態世界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鮮活的生態文學形象中,人心才容易感受到真理,達到空洞的理論說教無法達到的效果。
生態文學作品通過藝術形象建立一種屬人的生存世界,讀者在生態文學作品所構建的世界中領會自身生存的意義,從而體認生態原則的真理性。正如海德格爾所言,當這種生態的真理性被攝入作品,便被去蔽,從而顯現出來,這也就是作品的美,即作品的價值所在。[14](P56)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就顯現出生態的倫理價值。老人桑提亞哥在淺海捕魚84天,一無所獲,說明淺海已經被捕撈殆盡,生態環境已經惡化。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在小說的開頭已經交代:捕魚已經不是如傳統中那樣只是滿足自己腸胃的需要,而是為了運到市場上去換來大量的貨幣。正是由于捕魚的商業化運作造成了海洋生態的惡化。桑提亞哥在捉到大馬林魚時,首先映入其腦海的便是這將換來一大筆錢。年輕人就靠出售鯊魚肝獲得的資本購置了汽艇,這種現代科技一方面提高了捕魚效率,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海生態的破壞——往日魚類豐富的淺海現在已經無魚可捕。老人在經過84天的徒勞無獲后不得已去了深海,與大馬林魚斗爭,通過運用人類的理性、計謀終于捕獲并殺死大馬林魚后,卻又引來了海洋之王——鯊魚的圍攻。深海是鯊魚的領地,社會是人的領地,老人桑迪亞哥離開了人的社會,而去了屬于鯊魚領地的深海,人與魚類共生共存的生態平衡被顛覆,最終造成人的失敗:大馬林魚被鯊魚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這對于桑提亞哥而言毫無使用價值。小說的結尾是一對情侶將大馬林魚的骨架當成了鯊魚的骨架,這寓示人類對大海的無知,在人的眼中,大海只是資源,而非一種與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存在,這造成人類對大海的過度開發、掠奪,從而造成生態倫理的混亂。海明威研究的知名學者董衡巽和顧爾科(LeoGurko)指出,有人將老人桑提亞哥當作與大自然搏斗的硬漢,尤其有些警句至今常被引用,如“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運用文學倫理學的相關思想就可以看到老人桑提亞哥是生態環境的破壞者,大馬林魚并沒有給他造成任何麻煩,他卻想出種種辦法誘騙大馬林魚吞下釣餌,繼而一步一步設法找到其藏身之處,然后抓住并血腥地殺死它,其貪婪、陰險、狡詐的形象躍然紙上。[15](P212)[16]《老人與海》的倫理價值告誡人應該按自然所賦予的尺度去生存,而不能如桑提亞哥那樣跨越這一尺度,否則將造成生態危機,人類也將遭遇失敗。只有按自然所賦予的尺度去生存,才是海德格爾所言的“詩意地棲居”。“詩意地”(poetically)不是詩情畫意,在古希臘語中,“詩意地”的意思是創造,在海德格爾這里,“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是指人要遵從一定的尺度,這個尺度屬于大地,要按照大地所賦予的尺度生存。為了領會這一尺度,人首先需要認識這個世界,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般靠理性、邏輯對世界進行處理,而是將世界看成人類的一部分,將世界看成與人類同樣平等的存在。
人屬于這個自然界,雖然具有理性,但卻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真切領會到這一世界的存在狀態,必須訴諸感性世界的建構,只有被感性構形,事物才能呈現出其本真的存在意義。領會到生態存在意義的人,才會做出生態的決斷,采取生態的行動。卡森(RachelCarson)的海洋三部曲——《我們周圍的大海》(TheSeaAroundUs)、《海風下》(UndertheWindofSea)和《海之邊緣》(TheEdgeoftheSea)通過對大海世界的感性建構,促使“民眾的環保意識開始覺醒,環保運動也逐漸興起和發展;這些作品還促使美國政府開始正視環境保護問題,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政策和法案被制定出來”[17]。由此可見,生態文學作品中有真理的發生,這種作品改變著接受者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人類社會的生態原則。生態文學作品滋潤人之“本心”,讓其培育起生態的原則,獲得精神寄托,通過其在此基礎上的外部行為,達到社會世界的生態化。生態文學作品能發揮重要的社會倫理功能,指向未來的美好世界,指引未來世界的發展。未來世界在生態文學作品中預先被演繹,接受者在生態文學作品所展開的世界中,預先知曉未來社會的狀況,作品通過改變人們的言說方式,讓人領會到生態的意義。因此,生態文學作品參與著人類的生活實踐,并為人類的未來指明方向。理性主義的單向度發展造成人與自然的失衡、人與他人的不和諧,這些都是現代性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而且無法單靠理性自身來解決。感性的生態文學作品在此將發揮重要作用,它為人的倫理道德提升提供文本,使人類在未來的倫理生活中有所抉擇,由此自覺地踐行生態原則。由于生態文學作品指向未來,一旦在生活中出現了有損生態的行為,生態文學作品就會開始發揮警示作用,讓人自然聯想到作品中描繪的生態危機的可怕后果,從而奮起斗爭,自覺規訓自身的主體行為、維護世界的生態化。如果在感性領域中缺乏對生態性的領會,人類的生態進程就會受到自覺和不自覺地阻礙。總之,生態文學作品在生態世界的構建中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為人類建立精神家園,使人獲得心靈寄托,讓人與自然、人與他人和諧相處。因此,召喚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將是時代的要求。
作者:伍艷紅;周平
- 上一篇:語境在英美文學翻譯的功能及運用范文
- 下一篇:高校黨建工作創新探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