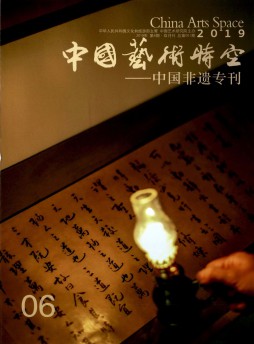徐復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心性詮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徐復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心性詮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河北學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性是“心的文化”,這一點與現代新儒家以“心性之學”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但他關于心性的闡釋則顯示出個人的獨特風格。他反對將哲學建立于“形而上的天道”的做法,認為這是將“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弄顛倒了”,“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從天道天命一步一步地向下落,落在具體的人的生命、行為之上”,并由此提出“形而中者謂之心”。他所講的心,是指“人的生理構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既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夾雜生理欲望之心,也不是西方唯心論的創造物質之心,亦不同于形而上學的抽象之心,而是通過一定的修養功夫排除了私欲與成見、回歸于本來面目的人心,即“本心”。徐復觀正是以這種心性觀來闡釋中國藝術精神的,并將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的根源歸于人的心性,試圖將世人帶入“古人所創發的‘心源’”。徐復觀所講的藝術精神,即“藝術的精神境界”,他對中國藝術精神的闡釋是在對儒、道兩家的審美心性觀的考察的基礎上逐漸展現出來的,認為中國藝術精神是在安頓現實人生、尋求心靈解脫的過程中所呈現的為人生而藝術的精神。他以仁心詮釋儒家藝術精神,以虛靜之心詮釋道家藝術精神,并以劉勰的《文心雕龍》為統一儒、道兩家藝術精神的典范。他既從心性觀角度分析了儒、道藝術精神的特質,又試圖以心性觀會通儒、道藝術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繪畫的發展史,開拓了現代中國心性美學的建構方向。
一、仁心與儒家藝術精神
徐復觀指出:“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由孔子所顯出的仁與音樂合一的典型,這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可以作萬古的標程。”他從音樂入手,以《禮記•樂記》和《荀子•樂論》為主要經典依據,分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藝術精神,進而提出,仁心是儒家藝術精神的主體,樂教是人格境界提升至仁的重要修養方法,孔子對音樂的重視及其“成于樂”之言,皆可證明孔子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典型,是儒家藝術精神的奠基人。首先,徐復觀以仁心為儒家藝術精神的根源。《禮記•樂記》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徐復觀認為,所謂“樂由中出”,即“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可以把一切的藝術追溯到藝術精神的沖動上去,因而也可以說一切的藝術都是‘由中出’”。在他看來,儒家所講的心,是經過一定的修養功夫,擺脫了其他生理活動、恢復了本來面目的心,只有這種心才能發出道德、藝術的活動,其與仁心、良心是同義語。他強調,構成音樂的三個基本要素———詩、歌、舞,皆本于心,直接從心發出來,不必假于外物,金、石、絲、竹等樂器作為音樂的外在形式,是音樂在向外發出的過程中獲得的。音樂的特點是“情深而文明”,“情深”是指它直接從人的生命根源處流出,亦即“樂由中出”。音樂之情深藏于內心深處,并且在根源上與內在的仁心融為一體,此仁心通過情的外流而“氣盛”,“于是此時的人生,是由音樂而藝術化了,同時也由音樂而道德化了”,音樂從仁心中流出而毫無痕跡,這就是儒家藝術化的人生。
《禮記•樂記》云“樂由中出故靜”。對此,徐復觀指出,此處“樂由中出”的“中”是從靜的角度而言的,所以“性德是靜,故樂也是靜。人在這種藝術中,只是把生命在陶熔中向性德上升,即是向純凈而無絲毫人欲煩擾夾雜的人生境界上升起”。儒家所講的“樂由中出”“表面上好像是順著深處之情向外發,但實際則是要把深處之情向上提”,實指“樂由性出”。此處的人性“是一片純真、純善,無外物滲擾于其間”,人性之靜就是擺脫世俗欲望之后的人心的一片純仁純善的境地。孔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倡導“無聲之樂”,因為無聲之樂正是仁的實現,所以徐復觀說:“無聲之樂,是在仁的最高境界中,突破了一般藝術性的有限性,而將生命沉浸于美與仁得到統一的無限藝術境界之中。”其次,徐復觀從樂與仁相統一的角度闡釋了儒家藝術與道德的融合。仁是道德,樂是藝術,儒家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途徑是“和”。徐復觀指出:“中與和是孔子對樂所要求的美的標準。在中與和后面,便蘊有善的意味,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尚書•堯典》中即有“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語,音樂中聲音的大小、清濁、高下、剛柔相濟相成,和諧統一,故而荀子說“樂言是其和也”(《荀子•效儒》),《禮記•樂記》也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因此,徐復觀認為,“和”是“樂的正常的本質”,“仁者必和,和中可以涵有仁的意味”。《白虎通德論》把樂與五常之仁相配合,提出了“樂仁”之說,即樂是仁的表現、流露,這揭示了樂的最深刻的意義。仁者一旦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當心內、心外皆為仁所充滿時,其精神狀態必定表現為和。
從上述兩點可見,徐復觀側重于從仁心的角度解讀儒家的藝術精神,尤其對美與善相互內在而統一的關系展開深入論證,這是對傳統儒家美學的重要推進。美與善是兩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對于二者關系的探討一直都是美學研究的重要論題。自孔子開始,儒家就堅持美善統一觀,但孔子只是提出了美善統一的理想目標,對于美善統一的根據與方法卻少有論及。此后受儒家影響的各種文化與藝術雖然也堅持美善統一,但美在多數情況下僅僅作為一種文化或藝術形式而存在,相對于作為內容的善而言,美已淪為載道的工具,其本身的價值論意義被淡化,美與善也就在實際上成為相互外在的工具及內容的關系。因此,孔子美與善相互內在而統一的理想也一直僅僅是作為一種理想形態,未得到深入論證。徐復觀指出:“樂與仁的會通統一,即是藝術與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時,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會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和統一;因而道德充實了藝術的內容,藝術助長、安定了道德的力量。”他從仁心的根源處論證了美與善是相互內在包含的關系,而不是外在的工具關系,這或許接近了孔子所言盡美盡善的真義,即“孔門通過音樂所呈現出的為人生而藝術的最高境界”。
二、虛靜之心與道家藝術精神
徐復觀指出:“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的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他認為,老、莊所建立的最高概念“道”,實際上是一種“最高的藝術精,老莊之道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格,是藝術得以成立的最終根據。老莊之道的“出發點及其歸宿點,依然是落實于現實人生之上”,“莊子也和孟子一樣,把作為人之本質的性,落實于更容易把握的心。而莊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藝術精神的主體”。首先,徐復觀提出,虛靜之心是道家藝術精神的主體。他所講的虛靜之心是由忘知而呈現的,其特征為虛、靜、明。他說:“我所寫的《中國藝術精神》,一個基本的意思,是說明莊子的虛、靜、明的心,實際就是一個藝術心靈;藝術價值之根源,即在虛、靜、明的心。”
這種虛、靜、明之心是人與自然直往直來而成就的自然之美的心,是道家藝術精神的主體。莊子以虛靜之心將審美觀照落實到人生上,即是人生的藝術化,即是可游的人生。莊子在心齋、坐忘之后以虛靈明凈之心及道與天地萬物相對無隔,無內無外,將自己的精神投入無限之中,即進入了游的境界。“上與造物者游”,“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徐復觀認為,這是由美的觀照升華到藝術精神的圣的瞬間。他將虛靜之心與現象學的純粹意識進行比較,認為“現象學之于美的意識,只是倘然遇之;而莊子則是徹底地全般地呈露”,因為凡是進入美的觀照的精神狀態,都是中止判斷之后的虛、靜的精神狀態,這正是以虛靜之心為審美觀照的主體。以虛靜之心應物所呈現的正是心與物冥的主客合一,正如莊子所言:“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用心若鏡”即以虛靜之心觀物;“不將不迎”,徐復觀將其理解為知覺直觀的情景。實現這種知覺直觀有兩個條件:一是將物脫離時空關系,呈現孤立狀態;二是不將自己的好惡成見強加于物,這樣也就能夠“勝物而不傷”。徐復觀指出:“所謂‘不傷’,應從兩方面說:若萬物撓心,這是己傷。屈物以從己的好惡,這是物傷。不迎不將,主客自由而無限隔地相接,此之謂‘不傷’。”
可見,“不將不迎”即在對主客雙方都不作人為歪曲(或屈己以從物———傷己,或屈物以從己———傷物)的自然狀態下主客體的完全呈現,此時主客完全統一于一片虛靈明凈當中,這種徹透內外的明凈正是審美觀照的實現。莊子以虛靜為體的人性自覺,將天地萬物涵攝于自己的生命之內,天地萬物皆成為有情的天地萬物,從而實現對萬物的審美觀照。其次,徐復觀分析了心齋、坐忘對于恢復心靈明靜的作用機理。在莊子看來,人心并非本然地呈現虛靈明靜的狀態,普通人的心只是世俗之心,常沉溺于對各種名利欲望的追逐之中,心之虛靜本體由此受到遮蔽。莊子以虛靜言性言心,正是要從欲望之心中超脫出來。要恢復心之虛靜,須通過心齋、坐忘的功夫。莊子對心齋的解釋是:“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他對坐忘的解釋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郭象解釋心齋為“虛其心則至道集于懷”,即摒除雜念而使心境虛靜純一。坐忘即徹底地忘已、忘身、忘世界,從而與天地萬物混然一體。徐復觀認為,心齋、坐忘既是藝術家人格修養的起點,也是其終點。
徐復觀認為,心齋、坐忘對于虛靜本體的恢復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是消解由生理而來的欲望,使欲望不給心以奴役,于是心便從欲望的要挾中解放出來。……另一條路是與物相接時,不讓心對物作知識的活動;不讓由知識活動而來的是非判斷給心以煩擾,于是心便從知識無窮的追逐中,得到解放,而增加精神的自由。”“墮肢體”、“離形”是從生理方面獲得解脫,“黜聰明”、“去知”則是從知識活動中獲得解脫。此時的主體與對象都呈孤立狀態,已從原有的時空關系中剝離了出來。在徐復觀看來,以心齋接物,不期然而然的便是對物作美的觀照,而使物成為美的對象,從而達到“物化”的境界,自己隨物而化,如莊周夢為蝴蝶,由此進入主客兩忘、主客冥合的藝術精神境界,這就實現了人的精神境界的極大自由,通過物化而實現了自身生命的美化、藝術化。自身人格的徹底藝術化是莊子藝術精神的最終落實,《莊子》中的神人、至人、真人、圣人都是這種藝術化人格的典型。
三、為人生而藝術———中國藝術精神的正統
儒家的“仁心”和道家的“虛靜之心”是心體的兩面。儒家發展了人心仁義的一面,但并不排斥虛靜的一面,孔子就提出了仁者靜的意境。道家發展了虛靜的一面,但并非完全排斥仁義的一面,老子與莊子均提出了對大仁、大義的追求。徐復觀進一步提出,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都是“為人生而藝術”,都立足于現實的生活世界,并在現實中解決問題,“為人生而藝術,才是中國藝術的正統”。“為人生而藝術”是徐復觀所借用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流行名詞,如梁啟超、宗白華、朱光潛在當時提出了“生活的藝術化”、“人生的藝術化”等口號,但他們多強調生活的趣味化、情趣化,趨于審美人格的塑造與詩性的人生,而徐復觀所講的為人生而藝術則強調道德人格的塑造以及道德人格與藝術境界的共生性。徐復觀認為,儒家的藝術精神是典型的“為人生而藝術”,它“可以作為人格的修養、向上,乃至也可以作為達到仁的人格完成的一種工夫”。從政治教化的角度來看,《荀子•樂論》曰:“樂者,圣人之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樂的教化作用可以使人民自己完成自己的人格,達到社會風俗的和諧。從個人修養的角度來看,《禮記•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徐復觀認為,“易直子諒”不應作為道德的節目來解釋,而應作為“和易、順暢、慈祥、誠實”四種道德情緒,“因為道德成為一種情緒,即成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道德與生理的抗拒性完全消失了……在道德(仁)與生理欲望的圓融中,仁對于一個人而言,不是作為一個標準規范去追求它,而是情緒中的享受”。因此,儒家的“為人生而藝術”是人生與藝術的相互成全,二者是相互內在而統一的。
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藝術精神從表面上看是“為藝術而藝術”,但其與西方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帶有貴族氣味的形式之美不同,莊子強調純素的人生與美,其本意只關注人生,而根本無心于藝術,他對藝術精神主體的把握及藝術精神的成就,是直接以人格中流出,因此徐復觀認為,“莊子和孔子一樣,依然是為人生而藝術”。雖然老子乃至莊子思想的起點不是以某種具體藝術作為其所追求的對象,但是,從老子、莊子“由修養的工夫所到達的人生境界去看,則他們所用的工夫,乃是一個偉大藝術家的修養工夫;他們由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本無心于藝術,卻不期然而然地會歸于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之上”。徐復觀指出:“莊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藝術家由此而成就藝術的作品;而莊子則由此而成就藝術的人生。莊子所要求、所待望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如實地說,只是人生自身的藝術化罷了。”
因此,莊子體道的人生正是藝術化的人生。徐復觀認為,中國藝術精神的現實發展主要表現為儒、道藝術精神的融合,而典型地將儒、道藝術精神融于一體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一方面,劉勰深受道家精神的影響,莊子倡導以“虛、靜、明”之心作為人與自然直來直往的藝術精神之主體,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提出,“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此處劉勰所言之虛靜,顯然出自道家,甚至后兩句直接引用了《莊子•知北游》中的話,明顯受到了莊子的影響。劉勰還在《文心雕龍•養氣》中提出,“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鉆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徐復觀指出:“《養氣篇》的所謂‘養氣’,上不同于孟子,下不同于韓愈,實乃道家的養生論對文學作者的進言。”另一方面,作為《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的《原道》、《征圣》、《宗經》諸篇都來自儒家,《原道》之道并非泛指天道,而是落實于周公、孔子之道。劉勰面對當時社會上沉溺于玄風的現狀,想要從形式與內容兩方面挽救當時文學的衰弊,便不得不征圣、宗經,這便由道家回到了儒家的大統,“由道家的人格修養而接上儒家的經世致用”。可見,徐復觀為了將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統一起來,尤其是在文學領域,力圖使道家的藝術精神也來承載傳播仁義的功能。
劉勰關于文學創作中的虛靜之旨,顯然不是如莊子一樣要達到徹底無我的審美狀態,而是指在文學創作之前要擺脫一切外在的個人私欲的羈絆,以保持創作的自由狀態,這既是莊子之靜的要求,同樣也是孔子之靜所具有的內容。但依劉勰征圣、宗經、文以載道的主旨,其創作之前的虛靜功夫,在拋棄小我的同時,不可能如莊子一樣將普世救世的仁心也一并拋棄。莊子是要達到審美之純粹境界,而劉勰是要原道;莊子的虛靜是一種徹底的解脫與超越,而劉勰依然是以入世為本旨。因此,劉勰的虛靜雖取言于莊子,但實質上還是孔子的虛靜。儒、道兩家作為藝術主體的心,其本質都是虛靈明靜的。徐復觀說:“虛靜之心,是社會,自然,大往大來之地;也是仁義道德可以自由出入之地。……不僅由此可以開出道德的實踐,更可由此以開出與現實、與大眾融合為一體的藝術。”
在這里,徐復觀表達了明確的會通儒、道的主觀意愿。事實上,儒家之心的虛靜從本性上說是一片純真、純善,沒有私欲和外物摻擾于其間,這種虛靜可謂是仁的另一種表述。道家之虛靜與此不同,是在經過心齋、坐忘的功夫之后,離形去智,擺脫了一切外在的生理和心理的束縛,不僅將自身從時空關系中脫離出來,而且將自己放到了“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地境界之中,此時的虛靜是超越了一切的審美的虛靜,被儒家所看重的仁義道德已無從入住其間。因此,徐復觀統合儒、道藝術精神的做法,實則有以儒解道的嫌疑。四、徐復觀心性美學建構之反思中國美學史是由現代學者回溯建構而成的,20世紀中國美學的建構主要有三種路徑:一是在中國傳統美學資源的基礎上建構中國美學,以王國維、宗白華、徐復觀等為代表;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建構中國美學,以李澤厚等為代表;三是用西方美學思想建構中國美學,以朱光潛等為代表。徐復觀從心性之學入手建構中國傳統美學,既與朱光潛、李澤厚從西方美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建構中國美學有明顯的不同,又與王國維的境界說、宗白華的律歷哲學的進路有明顯的不同。
第一,徐復觀創造性地提出了“藝術精神”概念,顯揚了中國藝術精神的文化價值。他所講的“藝術精神”即“藝術的精神境界”,亦即“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藝術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關鍵”。這種藝術精神不是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特征,雖然徐復觀專門論述了中國畫,但他未談畫的技法、線條、色彩等問題,而是從繪畫中“追體驗”藝術家的精神意境,尋找藝術作品的精神源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藝術的精神不只是一個藝術上的難題,實質上是一個哲學難題,一個屬于哲學的美學學科研究所面對的真正對象。”
因此,徐復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闡揚,雖然其所探討的對象涉及中國繪畫,但他主要是在哲學與美學的視域下進行探討,其工作屬于現代新儒家哲學與文化建構的一部分。徐復觀所講的藝術精神不同于王國維的“境界”和宗白華的“藝術境界”,王國維、宗白華強調藝術的審美價值,徐復觀則強調藝術的精神文化價值。王國維指出,“能寫真境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他所講的境界強調自然真實、沒有人為造作的真境物和真感情。境界的產生依賴于人的感覺的作用,王國維提出“以物觀物”和“自然之眼”等概念來呈現意境,正合于莊子思想中的感性直觀,強調寫景言情的真實而不假修飾。宗白華詮釋了“藝術境界”概念,他所講的藝術境界即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藝術境界主于美。”藝術境界是一個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的靈境,意境正是情景交融的結晶品。這種藝術境界的最后源泉,一方面有賴于藝術家超越尋常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則是“天地的節奏與和諧”。因此,宗白華的藝術境界剔除了道德內容,所呈現的是純粹的生命節奏的韻律。徐復觀則認為,道德、藝術、科學是人類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國文化在道德與藝術方面成就很高,中國人站在價值論的立場上實現了“主客交融、主客合一”的藝術境界,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很多偉大的畫家和作品。他反對將中國繪畫比附于西方繪畫的“寫實主義、抽象主義”。他的《中國人性論史》、《中國藝術精神》正是從道德與藝術兩方面闡發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
第二,徐復觀從心性之學的角度詮釋中國藝術精神,開拓了中國現代心性美學的建構方向。他的心性視角體現了現代新儒家重視心性之學的特色,而不同于朱光潛的心理學和宗白華的律歷哲學的美學建構進路。朱光潛注重借用西學的方法,側重于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美學,其《文藝心理學》正是這一方法指導下的成果,其“最大的局限是往往不容易上升到哲學的本體論和價值論的層面”。宗白華美學思想的立足點是中國哲學,他認為,中國哲學的本質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學,并由此出發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觀點;其所重視的是中國哲學中的生命情調與生命韻律,并由此提出一套律歷哲學:“美與美術的特點是在‘形式’、在‘節奏’,而它所表現的是生命的內核,是生命內部最深的動,是至動而有條理的生命情調。”他所重視的是生命的律動、節奏中的和諧之美。徐復觀以仁心為藝術的根源,以“為人生而藝術”作為藝術創作與欣賞的目的,相比于朱光潛、宗白華,徐復觀所講的藝術精神更注重對理想人格的塑造。
第三,徐復觀在本心的境界上超越了主客對立,不同于西方美學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他認為,西方美學多由“特定藝術對象、作品的體認,加推演、擴大而來”,而不是從人格根源處轉化出來,由此產生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中國文化則從根源之地超越了主客對立。在他看來,通過儒家的克己、寡欲或道家的心齋、坐忘功夫,將人的主觀性的束縛克除,就在本心的境界上實現了對主客對立的超越,避免了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走向。在超越主客對立的路徑上,徐復觀的心性學走向也不同于王國維和宗白華。王國維的境界說提出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問題,“有我之境”是以我觀物,物皆附上我的色彩,“無我之境”是以物觀物,以物化的方式超越主客對立,在審美境界上更勝一籌。王國維要求排除作者的任何主觀感情及個性特征,由此實現無我之境,此時的審美主體排除了生活中的私欲與利害關系,沉浸到無內無外的審美觀照之中。宗白華的藝境說則強調在情景交融中超越主客二分,意境是在藝術家的心源與外界相接觸的領悟中產生的,是客觀的外界景象與主觀的生命情感相互交融的結果。其與王國維的審美境界相類似,皆是以純粹的審美境界實現主客合一。而徐復觀則與王、宗二人不同,他的心性美學強調在仁心的根源處統合藝術與道德,在以美善統一為特征的價值論立場上,用本心的融攝性及其純靜純善的本質消融主客的界限。
第四,徐復觀將中國藝術精神的正統歸結為“為人生而藝術”,從道德與藝術相互內在的關系角度,實現了儒家美善統一論的現代轉型。他將中國藝術精神置于“整體審美意識和文化意識中來分析,從更深層次上發掘認識其美學內涵和文化品格”,著重從心性之學的角度總結中國美學“為人生而藝術”的特征。他認為,儒家之樂教的最終目標是政治教化上的移風易俗和個人人格上的美善統一,道家之悟道不期然而成就了藝術的人生,成就了圣人、至人、神人、真人的目標,二者都是“為人生而藝術”。儒、道之家的人生修養境界,最后都走向了道德與藝術的融合,實現了美善統一。孔子謂《韶》樂盡美又盡善,而《武》樂盡美而未盡善,提出了美善統一的問題。徐復觀認為,孔子將美與善對舉,說明美與善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美屬藝術范疇,善屬道德范疇,孔子之所以要求在樂中實現美與善的統一,是因為“仁中有樂”和“樂中有仁”的緣故。徐復觀通過對仁與樂的關系的考察,揭示了美與善相互內在的關系,接續了傳統儒家美善同建的人文傳統。徐復觀的美善統一論與牟宗三由圓滿的善來思考審美活動的理想境界,都是從道德的根源與藝術的本質角度闡述美的問題,體現了鮮明的價值論立場,超越了西方美學局限于認識論范圍內的美善之間的巨大鴻溝。
然而,徐復觀以“為人生而藝術”概括儒、道兩家藝術精神的特質,確有以儒統道之嫌。如果說孔子的“無聲之樂”是在仁的最高境界中實現了美與善的統一,那么,莊子的無言之美則是一種在歷經了心齋、坐忘之后與天地合一所體驗到的天地之美,是一種忘卻禮樂、排除了道德觀念的大美。劉勰的《文心雕龍》雖集儒、道藝術精神于一身,但道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人生觀方面,其關于文學創造的內容仍歸于儒家的經世致用,儒、道兩家對劉勰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徐復觀“混淆了莊學的實質和目的,卻因它追求‘純素地人生、純素地美’,而排除其‘無用’、‘無欲’、‘去知’的另一面,認為它同孔子一樣,也是‘人為生而藝術’,失之欠妥”。儒家主張道德與藝術相統一的藝術精神,而道家則強調純粹的藝術精神,徐復觀的矛盾正是由于他將儒、道兩家在人生觀上的可統一性應用于其在藝術精神上的不可統一性而產生的。
就總體而言,盡管徐復觀的心性美學在理論架構上存在一定的內在矛盾,但他在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進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藝術精神”概念,從心性之學的角度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內涵作了深入詮釋,無疑大大推進了中國現代美學的進展。雖然他坦言自己的研究目標沒有預定一個美學系統,但其實際效果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美學系統。他從心性之學的角度闡釋中國藝術精神,揭示了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對中國音樂與繪畫藝術的影響,并由此建構了中國繪畫藝術的新譜系。他并未糾纏于傳統與現代的話語藩籬,而是對中國藝術精神的特征作了現代詮釋,在中國文化重視心性修養和人格塑造的根本特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以“為人生而藝術”作為中國藝術精神的正統,從而成為中國現代心性美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作者:李春娟 單位:合肥學院 藝術設計系
- 上一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倫理維度范文
- 下一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傳播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