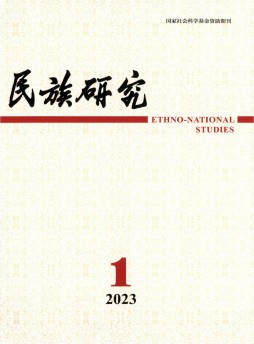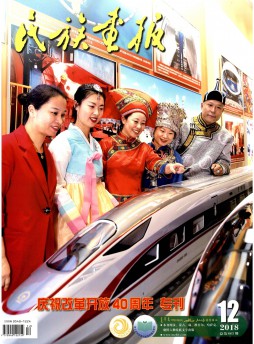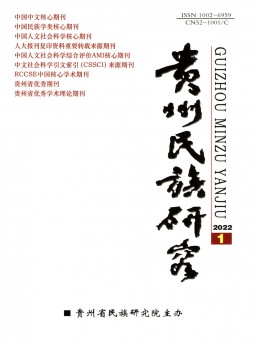民族問題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民族問題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鶻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數民族畫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對其族屬的表述紛紜。近代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兩種說法上。一說維吾爾人,一說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鄧文原在《行狀》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時用了“曾祖某”與“譜碟散佚,莫跡其所始”。可見,其曾祖父輩以上不是功業顯赫的名門,所以無事跡可述;所謂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從祖父輩移居大同的。從相貌特征上來看,潤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張雨云:“我識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澤嗜杯酒。”可見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統應該是無誤的。除了鄧文原的記載之外,相關的證據還有:“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畫似詩,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這些與高克恭同時或稍晚元人的詩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當時具有廣泛共識的。
1.名稱的由來與變遷
從字面上來看回鶻、回紇、畏兀兒、畏兀、輝和爾、瑰古、偉吾爾,均為回鶻語Uighur的不同音譯,他們雖然是同一個詞,但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指代的對象還是有區別的。回紇是唐代對袁紇與仆固、同羅、拔野古等的總稱。貞元四年(788年)自請改稱回鶻,取“回旋輕捷如鶻”之意。畏吾兒,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兩代對回鶻一詞的異譯。回回,為宋遼之際“回鶻”、“回紇”之音的誤傳誤讀。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兒人、唐兀人與欽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遺民,欽察人是欽察汗國的國民。畏吾兒人是高昌回鶻的后裔,“《元史》有時將畏吾兒人稱為回鶻人,或是稱他們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較復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概念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指來自花剌子摸的舊地,或來自更遠的中亞細亞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紀末,來華定居的穆斯林僑民,他們到中國經商,留居廣州、泉州等地,與漢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時還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現“回回”這個名詞。從廣義的概念來看,元代“回回”這個詞經常被混淆,蒙古統治者將不少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人稱為“回回”。在漢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還要廣泛,這也許是由于元朝的幅員過于遼闊,對于相對封閉的漢族來說,短期內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們無法一一理清頭緒,于是采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排除法,非漢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稱呼,用法上有點象今天的“外國人”。
2.學術界的兩種觀點
2.1回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陳垣據泰定時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為高克恭之婿,又據程拒夫《雪樓集》卷2烏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為益福的哈魯丁,系至元時回回國子學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為回回人。益福的哈魯丁為高克恭之親家,以此斷高克恭為回回人。潤又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陳垣認為:“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目之為回紇。長春西游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回紇,皆指伊斯蘭教國。其后漸覺有不同,于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惲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回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奸臣傳則稱阿合馬為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紇與回回一也”。陳高華先生的《元代畫家史料》認為“高克恭按其族源,屬于色目人”。又說:“有的記載說他是‘回紇長髯客’,可知其祖先應是伊斯蘭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為據。
潤確實在十幾歲時見過高克恭,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子敬與高克恭的關系非常好,“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同時潤在大都任職過四五年的時間。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兒”兩詞使用廣泛,潤對于有伊斯蘭教背景的人稱“回回”應該是清楚的。雖然有人認為“回紇”其實是“回回”一種比較高雅的寫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回紇”也是“回鶻”的古稱。
2.2維吾兒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卷上“古畫論”中載云:“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居官之暇,登山賞覽,喜湖山秀麗,云煙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峰巒皴法董源,云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畫也。”曹昭認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鑒賞家張丑(青夫)也沿襲曹昭的說法。從“回鶻”推斷高克恭是畏吾兒,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辭海》沿襲此說認為他是畏吾兒人,后來的書籍也亦多以此為據。當然,也有人認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馬明達先生在《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中通過對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據昆仲間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斷高克恭原名為高士安。此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們僅根據“回紇”、“回鶻”二字,來推斷高克恭是“回族”還是“維吾兒族”顯然是武斷的,因為一個民族的形成要考慮到地理位置、文化傳統、語言文字、等多個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從大的社會背景來考慮,而不要拘泥于個別的字句。
2.3民族問題的分析與推斷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時談到,其祖父高樂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時就可能已經來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將自己稱為“其先西域人”,否則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兒”豈不更好。同時“其先”是西域人,我們不僅要問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實在元代只有完全漢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漢人”,大多數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雖已高度漢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顯然還是色目人。所以《四庫總目》中的稱其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還有一些旁證:其一,從高克恭的姓氏來看,高克恭祖孫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漢族習慣,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樣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語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烏巴都刺,可見高氏家族漢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歸隱是否可以解讀為一臣不侍二主,否則與關心“經世要務”又要“歸老房山”的行為相矛盾。但這顯然不是高克恭族屬的終結,而是其華化過程的演繹。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鶻,還是高昌回鶻。首先要解開“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斷裂源于高昌回鶻的歸順,統治者出于統治的需要將西域分割為察合臺汗國與高昌回鶻國(畏吾兒)。從《長春真人西游記》與《北使記》來看,在當地伊斯蘭教徒與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鶻的統治者奉行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中亞原有的許多宗教,如薩滿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別派景教、襖教,甚至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傳統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鶻地區的擁有大量的伊斯蘭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國范圍內,西遼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統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蘭教一統。在元初“回鶻”、“回紇”只是對原西遼地區兩種不同信仰人群的稱呼,而非地理區域的劃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權的割裂,改“回鶻”為“畏吾兒”,改“回紇”為“回回”,而“畏吾兒”、“回回”在很大層面上轉化為地理區域的劃分,因此在不同時期這兩種區分是不一樣的。同時,改“回紇”為“回回”又使得他們與真正的“回回”混淆起來,這是元代統治者的另一種誤解。
從當時的角度來看,高克恭的祖先應該是西遼國人,其后入金入元;西遼的民族有回鶻、吐蕃、契丹、漢、蒙古等民族,不過回鶻占多數。高克恭是廣義回鶻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紇”還是“回鶻”,即有沒有伊斯蘭教背景,無從考證;潤的“回紇長髯客”只是孤證,而且“回紇”一詞語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蘭教背景,與高克恭的伊斯蘭教身份亦無關系。曹昭的“回鶻人”的考證也應該被看成是民族的統稱,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鶻(畏吾兒)人。高克恭的祖先離開西域的時間早于元初,在西遼的統治下并無“回紇”與“回鶻”概念的區分,所以這樣的研究是徒勞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屬于廣義的回鶻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鶻專指“畏吾兒”,而高克恭并不能確定自己是畏吾兒人,為了避免誤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劃分來看,回族與回紇、回鶻均無關系。回族雖然是回回族的簡稱,但“宋人的《夢溪筆談》和《黑韃事略》中,指的是回鶻。《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蘭教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明清的文獻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見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維吾爾族產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維吾爾族人,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推斷。
維吾爾族形成的地域主線是:漠北回鶻喀喇回鶻、高昌回鶻等西遼察合臺汗國、高昌回鶻(畏吾兒)察合臺汗國維吾爾族。宗教的傳播,伊斯蘭教從察合臺汗國傳向畏吾兒(高昌回鶻)地區。雖然在維吾爾族的形成上史學界還有爭論,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喀喇回鶻汗國、高昌回鶻汗國;從人員構成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廣義的回鶻人;在上信奉伊斯蘭教;在名稱上源于畏吾兒,即明代對元代高昌回鶻的稱謂的進一步演化。
綜上所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蘭教的民眾而逐漸形成的民族。維吾爾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鶻人皈依伊斯蘭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將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維吾爾族人,較為貼切。
參考文獻:
[1]黎東方.細說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1.
[3]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764.
注釋: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緝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元別集類》,(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傳輿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簡稱為《行狀》。
[元]潤:題高彥敬《房山圖》,載《存復齋集》卷10。
[元]張雨:高尚書山水,仲川弟請題橫幅上,載《貞居先生詩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都被稱為“回回”,如:欽察人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時亦將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稱,如稱猶太教徒為“術忽回回”,稱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為“愛薛回回”,稱信仰東正教的阿速人為“綠眼回回”。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5《美術篇·西域之中國畫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告訴他,“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值高克恭至,觀其畫轉而告訴姚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轉引自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頁。)
參見[元]鄧文原:《行狀》。
第2篇
(1)娛樂健身類功能:促進大眾的身心健康,為終身體育的開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2)政治經濟類功能:通過傳播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可以促進人們參加民族民間體育活動,促進特色體育產業的開拓。在許多民族民間體育活動中同時進行著技能交流與貿易活動。例如,傣族的“潑水節”是一個傳統節日,在節日期間,有許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參與,為該地區的貿易、旅游業等提供了強有力的發展土壤,在此過程中也加強了民族交往交流,促進了民族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繁榮。
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優化
2.1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的優化是通過系統結構的漲落有序來體現的
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優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整體優化,盡可能發揮該系統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統優化的實現,是通過系統組織、結構和功能的改進來實現的。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過程中,由于沒有有效的建立國內各地的傳播環境,政府主導與民間開發不能有效結合等多種原因,致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不能發揮整體功能。
2.1.1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要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就必須保障傳播途徑的通暢性必須保證大眾反饋的有效性,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達到該文化傳播與傳承的效果。在現有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中,如武術的傳播,包括學校、電視等都只重視動作本身的華麗,忽視了文化本身,這樣就破壞了武術傳播與傳承的整體性,致使武術文化缺失,必然導致其穩定性被破壞。
2.1.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各影響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協同關系
2.1.2.1研究目的與大眾的需求之間的協同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中受傳播的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若是研究的內容不能滿足大眾的好奇心與需求度,便會相對會抑制這一系統的有序發展,便會否定該系統的穩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內容超出大眾所現有水平,則循序漸進的向人們灌輸這一文化。從現階段的研究來看,這一文化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大眾的接受效果,阻礙了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在此方面發展較好的是濰坊風箏,在該活動中人們充分認識到了風箏的文化價值,審美價值,健身與娛樂功能,喚醒了人們的文化自覺,增強了人們的文化自信,這些就反應出了研究目的與大眾需求完美協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眾三者心理層次的協同這里指三者精神層面的高度一致性。在傳播與研究過程中,政府與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眾的心理、了解了大眾的現有精神層次,才能更好地進行研究與制定相應的措施。三者之間要形成良好的循環關系,這樣可以更好地挖掘該文化所擁有的多方面內容,更利于其傳播與傳承。
2.1.2.3政府、研究者、傳播媒介與大眾之間的協同政府與研究者向大眾輸出該文化信息或大眾向二者反饋信息都需要一定的傳播媒介,例如措施、電視,電影、物質設備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項傳播媒介都對該系統有效,應依據大眾需求、文化傳播需求、研究目的、傳播目的等選擇相應的傳播媒介。以傳統武術文化節目為例,有影響的是“武林大會”、“武林風”。這兩個節目都是技擊武術打斗的“真人秀”類型,完全撇開了傳統武術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氣、神”內核,缺少對民族民間體育文化資源的針對性傳播。如“武林大會”中就沒有充分體現北少林的剛猛強健、樸實簡練。
2.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有序結構的形式
2.2.1創設良好的環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有序結構的形成統觀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的現狀,其外界環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學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較重視體育動作的傳播,而對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則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課上講解,但由于考試重心在動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學生所忽視,這樣就間接地阻斷了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這一系統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有:
(1)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組織的開發,建立健全各級負責機構和組織,例如民族民間體育文化調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組織,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公司等等。
(2)建立民族民間體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開拓眼界,豐富自己的方法、視域等,構建起政府與研究者的良好橋梁。在學校中應重視相關人才的培養,使其能達到政府與大眾的要求。
(3)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中,缺少傳播手段與途徑,在現階段應有效利用電視、電影、娛樂節目,如云南白藥廣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體育文化進行創意,也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思維,進行網站設計、網上交流站的開發等。
(4)加強民眾的主動傳播意識,喚醒大眾的文化自覺,增加民眾反饋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與大眾文化主體之間可以有效循環。
2.2.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承系統各要素的質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應該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內容,具有自我調節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見。現在研究者的情況為研究力量比較零散,單兵作戰,研究方法較比較單一,視域狹窄,專業性較差,在今后的培養中,應針對這些問題作出相應的培育措施,如:定期舉行學術交流會、讀書報告會等。
(2)大眾大眾應具備一定的文化自覺性,具有積極參與民族民間體育活動的愿望、動機和興趣,并具備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運動經驗、能力和運動技能儲備,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具有穩定的群眾基礎,促進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確、清晰以及具體,以傳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民族民間體育活動為最終的目的,在研究過程中應根據實際情況來制訂相對區間和時期的目的。
(4)傳播內容傳播內容要寬泛,不能僅局限于身體活動,應當全面地進行傳輸,在以身體活動為重心的情況下,適當地進行文化引導,發揮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整體功能。
(5)傳播媒介與研究方法在傳播與研究過程中方法,手段要具備多樣性并必須適應于這一過程,如研究方法可以運用自身體悟法來進行研究,傳播媒介的物質條件要充足,充分利用電視、電影廣告,網絡空間等。
第3篇
論文題目: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傈僳族“阿尺木刮”
一、選題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著極為豐富的民歌樣式及種類,在人類學的視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傳統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與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產方式而形成的極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達的重要民俗藝術事項。長期以來,音樂學界對維西地區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圍繞音樂形態、音樂種類等方面進行的記錄和調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環境、生成因素以及在歷時與共時的交集中所產生的文化意義卻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研究。作為最能真實直接表達文化個性的民間歌舞事象,是每個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不能脫離它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和生態環境,不能脫離其生長、延續的空間、時間以及人們的音樂行為。一次偶然的機會,由黃凌飛老師引薦跟隨著云南大學的羅梅老師,一同前往怒江參加傈僳族的闊時節活動,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阿尺木刮”這一具有傈僳族傳統氣息的歌舞種類,讓筆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滿張力的文化獨特性,故選擇其為碩士階段畢業論文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一)選題目的
1、當今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作為人類文明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場革命。無論是從人最為基本的人權問題開始發生了改變,還是從學術研究上都有了質的飛躍。“阿尺木刮”是維西縣特有的傈僳族傳統歌舞,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社會的關注度較為廣泛,將這個地區的音樂,作為文化的重要特征進行研究時,應該考慮到這個地區各個族群之間音樂文化內在的本質。將云南滇西北地區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樂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理論方法背景中。筆者試圖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通過對維西地區傈僳族“阿尺木刮”這一歌舞生態系統的實地考察分析,運用音樂民族志的分析和音樂民族志的書寫方式來呈現文本,這樣對“阿尺木刮”進行專門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在以往的研究中,對于傈僳族“阿尺木刮”過多地運用音樂本體來分析其的音樂的特征,對于這個民族的認知方式、概念體系、音樂行為的描述很少。只有對于這個民族音樂文化的地方性知識的挖掘和闡釋,才能夠從生成機制中更好地傳承和保護該民族的音樂。
(二)研究意義
在研究對象確立的同時,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和其音樂文化的地性知識,力圖客觀地呈現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和價值。通過對“阿尺木刮”所依賴的生態環境進行調查和分析,對其文化內涵、族群中的族性認同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更深刻地認識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預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運用音樂民族志這樣一種闡釋性的理論范式;以文化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為理論視角,將維西地區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聲音及意義的社會背景中,拓寬了藝術審美的視野與領域。人類學家賴斯先生在梅里亞姆的三維模式基礎上所提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持——個人創造和體驗”整體模式的運用,體現重視共時研究與歷史性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取向,為中國民族藝術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過對于維西地區傈僳族村落調查,以個案的形式對其進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資料,對“阿尺木刮”進行音樂人類學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過理論的層面闡釋“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內涵和其背后的意義,并使的維西地區傈僳族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等得到多維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夠更好的認知傈僳族的文化內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維西傈僳族文化學者林永輝收集整理的《維西縣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對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論述的:傈僳族是我國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經歷了漫長的遷徙,直至怒江州、迪慶州維西縣一帶。“阿尺木刮”是維西地區傈僳族祖先創造且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歌舞事象,當地人在長期的游牧、遷徙生活中,與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過模仿山羊的聲音和動作形成的一種相互間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維西縣文化館非遺在中心主任和瓊輝老師講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圖騰,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傳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麗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頭人看上了,頭人想要娶這位女孩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這門婚事,連夜她就抱著兩頭小羊上山去了,為此躲避頭人的婚禮。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無時無刻地覺得孤獨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當作自己的朋友,跟它們交流。她學習羊的叫聲來唱歌與羊進行對話,學習羊的動作來跳舞與羊進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這種舞蹈,并且得以傳承下來。在“都市時報2008~2009‘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尋蹤’系列報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論述為:“傈僳族屬南遷的古氐羌人,從古代移民的畫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蕩蕩的移民大軍,在漠北悠遠的星空下南遷,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領們會選擇適當的節日祭祀,祭祀的羊兒歌舞即是起源。”
葉枝鎮新洛村“阿尺木刮”國家級傳承人熊自義老人告訴筆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幾乎與外界不往來,天長日久都過著采集、狩獵、游牧的生活。與山羊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將山羊放到山上,在這個孤獨寂寞的過程中放牧的傈僳人與羊朝夕相處,時常觀察著山羊的聲音、動作和體態,觀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時候的各種習性,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們的動作和聲音。日積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樂村大村一直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有關于“阿尺木刮”的美麗傳說“相傳同樂村在最早的時候是不叫同樂的,以前是叫“羅托臘”,在幾百年前,有兩個夫妻從外面私奔而來,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邊。但是他們兩個沒有后代,只是孤獨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時間后來了一對年輕的夫妻,老的夫妻問他們“你們從來哪里”,他們回答說“我們來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來你這里住嗎?”回答說“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過程中,他們就聊了彼此的來意,如他們是從哪里來到這的、他們叫什么名字等等,在這樣的聊天中兩對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輕的夫妻問他們,這個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長的夫妻說名字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來的時候帶著一匹小駱駝,在用我們的當地話來說就是“羅托臘”也就是駱駝來的意思,那么我們就把這里叫做“羅托臘”這個名字。年長夫妻說“我們兩個是因為彼此間相親相愛才跑到這里來生活的,而你們是因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來到這里的,我們情況都一樣,要不我們就做一家人吧”,從此這四個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通過大量的查閱相關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會歷史調查等文獻資料,了解維西地區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關記載與知識背景,通過對文獻資料的分析、比較、收集和整理以及歸納以往研究成果,從其中探尋出自己的研究視角以及切入點。
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維西縣的葉枝鎮及周邊村寨進行田野調查,運用主位與客位進行系的統調查,從個案入手,主要是對當地民間傳承人、當地的領導部門、參與活動的群眾等不同人群多方面進行采訪,觀摩并加入到當地群眾舉行“阿尺木刮”的活動,走訪當地民俗生活,向當地民眾研習“阿尺木刮”的方式、意義等,以便后期研究。筆者以局外人的視覺和局內人的視覺參與和觀察的雙重身份開始調查工作,與當地的傈僳族族群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習俗、思維方式等文化構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與行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將第一手田野資料與田野資料結合,從中尋找新的發現和視角。
五、寫作提綱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緒論7-11
(一)選題緣起7
(二)選題目的7
(三)研究意義7-8
(四)研究現狀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獻搜集法10
2、田野調查法10
3、深描10
4、綜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發生的生態環境11-17
第一節“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態空間11-13
第二節“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態空間13-17
一、服飾、飲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風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歷史記憶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動17-26
第一節“阿尺木刮”的歷史記憶17-20
一、傈僳學者的“阿尺木刮”記憶17-18
二、傳承人的“阿尺木刮”記憶18-20
第二節“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動20-26
一、展演活動相關概述及其活動說明20-22
二、展演活動過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構成要素26-35
第一節“阿尺木刮”的構成要素26-30
一、歌詞特征26-27
二、音樂形態特征27-29
三、體態特征29-30
第二節代表性藝人訪談實錄30-35
一、歌者熊自義30-31
二、李碧清與“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讀35-45
第一節“阿尺木刮”的時空構成與音樂行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時空構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樂行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傳達的社會秩序37-39
第二節“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歷史構成39-40
二、社會群體維護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個人創造和體驗中的“阿尺木刮”43-45
結語45-46
參考文獻46-47
附錄一47-49
附錄二49-51
致謝51
六、目前已經閱讀的主要文獻
[1]杜亞雄:《民族音樂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
[2]陳一.:傈僳族原始宗教與原始文化[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06)
[3]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云南省編輯組.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
[4]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云南省編輯組.傈僳族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5]管建華:《音樂人類學的視界》,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管建華:《音樂人類學導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7]黃昌莉.從創世神話中探討傈僳族的遠古生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1,(01)
[8][美]克利福德.格爾茲:《地方性知識》,王海龍、張家譯,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
[9][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自強.三江奇韻[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8
[11]林永輝.維西傈僳族民間音樂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12
[12]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
[13]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14]魯建彪.傈僳學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1
[15]馬世雯.傈僳族的傳統思想及其當代社會觀念的演變[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05);
[16]聶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4
[17]彭兆榮:《族性的認同與音樂的發生》,中國音樂學(季),1999年第3期;
[18]斯琴高娃、李茂林.傈僳族風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5
[19]斯陸益.傈僳族文化大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1
[20]田聯韜:《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1]湯亞汀:《歷史思潮與方法論》,上海高校音樂學院人類學E-研究院;
[22]湯亞汀:《西方民族音樂學方法論概要》,(上、下),載《中國音樂學》(季刊);
[23]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縣志編委會,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縣志,[M],云南:維西傈僳族族自治縣縣志編委會辦公室,2006年
[24]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文化體育局:《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民族民間傳統文化普查資料集成》,2006.10
[25]《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云南省編輯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26][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M].維西: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志編委會辦公室編印,1994.6
[27]楊曦帆.藏彝走廊樂舞文化選點考察與研究[D]:[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7
[28]楊杰、賀麗芬.傈僳族的圖騰與姓氏[J].民族文化研究,2001.4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