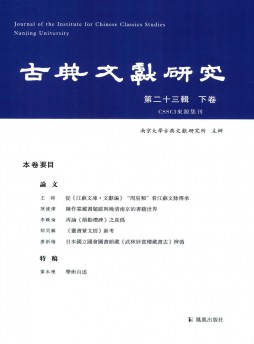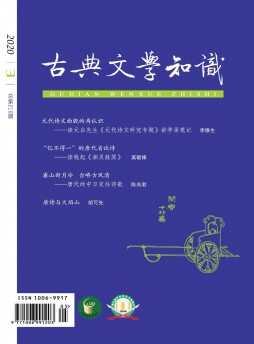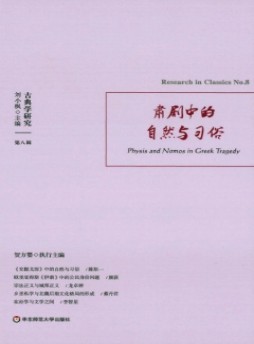古典文學(xué)總集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古典文學(xué)總集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我國(guó)古典散文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它與古詩(shī)一樣在古代文學(xu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歷史上也涌現(xiàn)出很多大散文家,漢代的楊雄、司馬遷、張衡、賈誼,魏晉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淵明以及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yáng)修等等,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漢時(shí)期散文就開始形成了,并產(chǎn)生敘事以及議論兩種形式。到南北朝時(shí)期散文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哲理政論等等形式的散文體層出不窮,散文家也是數(shù)不勝數(shù)。唐宋年間散文到了一個(gè)更加繁榮的時(shí)代,在這個(gè)時(shí)期描寫景物進(jìn)而來(lái)表現(xiàn)作者內(nèi)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歐陽(yáng)修的《醉翁亭記》、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記》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現(xiàn)了市井民眾所喜愛的適情作品。我們現(xiàn)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為基礎(chǔ)發(fā)展而來(lái)的,雖然格式上沒有以前沒那么嚴(yán)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現(xiàn)代的散文依舊和古代散文一樣語(yǔ)言優(yōu)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現(xiàn)代散文有時(shí)為了讀得更加流暢也會(huì)力求押韻,這都是古代散文對(duì)現(xiàn)代散文的影響。現(xiàn)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發(fā)展和繼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鎖,繼承了其優(yōu)美的語(yǔ)言和特有的表達(dá)方式,最終形成現(xiàn)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說對(duì)現(xiàn)代小說的深遠(yuǎn)影響
在古典文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影響的幾個(gè)表現(xiàn)中,古典小說對(duì)現(xiàn)代小說的影響是最明顯的。諸如魯迅將《儒林外史》這部作品的諷刺藝術(shù)應(yīng)用到自己的小說中,可以說時(shí)時(shí)可見。在《故事新編》這部小說中,魯迅應(yīng)用了大量的歷史傳說,以及古代神話,也就對(duì)古典小說因素的借鑒。同時(shí),魯迅的小說還有一個(gè)行文簡(jiǎn)潔的特點(diǎn),這也是對(duì)傳神寫意的良好借鑒。在魯迅之后,便出現(xiàn)了諸如郁達(dá)夫、孫犁等抒情小說家。這些抒情小說作品在對(duì)傳統(tǒng)詩(shī)歌抒情特點(diǎn)繼承的基礎(chǔ)上,更具有屬于自己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思想。出自郁達(dá)夫之手的小說《采石磯》,引用了大量的中國(guó)古詩(shī)詞,同時(shí)還有《遲桂花》等非常注重營(yíng)造良好的意境。此外,還有一批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小說家,他們通常更加注重小說的故事,不論是小說結(jié)構(gòu),還是小說語(yǔ)言,甚至是小說的表現(xiàn)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古典小說的結(jié)構(gòu)、語(yǔ)言,以及方式等。諸如出自趙樹理之手的《登記》以及《小二黑結(jié)婚》等都對(duì)白描手法進(jìn)行了集中的應(yīng)用,對(duì)于小說故事性的特別強(qiáng)調(diào),而且還在道具運(yùn)用等方面對(duì)古典小說進(jìn)行了一定的借鑒,這樣的白描方法與話本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有著相似性。在我國(guó)的現(xiàn)代文學(xué)中,還有一個(gè)分支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通常采用古典小說中的結(jié)構(gòu)形式與敘事方法,諸如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廣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狹義英雄傳》等等。
三、古典戲劇對(duì)現(xiàn)代話劇的深遠(yuǎn)影響
與前面敘述的詩(shī)歌、散文以及小說相比較,現(xiàn)代話劇與古典戲劇之間的聯(lián)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系還是存在的,古典戲劇對(duì)現(xiàn)代話劇的深遠(yuǎn)影響還是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的。我國(guó)現(xiàn)代從事于戲劇舞蹈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劇作家大都非常重視古典戲劇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yàn),吸取古典戲劇的精華。諸如的《雷雨》,整個(gè)戲劇的情節(jié)非常符合大眾的胃口,曲折的情節(jié)迎合了觀眾的欣賞習(xí)慣,尤其是大眾對(duì)于故事性情節(jié)的欣賞習(xí)慣。整個(gè)劇目通過對(duì)戲劇沖突進(jìn)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將整個(gè)故事情節(jié)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劇目的階段,廣大觀眾的心弦被緊緊地扣住了。與此同時(shí),我國(guó)的古典戲劇在情景交融方面有著獨(dú)一無(wú)二的特色,對(duì)于詞句的寫作更是備加注意。在戲劇中的詩(shī)詞,通常都是抒情詩(shī),意蘊(yùn)深厚。而在我國(guó)的現(xiàn)代話劇中往往正是缺乏這樣的詩(shī)意濃厚的作品,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國(guó)的時(shí)期,出現(xiàn)的新歌劇同樣也對(duì)古典戲劇的一些特點(diǎn)進(jìn)行了一定程度的繼承與發(fā)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變化的戲劇情節(jié),可讀性強(qiáng)的故事,同時(shí)在整個(gè)劇目的結(jié)構(gòu)上更是對(duì)古典戲劇的寫意方法進(jìn)行了全面充分的運(yùn)用,此外在音樂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節(jié)中與民歌、戲曲的一些素材結(jié)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大幅度的創(chuàng)新。在延安進(jìn)行舊劇改革時(shí)期,曾經(jīng)涌現(xiàn)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編歷史劇,這些劇目均是古典戲劇的演變與發(fā)展,是現(xiàn)代戲劇家對(duì)古典戲劇的創(chuàng)新與改革。
四、古典文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內(nèi)容上的深遠(yuǎn)影響
我國(guó)古典文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影響除了體現(xiàn)在以上四個(gè)方面以外,還有就是主題內(nèi)容上的影響。我國(guó)的古典文學(xué)作品中,在主題內(nèi)容方面也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造成了很深的影響。諸如愛國(guó)主義是我國(guó)古典文學(xué)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突出主題,其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影響非常大。再如我國(guó)著名文學(xué)家魯迅、聞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將前輩的愛國(guó)主義精神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詩(shī)經(jīng)》作為我國(guó)第一部詩(shī)歌總集,諸多內(nèi)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實(shí)際苦難,對(duì)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諸如艾青和魯迅的作品,都對(duì)《詩(shī)經(jīng)》中的風(fēng)雅進(jìn)行了一定的借鑒,同時(shí)還有《詩(shī)經(jīng)》中體現(xiàn)出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也在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鑒與應(yīng)用。《詩(shī)經(jīng)》通過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將下層人民群眾的辛苦勞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環(huán)境、生存狀態(tài)等充分地反映出來(lái),表達(dá)出人民群眾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阿Q正傳》作為魯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國(guó)的土地上》作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將現(xiàn)實(shí)主義體現(xiàn)出來(lái),表達(dá)出下層勞動(dòng)人民對(duì)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對(duì)政府救治的渴望。
第2篇
但是,慶歷以后,文風(fēng)丕變,流行五百年的《文選》的影響,呈式微之勢(shì)。陸游《老學(xué)庵筆記》卷八:“國(guó)初尚《文選》,當(dāng)時(shí)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呼‘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后,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見宋代文壇風(fēng)尚的變遷。
慶歷前后文學(xué)趣味的轉(zhuǎn)向表明,一個(gè)時(shí)期以為雅的東西,到另一時(shí)期則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雖然《文選》曾經(jīng)是、現(xiàn)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畢竟已被文人用得“爛熟”了。任何一種風(fēng)尚,一旦至于爛熟,必歸于俗,必遭厭棄。否棄《文選》,是符合美學(xué)上所講“陌生化”理論的。
而否棄《文選》之所以發(fā)生在慶歷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學(xué)經(jīng)歷了七八十年的發(fā)展,隨著宋代文人時(shí)代感與文學(xué)自信的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隨著范仲淹、梅堯臣、歐陽(yáng)修等當(dāng)代典范的樹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塵,而以學(xué)《文選》為陳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這些文章巨公周圍,已然生出大批追隨者,成長(zhǎng)為具有轉(zhuǎn)移風(fēng)氣意義的文學(xué)群體。因此,必然產(chǎn)生文學(xué)的代際,從而與前朝文學(xué)取向拉開距離。
帶頭唱響《文選》時(shí)代挽歌的,正是后來(lái)成為宋代文學(xué)巨擘的蘇軾。蘇軾對(duì)待《文選》的態(tài)度具有典型性。他幾乎凌駕于這部被前人極力推崇的文學(xué)經(jīng)典之上,敢于批評(píng)其不足。在他眼里,這部書不僅沒有因數(shù)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許神秘感,反而徹底揭開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紗。“恨其編次無(wú)法,去取失當(dāng)”,又說“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tǒng)尤為卑弱”。蘇軾這種平章古今、睥睨《文選》的姿態(tài),標(biāo)志著宋代新文學(xué)的成熟和新的文學(xué)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形成。
宋詩(shī)之所以在整體上能夠走出以《文選》為祈向的古典時(shí)代,還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們太熟悉這個(gè)時(shí)代,在他們筆下,平凡與不平凡,平淡與不平淡,雅與俗,都隨緣自然,在在共存。它們洗凈了六朝的綺靡,選擇了素樸淡雅的主導(dǎo)風(fēng)尚。
第3篇
1古典文學(xué)作品為傳統(tǒng)醫(yī)學(xué)提供傳播載體
上古之人,對(duì)于自然、社會(huì)和人的認(rèn)識(shí),還沒有形成理性意識(shí),文化呈現(xiàn)原始綜合態(tài)勢(shì),這種態(tài)勢(shì)成為古代孕育各門知識(shí)最初的搖籃,中國(guó)傳統(tǒng)醫(yī)學(xué)與古典文學(xué)的融通關(guān)系就是在這種原始態(tài)勢(shì)的影響下孕育起來(lái)的。當(dāng)傳統(tǒng)醫(yī)學(xué)還沒有從原始綜合文化體分離出之前,最早的文學(xué)樣式民歌、民謠,就已經(jīng)成為醫(yī)學(xué)的重要文字傳播載體。成書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國(guó)第一部詩(shī)歌總集《詩(shī)經(jīng)》,可謂是一部以詩(shī)傳醫(yī)的早期佳作。《詩(shī)經(jīng)》匯有詩(shī)歌305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社會(huì)生活,也較廣泛地記錄了陰陽(yáng)、五行、臟腑、疾病、藥物、治療、保健等醫(yī)學(xué)內(nèi)容。《詩(shī)經(jīng)》記錄各種花草約有149種,可以作為藥物的約60種,如芣苢,即車前子;蝱,即貝母。其中木本藥物約20種,如桐、柏、梨、槐等;蟲類藥物約90種,如蟾蜍、蠆(全蝎)、蛇等。《詩(shī)經(jīng)》對(duì)疾病也有了廣泛的認(rèn)識(shí)和記錄。如《國(guó)風(fēng)•卷脈唯從肉上行,如循榆莢似毛輕,三秋得命知無(wú)恙,久病逢之卻可驚”[2],短短四句把浮脈的脈位、脈象、臨床意義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賦體裁用以解說中醫(yī)藥知識(shí),使詩(shī)歌和醫(yī)理互融,于是枯燥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變得容易理解和掌握。歷史上許多醫(yī)學(xué)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學(xué)價(jià)值的作品。當(dāng)我們閱讀這些中醫(yī)古籍時(shí),體驗(yàn)到的是林間漫步的怡然,以及與智慧和自然對(duì)話的深邃。譬如現(xiàn)存中國(guó)古代第一部經(jīng)典醫(yī)著《黃帝內(nèi)經(jīng)》就是以對(duì)話文學(xué)為體裁編撰的,其開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yáng),和于術(shù)數(shù),飲食有節(jié),起居有常,不忘勞作,故能形與神俱,而能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用古典文學(xué)浪漫主義手法陳述了傳統(tǒng)醫(yī)學(xué)天人感應(yīng),陰陽(yáng)合一的醫(yī)道。
2古典文學(xué)作品蘊(yùn)涵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知識(shí)
自《詩(shī)經(jīng)》以來(lái),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涉醫(yī)內(nèi)容豐富,幾乎涉及中醫(yī)藥各方面的知識(shí)。舉凡疾病診療、中草藥知識(shí)、針灸,乃至氣功、養(yǎng)生之道等等,無(wú)一不在古代文學(xué)中得到充分的描寫。中國(guó)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曉醫(yī)道,有些人還親身從事過醫(yī)藥實(shí)踐。由于具備醫(yī)藥的知識(shí)背景和人生經(jīng)歷,因此他們創(chuàng)作的作品中的醫(yī)藥內(nèi)容,往往有科學(xué)或經(jīng)驗(yàn)的依據(jù),真實(shí)可信。先秦時(shí)期《左傳》、《莊子》、《呂氏春秋》等書都可見到不少醫(yī)藥寓言故事。在《三國(guó)演義》、《金瓶梅》、《紅樓夢(mèng)》、《醒世姻緣傳》、《老殘游記》等名著中所包含的豐富的醫(yī)學(xué)思想更是舉世罕見。羅貫中的《三國(guó)演義》就曾多次借用書中人物之口,描寫了劉備的痢疾,姜維的心絞痛,司馬昭的中風(fēng),曹操的頭疼等等。文學(xué)對(duì)醫(yī)學(xué)知識(shí)的靈活運(yùn)用,反映出不同時(shí)期醫(yī)學(xué)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況,也使得文學(xué)作品更加再現(xiàn)了生活的真實(shí)性。小說《鏡花緣》寫了17個(gè)醫(yī)方,或?yàn)樽髡呃钊暾渌詳M,或?yàn)槊耖g驗(yàn)方,都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清代醫(yī)家陸以湉《冷廬雜識(shí)》[3]嘗謂:“《鏡花緣》說部征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有人作過統(tǒng)計(jì)[4],《紅樓夢(mèng)》涉及疾病114種,方劑45個(gè),藥物約120種,書中用大量筆墨描述了弱不禁風(fēng)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診斷過程,“兩彎似蹙非蹙柳葉眉,一雙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醫(yī)看來(lái)就是肺腎陰虛。這些有關(guān)疾病醫(yī)療的描寫,不僅從一個(gè)側(cè)面著實(shí)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運(yùn),也生動(dòng)闡述了大量的醫(yī)理,推動(dòng)著性格與情節(jié)的發(fā)展。有的情節(jié)甚至直接表達(dá)出了作者的醫(yī)學(xué)觀點(diǎn)和見解。書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賈府保健醫(yī)生王太醫(yī)給林黛玉的診療過程:“六脈弦遲,素由積郁。左寸無(wú)力,心氣已衰。關(guān)脈獨(dú)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dá),勢(shì)必上侵脾土,飲食無(wú)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紅樓夢(mèng)》就有如此豐富的醫(yī)藥內(nèi)容,由一斑而窺全豹,可見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作品中所蘊(yùn)涵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之宏富了。傳統(tǒng)醫(yī)藥素材豐富了古典文學(xué)的內(nèi)涵,為古典文學(xué)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學(xué)的社會(huì)價(jià)值,成為傳統(tǒng)醫(yī)學(xué)與古典文學(xué)融織的結(jié)晶。與此同時(shí),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所反映的豐富的醫(yī)學(xué)素材,實(shí)質(zhì)也反映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的豐富內(nèi)容,可以看到傳統(tǒng)醫(yī)學(xué)對(duì)人們防病治病、養(yǎng)生保健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興盛所做出的貢獻(xiàn)。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醫(yī)學(xué)廣泛地浸透到不同時(shí)代人們?nèi)粘I畹母鱾€(gè)領(lǐng)域,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心理、行為和風(fēng)尚。
3傳統(tǒng)醫(yī)學(xué)作品承載文化內(nèi)涵
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是醫(yī)學(xué)的基礎(chǔ),是習(xí)醫(yī)者必備的文化素養(yǎng),歷代名醫(yī)無(wú)不運(yùn)用文學(xué)來(lái)編纂和撰著,以闡明醫(yī)理。中醫(yī)學(xué)很多寶藏,都保存在歷代文獻(xiàn)里,通過書面語(yǔ)言保留下來(lái)。醫(yī)學(xué)家沒有一定的文學(xué)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繼承下來(lái),更談不到整理、提高、發(fā)揚(yáng)。可以說凡醫(yī)學(xué)之有成者,無(wú)不嫻熟于文學(xué),只有這樣才能夠通過優(yōu)美的文字語(yǔ)言,促進(jìn)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中醫(yī)家歷來(lái)將文、史、哲作為治學(xué)的基礎(chǔ),沒有這個(gè)基礎(chǔ),是很難深刻領(lǐng)悟醫(yī)道的。清代醫(yī)家陸以湉[5]說:“醫(y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癥。”明代李梃在《醫(yī)學(xué)入門•習(xí)醫(yī)規(guī)格》寫道:“蓋醫(yī)出于儒”,正說明文學(xué)為醫(yī)學(xué)家構(gòu)筑文化底蘊(yùn),文學(xué)可以幫助醫(yī)學(xué)家加深對(duì)“人”的體驗(yàn),對(duì)人的社會(huì)性的認(rèn)識(shí)。醫(yī)儒不分,由儒而醫(yī),是中國(guó)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縱觀中醫(yī)發(fā)展史上,不少著名醫(yī)家是從飽讀經(jīng)書的秀才走上醫(yī)學(xué)道路的,在中醫(yī)史上,醫(yī)學(xué)家兼通醫(yī)學(xué)與文學(xué)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醫(yī)、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稱為“中醫(yī)針灸學(xué)之祖”的魏晉著名學(xué)者皇甫謐,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寫有《帝王世紀(jì)》、《高士傳》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癱瘓,憤而學(xué)醫(yī),所撰《針灸甲乙經(jīng)》成為針灸學(xué)奠基作之一。在這樣一部醫(yī)學(xué)巨著里,我們可以窺視到他的哲學(xué)觀點(diǎn),他在《針灸甲乙經(jīng)•精神五臟論》[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也。”體現(xiàn)了氣是構(gòu)成萬(wàn)物生命的根源這一哲學(xué)觀點(diǎn)。東晉著名醫(yī)學(xué)家葛洪精通文學(xué)和哲學(xué),他的文學(xué)代表作古記小說集《西京雜記》被魯迅先生稱為“意緒秀異,文筆客觀”。而他的著名理論著作《抱樸子》是研究我國(guó)晉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寶貴材料,這部著作不僅論述了神仙、煉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樸子內(nèi)篇•仙藥》中對(duì)許多藥用植物的形態(tài)特征、生長(zhǎng)習(xí)性、主要產(chǎn)地、入藥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詳細(xì)的記載和說明,對(duì)我國(guó)后世醫(yī)藥學(xué)的發(fā)展更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北宋范仲淹倡導(dǎo)“不為良相,當(dāng)為良醫(yī)”的人生理想,曾對(duì)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觀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大的影響。事實(shí)上有不少文人學(xué)士皆通醫(yī)道。如白居易、蘇軾、司馬光、沈括、陸游、元好問、蒲松齡、劉鶚等文學(xué)家雖不以醫(yī)名世,他們皆有關(guān)于醫(yī)學(xué)的論作。以博學(xué)和才情著稱的蘇軾,就曾寫有《人參》[8]一詩(shī):“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fēng)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綴紫萼,圓實(shí)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wú)炮制,龁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詩(shī)中生動(dòng)地描繪了它的形態(tài)、特性,介紹其服法和功用。文、醫(yī)皆通的東坡居士,將詩(shī)興與學(xué)識(shí)及人生感悟熔為一爐。文學(xué)家把在文學(xué)中關(guān)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轉(zhuǎn)向?qū)︶t(yī)學(xué)思想的審視。醫(yī)學(xué)家通過文學(xué)藝術(shù)來(lái)體驗(yàn)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過文學(xué)作品了解諸如人們抵抗病痛時(shí)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反應(yīng),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們?cè)诓煌谋尘跋碌男睦怼⑺枷牒颓榫w,從而加深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可以說古典文學(xué)奠定了醫(yī)學(xué)家堅(jiān)實(shí)的生活基礎(chǔ),提供了豐富的知識(shí)儲(chǔ)備,使得傳統(tǒng)的醫(yī)學(xué)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當(dāng)高的文學(xu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