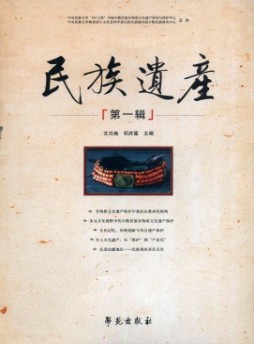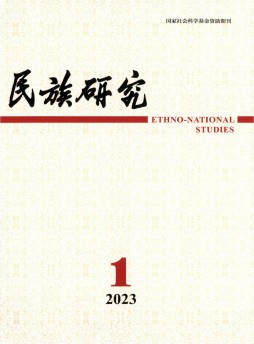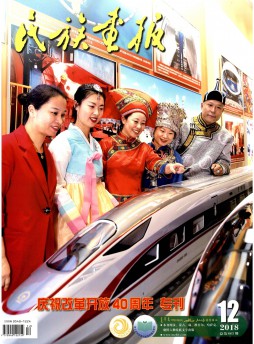民族聲樂藝術中的地位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聲樂藝術中的地位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民族聲樂藝術風格概述中國民族聲樂藝術是具有我國自身特殊性、民族風格多樣的歌唱表現形式,它是聲樂藝術的音樂表現形式之一。民族聲樂學科經歷著由傳統民族民間流傳的歌唱唱法階段,上升到對傳統聲樂進行系統專業的科學研究。到20世紀初西方音樂傳入中國,一批留學歸國的作曲家為中國的聲樂藝術創作,注入了新鮮血液,其作品將西方作曲方法與我國音樂風格相結合,創作了不少優秀民族聲樂作品。與此同時,西洋美聲唱法也進入中國,在演唱方法和表演形式上不斷借鑒和吸收,使中國民族聲樂藝術更為豐盈,體現出傳統風格與時代潮流相結合的創造性審美特征。發展至21世紀的今天,出現了中西聲樂文化不斷碰撞、交流、借鑒相結合的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當代中國民族聲樂演唱風格,融入了更多時尚氣息,與社會時代的發展緊密聯系,藝術形式更加多樣化、個性化。傳統與時尚的辯證統一,體現了我國聲樂藝術吸納百川,不斷發展與創新的美學思想。當代我國聲樂美學,是在中國傳統聲樂美學思想的基礎上,與西方音樂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動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發展,形成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綜合性的美學特征。在借鑒西洋美聲唱法的同時融入我國古代聲樂藝術、傳統民族民間歌曲藝術、戲曲藝術的一些技法,從而更好地歌唱出民族的藝術風格。在歌唱技法咬字吐字、行腔、聲腔、表演風格上有別于傳統的民歌、戲曲,與西洋美聲唱法有著一定的共性特征。民族聲樂歌唱的音色色彩不同于西洋美聲唱法,有著“甜、柔、亮、脆”的聲音色彩,合理借鑒美聲發聲方法并與中國的語言曲調相結合,使我國民族韻味的語言和行腔曲調建立在氣息共鳴的支持上,聲音的高低強弱運用自如、吐字咬字清晰、音色明亮更富有穿透力,具有全新的民族演唱風格。
(二)民族聲樂藝術中聲腔美的基本特征不同國度以及歷史文化間的差異,與之相應會產生不同的聲樂藝術形態、風格特征以及審美標準。聲腔作為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美學個性特征之一,是透出聲音色彩美的有聲造型,從音質、吐字咬字、行腔三個方面共同體現聲腔自身美的基本特證。1.音質之美音質之美是聲腔美所體現的首要特點。音質是聲音的本質,它是否有色彩,決定了演唱者所發出聲音的效果。演唱者音質有的甜美明亮、有的豐滿醇厚等等,聽到悅耳動聽飽滿的音質才是美的所在。而音質之美的產生,首當其沖就是氣息與共鳴。氣息是歌唱的支撐,發聲其音質優劣離不開對氣息、共鳴腔體平衡的掌握與運用,也是聲樂美最為堅實的基礎。我國民族聲樂音質之美的特征,首先是演唱的正確呼吸原則。呼吸是以橫膈膜的支持運動,吸氣時橫膈膜下降和肋骨張開是同時進行的,胸腔和腹腔全面擴張,使氣息盡量吸得深。民族聲樂一般是深呼吸,指腹式呼吸,將氣息保持在腰腹周圍,也借鑒采用美聲唱法的胸腹式聯合呼吸,只有掌握正確的吸氣,打開并穩定喉嚨,才能使整個腔體處于擴張通暢狀態。運用氣息演唱時要保持自然,使聲音通透流暢,而針對不同的聲樂作品,要會靈活使用氣息。其次,音質美還體現在音域。把握寬廣的音域,是在原有人聲的基礎上的更進一步音域擴展,高中低聲區音域控制自如,可塑造其聲樂的藝術表現形態,從而增強了演繹聲樂作品的表現力和聲腔美的效果。民族聲樂的音質美是聲腔美的基礎,也是聲樂美發聲效果的關鍵,在自身本質聲音的基礎上,還要有后天的不斷學習和系統的訓練,才能使音質美發揮出最佳的音響效果。再次是音量的把控。演唱聲樂作品中并不是音量大、音域高才為美。音量的強弱,應根據聲樂作品所表達的情感和演唱者二度創作理解的需要,做到張弛有度,強音高聲時不大喊,弱音低聲時,要有氣息的支撐,不散。民族聲樂歌唱胸腹式聯合呼吸和真假聲混合使用,加強整個腔體控制力,吸氣和存貯氣的量增大,使氣息運用更為自如,在唱中低聲區真聲多一些,高聲區假聲多一些,能使音域較為拓寬。而音量的強弱,是由呼吸的強弱,即通過氣息帶動聲帶的速度,唱低音時,更要有氣息的支撐,小腹拖住不能松懈,達到堅實而不散、飄,高音時不能扯著嗓子大喊,而是找準運用頭腔共鳴,提起軟腭、打開喉嚨,喉頭穩定,使氣息在腔體中貫通,音質更為通透、有張力。最后是音色。不同的音色鑄造不同的聲音色彩形態,不同性別具有不同的音域音色,不同的聲音類型具有不同的音質之美。2.咬字吐字之美如何在歌唱中體現語言字正之美呢?在我國古代聲樂美學思想,清代王德暉和徐沅徵在其《顧誤錄》一書中指出:“每字到口,需用力從其字母發音,然后收到本韻,字面自無不準。”“字到口中,需要留頓,落腔處需要簡凈。曲之剛勁處,要有棱角;柔軟處,要能圓湛”……清人徐大椿所著《樂府傳聲》中也有進一步的描述“:欲正五音而不于喉、齒、牙處著力,則音必不真。欲準四呼而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明•魏良輔的《曲律》,對字腔關系上,要求“生曲貴虛心玩味”;還詳細指出“喉音清亮”與聲腔美的區別,曰“:聽其吐字、板眼、過腔得宜,方可辨其工拙,不可以喉音清亮,便為擊節稱賞。”可見,古代就出現了對歌唱中咬字、吐字的準確表述,咬字吐字與腔的結合,運用傳統的“依字行腔”與當今語言聲腔的審美原則相結合,從而靈活地運用,達到“字正腔圓”的審美效果。這些聲樂技術理論,對當今的歌唱者、教學研究者和美學準則來說,仍具有非常寶貴的實用價值。中國民族聲樂吐字咬字之美體現在漢語語言的特點,不同的語言風格決定了不同的聲腔藝術風格。中國漢字本身四聲就具有一定的語言韻律美,發音拼音是由聲母和韻母而組成單音節字,字頭為聲母、字腹為韻母、字尾是要歸韻收聲。由于漢語語言的特殊性,其咬字吐字與美聲唱法五個基本元音字母(a,e,i,o,u)有著較大的區別。咬字強調出口時字頭要清晰,唇、牙、齒、喉、舌五個部位通過氣息,使出字更為迅速、靈活有彈性;字腹要引長,是單音字發聲中所占時間最長,共鳴的運用更富有立體感;字尾的歸韻收聲,形成了開口音和閉口音的咬字,一個單音字的發聲結束得輕而自然、干凈利落。這三個部分的銜接要緊密,氣息的保持、字與聲要融為一體,使每個字都能夠清晰飽滿。即形成了“聲韻多變,點面適合,字音融洽,意韻十足”的民族演唱和審美風格。使字與字之間所形成的句,句與句之間形成連貫而生動的語言。由于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演唱到地方民歌,不僅要了解當地風土人情、風俗習慣,還要在語言上突出地方的語言特色,多種多樣的各地民族方言,也突顯出了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演唱地方民歌,要了解地方語言的咬字發音習慣,如:在演唱湖南民歌《洗菜心》時,就要把握湖南民歌和湖南花鼓戲的鮮明特點以及當地湖湘語言習慣。其旋律活潑、優美流暢,具有很強的律動感。《洗菜心》中咬字要靈巧,切忌過重。此外歌曲中還運用花舌腔來演唱襯詞,也是曲目的難點和特點。如果不按其鮮明的地域特點演唱,而只用標準的普通話發音咬字演唱,就無法準確表現湖南民歌的特點,而其他地方民歌也如此,因此,在正確的咬字吐字的基礎上,更要注重地方方言的語言特點和民族習慣。3.行腔之美在聲樂演唱中,歌曲的行腔是對其旋律的潤飾技巧性的表現,除了要由通過呼吸所形成的氣息引起聲帶振動,發出美妙的音色、純正歌唱語言的基礎上,還要達到“腔圓”。歌曲行腔要求氣息控制運用自如、音質的不斷改善、音域的擴展、音量適度的把控以及音色的不斷豐富、語言斷句精準的基礎上,要注重其平滑流暢性的過腔和采用各種豐富的潤腔技法(潤腔技法包括斷音潤腔、裝飾音潤腔、音色變化潤腔、聲音造型潤腔)。行腔之美是在整個“聲腔美”特點上的一個升華,從而使聽覺達到最佳的藝術效果。中國民族聲樂是以漢字語言咬字發聲為基礎,以中國的歷史文化為背景、以行腔韻味為特色的歌唱藝術,歌唱中聲腔美的體現,在咬字發音符合漢語語言的規律,結合潤腔的藝術表現手法,使演唱達到“以字行腔、字正腔圓”的審美原則。以字行腔是建立在咬字吐字字調清晰準確的基礎上,聲調的變化在舒展的行腔中符合樂音韻律的歌唱方向和發展趨勢。民族聲樂藝術行腔美要求音色明亮、甜美,對詞曲的裝飾、修飾等要表達得當,行腔中抑揚頓挫要與作品情感的表達達到統一。行腔美是民族聲樂的魅力所在,也代表了其特有的審美核心價值,根據具體的聲樂作品,語言語氣與旋律的潤腔變化,體現了濃郁的民族特色。豐富的潤腔技法是產生行腔韻味之美的手段。潤腔技法之斷腔,是在民族歌唱中一字多音的長腔中,字與字間或腔與腔間鏈接根據聲樂作品旋律、情感的需要,所出現的停頓,斷字斷腔強調聲斷氣不斷、字斷情不斷。湖南民歌《洗菜心》中“哪一位年少的哥哥,撿了奴的戒箍子啊”就是運用了斷字斷腔的行腔手法,為歌曲增添了更多活潑、俏皮的色彩。“拖腔”的運用,是一字多腔的行腔表現手法,使旋律更悠長、優美,如《洪湖水浪打浪》中“怎比我洪湖魚米鄉”中的“鄉”共拖了12個音符,“晚上回來魚滿倉”中的“倉”“一年更比一年強”中的“強”就是一字多腔,共拖了14個音符,歌曲是一首經典抒情的湖北民歌,悠揚委婉的行腔,襯詞的使用也極具地方特色,體現出洪湖漁民勞作以及對鄉土生活的熱愛。因此,行腔之美的把握,應尊重并遵循作品本身藝術風格和語言風格的基礎上,靈活運用行腔技法,使演唱者賦予作品二度創作可塑性,更富有個人風格獨特性,才能真正體現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魅力。
二“、聲腔美”在民族聲樂藝術中的地位
(一)聲腔美與舞臺表演美我國民族聲樂在古代聲樂藝術審美思想的影響下,發展至當代已形成“聲、字、情、味、表、養、象”為一體,構成了新時期的民族風格、獨特的歌唱審美技術和聲樂文化特征。聲樂美是一種綜合創造之美,存在著整體和部分的辯證關系,體現在漢語言文學之美、演唱聲腔之美、聲樂舞臺表演之美,它們是既獨立又相互依存的美的內容。我國著名的音樂教育家李凌曾談及聲樂美學,他認為:“凡是好的演唱者應該給人以由音響的美、語言的美、思想的美、情感的美以至形體的美凝聚,化合成的綜合的美。”[6]聲腔美是聽覺藝術,舞臺表演美是直觀的視覺藝術,聲腔美是身體內部腔體在運作,而舞臺表演美則是身體外部五官面部表情和四肢肢體動作。在表演過程中,首先要注重不同的眼神所傳達出不同的音樂情感,以及與觀眾的互動交流。其次,還要注重豐富的面部表情。通過面部表情感受作品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使更具有感染力。第三,還要注重形體動作。在民族聲樂藝術當中,經常吸收和借鑒我國傳統戲曲的舞臺表演,這也是與演繹西方美聲作品形體動作相比,更為獨特的魅力所在。戲曲中在表演上,講究手、眼、身、法、步,有著固定的身段表演,以及具有程式化的表演動作和固定的手勢表演,吸收借鑒到民族聲樂表演當中,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也使歌者形體動作、手勢表演更為自然、協調。除了常規的舞臺表演形式,還需要歌唱者要根據實際的聲樂作品內容與情節的發展,做出符合人物形象的形體表演動作。如民族歌劇《白毛女》,喜兒一角,從一個善良、淳樸、聰慧的女孩子被欺凌變成一個在深山穴居,長期缺少鹽分的攝入,青絲變白發的“白毛女”,在飾演這一角色時,故事情節的發展逐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物情緒的表達、塑造鮮明的人物性格,在演唱和表演上,從活潑、柔軟、細膩的性格到變得堅強,動作隨其情感的深入,要做得夸張,體現出心中的憤怒、仇恨的復雜感情。我國民族聲樂藝術是歌唱的聲腔造型和舞臺藝術表演,是聽覺和視覺綜合性的藝術。發聲技巧和舞臺表現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因此,要求聲樂表演者在舞臺上能唱會演、形神合一,形是指身體動作肢體語言,神是指思想情感的表達、韻味神態相結合之美。兩者相互結合,才能達到完整的聲樂藝術形式。若是只具備了良好的基本音樂素養和正確的發聲演唱技巧來敘述歌詞,毫無肢體語言刻畫作品人物形象來表達情感,這僅僅是完成了聲樂演唱的一半;還必須在掌握正確的發聲技巧的基礎之上,通過肢體語言創造性的舞臺表演,通過敘述性的歌詞上升到更加形象化,為作品的原創藝術表現服務,才能更好地彰顯我國民族聲樂的藝術魅力,更加得出神入化,也同時達到大眾的視聽審美。聲腔美是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基礎,是必要條件;而豐富的舞臺表演和表現力是聲樂藝術表演美的再創造,對演唱者個人藝術表演風格以及藝術創造力的發展都十分重要,舞臺表演美是在聲腔美基礎上的升華,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如《老鼠嫁女》,是我國民族唱法青年歌唱家陳笠笠,在第十四屆青歌賽的舞臺上首唱,是一首歡快、活潑,描寫鼠女出嫁熱鬧場景的一首風格濃郁、個性突出的作品。旋律歡快跳躍,極具舞蹈性;樂曲中有湖南地方方言和花舌的融入,具有詼諧幽默的戲劇性。作品歌曲中第一句,“唱起來跳起來喜洋洋,唱起來跳起來喜洋洋”,在有序的速度中,有情緒的變化交織,在表現輕松、活潑的情緒之時,演唱急而不亂、快而不趕,顯露老鼠嫁女激動喜慶的濃郁氛圍。通過以聲傳情,把握聲樂的聲音形式、聲音技術,得以傳達和表現聲樂之情、聲樂之美;而通過豐富夸張和適時的肢體動作表演,使整首作品更加豐富生動,陳笠笠歌唱與形象的舞臺表演完美結合,使其大獲成功。
(二)“聲腔美”在民族聲樂藝術中的地位聲樂藝術的表達是“聲與樂“”歌唱與文學”相結合的特定表達形式。中國語言的特殊性,是字與聲的巧妙處理,歌詞誦讀吟唱的聲音走向與語言字調、旋律曲調、節奏相聯系。對于我國民族聲樂來說“,聲腔美”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演繹聲樂作品之時,倘若離開“聲腔美”,就會缺乏良好的呼吸共鳴、清晰的咬字吐字和流暢的行腔。首先依靠喉嚨發聲,對嗓子的損害以及聲區偏高、偏低,喉頭不穩定失去平衡,聲音發抖;發聲吐字沒有共鳴立體感,咬字含糊,并且只是機械式的咬字,一字一拍的演唱,無法讓聽眾聽清歌詞寓意和美感。其次,不具備掌握行腔之美或能力還不夠全面,也就不可能產生聲腔美或者存在美中不足之處。離開“聲腔美”,再優美的聲樂作品也是失去舞臺生命的紙質文本,失去了聽覺的審美價值,無法體現我國濃郁的民族藝術風格,二度創造個性且風格多樣的聲腔也就更無從談起。比如演繹中國古代聲樂曲《杏花天影》,在演唱時要注重“依字行腔”、詞曲句逗步節分明的藝術特點。尤其要注重“去聲字”的運用,其去聲字的旋律音,在歌曲處理上,不應拘泥于譜面一字一拍的演唱,需要適當的在協韻后轉折處和開頭處去聲字上延長時值,體現詞曲典雅、幽遠之美。作品分為上下闋,演唱“想桃葉當時喚渡”中第一個字“想”,為表現開頭上聲字調,字頭“x”的力度應由弱漸強,由上往下,從“x”與“ang”之間過渡,下滑至延長半拍,歸韻至兩拍半時值的“ang”上,字尾要收聲利落。演唱“更少駐”這一句,要注意其中“更”與“駐”都是去聲字,因此,都應在各自上方添加大二度倚音,聲腔由高變低,聲音由明變暗。體現出作者的惆悵、傷感之情。最后尾句“處”為去聲,做減弱延長處理,弱聲做到聲斷氣不斷,更突顯無可奈何的感慨。總之,在我國民族聲樂藝術中,只有建立在科學的發聲方法基礎上,把握漢語言咬字吐字、行腔韻味聲腔之美,才能更進一步追求聲樂藝術舞臺表演之美。
三、結語
中國民族聲樂藝術對“聲腔美”的追求由來已久,“聲腔美”作為具有我國聲樂美學中獨特的審美品格,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色彩及審美風貌。聲樂的美學價值和持久魅力,是其聲樂作品歌唱者與審視者主客體所構成的關系法則。民族聲樂藝術的美學研究以及審美變化與其發展是一脈相承,密不可分的。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從多個不同的學術視角積極探索、研究我國民族聲樂藝術,將會積極推動其發展。新時期中國民族聲樂,單靠技術方法和舞臺演出實踐,已不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推動其提升,聲樂藝術與其它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的研究,為歌唱過程中更深層次的問題研究以及對演繹聲樂作品,提供了寶貴的知識理論財富,未來也必將在理論上更加豐富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的研究,促進其創造性地發展。
作者:周子翔 李道琳 單位:滁州學院 音樂學院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