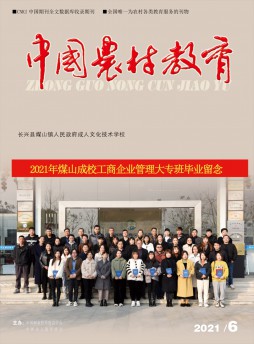農村教育知識的重要抉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村教育知識的重要抉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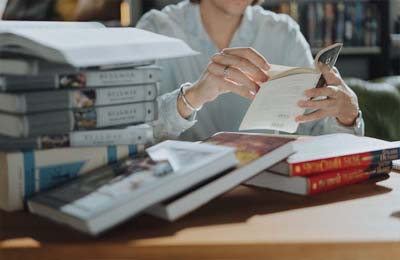
從大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來看,中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一大部分農民要完成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在這種歷史的發展趨勢下,農村教育的知識必然顯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城市化的教育知識理所當然地成為農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知道,城市化的教育知識與農村化的教育知識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而異質或異構的文化一旦碰撞總會發生較量,并遵循著“強者說了算”的規律。由于權力、財富等稀缺的社會資源通過與人的恐懼心理、享受心理結合,并通過它們所隱含的價值判斷,非常容易摧毀沒有這些稀缺資源的人的心理防線。中國的農村與城市相比,除了人數外,在所有重要的資源方面都極不對等,部分農村處于弱勢的地位。因此,只要農村的貧窮與城市的富裕產生強烈的對比將使農民感到失落,那么農民就會在羨慕、自卑的復雜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的那一套編碼,并反過來鄙棄曾給以自己安身立命的一個精神支點的文化。
由于城市文化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地位,不僅生活在城市文化中的城市人認為城市文化理應如此,就是農村中相當多的人也這么認為。這種情況反映到教育領域當中,便是農民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提供在面前的一系列教育知識做出相應的選擇:農村的學生具備了很多鄉土性知識,但從他內心來說并不對其所學的感到興奮,而恰恰對社會評價更高的城市化知識情有獨鐘;或者干脆就是對鄉村性的知識完全置之不理,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更吸引他的城市文化中去,因為城市性的教育知識也部分地符合了他們想脫離農村改變生活命運的一種愿望。于是,再沒有比這個更為心痛的事情發生了:農村教育培養的學生不是學業的失敗者,便是農村社會的逃離者。大批的失敗者抱怨他們的失敗是由于農村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而農村社會的逃離者卻也以勝利的逃亡而暗自慶幸。農村本土文化遭到了背棄!當然,也有人做出了其他的選擇。河南許昌興源鋪村的趙蘭卿和山東寧津孟金寺村的劉祺云,他們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了:趙蘭卿拍的《鬼子進村》反映的是1945年麥收時節日本鬼子在本村燒殺淫掠18天的歷史;劉祺云拍攝的則是反映劉氏一族在孟金寺村幾百年的奮斗歷程的電視劇。值得一提的是,趙蘭卿和劉祺云都著意強調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農民”這個詞看來不再是生活的負擔,他們似乎從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投身其中并樂此不疲,雖然他們的行為單從規格上可以被那些自命清高的人當做是粗糙的或者是幼稚的甚至是低劣的,但在他們身上傳統的中國農民形象——貧窮、沉默——正在發生著改變。正是這種改變使得農民的形象突然變得如此的輕松,這種輕松無疑源自經濟上的逐步自足。
農民拍攝電視劇,拍自己的發展史,可以解讀為群體意識或者階層意志的形成和強化。當農民這個階層在經濟上有了發言權之后,他們開始謀求在文化上的一席之地,以期形成本階層的可標識的文化氛圍。所以也有人將他們的拍攝行為稱作“農民的文藝復興”。這也許正是這些農民文化帶頭人反復強調自己農民身份的意圖所在。由此可見,農民主體意識在文化自覺上的巨大作用。正是這些因素的作用,才使得其成員憑著自尊感以及對所屬群體文化的認同感在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對抗、交流中得以站穩腳跟,并逐漸獲得發展壯大的機會。可見在自主意識下選擇的重要性比起缺乏自主意識狀態下的選擇要更具理性與進步意義。只有在其中的弱勢群體對自己所屬的集團以及自己的社會身份具有一定的自我認同,具備完整并獨立的理性時,農村教育才可能不陷入失敗的境地。而這一點歸根結底便是如今的要求農村教育不能夠忽略了教育中的人——也就是農民的主體意識。換句話說,農村教育必須針對農村主體意識的培養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否則,農村教育是沒有出路的。即便是“農村教育”看似取得了“成績”,但實際“農民教育”卻是失敗了。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之前的農民少有獲得主體意識發展的機會。漫長的自然經濟和封建宗法制的歷史,造成我國從未形成過西方意義上的個人主體,亦不具有真正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本位。中國傳統的社會不同于西方理性的社會,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在“個人”“社會”“家庭”三者中,以家庭為重。“家”使家庭成員固守家教、家規而受到壓抑,同時也限制了他們主體意識的蘇醒。新中國曾在農村地區進行了持續三年的運動,帶來的一個客觀后果便是:隨著農民獲得小塊土地和紳士地主階級被徹底消滅,傳統宗法社會的等級結構被打破,宗法共同體對農民人身的保護——束縛體制開始走向解體,獨立的個體小農破土欲出。然而,從互助組、農業合作社、一波接一波的集體化浪潮使剛剛擺脫宗法束縛的中國農民重又成為“公社共同體”的“附屬品”,“社會主義自然經濟”取代“宗法自然經濟”。雖然改變了農村社會的階級結構,但農民的人身依附特性未能解除。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目前而言,農民總體上來說還是缺乏個體的獨立意識,這種意識的缺乏對于農村教育知識的直接影響便是無法在城市化還是鄉土化之間做出獨立的選擇,而總是屈從于外界社會環境的限制。正是這種主體性意識缺乏使得農村教育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失去了目標,迷失了自我,那種自發的對鄉村繼承與發展也就失去了上升為自己的動機與條件,在這種背景下鄉村文化自然難以抵御來勢兇猛的文化殖民。而這種迷失反映在教育領域中就有可能會出現受教育者對城市化的知識推崇備至,奉為權威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工具性目的的影響下,農村教育不是單純地被用來支援農村經濟建設,就是被看成改變社會身份的跳板。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農民自身都對教育抱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農民的主體意識既得不到重視,也缺乏培養的環境。以至于培養農民群體獨立意識的農村教育漸漸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時展至今,農民的教育自主逐漸也在情理之中,其主體意識的作用日益顯著。可以預見,沒有農民及其子女的社會主體意識,農村教育就不可能縮短它與現實需求、民眾渴望之間的距離,從而擺脫危機,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如果農村教育能夠以培養農民的主體性意識為己任,那么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新局面。無論農民今后的發展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他的初始身份始終是農民,如果忽視了農民教育,無論對農民自身還是對農村而言,其后果都是相當嚴重的。農村教育的當務之急是將農民及其子女的社會主體意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我們理想中的農村教育真的是以培養農民主體性意識為主旨,那么關于農民主體性教育知識的引入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將很多精力投注在如何向農民呈現本鄉本土的文化,而對農民主體性的教育知識甚少關注。研究教育知識也需要研究意識形態,研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殊的機構中、特定的社會群體和階級把什么知識看做是合法性的知識。而且,它是一種研究的批判性定向形式,側重于在學校進行分配時,這種知識怎樣促進認知和情感的發展是以怎樣的內容與方式作用于社會現存的制度性安排的。因此,我建議要解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必須用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教育知識去應對。由于這些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教育知識其用意在于農民主體性意識的蘇醒,它著眼的是整個農民階層這個群體。在此,論者大致將這一類知識羅列出以下若干,權作為拋磚之舉:(1)關于農民的本質和歷史使命;(2)關于農民與農村以及與城市的關系;(3)關于農民在新時代承擔的歷史使命;(4)關于農民的現實背景以及發展前景;(5)關于農民的自我反思;(6)關于傳統與新型的農民……
引進這些知識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增強農民的主體性和個體理性,加強農民對本群體的歷史認同感,同時也理性地看待城鄉差距的存在,使他們能夠基于自己充分的主體理性之上對城市化還是鄉村化做出自己的選擇。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農村教育可以幫助那些行進在城市化途中的人既接受城市文化,同時又拒絕著城市文化;超越著鄉村文化,但又守望著鄉村文化,前者使他大膽邁進了城市,接受著城市;后者又使他抗拒著城市,守望著自己特有的心靈空間。這也是農村教育發展需要瞄準的目標,而要圓滿地達成這一目的,農民的主體性意識起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