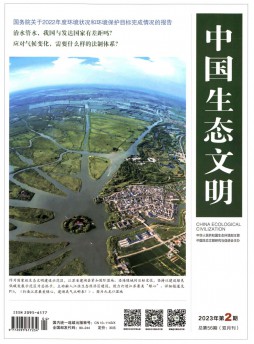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性的民族教育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性的民族教育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生態(tài)斷裂現(xiàn)象分析
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生態(tài)斷裂現(xiàn)象并不是自然、經(jīng)濟(jì)、文化中的某一類資源能夠?yàn)榻逃顒?dòng)制造不延續(xù)性,而是指以上三類生態(tài)資源與教育活動(dòng)之間沒有確立一種聯(lián)動(dòng)共生的關(guān)系,由此為少數(shù)民族教育帶來了發(fā)展障礙。首先,根據(jù)對(duì)少數(shù)民族教育的自然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性分析,應(yīng)認(rèn)識(shí)到自然地理?xiàng)l件作為原初性的“隨境式”教育環(huán)境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支配,因此“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自然生態(tài)范式的斷裂指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自生性共生教育的失落”,即教育空間與教育形態(tài)的分離。瑞士著名教育學(xué)家皮亞杰認(rèn)為,所有的學(xué)校教育活動(dòng)都是基礎(chǔ)教育形態(tài)的變種,如回族學(xué)校教育形態(tài)即是由田間教育、回坊教育、經(jīng)堂教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在回族古代田野教育過渡到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校教育的過程中,變化的不僅僅是形態(tài),還有空間。由于少數(shù)民族生態(tài)教育空間向社群教育空間的變化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使得教育形態(tài)創(chuàng)造大過一切,主要表現(xiàn)為對(duì)漢族教育形態(tài)的模仿,例如實(shí)施科研網(wǎng)拓展工程;進(jìn)行國(guó)家、地方、校本課程的三級(jí)管理;確立“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教育資源開發(fā)戰(zhàn)略等等。工具性知識(shí)教育極大壓縮了價(jià)值性知識(shí)教育的生存空間,在促使少數(shù)民族神學(xué)思維解體的同時(shí)放棄了生態(tài)環(huán)境對(duì)教育受眾的自主化行為塑造,存在著矯枉過正的現(xiàn)象。其次,在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性中,我們區(qū)分了經(jīng)濟(jì)類型與生計(jì)方式的不同影響機(jī)制,由于決定少數(shù)民族人才培養(yǎng)框架的經(jīng)濟(jì)類型具有較長(zhǎng)歷史時(shí)期的穩(wěn)定性,因此探討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與經(jīng)濟(jì)類型的關(guān)聯(lián)性必須以整塊歷史時(shí)期為參照系,不符合當(dāng)下教育活動(dòng)的改進(jìn)需要,因此我們傾向于從生計(jì)方式入手考察少數(shù)民族教育中知識(shí)控制與社會(huì)勞動(dòng)分工的脫節(jié)。我國(guó)民族教育學(xué)家林耀華先生曾指出,如果將少數(shù)民族家庭的社會(huì)勞動(dòng)看作一種教育,“那么它必然是一種自然的、直觀的、奠基性的教育”,將其與統(tǒng)一性的、體系化的、課題化的當(dāng)代教育模式接軌決不能照搬漢族學(xué)校教育慣常的“知識(shí)控制”手段。“知識(shí)控制”是指學(xué)校教育將社會(huì)生產(chǎn)中的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力的主流經(jīng)濟(jì)主張進(jìn)行理論化,通過學(xué)校教育增強(qiáng)其知識(shí)價(jià)值的普適性,這里面幾乎不涉及少數(shù)民族紡織、釀酒、栽培等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知識(shí),或者僅僅是將它們停留在認(rèn)知層面,對(duì)于如何進(jìn)行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資源的改造利用使其成為社會(huì)共有資源往往被教育忽略了。再次,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文化是作為“歷時(shí)態(tài)”還是“共時(shí)態(tài)”存在于教育活動(dòng)之中的區(qū)別,僅就結(jié)果而言,前者(歷時(shí)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社會(huì)大眾將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瀕危與少數(shù)民族教育文化生態(tài)鏈的斷裂等同,其中的誤區(qū)在于人們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瀕危是教育自身的傳承機(jī)制出了問題,實(shí)質(zhì)上卻不然。英國(guó)著名生態(tài)學(xué)家、教育學(xué)家埃里克阿什比曾說,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huì)沿襲依賴教育的傳播與借用,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接納卻不是簡(jiǎn)單的教育接觸能夠解決。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當(dāng)代德育教育的“禮”文化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推廣大多進(jìn)行了變形,不再純粹是孔孟儒家學(xué)說中的交際禮儀,而是用來強(qiáng)化少數(shù)民族個(gè)體或部落的“集體協(xié)作能力”。因此看起來是教育在選擇文化,其實(shí)是文化在選擇教育,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與文化生態(tài)的斷裂現(xiàn)象表面上是學(xué)校教育忽略了民族文化傳承,實(shí)質(zhì)上卻是文化教育與接受主體的銜接出現(xiàn)了障礙。
二、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生態(tài)鏈接途徑
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生態(tài)鏈接是通過修復(fù)少數(shù)民族教育與自然、經(jīng)濟(jì)、文化之間的聯(lián)動(dòng)關(guān)系,維系少數(shù)民族教育系統(tǒng)的生態(tài)平衡。首先,少數(shù)民族自然生態(tài)教育空間向社群教育空間的演變促使工具性知識(shí)大大壓縮了價(jià)值性知識(shí)的比例,削弱了生態(tài)環(huán)境對(duì)教育受眾的自主化行為塑造。因此,重建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與自然生態(tài)的鏈接需要“從共生的角度解決教育空間與教育形態(tài)的分離”。盡管隨著時(shí)展,少數(shù)民族自然崇拜讓位于科技、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但塑造兩者的對(duì)立并不利于少數(shù)民族價(jià)值性知識(shí)的合理組織,須知在我國(guó)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最為崇尚西學(xué)的年代也沒有完全以科學(xué)知識(shí)代替“四書五經(jīng)”,而是將它們置入“釋典禮”、“成人禮”、“開學(xué)禮”等教育環(huán)節(jié),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行為禮儀規(guī)范及治學(xué)精神。因此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維持學(xué)校工具性知識(shí)教育與外圍價(jià)值性知識(shí)教育的平衡需要在對(duì)現(xiàn)代教育思潮的適應(yīng)中融入“民族教育”關(guān)于自然審美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或人文意蘊(yùn)等方面的價(jià)值尺度,例如塔塔爾族的學(xué)位授予儀式是在田野上舉行的,要求學(xué)生親自殺豬、犁地來作為學(xué)生生涯的結(jié)束,此類自然儀式體例即是對(duì)少數(shù)民族自然生態(tài)教育空間的保留,促使教育的最終目的指向受教育者應(yīng)該承擔(dān)的個(gè)體責(zé)任,工具性知識(shí)與價(jià)值性知識(shí)得以銜接。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經(jīng)濟(jì)生態(tài)鏈接同樣要求學(xué)校教育提升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資源的價(jià)值普適性,而不是僅僅將它們作為認(rèn)知性成果給予呈現(xiàn)。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中的知識(shí)控制現(xiàn)象主要表現(xiàn)為對(duì)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勞動(dòng)技術(shù)的史料性介紹,無法滿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應(yīng)用性需要。對(duì)此,“任何少數(shù)民族都創(chuàng)造、發(fā)明過自己的科學(xué)”,例如彝族的“十月太陽歷”、傣族的水利灌溉“分水器”,這些曾經(jīng)在少數(shù)民族經(jīng)濟(jì)生活中被廣泛應(yīng)用過的傳統(tǒng)科學(xué)技術(shù)怎么才能擺脫“歷史文獻(xiàn)”整理的范疇,使其與當(dāng)代自然科學(xué)教育、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教育充分結(jié)合呢。筆者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本身便具有文科與理科的綜合性功能,例如云南少數(shù)民族旅游經(jīng)濟(jì),如果納西族傳統(tǒng)城鎮(zhèn)設(shè)計(jì)、哈尼族的傳統(tǒng)梯田技術(shù)沒有融合在少數(shù)民族旅游景點(diǎn)之中,那么少數(shù)民族旅游經(jīng)濟(jì)便失去了獨(dú)有的魅力,因此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完全可以通過綜合性課程設(shè)置“促使歷史經(jīng)濟(jì)遺跡與當(dāng)下社會(huì)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保持一致”,而不是將它們隔離劃分,這樣教育才能真正擔(dān)負(fù)起對(duì)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的保護(hù)、傳承與開發(fā)責(zé)任。少數(shù)民族教育活動(dòng)的文化生態(tài)鏈接也是如此,需要少數(shù)民族教育發(fā)展與少數(shù)民族社會(huì)文化建立“共時(shí)態(tài)”的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我國(guó)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潘光旦先生的文化“位育”理論認(rèn)為,文化起到了將生物人與社會(huì)人結(jié)合的作用,學(xué)校教育培養(yǎng)的即是社會(huì)人,文化與教育的“共時(shí)態(tài)”關(guān)系旨在“致中和”,人無法放棄對(duì)自身生命的關(guān)注,“文化”輔助教育活動(dòng)協(xié)調(diào)人性與社會(huì)性的沖突,筆者提倡少數(shù)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態(tài)鏈接采用“多種族文化教育”策略而非“多元文化教育”策略。當(dāng)代教育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個(gè)模糊概念,雖然它具備文化統(tǒng)整、降低偏見、平等團(tuán)結(jié)等開放性教育框架,但其提供給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的價(jià)值判斷卻并不明確。以納西族多元文化教育為例,納西族學(xué)校教育通過增能校園文化來打造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的社會(huì)公民身份,從而實(shí)現(xiàn)文化兼容的教育目標(biāo)。然而文化生態(tài)鏈接并不是對(duì)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多元文化教育策略是“舍一體而倡多元”,此種教育主張抑制了少數(shù)民族自身文化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機(jī),暗含著傳統(tǒng)民族文化生態(tài)斷裂的危險(xiǎn)。因此,筆者提倡以“多種族文化教育”取代“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文化的兼容并蓄,而是直面“教育如何解決傳統(tǒng)文化取舍與現(xiàn)代文化迎拒的矛盾問題”。多種族文化教育是區(qū)別了民族性的文化教育,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同時(shí)也尊重文化價(jià)值判斷的主體對(duì)象,使得學(xué)生文化吸收具備自身民族性的“主體立場(chǎng)”,提升學(xué)生主動(dòng)選擇文化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無止境地進(jìn)行泛文化輸入,更容易被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所接受。
作者:龍雪津單位:華中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廣西廣播電視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