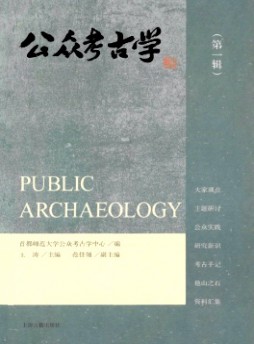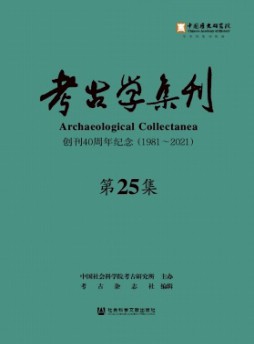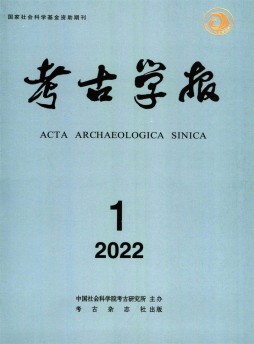考古學專業語言特征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考古學專業語言特征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夏明亮童雪蓮單位: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長城地帶”概念的形成過程
“長城地帶”,從其作為一個地理概念上的探險考察區域稱法的提出,到作為學術研究區域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區域范圍的界定),再到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固定概念的形成,經歷了明顯的階段性過程。
1.20世紀初西方學者對長城及其周邊區域的探險考察活動與“長城地帶”稱法的較早提出
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30年代,英、德、日等國家掀起了考察中國西北新疆、內蒙古、甘肅地區的探險考察活動,這些活動雖然帶有刺探我國資源情報、掠奪文物資源的性質,但也促進了學術研究的發展,這些考察一定程度上涉及長城及長城地區的考察和研究,長城地帶是作為地理概念上的一個探險考察區域而被使用的。
英國人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3次到中國西北考察,對于長城有精彩的論述。在其1932年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他用了兩章多的篇幅論述了漢武帝所筑長城及其周邊區域。②1927年,斯文•赫定組織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其考察路線從北京經過包頭、百靈廟至額爾濟納河流域,最后回到北京。中方團員黃文弼在對額濟納河流域進行考察時,發現了秦漢故長城遺址和居延漢簡,這些發現及對其整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成為深入研究長城區域社會經濟的寶貴資料。
1930年,日本考古學家江上波夫與水野清一作為偽滿考古機構“東亞考古學會”的留學生,考察了長城地帶和錫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內蒙古•長城地帶》一書,至今仍是有關中國北方考古學文化的重要論著。③該書是目前所見最早具體提出和使用“長城地帶”這一稱法的論著,主要是用來指稱地理范疇上內蒙古地區沿長城地帶的區域。
另一個對長城地帶做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國地理學家歐文•拉鐵摩爾,拉氏在1930年代初,對中國整個長城邊疆地帶進行旅行和學習。1939年寫成《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以長城及其周邊的區域作為對象,從邊疆史角度探討中國歷史及其地緣政治問題。提出了“長城邊疆地帶”的概念,認為長城不是一個絕對的邊界的“線”,而是一種“被歷史的起伏推廣而成的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
④他認為長城邊疆地帶的形成是自然、社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長城一帶既是中國遼闊邊疆的縮影,也是反映中國歷史的視窗。”⑤拉氏是第一個明確將長城作為一個“地帶”去考察其周邊區域的人地關系、社會景觀、歷史功能等的學者,明確了長城地帶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線”或者“帶”的概念,更是沿長城一線而形成的一個具有特定歷史、人文、自然等綜合內涵的區域地帶的概念。拉氏的這一提法促進了日后“長城地帶”概念的形成,并推動了其學術意義和研究內涵的豐富和擴展,學術意義不容低估。
2.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者對長城地帶的考古研究及蘇秉琦對“長城地帶”考古學區系
概念的初次界定1971年,姚大中在臺灣出版《古代北西中國》⑥,從邊疆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長城,分析指出,長城從初建時的國界線到漢代的攻勢長城及其后世的防御長城,在歷史的不斷發展中其性質不斷變化。從中探討分布在古代長城區域中的游牧民族的歷史,進而以此來考察分析古代“中國”的歷史。其視角和視野都相當有創建性。
1979年,逯耀東分析了鮮卑族進入中原后的漢化過程,指出在長城與游牧民族之間存在著一個半農半牧的中間過渡地帶,這一地帶曾是“漢武帝為阻止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建立的防衛性的屯墾區。這些地區在漢朝崩潰后孤立地發展,成為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的過渡地帶。”認為游牧民族南下越過長城后,其“漢化程度的深淺與緩速,恰和他們居住在這個地帶時間的久暫成反比”。⑦大陸學者最早、最全面對“長城地帶”進行論述、劃分的是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經過多年考古發掘和思考,他在1975年8月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學生講課和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暨全國考古規劃會議上,提出了思考多年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學說。
⑧1981年發表《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一文,以書面形式闡述了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將全國劃分為六大區系,其中之一即為“以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地區”。⑨正式把“長城地帶”作為北方地區的核心提了出來。同時,蘇先生對其范圍進行了大致的劃分,指出:“這一地區從東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為中心的地區;河套地區;以隴東為中心的甘青寧地區三個部分。”對長城地帶作了一個比較明確完整的區域劃分。蘇先生提出這一區系理論,得到了考古學界的廣泛認同。在蘇先生的帶領之下,更明確了“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這一專門課題,其后,從1982-1986年召開了一系列有關北方地區考古的學術會議,長城地帶作為北方區系的核心地帶在考古學界得到普遍的認同。⑩
3.改革開放后長城地帶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
與多學科“長城地帶”概念的探討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研究的視野得到了大大的開闊,綜合考察研究長城,成為推動長城研究的關鍵問題。隨著領域的開闊和多學科研究的深入,對長城的關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長城概念所包含的內涵,加深長城周邊區域的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變遷的研究。長城周邊區域研究的深入,對于這一區域的具體范圍和名稱定義,成為各個學科的研究者需要討論的問題。與“長城地帶”相類似的概念也相應出現。隨著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這一區域進行定義、區域劃分,長城地帶所包含的語境意義不斷擴大。
20世紀90年代初,李鳳山結合多年的民族學研究的成果,從民族的角度提出了“長城帶”的概念。他指出“兩千年間,活動在以萬里長城為中介的廣闊地域范圍之內的民族,與長城、與長城區域內的各個人類群體發生著密切的關系”,認為“這樣的歷史的動態關系,僅一線物化了的長城,是不能代替和反映的”,因此,提出了“長城帶”這樣一個概念。他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長城帶”民族融合、經濟文化交流等角度論述,深化長城帶的區域研究。同時劃定其范圍為“以萬里長城為中介,范圍大致包括今天遼寧、內蒙古、寧夏、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以及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微和青海、新疆的相當一部分地區。在中國北方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萬里長城南北各數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東西數千公里的廣闊地帶。”它從民族融合角度定義了“長城帶”,在長城區域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
1995年馮嘉萍等《萬里長城的地理界限意義》一文,從地理學的角度考察長城地帶,全面闡釋了長城的“地帶”意義,認為“自然地理環境是長城形成的基礎,然而‘人’———不同時期各種政治力量,對地理環境有很強的選擇。長城地帶正是歷代各政治集團的統治者,為了地域的擴張或防御,選擇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帶”。
同時,從自然、政治、文化、經濟地理的角度,充分分析了長城的“地帶”性特征,對長城地帶的地理特征進行了比較系統的闡釋和說明。反映了長城地帶這一名稱含義的不斷深化以及廣泛化。由于長城及其分布地區處于生態敏感帶。近年來,長城地帶的生態環境變遷研究成為長城研究的重要關注點。孔繁德從生態學的角度,考察長城在修筑、使用過程中對區域環境的影響,借此分析現代長城地帶生態環境問題和解決對策。鄧輝、韓昭慶等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出發,以長城作為標尺,考察長城地帶歷史時期的環境變遷問題。這些研究拓寬了長城地帶研究的領域。多學科、多視角的研究也深化了長城學的研究。
4.“長城地帶”概念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
通過梳理長城地帶研究的過程,不難看出,“長城地帶”這一概念在學術界和學科研究中的形成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最初,“長城地帶”是作為地理意義上一個區域指稱而出現的,由20世紀30年代西方來華探險考察活動催生,其第一次被明確使用則是源于考古學,是由日本考古學家江上波夫與水野清一在《內蒙古•長城地帶》一書中提出的,用以指稱地理范疇上沿長城地帶的區域。概念的第一次深化是由美國的地理學家歐文•拉鐵摩爾提出的,他是第一個明確將長城作為一個“地帶”去考察其周邊區域的人地關系、社會景觀、歷史功能的學者,明確了長城地帶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線”或者“帶”的概念,更是沿長城一線而形成的一個具有特定歷史、人文、自然等綜合內涵的區域地帶的概念。
接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考古學者越來越深入地對長城地帶進行研究,“長城地帶”這一概念作為一個考古學名詞開始被規范化應用。蘇秉琦先生最早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將其作為考古學區系類型中的北方地區核心提出來,對其范圍進行了大致的劃分,在一系列的有關北方地區考古的學術會議上。長城地帶作為北方區系的核心地帶在考古學界得到普遍的認同,并開始作為考古學名詞被固定下來。
改革開放后,隨著長城研究的不斷發展,歷史地理學、邊疆史、民族學、人類學、生態學等各個學科將目光集中在長城研究方面。對于這一地區的稱謂也不斷出現,如“長城地帶”、“長城帶”、“長城分布地區”、“長城沿線”等一系列稱呼相繼提出。而被考古學界規范應用的“長城地帶”受到了各個學科的認同,成為指稱長城區域的規范化名稱。許多學者亦從本學科的角度對這一地帶所涵蓋的范圍進行劃分,長城地帶的定義逐漸明晰化。同時,考古、民族、地理、歷史、邊疆研究等學科也在努力構建著長城地帶的“區域史”。
“長城地帶”概念表述的合理性
及其源于考古學的緣由“長城地帶”概念之所以形成,并在后來被固定為用以指稱長城沿線地帶這一特定區域的學術術語,是有其合理性的。
1.長城的帶狀分布特征符合“長城地帶”的表述方式
長城是冷兵器時代重要的軍事防御設施,其修筑主要為了防御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侵擾。自春秋戰國以后,秦、漢、金、明等20幾個王朝都修建了長城,這些長城分布具體位置不完全相同,但各朝代長城的走向卻具有一致性,都沿著北方地區自東向西呈帶狀延綿分布。“由西向東,自甘肅玉門關外,沿著河西走廊北側,東行經沙漠和黃土高原的交界處,再循內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錯帶,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嶺的背脊上,隨山勢而轉,直抵大海邊緣。”是一條重要的人文界線。
這些長城大都分布在自然地形地勢的過渡地帶上。長城帶北部分布著遼闊的蒙古高原,南邊則是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及河西走廊,是地理地貌上的帶狀過渡區。除此之外,這些長城還分布在氣候的過渡帶及其影響下的農牧界限的過渡帶上。除東西兩端分別位于半濕潤和干旱地區外,長城地帶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國由半濕潤向干早氣候區過渡的半干早氣候區,由于水分、氣候因素的影響,這一地區恰好處于我國的農牧交錯地帶。農牧界限空間在這一地區頻繁搬動,長城成為這一地帶的重要分界線。由于這些長城的帶狀過渡區域性質,歷史上的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向來沿著長城一線不斷彼此爭奪,使之成為歷代各政治集團為了地域擴張或防御,選擇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帶。因此,“長城地帶”的表述在學術研究上來講,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2.長城地帶的帶狀文化特征符合考古學區系
類型理論的分析和運用據前文所述,“長城地帶”作為一個名詞第一次出現是由考古學者(日本的江上波夫與水野清一)提出,其作為真正固定的學術概念術語是由中國的考古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并界定的,可以說,“長城地帶”是源于考古學科的一個學術概念和術語。究其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1)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研究方法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是通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探索生活在特定地區的古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學科。中國大陸幅員遼闊,不同區域之間的地理環境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別。在這些地理環境迥異的大部分區域內,人們適應著各自獨特的生態環境而生活著。不同地域的人類共同體所遺留的物質文化遺存必然有著獨特的特征。這些遺跡和遺物都有著空間維度。許多研究都指明考古資料具有重要的空間指示意義。因此,自考古學出現以來,許多的考古學作業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空間分析方法。通過對不同區域的考古遺存進行比較研究,從區域的物質差異和分布差異角度來探討文化的形成和解釋文化復雜性,從而揭示史前時期不同地區文明的形成,這一方法來自于地理學,在考古學上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區域劃分對考古學發展有重要意義。
中國的考古學文化研究從20世紀20年代,即近代考古學形成初期,就進行了分區研究。無論是梁思永和尹達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東西二元對立說,還是梁思永關于龍山文化的分區研究,都是力圖來發現和分辨當時所知文化的區域差異。
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紛紛開展,考古資料迅速增加。人們認識到各個地區的文化屬于不同系統的古代文化。這以后關于新石器時代的著作中,往往分區域來論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20世紀60年代,關于仰韶文化的考古資料空前增多,蘇秉琦把仰韶文化分為從洛陽到隴東這樣一個東西狹長的中心區及其外圍地區。中心區和外圍都可以根據區域性特征再劃分不同的類型。
20世紀70-80年代,蘇秉琦把分區研究理論應用到了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之上,提出了著名的區系類型學說,將全國范圍內的考古學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并親自應用它指導實踐活動。蘇先生的這一學說得到了考古學界的廣泛認同,在他的帶領下,各個區紛紛以區系理論指導具體的考古活動,區系研究理論成為指導新時代考古學的重要理論方法,區域分析的重要性被考古學者充分認識,并在考古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被應用。
長城地帶處于氣候過渡帶,環境脆弱地帶,從史前到歷史時期都是北方游牧文化與黃河流域農耕文化接壤、過渡地帶,是一條獨具特色的文化地帶。具有豐富的文化遺存。是中國北方區系的核心地帶,具有極大的考古研究價值。加之,1980年開始,蘇秉琦先生以長城地帶作為區系理論的重要“試驗地”,親自指導這一地區的考古工作,推動了長城地帶在中國考古學界重要地位的確立。
(2)長城地帶的階段性區系文化特征
長城及其附屬設施在歷史上呈“帶”狀分布在中國北方地區,這一地區在長城修建以前的史前時期即有著燦爛的文化,歷史時期的各種文化更是延續不斷。長城地帶史前時期就有著燦爛的文化,長城地帶東段屬于“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文化區系,經歷了興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趙寶溝、紅山、富河文化(約距今7000-5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距今4800年),夏家店下層文化(早期青銅文化,距今4500-3500年)。長城地帶西段屬于黃河中上游以仰韶文化為中心的文化區系,經歷了老官臺文化(距今7800-7300年),馬家窯文化(距今7000年-4000年),齊家文化(距今2025±155年-1915年±155年)各階段。長城地帶東西兩大區系的古文化開始直接接觸開始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地點在河套至岱海一帶。當中原文化進入龍山文化以后,這個地區的古文化也強烈表現出龍山文化的特點。同時,此時在長城地帶西部興起的齊家文化亦悄然出現于河套地區。
夏商時期,長城地帶的東部和西部,古文化的演變空前激烈,文化面貌與中原文化的反差愈來愈突出,東西部之間的聯系明顯加強,南北向各自和中原文化聯系,逐步為東西向的長城地帶東西部之間的聯系代替。“隨著聯系的不斷加強,長城地帶形成了一條以花邊鬲為代表的陶器群,和北方系銅器群一起,在長城地帶構成一條特征鮮明的文化分布帶。這條文化帶到周代經歷了一次較大的組合,變成以青銅短劍為特征,東部流行曲刃劍,西部流行觸角式劍,在長城地帶東西對峙,長城亦隨之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諸侯與北邊匈奴等民族的斗爭日趨激烈,秦、趙、燕等諸侯紛紛在北邊修筑長城,其后,為防御北邊匈奴等游牧民族,秦、漢亦大規模修建長城,在長城地帶形成了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的較量。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秦、漢政權除修筑長城外,還不斷往這一地區移民屯墾,大量的人口被遷移到了長城地帶,在這里,中原民族與游牧民族相互斗爭、不斷融合,長城地帶成為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一個匯聚地帶。
自秦漢以后,每個朝代長城的修筑都標志著一條特殊的文化帶的興起,這些文化帶不僅僅包含考古學文化,同時有著更加豐富的內涵。這些文化帶也都是長城文化帶整體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長城地帶的文化一直在這種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此消彼長中不斷發展,形成了很好的延續性,構成了北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長城地帶”概念在考古學科的日漸廣泛應用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區系類型理論,長城地帶成為北方區系考古文化分布的核心。與其有關的考古研究蓬勃發展,大批的專家投入到這一區域的考古研究中。“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這一專題逐漸深入,大量的相關成果不斷發表,一系列以“長城地帶”命名的學術研討會召開,這使“長城地帶”逐漸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考古學名詞。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考古學界,“長城地帶”被廣泛地規范化應用,日漸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考古學概念。其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1.以“長城地帶”考古為論題的專題學術討論會、座談會的召開
在蘇秉琦先生的主持和帶領下,以長城地帶為核心的北方地區考古工作火熱地展開,充分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在河北張家口蔚縣西合營三關考古工地、遼寧省朝陽市和喀左縣、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甘肅蘭州市和內蒙古包頭市召開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其中1983年的朝陽會議和1984年的呼和浩特會議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這一專門課題,會議還專門編輯了座談會文集輰訛輦,推動了長城地帶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進入21世紀以后,長城地帶考古文化研究繼續發展,分別于2001年8月在吉林召開了“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青銅時代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開了“內蒙古長城地帶考古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匯集了中、日、俄、美、韓、蒙等國的大批考古學家參加,會后出版了專門性的論文集。這些會議的召開,說明了長城地帶在中國考古學中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考古學界對長城地帶考古工作的重視。
2.以“長城地帶”作為題名的專業論文、學術著作的刊著
蘇秉琦先生提出以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區系以后,大批的學術論文、學術著作的章節以“長城地帶”作為題名或關鍵詞,圍繞長城地帶的考古發現及其所包含的考古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一篇博士論文以北方“長城地帶”命名,還有大量的文章雖然沒有以“長城地帶”作為題名和關鍵詞,亦圍繞這一論題進行相關的研究(如表二)表明長城地帶考古專題在考古學界得到了比較廣泛的關注。
3.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大批相關專家的出現
自上世紀80年代蘇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學區系類型論以后,考古學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以長城地帶為核心的北方地區考古工作從以往被忽視的境地中走出來,大批的專家學者和專門的研究機構進行著長城地帶的考古研究。最重要的“陣地”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該中心設立于1999年,其前身是“吉林大學中國北方考古研究室”,長期致力于以中國邊疆及其毗鄰地區的古代文化、古代人類、古代環境等課題為重點研究內容。許多在長城地帶研究有巨大貢獻的學者,如朱泓、林沄等都在這里從事研究工作,培養了大批的學術人才,還定期出版專題性的學術刊物《邊疆考古研究》,目前已經出版了9輯。
另外,內蒙古文物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等單位對于長城地帶的研究也做了許多的工作,促進了長城地帶考古研究的發展。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長城地帶考古研究在考古學界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研究方向。20世紀80年代和21世紀的初期,是長城地帶考古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期,考古學者對這一區域做了大量的研究,“長城地帶”逐漸成為考古學者經常使用和廣泛認同的學術術語。
結論
長城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象征。對于長城的深入研究不僅能為長城的保護提供合理建議,同時可以了解長城所承載的豐富的文化內涵。長城地帶是古代長城分布的主要區域,是長城這一工程的承載區域,是古代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主要區域。中國歷史上的諸多問題,都集中的反映在這里;同時,長城地帶也是生態敏感帶、農牧交錯帶,中國北方自然環境變化,最迅速地在這一區域表現出來,因此對于長城的區域研究是相當重要的。
綜上所述,本文梳理了“長城地帶”概念的形成過程,從最初作為一個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探險考察區域稱謂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到作為學術研究區域概念的界定,再到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固定概念,在考古學中廣泛應用,同時探索其在考古學中廣泛使用的原因及其表現。隨著長城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擴展,“長城地帶”概念逐漸被不同學科接納和逐漸廣泛應用,其在不同學科的具體的擴展過程和內涵界定尚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