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及教育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人的存在及教育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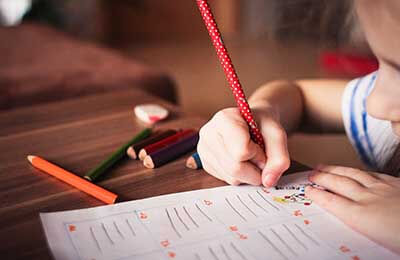
(一)存在的絕對(duì)性
無(wú)論是作為個(gè)體的人還是作為總體的人,人首先存在,才能思考存在,也才能籌劃如何存在。存在先于生活、先于生活的意義。存在具有絕對(duì)的價(jià)值,也是一切價(jià)值的基礎(chǔ)、依據(jù)和目標(biāo),這是人存在的絕對(duì)性基本含義。在這個(gè)意義上,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剝奪人存在的權(quán)力。“生存權(quán)”是一種基本人權(quán),是應(yīng)該得到全世界人民尊重的基本人權(quán),也是人道主義的最低原則。全人類(lèi)應(yīng)該共同反對(duì)旨在威脅和消滅自己及他人存在的一切自殺、暴力和戰(zhàn)爭(zhēng)行為,將其判定為最不人道的事情。正是由于這種存在的絕對(duì)性,所以每個(gè)人在正常的心態(tài)下,都有強(qiáng)烈地維護(hù)自己的存在或安全的動(dòng)機(jī)或本能。這種自衛(wèi)性的動(dòng)機(jī)或本能也是人生最根本的動(dòng)力。
(二)存在的意向性
人作為人的存在,不同于動(dòng)物的存在。在目前人類(lèi)意識(shí)所能達(dá)到的范圍內(nèi),動(dòng)物的存在是一種機(jī)體的活著,最多只活在自己的“感受性”里。而人的存在首先是作為一種“意向性的存在”,其存在的方式是受意識(shí)指引的,而不是受感覺(jué)指引的。意向性是人作為人的存在從可能不斷走向現(xiàn)實(shí)并開(kāi)創(chuàng)未來(lái)的前提條件。失去了意向性,人不僅失去了歷史,也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未來(lái),失去了生命的連續(xù)性,活在一個(gè)個(gè)毫無(wú)意義的不可理喻的瞬間。人對(duì)人的理解,包括對(duì)其自身的理解,都是通過(guò)對(duì)意向性的理解來(lái)達(dá)成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意向性是人類(lèi)的本性,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quán)。而意向性的基礎(chǔ)是“意志自由”。只有意志自由的人才有真正的意向性,也才能成為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人。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灌輸”、“洗腦”是不人道的,是違背人性的,是“精神上的屠殺”。
(三)存在的文化性
人是作為文化的存在而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被當(dāng)作人一樣來(lái)尊重,并不是因?yàn)樗哂腥说耐獗?而是因?yàn)樗哂腥说膬?nèi)心和外在行為表現(xiàn)。而這些東西都是文化的產(chǎn)物。不了解人所處的文化,就不了解人的存在本身。我們之所以被別人當(dāng)作人一樣來(lái)尊重,一定是因?yàn)槲覀兩砩系奈幕€可以被對(duì)方接受和理解。了解他人,就是理解他的文化。對(duì)人和人的生活進(jìn)行文化的說(shuō)明,有助于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和言行。
(四)存在的時(shí)間性
人作為人的存在是一種時(shí)間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與時(shí)間性比較起來(lái),人存在的空間性只是一種附帶的屬性。人的時(shí)間性才是第一位的。人是存在于時(shí)間之中的,是不斷呈現(xiàn)的和實(shí)現(xiàn)的。人的存在是歷史性的,是不斷向未來(lái)籌劃的,而且在本質(zhì)上是自我籌劃的。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造就人,只有人自己才能造就自己。我們必須反對(duì)在人的生成問(wèn)題上的各種各樣的決定論和宿命論的觀點(diǎn)。作為時(shí)間性的存在,人的存在又是有限的存在。存在的有限性是人生意義的基礎(chǔ)。認(rèn)識(shí)不到存在的有限性,就不能很好地深思存在的意義。
(五)存在的語(yǔ)言性
人作為人的存在還是一種語(yǔ)言的或話(huà)語(yǔ)的存在。因?yàn)?無(wú)論意向、意識(shí)和文化都表現(xiàn)為一種語(yǔ)言的形式。離開(kāi)了語(yǔ)言,我們既不能認(rèn)識(shí)自己,也不能理解別人。我們關(guān)于自身和世界的哪怕最簡(jiǎn)單的感覺(jué)也是由語(yǔ)言參與其中完成的。語(yǔ)言不單是交流的工具,而是我們的家,是我們的棲息之地。“失語(yǔ)”就等于讓我們踏上流浪的路程,改變我們的話(huà)語(yǔ)就改變了我們自己。在這個(gè)大眾媒體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媒體帝國(guó)主義”所推行的正是語(yǔ)言的暴力。一些人憑借政治上的、經(jīng)濟(jì)上或智力上的優(yōu)勢(shì),把自己的聲音廣為傳播,而使大多數(shù)人的聲音歸于沉寂。讓人說(shuō)話(huà),建立一個(gè)人人可以發(fā)言的社會(huì)制度,是民主社會(huì)的基石。
(六)存在的獨(dú)特性
世界上沒(méi)有兩片相同的樹(shù)葉,也沒(méi)有兩個(gè)相同的人。這不僅是在人的身體特征上,更是在人的精神特征和個(gè)體行為習(xí)慣上。精神特征的獨(dú)特性主要是認(rèn)識(shí)背景的獨(dú)特性和認(rèn)識(shí)結(jié)果的獨(dú)特性。個(gè)體行為習(xí)慣上的獨(dú)特性主要表現(xiàn)在人們?cè)诿媾R一種刺激上,所做出的反應(yīng)的方式和強(qiáng)度不同。人存在的獨(dú)特性也給他的生活世界涂上了個(gè)性的色彩,每一個(gè)人的生活世界都是獨(dú)特的,不同的事物和事件在各人的生活世界中被解釋為不同的意義。人的獨(dú)特性和其生活世界的獨(dú)特性是不可喪失,也是不可讓渡的。否則,人就被他人或社會(huì)力量異化了。
二、人作為人的存在問(wèn)題
上述人作為人存在的特點(diǎn)決定了人的一生中必須面對(duì)的下列“存在問(wèn)題”。這里所說(shuō)的“存在問(wèn)題”區(qū)別于“生存問(wèn)題”,后者一般只涉及到具體的存在方式,而前者則關(guān)系到存在本身的意義、價(jià)值或根據(jù)。從邏輯上說(shuō),存在問(wèn)題是人生的根本問(wèn)題,生存問(wèn)題是人生的枝節(jié)問(wèn)題。從日常經(jīng)驗(yàn)上說(shuō),存在問(wèn)題的提出要早于生存問(wèn)題。一般來(lái)說(shuō),人們?cè)诔赡暌郧熬筒粩嗟刈穯?wèn)和探求存在問(wèn)題,而生存問(wèn)題只是到了成年后才真正成為個(gè)體所關(guān)心的問(wèn)題。不僅如此,就是到了成年階段,存在問(wèn)題依然存在。所以,在人的一生中,無(wú)論什么時(shí)候,人們對(duì)存在問(wèn)題的觸及和思考,都會(huì)更加有益于生存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和解決。
(一)死亡的問(wèn)題
作為絕對(duì)的存在,人在本性上都是趨生避死、樂(lè)生畏死的。作為時(shí)間的存在,盡管人在自己的天年之中可以籌劃自己的生活,但人總有一死。最后的死亡是對(duì)人存在絕對(duì)性的決定性毀滅。這是人生的大悲劇。正如布洛赫所說(shuō),“死亡把一切咬碎。……沒(méi)有哪一種失望可以同死亡的消極前景相比,在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前,沒(méi)有哪一種背叛可以與死亡的背叛相提并論。”[1]死亡給人們帶來(lái)了恐懼,即使勇敢者也不例外。為了逃避死的恐懼,人們采取各種辦法:避免談?wù)?避免回憶;假裝與自己無(wú)關(guān);祭祀;把死亡解釋為偶然事件;把死亡美化;杜撰“輪回說(shuō)”或“復(fù)活說(shuō)”。然而這一切面對(duì)必然的死亡都無(wú)濟(jì)于事。人們終究要獨(dú)自面對(duì),獨(dú)自承受,獨(dú)自經(jīng)驗(yàn),無(wú)法逃脫。但死亡并沒(méi)有那么可怕。死亡對(duì)于人生來(lái)說(shuō)不是無(wú)意義的,而是有意義的,不僅意味著毀滅,更意味著創(chuàng)造。“假如沒(méi)有死,任何東西都失去真正的份量,我們的一切行為永遠(yuǎn)是極不現(xiàn)實(shí)的。……只有死才創(chuàng)造了無(wú)可挽回的嚴(yán)肅性和毫不留情的‘永不重復(fù)!’換句話(huà)說(shuō),死亡創(chuàng)造了責(zé)任,正因?yàn)槿绱艘矂?chuàng)造了人的尊嚴(yán)。”[2]波普爾也認(rèn)為:“有些人認(rèn)為生命沒(méi)有價(jià)值,因?yàn)樗鼤?huì)完結(jié)。他們沒(méi)有看到也許可以提出相反的論點(diǎn):如果生命不會(huì)完結(jié),生命就會(huì)沒(méi)有價(jià)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每時(shí)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xiǎn),才促使我們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生命的價(jià)值[3]。”事實(shí)上,生者只有在面對(duì)死亡的時(shí)候,只有在與亡者對(duì)話(huà)的時(shí)候,才有獲得一種存在意義上的寧?kù)o與超越,才能獲得生活的內(nèi)在勇氣和智慧。
(二)奴役的問(wèn)題
作為意向性的存在,反抗奴役,追求內(nèi)在的和外在的自由是人的本性。自由對(duì)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shuō),一部人類(lèi)的斗爭(zhēng)史就是追求自由的歷史,一部人類(lèi)的文明史也就是自由不斷實(shí)現(xiàn)和擴(kuò)展的歷史。就個(gè)人而言,自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自由的狀態(tài)是我們創(chuàng)造性地思考的狀態(tài)。沒(méi)有自由,個(gè)體就不會(huì)有新的見(jiàn)解,人類(lèi)就不會(huì)有知識(shí)的進(jìn)步,從而也就不會(huì)有新的明天。然而,正如啟蒙思想家盧梭所說(shuō),“人生來(lái)是自由的,但無(wú)時(shí)不在枷鎖之中”。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所遭受的鉗制和奴役是多方面的,以至于單憑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就可以斷定自由是一種多么奢侈的價(jià)值要求。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深入研究了人的奴役與自由的關(guān)系,提出了人所遭受的多種奴役形式,如受“自然的奴役”、“社會(huì)的奴役”、“文明的奴役”、“自我的奴役”,等等。“自然的奴役”是指“受自然的客體化、異己性和決定性的奴役”。[4]“社會(huì)的奴役”是指:人受社會(huì)的客體化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外化的奴役。“社會(huì)一旦被視為擁有比人的個(gè)體人格更高的位置,人也就被貶成了奴隸。”[5]社會(huì)“有機(jī)論”是社會(huì)客體化的幻想。“文明的奴役”是指:人感受到自身被文明的碎片所擠壓,人被置于一種特殊的工具的統(tǒng)治下。“自我的奴役”是指人把自身向外拋出,異化了自身,其根源是“奴役的社會(huì)”、“自我中心主義”、“動(dòng)物式的本能”等。哲學(xué)家羅素懷著極大的熱情歌頌人的自由,吁請(qǐng)人們捍衛(wèi)自由,同時(shí)指出威脅人的自由的五種社會(huì)因素:法律制裁、經(jīng)濟(jì)懲罰、證據(jù)歪曲、不合理的教育、宣傳工作。因此,人生要想獲取自由,就必須為之而奮斗。
(三)有限的問(wèn)題
作為時(shí)間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存在。不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由此導(dǎo)致了人的發(fā)展空間和發(fā)展能力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在經(jīng)驗(yàn)的世界中往往給人們以渺小的、卑微的和可憐的感覺(jué)。這是任何一個(gè)有反思能力的人所共有的感受。這種感受盡管不像對(duì)于死亡的感受那樣從根本上毀滅生命的希望,但是也每時(shí)每刻地動(dòng)搖著人們生活的信心和勇氣。超越這種有限性,從而達(dá)到一種無(wú)限的境界,是人近乎本能的渴望。這種渴望本身反映了人作為一種時(shí)間性存在所具有的內(nèi)在矛盾。這種內(nèi)在矛盾不僅存在于個(gè)體的身上,而且存在于人類(lèi)的群體無(wú)意識(shí)之中。就個(gè)體而言,中國(guó)古代士大夫“青史留名”的追求和西方基督徒對(duì)永恒天國(guó)的向往,無(wú)不體現(xiàn)了個(gè)體試圖通過(guò)自己的努力達(dá)到對(duì)生命有限性超越的渴望;就人類(lèi)而言,對(duì)外部世界無(wú)止境的開(kāi)掘和對(duì)內(nèi)部世界的持續(xù)理解,其終極目的也就是要克服存在的有限性帶來(lái)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而來(lái)的生存焦慮,從而將一個(gè)有限的存在錨在一個(gè)無(wú)限的背景上。宗教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各種獻(xiàn)身行為從深層的心理需要說(shuō),恐怕都是為了幫助人們認(rèn)識(shí)此時(shí)此刻生命的有限性,并幫助人們從內(nèi)在或外在方面超越這種有限性,以臻達(dá)某種形式上的無(wú)限境界。對(duì)“無(wú)限”、“永恒”、“普遍”等等的追尋,永遠(yuǎn)是“有限”的人生不可遏制的沖動(dòng)。但是,頗具悲劇色彩的是,我們作為時(shí)間性的存在,永遠(yuǎn)也無(wú)法去真正地以我們能夠理解的方式臻達(dá)無(wú)限、永恒和普遍的境界。
(四)孤獨(dú)的問(wèn)題
作為獨(dú)特性的存在,人總是孤獨(dú)地以自己的方式活在這個(gè)世界上。這個(gè)世界對(duì)于某一個(gè)人來(lái)說(shuō),可能給予他很多很多東西,但是惟一不能給他的就是“又一個(gè)”他自己。當(dāng)代的克隆技術(shù)最多也只能給予一個(gè)人生理上的“又一個(gè)”他自己,而不能給予一個(gè)人精神上的“又一個(gè)”他自己。所以,人,生命,就是惟一,就是孤獨(dú),它從我們出生的時(shí)候就伴隨著我們,一直跟隨我們到老。由孤獨(dú)所引起的無(wú)助感、寂寞感和恐懼感時(shí)常爬上心頭。為了走出這種惟一和孤獨(dú),為了克服這種無(wú)助感、寂寞感和恐懼感,人必須向別人開(kāi)放,必須借助于自己的文化性和語(yǔ)言性與他人交往,從而獲得親密感、歸屬感和安全感。然而,這種交往并不必然是愉快的過(guò)程,并不一定能達(dá)到目的。語(yǔ)言的障礙、文化的隔閡以及利益的沖突總是使得一個(gè)又一個(gè)的“聚會(huì)”不歡而散。不僅如此,熱鬧的“聚會(huì)”之后,是更加難以忍受的孤獨(dú)。
(五)自我認(rèn)同的問(wèn)題
作為絕對(duì)性、獨(dú)特性和時(shí)間性的存在,人總是以一種非常夸張的方式來(lái)看待“自我”,伸張自我的權(quán)力,追求自我的實(shí)現(xiàn);作為一種意向性的存在,人總是在反復(fù)地提出一個(gè)問(wèn)題———“我是誰(shuí)?”或“我是什么?”作為一種語(yǔ)言性和文化性的存在,人又總是很難將自己與他人區(qū)分開(kāi)來(lái),“我”存在于“我們”之中;“他”存在于“他們”之中,以至于不理解“我們”就不能理解“我”,不理解“他們”就能不理解“他”。如此一來(lái),作為價(jià)值和意義中心的“自我”究竟存在不存在?能不能清晰地辨別?我能在意識(shí)中給自己清晰地畫(huà)一幅肖像嗎?這樣的問(wèn)題,毫無(wú)疑問(wèn)地存在于我們內(nèi)心的最深處;我們每一個(gè)人也都經(jīng)常地處于由這些問(wèn)題所引發(fā)的自我認(rèn)同危機(jī)之中。上述人作為人的存在問(wèn)題在不同人的不同年齡段都會(huì)以不同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所有的人都應(yīng)該高度重視這些存在問(wèn)題對(duì)于生活的影響。日常生活中,每個(gè)人也都會(huì)基于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對(duì)這些問(wèn)題進(jìn)行或多或少的思考,但是這種思考是很不夠的,也不能完全地幫助我們擺脫上述問(wèn)題的困擾。只有當(dāng)我們對(duì)這些存在的問(wèn)題進(jìn)行系統(tǒng)和深入地思考后,我們才能活得清醒、堅(jiān)定,富有熱情,充滿(mǎn)朝氣。
三、人作為人的存在及其教育
時(shí)下最時(shí)髦的一句教育口號(hào)是“教育‘以人為本’”,而人作為人的存在卻具有上述的一些問(wèn)題。因此,教育也必然地是與上述存在問(wèn)題相伴隨的,上述存在問(wèn)題也必然會(huì)影響到教育,表現(xiàn)在學(xué)校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不能不知道這一點(diǎn),也不能假裝看不到這一點(diǎn)。然而,遺憾的是,在現(xiàn)代教育實(shí)踐和教育學(xué)研究中,由于種種復(fù)雜的原因,絕大多數(shù)教育家和教育學(xué)家確實(shí)在這方面存在著視盲區(qū)。他們只認(rèn)識(shí)到人的“生存問(wèn)題”及其對(duì)個(gè)體和社會(huì)所構(gòu)成的威脅,看不到人作為人的“存在問(wèn)題”及其對(duì)個(gè)體和社會(huì)所構(gòu)成的威脅。所以,現(xiàn)代教育歸根到底就是“生存教育”(educationforsurviving),而不是“存在教育”(educationforbeing)。這種生存教育給予了人們以生存的意識(shí)和能力,卻沒(méi)有給予人們以生存的理由和根據(jù);給予了人們對(duì)于自己和人類(lèi)文明盲目的樂(lè)觀,卻沒(méi)有給予人們清醒的頭腦。其結(jié)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現(xiàn)代人擁有了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強(qiáng)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卻越來(lái)越對(duì)存在的必要性發(fā)生懷疑。這種懷疑使得現(xiàn)代人的生活充滿(mǎn)了無(wú)聊、空虛、寂寞和無(wú)意義感,從根本上威脅到人生的幸福與人類(lèi)文明的進(jìn)步。因此,“以人為本”的教育不能只考慮作為“工具的人”,也應(yīng)該考慮作為“目的的人”;不能只考慮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也應(yīng)該考慮如何增加人的存在的意義。今日的教育,應(yīng)該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首先就應(yīng)該改變教育的對(duì)象觀。
教育的對(duì)象觀包括兩方面的認(rèn)識(shí):一是教育的對(duì)象是什么,另一是如何認(rèn)識(shí)教育的對(duì)象。關(guān)于前一個(gè)問(wèn)題,答案也許并不難找。在終身教育理念提出來(lái)之前,人們認(rèn)為教育的對(duì)象就是兒童或青少年學(xué)生;在終身教育理念提出來(lái)之后,人們認(rèn)識(shí)到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教育的對(duì)象,有關(guān)教育對(duì)象范圍的認(rèn)識(shí)擴(kuò)展了。但是,關(guān)于后一個(gè)問(wèn)題,卻很不容易回答。從教育史上看,人類(lèi)有關(guān)“作為教育對(duì)象的兒童”的認(rèn)識(shí)有一個(gè)變化過(guò)程:在古代,人們認(rèn)為作為教育對(duì)象的兒童就是“作為成人雛形的兒童”或“小大人”,否認(rèn)兒童有著獨(dú)特的心理活動(dòng)和發(fā)展規(guī)律;在現(xiàn)代,由于受兒童中心主義和心理主義的影響,人們認(rèn)為作為教育對(duì)象的兒童就是“作為兒童的兒童”,強(qiáng)調(diào)整個(gè)教育工作要遵循兒童身心發(fā)展特點(diǎn)和規(guī)律;在后現(xiàn)代,一切教育者不僅要意識(shí)到“作為兒童的兒童”,而且要意識(shí)到“作為人類(lèi)的兒童”。這就是說(shuō),“兒童”和“我們”同樣既分享著人類(lèi)的尊嚴(yán),又遭遇著人作為人的存在問(wèn)題,為它們所苦惱。因此,教育兒童或其他所有人,就不僅意味著要幫助他們提高生存能力,而且要幫助他們提高存在的智慧;教育者不能僅以功利的眼光來(lái)看待教育的對(duì)象,還應(yīng)該以存在的眼光來(lái)打量教育的對(duì)象。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其次必須重構(gòu)教師的自我意識(shí)。無(wú)論什么時(shí)候,教師在教育過(guò)程中的作用都是不能代替的。而教師在教育過(guò)程中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以及如何發(fā)揮作用,一方面取決于教師的學(xué)生觀,另一方面取決于教師的自我意識(shí)。所謂教師的自我意識(shí),就是教師如何看待自我。關(guān)
于這個(gè)問(wèn)題,歷史上也有一個(gè)變化過(guò)程:在古代,無(wú)論是“作為神啟的教師”還是“作為官吏的教師”,都將自己看作是一種特殊社會(huì)利益階層的代表;在現(xiàn)代,隨著師范教育和教師專(zhuān)業(yè)化運(yùn)動(dòng)的開(kāi)展,教師將自己看作是一種“專(zhuān)業(yè)人士”———依靠特殊的專(zhuān)業(yè)態(tài)度、技能、知識(shí)及其訓(xùn)練而生活的人,并擁有相應(yīng)的專(zhuān)業(yè)權(quán)威。這中間,體現(xiàn)了一種歷史的進(jìn)步性。但是,無(wú)論是“作為神啟的教師”、“作為官吏的教師”,還是作為“作為專(zhuān)業(yè)人士的教師”,他們?cè)谝庾R(shí)中都將自己“功能化”了,將自己看成是肩負(fù)著某種特殊的社會(huì)功能的人,而沒(méi)有注意到自己也是“人”并作為“人”而存在著。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教師本人必須要撕破“教師”這個(gè)“面具”,回到他本來(lái)的和豐富的人性狀態(tài)。再次,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就必須在更新教育對(duì)象觀和教師自我意識(shí)的基礎(chǔ)上重構(gòu)師生關(guān)系。受制約于現(xiàn)代的教育對(duì)象觀和教師的自我意識(shí),現(xiàn)代的師生關(guān)系基本上是一種“功能性的關(guān)系”,即為了滿(mǎn)足某種外在的個(gè)體或社會(huì)的功能性目的而建立起來(lái)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教師和學(xué)生不是以完整的人的存在方式出現(xiàn)的,而是以各自所扮演的“教師”和“學(xué)生”的角色面貌出現(xiàn)的,教師和學(xué)生真實(shí)的自我深深地掩藏在這種角色互動(dòng)的表面之下,彼此之間缺乏一種本源性的真誠(chéng)和信任,也根本不把對(duì)方作為存在意義上的“人”來(lái)看待。評(píng)價(jià)這種師生關(guān)系質(zhì)量的惟一標(biāo)準(zhǔn)就是輔助完成預(yù)期社會(huì)或個(gè)體發(fā)展功能的多少或大小。這種師生關(guān)系導(dǎo)致整個(gè)教育生活過(guò)于注重“才”的培養(yǎng)和選拔,而忽略“人”或“人性”的尊重和教化。在今天這樣一個(gè)極端功利主義的時(shí)代,指望在短時(shí)期內(nèi)徹底改變這種師生關(guān)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師生關(guān)系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即主要局限于“生存”的層次,而不能達(dá)到“存在”的層次。為了更好地關(guān)注日益嚴(yán)峻的青少年一代作為人的存在問(wèn)題,師生關(guān)系有必要從“功能性關(guān)系”深入到“存在性關(guān)系”。
所謂存在性關(guān)系是指:師生關(guān)系首要的不是“教師”和“學(xué)生”之間的關(guān)系,而是“作為教師的人”與“作為學(xué)生的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功能性關(guān)系中,師生之間是有差別的,教師是“雙料專(zhuān)家”(“學(xué)科專(zhuān)家”與“教育專(zhuān)家”),擁有“專(zhuān)業(yè)”所賦予的權(quán)威。在存在性關(guān)系中,師生之間的共性就凸顯了出來(lái),面臨著共同的存在問(wèn)題。在面對(duì)和解決這些問(wèn)題的過(guò)程中,教師作為成年人的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是有用的,但卻是不充分的,教師的絕對(duì)權(quán)威自然也就不復(fù)存在。在這個(gè)關(guān)系層次上,師生之間需要的是真誠(chéng)的交流、深刻的反省和積極的對(duì)話(huà)。也正是在這種存在性關(guān)系中,學(xué)生的存在問(wèn)題才能顯現(xiàn)出來(lái)并從教師存在經(jīng)驗(yàn)的反省中獲得啟迪。第四,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就應(yīng)該引導(dǎo)青少年學(xué)生用一種嚴(yán)肅的態(tài)度來(lái)看待人的存在問(wèn)題,防止他們將這些問(wèn)題看成是似有非有或可以置換的問(wèn)題,啟發(fā)他們?nèi)ンw驗(yàn)和討論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問(wèn)題,最終培育他們存在的智慧。可能有人要問(wèn),在青少年學(xué)生的日常生活中,存在這些問(wèn)題嗎?即使它們存在,有沒(méi)有必要引導(dǎo)他們?nèi)ンw驗(yàn)和討論這些問(wèn)題?青少年學(xué)生的主要任務(wù)難道不應(yīng)該是“學(xué)習(xí)”和“發(fā)展”嗎?這樣的問(wèn)題恰恰說(shuō)明,受功利主義的支配,教育長(zhǎng)期以來(lái)已經(jīng)遺忘了青少年一代作為人的存在所遭遇的“存在問(wèn)題”,將青少年學(xué)生的所有問(wèn)題都?xì)w結(jié)為“學(xué)習(xí)”和“發(fā)展”的問(wèn)題。事實(shí)上,這些“存在問(wèn)題”,不僅在青少年學(xué)生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只不過(guò)整個(gè)現(xiàn)代教育———學(xué)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huì)教育———沒(méi)有給予提出的機(jī)會(huì)或討論的空間罷了。然而,這些受到忽視或壓抑的存在問(wèn)題卻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困擾著青少年學(xué)生的生活。
最后,教育要關(guān)注人的存在問(wèn)題,就應(yīng)該將存在問(wèn)題的討論與青少年學(xué)生存在經(jīng)驗(yàn)的自我反思結(jié)合在一起,而不是單純地講解一些存在的現(xiàn)象或知識(shí)。存在問(wèn)題不是一種外在于人生的問(wèn)題,而是一種內(nèi)在于人生的問(wèn)題。所以,存在問(wèn)題的討論必須訴諸于討論者本人的存在經(jīng)驗(yàn)。這正是我們當(dāng)前的教育所缺乏的。實(shí)事求是地說(shuō),當(dāng)前我們的教育中也偶爾涉及上述的存在問(wèn)題。但是,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都基本上將那些問(wèn)題當(dāng)成是一種外在的問(wèn)題,而非把它們看成是與自己的存在有密切關(guān)系的內(nèi)在問(wèn)題來(lái)對(duì)待。因此,個(gè)體的存在經(jīng)驗(yàn)基本上是不參與整個(gè)教學(xué)過(guò)程的。例如,各個(gè)教育階段的教科書(shū)中都會(huì)涉及到“死亡”這個(gè)主題。但是,教科書(shū)的死亡故事給人的印象是:死亡是別人的和將來(lái)的事。我可以贊賞、哀悼或嘲笑各種各樣的死,但我自己是不用為之操心的。這樣的存在主題根本不能觸及和觸動(dòng)個(gè)體的存在經(jīng)驗(yàn),因而也不能使個(gè)體從中受到存在的教育,克服存在的危機(jī),提升自己的存在智慧。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教育也許就是存在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