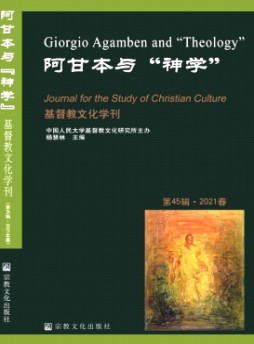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結合思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結合思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打從寸九世紀初馬禮遜來華傳教始,基督教在中國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百多年間,她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一直以“洋教”的形象出現。解放前,傳教士被稱為“洋教士”,中國信徒也背上“二毛子”的稱號,“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成為不少國人對基督教的指控;而中國教會如何完成“本色化,’的任務,也一直成為很多傳教士及華人信徒熱衷討論的課題(‘解放后,在“反帝”的政治浪潮下,基督教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強烈的沖擊;在教會內部展開的‘’凈化教會”運動,無寧說明了在政府眼中,教會與西方帝國主義間的密切關系。今天,雖然中國教會在三自的目標下,已達致由中國人自治、自養及自傳的目標,但在眾多中國人心目中,基督教仍具有相當的“洋教”形象,卻是毋庸爭議的。本文旨在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近百年來中國教會在從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方面的努力,期望通過評檢過去,從而為今天反省的一個參照。
一、福音的現代化關懷
基督教傳人中國之時,適值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一頁頁充滿內憂外患的近代歷史一于焉揭開。打從鴉片戰爭以還,中國屢敗于西方帝國主義,受盡屈辱,向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的優異;如何尋求“富強”也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主流觀念。所謂“富強”,用今天的說法,就是現代化(modernizati()n)的意思。當然,對于中國文化如何步向現代化,朝野間也呈現了不同的體驗,但無論如何,大家均相信“變”是必須的,只是在變的程度上,彼此存有爭論而已。但是總的來說,隨著十世紀末國人危機意識的普遍高漲,在“救亡”的呼聲下,國人愈益傾向質疑及批判傳統文化的價值,并認定西方文化(即“啟蒙,’)在各方面優越。現代化因而成為中國擺脫亡國運,邁向富強的先決條件。現代化不僅是中國的需要,也成為基督教的關懷。事實上,在一個非基督教的社會里,基督教作為外來的宗教,其傳播委實面對著很多的困難。“我為甚么要成為基督徒?”成為每一個中國人考慮阪信時必定發出的疑問。職是之故,在普遍國人正關懷國家文化的現代化時,中國教會遂認定:要是基督教能在中國文化處于變動、尋求更新之際,證明信仰的貢獻的話,則基督教便可以找到她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合法性及必須性,這也是福音在這片上地上得以生根的關鍵所在。另方面,不少中國基督徒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反省,除了是從宣教的立場出發外,也是出于個人自身的關懷。特別是那些從儒入耶的信徒,他們在阪信新宗教的時,卻不是意味著要對舊有的信仰(儒家統)的全盤否定;因此,反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正是他們尋索中國基督徒身分的表現,并確立其安身立命的基礎所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華的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便致力于結合基督教信仰對中國文化的關系。扼要而言,他們的工作主要分兩方面:第一、是調適與對話的進路,即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共同點,調和兩者存在的差距,以減少傳教時面對的阻力;第一二、是改變與更新的進路,即是說明信仰如何更新中國文化,成為其步向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的動力所在。
二、十九世紀的努力
1.西化與基督化盡管我們現在可以若干客觀的標準來界定現代化,但毋庸置疑的是,現代化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具體的指涉就是“西化”(westernization)。因為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西方國家就是富強與進步的象征,也是他們唯一可以學習的對象。這樣看來,壓根兒就不存在一個非西化的現代化的內容。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下,清廷終于在一八六O年展開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這場運動背后的指導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長技”就是西方的“船堅炮利”。換言之,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戰敗后,終于從昔日天朝意像中清醒過來,承認自身在“器物”(teehnologieal)層面的落后。不過,中國在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中敗于日本,卻又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失敗。甲午戰敗所引發的危機意識,逼使更多國人認定,中國文化的不足,不僅是在器物的層面,更進深至制度(institutional)層面。日本自明治維新后推行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因而成功地躍升為東亞強國,正說明改革制度的必要。在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不同程度的檢討時,不少傳教士與中國信徒也致力于提供一個基督教版本的連釋。這個連釋的基本假設,就是建基于西化與基督教的關系之上。絕大多數的來華傳教士均深信,西方文明富強的關鍵,乃根源于基督教精神。換言之,西化與基督化之間,乃存在著某種源于本質的因果關系,基督教信仰是“因”,西方富強文明是“果”。既然西方文明乃從基督教精神中孕育而生,那么現在中國文化正處于去舊迎新,向西方學習之際,傳教士便應全力參與其中,好讓中國擺脫“異教”的國度,迎向西化的模樣之中。傳教士相信,“西化”的環境,將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傳播。所以,他們對中國正在從事的西化改革,均抱以極大的期望。不僅如此,他們更全力參與其中,好改變中國的異教上壤,以促進中國的基督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傳教士乃調整其傳教策略,致力參與中國的教育、社會及文化改革工作。他們認定,此等工作本身已具有“目的”(ends)的意義,而非僅是依附于傳教工作的“手段,’(means)。這些傳教士包括林樂知、李提摩太及丁題良等,他們的工作自然引起其他“基要派”傳教士的激烈反對,并被斥責為偏離了正統的傳教路線,有關問題也在一八七七及一八九O年兩次在華教士會議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及討論。在改變與更新的進路上,除了上述的傳教士相信西化可以促進基督化外,也有不少中國基督徒從另一個角度來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他們同樣認同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密切關系,但是他們卻確認,中國文化若單憑制度上的革新(西化改革),并不足以促成富強的實現。例如有信徒指出,一切的“洋務”、“新法”不過是“末技”而己,中國振興的關鍵,不在這些“末技”,反倒是作為“根本”的“天道”。若不是先以“天道”改變人心,則任何的新法新學,也不過是以舊人行新法而已!換言之,基督化才是促進中國實現西化的首要條件及充份保證。
2.文化適應
除了改變與更新的進路外,十九世紀中國教會結合信仰與文化的另一條進路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調適與對話的_I_作。這里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具體一點,就是儒家思想。盡管儒學傳統在十九世紀末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畢竟其作為二千多年的正統思想,在中國社會里仍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力。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遇之時,不少中國人強調儒學已具自足價值,根本不需信仰基督教;抑有進者,他們更以儒家思想作為反對基督教的理據。職是之故,基督教信仰與儒家傳統的關系,遂成為十九世紀中國教會不得不認真處理的課題。扼要而言,中國教會在這方面,主要是在“基督或孔子”(ChristorConfueius)及“孔子加基督”(ConfueiuSplusChrist)之間,展開激烈的討論。大部分的傳教士確信,儒家思想正是基督教在華傳播最大的障礙,因此,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因為“天道”與“人道”之間.必須予以嚴格的界別,不容混淆。不過,也有少部分傳教士,以及不少中國基督徒(特別是從儒人耶者)卻確信,基督教與儒家之間,不僅有共通的地方,抑且前者可以完善后者,補其不足。“合儒”、“補儒”的理論,由此建構起來。例如有一位名何玉泉的倫敦會長老,在(萬國公報》_卜,主張中國六經所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要告白的上帝。另一些信徒也指出儒家“以五倫為本”,而圣教則屬“感化救贖之道”,正可以“補儒者之未發”。這些言論表明,不少入教的中國儒生之阪信基督教,雖然意味著他們對儒家傳統有所不滿,但仍得留意,他們卻并沒有完全與之劃清界限,反倒是致力于調和兩者間的張力。
3.小結
我們該如何看待中國教會在十九世紀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努力呢?首先,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充分肯定基督教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十九世紀中國人獲取西學的途徑,主要是通過翻譯、新式學堂、學會、報刊雜志及出國留學五途。但是,我們得留意,這些途徑,絕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紀末才普及的(如學會、新式教育、留學日本及報刊),在此之前,只有清政府一旱期的幼童留美計劃及在洋務運動中從事的官辦翻譯工作:這些_L作要不是中途中輟,便是把西學局限在“器物”的層面。但與此同時,傳教士已經通過為數眾多的教會學校及報IjJ大量引介西方思想文化。換言之,基督教成為早期國人獲取西學的重要渠道,其貢獻不容忽視。其次,盡管中國知識分r在中國文化劇變之際,對西方文明的認同程度愈益加深,但是他們卻沒有像傳教士的預料般,一并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背后的基督教信仰。中國教會“配套式”的傳教乎段,不管是主張西化促進基督化,或是基督化成全西化者,均未能收到期望的果效。抑有進者,當十九世紀末以還,中國人學習西學的途徑驟增時,基督教一方面失去其昔日的優勢,另一方面也開始要承受國人從西方引介的無神論思潮的沖擊。最后,中國教會在協調信仰與文化的進路上,誠然成為基督教本色化的初步反省。今天我們常常有一個印象,以為中國教會對文化層面的本色化的討論,大抵是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因應“非基運動”的沖擊才開始;但事實上,撇除個別西方傳教士不談,晚清中國基督徒知識分一子大致上在“合儒”及“補儒”論方面,均有頗為一致的集體反省,為日后的工作奠下基礎。
三、二十世紀的反省
1.救亡壓倒啟蒙
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問題方面的困擾并沒有隨著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而得到解決,反倒是局勢的變化,使他們在思考與反省時,愈趨走向一條激進之路。他們感到困擾的問題是:共和政體的建立,表明中國人在制度層面徹底改革的決心,但是,中國的問題卻并沒有隨著帝制的結束而改善過來,相反,卻是內困于袁世凱及軍閥割據之苦,外侮于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之侵。救亡圖存的心態,逼使知識分子更多地以“一元”的思想模式來思考“救國”的問題。他們急于為中國面對的困局尋找出路,并將復雜的國家、社會、文化問題約化為一個終極的“根本”問題(如民心、帝國主義)。然后再希望能夠迅速地找到一個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出路;唯有這樣,則中國人才能從亡國的陰影中得到解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才有希望。
2.“基先生”與救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在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進路上,顯然也不能豁免于整體時代的趨勢。由于此時儒家傳統也受到新文化思潮的沖擊,備受批判,失去昔日正統權威的角度,所以儒家作為本色化的對象的進路,顯然已不是此階段的重點所在。例如吳雷川在二十年代初期,尚致力于調和儒家與基督教,但到三十年代,也揚棄了這種方‘法,改以現實處境作為結合信仰與中國的進路了。毋庸置疑,在國家處于多事之秋,救國成為國人普遍的終極關懷之時,基督教要是要說明她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證明在國家社會的問題上,她可以提供的出路了。正如前述,此時國人正急于診斷中國的問題,并尋索根治的良藥。于是,“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馬先生,’(馬克思主義)、“美小姐,’(美學)、“孔夫子,’(新儒家)紛紛登上歷史的舞臺,企圖向國人證明其救國的能力。正當百家爭鳴、群雄并起之際,“基先生”也代表中國教會參與競賽,期望基督教能夠成為根治中國問題的良方妙藥,從而達致“中華歸主”的宏愿。盡管中國教會認定基督教是拯救中國問題的唯一方案與“獨家出賣”(王治心語),但是,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之間,對基督教如何救國,卻有著殊異的理解。換言之,“基先生”也以不同的形象,呈現在國人面前。扼要而言,二十世紀前期在中國出現的耶穌基督,一共有四個形象。第一、是作為道德人格重建者的基督。主張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端在人格、民心的更新,而耶穌的人格,正是理想完美人格的典范。他的愛、犧牲、舍己的精神,恰好是醫治中國道德及精神問題的良藥,也是社會重建的文化基礎。余日章、趙紫哀等即持此論。第二、是作為社會改造者的基督。他們相信,中國的問題,端在于社會的種種缺漏。因此,基督徒應致力參與不同層面的社會改革(如教育、農村建設等);而耶穌在世的最大使命,正是鼓吹改革社會的意識,從而實現天國降臨的基礎。第三、是作為社會革命者的基督。持守這個形象的基督徒強調,要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能單靠個別層面的改革,因為這里涉及根本及全盤的問題,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另建新的制度,方能完成救國的使命。耶穌的榜樣,便是典型的革命家,至于怎樣的革命才符合基督教的理想,又因著不同的革命立場而異;是故耶穌既可以支持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也能擁護社會主義革命!吳雷川、吳耀宗、王治心等便是這類的典型代表人物。第四、是作為靈魂拯救者的基督。其實,持守這個立場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反對信仰與國家、社會和文化間,存在任何的關系。他們深信,教會在地上唯一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拯救罪人的靈魂,舍此別無他求。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改革,因為世界最終的命運是接受上帝的審判!換言之,基督是救人”而不是救“國”的。大多數中國的基要派教會領袖便屬此類。總的來說,在中國處于危急存亡之際,中國文化又在劇變之時,中國基督徒為了證明基督教乃救國的唯一法門,乃致力將之診釋具有強烈群體救贖意義的信仰。這樣,耶穌不僅變成“世俗彌賽亞”,失掉其神性的本質,抑且,更成為不同的世俗救國方案的附屬品;耶穌的不同形象,恰好說明中國基督徒是首先確認中國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再尋索根治有關問題的藥方,然后用基督教包裝此等方案。歸根究抵,基督教只扮演合理化或神圣化這些世俗方案的角色,而非如他們原先所言,舍基督教以外無法救國。耶穌基督在二十世紀前期在中國的不同形象,正好反映出中國教會在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時所面對的困局。
四、結論
上文簡單的討論,可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會在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方面,曾經走過的道路。如果我們說歷史的經驗,可以讓后人有所借鑒的話,那么,當今天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仍然是華人信徒的一個目標的時候,我們實在有必要從歷史中吸取一些教訓了!當我們要問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或者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可以扮演的角色時,必須揚棄昔日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元”思想模式,以及整體的思考方向。我們不要在把中國的問題簡單化的同時,又將答案神話化或絕對化!作為基督徒,更應提醒自己,切忌抱著基督教擁有一切根治中國問題的答案的心態,將任何的理念神圣化。事實上,國家、社會、文化的問題是十分復雜的,我們真的可以找到一個根治問題的“靈丹妙藥”嗎?真的存在根本的解決辦法嗎?基督教又是否擁有解決一切國家社會文化問題的答案嗎?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深思后省的。我們明白,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激進化,與當時普遍存在的亡國意識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問題是,今天中國是否仍處于亡國的邊緣?中國無疑仍落后于其他先進國家,這也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人提出中國將被開除“球籍”的原因。但是,我的問題是,這只是因著落后而引發的危機感,與當下生死存亡而掙扎的亡國意識迥異。要是我們能擺脫這種亡國的意識,那么在面對中國的問題時,便不用急于尋找根本的問題及靈丹妙藥了。這樣,我們也不會單單神圣化自己的理想,而無視其他方案的價值及意義。唯有當我們接納基督教并不是“全能”的時候,我們才不會為基督教設定一些超出本身能力與角色的假設;否則,“基先生”只會淪為“基菩薩,’!我深信,在中國文化邁向廿一世紀之際,基督教信仰確實有其可以貢獻的地方,但是,我們得留意,她不一定是唯一的貢獻!告別二十世紀,也要與追求“靈丹妙藥”、“根本解決”的心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