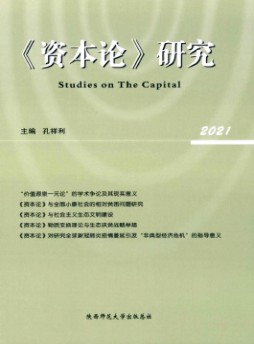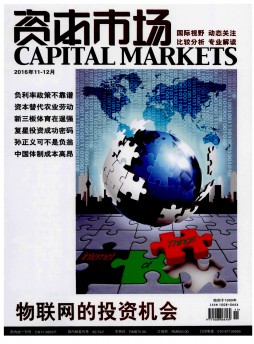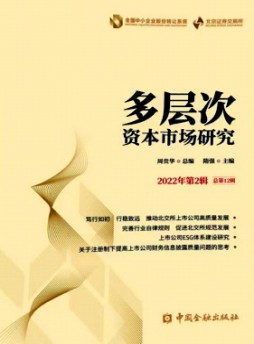資本主義精神生成的倫理動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資本主義精神生成的倫理動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是近代以來諸多思想家普遍關注的問題。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倫理》)一書中,馬克斯•韋伯從研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現代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的歷史必然性。這也就是學界所謂的“韋伯命題”①的由來和內涵所在。從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成意義上說,韋伯命題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一是資本主義是怎樣產生的?二是資本主義為什么會在西方發生?三是怎樣才能發展資本主義?對此,韋伯遵循歷史的、邏輯的方法,通過對路德教派天職觀和加爾文宗預定論的考察,對資本主義精神生成的倫理動因作出了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展示了新教倫理所特有的經濟社會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資本主義精神何以源起于西方
考察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是《新教倫理》一書的主旨所在。韋伯在開篇引言中通過對中西方文明的對比,盛贊了西方在科學、政治體制和文化方面所達到的較高發展程度。他毫不諱言西方文明所具有的優越性,并明確指出世界文化史的核心問題就是“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和與之相伴的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形式是如何起源的”問題,即“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原初形式來看,這種對于利益的追求與西方資本主義本沒有直接關系,但卻客觀上促使西方最終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通過中西方之間這種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的對比,韋伯順勢提出了問題:在這種獲利欲望的驅動之下,為何中國和印度不能同樣走上這種西方獨有的理性化道路呢?很顯然,各種物質技術、規章制度等都對資本主義的現代形態的出現和發展產生了影響,但從根本上說,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在“西方文化獨特的理性主義”,并把這種“理性主義”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獨有的特征。韋伯認為這種獨特性就體現在: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資本主義對于利益的追求是“有理性的”,正因為這種對理性化的訴求,使得現代資本主義與以往時期相比具有不同的特點。這一特點的最突出之處就在于理性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生活的全面掌控。在韋伯看來,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就意味著根據這種新的“經濟理性主義”組織的經濟活動。不僅如此,現代資本主義生活的各個部分以及文化的所有領域都不同程度地體現著這種理性化,理性主義已滲透進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理性主義驅使之下,把賺錢盈利視為人生的終極目的,同時節制各種非理性的欲望享樂,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最具實質性的內涵所在。韋伯注意到了廣泛存在于西歐商界和企業界的新教教徒現象,證實了社會分層與宗教倫理信仰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他通過考察發現,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類型和在現代工業里的不同身份是由生活和居住環境中的宗教因素潛移默化所造成的。此外,根據宗教少數派群體在社會不同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認為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因素而言,宗教信仰的內在精神特質比外在的歷史政治環境更為重要,這就強化了宗教因素對于一定群體的行為的影響作用。對于新教教徒身上所具有的這種“全力以赴的精神、積極進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稱呼的精神”,韋伯認為,“這些精神的覺醒都傾向歸功于新教教義”。韋伯所言的“這些精神”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精神。但是,在資本主義生成的過程中,追求財富的內在動力并沒有與獲有財富而盡情享受現世生活相結合,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韋伯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新教的理性倫理觀念密切相關,尤其是與加爾文宗的倫理道德觀念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新教倫理的“天職”觀和預定救贖論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親和性。在以后的篇章中,韋伯對這些新教倫理觀念作了歷史的邏輯的的考察,以求說明資本主義精神與這種獨特的理性倫理之間的關系。
二、路德“天職”觀:時代價值與局限
(一)“天職”概念的緣起我們現在所廣泛稱為的“新教”,常被用來指稱16世紀以來興起的“那些不接受教皇權威的西方基督教形式”,宗教改革時期產生的新教派是它的主要組成部分。韋伯認為,早在宗教改革運動興起之前,天職(Beruf)一詞的觀念就已存在,只不過當時被譯為“職業、職務”的形式。在這里,“天”無疑指代神圣的上帝,作為一種宗教觀念,這是指上帝交付給人類的任務,體現為對“上帝的召喚”的積極響應。后來路德在翻譯《圣經》時根據需要注入了自己的主觀意志,明確把“天職”的概念提出來,將上帝的神圣意旨與普通人的世俗職責相結合,形成了其獨特的天職觀,并用以宣揚自己的宗教改革理念。在這一重新解構的過程中,路德成功實現了“天職”觀念的兩個轉向:一是受職主體的大眾化,把中世紀只有羅馬教會神職人員所擁有的天職轉變擴大為普通大眾所共有;二是職責內容的世俗化,使“天職”逐漸剝離虛幻的神性色彩,實現與看得見、摸得著的世俗生活相聯系。這兩種轉向實現了概念上的革命性轉變,賦予“天職”以積極的現實意義,使之廣為教徒和普通民眾所接受。正如韋伯所指出的,“上帝唯一能夠認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過隱修禁欲主義來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個人在現世中所處位置所賦予他的義務。這是他的天職。”“天職”觀正是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中考察的源頭,并進而考察了世俗活動中的新教理性行為。
(二)勞動是“天職”觀的核心內容從歷史上看,古希臘羅馬文化對體力勞動是持一種輕視的態度。而實際上從古代猶太教的“舊約”時代起,基督教就已開始了其世俗化的歷程,早期的基督徒們對待勞動的觀點與此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勞動和工作為尊貴且討上帝喜悅”的,不僅肯定了勞動的價值,并且認為勞動是一種有尊嚴和高貴的行為。到宗教改革運動以后,基督教的世俗化過程真正具有了革命化的特征。在韋伯看來,作為宗教改革的成果,路德的最大貢獻即是確定了勞動在“天職”中的核心地位,肯定了世人“履行世俗事務的責任”,“相比于天主教的態度,宗教改革的影響只是使那些為了履行天職而進行的有組織的世俗勞動得到越來越多的道德重視和宗教認可。”與天主教傳統觀念告誡人們“安分守己”、超越世俗生活相對照,路德的宗教改革則為世俗活動進行了道德上的辯護,使世俗勞動獲得了宗教意義上的合法性。神圣職責世俗化、世俗勞動神圣化,神性與世俗在履行天職的勞動這里找到了相互之間的完美契合點。韋伯還通過對早期資本主義工廠中不同技術工人所從事工作的分析,闡述了他對于勞動的具體看法。他認為,“在技術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現出了非常強烈的留守本行業的傾向,更多的時候他們會成為本行業的師傅,然而新教教徒則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廠里成為高級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這表明,由于受到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影響,不同群體和個人所選擇從事的職業也會有不同。與所信仰宗教的教義結合起來看,這種不同職業的選擇無疑體現著上帝的意志,都是“上帝安排的任務”,要求認真去履行這一職責。路德“把工作視為不僅討上帝喜悅更是一種侍奉上帝的呼召(天職)”,這種工作概念的革命性轉變在于使工作的意義從“什么”、“怎樣”轉向“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把工作本身視為人生的目的,而路德更突出強調工作的目的指向和意義指向,認為工作是人本身的一種職責,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榮耀上帝和為他人服務的差事。很顯然,在路德看來,人所從事的是何種具體職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事該職業應盡職盡責的意義。既然所有工作都是作為榮耀上帝的行為而存在,那么工作就沒有好壞和優劣之分,“所有正當類型的工作都是圣潔的”。[5]此外,韋伯還通過結合富蘭克林對于金錢的道德勸誡,深刻形象地闡明了遵守天職、合法賺錢的必要性。在富蘭克林看來,時間、信譽和金錢本身都是我們進一步賺錢盈利的資本,“除去勤勞節儉,對一個年輕人安身立命最有益處的就是保證他的所有行為都是守時和正義的”。當然,在韋伯看來,富蘭克林的所言所行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獨特的倫理”,是“人們履行天職的責任”在現實行為中的具體體現。韋伯指出,“在現代的經濟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賺錢,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種遵守天職美德的結果和發揮天職能力的表現”,“人們完全被賺錢和獲利所掌控,并將其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勤奮勞動、努力賺錢,這正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首要原則的現實體現。
(三)路德“天職”觀的保守局限性韋伯認為,盡管天職的觀念最早被路德引進,但這并不表明路德具有前述富蘭克林所擁有的那種同樣激進的“精神氣質”。③因為就當時的宗教改革者(包括之后的加爾文宗等清教派別)來說,只有靈魂的救贖才是他們生命和工作的中心,各項倫理改革計劃也只是從屬于并為這一中心任務服務的。具體到當時路德所持有的觀點,他認為“個人應該一直安分地保持上帝安排給他的身份和天職,并且應該根據已經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動”,他“認為絕對服從神的意志與絕對接受現狀是一致的”。透過這些簡要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路德在強調天職的必要性的同時,刻意夸大了天職觀中“神的旨意”的重要作用,教導要安于現狀、被動適應,顯示了其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也表明路德本人并“不具備資本主義精神”。路德的天職觀始終是傳統主義的,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按照韋伯的分析,這與路德畢生所從事的牧師職業、賴以解讀的文本帶有傳統主義性質等多種因素有關。很顯然,僅僅依靠路德的天職觀并無法全部回答資本主義精神所應具有的全部意義。在韋伯看來,作為一種更具現實價值理念的天職觀,是在加爾文宗等禁欲主義各教派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
三、加爾文宗:預定論與入世禁欲主義的現實演進
法國宗教改革家加爾文生活在比路德稍晚的一個時期,作為一名思想上更趨激進的宗教改革者,他繼承并發展了路德的天職觀新教理念。與前任改革者相比,加爾文的創新之處在于以他已有的神學思想為基礎,同時融合進了路德的天職觀,并將“天職”與預定論有機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信徒確證自我上帝選民身分的重要依據之一。正如韋伯所指出,“盡管沒有路德個人宗教思想的發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這一改革在精神層面上長期受到路德個人品格的影響,但是如果沒有加爾文主義,路德的工作就不可能擁有持久而具體的成功。”正是由于加爾文的與時俱進,這一時期的宗教改革出現一種創新發展的局面。
(一)作為教理前提的“預定論”韋伯首先從分析加爾文宗等禁欲主義派別的“預定論”入手來逐步說明問題。根據基督教的“原罪”說,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在天主教的傳統主義觀念中,人是可以通過購買贖罪券來獲得上帝諒解的。隨著贖罪券的推行濫用,也孳生了教會的種種腐敗行為,這是引致路德宗教改革運動發起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何才能夠獲恩得救呢?“預定論”被視為加爾文宗“最為典型的教理”,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按照韋伯的分析,“預定論”實際上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內容所構成:一是人在現世的得救與否由上帝“預定”,上帝的“選民”注定得救,“棄民”則注定為上帝所擯棄;二是上帝的預旨神秘不可知,“一切事物,包括我們每個人命運的意義在內,都隱匿于冥冥的奧秘之中,而這是不可能被參透的,也是不容置疑的”;三是“上帝的預旨不可更改”,“上帝已經給予恩典的人就永遠不會失去這一恩典,而上帝拒絕給予恩典的人也永遠不可能獲得恩典”,除此之外,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不難看出,“預定論”帶有強烈的宿命論和不可知論色彩。可以說,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上帝的“預定”主宰著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切,而這一“永享恩典、永墮地獄”特征鮮明的教義又極度脫離人性,“選民”或“棄民”身份的不同成為其一生人際遭遇的根本區別。因此,這也成為教徒們最為關心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為上帝所選中呢?“我是上帝的一個選民嗎?”這個振聾發聵的問題又因關于上帝的不可知論和揣摩“上意”屬“不道德行為”而似乎陷入絕境。這也為天職觀在實踐中的進一步發展和入世禁欲主義的提出奠定了教理上的前提。
(二)入世禁欲主義提出的實踐必然作為對于“上帝的選民”問題的解答,加爾文提出了“救贖確認”的兩種途徑:其一是對上帝的堅定信仰,自信蒙受上帝恩典;其二就是“緊張的世俗活動”。與前一種救贖途徑的不確定性相比,后者在現實中“世俗活動可以驅散關于宗教的疑懼,并給予人們蒙恩的確定性”,因易于量化把握而被視為確證救贖的最合適的方法,即以實踐中的實際行為驗證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選民”。在這里,加爾文把天職觀與預定論有機結合起來。他指出,上帝選民的唯一證據就是現實中的每個人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天職,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而天職完成的好與差取決于世人獲得財富的多與寡,“一項天職是否有益并且就此博得上帝的青睞,主要是依靠道德標準進行衡量,進而就是根據這一天職為‘共同體’所提供財富的重要性來衡量。然而另外一個更為深層的、在現實中也最為重要的評判標準,是私人的可營利性”。與路德相信工作的重要性在于為他人服務因而給上帝帶來榮耀的觀念不同,加爾文宗與那些逃離俗世而歸隱于修道院的隱修士一樣,他們亦否定自身快樂,但認為擁有的財富越多即是受到上帝祝福和挑選的證明,因而把勤奮工作和生活節儉視為獲得這一證明的必備途徑。選民恪盡職守做好自己的天職,通過勤奮勞動集聚大量的財富,這是取悅上帝,“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的行為,理應獲得救贖。如此看來,要分析說明加爾文的預定論在何種程度上發展了路德的天職觀,那么我們似乎可以認為,路德的天職觀賦予了世俗職業以神圣意義,加爾文宗的預定論則賦予了職業勞動者以神圣意義。但是,我們這里要明曉的是,在對于財富問題的態度上,早期基督教派與加爾文宗的實質差異并不在于追求財富本身,而在于擁有財富所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方面。早期基督教徒“他們真實的道德異議在于,擁有財富會使人懈怠,享受財富會使人懶散并沉溺于肉體的享樂,最為重要的是它會使人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時精神渙散”。擁有財富“有使人懈怠的危險”,有損于上帝的榮耀,憂心的是一種潛在出現的不良后果,這是前者對財富抱敵視態度的根本原因所在。有鑒于此,在韋伯看來,與“恪盡職守”的天職觀相結合,加爾文宗最重要的是在實踐中提出了入世禁欲主義的倫理理念,“這種倫理的‘至善’就是賺取更多的錢與嚴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樂的結合”,獲取財富并不是為來用于生活享樂,相反是要身體力行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獲取財富僅僅是為增添上帝榮耀、確證自己“選民”身份的途徑和手段。“上帝召喚的并非是勞動本身,而是在履行天職時的理性勞動”,“清教天職觀的重點始終在于這種入世禁欲主義的條理性”。入世禁欲主義的“理性”就是通過正當的理性活動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財富的追求,與把錢財用于非理性欲望的節制相結合,這樣一種勤儉禁欲的倫理,就是韋伯所稱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征。這正如韋伯所指出的那樣,“基于天職觀念的理性行為,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現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這種理性行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精神”。入世禁欲主義的實踐發揮最終催生了具有理性特征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論證了他在開篇提出的那個假設,對此問題作出了有價值的解答。
四、結語
韋伯以歷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的方法,通過“天職觀—預定論—入世禁欲主義”這一邏輯進路,證實了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之間所具有的內在親和性,顯示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生成方面的巨大價值。新教倫理從本質上說是作為一種宗教思想而存在。韋伯認為正是這種新教思想生成并發展出具有理性特征的資本主義精神,并產生了相應的物質經濟形態。這似乎夸大了思想意識的能動作用。然而,這一論斷為我們科學認識倫理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和方法。
作者:趙亮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
擴展閱讀
- 1虛擬資本現實資本
- 2資本主義貨幣資本對自然資本的影響
- 3混合資本工具資本管理
- 4工商資本金融資本
- 5資本成本
- 6民間資本大
- 7城鄉資本流動探析
- 8國際資本流動比較
- 9邊際資本成本
- 10智力資本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