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卡寧后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藝術(shù)特色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馬卡寧后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藝術(shù)特色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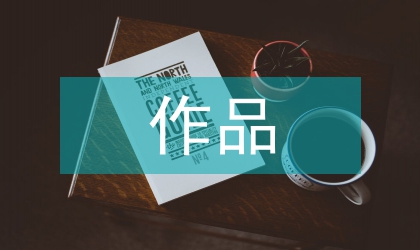
1、馬卡寧的語言藝術(shù)
傳統(tǒng)的語言觀認為,語言是表達思想、交流感情的載體,在文本中處于從屬地位。所以,秉承這一觀點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都將語言視為可靠的工具,用它來描述自己眼里的“真”。但隨著認識的發(fā)展,尤其到了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很多人驀然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一直是符號動物,在先前的文學里人是被作者設(shè)計好了的、本性已經(jīng)被完全遮蔽住了的理性人。正是在這種認識的指引下,在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那里,語言的表現(xiàn)生活、塑造形象的“工具論”這一傳統(tǒng)觀點遭到了徹底顛覆,語言與主體(使用語言的人)的角色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錯位。“語言不再是主體的功能,主體成了語言的功能。”正是在這種認識的激發(fā)下,后現(xiàn)代主義作家打破常規(guī)的語言法則,通過戲仿、拼貼、游戲,對傳統(tǒng)話語進行顛覆、解構(gòu)。
而與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既不贊同文學應該像很多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作家那樣建立一種語言主導模式,又不像后現(xiàn)代主義那樣決絕地破除“高雅”與“通俗”、“精英”與“大眾”的二元對立結(jié)構(gòu),建立以大眾化、通俗化為主流的一元化結(jié)構(gòu)。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主張建立語言的多邊性對話。
馬卡寧在其后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中,在關(guān)注作品思想內(nèi)容,依靠心靈的敏感來把握精神礦藏的位置和方向的同時,也在不斷摸索、斟酌與他的思想認識和文學理念最為契合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馬卡寧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語言藝術(shù)的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其語言的“民主化”傾向。馬卡寧站在時代交替的邊界上,為文化中的轉(zhuǎn)換狀態(tài)所吸引。他剔除了大眾對語言的慣常賦意,使詞語、句式、乃至標點符號等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與話語權(quán)。
2、整體隱喻
隱喻是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建構(gòu)藝術(shù)圖景重要的藝術(shù)手段。在后現(xiàn)實主義作家看來,隱喻是實現(xiàn)“曲徑通幽”的最佳方式之一。因為隱喻本質(zhì)的特征就是能夠在本體與喻體之間架設(shè)起聯(lián)系的橋梁,能夠在分別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的事物、事件之間建立起某種“共容性”,而這恰恰符合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即在混亂、模糊、間斷狀態(tài)中進行“多邊性對話”,尋找實現(xiàn)“和諧性”的努力。馬卡寧在其后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中也非常重視隱喻的運用。一方面,馬卡寧的這些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文學的共性,即,重視局部隱喻的應用,善于運用背景、姓名等具體細節(jié)進行喻涉,從而達到豐富人物內(nèi)心世界,渲染故事情節(jié)的效果。另一方面,我們發(fā)現(xiàn),馬卡寧后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中的隱喻具有一種整體性,具備了一種新的藝術(shù)構(gòu)形能力。隱喻不再被作為附加的潤飾物,而是被看做一種思想。隱喻在這里已經(jīng)成為文本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隱喻表達已然成為行文結(jié)構(gòu)與主題創(chuàng)建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空間隱喻為例。馬卡寧往往通過一個外在景觀或場景空間建立起一個有關(guān)社會、群體、個體的精神狀態(tài)乃至存在等諸多生存層面的抽象“空間”的隱喻,從而將整個文本納入隱喻當中。
小說《地下人,或者當代英雄》中的“筒子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地下人,或者當代英雄》中,“筒子樓”這個空間背景的選擇對于整部作品都頗為重要。雖然它不是一切故事發(fā)生的唯一地點,但所有的故事無不與它直接或者間接交叉,它不僅幫助作品建立了一個空間坐標軸線,成為故事的匯集地,而且還具有很強的整體性隱喻品質(zhì)。在《出入孔》這篇小說中,作者利用“出入孔”的空間屬性為我們建立了一個有關(guān)生存狀態(tài)與生存意義的隱喻復合體,從而將作者建構(gòu)文本的診斷疾病,開出藥方的意圖完全納入了通過“出入孔”所建構(gòu)的隱喻體系當中。
3、放射狀非線性敘事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單向、一維的物理時間觀念在東、西方世界的時間認識中曾長期占有絕對統(tǒng)治地位。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多以講故事為中心,講究按照現(xiàn)實時間的順序安排情節(jié)的展與事件的發(fā)展。為了保持情節(jié)線索的連貫性與完整性,體現(xiàn)出一種因果性邏輯,這類小說一方面盡量要求在敘述中把敘述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故事時間一一交代清楚,力保敘事時間的連貫性,另一方面,小說敘事的起、承、轉(zhuǎn)、合也多與事件發(fā)展的不同時刻相對應,敘事時間的進程盡量與事件的自然時間進程保持一致。其間,盡管作家可能意識到敘事時間的線性延續(xù)會導致讀者對敘事的程式化、單調(diào)化的厭煩,因此會采取插敘、倒敘、補敘等各種手段來豐富敘事,但這只是表象而已,因為這些時間的變形通常只是在局部展開,并且相對于整個篇幅而言,占據(jù)很少的比例,所以它們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整個小說故事敘述的邏輯性、完整性走向。
與以張揚非理性為目的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以及以顛覆為旨歸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非線性敘事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在奉行開放性藝術(shù)哲學、試圖在縱向以及橫向之間建立一種和諧模式的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非線性敘事模式呈現(xiàn)出一種放射性特征,并藉此使作品達到了深遠的透視效果。雖然在《審訊桌》里,在敘事上存在非線性安排,但它并沒有通過“小敘事”來消解“大敘事”,從而造成“大敘事”價值的下跌。作者通過從題名開始就建構(gòu)的放射模式最終使文本成功地達到了片段性、碎片化與條理性、連貫性的有機結(jié)合,無形中踐行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非理性與決定論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策略。
作者:郭天宇 單位: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國立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