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戲劇藝術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高行健戲劇藝術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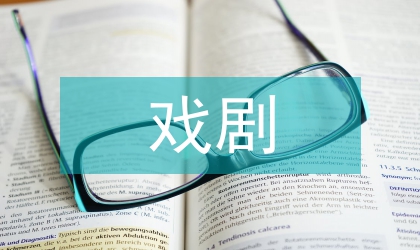
一、共同的現代主義戲劇手段
1.荒誕作為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作,《等待戈多》用獨特的荒誕手法展示了人類生存的荒誕,具體表現為:荒誕乏味的情節,空洞無聊的語言,以及直喻的表達方式。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高行健仔細研究了這一手法,并且在《車站》中作了首次嘗試。盡管他只使用了上述第三點荒誕手法,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產生的反響是地震式的。《等待戈多》沒有完整的情節,也沒有矛盾或沖突,兩幕都發生在黃昏鄉村的路邊。兩個流浪漢在等待戈多,卻不知道戈多是誰;波卓和幸運兒第一天路過此地時都是好好的,第二天路過時卻都已莫名其妙地殘疾了;結尾處兩個流浪漢決定繼續等待。這出戲中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埃斯林指出其“沒有動作的戲劇”的本質:“把根本上沒有動作的動作拆散成幾個動作的片斷,這些片斷互相消解,每一個短暫的片斷取消前一片斷中的積極行動,因而總是回到什么也沒有發生的狀態”⑩。這與古希臘理論家亞理士多德提出的“戲劇的本性是動作”的理論相悖,以反傳統的形式揭示了生命的無意義。戲劇語言通常是最重要的戲劇手段,但是在《等待戈多》中,語言失去了交際的功能。劇中人物總是頭腦不清,他們說話不過是為了消磨時間或取樂,也無需同伴的答復,所以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交流。高行健曾經作此評價:“《等待戈多》中的人物的臺詞,大都寫得十分平淡,近乎現實生活中不求連貫的語言的碎片,然而全劇貫穿起來看,卻荒誕至極,細細一想,竟又十分深刻”輯訛輥。這出戲里有很多手段———包括模棱兩可、文字游戲以及手勢的使用———剝奪了語言的強制力輰訛輥。幸運兒的一大段獨白則是其破碎語言的典型———現代社會使人們痛苦不堪,甚至喪失了理性地富有邏輯地表達內心苦悶的能力。劇中也很少有連貫的對話,常常是重復自己或別人的語言。例如:愛斯特拉岡:……我們走吧。這樣的對話在劇中重復出現,使語言的交際功能失去作用,因為重復使語言變得模棱兩可,遮蔽了人物的思想,增加了人物的荒誕感。直喻,即直接的表達模式,也就是直接通過人物的外部形象來表達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無論是《等待戈多》還是《車站》都使用了這種方法,具體表現在人物的動作設計和時間處理上。首先看動作。正如埃斯林所說,“荒誕派戲劇放棄了對人類荒誕處境的討論;它僅僅是展示———也就是說,以具體的舞臺形象來表現存在的荒誕”輲訛輥。《等待戈多》中的兩個流浪漢總是在脫靴子、穿靴子和摘帽子、戴帽子,而幸運兒則被波卓用繩子牽著走來走去。帽子、靴子和繩子都直喻荒誕的生活,人們深受其折磨而又無法擺脫。《車站》中的人物同樣被捉摸不定的命運擺布,找不到合理的方法預知未來。“戴眼鏡的”認為命運就好比一塊硬幣,只能靠拋硬幣來決定等待還是離開。這表明他們不僅失去了理性地解決生活中的困難的信心,而且屈從于命運和荒誕生活的擺布。《等待戈多》和《車站》都探討了存在主義的主題,但是在動作設計方面前者明顯地完全運用了直喻的手法,而后者只是部分地運用了這一手法。其次,兩劇中的直喻還表現在不可思議的時間飛逝加劇了等待的焦慮感。時間是劇中最有意義的因素之一,它把等待的行為與生命的價值以及等待中如何打發時間聯系在一起。兩劇在時間方面有共同點。第一,時間荒唐地飛速流逝。《等待戈多》中第二幕發生在第二天的同一時間,然而“,樹上長出了四五片樹葉”輳訛輥,波卓瞎了,幸運兒成了啞巴,這些顯然都不是一夜之間能發生的事情。《車站》中也是如此,七個乘客等車進城,這一等居然就是十年,手表的指針飛速地運轉,人們突然意識到他們老了,由此產生了焦慮。不同的是,《等待戈多》中時間悄悄地流逝,兩個流浪漢幾乎沒有發覺,只是感到乏味,因為等待好像是漫無止境的,而在《車站》中人們突然覺察到時間的飛逝。第二,在時間的飛速流逝中等待的人們身上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事情,這使時間失效,而等待變得無意義。兩劇中時間流逝給外面的世界帶來了變化,卻遺忘了等待的人。愛斯特拉岡抱怨“:他們都在變。只有我們變不了”輴訛輥。戴眼鏡的說“:我們被生活甩了,世界把我們都忘了,生命就從你面前白白流走了……”輵訛輥。正如貝克特在《尋找自我》中所說:“等待就是經歷時間的運動,是不停地變化的。然而,當什么都不發生時,變化本身就成為幻想。時間不停的運動就是事與愿違、毫無目的的,因而是無效的”輶輥訛。第三,兩劇中的人物都缺乏清晰的時間觀念,他們等待的時間越長,就越感覺不到時間的變化,同時對時間的流逝越感到迷惑。波卓認為死亡和出生是同一天同一秒的事,愛斯特拉岡甚至不能確定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還是星期五。《車站》中的乘客們等得太久以至于他們想不起來到底是從哪一天開始等待的。時間是秩序的象征,人們通過它了解世界,尋找夢想。時間記錄著生命和價值,使人們確切地感受到它們的存在。一旦被剝奪了時間感,人們將不僅僅陷入存在的混亂,而且會感覺不到存在。也就是說,喪失了時間感即喪失了存在的意義,這加劇了人類處境的荒誕。
2.藝術的抽象高行健對藝術的抽象及其在《等待戈多》中的運用作了深入的探討:“戈多是貝克特對現代社會的一種認識,或者說是他的世界觀的一種藝術的概括……我們這里僅僅就藝術創作方法而言,不能不認為這種手法的運用是出色的。貝克特塑造戈多這個形象用的這種方法,我們不妨稱之為藝術的抽象”輷訛輥。有了對戈多和貝克特的認識和欣賞,才有了對其手法的借鑒和運用。如果戈多是對現代社會的認識,那么兩個流浪漢就是荒誕境遇中的普遍人類的代表,他們過著無意義的生活,渴望變化卻注定得不到。我們無論是考察該劇的時間、地點還是場景,都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共同點———普遍性。時間是“傍晚”“,第二天,同樣的時間”;地點是“鄉村的小路”;場景非常簡單,“一棵樹”。而《車站》中的時間是很具體的,禮拜六下午,特殊的時間決定了人物等車進城的行為;地點和場景本身也是具體的,盡管象征手法同時賦予它們普遍的意義。《等待戈多》中的情節、人物以及人物關系都未被貼上時代、社會和民族的標簽;而《車站》中直截了當的對話內容,諸如恢復高考、走后門、十年的等待都給劇本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在《車站》中,沉默的人是藝術的抽象的中心,代表著積極的生活態度和不斷進取的精神。在他離開車站步行進城后,“沉默的人的音樂”不時響起,時而是“探索的節奏”,時而是“歡快的調子”,最后成了“宏大然而詼諧的進行曲”輮輦訛,這不僅凸顯了人物形象,而且實現了作者的創作意向,即在《有關演出的幾點建議》中指出的,“如果有條件作曲的話,沉默的人的音樂形象最好從同一個動機出發,進行各種變奏”輯訛輦。在這里他還明確提出該劇追求藝術的抽象,也就是神似。所有這些都表明了這樣的事實:沉默的人是藝術的抽象,是“一個概念、一種精神、一種情緒、一個名稱……”。總之,《等待戈多》從人物到情節、場景都充分運用了藝術的抽象;相比較而言,高行健的《車站》由于其現實主義的主題和人物形象,只是部分地應用了這一手法,集中表現在沉默的人和他的音樂上,以使得該劇的主題更加易于為觀眾所把握。
二、《車站》中的創新手法
高行健對中國現代戲劇做出了很多貢獻,不僅僅在于他是一個劇作家,還在于他在劇場實踐方面的廣博知識和豐富經驗。我們認為西方現代戲劇的確對高行健有很大影響,但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尤其是戲曲對他的影響也不亞于前者。他的假定性、劇場性和敘事性的觀念構筑了一種新的戲劇,他稱之為“完全的戲劇”輱訛輦。與中國傳統戲劇觀念不同的是,高行健認為“戲劇不是文學”,因為戲劇不同于戲劇文學,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戲劇是一種表演藝術”輲訛輦,最終是演員舞臺上的表演使戲劇成為一門鮮活的藝術,實現了與觀眾的溝通。對戲劇本質的認識為他對戲劇特點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例如,劇場性在于演員和觀眾之間的交流———觀眾陶醉于演員的生動表演,而演員也從觀眾的呼應中增強對自己演技的自信,從而形成了臺上臺下交融的劇場氣氛。對劇場性的探索實踐有“小劇場運動”的興起,開始于林兆華執導的一部高行健的作品《絕對信號》,接著就是《車站》。作為探索劇的“產品”之一,這一運動著力于打破傳統戲劇的四堵墻的模式。《車站》演出時,在很小的空間里,觀眾圍著舞臺四周,席地而坐。這樣一來,傳統劇場里存在于演員和觀眾之間的障礙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和諧的氣氛,有利于解放觀眾的想象力,加強演員和觀眾之間的交流。高行健還探討了“完全的戲劇”的核心內容:假定性。他認為,假定性是中國傳統戲曲的基本特點,而相對而言,西方戲劇在藝術上更追求真實感。高行健指出,“演員恰恰是把假定的環境當作真的來做戲,這便是我們稱之為舞臺藝術的假定性……現代戲劇卻越加強調自己這門藝術的假定性,而且毫不掩飾,居然聲稱戲劇藝術的全部魅力正在于假戲真做”。因此假定性揭示了演員、角色和觀眾之間的真實關系:演員只是角色的扮演者而并不是劇中的真正角色,然而觀眾認可這種假定關系。假定性有利于調動觀眾的想象力,是敘事性的多樣化的前提。一出戲的成功依賴于演員和觀眾對假定性的確認。布萊希特的間離敘事方式給高行健以啟迪。他在戲劇中借鑒了這樣的方法———敘事角度的轉換,就像說書人的表演一樣。這種方式允許演員暫時從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分離出來,像旁觀者一樣對角色或劇情發表評論或批評。在《車站》的結尾處他就用了這樣的手法。七個演員“各自凝視前方,有走向觀眾的,也有仍在舞臺上的,都從各自的角色中化出。
光線也隨之變化,明暗程度不同地照著這些演員,舞臺上的基本光消失”,演員以自身而不是其飾演的角色的身份對觀眾說話,表示毫無目的和希望的等待是毫無意義的。演員和觀眾之間的交流既是以假定性和劇場性為前提,也同時可以說是其結果,因此強化了交流的效果。敘事語言是敘事性的主要部分,盡管高行健認為戲劇是表演藝術而不是語言藝術,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忽視語言的功能。“它在劇場里是一種可以感知的直現,它不僅僅表述人物的思想感情,還可以在演員與演員之間,演員與觀眾之間,實現一種活生生的交流”。高行健從中國傳統戲曲和音樂中得到了啟發。在1984年創作的《喀巴拉山口》中,他借用了江南的一種曲藝形式———評彈,當然作了一些變動以適應他的戲劇理念。“劇場里的語言既然是一種有聲的語言,就完全可以像對待音樂一樣來加以研究……劇場里的有聲語言既可以是多聲部的,也有和聲和對位,形成種種和諧的與不和諧的語言的交響”。在《車站》中,多聲部不時出現,有時兩個聲部,有時三個或六個,最多的時候七個演員同時直接地對觀眾講話。高行健以這種方式引出多聲部:“以下臺詞,七個人同時說。甲、己、庚的話,穿插串連在一起,成為一組,構成完整的句子”。高行健認為演員們同時講話,“便出現一種復調的成份”。這一手段從理論上聽起來很不錯,然而,實際演出的效果恐怕不會令作者滿意。幾個人同時講話聽起來勢必是鬧哄哄的噪音,與音樂的多聲部畢竟大相徑庭,或許是一種不和諧的語言的交響;至于講話的內容,觀眾只能聽清離他最近的演員的臺詞。創作理想與實際效果之間產生了距離。高行健的敘述場景的處理與他的敘事語言的理念密切相關。“作為一種生理和心理現象的語言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約束的”,由此各種時空關系都可以在舞臺上得以展示,而不必拘泥于場景的變換,表演像語言一樣無所不能,獲得了充分的自由。這實際上是沿襲了中國戲曲的傳統。東西方戲劇對布景的處理方法顯然有很大差異:西方戲劇追求真實感,要求更換場景,所以必須分幕;在高行健的戲劇中,假定性和敘事性使得時空自由轉換成為可能,因此多是獨幕劇。《車站》中的音響也展示了語言所具有的特殊效果,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敘事音樂。在《有關演出的幾點建議》中,高行健明確指出,音響,包括音樂,不應該是直接解說性的———音響可作為一個獨立的角色,和劇中人以及觀眾進行對話。在演出過程中,沉默的人不停地在觀眾中行走,他的音樂也不時響起,與等待的人們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同一個劇場中同時構筑了兩種不同的時空關系。這樣的音響對比很自然地引出了積極的主題,豐富了劇作的內涵。應該承認,《車站》的現實主義特點與現代主義手段,尤其是荒誕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戲劇的內在割裂。高行健從戲劇表現手法出發進行創作是造成割裂的主要原因。此外,多聲部的創作實踐與理論的反差、人物形象稍顯單薄是該劇的不足之處。盡管如此,高行健的戲劇探索是有意義的,其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對戲劇觀的明確把握使他能夠對傳統戲曲和外來戲劇大膽借鑒。他充分發揮戲劇的假定性特點,利用多聲部和小劇場縮短演員與觀眾的距離。同時,他還豐富了戲劇的表現手法,使話劇不再是純粹說話的藝術。總之,《車站》是一部立足于中國表演藝術的傳統、吸收荒誕派的戲劇手段、反映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情緒的戲劇。
作者:景曉鶯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