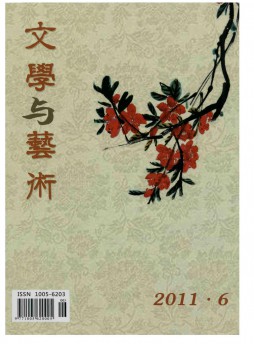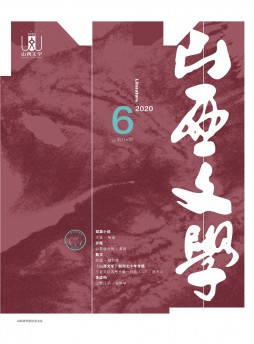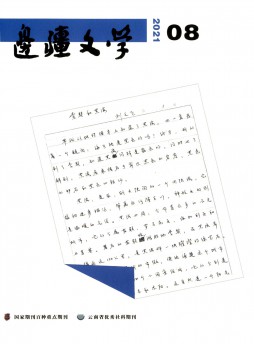文學(xué)焦慮與網(wǎng)絡(luò)媒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焦慮與網(wǎng)絡(luò)媒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世紀(jì)的中國文學(xué),總處在焦慮和浮躁之中。這種焦慮和浮躁先是來自對(duì)文學(xué)的過分關(guān)注:人們賦予了文學(xué)以“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移風(fēng)易俗”、“解放思想”的重大社會(huì)責(zé)任;其后又來自所謂“邊緣化”的痛苦。盡管學(xué)界內(nèi)對(duì)“邊緣化”的表征及其產(chǎn)生的原因眾說紛紜,但有兩個(gè)基本的傾向是大家都承認(rèn)的,一是讀者的喪失,二是文學(xué)功能的退化。這兩個(gè)傾向,可以表述為一個(gè)傳播學(xué)的術(shù)語,那就是“失語”。因?yàn)槭鼙姷膹V度決定著話語權(quán)的量度,而話語權(quán)的量度又是實(shí)際功能執(zhí)行權(quán)利的量度。文學(xué)對(duì)“受眾”的號(hào)召力減弱了,文學(xué)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介入權(quán)利被削減了,于是,它“失語”了。
視聽霸權(quán)的出現(xiàn),又使得文學(xué)的失語現(xiàn)象日益嚴(yán)重。20世紀(jì)正是哈特所謂的機(jī)器媒介時(shí)代,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機(jī)器媒介,挾著大眾消費(fèi)文化的強(qiáng)大浪潮,憑借震撼性的視聽感官?zèng)_擊力,迅速剝奪著文學(xué)的話語權(quán)。可以說,在中國,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以后,視聽媒介、快餐文化、后現(xiàn)代解構(gòu)思潮與文學(xué)的失語是同步進(jìn)行的。這種同步似乎正好印證了傳播學(xué)上的媒介決定論:媒介的轉(zhuǎn)換極大地改變著文學(xué)的生存范式。
在這個(gè)時(shí)候,也許有人會(huì)問,如果說機(jī)器媒介真的加深了文學(xué)的焦慮和危機(jī),那么,在世紀(jì)之交進(jìn)入中國的網(wǎng)絡(luò)媒介又會(huì)對(duì)文學(xué)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新世紀(jì)的文學(xué)焦慮會(huì)因此而愈演愈烈,還是會(huì)因此而得到紓解?要回答這個(gè)問題,首先就要弄清產(chǎn)生文學(xué)焦慮的內(nèi)在根源究竟是什么,然后再分析媒介力量是通過怎樣的路徑對(duì)文學(xué)焦慮發(fā)生作用的。最后,我們才能在學(xué)理上辨析網(wǎng)絡(luò)媒介能否消解或紓緩產(chǎn)生文學(xué)焦慮的原因。
一、文學(xué)焦慮產(chǎn)生的根源是文學(xué)身份與文學(xué)角色期待的沖突
心理學(xué)認(rèn)為,焦慮來源于“角色緊張”。也就是說,當(dāng)一個(gè)人感覺到自己不能成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感到自己的扮演與社會(huì)對(duì)其角色的期待有較大距離時(shí),就會(huì)導(dǎo)致精神的焦慮。這提示我們引入文學(xué)身份和文學(xué)角色這兩個(gè)概念,來分析文學(xué)焦慮產(chǎn)生的解構(gòu)性因素:
1、所謂文學(xué)身份,是指文學(xué)在整個(gè)人類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所處的位置。一定的文學(xué)身份代表著它在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被賦予的地位,并由此代表著它應(yīng)當(dāng)履行的社會(huì)文化職能。
2、所謂文學(xué)角色,是指人們對(duì)文學(xué)在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應(yīng)當(dāng)履行的職能和行為的期待。
按照上述的定義,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gè)基本的理論假定:文學(xué)身份和其角色期待的吻合程度與其焦慮程度成反比。事實(shí)上,文學(xué)的身份是通過其職能履行來體現(xiàn)的,而正如我們上面所說,職能履行的量度等同于話語權(quán)的大小,那么,上述的假定也可以表述為:文學(xué)話語權(quán)的大小和其角色期待的吻合程度與其焦慮程度成反比。我們可以通過對(duì)文學(xué)史的簡單回顧,來驗(yàn)證一下這個(gè)假設(shè)。
文學(xué)話語權(quán)的大小,是通過兩個(gè)維度來測量的。第一個(gè)維度是文學(xué)話語的接受廣度,也就是說,一個(gè)時(shí)期的文學(xué)擁有越多的讀者和關(guān)注者,它的話語權(quán)就越大,反之亦然。第二個(gè)維度是文學(xué)話語左右其他領(lǐng)域話語的強(qiáng)度,也就是說,一個(gè)時(shí)期文學(xué)話語對(duì)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其他領(lǐng)域的影響越大,它的話語權(quán)就越大。反之亦然。下面,我們就通過這兩個(gè)維度,來考察一下歷史上文學(xué)的話語權(quán)與其角色期待之間的關(guān)系。
在口頭傳唱時(shí)代,文學(xué)話語的接受幾乎是“全民”。由于沒有文字,文化的傳承主要依賴便于記憶的韻文傳唱來進(jìn)行,這是人人都能聽懂的語言,不會(huì)將某些接受群體排除在外。同時(shí),這個(gè)時(shí)代文學(xué)實(shí)際上不是獨(dú)立的,它是所有文化產(chǎn)品的承載者,它的話語也就幾乎等同于全部的文化話語,而實(shí)際上,當(dāng)時(shí)人們也是這么看待文學(xué)的,也期望著文學(xué)能夠很好地履行文化傳承的功能,因?yàn)閯e無選擇。很顯然,這個(gè)時(shí)期的文學(xué)話語權(quán)最大,人們對(duì)它的期望值也最大,這個(gè)時(shí)期的文學(xué)沒有焦慮。
在書面文學(xué)出現(xiàn)后,文學(xué)依然擁有話語強(qiáng)權(quán),它被寄予“觀風(fēng)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角色期待。盡管在這個(gè)時(shí)代,文學(xué)已不再呈現(xiàn)為全民傳唱的統(tǒng)一圖式,精英文學(xué)的話語傳播范圍也相對(duì)縮小;但是,精英卻通過自身地位壟斷了主流文學(xué)(書面文學(xué))的話語權(quán)。文學(xué)身份與其角色期待之間仍然相對(duì)吻合,文學(xué)的焦慮和失落感并不明顯。
但是,也不能說這個(gè)時(shí)代完全沒有焦慮。從兩漢時(shí)期“類比俳優(yōu)”的傷懷,到初唐“文章道弊五百年”的感嘆,再到宋人“作文害道”的懷疑,直到清代對(duì)文學(xué)“真種子”失落的迷茫,文學(xué)焦慮的胚胎已然隱隱孕育。是什么力量孕育了這種胚胎呢?通過與口頭傳唱時(shí)代對(duì)比,我們自然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個(gè)焦慮孕育的時(shí)代,正是文學(xué)傳播媒介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時(shí)代。那么,是媒介的變革埋下了文學(xué)焦慮的隱憂嗎?媒介又是通過怎樣的路徑對(duì)文學(xué)施加作用的?
二、文學(xué)傳播媒介的變革使文學(xué)身份產(chǎn)生裂變
首先,再現(xiàn)媒介的出現(xiàn),使文學(xué)話語分裂成為兩套系統(tǒng):一是仍然流布民間的口語系統(tǒng),另一則是文化精英壟斷的書面語系統(tǒng)。修辭學(xué)的誕生使書面語日益精美,從而成為不識(shí)字的人群難以理解的話語系統(tǒng)。在再現(xiàn)媒介的前期,文學(xué)是分裂的:在民間,大量的民歌、戲劇等利用示現(xiàn)媒介進(jìn)行傳播的文學(xué)樣式滿足著平民大眾追求娛樂和私情交流的欲望;在精英社會(huì)中,文學(xué)通過再現(xiàn)媒介強(qiáng)力地介入精英的政治生活和哲學(xué)思考。這兩套話語系統(tǒng)各有自身對(duì)文學(xué)的期待:對(duì)民間話語系統(tǒng),人們認(rèn)為文學(xué)就是聲色娛情的工具;而對(duì)精英話語系統(tǒng),文學(xué)則是教化載道的工具。這樣,在民間文學(xué)系統(tǒng)中,文學(xué)話語介入其他文化領(lǐng)域的力量衰弱了,其話語權(quán)相對(duì)也就弱化了,但是,民間對(duì)文學(xué)的角色期待也降低了。因此,這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身份產(chǎn)生了裂變,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同時(shí)存在著兩種文學(xué)身份和兩種文學(xué)角色的期待。當(dāng)這兩套“身份-期待”系統(tǒng)各自為陣時(shí),文學(xué)是安靜的;但當(dāng)這兩套系統(tǒng)發(fā)生碰撞和沖突時(shí),文學(xué)就開始了迷惑和浮躁。
在再現(xiàn)媒介時(shí)代的后期,尤其是紙媒的推廣和印刷術(shù)的進(jìn)步,使文學(xué)的焦慮開始凸現(xiàn)。在這個(gè)時(shí)代,文學(xué)的兩套話語系統(tǒng)開始出現(xiàn)和融合的態(tài)勢:一方面,文化普及成本的降低使更多的人可以掌握書面語,打破了精英對(duì)書面語的壟斷;另一方面,商業(yè)化的力量是書面語逐漸迎合民間口語,形成了書面文學(xué)語言的俗化現(xiàn)象。兩套話語系統(tǒng)的融合導(dǎo)致了兩種不同的對(duì)文學(xué)角色期待的沖突:一方面,精英們希望文學(xué)繼續(xù)承擔(dān)濟(jì)世安民的角色來維持其對(duì)文學(xué)話語的壟斷權(quán);另一方面,民間大眾通過商業(yè)的力量極力把文學(xué)塑造成一個(gè)娛情蕩志的角色。宋代以來尤其是明清之后關(guān)于文學(xué)功能的大爭論,就反映了這種沖突。但是,這個(gè)沖突在20世紀(jì)前并沒有導(dǎo)致文學(xué)的嚴(yán)重焦慮。
角色的緊張是在20世紀(jì)真正開始的。當(dāng)文學(xué)被賦予“喚起民眾”、“啟迪民智”的重大責(zé)任時(shí),實(shí)際上也超出了被“喚起”的民眾對(duì)文學(xué)傳統(tǒng)的角色期待。為了不斷調(diào)適自己以適應(yīng)新的角色期待,文學(xué)就對(duì)自己開始了革命:先是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語言系統(tǒng),然后是改變自己的敘事風(fēng)格,最后又開始改造自己的文化范式。當(dāng)把自己改得面目全非之后,又突然發(fā)現(xiàn),被“喚起”的民眾并沒有承認(rèn)文學(xué)努力扮演的新角色,所有偉大的政治責(zé)任和哲學(xué)使命無非是精英們的虛擬,而民眾期待著文學(xué)的娛情蕩志!于是,文學(xué)的精神崩潰了,它又企圖以解構(gòu)的方式來安慰自己,一切的崇高、一切的責(zé)任、一切的嚴(yán)肅,都統(tǒng)統(tǒng)卸下,不承認(rèn)自己在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具有強(qiáng)大的話語。文學(xué)解構(gòu)了自己的身份,它的力量、功能,頓時(shí)變得模糊不清起來。
也正在這個(gè)時(shí)候,機(jī)器媒介開始出現(xiàn)了。本已開始融合的文學(xué)話語系統(tǒng)又開始分裂:一套是口語化了的書面話語系統(tǒng),一套是更加感官化的機(jī)器話語系統(tǒng):幻燈、電影、廣播、電視。這種新的感官化話語系統(tǒng)似乎在向原始的讀圖時(shí)代回歸:它更加傾向滿足個(gè)人肉體快感的“充欲”的功能角色。民眾發(fā)現(xiàn)了新文學(xué):這種新文學(xué)通過機(jī)器的大量復(fù)制和感官滿足是那樣符合民眾對(duì)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期待,他們很快不再指望再現(xiàn)媒介的文學(xué)做什么,而把滿腔的熱情和期望都奉獻(xiàn)給了機(jī)器媒介的文學(xué)。于是,紙媒文學(xué)的話語接受范圍大大縮小,越來越越與其對(duì)自身的身份認(rèn)定不相稱——它還沉浸在昔日左右文化浪潮的輝煌之中呢。在電媒文學(xué)日益受到追捧的同時(shí),紙媒文學(xué)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落,終于,它的話語權(quán)僅僅局限于象牙塔里極少數(shù)的“文學(xué)家”中間,對(duì)廣大民眾而言,它確實(shí)被邊緣化了。
隨著傳統(tǒng)的紙質(zhì)文學(xué)而形成的文學(xué)身份正在因人們對(duì)文學(xué)角色期望的多元化而不斷分裂,而由傳統(tǒng)精英文學(xué)時(shí)代形成的強(qiáng)大的文學(xué)話語權(quán),也正在被機(jī)器不斷地分類給不同公眾人群。社會(huì)似乎不再有一個(gè)主導(dǎo)的文學(xué)觀,各種文學(xué)的不斷碰撞與沖突,就構(gòu)成了20世紀(jì)文學(xué)的主基調(diào)。這個(gè)基調(diào)會(huì)隨著20世紀(jì)的逝去而淡化嗎?或者說,在新世紀(jì)里,被撕裂了的文學(xué)身份會(huì)重新得到建構(gòu),走向認(rèn)同嗎?其實(shí),上個(gè)世紀(jì)末誕生的,在新世紀(jì)里注定要迅猛發(fā)展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正在悄悄地改變著這一切。
三、網(wǎng)絡(luò)媒介的功效在于使分裂的文學(xué)身份重歸融合
網(wǎng)絡(luò)媒介與機(jī)器媒介相比,有三點(diǎn)根本的不同,而這不同恰恰對(duì)未來文學(xué)身份的重新建構(gòu)和認(rèn)同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首先,網(wǎng)絡(luò)媒介彌補(bǔ)了機(jī)器媒介符號(hào)流逝性的不足,從而彌補(bǔ)了書面話語系統(tǒng)與機(jī)器話語系統(tǒng)的裂隙。相對(duì)于紙媒而言,機(jī)器媒介的最大優(yōu)點(diǎn)在于其感官?zèng)_擊力,同時(shí),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其傳播符號(hào)的流逝性:電臺(tái)里播放的一首歌和電視里的一組鏡頭,瞬間即逝,很難以凝固的方式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供受眾反復(fù)咀嚼。因此,機(jī)器媒介只能以最通俗化的方式來完成符號(hào)編碼,通過感官的強(qiáng)烈刺激來彌補(bǔ)符號(hào)流逝的損失。然而,網(wǎng)絡(luò)媒介卻彌補(bǔ)了這種不足,但同時(shí)又保留著機(jī)器媒介的優(yōu)點(diǎn)。通過強(qiáng)大的服務(wù)器支持和文字處理軟件,網(wǎng)絡(luò)媒介照樣可以像紙媒那樣將符號(hào)信息凝固在任意的時(shí)間長度中,保留了紙媒的優(yōu)點(diǎn)。同時(shí),多媒體的效應(yīng)又能同樣荷載聽覺和視覺的傳播功能,保留了機(jī)器媒介的優(yōu)點(diǎn)。這樣,通過多媒體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媒介將紙質(zhì)媒介和機(jī)器媒介的各種功能完美地糅合起來,從而為消解書面話語系統(tǒng)與機(jī)器話語系統(tǒng)的分裂提供了基本技術(shù)保障。
其次,網(wǎng)絡(luò)媒介以“點(diǎn)對(duì)點(diǎn)”的傳播方式彌補(bǔ)了機(jī)器媒介“點(diǎn)對(duì)面”的傳播方式的不足,從而彌補(bǔ)了由于“點(diǎn)對(duì)面”傳播而形成的“傳-受”關(guān)系的模糊性,使文學(xué)身份在微觀上更容易與其角色期待相吻合。無論紙媒與機(jī)器傳媒——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大眾傳媒”,都是采用“點(diǎn)-面”的傳播模式。這種模式固然有比較高的傳播效率,但卻模糊了“傳-受”關(guān)系。“傳-受”關(guān)系的模糊化會(huì)帶來什么后果呢?在回答這個(gè)問題之前,我們先簡單討論一下傳播學(xué)中的話語適配性原則和話語協(xié)同性原則。
所謂話語的適配性原則,是指話語的內(nèi)容、形式和風(fēng)格必須與話語雙方(即傳播的傳者和受者)的關(guān)系相適應(yīng),唯有這樣,話語內(nèi)容才能為話語對(duì)象所接受,而接受者的理解意義與說話人的意圖才能般配。否則,傳播意圖就會(huì)被曲解,傳播話語將會(huì)失效。
所謂話語的協(xié)同性原則,是指說話人和接受者之間應(yīng)當(dāng)共同努力,完成話語的傳播。一次成功的傳播,是傳播雙方相互適應(yīng)、相互協(xié)調(diào)的結(jié)果。
以上兩個(gè)原則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接受而言,有著重要的闡釋意義。首先,文學(xué)作品的產(chǎn)生一定要符合適配性原則,也就是說,任何作者在寫作的時(shí)候,都有他特定的或假想的傾訴對(duì)象,是針對(duì)這個(gè)人或者借描述某件事情來抒發(fā)自己的情感而進(jìn)行的。創(chuàng)作主體這種對(duì)接受話語對(duì)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們?cè)趧?chuàng)作中自然而然地確定了基本的話語內(nèi)容、風(fēng)格和形式。其次,文學(xué)作品的接受也必須符合協(xié)同性原則。一件文學(xué)作品可能并不是寫給某位讀者的,但讀者在閱讀的時(shí)候必須幫助作者完成作品意義的詮釋和理解,使話語傳播得以有效。
但是,“點(diǎn)-面”的“傳-受”模式使上述兩個(gè)原則的履行產(chǎn)生了困難。試想,“點(diǎn)-面”的“傳-受”模式,就是一個(gè)傳播主體對(duì)多個(gè)甚至無數(shù)個(gè)接受主體,這個(gè)傳播主體與所有的接受主體不可能具備同等的關(guān)系,于是,其話語內(nèi)容和表述方式的選擇就出現(xiàn)了困難,它只能將這種關(guān)系模糊化處理,盡量采用適合最大多數(shù)人的選擇。而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越高層次的需求越具有個(gè)性化,那么,“點(diǎn)-面”的“傳-受”模式最好的選擇就是盡量滿足受眾的最低層次需求,因此,大眾傳媒的庸俗化實(shí)際上就其“傳-受”模式導(dǎo)致的必然產(chǎn)物。在庸俗化的趨勢下,文學(xué)話語退出精英領(lǐng)域也就變得難以避免。
網(wǎng)絡(luò)媒介既可以采用“點(diǎn)-面”傳播模式,也可以采用“點(diǎn)-點(diǎn)”傳播模式。所謂“點(diǎn)-點(diǎn)”傳播模式,是指“傳-受”雙方是具體可知的一對(duì)人,二者的關(guān)系是明晰而確定的。比如新近流行的“博客”現(xiàn)象,就是利用了這種“點(diǎn)-點(diǎn)”傳播模式的優(yōu)點(diǎn)。說話人可以事先得知受話人具體是誰,由此也可以針對(duì)自己與受話人的關(guān)系選擇最合適話語內(nèi)容和表述方式。這樣,就不必以庸俗化的代價(jià)來保證接受人群的穩(wěn)定,從而使文學(xué)話語權(quán)保持最大限度的發(fā)揮。
網(wǎng)絡(luò)媒介的“傳-受”互動(dòng)功能彌補(bǔ)了機(jī)器媒介單向傳播的不足,從而彌補(bǔ)了由于單向傳播導(dǎo)致的“身份-角色”差異的凝固化,使文學(xué)身份與文學(xué)角色期待能相互調(diào)適,主動(dòng)吻合。傳統(tǒng)的機(jī)器媒介是一種單向傳播,也就是說,傳播主體不能及時(shí)得到受眾的反饋,因而無法了解對(duì)方對(duì)自己的角色期待,因此就形成一種“身份-角色”差異,也就是說,傳話人所具有的身份或其扮演行為與受眾對(duì)它的期待有一定的距離,而這種距離一時(shí)間又無法消除,文學(xué)身份與文學(xué)的角色期待之間不能及時(shí)調(diào)適,從而將這種“身份-角色”差異凝固化,以致形成角色緊張。而網(wǎng)絡(luò)媒介正好以其良好的互動(dòng)性彌補(bǔ)了這個(gè)缺陷,使傳話人能及時(shí)了解受話人對(duì)自己的角色期待,從而迅速彌補(bǔ)“身份-角色”差異,從而消除“角色緊張”。
綜上所述,在新世紀(jì)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參與使文學(xué)身份得到了重新建構(gòu):它不是建構(gòu)成為單一化的文學(xué)身份,而是建構(gòu)出一種能隨時(shí)調(diào)適自己以滿足各種角色期待的多元化身份系統(tǒng)。這個(gè)系統(tǒng)對(duì)外界的響應(yīng)和反饋功能保障了“身份-角色”的相互認(rèn)同,從而消解了文學(xué)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