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類與文學經典論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類與文學經典論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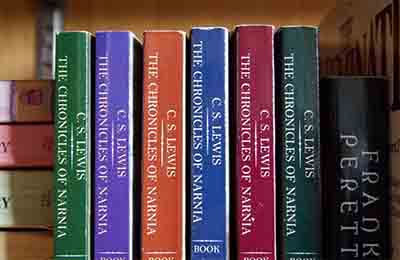
關于文學經典因文類而被建構的認識,一些理論批評家也曾有過一些概括性的模糊意識。例如在上世紀數次重版、影響較大的《簡明外國文學詞典》一書中,美國著名學者阿伯拉姆在為“史詩”、“悲劇”兩文類詞條釋義時寫道:(文學史詩)通常具有下列基本上來自荷馬的傳統史詩的特征:……對悲劇形式進行詳盡的探討……是從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典型分析開始的。亞氏援引古希臘作家埃塞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為例證,從中歸納出結論,并以它為他的理論基礎。②釋義告訴我們:凡談史詩,不能不提及荷馬史詩;論及亞氏悲劇理論,不能不根據三大悲劇詩人的劇作。這正是文學經典最基本的氣質。法國啟蒙主義作家、批評家博馬舍也指出:“難道范例的作品從最早不就是規則的基礎嗎?”③盡管其本意是反對拘守于已有文學規則,而又恰恰道出了文學作品因為作為其所屬文類的規則而成為“范例的作品”、成為文學經典的事實。法國浪漫主義代表的雨果也說過:“典范有兩類,一類是根據規則產生的,但在這類典范之前還有一類典范,即人們據以總結出規則的典范。”④后者即我們這里正在探討的情形。
當代美國學者希爾斯認為:“‘杰作’這一范疇本身就意味著對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做過的篩選和評價;它設定了某種類似于教規(Canon)的準則。”當一部或某些文學作品因文類而被建構為文學經典后,這些文學經典遂與其所屬文類共同具有了某種無形的規范性和秩序力,從而對其后的文學創作及后續文學經典的形成構成無法避免和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是因為,文學傳統“總是給偉大作品留有位置,無論這些作品的數量多大。”①
一旦文學作品的經典身份得以確立,由于其接受廣度和力度的優越性必然使其享有了其他一般性文本所無法企及的社會資本,亦即:任何創作活動的發生都無法回避既有文學經典的存在,都必須學會從業已存在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既有文學經典中汲取創作的技巧、方法等養分。所以繼亞里士多德對荷馬史詩、悲劇作品的高度肯定,賀拉斯也說:“你們應當日日夜夜把玩希臘的范例。”②法國新古典主義代表布瓦洛談及牧歌的寫作時,也把視線投向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你唯有緊緊追隨陶克利特,維吉爾:/他們的篇什纏綿,是‘三媚’心傳之作,/你應該愛不釋手,日夜地加以揣摩”。③歌德也認為,對前人文學經典的學習與參悟是提高創作方法的不二法門:“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觀賞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讓我們學習莫里哀,讓我們學習莎士比亞,但是首先要學習古希臘人,永遠學習希臘人。”④高爾基也結合自身體會開出了初學者必須認真研讀的眾多經典作品:“‘優秀的’法國文學———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的作品對我這個作家的影響,具有真正的、深刻的教育意義;我特別要勸‘初學寫作者’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這是些真正有才能的藝術家,最偉大的藝術形式的大師,俄國文學還沒有這樣的藝術家。”⑤如果說上述觀點部分地具有強烈的流派色彩,那么意大利文藝復興批評家明屠爾諾的經典觀可能更具說服力:“如果我們以下品的詩人為模范,我們將一落千丈,不值得贊美。如果我們以上品的詩人為模范,即使我們落于其下,我們還可以留在備受贊美的詩人之列。”
⑥由此可見,既有文學經典作為一定社會或群體認可的公共資源,是后來一切文學創作活動無法逾越的起點,甚而可以說這種行為規律早已經內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不過,事情總是辯證的:對既有文學經典的學習在產生積極意義的同時,也不免孳生對既有文學經典的某種依賴,一味蜷伏于文學經典的陰影之中,必將對文學創作帶來不由自主的束縛和限制,導致創作主體個性的迷失,墮入平庸之淵藪,影響創作水準的提高以及文學經典的再生產。所以,接受美學創始人之一的耀斯曾指出:“就典范而言,審美經驗的根本矛盾總是表現在它本身包含兩種‘模仿’的可能性:一是通過典范來自由地學習理解;一是機械地、不自由地去遵循某條規則。”
⑦所以,就文學創作與文學經典關系而言,必須經歷一個“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漫長而艱辛的妊娠過程。20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力的詩人、批評家之一的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的著名論文中曾經指出: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作出來時,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都同時受到了某種影響。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之后,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么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盡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①這種對既存的“完美的體系”的修改,注定了憑借“出乎其外”來實現文學經典再生產必然充滿斗爭與苦痛。縱觀西方文學史和文論史,我們不難發現:既有文學經典顯露出的文類規范對后世文學經典的產生著實構成了巨大壓力。不過,與原生文學經典因文類而被建構不同的是,此時就次生文學經典而言,文類恰又因文學經典而被建構。后世文學經典再生產、再確認與對新生文學作品別立新型文類名稱緊密相依。例如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第一次“古今之爭”中,以明屠爾諾為代表的“古”派以古希臘羅馬諸多文類規范詩學為圭臬,奉為萬世楷模,不可稍加變更。他指出說:亞里士多德和賀拉斯這兩位古人“用荷馬的詩作例證,拿出一種真正的詩藝來教導人,我就看不出另一種詩藝怎樣能建立起來,因為真理只有一個,曾經有一次是真的東西在任何時代也會永遠是真的。”
②故而對當時意大利作家阿里奧斯陀寫作的敘事詩《羅蘭的瘋狂》予以了批判,認為它違反了亞氏關于情節整一性的要求。但問題是,永遠以古人文學經典中涵括的文類規范和法則為準繩,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后人的寫作永遠缺乏足夠的新穎性,永遠匍匐在古人的陰影里。正所謂古語“同則不繼”的道理,文學史將變得不再可能,文學鮮活的軀體亦將枯竭衰敗。所以明屠爾諾的觀點遭到了以欽提奧、瓜里尼為代表的“今”派的強烈反對。欽提奧一方面否定了亞里士多德的文類詩學的普適性:“亞理斯多德心目中的詩是用單一情節為綱的,他對于寫這類詩的詩人所規定的一些界限并不適用于寫許多英雄的許多事跡的作品。”一方面提出,從發展的眼光看,有創作才能的作家不應該一味受制于古人,束縛了自身創作自由,而且充分肯定了當時意大利文學創作取得的足以比肩古人的巨大成績。他說:“我們不應該指望拿約束過希臘拉丁詩人的框子來約束我們塔斯康尼詩人。”“我們塔斯康尼詩人們的作品在我們的語言里的價值,比起希臘拉丁詩人們的作品在他們的語言里的價值也并不減色,盡管塔斯康尼詩人們并沒有遵照前人的老路走。”那么,現時代的作家如何開展創作呢?欽提奧進一步指出,亞氏和賀氏“兩位古人既不懂我們的語言,也不懂我們的寫作方式。”“正如希臘拉丁人是從他們的詩人那里學到了他們的詩藝,我們也應從我們的詩那里學到我們的詩藝,謹守我們的最好的傳奇體詩人替傳奇體詩所定下來的形式。”“傳奇體敘事詩不應受古典規律和義法的約束,只應遵守在傳奇體敘事詩里享有權威和盛名的那些詩人所定的范圍。”所以對阿里奧斯陀寫作的這類新型敘事詩,即傳奇體敘事詩給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贊揚,認為傳奇體敘事詩不同于傳統敘事詩的優越之處在于:“情節的頭緒多,會帶來多樣化,會增加讀者的快感”③。可見,新生作品《羅蘭的瘋狂》對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中的古典文類法則的悖反,確認了自中世紀伊始的“傳奇體敘事詩”這一新型文類的存在合法性和必要性。這一時期的瓜里尼、維加等人則通過各自創作實踐如《牧羊人裴多》、《羊泉村》等,再次宣告古希臘羅馬文類詩學的失效,在他們的作品中把悲劇和喜劇這兩大曾經壁壘森嚴的文類混合為一體,高高在上的國王、貴族與一貧如洗的下層人等同處一個舞臺,于是隨著《牧羊人裴多》和《羊泉村》等作家經典作品身份的被認可,“悲喜混雜劇”的新文類名亦應運而生。維加就指出:“誰要是按照藝術的法則來編寫喜劇,就沒沒無聞,窮餓而死。”他的成百上千的作品盡管嚴重違反了古典文類法則,但卻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假如我的喜劇另是一個樣兒也許更好些,可是不會那么風行。有時候不合規格的東西正因為不合規格而得人喜愛。”
①與之類似的還有,18世紀法國狄德羅和博馬舍等人由各自創作的《私生子》、《一家之主》、《歐仁尼》等作品創立“嚴肅喜劇”、“嚴肅戲劇”兩大新型文類。博馬舍就認為:“規則在哪個部門的藝術里曾經產生過杰作?”②言下之意即文學經典都會對既定文類法則提出某種程度的挑戰,而新型文類恰是“杰作”在違反古典文類規范詩學之后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衍生物。這一點在現代西方文論中顯現得尤其典型,試以“荒誕派戲劇”為例說明之。上世紀中葉,貝克特《等待戈多》、尤奈斯庫《椅子》、品特《生日宴會》等一系列新生劇本的面世,讓許多戲劇理論批評家莫名其妙,常常冠以“胡言亂語”、故弄玄虛的罪名而棄之不顧。實質是它們對傳統戲劇觀念做出了重大變革:假如說,一部好戲應該具備構思巧妙的情節,這類戲則根本談不上情節或結構;假如說,衡量一部好戲憑的是精確的人物刻畫和動機,這類戲則常常缺乏能夠使人辨別的角色,奉獻給觀眾的幾乎是動作機械的木偶;假如說,一部好戲要具備清晰完整的主題,在劇中巧妙地展開并完善地結束,這類戲劇既沒有頭也沒有尾;假如說,一部好戲要作為一面鏡子照出人的本性,要通過精確的素描去刻劃時代的習俗或怪癖,這類戲則往往使人感到是幻想與夢魘的反射;假如說,一部好戲靠的是機智的應答和犀利的對話,這類戲則往往只有語無倫次的夢囈。不難相信,如果這時還繼續以傳統文類規范來作衡量標準,無疑“要被視為令人難以容忍的無禮欺騙。”于是,英國批評家馬丁•埃斯林把如許之類具有驚人演出效果、受到廣泛贊揚的新型戲劇命名為“荒誕派戲劇”。③所以,德國學者巴爾納提出:“在遇到應當把某種標準體系長期固定下來,并使之成為一種新的傳統時,要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命名一批典范的作品。”④法國著名比較文學研究家布呂奈爾也曾指出說:“公認的體裁的束縛和作家的獨創之間的沖突,就使得在杰作和平庸的模仿作品之間,以及在所有中間等級之間加以區別成為可能。”⑤
這里也正揭示出文類因文學經典而被建構的觀念:就文學發展史而觀,文學經典通過反抗傳統文類規范詩學施加的壓力,演繹出某種新型的標準體系,而新型文類的命名不僅是對標準體系的維護和首肯,亦是對文學經典身份進行再確認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雖然文學經典與文類之間關系比較復雜,文學經典有時盡管對既有傳統文類規范有所變化,卻并不一定意味著非得提出新文類以命名之,但是仍不妨礙我們得出這樣的認識:新型文類的誕生和文學經典之間可謂如影隨形,自然天成,相得益彰。新型文類名稱讓新生文學經典在文學史上文學經典長河中別具一格,卓然獨立,與此同時,新型文類名稱也為新生文學經典的接受拓寬了期待視野,強化了新生文學經典的可接受性,功莫大焉!
位序與權力:文類等級區劃與文學經典
美國著名學者阿•福勒指出:“在決定文學經典的眾多因素中,文類絕對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不僅是因為某些文類乍看起來比其他文類更經典,還因為個別作品或段落會由于它們代表的文類的等級而相應地得到或高或低的評價。”①眾所周知,文學發展的一定階段,都會產生與之相應的某些文類特別繁盛的情狀,進而成為代表此一階段的主要文學成就,即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道理。例如我們從先秦的諸子散文、詩騷,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傳奇小說等等;西方亦如是:古希臘的史詩、悲劇,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新古典主義時期的戲劇、啟蒙主義時期的戲劇、浪漫主義的抒情詩歌以及20世紀的小說等,都是書寫文學史時永恒不變的文類經典。這些足以代表某一發展階段成就的、相對比較繁盛的文類于是各自占據了文學史上的高等級之位,對其他相對低等級的文類構成不容小覷的勢能,干擾和影響低等級文類的創作及接受和發展的正常軌跡。在文類等級與文學經典關系的認識問題上,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文類等級通過對審美主體創作熱情的影響,從根本上極大制約了屬于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生產的可能性。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都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內在驅動,我國向有“詩言志”、“文以載道”、“不平則鳴”、“發憤著書”等動機傳統,皆可為證。而作家作品的廣為傳播、接受、好評無疑是這種自我實現的最高肯定。而文類等級在此創作和傳播過程中的角色不可低估。從創作活動來說,作家必須選擇明確的文類載體進行,而社會認可的高等級文類無疑是第一選擇。設若你創作起初就選擇了低等級文類,那么即意味著你從一開始就自動退出了正統文學品評的領域,而這對作品的傳播、流傳極其不利。如果當世及后世對作品關注度很低,那么贏取文學經典的資格只能是微乎其微。古希臘文學的黃金時代,史詩和悲劇位列文類等級至高之巔,喜劇、抒情詩受到貶視。埃斯庫羅斯等三大悲劇詩人共創作了300多部作品,傳世111部(79部僅存其名),而喜劇唯有阿里斯托芬一人有完整作品傳世。而在整個古希臘文學中,喜劇也只有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區區二人有完整作品傳世。正為此故,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還是新古典主義階段,戲劇一直是文學創作的主導文類,這種影響一直波及此后的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涌現出了莎士比亞、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狄德羅、雨果、歌德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經典劇作家。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也說:“有的由諷刺詩人變成喜劇詩人,有的由史詩詩人變成悲劇詩人,因為這兩種體裁比其他兩種更高,也更受重視。”
②這里也明確道出了文類等級對作家創作中文類選擇的重要影響。再以我國為例,詩、文一直是登堂入室的高雅文類、正統文類,而視詞曲小說等低等級文類為“小道”、“末技”、“文章余事”,不屑用力其間。翻閱整部文學史,還沒有一個作家在其創作生涯尤其是創作早期,沒有創作過詩、文篇什。因為家教傳統、社會評價機制等緣故,詩、文這樣的高等級文類成了進入文學的不二法門。現存近萬首詩的陸游直到晚年還在為自己的填詞行為而自責:“少時汩于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能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③元代虞集在反思元曲創作中詞與律不能兼美的遺憾時,認為原因在于“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④“薄其事而不究心”一語正可謂道出了傳統文人士子對待低等級文類的極其典型的態度。所有這些無不從創作動機、選擇視野、選擇對象范圍上客觀決定了從高等級文類名下文學經典身份的易得性。
那么,這里需要解釋一個特殊現象:為何不少作家的經典作品不是詩、文,而是當時如戲曲、小說這樣的低等級文類呢?尤以宋元明清時代的詞、戲曲、小說為典型,如柳永、王實甫、“元曲四大家”、湯顯祖、洪升、孔尚任、馮夢龍、凌濛初、蒲松齡、吳敬梓等,世人往往僅僅關注其突出的低等級文類上的杰出成就,這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以為這并不否認文類等級對源于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產生的重要影響。一是從正常發展邏輯來說,我們只是認為文類等級對源于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的產生所施加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不容忽視,但是這種負面影響并非絕對的。二是在詩文為高等級文類的場域中,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的形成具有比較復雜的原因。這種原因大概來自于社會時代和主體經歷兩大方面。就社會時代方面而言,可以元曲為代表。在外族對漢人的統治秩序下,以詩文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體系遭到顛覆,“九儒十丐”的社會地位自然逼得像關、馬、鄭、白“四大家”等傳統文人向俗文學中尋求寄托生活之道,無心插柳柳成蔭,傳統詩文的積淀與俗文學的二次熔鑄,催生了戲曲文類的成熟及其經典作品的產生。可以說,低等級文類里的文學經典的產生,其根源仍是高等級文類及其經典作品的豐厚滋養。就主體經歷原因而論,我們以為源于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的創作往往與古代傳統文人坎坷遭遇的不幸關聯甚緊。后者埋設下了高等級文類作品創作向低等級文類作品創作轉變的核心內在動力。生活經歷的不幸拉近了以詩文創作為絕對主導的傳統文人與低等級文類之間的情感距離。傳統文人與低等級文類作品創作的媾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傳統文人對不幸社會遭遇反抗的象征符號。試想,柳永若非數次考試未果,自亦不會輕易拋棄世代為官的家族傳統而甘與青樓歌姬為伍,以吟作不入正統文人法眼的詞這一低等級文類營生。詞作數量僅占詩作數量約十分之一的文學巨匠蘇軾適逢北宋政治危機萌發之際,激烈的政治斗爭伴其一生,與變法的抵牾,終遭以“烏臺詩案”的重大變故。蘇軾開始寫詞概在熙寧五年(1072)①,正是反對新法而自請外放杭州之時。蘇軾在杭州三年后移知密州的第二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與鮮于子駿(二)》里說道:“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②
這里透露了非常重要的消息:一是詞非高等級文類,二是自外放以來在詩文之外也開始多作詞了,而且是在說無暇作詩的語境下作詞。此種不無自相矛盾的表達背后,透露的正是創作者仕途不達與低等級文類之間的某種情緒上的契合。又如湯顯祖一生寫作了2200多篇詩文,而“玉茗堂四夢”的相繼問世也是在他仕途遭受數次打壓終而辭官返家之后。素有“南洪北孔”之譽的洪升、孔尚任則稍顯特殊,他們的平民身份比較突出。孔尚任37歲之前一直賦閑在家,后因皇帝直接征召才入仕為官,至被免職總共十余年的官宦生涯。相對于早早邁入仕途的文人,孔尚任的這種經歷決定了他較少受到高低等級文類觀念的束縛;洪升雖少有才華,資稟非凡,但是卻過著賣文為生的窮苦生活,著意低等級文類的俗文學戲劇的創作自亦不難理解。小說家如蒲松齡、吳敬梓、凌濛初、馮夢龍等亦皆舉業不順,窮困潦倒,壯志難酬,遂投入當時不入流的小說文類的創作,諸如此類,限于篇幅,不復一一贅述。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關于低等級文類創作與審美主體人生坎坷遭遇的聯系這一命題,比較復雜,亦頗耐人尋味,它提醒我們務必加強對作家作品編年研究價值的重視,而非僅僅視作家所有作品為平面上的堆疊。上述諸例雖非搜羅殆盡,在某種程度上卻也是該命題某種程度上的彰明。無獨有偶,葉嘉瑩先生在論述蘇辛眾名家詞作過程中也顯露出了對該命題的支持和響應。例如,認為“辛棄疾之于詞,乃是以其全心力之投注而為之的。那就因為他在事功方面既然全部落空,于是遂把詞之寫作,當做了他發抒壯懷和寄托悲慨的唯一的一種方式。”論蘇軾詞時表達得更加細致到位:“蘇軾致力于小詞之寫作,就正是從他到達杭州之后開始的。我認為此一開始作詞之年代與地點,對于研究蘇軾詞而言,實在極值得注意。因為由此一年代,我們乃可以推知,蘇軾之開始致力于詞之寫作,原來正是當他的‘以天下為己任’之志意受到打擊挫折后方才開始的。”
①不過略顯遺憾的是,葉先生只是注意到了創作主體窮而作詞的事實,并未進一步揭示出窮而后為何在眾多文類中選擇作詞之由。其次,文類等級通過影響作品的接受與傳播,進而作用于文學經典的形成。文類等級不僅可以對文學經典的創作產生影響,而且也對文學作品的接受與傳播施加足夠的壓力,進而作用于文學經典的形成。例如詞這一文類,因為其俗文學的低等級文類之故,詩人文人的詞作大都是其詩文集外單行,給傳播留存帶來較大難度。著名的明末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家名家詞》的自跋中有言:“東坡詩文不啻千億刻,獨長短句罕見。近有金陵本子,人爭喜其詳備,多混入歐、黃、秦、柳作,今悉刪去。”②就陸游《渭南文集》50卷中收錄了詞作2卷而言,一則詞作只是作為附錄的角色廁身其間,二則書名絕然不提“詞”字。可以說,文類等級觀念給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一點我們不妨還可以作品選編現象為例予以說明。盡管我們一再聲稱“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但在作品選編過程中顯現出來的文類等級意識卻非常顯著,詩文兩大文類占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和分量。試以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1980)收錄宋元明清作品數為例:由表1我們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出,盡管詞、戲劇、小說在宋元明清諸代達到成熟繁盛,但是在作品進入選編程序時,這些當時代的低等級文類的作品仍然在詩文為高等級文類的傳統里顯現不出多大的優勢。詩文兩大傳統文類在宋元明清四朝占據著絕對主導的位置,詞這一文類甚至在元明兩代竟付之闕如,不予選摘。不難想象,對已有文學作品的選編就如同過濾網,詩文為高等級文類的意識實質上是在過濾網之外獨辟了特殊通道,享有其他低等級文類的作品所不可具有的優先權、優勢權。這無疑是在同等條件下首先大大削減了低等級文類的作品傳播、流傳的概率。如果說,文類等級在創作主體上對文學經典產生的影響是橫向上的制約的話,那么,這里所說的文類等級在作品傳播接受方面對文學經典形成的影響則又在縱向上構成了第二重牽掣。最后,文學經典有助于低等級文類的身份認同。文學經典因為其在文學史長河中積蓄的重要文化資源能量,使其具有了非一般文本所可企及的影響力。就文類等級與文學經典而論,作為特殊的文本,文學經典能夠對低等級文類的身份認同起到較大作用。眾所周知,設若沒有[雨霖鈴](寒蟬凄切)、[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江城子](十年生死)、[江城子](老夫聊發)、[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大江東去)、[鵲橋仙](纖云弄巧)、[聲聲慢](尋尋覓覓)、[釵頭鳳](紅酥手)等琳瑯滿目、傳誦不絕的經典詞作,怎么會吸引數以百計的傳統文人詩人紛紛撰寫林林總總的“詞話”?又如何能從傳統詩人文人口中筆下傳出“天地奇觀”、“獨絕千古”、“垂之千古而不可泯滅”之類的贊譽呢?設若沒有《竇娥冤》、《梧桐雨》、《墻頭馬上》、《西廂記》、《琵琶記》、《荊釵記》、《牡丹亭》、《拜月記》、《長生殿》、《桃花扇》等被褒贊為“千古絕技”、“千古第一神物”、“文章家第一流”、“千古傳神文章”的經典之作,包括戲劇、詞、小說等當時的低等級文類又如何才會有身份認同的那一天呢?這一點,前面的論述也告訴我們,西方情形亦大致如是。屬于低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以其切實可感的高超入妙的審美魅力,令人信服地一舉沖決了無端附著在文類之上的關乎等級的狹隘偏見。文學經典對文類身份認同的助益還體現為:現有文本通過對既有文學經典尤其是高等級文類的文學經典的譬喻性關聯,在肯定自身審美價值的同時,亦帶動其所屬低等級文類的身份認同。例如明清時期的胡應麟、王驥德、祁彪佳、張祥齡等人在批評戲劇或詞作品時就往往表現出濃烈的這種傾向,不勝枚舉。胡應麟說:“《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王驥德說:“《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祁彪佳也指出說:孟稱舜的劇作,“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詩》三百篇,莫能逾之。則以先生之曲為古之詩與樂可;而且以先生之五曲作《五經》讀,亦無不可也。”①甚至有人認為:“《西廂記》一書,正者十六折之文,語語化工,堪與《莊子》、《史記》并垂不朽。”②
以上諸人在批評作為低等級文類的劇作時,把《西廂》《琵琶》等比附于唐詩中的李杜、《五經》、《史記》等既有經典,既是對具體劇作審美價值的高舉,亦期借以彌合高低等級文類之間的溝壑。又如清人張祥齡在評論眾名詞人時也如是指出:“周清真,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溪也;張玉田,白香山也。”③也是憑借周邦彥、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名詞家與唐代李頎、杜甫、李商隱、白居易等著名詩人的并稱,把詞和詩兩種不同等級的文類拉回同一對話維面,努力實現詞的文類身份認同。
結語
綜上所述,探究文類與文學經典的關系問題,至少具有文類和文學經典研究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它不僅深化了文類與作家、作品的關系認識,因為從文學經典角度更能顯著地揭示文論史上以文類規范為核心的規范詩學的特征,更能突出迄今作家創作中少為人問津的文類選擇傾向;而且也提供了審視文學經典問題的嶄新維度,因為文類在文學作品經典化過程的傳播、接受扮演著潛隱而可感的實在作用。所以,將同是作為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文類與文學經典作交叉研究,是饒富新意且具較高研究價值的一項課題,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注意和重視。
作者:陳軍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