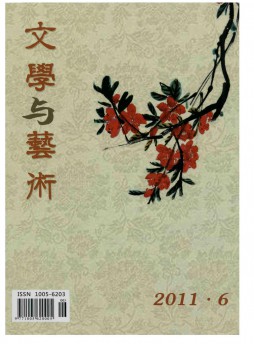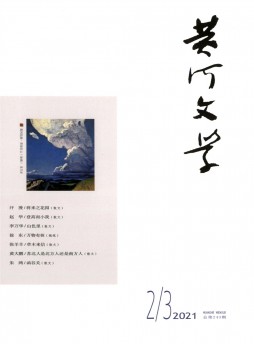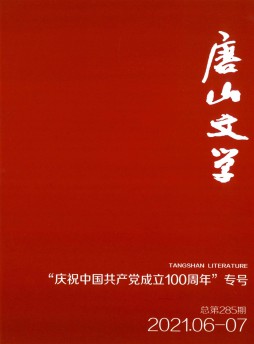文學論述的構建與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論述的構建與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史修永單位: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
米歇爾的論述向我們提供了這樣的觀念:一是在語言學、符號學中隱藏著圖像轉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語言研究中,圖像承擔著與語言文字一樣傳達意義的功能,只是比較起來顯得初級;二是對非語言符號的研究。從傳統上看,我們只能用語言具有的意義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語言符號,這樣一來,語言被擴展到各種符號的表意行動中,反而忽視包含圖像在內的視覺符號自身的意義;三是我們應該注意到話語與視覺、文字與圖像之間存在的縫隙,注重視覺圖像與視覺感知在建構世界和創造文化秩序中的獨立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理論思維的角度,視覺圖像向語言文字發起挑戰,開始撼動語言在哲學與文化領域中的中心地位。“語言學轉向”強調的是世界是由語言建構的,語言符號之間的不斷轉換產生了世界的意義。換句話說:意義的產生不過是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完成了語言對世界的編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個經驗和實體的世界,而是一個語言符號的世界,我們的知識和認識是由語言來塑造的,在語言的主宰下,語法、句法、語用、詞匯、話語、語境、意義、文本、敘事、修辭等跟語言學相關知識被廣泛運用到其它學科領域中,以至于語言學的模式和方法成為人文科學普遍的思維模式和方法,因此,“語言與存在”取代了傳統的“思維與存在”的命題成為整個知識范式轉換的重要表征,這也從根本上揭示了語言的本體含義,它遠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維特根斯坦所宣稱: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
從歷史實踐上看,作為人類交往活動中最常見的兩種媒介形式,圖像與語言文字相比所處的地位不一樣。在文字發明之前,圖像是先民表達和記錄的方式;當文字出現之后,文字以語法和修辭結構來表達具有豐富的聯想性和多義性的意義,而圖像被降低為識字的輔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圖像被認為是感性的、直觀的、平面的、零碎的,人們重視語言的理性邏輯,強調語言與圖像的異質性,而忽視圖像與語言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圖像的獨立性和意義的建構性。米歇爾發起了對語言主導文化的解構性批判,他認為:“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在某些時刻,這種斗爭似乎進入了沿著開放邊界展開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時刻(恰如萊辛的《拉奧孔》)這些邊界關閉了,彼此相安無事。
所謂的顛覆關系就存在于這一斗爭最有趣和最復雜的種種形態中”[2](P187)。在這里,米歇爾強調了語言與圖像之間漫長的斗爭過程,認為兩者之間辯證復雜的張力關系構成了文化的發展。如果說傳統文化是語言實施著對圖像的壓制和控制,那么,進入當代的視覺文化時代,圖像應該站在與語言構成對立面的基礎上,消解語言中心主義的局面,通過制造圖像和觀看圖像承擔世界意義的建構。但是,圖像的興起以及形成的對語言的挑戰,并不意味著圖像取代語言成為知識體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將圖像在語言中心論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擺脫語言論的控制,在關注語言與圖像之間的“互文”性闡發中重新挖掘和創造圖像,讓圖像再度被發現,讓圖像徹底釋放出自己的知識能量。
圖文之爭與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
圖文之爭的介入給當代文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隨著圖像意識的增強,文學與傳媒、文學與圖像、文本形式、文學的存在方式、圖像敘事與文本敘事等諸多問題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如米歇爾在《圖像理論•序》所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文化時代,所有的媒體都是混合媒體,所有的再現都是異質的,文學與視覺藝術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再現,它們與權力、價值和人類的利益糾纏在一起,影響到文化模式的變化。一種閱讀文化與一種觀看文化之間的差異不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它含蓄地指出社會性和主體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種文化所構成的各種個體和制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文學與圖像的關系問題可以在媒體再現中找到交匯點。換句話說,圖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異質關系,兩者之間的研究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毫無價值的平行對照,相反,兩者之間內在的互動關系以及構成的外部關聯使得不同藝術之間的關系研究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圖像與語言的關系為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因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文藝理論觀念。
從歷史上看,在語言學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心和旨歸是文學語言本身,認為語言是一種線性的、穩定和邏輯的符號,先行地設定文化、文學發展變遷的規律。在這種觀念中,語言占據主導優勢,而圖像只是語言之外與人的感性層面相關聯的不可靠的形式,圖像與語言根本無法聯袂,亦無法在一種張力的結構中生發出更高意義上的思維模式。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視覺文化和讀圖時代的來臨,單純的語言學思維方法已經不能完整有效地對當今文學圖像化和傳媒化趨勢作出有力的闡發,同時它也無法表征當前層出不窮的文學審美現象。
因此,當前文藝理論研究必須擺脫傳統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關切當代傳媒視野中的文學現實問題,在正視語言學等研究方法的同時,側重考慮在圖像與文字之間尋找文藝理論研究的生長點。本雅明是建構此種研究范式的積極實踐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攝影與電影的過程中預言電影將成為未來語言的者,認為以文字和書籍為代表的傳統印刷文化必將受到以圖像為主的機械復制文化的沖擊,這昭示著圖文之爭在現代文學藝術發展過程中將成為一個待解的問題。與本雅明不同,利奧塔從解構理論的角度對西方傳統文藝理論中存在的理性與感性、理智與欲望、話語與圖像、推論和感知等二元對立模式進行批判性考察,為感性、欲望、圖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尋找依據,解構西方傳統的元敘事話語和思維模式,達到攻擊現代性的目的。鮑德里亞比本雅明和利奧塔走得更遠,他在由電腦所創造的虛擬圖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傳統的文學生成和存在方式,認為虛擬圖像比真實存在更完美真實。
在此觀念下,文學藝術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應該重新設置和厘定,也就是說:圖像與現實的脫節、虛擬與真實界限的消解,使得傳統的“文學藝術模仿生活”的觀念出現問題,這無疑對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本雅明、鮑德里亞在文化和藝術層面上對圖文關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藝理論對圖文關系的重視源于當代文化給作者和讀者帶來的新的創作和閱讀感覺經驗,它是對當下文學藝術發展的理論總結和建構。顯然,西方文化領域對圖文關系的研究已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傳統的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已進入到圖像文化分析、社會歷史分析、符號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綜合、交叉的層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圖像與文學差異、互動和互通的特征,進而進入圖文生產、消費與社會權力表達、文化模式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的探究上。
當前國內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圖文關系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展開,這主要沿著兩種思路進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探討圖像與語言文字的關系,強調圖像的強勢原因、表現方式和審美效果等。這是當前文學遭遇圖像時代問題的一種“宏大理論”式的闡發,這種研究并沒有在圖像與語言之間折疊、纏繞的復雜關系中解決文學變化的具體問題;二是沿著“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歷史命題,在文學與傳媒的關系日益緊張的今天,根據文學和視覺藝術兩者的交叉滲透,從文學語言的角度來關注視覺藝術,同時強化從圖像的角度來審視文學,試圖在文學與圖像之間建構一種互文性的文學理論。具體而言:從文學語言的角度研究視覺圖像,就是理解圖像如何借助物理時空的張力結構,來接近文學并通過語言立“象”達到充滿想象力的審美至境。
反之,從圖像的角度來分析文學語言,就是理解圖像如何賦予文學語言新的意義,探索圖像在文學語言塑造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歷史形態:以圖言說、語圖互仿和語圖互文,以此揭示語圖關系發展的規律。顯然,以上所說兩種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同:前者側重語言與圖像的對立,以此勾畫出當代文化模式的變遷,以及帶來的審美方式的變化;后者則側重語言與圖像兩種媒介所具有的思維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學本身,回答文學在傳播過程中因媒介不同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說前者側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則是從內部探討文學的根本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敘事學中,傳統的文字敘事所固化的領域開始成為語圖關系研究的重要目標,從而形成一種嶄新的敘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圍繞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的敘事特點,主要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考察圖像與文字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突出圖像對敘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現問題,旨在解構文字敘事在敘事傳統中的絕對主流,擺脫與語詞共存和競爭中圖像的壓抑性地位。通過圖像與文字之間復雜關系的梳理,讓兩者在交互敘事中建構不同的價值維度,以此彰顯不同的審美意義。諸如此類的研究對于我們今天重新理解文學有太多的啟示,這昭示著當前文藝理論研究觀念的重要轉變,這些探索對于建構文學理論研究范式具有啟發性和創新意義。
圖文之爭與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幾點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文藝理論界關于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一直存在論爭,不同觀點的研究者在本質建構和拆解的論爭中宣揚自己的文學理論觀念。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作為文藝理論研究的現實問題,在為文藝理論營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時,跳出本質主義、歷史主義和解構主義等思維模式,力求返回文學活動本身,沿著亞里士多德所設定的文學媒介理論的路線尋求“拯救文學現象”,這無疑將為我們重新反思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契機。
首先,文藝理論研究應從文學現實出發,避免抽象化。何謂文學現實?在我看來,其實質就是被文學本質思維模式所遮蔽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交織、文學本身新變的現實問題。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理論觀念指引下,文學理論研究大都圍繞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繹展開討論,試圖勾畫出一幅以理念存有為深層基礎的文學圖景。這是一種本質先行的理論模式,此種模式直接規定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達到一種理論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終,文學現象被置換成一個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學活動的樸素性和現實性逐漸消失。
圖像與文學的關系問題不同,它是當代傳媒文化現實中文學發展出現的真問題,它帶動文學活動各要素在傳媒世界中發生了新變。比如依照新媒體觀念,圖像、語言和其他文本都混雜其中構成超文本文類,讀者面對如此復雜而豐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種變化打亂了以往文學理論設定和裁量文學的標準。因此,文學理論必須真正面對這些問題,從學理層面加以闡發,進而把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向前推進。
其次,回歸文學本身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文學理論問題。傳統的語言學研究范式注重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認為語言是文學的內在規定性和永恒性。這是它的功績,也是它的偏頗。因為,它在把文學的文學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時忽視了語言以外、或者與語言相關的知識場域(比如,文學與其他藝術語言之間的關系)。當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學理論學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學社會學的姿態,把觸角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使得文學研究的邊界變得模糊,文學本身的問題幾乎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話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學基礎理論知識體系的松散和脆弱。在兩種研究方式面前,我以為,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是文學理論重新思考文學自身問題反彈的重要表現,它介乎語言和文化之間,尋找理解和闡發文學的新維度,同時這也是對強調文學性研究的形式主義文論和強調文化權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種反駁和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語圖關系研究意味著在經典意義上的理論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思路。最后,應該提倡文學理論研究的多元主義理念。
文學是復雜多元的,不同的閱讀欣賞群體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現實存在的特殊性、差異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學本身就變成鐵板一塊。語圖關系問題從一個現實的側面證明了文藝理論研究應立足文學自身的多元關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藝術形態展開自身,并在各種關系的澄明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就語圖關系而言,這種關系指的是圖像作為他者在場以及互動雙方的意義建構所具有的不確定性。這種關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雙方的認同和溝通的樣式,它們在思維設置、知識分布、言說方式、審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過程中構成一種纏繞和錯落的復雜關系,并常常以微觀形式滲透、穿行在文學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因此,語圖關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藝術形式之間關系性存在的價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藝術形式之間關系研究的理論范式,將為我們重新檢視當代文藝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總之,語言與圖像的關系問題給現存的文藝理論注入了新的結構成分,它不僅引發我們對現存文藝理論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時警惕自己應保持一種建立在學術立場上的理論自反性,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文學理論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識生產場,也不是停留在責難層面上的集體“圍觀”場景,而是踏踏實實地解決問題的文學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