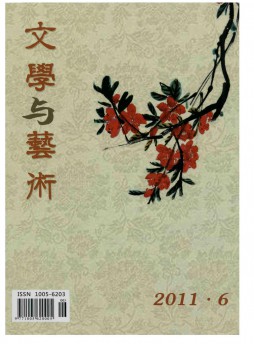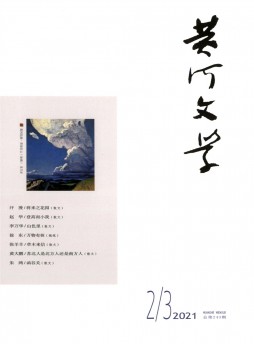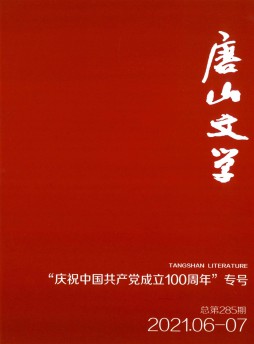文學(xué)翻譯的再創(chuàng)性與其限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翻譯的再創(chuàng)性與其限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引言
長期以來,“忠實(shí)”都被視為翻譯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絕對標(biāo)準(zhǔn)”則是原作。大多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都是提倡“信、達(dá)、雅”這些標(biāo)準(zhǔn)無一不是以忠實(shí)于原文為評判標(biāo)準(zhǔn)的。而對于實(shí)施翻譯的主題——譯者卻很少有研究和關(guān)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作為翻譯的主體,其客觀存在的主觀能動性就一直未能得到相應(yīng)的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得不到應(yīng)有的發(fā)揮,可想而知,這樣的譯本出現(xiàn)在公眾的視野之前,也會得到一些質(zhì)疑的聲音。
這里,筆者還想提到另外一個概念,那就是文學(xué)翻譯。文學(xué)翻譯,顧名思義,就是對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的翻譯。提到它的原因既簡單又復(fù)雜。就正如它本身是一項既簡單又復(fù)雜的活動一樣。文學(xué)翻譯注定是不同的。它除了具有翻譯活動的一般特性之外,還有著其特殊的性質(zhì)。除了說明要傳達(dá)出想要表達(dá)的文字和思想內(nèi)容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文學(xué)風(fēng)格的一種傳承、所以,在文學(xué)翻譯當(dāng)中也存在著創(chuàng)造性和叛逆性。如此一來,譯者則更好的在文學(xué)翻譯中實(shí)踐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樣一種命題,本文則重點(diǎn)討論譯者在文學(xué)翻譯中所進(jìn)行的創(chuàng)造性和叛逆性。
一、什么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
法國的社會文學(xué)家羅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在《文學(xué)社會學(xué)》一書中曾針對文學(xué)交際提出過“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概念。他指出“翻譯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他認(rèn)為,翻譯界一直認(rèn)為對于原作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增減和一些幅度的修改,和出于某種需要基于原作的杜撰都是對于背于原作的初衷。這顯然是對于原作的一種背離。但是,羅伯特.埃斯卡皮又指出,這樣看似背離原作的方法其實(shí)是一種文學(xué)再創(chuàng)造。它是給原作注入了“叛逆”這樣一個新鮮的血液和生命,也許擁有著嶄新面貌的原作會更加得到讀者的贊賞。
然而,對于“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概念的認(rèn)識,埃斯卡皮并沒有進(jìn)行詳細(xì)的闡述,他認(rèn)為所謂的“創(chuàng)造性背叛”實(shí)際上僅僅是存在于語言環(huán)境與語言外殼的轉(zhuǎn)換。這樣的解釋未免顯得過于簡單了。國內(nèi)的翻譯學(xué)理論大師謝天振教授曾自己的著作《譯介學(xué)》一書中指出,“文學(xué)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現(xiàn)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文學(xué)翻譯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dá)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但是,這僅僅是從理論上而言,在實(shí)際的文學(xué)翻譯中,創(chuàng)造性與叛逆性其實(shí)是根本無法分隔開來的,它們是一個和諧的有機(jī)體”。
此時,與傳統(tǒng)的議論相結(jié)合,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行為更多地可以理解為:譯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再創(chuàng)造者。他們是在明確的創(chuàng)作目的激發(fā)下完成一種作品再增添光彩的過程。這樣的過程無疑是需要積極發(fā)揮和運(yùn)用主觀能動性的,并且對于原作品的文字,音韻,內(nèi)容、修辭及美學(xué)效應(yīng)等層面進(jìn)行自我的一種再創(chuàng)造。
二、文學(xué)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文學(xué)翻譯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
翻譯包含很多內(nèi)容,如日常翻譯、科技翻譯和文學(xué)翻譯等等。就從其形式上看,翻譯似乎只是一種語言轉(zhuǎn)換的行為,在原語和譯語間不間斷的轉(zhuǎn)換過程。文學(xué)翻譯和人一樣,不能少了自己的個性,要么則會顯得蒼白無血和毫無生氣。這并不是一個機(jī)械的過程,這是一種為讀者“服務(wù)”的追求最大化的工作。而這種“最大化”則是給讀者帶來最大化美感的過程。這里重點(diǎn)則是重現(xiàn)原著國家的風(fēng)土文化和人情。
文學(xué)翻譯又是有叛逆性的。
如果將文學(xué)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理解為譯者充分發(fā)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和高超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才干去對原文的一種展現(xiàn)甚至是升華的話,文學(xué)翻譯中的叛逆性就不能簡簡單單地理解為對原作的一種客觀背離。這樣的一種客觀背離又帶著某些主觀的意味,這里理解為是在為了達(dá)到某一主觀目的的基礎(chǔ)上的。譯者一定是根據(jù)一定的主觀目的,有分寸和把握地實(shí)施這一叛逆的計劃。
還應(yīng)提出的一點(diǎn)事,文學(xué)翻譯中一般不將創(chuàng)造性和叛逆性分開而看。以上的分析只是僅僅從理論上進(jìn)行一個系統(tǒng)的梳理。優(yōu)秀的譯者都知道,在操作文學(xué)的翻譯過程中,創(chuàng)造性與叛逆性是一個和諧的有機(jī)體。
三、文學(xué)翻譯中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發(fā)生的原因
譯者是溝通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在翻譯過程中發(fā)揮著無比重要的主體作用。這就決定了譯者在整個翻譯中是起著決定性的因素的。那么譯者作為一個人,他身上存在的多種主觀和客觀的因素都會對他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叛逆產(chǎn)生不可磨滅的影響。這里的因素和他所生長的環(huán)境,包括地理和文化環(huán)境兩種。還有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和譯者在成長中和人生中的感悟能力,統(tǒng)稱為價值取向都有著非常大的關(guān)聯(lián)。當(dāng)然還有一些小細(xì)節(jié)也可以對其翻譯的作品有些不可名狀的出其不意的效果。翻譯是一個和語言有關(guān)的活動,而語言又深深根植于和它有著千絲萬縷關(guān)系的文化之中,所以,譯者本身的這種主觀能動性則必然帶來文學(xué)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上面論述也曾提到,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都是基于一定的主觀目的下的。而這種主觀目的實(shí)際上指的就是譯者本身存在的這些個別的因素。當(dāng)他們追企鵝自己獨(dú)特目標(biāo)的時候,對于原作無論是“再創(chuàng)造“還是”背離“都是有其值得肯定之處的。這樣做,不僅可以傳遞原文的精髓,有時候的叛逆還會令人更加難忘。
這里有一則非常有利的例證。許淵沖先生是這樣翻譯過李之儀的名句:“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譯文如下:
“Iliveupstreamandyoudownstream,
FromnighttonightofyouIdream.
Unlikethestreamyou’renotinview,ThoughbothwedrinkfromRiverBlue.”
譯文中的閃光點(diǎn)在于許淵沖先生并沒有按照慣例地將地名“長江”翻譯成為“YangtzeRiver,”而是別出心裁地譯成“RiverBlue”。這樣的創(chuàng)造看上去實(shí)屬小細(xì)節(jié),好似譯者漫不經(jīng)心的一個遣詞。然而,仔細(xì)品味譯文之美的行家們對這樣的翻譯真是贊不絕口。我們應(yīng)該看到譯者的“再創(chuàng)造“意圖在這里開始展現(xiàn)。許先生想借英文“blue”這個詞所透露出的傷感、憂郁氣質(zhì)而表達(dá)戀人兩地分居,常年不能相見的這樣別離愁緒。和這樣真摯細(xì)膩,難能可貴的情感相比,不論是”長江“還是”黃河“這樣的地理名詞的準(zhǔn)確譯法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因?yàn)樵S先生才是真正的大智之人,他看清了翻譯的重點(diǎn)所在,并且有勇有謀。大膽發(fā)揮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樣帶著傷感氣質(zhì)的河流既渲染了詩歌的整個悲傷氣氛,又拉近了英語讀者和中國特殊風(fēng)土文化人情之間的距離。整首詩歌譯文并無難理解之處,可謂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成功典范。
四、文學(xué)翻譯中需掌握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限度
“事無規(guī)矩不成方圓。”這里,我們不妨談?wù)効磳τ谠诓僮魑膶W(xué)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需要知道的一些尺度問題。我們必須認(rèn)識到文學(xué)翻譯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同時卻又是一種特殊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這是由文學(xué)翻譯本身的特點(diǎn)所決定的。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在這里其實(shí)是一種二度創(chuàng)造,是不同于原作家的創(chuàng)作。這就意味著,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是要受到制約的。這里認(rèn)為,翻譯實(shí)踐中文學(xué)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應(yīng)“適度”,叛逆性應(yīng)“分層次對待”。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文學(xué)翻譯的藝術(shù)性雖然較強(qiáng),應(yīng)引起重視,但是如果譯文的藝術(shù)性超出了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和限度,成為浮夸和飄渺的所謂的純藝術(shù)載體,那么這就造成了另一種反效果,這樣的譯文同樣的不可取的。讀者對于這樣的譯文也會嗤之以鼻,不為大眾所接受。那么這樣達(dá)到的效果則是更令人厭煩。
這樣譯文的特點(diǎn)是自由發(fā)揮太大,主觀隨意性太大。最突出的例子莫過于林紓的“翻譯”,他的譯文實(shí)際上已經(jīng)不再是“反映了”,而是“編譯”或“譯寫”了。因?yàn)榱旨偩哂猩詈竦奈膶W(xué)造詣,他的譯文固然是具有不可否認(rèn)的文學(xué)價值的。但是有些人則認(rèn)為那不是文學(xué)翻譯的藝術(shù)了,而是“譯寫”的藝術(shù)了。還有一些經(jīng)典的翻譯例子是:把“askforGod''''sblessing”譯成“求菩薩保佑”顯然是有些太“中國化”了,譯作“求上帝保佑”或“求神保佑”既考慮到了中國讀者的接受程度,同時又不顯得那么過猶不及。
英國漢學(xué)家HeberA.Giles也對中國詩歌文學(xué)翻譯有所研究。在楊巨源詩《城東早春》中有一句:“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這位英國漢學(xué)家則譯成:“ThelandscapewhichthepoetlovesisthatofEarlyMay,Whenbuddinggreennesshalfconcealedenwrapseachwillowspray.”
在譯文中,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體現(xiàn)在對“新春”這一詞語的翻譯。他將其翻譯成了“EarlyMary”。雖然譯者在后文又用“willowspray”一詞與之前的“EarlyMary”形成尾韻,但是這樣的過左的譯文其實(shí)是違反了原語的文化規(guī)范和文化積淀。在中國的五月初,其實(shí)已經(jīng)是暮春時節(jié)了。所以這里譯文未免顯得很不地道,沒有參透原語的文化就草率翻譯,實(shí)在令人反思。
由此可見,翻譯家盡可大方展現(xiàn)自己的翻譯風(fēng)格和特色,在選詞造句上也可以顯示出自己的獨(dú)有偏好。但是,筆者始終認(rèn)為文學(xué)翻譯還是始終要遵循客觀規(guī)律的。在文學(xué)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上,我們應(yīng)時時刻刻強(qiáng)調(diào)“度“的重要性。任意超乎自然客觀規(guī)律的創(chuàng)造是不值得推崇的。
結(jié)語
文學(xué)翻譯的特殊性決定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存在和可行性。譯者需要在深刻理解原作和把握原作精神實(shí)質(zhì)的基礎(chǔ)上,再發(fā)揮自我主觀能動力將原作的內(nèi)容和藝術(shù)魅力最大化呈獻(xiàn)給讀者。而這其中,更需要注意,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需要建立在客觀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的,只有這樣,譯者才能帶著鐐銬跳出最美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