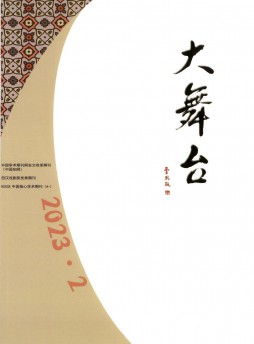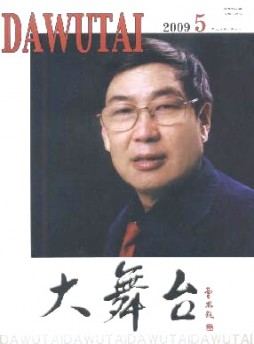舞臺(tái)藝術(shù)史下的音樂史缺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舞臺(tái)藝術(shù)史下的音樂史缺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居其宏單位: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diǎn)基地重大項(xiàng)目
綜合藝術(shù)與綜合學(xué)術(shù)中國之戲曲以及中外之歌劇、音樂劇和舞劇,是音樂、戲劇、舞蹈、舞臺(tái)美術(shù)及表演藝術(shù)高度融合的綜合體,因其構(gòu)成藝術(shù)要素的橫跨多個(gè)藝術(shù)門類及其高度綜合性特點(diǎn),歷來被稱為“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而這些藝術(shù)要素的跨門類綜合,從來就不是各個(gè)藝術(shù)要素的簡(jiǎn)單拼湊和機(jī)械疊加,而是它們?cè)诔浞职l(fā)揮自身表現(xiàn)優(yōu)勢(shì)的同時(shí),又與參與綜合的其他藝術(shù)元素結(jié)成相互滲透、彼此制約的共生關(guān)系,在綜合過程中既因受到其他藝術(shù)元素的牽動(dòng)而不斷改變著自身,也以自身固有的表現(xiàn)優(yōu)勢(shì)而牽動(dòng)了其他藝術(shù)元素的不斷改變,由是產(chǎn)生神奇而又美妙的化合、融匯和增墑效應(yīng),將聽覺藝術(shù)與視覺藝術(shù)、時(shí)間藝術(shù)與空間藝術(shù)、表現(xiàn)藝術(shù)與造型藝術(shù)之所有表現(xiàn)優(yōu)勢(shì)和獨(dú)特美感融于一體,熔鑄出一種為其他單科藝術(shù)所絕無而僅為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所獨(dú)有的綜合美質(zhì)。
恰恰因?yàn)槿绱耍C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及其下屬的戲曲、歌劇、舞劇各門類才被稱為“藝術(shù)皇冠上的寶石”而備受推崇,而音樂劇才被稱為“朝陽藝術(shù)”和“朝陽產(chǎn)業(yè)”而風(fēng)靡全球。它們?cè)谒囆g(shù)上所達(dá)到的高度,代表著一個(gè)國家、民族之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水平和整體成就。
也正因?yàn)槿绱耍瑹o論是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進(jìn)行整體性的史論研究,還是對(duì)其下屬各門類(戲曲、歌劇、音樂劇和舞劇)分門別類地從事基礎(chǔ)理論研究、發(fā)展歷史研究及批評(píng)實(shí)踐,同樣是橫跨多個(gè)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音樂學(xué)、戲劇學(xué)、舞蹈學(xué)、美術(shù)學(xué)、設(shè)計(jì)學(xué)及表演藝術(shù)學(xué))的綜合性研究,因此將它稱之為“綜合學(xué)術(shù)”恰如其分。它的學(xué)術(shù)使命,是以參與綜合美營造的各元素之固有特質(zhì)為研究起點(diǎn),探討它們?cè)诰C合過程中的堅(jiān)守與變異,破解各元素相互關(guān)系及其化學(xué)反應(yīng)的諸多奧秘,揭示在不同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門類中各個(gè)不同的綜合形態(tài)、綜合美質(zhì)及其生成規(guī)律。而多視角、多向度和整一性研究,正是這種“綜合學(xué)術(shù)”之根本特點(diǎn),也是其研究方法的獨(dú)門絕技。
傳統(tǒng)學(xué)科格局下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在傳統(tǒng)學(xué)科格局之下,以往的中國音樂史對(duì)于戲曲、歌劇、音樂劇、舞劇發(fā)展歷史的記敘和研究,究竟呈現(xiàn)出怎樣的狀態(tài),暴露出怎樣的缺失,遭遇到怎樣的尷尬?再問之:這種狀態(tài)、缺失和尷尬,在其他姊妹學(xué)科的史學(xué)研究中是否也同樣存在且同樣嚴(yán)重?事實(shí)已經(jīng)給我們提供了確鑿的答案。
單科體制與單一視野下的綜合藝術(shù)門類史自我國現(xiàn)代高等專業(yè)藝術(shù)教育創(chuàng)建以來,基本仿效歐美藝術(shù)教育體制,按藝術(shù)分類原則設(shè)置院校,從中央到地方,各類音樂學(xué)院、戲劇學(xué)院、舞蹈學(xué)院、影視學(xué)院、美術(shù)學(xué)院均為單科制院校,按照藝術(shù)教育的普遍規(guī)律和各自的獨(dú)特藝術(shù)規(guī)律,對(duì)學(xué)生實(shí)行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專門技能訓(xùn)練。即便是綜合性藝術(shù)高校、某些戲曲學(xué)院以及師范類高校中的藝術(shù)學(xué)院(系),幾乎將所有藝術(shù)門類都囊括其中,但其院系設(shè)置原則和教學(xué)理念仍舊是單科思維,下設(shè)之音樂、戲劇、舞蹈、影視及美術(shù)等院系雖在同一道院墻中,但單科思維及其所造成的專業(yè)壁壘卻如一道無形院墻,將各院系彼此隔絕開來,本院與他院、教師與教師、同學(xué)與同學(xué)之間每每“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這種單科制的院校設(shè)置和教學(xué)理念,培養(yǎng)出大量通曉本專業(yè)規(guī)律、掌握了較豐富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特長(zhǎng)的專業(yè)藝術(shù)人才,這就是它的特殊優(yōu)勢(shì)和貢獻(xiàn);但也暴露出藝術(shù)視野過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缺項(xiàng)較多等弊端。
這種單科制辦學(xué)理念及其弊端,同樣也在藝術(shù)學(xué)理論下屬各學(xué)科的教學(xué)和研究實(shí)踐中反映出來。分別從音樂學(xué)、戲劇學(xué)、舞蹈學(xué)、美術(shù)系專業(yè)出身的學(xué)者,只熟悉本門藝術(shù),對(duì)其他姊妹藝術(shù),少數(shù)知其大概,余則茫然不知。故而他所從事的研究,僅能從本門藝術(shù)的單一視野切入對(duì)象;一旦研究對(duì)象超出他的學(xué)術(shù)視域,往往茫然無措、悵然失語。
在中國音樂史研究中,此類情況不在少數(shù),特別在研究對(duì)象是戲曲史、歌劇史、音樂劇史或舞劇史,從事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門類史研究時(shí),學(xué)者們通常的應(yīng)對(duì)之策是取單一視野以揚(yáng)長(zhǎng)避短,只談音樂不及其他;于是筆下的戲曲史、歌劇史、音樂劇史、舞劇史就蛻變成了“綜合藝術(shù)元素史”,亦即戲曲音樂史、歌劇音樂史、音樂劇音樂史或舞劇音樂史。實(shí)際上,有諸多藝術(shù)元素均參與了這些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之綜合美的營造,音樂只是其中最主要的藝術(shù)元素之一;在這些綜合藝術(shù)體中,音樂元素自有其相對(duì)獨(dú)立性和獨(dú)特的表現(xiàn)優(yōu)勢(shì),但同時(shí)也接受著來自其他綜合藝術(shù)元素的制約和影響并不斷改變自身。
因此,以往諸多研究的事實(shí)已經(jīng)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將音樂元素從綜合藝術(shù)體中單獨(dú)剝離開來,僅從音樂這個(gè)單一視野對(duì)綜合藝術(shù)體中的音樂元素做單向度的觀察,便很難避免“只窺一斑、不見全豹”之弊。
首先以歌劇史中民族歌劇音樂戲劇性展開方式研究為例。民族歌劇為什么要在歐洲歌劇普遍采用的主題貫穿發(fā)展手法之外另辟蹊徑、要采用板腔體這種獨(dú)特的音樂思維方式來展開戲劇性?它與中國戲曲的音樂戲劇性思維、與中國當(dāng)時(shí)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與廣大觀眾的審美習(xí)性呈現(xiàn)出怎樣的關(guān)系?板腔體結(jié)構(gòu)在民族歌劇中經(jīng)歷了怎樣的萌芽、生長(zhǎng)、成熟、發(fā)展等不同階段,其具體音樂形態(tài)有何發(fā)展變化?在二度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怎樣的體現(xiàn),取得了怎樣的審美效果?到了新世紀(jì)之后,這種板腔體民族歌劇又為何成了“一脈單傳”?要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從音樂創(chuàng)作視角出發(fā)對(duì)之進(jìn)行研究,固然能夠得出部分答案,但若不以綜合思維和綜合視野并聯(lián)系中外戲劇藝術(shù)思維和審美趣味的差異性、中國戲曲的寫意美學(xué)和音樂戲劇性展開的特殊性,聯(lián)系當(dāng)時(shí)之社會(huì)思潮,對(duì)之做多向度、全方位、綜合性的歷時(shí)考察,便無法對(duì)上述問題中諸多深層次命題做出圓滿合理的深度闡釋。其次以戲曲史中“樣板戲現(xiàn)象”研究為例。
“樣板戲”的創(chuàng)腔實(shí)踐和樂隊(duì)編配思維,除了受到中國傳統(tǒng)戲曲寫意美學(xué)和音樂戲劇性思維的影響至深至巨并將之當(dāng)作自己傳承和創(chuàng)新變革的基本立足點(diǎn)之外,往近里說,同時(shí)也接受了我國40年代以來民族歌劇的影響;往遠(yuǎn)里說,同樣也受到五四以來我國新音樂創(chuàng)作的影響;往更遠(yuǎn)處說,歐美戲劇藝術(shù)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美學(xué)傳統(tǒng)、藝術(shù)音樂創(chuàng)作(特別是歌劇音樂和交響音樂創(chuàng)作)中主題貫穿發(fā)展的音樂戲劇性思維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響了“樣板戲”的音樂創(chuàng)作。
若不將上述因素融會(huì)一處、了然于心并做整體性、綜合性的多維審視,其中諸多曖昧不清的重要命題便斷難說明。再次以舞劇史中舞劇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為例。
中外舞劇史證明,作為舞劇藝術(shù)綜合體中一個(gè)極為重要的元素,舞劇音樂同樣是戲劇性音樂,從事舞劇音樂創(chuàng)作的作曲家們普遍采用主題貫穿發(fā)展這一嚴(yán)密有機(jī)且行之有效的音樂戲劇性思維來展現(xiàn)戲劇沖突、刻畫人物性格。而現(xiàn)今之中國舞劇音樂創(chuàng)作,絕大多數(shù)作曲家均擯棄主題貫穿發(fā)展手法和音樂戲劇性思維、轉(zhuǎn)而采用一種可稱之為“場(chǎng)面描繪性思維”、“激情渲染性思維”來譜寫音樂,其音樂布局因缺乏貫穿統(tǒng)一的結(jié)構(gòu)力而益顯松散雜亂,其音樂描寫因與戲劇情節(jié)、人物性格、戲劇情境未能構(gòu)成明確可辨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而令人對(duì)其音樂表現(xiàn)目的何在頓生疑竇;還有更為等而下之者,則將央視大型歌舞晚會(huì)“大呼隆”式的音樂思維直接橫移到舞劇音樂創(chuàng)作中來。舞劇音樂史研究者如果不聯(lián)系劇情和人物性格,不對(duì)作曲家的音樂描寫與舞蹈本體和舞臺(tái)上所發(fā)生的一切進(jìn)行綜合性考量,僅從音樂本體形態(tài)視角出發(fā)對(duì)之做微觀層面的作曲技法分析和評(píng)價(jià),便絕難得出準(zhǔn)確可靠的結(jié)論,甚至極有可能將這種起因于創(chuàng)作心態(tài)浮躁、急功近利之風(fēng)盛行而產(chǎn)生的對(duì)于舞劇音樂創(chuàng)作戲劇性原則的倒退看成是一種觀念更新和歷史進(jìn)步。
其實(shí),在單科體制與單一視野下,不僅音樂史對(duì)于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門類史的研究存在上述諸多缺失,戲曲學(xué)中的戲曲史研究、舞蹈學(xué)中的舞劇史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戲曲學(xué)者研究戲曲史時(shí)只談腳本和劇詩不論音樂及其他、舞蹈學(xué)者研究舞劇史時(shí)只談舞蹈不論音樂及其他這類情形,我們?cè)谝酝难芯繉?shí)踐及其成果中隨處可以見到。
單科體制與單一視野下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單科體制與單一音樂視野下的綜合藝術(shù)門類史研究,盡管存在上述諸多缺失,但它畢竟從一個(gè)特定側(cè)面、部分地揭示了音樂藝術(shù)元素在綜合藝術(shù)體中的重要地位、表現(xiàn)意義和具體形態(tài)特點(diǎn),因此仍是一種常規(guī)的、有價(jià)值的研究思路,不宜對(duì)之做過多的責(zé)難,否則便失之偏頗;至于過往研究中的諸多缺失,也確有增強(qiáng)“綜合藝術(shù)”意識(shí)、拓寬“綜合學(xué)術(shù)”視野來逐步加以彌補(bǔ)和完善之必要。對(duì)戲曲學(xué)中的戲曲史研究和舞蹈學(xué)中的舞劇史研究,亦應(yīng)作如是觀。
然而,每當(dāng)我們一旦超越“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門類史”這個(gè)層面,將戲曲史、歌劇史、音樂劇史和舞劇史躍升到它們所隸屬的更高一級(jí)邏輯層次“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來觀照時(shí),總會(huì)遭遇到被無視、被遺忘甚至被拋棄的尷尬。謂予不信,請(qǐng)看下列事實(shí):在傳統(tǒng)學(xué)科格局之下,鑒于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研究屬于“綜合學(xué)術(shù)”,為藝術(shù)學(xué)各學(xué)科自身的單科性質(zhì)和特定范疇所決定,不僅中國音樂史研究自然將“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研究根本排除在本學(xué)科的劃定邊界之外,而且中國戲曲史研究、中國舞蹈史研究也同樣如此。這也難怪。
如前所說,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分類以單科思維為依據(jù),于是,在藝術(shù)分類中,除了相關(guān)的單科藝術(shù)之外,在藝術(shù)分類群落中并無“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地位;傳統(tǒng)的學(xué)科分類亦以單科思維為依據(jù),除了與之相適應(yīng)的以單科藝術(shù)為研究對(duì)象的各學(xué)科之外,在學(xué)科分類群落中亦無“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地位。在人類藝術(shù)史上有千年歷史的戲曲、數(shù)百年歷史的歌劇和舞劇、百余年歷史的音樂劇,這些曾經(jīng)誕生過無數(shù)大師和杰作、充分體現(xiàn)出人類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驚人天才和偉大成果并且至今仍是人類高尚精神生活斷不可缺之藝術(shù)品種,居然在藝術(shù)分類和學(xué)科分類中處于極度尷尬的、名不正言不順的窘境之中———盡管戲曲被稱之為“戲曲學(xué)”,盡管歌劇和音樂劇被迫屈居于“音樂學(xué)”、舞劇被迫屈居于“舞蹈學(xué)”,但恰如前已指出的那樣,由于這些學(xué)科的單科體制和單一視野,各學(xué)科之間非但界限明顯,而且壁壘森嚴(yán);在現(xiàn)行單科藝術(shù)教育體制和學(xué)科布局之下,若要它們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學(xué)科間的既有界限和學(xué)科壁壘,對(duì)這些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品種之綜合要素、綜合機(jī)制、綜合美質(zhì)、綜合效應(yīng)進(jìn)行跨越多個(gè)學(xué)科的綜合性研究和多維度審視,即便不是天方夜譚,也是極為困難的。更具悲劇意味的是,這種因傳統(tǒng)學(xué)科布局不合理而造成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或被活生生肢解到各個(gè)單項(xiàng)學(xué)科之中、或遭整體性遺棄而長(zhǎng)期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現(xiàn)實(shí),學(xué)界人士對(duì)此多習(xí)以為常,甚至漸漸積淀成一種思維定勢(shì)。
為此,戲劇類雜志常常拒絕刊登包括音樂元素在內(nèi)的歌劇史和音樂劇史研究論文,音樂類雜志常常拒絕刊登包括舞蹈元素在內(nèi)的舞劇史研究論文,舞蹈類雜志常常拒絕刊登包括音樂元素在內(nèi)的舞蹈史研究論文;其牛氣沖天的理由,一般都是“專業(yè)不對(duì)口”。
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長(zhǎng)期活躍、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研究的長(zhǎng)期闕如以及這兩者的長(zhǎng)期并存,于是便釀造了一出削足適履式的悲劇且已上演了數(shù)百年;究其悲劇成因,不能不歸咎于單科體制和單科思維,以及傳統(tǒng)學(xué)科布局對(duì)于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這個(gè)鮮活大家族的整體性漠視。缺失與尷尬的兩種解決之道中國音樂史在面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研究時(shí)所常見的缺失、所遭遇的尷尬,因其屬于體制性痼疾且由來已久,故此不易得到根本解決。筆者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當(dāng)代音樂史、歌劇音樂劇史研究多年并有幾部著述面世,每到涉筆戲曲、歌劇、音樂劇、舞劇這些史學(xué)對(duì)象時(shí),亦常懷捉襟見肘之憾。故此思之再三,特提出如下兩種解決之道供同行參酌指正。
權(quán)宜之計(jì):在現(xiàn)行學(xué)科布局下完善學(xué)者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中國音樂史之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研究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主要是來自學(xué)術(shù)隊(duì)伍的專業(yè)背景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局限,而單科制的藝術(shù)教育體系則是造成這種局限的主因———從現(xiàn)行教育體制中很難成批培養(yǎng)出能夠勝任并自如駕馭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進(jìn)行多學(xué)科、綜合性史學(xué)研究和批評(píng)的學(xué)者。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自身研究傳統(tǒng)和學(xué)術(shù)積累之所以薄弱,當(dāng)與學(xué)者隊(duì)伍的這一局限關(guān)系極大。于是便有學(xué)者據(jù)此提出質(zhì)疑:學(xué)者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局限若不能合理解決,合格的研究隊(duì)伍便付之闕如,理想中的中國音樂史之“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研究豈不成了“無人地帶”,本文所描畫的種種優(yōu)越性美景,與海市蜃樓何異?有鑒于此,在維持現(xiàn)行學(xué)科布局的前提下,我認(rèn)為這一難題暫有兩條破解之法:
其一,在我國從事中國音樂史的學(xué)者中,鐘愛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對(duì)其史論研究及批評(píng)懷有濃厚學(xué)術(shù)興趣且在以往的研究實(shí)踐中有一定成果積累者不乏其人。只要這些學(xué)者對(duì)自身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局限抱有清醒認(rèn)識(shí)并通過個(gè)人修為和不懈努力,仍有較大可能增其強(qiáng)補(bǔ)其弱,進(jìn)而逐步實(shí)現(xiàn)綜合藝術(shù)素養(yǎng)、技能的自我完善和理論視野的多維拓展。當(dāng)然,這種僅靠個(gè)人修為和努力以達(dá)成學(xué)者知識(shí)結(jié)構(gòu)自我完善的方案,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設(shè)計(jì)和保證,既有較多的偶然性,也帶強(qiáng)烈的個(gè)別性;但也不可否認(rèn),“制度外成才”或“自學(xué)成才”現(xiàn)象仍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人才培養(yǎng)之路。
其二,在有條件的藝術(shù)高校、特別是在打破單科思維和學(xué)科壁壘方面擁有特殊優(yōu)勢(shì)的綜合性藝術(shù)高校,明確提出“以綜合思維辦綜藝高校,化綜合潛能為綜合優(yōu)勢(shì)”的目標(biāo),打破無形院墻,充分發(fā)揮綜合性藝術(shù)高校的有利條件,在本科各理論專業(yè)的教學(xué)中試行以本學(xué)科為主、兼學(xué)其他學(xué)科的制度;同時(shí)專門設(shè)立“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這個(gè)新專業(yè)或新學(xué)科,通過碩士、博士學(xué)位教學(xué)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將本校或其他高校本科、碩士和博士中那些既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某一門類及其史論研究和批評(píng)有較扎實(shí)的專業(yè)基礎(chǔ)和一定學(xué)術(shù)積累、又有廣泛的藝術(shù)興趣、理論視野較為開闊、具有培養(yǎng)潛質(zhì)的學(xué)生招收入學(xué)或從事合作研究,令其廣泛接觸其他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經(jīng)典作品和學(xué)術(shù)文獻(xiàn),在積累更多鮮活感性經(jīng)驗(yàn)的同時(shí),從基礎(chǔ)理論和專業(yè)技能諸方面對(duì)之進(jìn)行針對(duì)性的增強(qiáng)補(bǔ)弱訓(xùn)練。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高層次學(xué)位教學(xué)和合作研究,前述“制度外成才”所特有的偶然性和個(gè)別性得以有效避免,如能堅(jiān)持七八年、十?dāng)?shù)年,一批批真正合格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學(xué)者之有望從各院校中培養(yǎng)出來,當(dāng)不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一個(gè)具體實(shí)例是,筆者從2004年以來在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設(shè)立“歌劇音樂劇史論研究”方向,通過碩士、博士教學(xué)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對(duì)入學(xué)和進(jìn)站的中青年學(xué)者進(jìn)行這兩門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史論訓(xùn)練,效果良好。如果戲曲學(xué)、舞蹈學(xué)這兩個(gè)學(xué)科也嘗試這樣做,相信同樣能夠取得良好效果。
當(dāng)然,上述建議和方案也未必能夠得到學(xué)界同仁的廣泛認(rèn)可,即便經(jīng)過深入討論和爭(zhēng)鳴最終能夠獲得多數(shù)同行的共識(shí)也還有待時(shí)日。但從中國音樂史對(duì)于戲曲史、歌劇史、音樂劇史和舞劇史研究隊(duì)伍培養(yǎng)來說,仍不失為一條可行的權(quán)宜之計(jì)。
根本之道:作為藝術(shù)學(xué)理論之二級(jí)學(xué)科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近來,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huì)頒布了最新學(xué)科目錄,將藝術(shù)學(xué)從文學(xué)中獨(dú)立出來,列為第十三個(gè)學(xué)科門類;在其之下,設(shè)立“藝術(shù)學(xué)理論”、“音樂與舞蹈學(xué)”、“戲劇與影視學(xué)”、“美術(shù)學(xué)”和“設(shè)計(jì)學(xué)”5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
盡管藝術(shù)學(xué)界仍有一些學(xué)者對(duì)這個(gè)最新學(xué)科目錄持有異議,但僅就它將藝術(shù)學(xué)從長(zhǎng)期從屬于文學(xué)這種寄人籬下的困境中解放出來這一點(diǎn)而論,當(dāng)為我國藝術(shù)創(chuàng)作、藝術(shù)教育、藝術(shù)學(xué)研究的整體性繁榮發(fā)展提供了一個(gè)獨(dú)立平臺(tái),因此有難以估量的戰(zhàn)略意義;而包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史”、“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論”、“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批評(píng)”在內(nèi)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其長(zhǎng)期“妾身猶未明”式的尷尬處境,也因此現(xiàn)出了“必也正名乎”的曙光。本文的論旨之所以從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缺失與尷尬轉(zhuǎn)向并最終歸結(jié)到“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的學(xué)科定位和學(xué)科建設(shè)上來,并將它列為徹底解決上述諸多難題的“根本之道”提出,其基本立意正在于此。
竊以為,從“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的學(xué)科性質(zhì)、研究對(duì)象、理論范疇的綜合性和特殊性及其跨學(xué)科多維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做統(tǒng)籌考察,其最佳的學(xué)科定位,是將它置于一級(jí)學(xué)科“藝術(shù)學(xué)理論”之下,與“藝術(shù)原理”、“藝術(shù)史”、“藝術(shù)批評(píng)”共同構(gòu)成4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
我之所以如是說,不單單是為“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尋找到最佳的學(xué)科定位,同時(shí)也是針對(duì)藝術(shù)學(xué)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而給出學(xué)科建設(shè)建議。因?yàn)椋^往之藝術(shù)學(xué)理論,無論它是曾經(jīng)的二級(jí)學(xué)科還是如今的一級(jí)學(xué)科,其研究一般均呈現(xiàn)出如下兩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理路:
其一,現(xiàn)今從事藝術(shù)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多系文學(xué)、史學(xué)、美學(xué)或哲學(xué)專業(yè)出身,其長(zhǎng)處是文史哲修養(yǎng)和抽象思辨能力較高,著述的邏輯性強(qiáng),文字表達(dá)功夫到家;然終因各種主客觀條件(特別是教育背景)的限制,其筆觸往往由于未經(jīng)某一門類藝術(shù)本體理論和技術(shù)技巧的系統(tǒng)訓(xùn)練而缺乏堅(jiān)實(shí)的立足點(diǎn)和真切豐富的感性體驗(yàn),常常無法真正探入到特定藝術(shù)門類的本體結(jié)構(gòu)和形態(tài)特征之中去探知其美的生成規(guī)律和獨(dú)有奧秘,因此普遍存在著某種“泛理論”傾向,絕大多數(shù)成果均在天馬行空、行云流水般的高談闊論中難免露出粗疏空泛、隔靴搔癢之弊,甚至流于“門外藝談”———此即所謂“不通一藝莫談藝”也。
其二,經(jīng)歷了某一門類藝術(shù)之技術(shù)技巧系統(tǒng)訓(xùn)練的學(xué)者,往往又缺乏寬廣的藝術(shù)視野和超拔的哲學(xué)-美學(xué)素養(yǎng),難以進(jìn)行跨門類、跨學(xué)科的綜合研究和理論概括,其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門類的本體論研究、史論研究或批評(píng),其成果每每鐘情于本門藝術(shù)某些技術(shù)細(xì)節(jié)的描述和分析,并止步于具體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的玩味,卻無法將其理論視野提升到真正意義上的藝術(shù)學(xué)層面,因此存在某種“經(jīng)驗(yàn)論”傾向,終令藝術(shù)學(xué)理論的學(xué)科屬性未得到真正彰顯而常遭名實(shí)不符詬病———此即所謂“僅通一藝難論藝”也。
當(dāng)上述兩類學(xué)者面對(duì)戲曲、歌劇、音樂劇和舞劇這些研究對(duì)象時(shí),其專業(yè)背景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的固有弱點(diǎn)以及由此形成的“泛理論”或“經(jīng)驗(yàn)論”缺憾便更加暴露無遺,根本無法勝任對(duì)它們做多藝術(shù)元素綜合審視和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的學(xué)術(shù)使命;至于上升到“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這個(gè)層面,對(duì)之做更高層次的綜合審視和超拔研究,則更無從談起———這也是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及其史論研究和批評(píng)迄今為止從未進(jìn)入藝術(shù)學(xué)學(xué)者研究視野的根本原因。正因?yàn)槿绱耍P者才放膽建議:將“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列為一級(jí)學(xué)科“藝術(shù)學(xué)理論”項(xiàng)下的一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這一建議倘獲采納,我想它的優(yōu)越性至少可概括為如下三個(gè)方面:
其一,長(zhǎng)期被遺落在諸多學(xué)科之外、一直處于居無定所狀態(tài)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及其綜合性史論研究和批評(píng),從此結(jié)束流浪者和棄兒身份,終于找到了名正言順的棲身之所;而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的整體性、綜合性研究,也將因此受到藝術(shù)學(xué)界的認(rèn)可和重視,無論從理論與實(shí)踐兩方面均將大有益于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表演、教學(xué)及其學(xué)術(shù)研究的繁榮和發(fā)展。
其二,一級(jí)學(xué)科“藝術(shù)學(xué)理論”因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的加盟而從此有了專屬于本學(xué)科的研究對(duì)象,從而使學(xué)科內(nèi)涵更為充盈,學(xué)科結(jié)構(gòu)更具縱深感。尤為重要的是,實(shí)際上,藝術(shù)學(xué)基礎(chǔ)理論研究的真諦多深藏于舞臺(tái)綜合藝術(shù)的基本理論之中;舞臺(tái)綜合藝術(shù)研究及其成果可以為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理論建設(shè)提供一條切入路徑、一種學(xué)術(shù)架構(gòu)、一個(gè)新的理論生長(zhǎng)點(diǎn),從而有助于藝術(shù)學(xué)研究得以超越“泛理論”和“經(jīng)驗(yàn)論”層面,逐步躍入真正的藝術(shù)學(xué)境界。
其三,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成為二級(jí)學(xué)科之后,與其他學(xué)科的學(xué)者從音樂學(xué)、舞蹈學(xué)、戲劇戲曲學(xué)、影視學(xué)、美術(shù)學(xué)、設(shè)計(jì)學(xué)視角對(duì)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各門類、各要素進(jìn)行單科性或交叉性研究非但并行不悖,且互為補(bǔ)充、彼此增益,共同打造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研究的大格局。
這樣一來,既為“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學(xué)”找到最為理想的棲身之所,也令“藝術(shù)學(xué)理論”有了專屬于本學(xué)科的藝術(shù)門類立足點(diǎn)———有如此互補(bǔ)雙贏、兩全其美效應(yīng),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