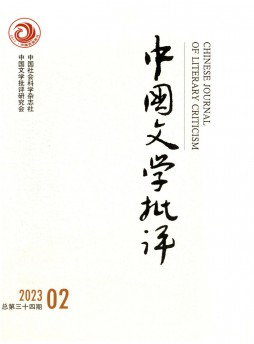文學批評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建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批評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建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批評意識的契合與民族認同的自覺
在西部文學的大視野中,寧夏“三棵樹”的寫作有著特殊的意義,對他們總體性的定位或許更能說明一切,如有評論者這樣評價陳繼明的小說,“其鄉土小說對轉型期西部農村經濟秩序和鄉村傳統道德文明體系的崩潰、鄉村人際關系的分崩離析、鄉民在金錢誘惑下的人格扭曲和人性異化都有精細的表現……其獨特之處就在于穿透喧嘩都市的表層生存風景,發現和揭示轉型時期都市人的浮躁和抑郁心態所導致的非理性行為,直逼人物內心微妙、復雜的情緒變化與心理沖突,亦即‘陳繼明式的情緒騷動’,并將之引向對生命存在意義的揭蔽與追尋,表現出相當鮮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的哲理色彩”。以修史見長的評論家,其判斷往往高屋建瓴,但高度的概括往往流于以偏概全的評論姿態,如果單純從陳繼明創作的表象來看,對陳繼明這樣的評價也無可厚非,作為域外論者受題材論的影響,致使結論多少帶有先入為主的嫌疑,這樣的結論可以說是進一步體驗與思考了陳繼明已經體驗與思考過的觀念,但是卻不夠深入。問題的癥結在于,對于陳繼明文學價值的定位如果放置在現代主義背景下,這樣的結論則被極度類型化,也就遮蔽了小說家的獨特性。而作為域內論者的牛學智洞悉了文學史家的偏頗之處,通過與陳繼明本人的對話,觸及作家本人真實的內心世界及創作思維,也揭示出陳繼明創作之中易被掩飾的部分,“細讀陳繼明的某些被有意無意忽略的作品,感覺他并不是自閉式的心理分析,他對人物精神存在性的剖析是嚴重地介入現實結構,并且眼光向外的。或者說他始終關注的是人物的現實處境、歷史處境”。結合這句論斷,再回到陳繼明的小說《月光下的幾十個白瓶子》,這篇小說“以深刻的洞察力敏銳而準確地捕捉到了當下紛擾社會情勢下的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消極心理———‘煩著呢’,并揭示出了這種異常的社會心理所蘊藏的巨大危險性”。陳繼明對小說人物的刻畫,雖側重于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創作風格———“陳繼明式的情緒騷動”,但陳繼明創作的旨歸是指向社會現實,他的心理分析是為了更好地介入現實結構中來。牛學智的觀點顯然要比域外評論家的定位更到位,尤其是牛學智在論及陳的長篇小說《一人一個天堂》時,指出小說之中的“父性”問題所觸及的文化反思,得到了陳繼明的認可。究其原因,在于論者與作家本人在對社會的認知上都不約而同地歸結到文化語境中的社會反思這一層面。這要比有些論者動不動就在“人性”“道德倫理”等常規的小視域中打轉轉要高明了許多。批評意識的契合還源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同一民族情結所具有的認知趨同的自覺。這一點在對石舒清的評論中得到較為明顯的應驗。文學史家對石舒清的評價,將石舒清放置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大背景下來談及,身為回族作家的石舒清,其文學創作帶有強烈的民族特色。在他的小說中,常常伴有一些回族宗教禮儀、婚喪嫁娶、生活習慣等生活場景,表現出回族文化獨特的審美風格和特殊的心理內蘊。他對自己的民族身份充滿著強烈的認同。“我更慶幸我是一個回族作者。……回族民族,這個強勁而又內向的民族有著許多不曾表達難以表達的內心聲音。這就使得我的小說有無盡的資源。”
伴隨著石舒清文學創作的不斷獲獎,石舒清也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對石舒清的評論,如果從民族認同這一角度,回族評論者對石舒清的評論或許更為恰當,因為他們與作家本人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與文化傳統,石舒清小說之中反映出來的民族意味、民族表達尤其是作品靈魂的民族精神的張揚,都會在無意識之中觸動回族評論者的神經。因此,從他們的評論文章中,感受回族這一共同體特有的民族文化魅力,尤其是涉及宗教、民俗等獨有的民族符號時,回族評論者的解讀無疑更為準確到位。考量他們的評論,不僅是一種批評意識的契合,更是一種民族認同的自覺。這一點,域外學者已經意識到評論的失語,在對石舒清名篇《清水里的刀子》分析中,文學史家認為:“馬子善老人從牛的舉止中得到啟迪,心情趨于寧靜。這種在漢族人、現代都市人中罕見的內心令都市讀者怦然心動。事實上,石舒清的用心和期望也正在這里”。這樣的解讀對于熟識回族文化背景的回族論者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判斷顯然是不熟悉回族文化背景的可笑誤讀。同一細節,回族論者楊文筆寫道:“小說表面是在講述一頭即將獻祭的牛為‘有一個清潔的內里’作為通向彼岸世界的門票而不食不喝的神奇故事,其深層內涵體現著回族人生活中講究清潔和心靈潔凈以追求‘清真人’的精神理念。如此馬老漢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死期,這不僅僅是‘他會將自己洗得干干凈凈,穿一件潔潔爽爽的衣裳’,更是他要為自己收拾和準備一個清潔的內里,清清潔潔地歸真復命”[9]。楊文筆從回族群體的民族理念與精神追求去解讀作品,這首先是一種民族認同的自覺,換句話說,石舒清的“用心和期望”應該是民族習性的使然,對比之中,楊文筆的結論更符合石舒清意識深處的生命體驗。
二、終極關懷與精神價值的建構
談及西部文學,在人們常規的閱讀思維中,總覺得西部文學與現代化是不能對等的,與東部沿海城市,尤其是與“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相比,對西部的評價,更確定說是一種文化想象,總是與原始、荒涼、野性這樣的描述相聯,這可能源于西部特有的地理風貌,可實際上,“‘真正的西部’有大漠、戈壁和荒原,也有自己的現代城市”。但從文學這一視角看去,西部文學反映現代城市有影響的小說是比較匱乏的,西部文學還是以鄉土文學見長。不言而喻,西部的作家對現代文明的接受并沒有化成血肉,變成生活習慣,大量的西部作家從人生經歷來看,多有著農村的生活背景。因此,他們的文學創作首先是在人生經歷與個人記憶中尋找創作的題材。這一點,在寧夏作家之中尤其明顯。域外學者之所以認可寧夏文學,認可寧夏“三棵樹”,就源于在他們的創作中,看不到先鋒小說那種充滿灰暗氣息和頹廢情緒的書寫,也看不到一些作家對“性”的近乎瘋狂的渲染,對女性近乎野蠻的傷害與侮辱。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精神充盈的價值世界”,是關乎人類生存意義的探尋,是對真善美的鼓吹與吶喊,是對美好人性的禮贊。從譜系上看,他們繼承了魯迅鄉土小說的批判性,又兼具沈從文小說的詩性與理想主義。放置于現代性的文化語境中,寧夏小說的這些特點的確在如此浮躁功利的社會風氣中呈現出獨有的價值與意義。評論者在研讀寧夏文學時,更看重的是寧夏文學特殊的題材所展現出的精神價值。這一點在圍繞石舒清小說創作的評論中得到驗證。2001年,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獲得魯迅文學獎,2002年在《名作欣賞》第5期得到轉載,2003年《名作欣賞》雜志發表了10篇關于《清水里的刀子》的專篇解讀的評論文章。整合這些評論文章,發現這些論者不約而同地將關注點集中在“終極關懷”這一哲學層面。小說的確涉及生死觀的理解,老漢馬子善在侍弄著一頭待死的牛,實際上面對牛的過程是走向自己縱深的內心過程。看到牛的待死,想到自己的待死。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終極關懷是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向。終極關懷正是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無限的超越性本質,它是人類超越有限追求無限以達到永恒的一種精神渴望。對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構成人生的終極性思考,這是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的哲學智慧;尋求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尖銳對立的緊張狀態,這是人的超越性的價值追求。只有終極關懷才能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無限的緊張對立,才能克服對于生死的困惑與焦慮。終極關懷是人類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徑。再加上石舒清的回族特征,信仰伊斯蘭教,眾多域外論者將小說生死觀的解讀與作者的宗教意識相聯系,將“終極關懷”推向一個彼岸世界中去,“朝圣”“抵達天堂”“宗教儀式下的人性與神性”“生命的思考與終極關懷”“哲學意蘊”等,一時間一篇短篇小說承載了眾多的意義,這也許連作家本人也沒有想到。實際上對作者本人而言,他關注的的確是回族民間傳統的精神,但絕非要將這種精神推向“終極”。石舒清自己就說道:“我不想說‘終極意義’一類大詞,也不愿用‘拷問’一類說法逼迫自己,使自己難堪。”
再說了,一篇短篇小說如果完全是在宗教理念驅動下完成的,那么這篇小說肯定因為“理念先行”而失去文學上的價值。《清水里的刀子》之所以獲得魯迅文學獎而被方家認可,不僅是因為小說里所蘊含的宗教因素,如果僅僅是宗教因素,那么小說的深刻主題意蘊就被簡化了。“宗教只是文化的一個方面,不能以此作為整體的名稱”。小說被認可,更重要的是觀念背后所隱藏的文化因素。穆斯林歸真復命的文化心理是小說價值所在。可以說“終極關懷”是小說的果,小說的因則是民族的文化心理。石舒清的小說創作一直堅守民族文化傳統的禮贊,眾多評論文章在論及石舒清小說的精神價值時往往事先進行一個背景的預設,那就是石舒清的家鄉———西海固。西海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但就是這樣貧瘠的地區卻養育著成千上萬的西海固人民,并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出了眾多知名的作家。他們在消費本土化的經驗,實際上也是在享用本土化的經驗,是這片土地賦予了作家創作的靈感來源。西海固的苦難造就了西海固人精神的堅忍。石舒清是這種精神的鼓吹者,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回族老人與婦女的形象,在他們身上,總是能夠展示出不因苦難而喪失尊嚴的精神。回族學者馬梅萍在《西海固精神的負載者———論石舒清筆下的女人》中,梳理了西海固不同的女性形象,并指出贊母失父的潛在情緒構筑了西海固的群體人格:“西海固如一個自尊的未成年人一樣在憂傷中思索自我、探尋終極關懷”。回族評論家白草更是不吝溢美之詞,稱贊石舒清小說集《暗處的力量》是“一個精神充盈的價值世界”。精神價值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了作家的創作題材和描寫對象,石舒清小說的鄉土地域本色與宗教情懷使評論者集中在“堅忍”“自尊”“關于心靈、關于生命的‘詩意與溫情’”等這樣的概念闡發上。
對于陳繼明和金甌而言,他們小說所彰顯出的精神價值又是別樣的表現方式。陳繼明的小說側重于“在平庸的精神廢墟上尋找靈魂棲居的天堂”。陳繼明的小說也談生死,在他的長篇小說《一人一個天堂》之中,也寫到人物的死亡問題,但小說文本還原到歷史語境之中去描寫死亡,其意義就不是“終極關懷”這樣的概括所能界定的。由于潛在的政治話語所構成的文本內部的沖突,使得小說表現出一種解構與否定的精神,“《一人一個天堂》中的終極意味,就是取消終極”。陳繼明小說往往表現出不堪的現實圖景,但不堪只是表面,陳繼明積極努力正是要追問不堪現實圖景下人的救贖問題。學者趙炳鑫分析陳繼明的小說后得出“文學的精神和價值維度要有形而上的意義建構,要體現文學的終極命題:愛、悲憫、寬恕、拯救等”,而“愛、悲憫、寬恕、拯救”也正是陳繼明小說所反映出的精神價值。金甌的小說被李興陽在《中國西部當代小說史論》歸在“西部先鋒小說”之中,金甌的寫作受福克納、塞林格、菲茨杰拉德等美國先鋒作家的影響,他的小說表現出相當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真正的先鋒是精神的先鋒,李興陽認為金甌等作家是“西部最有先鋒精神的先鋒作家”。按照學者謝有順的說法:先鋒就是自由。金甌在小說創作中,追求的就是自由。只不過在具體的寫作中,這種自由的精神是通過敘事表現出來的。郎偉就指出金甌的小說《前面的路》“是一篇言說‘尋求自由’話題的小說”。金甌借鑒現代派的藝術表達方式,通過獨具特色的敘事方式追求自由化的精神價值。在評論者看來,金甌自由精神價值的建構是內化于小說的文本形式。但實際上,對于小說而言,形式與內容又是統一的。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指出:“只有內容與形式都表明為徹底統一的,才是真正的藝術品。”所以,細讀金甌的小說,那種“別一樣的敘事方式”與小說中的那些狂妄不羈的人物統一在一起,建構出了金甌所要表達的先鋒精神。
三、語言藝術的自覺與小說文體的審視
最近幾年,關于文學本體的討論一直不斷,原因就在于對文學認識上有眾多的分歧,有的作家與學者認為,文學一定要兼具社會學、哲學的意義才夠深刻,而有的則認為,文學畢竟是一門藝術,要盡量還原文學的藝術品質。其實,關于文學的多種認識都存在合理性。但不可否認,文學畢竟是一門藝術,一門審美藝術,更確切說是一門關于語言的審美藝術。汪曾祺先生就強調: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當下“作家論”的寫作日漸形成一種范式———“題材”“主題”“藝術特色”,因此藝術特色的研究是當下作家論研究的一個重點。同樣對于寧夏“三棵樹”的研究,也脫離不了這樣的常規范式。從藝術的角度看,寧夏“三棵樹”的小說確實呈現獨特的藝術面貌,形成各自獨有的藝術風格。作家張賢亮曾指出:陳繼明的文風是冷靜的客觀的,甚至克制的,他常常故意把戲劇性降到最低點,石舒清非常善于寫細微的東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滿了詩意和溫情,金甌的筆調則是極為強悍的、激越的。他們的風格不同,對他們的區分最終都是要通過他們的文本語言來實現的。石舒清在小說語言的加工上可謂頗具匠心,在石舒清的評論中,眾多論者都被石舒清的小說語言打動,在論者看來,石舒清的小說語言已經化為作家的一種自覺的藝術行為。申霞艷認為,石舒清的小說語言與內心世界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甚至語言能夠主宰人生的片段。“語言是通向內心的幽徑,語言呈現內心。每顆心都是一個世界,有什么樣的內心世界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語言什么樣的文學。語言暴露觀點,作者、敘事者和人物無一例外。”
由于對魯迅作品的執著偏愛,石舒清的小說語言不免受到魯迅的影響。達吾則指出“石舒清的語言越來越有了魯迅那種蒼涼荒疏的品質,暗藏的熱情,憫柔的憂傷,力透紙背的精確和不可復制的隱喻”。石舒清的小說“用平淡、質樸的語言,從不運用那些修飾性很強的語言”。這要分開來看,在石舒清小說的“日常敘事”中,語言風格一般比較平實,一旦卷入“死亡敘事”,語言則內斂沉郁,多暗示,多情味,富有張力。陳繼明的小說語言“平淡、清雅、舒緩而又具解析力、口語化”。有些小說如《青銅》,語言則顯得冰冷,似一種零度情感式的寫作。這是陳繼明在語言上的嘗試,麻木的語言背后是陳繼明一顆充滿溫暖的愛心。金甌的小說語言經過多年的摸索與調整,逐漸形成自己的語言特色。“金甌小說的語言運用正越來越強烈地呈現個人風格……讀者在其小說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想要追求一種潔凈、硬朗的語言風格特點,力圖在相當節制的敘述中傳達更為深厚的語言內涵,在有所遮蔽中釋放更多的能量。為此,他信手拈來‘陌生化’等語言手段,并且創造了一些佳句”。這是為數不多的對金甌小說的語言進行專門評論的文字。追求“陌生化”的語言表達,也是先鋒派作家常用的藝術技巧。
按照陶東風的定義,所謂“文體就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體的結構方式……文體是一個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根據文學創作的常識,一般創作成熟的作家都有著非常自覺的文體意識。寧夏“三棵樹”在長期的創作中,業已形成自己獨特的文體。文體也是眾多論者研究興趣的一個集中點。然而對論者而言,對文體特征的揭示并沒有形成專門的章節去加以深刻闡釋,因為小說文體的研究往往在藝術分析過程中得到零星的呈現。即便如此,對于寧夏“三棵樹”而言,其小說文體特征得到了相應的闡釋。論者普遍認為,石舒清的小說具有散文化詩化的特征,情節的淡化、敘述的抒情化、結構的散文化、小說思維的抽象化。獲魯迅文學獎的《清水里的刀子》更是集大成之作,體現出“簡潔中的豐富”。石舒清的文體深受現代鄉土文學的影響,尤其是廢名、沈從文等小說的詩化特征,在石舒清的小說中得到了繼承。另外,石舒清小說所表現出的“地域化鄉土風俗人情”的內容決定了其小說形式要相對舒緩詩化。論者認為,陳繼明的小說側重于心理沖突描寫,被稱為“陳繼明式的情緒騷動”。陳繼明的小說善于挖掘在當今社會現實下人物內心之間的心理沖突及隱秘的心理動機,所以陳繼明的小說在形式上更觀照人物的心理描寫。論者稱金甌的小說為“沒腦子”的小說,是因為金甌的小說帶有明顯現代主義風格,碎片化、寓言體、拼貼、陌生化等形式無疑不是現代主義常用的表達方式。在《雞蛋的眼淚》中的“寓言體”表達,在《前面的路》中的“陌生化”的語言,甚至在金甌的其他小說之中,先鋒的姿態決定了金甌的小說不會循規蹈矩,不會受現實主義的羈絆,于是在小說的形式上也呈現出先鋒的姿態。
四、文學批評的距離與歷史語境
近些年,隨著陳繼明離開寧夏遠走珠海,石舒清的小說寫作斷斷續續,精力多集中在隨筆的寫作上,金甌停筆后也已經逐漸淡出文學的視野。隨之而來的是,對寧夏“三棵樹”的關注度較之世紀初已經大大降低。前面的論述也是基于前期對他們的評論,縱觀這些評論文章,雖然有些文章表現出較為深刻的見解,但由于評論的圈子化、地域化問題,批評因缺乏必要的距離而流于平淡,這一點在域內論者對石舒清的評論中比較明顯。由于對民族文學有著濃郁的歷史認同感,所以面對批評對象時往往因民族情感上的認同忽視了必要的問題意識。在大量的論述中,幾乎找不到對石舒清創作進行批評的文字,究其原因是因為對批評對象的強烈認同而失去判斷能力。比如回族評論家白草是一個文本細讀的高手,對于張學東、季棟梁的某些小說都曾提出過批評,可是面對回族作家石舒清時,大都是贊美的文字。實際上,在對待自己本民族的文學文本及批評對象時,要在思維的理念和方法上拉開自己同本民族文化、文學精神的距離,以免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這時需要評論家作為一個“包廂里的觀看者”去對民族文學的文本及批評對象做出相對客觀、辯證、準確的闡釋。薩義德曾說:一個人離自己的文學家園越遠,越容易對其做出判斷。實際上,文學批評也是如此。
整合寧夏“三棵樹”的評論,還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大量評論沒有結合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去做出判斷。要么,論者拘泥于封閉的文本進行闡釋,從結構主義、原型批評等方法入手分析文本。要么,對文本進行社會學的批評,但在批評時卻離開真實而豐富的社會語境。從批評的理論資源來看,不談“現代性”是寧夏“三棵樹”評論的一個短板,沒有現代性的理論資源,使得評論缺乏應有的社會歷史語境。面對小說文本之中人的生存危機,評論往往陷入失語的狀態。因為論者沒有真正意識到小說文本內外的沖突,文本內的人是詩意的,有堅忍的精神和尊嚴,可是文本外的社會現實卻不是如此,也就是小說內的詩意人生與小說外嚴酷的社會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論者沒有借鑒現代性有效的理論資源對小說進行社會學意義上的審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論者的論述與作家的文本是契合的,但與社會現實卻是斷裂的。當然,對于評論者而言,還要取決于研究對象的豐富與深刻,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同時還要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讓文學批評真正成為闡釋性的批評,能夠把寧夏“三棵樹”的作品的價值最大化地闡釋出來。
作者:許峰 單位:寧夏社會科學院 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