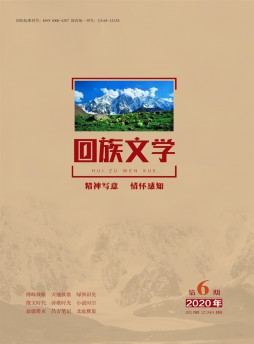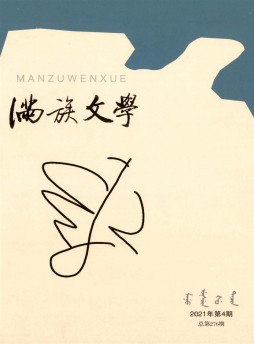文學閱讀式微文化語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閱讀式微文化語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引言
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徑,文學經典作品的閱讀,對于開啟心智、陶冶情操、提高審美修養更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眾文化生活的日益豐富,我國的國民閱讀率卻持續多年走低,即便是在閱讀,也多以消遣性讀物和時尚類期刊為主;于是,“閱讀危機”和“文學經典危機”的呼聲不斷現于各種媒體,不少人將其歸咎于世風浮躁、人心浮華。實際上,閱讀率下降、文學經典受到冷落絕不能簡單地歸咎到社會或個人,它的出現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消費文化的興起、媒介的積極介入、圖像的大行其道等都對這一現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消費文化的影響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起,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逐漸向消費社會過渡,尤其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物質生產力和消費力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此情形下,“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1]1。所謂“物的包圍”,不僅表現在商品種類和數量的極大豐盛,而且顯示為包圍消費者的商品是以整體的形式出現的,“它們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因為它們相互暗示著更復雜的高檔商品,并使消費者產生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動機。”[1]4這種“物的包圍”景觀強烈刺激著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誘惑著人們去不斷消費,在提高生活品質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生活態度、社會關系、價值理念等一系列的變化。與消費社會相伴而生的是消費文化,它是一種為消費行為尋找意義和依據的文化。為了贏得自身繁榮和強勢地位,它必須遵循市場和資本的邏輯,迎合世俗的道德標準、欣賞品味和思維習慣,制造時尚,激發消費欲望,以此占有大眾,贏得豐盈利潤。與生產型社會注重產品的物理性能、使用價值不同的是,消費文化更關注商品的符號價值與文化內涵,符號消費也因此成為消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1]48在符號消費的浪潮中,人們追逐著被制造出來的欲望,體驗著由此帶來的經濟地位、階層差異以及情趣、品位、現代、時尚等象征意義,沉迷于馬爾庫塞所批判的“虛假的需求”實現后的滿足與歡樂之中。“遵循享樂主義,追逐眼前的快感,培養自我表現的生活方式,發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這一切都是消費文化所強調的內容。”[2]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電視欄目《超級女聲》、《非誠勿擾》的受歡迎程度以及芙蓉姐姐、鳳姐、干露露等網絡人物的走紅中得到驗證。
消費文化的這些表征直接影響到受眾的審美情趣,尤其是在面臨著緊張的生活節奏和嚴酷的競爭壓力時,人們為了緩解精神焦慮,往往傾向于參與輕松、娛樂和休閑性的文化活動,滿足于感官享樂;于是,日常生活的各種事物和現象開始被藝術符號所統攝,成為技術操縱下的審美對象,這樣就構成了審美的泛化。審美泛化消弭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也對整個文化藝術市場形成了強烈沖擊,因為感官刺激代替了精神愉悅,符號消費綁架了審美過程,消費因素滲透到了文藝生產的機制深處,所有藝術產品的傳播都受制于商品邏輯的操控之下。在此情形下,“藝術商品自身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藝術也是商品,這并不新鮮,這一變化新就新在藝術心悅誠服地承認自身就是商品;藝術宣布放棄其自律性,并且能以能夠在消費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驕傲”[3]。而在這一蛻變的進程中,文學,這種歷來被視為人類精神家園守護神的藝術形式,面對著物欲至上、文化消費日趨多元化、淺表化和娛樂化的現實,也不得不黯然走下神壇,服膺商業規則,以市場的叫賣聲為指歸。于是,文學的場域開始分融,由此帶來文學生成與接受兩方面的巨大變化:從文學的生成角度看,作家的文學創作正在被出版商、發行商、寫作者等合謀的文學生產所僭越。文學創作本是一種極其復雜并帶有鮮明個性特征的精神勞動,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是作家殫精竭慮、窮畢生氣力之所作,它飽含了作家對生活的深層感悟,體現了作家對社會、人生的的嚴肅思考與終極關懷。然而隨著消費時代的來臨,一些嚴肅作家面對著人文知識階層社會地位的滑落、再加上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其創作精神也滑向了媚俗,為了迎合讀者的欣賞趣味,其作品不再表現宏大的文學敘事,也缺乏雋永意義的追尋,通過傳奇性、娛樂性、追逐欲望等的描寫來博得市場占有率。于是,“青春化寫作”、“欲望化敘事”、“美女作家”、“名人寫作”等大放異彩,在滿足了大眾獵奇、窺視欲望的同時,也獲得了暫時的名利雙收效果。而在此過程中,出版商、策劃人、銷售商的作用不容忽視,為了最大程度榨取文學的資本價值,他們一方面會以種種方式操縱作家的選題和寫作,另一方面會通過不斷制造、傳播新概念來達到對消費者文學趣味的控制。可以說,消費時代文學作品的出爐與暢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所操控的市場的引導和刺激,其中,市場策劃、創意與運作發揮著主導作用,而那些曾經追求自由創作的作家則淪為現代出版體制內的,成為文學批量生產線上熟練的裝配工。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矛盾現象:雖然我國目前每年有多達上千部看似厚重的長篇小說出版問世①,但真正的精品卻鳳毛麟角,因為文學的自主性早已湮沒于各具特色的消費符號和商業活動中了。
從文學的接受層面看,文學閱讀的氛圍正在被文學消費的潮水所稀釋,文學作品的閱讀者正在向文化產品的消費者蛻變。傳統的文學閱讀是讀者通過解碼文學語符獲取豐富內部意義、實現審美感悟與鑒賞的的過程,其影響范圍僅局限在社會精英階層內。而如今,以70至90后為主體的消費群體開始崛起為文學藝術的主要受眾,由于工作壓力、生活快節奏等多方面原因,他們在接受文學作品時,絕非陶然忘我的品鑒或嚴肅冷靜的反思,而是習慣于享受其中輕松愉悅的成分和作品里的流行時尚元素,把作品的意義深度削平,把文化藝術同生活直接對接。在他們眼中,文學不過是眾多可供選擇的、用來消遣的精神消費方式的一種,而消費又是表達自我欲望、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于是他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過程自然也就打上了很深的符號消費烙印。不僅如此,他們還不自覺地參與著文學消費的創造和推廣活動,這種參與性尤其體現在作家明星化、讀者粉絲化的時尚現象中:讀者充分配合媒體、作家和出版商,積極投身于文學產品傳播的互動與狂歡,卻未曾意識到早已身陷于媒介所策劃的預設程序中;據“紅袖添香”文學網站的一項調查顯示①,當前中學生對曾煒、郭妮、明小溪等新銳青春作家的瘋狂追捧遠超過對韓寒、郭敬明的喜愛,其狂熱的粉絲表現完全像是對明星藝人的追逐;而中學語文課本里涉及到的經典名家如魯迅、冰心則排名明顯靠后,至于學院派所推崇的其他嚴肅作家則根本就不在他們的興趣之列。這種現象一方面表明了青少年對流行文學的快速消費和消化能力,他們的閱讀興趣已迥別于前代,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傳統經典作家和作品的當代落寞與無奈。筆者以為,青少年對嚴肅文學的極端漠視,是否會引發他們人文素養的嚴重缺失十分值得人們關注。
三、媒介的作用
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一書中指出:“媒介即是訊息……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4]在他看來,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訊息”并非媒介所傳播的內容,而是不同時代傳播工具的改變所帶來的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化自身形態和整個社會生活面貌的改變。在口語媒介時代,最主要的文學形態是口耳相傳的歌謠,文學創作者即為文學的直接傳播者;當文字媒介出現后,獨立的詩人和作家代替了原先的口頭集體創作,而文學傳播也突破了口語媒介時送者(作者)和接收者(讀者)必須同時在場的時空限制,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隨著印刷媒介的發明和改進、尤其是隨著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大眾傳媒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顯示出其強大的滲透作用,在此情形下,文學作品必須借助于傳媒力量,通過機械復制和媒介的操控運作才能有效傳遞到文學受眾那里,實現其文學的消費價值。媒介對當代社會文化之所以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因為它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憑借自身優勢建立起了強大的話語霸權。首先,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賦予其話語霸權的可能性,它決定了哪些信息可以成為重要的、被關注的對象;其次,大眾媒介信息傳播表面上公開、客觀、公正的特點使其在受眾心目中建立起了權威形象。在媒介產業化的進程中,媒介積極介入到文學領域,憑借著對話語權的掌控,它一方面不斷制造文學消費熱點,迎合受眾心理,吸引受眾眼球,將原本正常的文學創作新聞化、事件化、娛樂化,另一方面將文學批評納入到它的運作邏輯,左右輿論導向,引導消費潮流,推動文學消費活動。不過媒介所關注、聚焦的“熱點”并非真正文學性的內容,而只是一些與文學沾邊的因素,“在媒介文學事件中,在媒體上進行‘表演’的主角不再是文學作品,甚至不是文學,而是作家,作家的性別、年齡、經歷、外貌、作家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等等,都成為了事件的‘主角’”。[5]于是,文學的崇高訴求被媒介所報道的“邊角料”所淹沒,“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6]4而受眾則在媒介的爆料與運作中不知不覺地消費著各種文化符號。在這種風尚的引領下,嚴肅文學作家和作品風光不再、備受冷落,而言情、武俠、玄幻、都市、懸疑、恐怖、搞笑類通俗文學作品則迅速火爆市場,整個文學場域充滿了濃重的商業氣息。
如果說大眾媒介對文學受眾和文學發展的影響只是單向的、缺乏及時反饋機制的話,那么網絡媒介和其它數字新媒體的崛起則是對施眾與受眾關系的根本顛覆。網絡媒介具有瞬間傳輸、交互性強、海量信息、多媒體等多種特征,文學與網絡的結緣不僅體現在用敲擊鍵盤移動鼠標代替傳統的執筆書寫和機械印刷、把紙媒存儲轉換成虛擬的賽博空間上,它更體現在為所有文學大眾提供了一個平等、自由、開放和包容的言說空間。在傳統的文化體制里,文學是作家、編輯和評論家們的專屬權利,普通文學受眾只有閱讀欣賞和膜拜的義務;但網絡卻是一個反中心化、非集權性的世界,它鄙視權威,消除等級,網絡文學的出現,為草根文學族群搭建了一個傾吐心扉、張揚個性、釋放情感的傳播平臺,使傳統作家對文學言說的壟斷被打破,社會精英和文化貴族的話語權力被分享,無等級的文學參與逐漸成為文化時尚。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學讀者在向網絡寫作者轉換的過程中,他們的文學素養是良莠不齊的,很多作品只是單純地表達感性愉悅和情感宣泄,寫作目的也多是為了展示自己、贏得喝彩,這些作品在追求技術的藝術化、在充分實現本雅明所說的機械復制藝術“展示價值”的同時,也失卻了有“韻味”藝術應具有的“膜拜價值”和本體的真實性①,“盡管它很忠實地復制出現實,但也正是在這種復制中,形象將現實抽掉了,非真實化了”[7];此外,網絡寫作者還喜好用詼諧搞笑的語言娛人自娛,拒絕深度,抹平厚重,淡化意義,逃避崇高,嘲弄典雅,調侃尊貴,在對詩學信念進行技術化演繹的過程中,肆意解構傳統的文學經典范式和文學價值理念,大話西游、水煮三國,許多曾在人們心目中占據不朽地位的文學經典被迅速通俗化并遭到破壞性地顛覆、戲說,由原本精神上的盛宴淪落為大眾即時消費、用完即棄的“文化快餐”,這樣就形成了“對宏大敘事的能指飄浮和審美邏各斯的消餌”[8],文學圭臬與經典在俗眾狂歡的瀆圣喧嘩聲中被拉下了神壇。
網絡媒介和其它數字新媒體的崛起不僅帶來了文學經典的祛魅,它們也對讀者的閱讀方式、閱讀習慣、閱讀心態乃至閱讀思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此引發了文學受眾閱讀范式的結構性變化。在傳統的紙媒印刷閱讀中,“閱讀文字意味著要跟隨一條思路,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6]67,它需要閱讀者縝密思索文本的意義領悟和道義承載,深度發掘閱讀對象的雋永寓意,正因為如此,波茲曼把印刷機流行美國的那個時代稱作“闡釋年代”,并認為“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6]83。而隨著網絡的普及和個人電腦、大屏幕手機、MP4、PDA、iPhone等新媒體的不斷涌現,讀者獲取文本和信息的方式也更趨多元化,這些數字新媒介在給受眾提供豐富、方便、快捷的閱讀信息的同時,也將閱讀方式帶入了讀屏時代。讀屏的信息是以比特為基本單位存儲于虛擬空間、它可以在不同數字媒介中自由復制、游移,使閱讀者可以通過復制、粘貼、超鏈接等多種方式獲取閱讀的自由選擇權。另外,相較于紙媒印刷閱讀通過靜觀獨處、沉思冥想獲取深邃的審美內涵來說,讀屏是一種能使閱讀者擺脫孤獨、帶來愉悅和松弛的方式,但同時它也很容易使自己在浩如煙海的信息海洋里迷失方向,難以實現知識的積累與意義的建構,最終導致閱讀者心態的浮躁、思想的淺薄和思維的惰性,因為在讀屏的過程中,“讀者不得不加快鼠標拖動的速度,用快速瀏覽取代閱讀印刷文本時的沉潛把玩。結果,讀者表面上讀完了一個文本,但實際上真正的閱讀活動卻沒有發生。因為讀者只獲得了某些信息,卻把伴隨著閱讀活動那種必不可少的沉思冥想丟在一邊。”
四、圖像的沖擊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在《可見的人———電影精神》里就預言了圖像文化的光輝前景:“另一種新機器將根本改變文化的性質,視覺表達方式將再次居于首位”[10]。如今,當我們留意身邊,會發現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各種類型的圖像:電影、電視、廣告、新聞圖片、電腦游戲畫面、手機視頻、數碼相片……圖像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自身在當今都已處于視覺成為現實主導形式的社會”[11]5。圖像時代的來臨必然引起人們對它的高度關注。早在古希臘時期,西方就有視覺中心主義的觀點,而在中世紀,基督徒破壞偶像的舉措恰好映射了這些人對圖像優勢的懼怕心理。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攝影、電影、電視等影像技術陸續誕生并對社會生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提出了“世界圖像時代”的理念:“從本質上來看,世界圖像并非意指一幅關于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12],居伊•德波分析了“景觀社會”的實質:“景觀不是附加于現實世界的無關緊要的裝飾或補充,它是現實社會非現實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聞、宣傳、廣告、娛樂表演中,景觀成了主導性的生活模式”;[13]此外,丹尼爾•貝爾、本雅明、杰姆遜、麥克盧漢、利奧塔等都從不同角度精辟揭示出圖像增殖對傳統紙媒社會帶來的深刻震蕩,而艾爾雅維茨則在前人探究基礎上,由衷感慨它給文學帶來的沖擊和擠壓:“在后現代主義,文學迅速游移至后臺,而中心舞臺則被視覺文化的靚麗輝光所普照”。[11]5
圖像之所以會對文學形成如此強烈的沖擊,首先在于它爭取受眾方面的先天優勢。“在文學性中,詩意的語言是最重要的,而語言所描述的對象則是無足輕重的”,[14]但“詩意的語言”往往具有模糊、抽象、不確定性的特點,有時還通過刻意追求形式上的陌生化來體現創作主體的審美訴求和對現實與世俗世界的精神超越,如此勢必會對接受者的受教育程度、藝術修養和想象力設置較高的門檻,限制它的傳播范圍;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文學接受上的障礙隨著消費文化的盛行會愈發突出,因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表征形式就是淺表化和平面感,它們構成了對傳統文學內在精神結構的抗衡與解構。而圖像則恰恰相反,它不強調有序排列而是呈空間并列,并以瞬間“爆炸”方式直接呈現在受眾眼前,能給受眾帶來整體上的強烈的視覺沖擊和眩暈力;這種形象直觀、具體可感、信息量大的視覺形象一方面使受眾擺脫了對艱深晦澀文字的依賴,賦予了不同階級、階層、文化素養甚至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受眾以相同的圖像閱讀資格和權利,另一方面也使當代處于“物的包圍”中的主體在瞬間被剝奪了進行判斷、思考的時空距離,在輕松愉悅的感性體驗中即可惰性地獲取追逐時尚與炫耀展示的平臺和途徑。所以,圖像在滿足受眾欲望消費和享樂過程中形成的視覺快感和情感體驗的同時,也使他們逐漸喪失了傳統上欣賞文學作品所需要的深度閱讀能力、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由此推動了從語言主因到圖像主因的視覺轉向。
圖像對文學的沖擊并不僅局限于此。隨著影像制作技藝的不斷進步和仿真技術、虛擬現實等的出現,圖像已經能給主體帶來身臨其境的當下感與參與感,這使很多人情愿相信事物的指代符號而不是事物本身,情愿相信復制品而不是原件,情愿相信幻象而不是真實,這種情狀就是鮑德里亞所謂的“擬像”。擬像完全背棄了表象對真實與真理的追摹,它不僅可以把現實而且還能把非現實對象化、直觀化;它沒有本原,沒有模仿的特定所指但卻可以無限復制、自我指涉;它是人為制造出來的漂浮的能指、表現為比真實更“真實”的超現實,而且這個超現實的世界“并不滿足與現實界并行、并列,而是試圖將現實納入其擬像的序列,將現實本身變成超現實的一個部分”。[15]這種癥候尤其體現在好萊塢風格的影視大片中,諸如《阿凡達》、《加勒比海盜》等,主人公在虛擬世界和現實存在中來回穿梭,讓觀眾如醉如癡于宏大而“真實”的視覺奇觀中不能自拔;此外,以暗示勸導為手段的情感訴求電視廣告、當前火爆熱播的選秀相親欄目、沉湎于虛擬網絡游戲帶來的身份認同困惑……這些視覺文化現象的背后都潛藏著擬像邏輯,貌似真實的背后掩蓋了現實的缺席,其能指游離于所指或是暴力性地糾纏在一起而凸顯其實質性的分裂。擬像無止境的創造、復制與泛濫模糊了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導致了藝術與現實生活距離的消失;而距離的消失,則意味著審美主體無法在心理上同實際生活世界保持適當距離、超越功利進行審美移情,這樣一來,傳統美學所標榜的“距離產生美”就失去了現實意義,因為“處處皆美,則無處有美,持續的興奮導致的是麻木不仁”[16];而審美主體對瞬間視覺快感、淺表化和碎片化形式的追求也導致了對美感凈化與超越的審美精神的漠視,于是文學的詩性暢想被放逐,圖像文化的視覺感知被放大,而其進一步后果就是文學價值、文學觀念、文學創作乃至整個文學場域的深刻震蕩和變異。
面對著圖像的強勢介入,文學的傳統闡釋與表現空間一再受到壓縮而不得不進行自適性變革。這種變化至少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文學作品的影視化轉換。為了爭取受眾,擴大知名度,越來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將自己作品影視化的隊伍中,一些作家如周梅森、劉恒等甚至身兼編輯、導演的身份,還有一些作家如海巖等則熱衷于影視同期書的編寫與傳播,為自己創造名利雙收的效益。二是文學文本的圖像化包裝。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無論是圖書還是期刊,都特別講究裝幀藝術,對文本的形態、用料和制作等進行精致的設計,尤其配以新奇、精美、富有視覺震撼力的圖片,以吸引受眾眼球。三是文學敘事的圖像化表征。受創作意圖、傳播方式等多方面影響,文學敘事的視覺化傾向也越來越明顯,不少作家依據影視劇本的規范,注意場景交代,注重畫面和時空轉移,情節跌宕起伏,追求蒙太奇效果,并大量運用意識流、零度敘述、生活流敘事等手法以增強文本表達的視覺效果。應該看到,文學的圖像化只是它面對著圖像咄咄逼人態勢的一種無奈之舉,它在暫時為作家、作品帶來聲譽的同時,弱化了對作品結構藝術的探求,忽視了對復雜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和對主體精神境界的建構。為了迎合大眾趣味,文本的影視化、圖像化往往不惜損傷原作的個性與深度,將原作修改得面目全非。更有甚者,一些新銳作家為了賺取噱頭,刻意進行身體寫作,赤裸裸地顯示對性和物欲的渴望,通過私密、走光、肉感的身體展示刺激著讀者的窺探欲望,這或許是文學圖像化過程中最不幸的表現吧。
五、余論
上世紀80年代,我國曾掀起過一次全民讀書熱的高潮,每一個文學青年都能為自己擁有心儀的文學名著而魂牽夢縈。然而從90年代后期延續至今,很少有作品能再一次真正觸動到讀者的心靈并引發廣泛的社會反響,文學失去轟動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過程中,消費文化的盛行、媒介的強勢介入以及圖像霸權深刻地改變了文學的創作精神、作品內容、文學批評、閱讀方式、審美心理、運作模式、場域等,進而逐步造成了文學中心地位的旁落和邊緣化。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無意于渲染文學終結論的思想,因為文學的內視性想象和對存在詩意的內在體驗確實可以使人超越感性空間的束縛、獲得時間的永恒性并進而獲取對人本身信仰和超越現實生存的精神力量,這也是在一個符號化、碎片化、淺表化的感性時代,文學能夠得以繼續存在的根本原因。[17]但如果據此就罔顧文學閱讀的式微和文學經典正在祛魅的事實、抱守“文學是語言藝術”的信條而不肯對文學做出與時俱進的闡釋,甚至認為只有純文學刊物上的作品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為此不惜扮演悲壯的守望者角色,那么文學或許會真的走向衰落。文學是永存的,但文學的秩序已發生改變,消費時代、媒介時代和圖像時代的來臨使文學呈現出嶄新的特征,如與影視的親密結合、泛文學文本的大量產生等,這一方面說明文學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高度重視和研究文學新的內在規定性及其外在表現形式,為文學的返魅創設契機。[18]就文學閱讀而言,如何協調讀圖時代“快、輕、淺”和工業時代“慢、重、深”之間的矛盾、“懂得快中求慢、輕中有重、由淺入深的道理”就成了當前需要迫切解決的一個問題。[9]148借用J•希利斯•米勒的一句話作為結束語:“文學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溝溝坎坎、因特網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雖然從來生不逢時,雖然永遠不會獨領風騷,但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網之星系上的黑洞———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