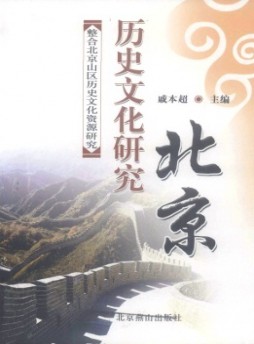緣情綺靡歷史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緣情綺靡歷史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歧說紛紜:“緣情綺靡”的歷史評價(jià)
清代以降,唯有少數(shù)學(xué)者對“緣情綺靡”持贊賞的態(tài)度,如毛先舒《詩辯坻》曰:“古人善論文章者亦有自攄獨(dú)欣,不可推放眾制者,如子桓‘詩賦欲麗’,士衡‘綺靡’、‘瀏亮’語是也。”[5]71表現(xiàn)出獨(dú)到的審美眼光。大部分學(xué)者則幾乎全部集中在批判上,如紀(jì)昀《云林詩抄序》曰:“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繪畫橫陳,不誠已甚歟?”[6]537雖拈出“緣情”二字,批評點(diǎn)卻在“綺靡”,認(rèn)為“緣情綺靡”造成了詩歌雕繪滿眼,缺少誠摯的情感。朱彝尊《與高念祖論詩書》亦曰:“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dá)之意,惡在其為詩也。”[6]283將六朝浮艷文風(fēng)完全歸罪于“緣情綺靡”的誘導(dǎo)。這種批評實(shí)是明人批評“緣情綺靡”所造成六朝詩歌流弊的引申發(fā)揮。比較而言,沈德潛的批評則直入本質(zhì)。其《說詩晬語》曰:“‘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涂澤,先失詩人旨。”[5]532《古詩源》也重申這一觀點(diǎn),認(rèn)為陸詩“詞旨敷淺,但多涂澤”,“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fù)存矣”。[7]133將陸機(jī)理論與創(chuàng)作聯(lián)系考察,認(rèn)為“緣情”本未可非,然追求“綺靡”,描摹物色雕繪,致使喪失了“空靈矯健之氣”。雖未必切合陸機(jī)理論的本意以及創(chuàng)作的特點(diǎn),但所闡釋的理論卻是正確的。論“緣情”,近代學(xué)者或以為與“言志”無涉。如朱自清《詩言志辨》認(rèn)為,“陸機(jī)《文賦》第一次鑄成‘詩緣情’這個新語,是‘詩言志’以外的‘一個新目標(biāo)’”[8]35。周汝昌也認(rèn)為:“陸機(jī)本意之與‘言志’,與‘閑情’、‘艷情’、‘色情’并無干涉按陸機(jī)本意,‘緣情’的情,顯然是指感情,舊來所謂‘七情’。”[9]58-65認(rèn)為陸機(jī)所言之情,是指緣諸人之生命的喜、怒、憂、懼、愛、惡、欲之情,既與傳統(tǒng)的“言志”之志不同,也與一般表達(dá)情色的詩歌不同。早期朱東潤《中國文學(xué)批評大綱》,后來李澤厚、劉綱紀(jì)《中國美學(xué)史》等基本上都持這一觀點(diǎn)。或以為“緣情”“言志”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如裴斐《詩緣情辨》認(rèn)為,言志論本身就包含著緣情的觀念。言志論不僅充分認(rèn)識到詩的緣情特征,并且指出了情之所生的客觀依據(jù)。“緣情論既脫胎于言志論,又是對它的否定”,即繼承了先秦詩論家所揭示的詩的緣情特征,否定了以志抑情的詩教觀念,“于是,在緣情論里‘志’與‘情’便不存在矛盾,成了一個東西,很難以加以分別”[10]13-22。詹福瑞《“詩緣情”辨義》從內(nèi)涵與外延上闡釋了二者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詩言志’是志中含情,‘詩緣情’則是情中有志。漢儒說《詩》,用以補(bǔ)充‘詩言志’的情,主要指世情,且多群體之情;而陸機(jī)‘詩緣情’的情,主要是物感之情,多指詩人一己之情。”[11]64-65情與志互相包蘊(yùn),然而漢儒說《詩》,具有強(qiáng)烈的社會性,陸機(jī)言情則帶有強(qiáng)烈的主體性。論“綺靡”,或分而言之,認(rèn)為“綺靡”是同義復(fù)詞,如20世紀(jì)30年代陳柱在《講陸士衡〈文賦〉自記》中明確指出:“綺言其文采,靡言其音聲。”[12]周汝昌亦有類似的論述;或合而言之,認(rèn)為“綺靡”是一個詞,如20世紀(jì)60年代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史參考資料》注曰:“綺靡,猶言侈麗、浮艷。”[13]261近年出版的幾部文學(xué)批評或文學(xué)思想史著作亦有近似論述,如《中國詩論史》說:“‘緣情’為‘意’,‘綺靡’為文。”[14]202《中國文學(xué)批評通史》曰:“‘詩緣情而綺靡’一語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用‘緣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沒有提出‘止乎禮義’,而強(qiáng)調(diào)了詩的美感特征。”[15]102似乎都以整體意義為著眼點(diǎn)的。以上論述,無論是論述“緣情”與“言志”的關(guān)系,或從詩學(xué)發(fā)展上說,或從范疇外延上說。還是論述“綺靡”,或指語言精妙,或指整體風(fēng)格;或以為是一個詞組,或以為是一個單詞,在筆者看來,似乎都還沒有觸及問題的深層本質(zhì),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二、“緣情綺靡”:詩歌發(fā)生的審美機(jī)制
研究“緣情綺靡”的理論內(nèi)涵,首先,厘清“緣情”“綺靡”的語詞意義及其作為詩學(xué)范疇的理論內(nèi)涵;其次,必須合理闡釋“情”與“志”的關(guān)系。本文基本觀點(diǎn)是:“緣情”是從詩歌發(fā)生的角度說,是詩歌發(fā)生的審美機(jī)制;“言志”是從詩歌表現(xiàn)的角度說,是詩歌表現(xiàn)的審美狀態(tài),二者屬于不同層次的詩學(xué)范疇。先說“緣情”。人們習(xí)慣于將“緣情”與“言志”對比論述,爭論的焦點(diǎn)不外乎是內(nèi)涵的界定以及二者的內(nèi)在關(guān)系。這實(shí)在是一種思維視角上的誤區(qū)。其實(shí),“詩緣情”是說詩緣情而生,從詩歌發(fā)生的角度闡釋詩歌的特征;“詩言志”是說詩表達(dá)情志,是從詩歌表現(xiàn)的角度描述詩歌的特征。二者是分屬不同的邏輯層次,有著本質(zhì)的差異。緣情之“緣”意即因緣。“緣情”的意義不是抒情,而是因緣于情。考其字義,則雖生于中土,卻與佛教之“格義”關(guān)系密切。《說文》:“緣,衣純也。”即衣服的邊飾。引申為順、沿著。《莊子山木篇》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玄英注:“緣,順也。”漢桓寬《鹽鐵論刑德》所言之“緣人情”,也是指順乎民情,與魏晉之“緣情”意義亦不同。然《漢書藝文志》之“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乃有因由、依緣之意,與“緣情”之緣意義相近。但是,從歷史文化語境上看,陸機(jī)提出“緣情”說,正是佛教“格義”盛行之時(shí),也是佛教開始全面向士大夫思想意識滲透之時(shí)。因此,緣情之“緣”不可能不受佛教“格義”之影響。而佛教之“緣”即是“格義”的產(chǎn)物,既取漢代之因由、依緣之意,又包含著特定的佛教意蘊(yùn)。佛教之“緣”有二義:一是因緣之緣,指事物之間相關(guān)聯(lián)的因果關(guān)系;二是緣慮之緣,是心緣外境而生識的因果關(guān)系。在佛教中,“緣”又是“緣因”之略。緣因就是二因,亦有二義:一是生因和了因。生因是能夠產(chǎn)生果實(shí)的本源,如物種生芽,芽生果實(shí);了因是以智慧透視事物的原理,如燈照物,了了可見。二是正因和緣因,正因是主要的因,緣因是助緣(次要)的因。若依佛教對“緣”的闡釋,“詩緣情”則是說詩因緣于情——由情而生;情因緣于境——因物而感。故《文賦》曰“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思?xì)w賦》亦曰“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從詩歌發(fā)生學(xué)上看,情是因,詩是果。情亦包含智慧感悟之物理,與“道”同生;詩亦為智慧物理之載體,亦可以明“道”。故《嘆逝賦》曰“樂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文賦》曰“理扶質(zhì)以立干,文垂條而結(jié)繁”,《遂志賦》又曰“作詩以明道述志”。由此可見,在詩學(xué)意義上,“緣情”之情是情、志、理的三者統(tǒng)一。后來,蕭統(tǒng)《同泰僧正講詩序》曰:“大正以貞俗兼解,郁為善歌;璉師以行有余力,緣情繼響。余自法席既闌,便思和寂。”說明佛教徒頌經(jīng)開講之余,緣情而作,以發(fā)抒佛理。其詩亦曰:“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伊予寡空智,徒深愛怯情。”則是對緣情說的佛理闡釋。次說“綺靡”。從語詞上說,“綺靡”在魏晉時(shí)期并非聯(lián)綿詞,而是一個雙音節(jié)詞。由于“綺靡”同另一聯(lián)綿詞“猗靡”音形皆近,遂至誤用,后來“綺靡”才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聯(lián)綿詞,因此造成今人理解上的困難。“綺靡”之“綺”,《說文》:“綺,文繒也。”《六書故工事六》:“織采為文曰錦,織素為文曰綺。”亦即以素為底色,織以文彩,這似乎已成共識。問題在于“靡”究竟如何索解?周汝昌引《方言》卷二曰:“纖,繒帛之細(xì)者謂之纖,東齊言布帛之細(xì)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靡,細(xì)好也。”如果依照《方言》所言,確如周汝昌所言:“‘綺靡’連文,實(shí)是同義復(fù)詞,本義為細(xì)好。”然而郭璞解為“細(xì)好”——細(xì)而美,似應(yīng)是形容詞,而不再是繒、綾之名,其間透出了從漢至?xí)x的語詞變化信息。其實(shí),綺、靡二字到了魏晉以后,由原來的名詞轉(zhuǎn)化為形容詞。漢人所言之“靡”固然義項(xiàng)豐富,但是以“靡”形容聲音之悅耳,亦為常用義。如東方朔《答客難》:“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靡耳”顯然是指聲悅于耳。這從后來的《文心雕龍》也可得到證明:“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矣”(《樂府》),“晉世群才,稍入輕綺”(《明詩》)。顯然,劉勰所言之“靡”指音調(diào)的圓潤連貫,“綺”指文辭的華美綺艷。可知,“綺靡”二字是并列結(jié)構(gòu),而非同義復(fù)詞,更不是聯(lián)綿詞。這在《文賦》中也可找到內(nèi)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綺”喻色彩清麗;“或寄辭以瘁音,言徒靡而弗華”,“靡”指音調(diào)宛轉(zhuǎn)。故陳柱曰:“綺言其文采,靡言其音聲。”《文心雕龍》多次連用“綺靡”,如“結(jié)藻清英,流韻綺靡”(《時(shí)序》),“《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辨騷》)。“綺靡”連用,其意有三:一指色彩華美,如班婕妤《搗素賦》:“曳羅裙之綺靡,振瓊佩之精鳴。”二指音韻和諧,如阮瑀《箏賦》:“浮沉抑揚(yáng),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所為。”三指情感縈繞,如阮籍《詠懷詩》:“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從《文賦》看,既指文辭與音韻,也包含情感在內(nèi)。其后謝靈運(yùn)《曇隆法師誄》所說的“繁弦綺靡”,則主要從音韻與情感著眼。概括言之,“緣情綺靡”,闡釋了詩歌發(fā)生與情感表達(dá)的關(guān)系,也揭示了詩歌風(fēng)格的一般性審美特征。再說“緣情”與“言志”。由上所論,“緣情”與“言志”并非一個邏輯層次上的范疇,因此本文并非從詩學(xué)范疇上論述二者關(guān)系,而是從構(gòu)成這一詩學(xué)范疇的主要元素上論述“情”與“志”的關(guān)系。先秦時(shí)期,情、志是同源字,二者意義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王運(yùn)熙等說:“‘詩緣情’的說法,實(shí)際上與傳統(tǒng)的‘詩言志’、‘吟詠性情’有著繼承關(guān)系,都將詩視為作者內(nèi)心世界的表現(xiàn)。先秦時(shí)所謂‘言志’之‘志’,本來不是不包含感情的,但當(dāng)時(shí)人對于詩抒發(fā)情感、以情動人的特點(diǎn)缺少自覺。”[15]101毫無疑問,先秦所說的“志”,包含著情。《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孔穎達(dá)《正義》曰:“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16]1454六志即六情:好惡喜怒哀樂。然而先秦的“志”比“情”內(nèi)涵更為豐富。《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在心為志”與“情動于中”意義基本相同,因?yàn)椤对姶笮颉酚謴?qiáng)調(diào)“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才導(dǎo)致后人諸多誤解。魏晉以降,情、志幾乎成為同義詞,二者在內(nèi)涵與外延上也幾乎互相疊合。以拙著《陸士衡文集校注》所收篇目統(tǒng)計(jì),陸機(jī)用“情”字共出現(xiàn)67次,除去“情欲”1次、“人情”1次、存疑作品《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3次之外,尚有62次;“志”共出現(xiàn)47次,除去“志士”6次、存疑作品《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3次之外,尚有38次。二詞意義幾乎完全疊合,如《遂志賦》序曰:“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志與情顯然同義,否則就無法解釋“志壯而泛濫”。情、志作為同義復(fù)詞連用,在漢魏相當(dāng)普遍,如蔡邕《釋誨》“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嵇康《琴賦》“可以導(dǎo)養(yǎng)神氣,宣和情志”等,都能說明這一問題。如果糾纏于情、志內(nèi)涵與外延上差別實(shí)在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情志合一的詩學(xué)觀念,也使陸機(jī)詩學(xué)有強(qiáng)烈的儒家詩教的思想傾向。梅運(yùn)生先生指出:“陸機(jī)要求包括詩賦在內(nèi)的十體文章‘亦禁邪而制放’,也就是要止乎禮義,設(shè)了禮義的大防。‘詩緣情而綺靡’與‘亦禁邪而制放’是互相銜接的完整的命題,比起《毛詩序》所論‘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命題,有了重要的豐富和發(fā)展,但無本質(zhì)意義上的區(qū)別。”[14]148《文賦》曰:“佇中區(qū)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shí)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遂志賦》又曰:“作詩以明道述志。”可見,“緣情”與“明道述志”,是陸機(jī)強(qiáng)調(diào)的并行不悖看似二而實(shí)為一的詩學(xué)原則。所不同的是:前者強(qiáng)調(diào)詩的發(fā)生,后者強(qiáng)調(diào)詩的表現(xiàn)。所以陸機(jī)所言之志,以道為骨,以情為氣,而且情志一也。他強(qiáng)調(diào)“頤情志于典墳”,典墳,孔安國《尚書序》曰:“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17]4頤養(yǎng)高潔情志,一旦發(fā)諸詩,必然是意蘊(yùn)深厚,志氣充沛,情思濃郁。“理扶質(zhì)以立干”正是其警策的描述。所以錢謙益《增城集序》曰:“緣情綺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18]958雖然也混淆了詩歌發(fā)生與詩歌表現(xiàn)之差別,但論情志之關(guān)系則是正確的。上文已引,沈德潛認(rèn)為,“緣情綺靡”不僅“言志”——抒情,而且“章教”——彰顯儒家詩教。可見陸機(jī)詩學(xué)也是以儒家詩教為理論基石的。然而陸機(jī)所言之“理”不唯包含“道”,亦且包含四時(shí)之嘆、瞻物之思、人生感悟、中區(qū)玄覽等沉積于情感深處的思想理性。這種詩學(xué)思想又受荀粲“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yùn)而不出矣”[19]320之類的玄學(xué)思維影響。簡言之,“緣情”是詩歌的發(fā)生過程,“綺靡”是詩歌的審美特征;“緣情”是情、志、理的統(tǒng)一;“綺靡”是文辭、音韻、情感的統(tǒng)一。補(bǔ)充說明的是,陸機(jī)《羽扇賦》“夫創(chuàng)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憲靈樸于造化,審真則而妙觀”,既強(qiáng)調(diào)由樸至妍的文學(xué)進(jìn)化觀,又強(qiáng)調(diào)憲法自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觀。與“緣情綺靡”的理論內(nèi)涵是一致的。
三、“緣情綺靡”生成的歷史文化語境
從佛教語言上說,解釋“緣情”之緣為因緣之緣、緣慮之緣,是否悖離了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文化語境?從審美風(fēng)格上說,“綺靡”是西晉詩風(fēng)的基本特點(diǎn),與佛教有無關(guān)聯(lián)?要解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將“緣情綺靡”放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闡釋。從陸機(jī)現(xiàn)存的作品看,似乎很少受佛教影響。以儒為根,徘徊于儒道之間,是其詩學(xué)思想的基本特點(diǎn)。但是,并不能說陸機(jī)詩學(xué)與佛教沒有絲毫關(guān)聯(lián)。佛學(xué)發(fā)展到魏晉,逐漸為士大夫所接受。朱士行毅然出家皈依佛門,并西渡于闐取回真經(jīng);曹植熟悉梵唄經(jīng)聲,并應(yīng)用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即為明證。陸機(jī)早年生活在一個佛教氣氛極為濃郁的東吳,維祗難、竺律炎、康僧會都是在東吳傳播佛教的高僧。康僧會影響尤其深遠(yuǎn),《高僧傳》本傳載:康僧會世居天竺,后隨父移居交趾。出家后,受業(yè)于著名佛教翻譯家支讖弟子支亮。“博覽經(jīng)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xí),遍學(xué)異書,通六國語。漢獻(xiàn)末亂,避地于吳。孫權(quán)聞其才藝,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dǎo)東宮,與韋曜(昭)諸人共盡匡益。”僧會于赤烏十年(247)到達(dá)建鄴,設(shè)像傳道,“由是江左大法遂興”。后來孫皓又“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并就僧會受戒,“宣示宗室,莫不必舉”。康僧會特別善于援引儒學(xué)經(jīng)典以闡釋佛教義理,如對孫皓曰:“夫明主以孝慈訓(xùn)世仁德育物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于隱,鬼得而誅之;為惡于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余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xùn)。”[20]14-18這種融合儒佛的釋經(jīng)方式,促進(jìn)了佛教在江南士大夫中的傳播。陸機(jī)青壯年時(shí)期都是在這樣佛教濃郁的地方中度過的。太康末,陸機(jī)入洛,洛陽也是佛教隆盛之地。譯經(jīng)豐富,寺廟林立。西晉譯經(jīng)達(dá)165部之多;《洛陽伽藍(lán)記序》記載,“至于晉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21]4。歷經(jīng)戰(zhàn)亂,尚有如此之多的寺廟,可以推想元康之前佛教的盛況。佛教信仰也開始滲透于士族之間。與陸機(jī)同時(shí)的周嵩“精于事佛”,石崇“奉佛亦至”,名僧支孝龍與阮瞻、庾敳等“并結(jié)知音之友”。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佛教語言滲透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進(jìn)而影響詩學(xué)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由蜀入洛的李密所作《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就是典型的佛教用語。而且由“人亦有言”句看,“有因有緣”的佛教用語已經(jīng)傳播相當(dāng)普遍,成為習(xí)見的口語。而且錢鍾書《管錐編》一三八則解陸云“文適多,體便不清”曰:“適,倘若也。”又補(bǔ)注曰:“晉人譯佛經(jīng)中常用‘適’,義與陸云同。”[22]1862也可說明佛教與文人用語的互相滲透。如前所論,“緣情”之類的意義表述雖在漢代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作為一個固定的詞語,卻不見載于漢前典籍,至魏晉而大行,如袁準(zhǔn)《袁子正書》、潘岳《寡婦賦》、徐邈《答曹述初問》、徐廣《答劉鎮(zhèn)之問》等都用過“緣情”一語,可見已經(jīng)成為魏晉以來的流行之語。其后法琳《對傅奕廢佛僧表》、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蕭統(tǒng)《同泰僧正講詩》等,直接將“緣情”一語引入佛理闡釋之中,這也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了“緣情”與佛教有密切的聯(lián)系。西晉詩風(fēng)以“綺靡”為主要審美傾向。《文心雕龍明詩》曰:“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又《時(shí)序》曰:“晉雖不文,人才實(shí)盛。茂先揺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lián)璧之華,機(jī)、云摽二俊之采;應(yīng)、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并結(jié)藻清英,流韻綺靡。”“結(jié)藻清英,流韻綺靡”,是西晉抒情詩歌詞采、音韻的基本特點(diǎn),從而構(gòu)成了西晉詩歌“輕綺”的美學(xué)風(fēng)格。鐘嶸《詩品》亦稱陸機(jī)詩歌“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可見,從理論上抽象出“緣情綺靡”的詩學(xué)思想,既是陸機(jī)對西晉詩風(fēng)的概括,也是自己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總結(jié)。然而,追求“綺靡”的審美傾向,亦非止于西晉文士,早期佛經(jīng)之翻譯、傳播亦有“綺靡”的傾向。天竺佛經(jīng)語言藻麗,音韻流靡,早期譯者頗以“失其藻蔚”為憾。鳩摩羅什《西方辭體論》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jīng)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23]2405重文制、音韻,求辭藻蔥蔚是天竺文體的重要特征。譯梵為漢,往往只能譯其大意,而文體殊隔。因此,“尚質(zhì)”抑或“尚文”成為困擾著早期佛經(jīng)翻譯家的重要問題。然而,追求“尚文”卻成為早期佛經(jīng)翻譯的主流傾向。支敏度《合首楞嚴(yán)經(jīng)記》曰:“(支)越才學(xué)深徹,內(nèi)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shí)好簡略,故其出經(jīng),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24]270支讖授學(xué)于支亮,支亮授學(xué)于支謙(又名越),支謙授學(xué)于康僧會。支謙譯經(jīng)“尚文”,“頗從文麗”,道安甚至引莊子之喻,批評其譯文是“斫鑿之巧者也竅成而混沌終矣”[24]290。康僧會的譯經(jīng)風(fēng)格必然受支謙影響。《高僧傳康僧會傳》載:“會于建初寺譯出眾經(jīng)并妙得經(jīng)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jīng),并制經(jīng)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并見于世。”[20]18也就是說,僧會譯經(jīng)妙得天竺文體,辭義允正,且又傳梵唄之聲,音韻“清靡哀亮”,竟成“一代模式”,可見影響之大。而其注經(jīng)所作的序論,也辭趣雅潔,意旨繁富。從支謙到康僧會實(shí)際上逐漸形成了“綺靡”的譯經(jīng)風(fēng)格。這也必然影響東吳文風(fēng),陸機(jī)浸染其中,亦必受其影響。只是史料闕如,難以確考而已。無論是梵漢文體殊隔,還是在翻譯中有“尚質(zhì)”“尚文”之別,但是佛經(jīng)本身的特點(diǎn)必然對佛經(jīng)翻譯有潛在的規(guī)定性。早期佛教并非僅僅以只言片語開啟人心,反復(fù)申說,舉譬設(shè)喻,也是其特點(diǎn)之一。加之梵唄的清靡哀亮,也使佛經(jīng)本身呈現(xiàn)出繁縟“綺靡”的風(fēng)格。支讖所譯的《道行般若經(jīng)》這種特點(diǎn)尤為明顯,如卷五《分別品》:“說諸法空,是亦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諸法空,諸法無有想,諸法無有處,諸法無有識,諸法無所從生。諸法定,諸法如夢,諸法如一,諸法如幻,諸法無有邊,諸法無有是,皆等無有去異。”[25]631以無來、無去、無想、無識、無處、無生,周遍一切,無有差別,闡釋“自性空”不生不滅的特點(diǎn),形成了意旨繁縟的特點(diǎn)。而且以如夢、如一、如幻為喻,運(yùn)用一系列排比、對偶的修辭句式,也形成了綺靡的語體風(fēng)格。佛經(jīng)中還常以綺麗鋪陳的筆觸描寫佛國的境界,如上書卷九《薩陀波倫菩薩品》所描繪之犍陀越國:“皆以七寶作城,其城七重,其間皆有七寶琦樹;城上皆有七寶,羅縠緹縵,以復(fù)城上;其間皆有七寶交露垂鈴。四城門外,皆有戲廬。繞城有七重池水;水中有雜種優(yōu)缽蓮華、拘文羅華、不那利華、須犍提華、末愿犍提華,皆水池中生。犍陀越國諸菩薩,常共恭敬曇無竭,為國中央施高座,隨次轉(zhuǎn)下施座,中有黃金座、白銀座、琉璃座、水精座;座皆有雜色文繡婉,座間皆散雜種香花,座上皆施雜寶交露之蓋;中外周匝,皆燒名香。”寫城上七寶琦樹、羅縠緹縵、交露垂鈴已是目不暇接;池中種種蓮花也是風(fēng)光滿眼;佛座之華貴精美、文繡之婉流光、奇花之香艷雜陳、珠寶之交露覆蓋,再加之香霧繚繞,彌漫周遭,更使人目亂心馳。鋪陳描寫,色彩繽紛,香羅綺澤。且多以短句為主,或連用平聲,或連用仄調(diào),極盡“綺靡”。若比較西晉酬贈應(yīng)制之詩,其格局、筆法都投映著佛教的影響。西晉詩風(fēng)的意旨繁縟,并非僅僅受賦體影響,也有佛教影響的元素;風(fēng)格綺靡,不惟是西晉詩風(fēng)的特點(diǎn),也是天竺佛經(jīng)的特點(diǎn)。許里和指出,系統(tǒng)地翻譯佛典,“標(biāo)志著一種文學(xué)活動形式的開始,而從整體上看來,這項(xiàng)活動必定被視為中國文化最具影響的成就之一”[26]46。一個時(shí)代的詩學(xué)是多元文化交融疊合的產(chǎn)物,如果僅僅從中國詩學(xué)發(fā)展史上追尋陸機(jī)詩學(xué)范疇的生成,而忽略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顯然是以線性的思維替代了開放的思維,其結(jié)果必然無法揭示詩學(xué)生成的文化多元性。誠然,西晉時(shí)期,佛教思想并不像東晉那樣深入文人的心底,但是佛教文化的語言、風(fēng)格,卻成為影響西晉文人的重要因素。這既符合對外來文化接受的一般規(guī)律,也可以從西晉詩學(xué)中尋出一些蹤影。李密的詩、“緣情綺靡”詩學(xué)范疇的產(chǎn)生,都與佛教有絲絲縷縷的聯(lián)系。
四、“緣情綺靡”的詩學(xué)史意義
陸機(jī)“緣情綺靡”的提出,也是詩學(xué)發(fā)展的必然。曹丕“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是詩歌緣情的具象描述;“詩賦欲麗”,是詩歌綺靡的抽象表述。雖然如上文所論,漢儒所言之“志”也包含“情”,卻又比“情”內(nèi)涵寬泛。“情”偏于感性,緣諸生命的沖動;“志”偏于理性,緣諸文化的積淀,所以才強(qiáng)調(diào)“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突破漢儒詩教理性的限制,承認(rèn)緣諸生命沖動之情的合理性是在建安時(shí)期。這種思想的解放建立在兩個前提下:一是“人的覺醒”。文人在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同時(shí),也開始關(guān)注自我,從而確立了主體意識。而只有社會對人的主體意識有更多的認(rèn)同感和包容度時(shí),緣諸生命的沖動之情才可能在文學(xué)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二是“文的自覺”。當(dāng)文人真正認(rèn)識到文學(xué)不僅具有教化、認(rèn)識功能,也具有審美、娛樂、宣泄情感的功能時(shí),緣諸生命沖動之情才真正能在文學(xué)作品中真實(shí)地流露來。建安時(shí)期,雖然等級壁壘在政治體制中沒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但是鄴下文人的主體意識色彩卻非常濃郁。建安時(shí)期所崇尚的主體“通脫”,既是一種行為特征,也是一種生命情懷。只有擺脫了儼然夫子、拘拘于儒的行為與心理,才能自由地發(fā)抒性情,才能在文學(xué)作品中自由地書寫緣諸生命的沖動。曹丕《又與吳質(zhì)書》所說的“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就完全擺脫了等級壁壘的桎梏,表現(xiàn)出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特別是“酒酣耳熱,仰而賦詩”,一任緣諸生命沖動之情的自由抒發(fā),即如李白“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俠客行》),表現(xiàn)的是一種生命的本真,才真正達(dá)到了“緣情”的境界。只要翻閱一下阮瑀、陳琳《止欲賦》,王粲《閑情賦》,應(yīng)玚《正情賦》,繁欽《抑檢賦》,曹植《靜思賦》等,就可以約略看出。這些作品絕少禮教大防的意識,如陳琳《止欲賦》全是寫美人“色曜春華,艷過碩人”的容貌,“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的相思;曹植《靜思賦》除表現(xiàn)美人容貌艷冶之外,也表達(dá)“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求之不得的哀傷;只有阮瑀《止欲賦》加上一條“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的尾巴,似乎有所克制。其實(shí),“文以氣為主”(曹丕《典論論文》),突出作家創(chuàng)作與風(fēng)格的個性;“人各有所好尚”(曹植《與楊祖德書》),突出文學(xué)鑒賞與批評的個性,二者在詩學(xué)理論上形成互補(bǔ)的關(guān)系。不僅彰顯了文的自覺,其底色也是一種生命意識的自覺。唯此,才可能形成建安文學(xué)“以情緯文”的審美特質(zhì)。西晉詩歌抒情繁縟,正是在建安詩歌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而“緣情”的詩學(xué)理論也正是植根于建安詩學(xué)且又是對西晉詩歌創(chuàng)作的理論抽象。“緣情”說也因?yàn)榘鴮壷T生命沖動之情的肯定,所以才造成紀(jì)昀《云林詩抄序》將六朝“繪畫橫陳”的色情文學(xué)歸罪于陸機(jī)的主要原因。需補(bǔ)充說明的是,作為一個社會的人,任何生命沖動之情都無法擺脫“集體無意識”的影響,陸機(jī)對這種“情”的肯定,并非與儒家詩教對立。毛先舒《詩辯坻》謂“子桓‘詩賦欲麗’,士衡‘綺靡’‘瀏亮’語是也”,則揭示了“綺靡”說與“欲麗”說在詩學(xué)思想上的繼承關(guān)系。“麗”作為一種語體風(fēng)格,漢代就非常重視。如陳忠強(qiáng)調(diào)詔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27]1537,漢宣帝認(rèn)為辭賦“小者辯麗可喜”[28]2829,而揚(yáng)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29]49,尤為著名。建安以后,隨著“文的自覺”,追求辭采華美,成為一代審美風(fēng)尚。秦宓提出“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對或問自比巢許四皓》),卞蘭稱贊曹丕“著典憲之高論,作敘歡之麗詩”(《贊述太子賦并上賦表》),曹植崇尚“辭各美麗”(《七啟序》)等,都以文辭之麗作為審美標(biāo)準(zhǔn)。所以“詩賦欲麗”的詩學(xué)觀念是在繼承前人基礎(chǔ)上對當(dāng)代審美習(xí)尚的理論抽象。自覺地注重音韻對偶、清濁宮商,應(yīng)當(dāng)始于對漢語音節(jié)結(jié)構(gòu)的深入認(rèn)識和科學(xué)分析。這一問題實(shí)際上到了“永明體”產(chǎn)生后才真正得到解決。但由于中國詩、樂、舞三位一體,所以詩歌產(chǎn)生伊始就具有強(qiáng)烈的音樂性和節(jié)奏感。《左傳昭公二十年》所揭示的五聲“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cè)帷⑦t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jì)也”,既是音樂的特點(diǎn),也是詩歌的特點(diǎn)。漢代以降,文人又自覺將詩歌的音樂性和節(jié)奏感引入辭賦創(chuàng)作中,如《西京雜記》卷二載:“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30]89宮商經(jīng)緯交錯,使賦具有強(qiáng)烈的音樂性和節(jié)奏感,從而增加賦的可誦讀性。建安詩學(xué)理論,明確強(qiáng)調(diào)詩賦的音樂性似不多見。然而有兩點(diǎn)值得注意:第一,在漢語音節(jié)研究上,出現(xiàn)了魏李登《聲類》之類的音韻學(xué)著作。潘徽《韻纂序》曰:“至于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才分宮羽。”[31]1744漢代字書唯別形體、讀音,至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始判清濁,才分宮羽”。說明魏晉文人開始對漢語音韻有了理性認(rèn)識。而且當(dāng)時(shí)對漢語音韻的古今變遷認(rèn)識也相當(dāng)深刻。如《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車舍也。”[32]407對漢語音韻的理性認(rèn)識,必然影響建安詩賦在韻律上的審美特質(zhì)。第二,隨著佛教流傳日益廣泛,梵唄經(jīng)聲也開始影響中國的音韻學(xué)的產(chǎn)生。《高僧傳經(jīng)師論》又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然東國之歌也,則結(jié)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fù)歌贊為殊,而并以協(xié)諧鐘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于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shè)贊于管弦,則稱之以為唄。”[20]507可見,梵唄經(jīng)音的本身就具有詩性的特點(diǎn)。而且當(dāng)時(shí)本土文人也已注意梵唄之音,如“始有陳思王曹植,深愛音律,屬意經(jīng)音”,“刪治《瑞應(yīng)本起》”,并以梵唄之音著《太子頌》及《睒頌》,從而成為“學(xué)者之宗”[20]506。這一時(shí)期的僧侶也開始研究中國音樂,如《隋書經(jīng)籍志》載魏僧《樂元》一卷,《當(dāng)管七聲》二卷。“魏僧”顯然不是人名,而是魏之僧侶。中土文人對梵唄之音的有意汲取與僧侶對中土音樂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二元互動,必然影響對漢字音韻的深刻認(rèn)識。而佛經(jīng)翻譯偈頌,一方面要研究中土詩頌音韻的特點(diǎn),另一方面又反過來影響中土詩頌的音韻發(fā)展,所以才出現(xiàn)李登《聲類》等“始判清濁,才分宮羽”的韻書。建安后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所滲透的自覺接受音韻的影響,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所以,至西晉以降,“結(jié)藻清英,流韻綺靡”成為一代詩風(fēng)的特點(diǎn)。陸機(jī)的“綺靡”說以及“既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凸顯詩歌風(fēng)格華美,音調(diào)圓潤,正是對建安以來詩歌創(chuàng)作的理論抽象,標(biāo)志著“文學(xué)自覺”的深化。“緣情綺靡”說產(chǎn)生后,從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研究詩歌,強(qiáng)調(diào)詩歌的藻麗音韻,成為東晉詩學(xué)理論的重要特點(diǎn)。產(chǎn)生于東晉的“興感”說、“理感”說是“緣情”說的理論延伸,葛洪《抱樸子外篇》所言之“群色會而袞藻麗,眾音雜而《韶》《濩》和也”[33]172-173,則是“綺靡”說的具體內(nèi)涵。劉宋時(shí)代,聲色大開,成為詩運(yùn)的轉(zhuǎn)關(guān),陸機(jī)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兩個方面都起到了導(dǎo)夫先路的作用。
作者:劉運(yùn)好段夢云單位:安徽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