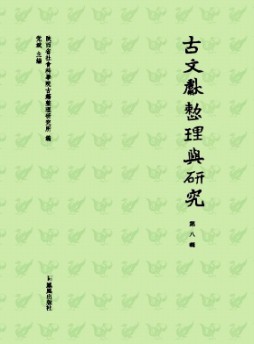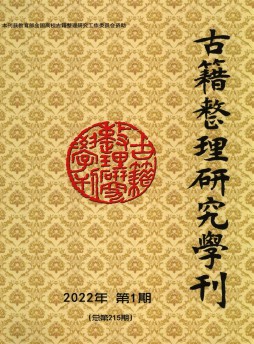漢畫整理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漢畫整理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漢畫(漢代畫像石、畫像磚、銅鏡、漢墓壁畫以及畫像石、畫像磚、漢墓壁畫上所刻文字等的合稱)是漢代民間結合自己的生存環境創造的一個象征世界,表達著他們的愿望和期待。作為一種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年,躲過無數兵燹戰火的民間藝術,它真實地記載了一些早期佛教影響傳統家庭觀念的資料。這些資料展呈了早期佛教在民間的傳播方式,反映了佛教對民間影響的程度,對之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對于豐富漢代早期佛教的研究資料和全面總結早期佛教的傳播規律、糾正學界通說具有重要意義。要把早期佛教的研究引向深入,這些來自民間的漢畫有著異常珍貴的價值。
[關鍵詞]佛教漢畫;早期佛教;民眾愿望;家庭倫理
東漢佛教作為宗教史和兩漢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一直都是眾多學者靈魂騖趨的前沿熱土。在這片熱土上,盡管思維光新、形制厚重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但是,也應看到,由于長期以來哲學學科屬性所形成的思維取向無形中弱化了漢代佛教的歷史學屬性,資料的來源始終沒有得到過有效開拓。作為一種跟民間聯系極為密切的宗教,該教對于東漢民眾生活的影響囿于資料一直都沒有給予過足夠的說明。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大批佛教題材漢畫被發掘出土,為彌補這一缺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為此,筆者以與東漢社會相融的視境和貫通儒佛學科的方法,探賾索隱,抉要發微,對東漢儒佛關系下的佛教題材畫像資料進行一次系統的鉤稽、整理與研究,從史學角度為這項研究工作增添一些新資料、提出一些新問題。
一
欲考查儒佛家庭倫理觀念在漢畫中的消漲進退,似應當先對其家庭觀念的異同進行疏解和辨析。
儒家重視禮,把在禮的規范下實現仁義當作人生完滿的重要標志。何謂仁義?孔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把仁義建構于愛親的倫理層面,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認為仁義是人的固有道德,生來就有,個人要在它的規范下自省自律以實現“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倫理秩序。實行仁義的方法,在儒家心目中,是帶有原始人道主義色彩的“十義”。孝為“十義”之首,是抵達仁義境界的基礎。孔子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還說:“人之行,莫大于孝。”儒家認為,個人受惠于父兄,理應敬親尊長、反本報施。因此,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孝經》也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漢家踐祚伊始,即開訓孝施政之風,后經董仲舒等新儒家的加工改造,儒家的家庭倫理中不僅被糅進父為子綱、父尊子卑的內容,而且還發生了從先前“父慈,子孝”的雙向關系向孝敬雙親單向關系的轉變。董仲舒們的論說作為一份文化富藏,對人們的家庭倫理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國論文聯盟整理)理論的新變和前行不僅在源頭上影響著時代精神,相關理念的普及和接受層面的擾攘喧嘩還能在漢畫的制作中引發更加激越的蹈襲氣象。作為漢代厚葬大潮中濺起的一朵浪花,漢畫以特殊的語言對當時文化背景下的孝道要旨進行了充分的闡揚。首先,贍養父母,讓父母衣食無憂。孟子云:“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行為有五,不顧父母之養即占其三,可見子女奉養父母之事在孟子心目中的分量。正因為讓父母吃飽穿暖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行,所以《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漢畫中刻繪了很多奉養雙親的內容,且大多刻有榜題。如山東泰安大汶口漢畫墓出土的“趙茍哺父”圖上,一老一少席地對坐,少者以口喂老者食。為避免無謂的猜測,畫者曲終雅奏,在老者旁題“茍父”,在少者旁題“孝子趙茍”。邢渠性至孝,其哺父故事在漢代家喻戶曉。在武氏祠畫像中,反映這一內容的畫像多達3處,都是邢渠跽跪著以筷為父喂食的內容。僅一處有畫無題外,其余兩處均刻有“邢渠哺父”的榜題。此類孝道內容還出現在山東嘉祥和四川滎經的漢畫墓中。墓石之上刊刻此類內容,毫無疑問,是時人對篤好孝道、恭謹節儉奉養父母行為的播揚。其次,尊敬父母,使其精神愉快。孔子認為行孝不能光養不敬,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儒家的倫理范疇極重敬親,把它看作孝行的最高層次。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于尊親。”《孝經》中也把居致敬、養致樂當作孝親的重要方式。從漢代大肆刻繪尊親畫像的行為來看,儒家的這種倫理規范顯然受到了人們的贊揚。武梁祠西壁所刻繪的孝子故事中,最醒目者要數老萊子娛親畫像,場面大,榜題字數也多。行年七十的老萊子手持鳩杖仆地作嬰兒啼狀,畫旁特鐫30字銘文介紹萊子致親歡樂的動機、方式和社會對他的評價:“老萊子,楚人,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歡,君子嘉之,孝莫大焉。閔子騫,名損,孔子門生,也是隱忍苦衷而讓父母快樂的典范,在《論語·先進》中孔子曾先后4次褒揚他的德行,南朝的師覺授在《孝子傳》中還專門為他作傳。傳云:“早失母,后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葈為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后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后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譴妻。諫日: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譴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藝文類聚》也有類似記載。武梁祠老萊子畫像旁刻有閔子騫失棰圖,榜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這種關心體貼父母使其精神愉快的畫像,有文有質,體現了人們對儒家孝德相關意蘊的肯定與認同。此類孝行圖是漢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數量很多,全國漢畫產區中都有出土,反映了古人刻繪畫像時所面臨的特定語境,其深沉的吐納展現了儒家的倫理真機。再次,祭祀祖先。在儒家君臣父子的差序結構中,祭祀宗祧跟孝順父母一樣,也是個人踐行禮的有關規范、通過家庭走向社會并兼濟天下的必備條件。《禮記》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認為在禮的規范下以盡“敬而時”的祭祀責任是不可輕視的“孝子之行。漢畫是時代風習、民眾意識的重要實現方式和表達形式,祭祖漢畫是民眾在墓室用圖畫的形式對儒家相關義理所做的領會和理解,表現了民間崇拜祖先的倫理傾向。從漢畫來看,古人祭祖相當隆重,三牲齊備,祭主正面端坐,祭拜者或揖手肅立,或匍匐于地,莊嚴而肅穆。在山東沂南北寨漢畫墓中室南壁刻繪的祭祖畫面上,右上角為祭祀用的三牲,左為12人分列4排每排3人組成的拜謁方陣,前排為跪姿,后3排為立姿,均朝向右下祭主所在的方向。山東嘉祥、微山等地流行墓前置祠堂之俗,祭祀圖像一般被刻在祠堂后壁顯眼位置。祭祖畫像這種表意模式和敘事成規在漢墓中廣泛存在,既是儒家人倫文化的體現,也是古人踐履儒家仁義要求,著意加強自我道德修養的標志。
儒家文化之所以強調孝道,是因為孝是增強家庭成員間的凝聚力、消解家庭矛盾,實現家齊的基礎。只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謹盡孝道,自覺履行道德義務,才能各履其份,修己安人,個人的內在修養才能夠達到圓滿自足的仁義之境。儒家強調移孝作忠,認為只有盡孝,才能盡忠;只有齊家,才能治國。《禮記》所謂“家齊而后國治”和《孝經》所謂“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在儒家的這種倫理取向中,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因對忠孝倫理責任的強調而變成了個人與家庭的倫理關系,行孝的目的,已不在為己,而在于立身和顯揚父母。“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由于倫理秩序中將孝與忠對等,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的最后歸宿也只能是為君王盡忠。在這種倫理體系中,君王父母為重,無論是“修己以敬”,還是“修己以安百姓”,“孝”“仁義”都是手段,效忠君王和建立美滿家庭并使父母顯榮于天下才是根本目的。
佛教主張依三藏修持三學,講究“四諦”、“五蘊”和“十二因緣”,斷除煩惱,獲得涅槃的超脫境界是它追求的最高目標。在佛門看來,人間充滿了苦難和煩惱,而招感此類煩惱的業因,則始于人類的愛欲。《人本欲經》云:“愛為穢海,眾惡歸焉”。《大集經》云:“一切煩惱,愛為根本”。《四十二章經》也認為“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家庭在滅情歸性的佛門看來是孽債之淵藪,女色更是“眾惡之所在”。因此,為了“垢去明存”,徹底消除世間苦集二諦之因果,只有“斷欲去愛”,拋家棄親,割斷與家庭眷屬之間的血緣聯系。可以認為,面對家庭這一人類社會的基本制度和不可破壞的生活秩序,儒家孜孜以求的倫理責任和義務在佛門眼里輕如鴻毛。
在佛智境界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法界同融,閻浮提的一切存在均由種種因緣和合而成.故而他們不僅在閻浮提相互依存,無法脫離集群而獨立存在,而且因道同在,無論大小,是否有情,都擁有佛性,父母子女也不例外。緣于這樣的緣由,佛教不僅以“四恩”“五道”規定了父母子女責任和義務,而且特別重視感恩基礎上的出世之孝。就家庭而言,要求子女在父母在世時不僅供給衣食,而且還要勸他們持齋念佛、潛神教義;父母離世后則要參悟佛法,為父母精進成佛享受出世之樂助緣。讓父母出離三界并從中體認一切法不生相,是佛門最大的孝。
在家庭的倫理觀念上,儒佛之間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首先,以董子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家強調父尊子卑,認為“父者,子之天也。”。為子者要時刻愛敬致恭于父母,及時解決父母所遇到的心身之困,“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只有堅守了這種利長尊親的價值取向和奉獻精神,才算是盡了為人之道。佛教認為父母對子女有恩,出于感恩,做子女的不管父母是否愿意、覺悟,都要積極主動地為他們誦經懺悔,以使其“離地獄苦”而“獲安隱處”。其次,儒家文化以忠孝為核心,把個人的倫理道德修養看作治國平天下的基點,強調修身與治國、孝親與忠君的關系。這種倫理義務和責任既是家庭的,更是社會的,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政治性。佛教主張兼修六度,普度眾生,以萬有成佛為終極目標,子女要幫助父母獲得佛教的解脫,帶有相當的理想化和虛幻色彩。再次,儒家重視血緣關系,它的內圣外王之學立足于日常的倫理生活,只有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后,方可治國兼濟天下。在這種倫理政治化的變換中,人成了社會化的人,家庭也與社會相差無幾,個人只有在家庭的基礎上和社會、君王聯系在一起,“修己以安人”,才是有價值的,人生才有意義。佛教認為萬般皆空,以絕對虛無的眼光審視人間萬有,鼓勵教徒出家修行,建立以寺院為依托的無血緣關系家庭,并以此來構筑人際關系。由于“諸法無我”,“諸行無常”,不僅家庭中的倫理道德是虛無縹緲的,而且人的自然生命及其生命形態也不會一成不變、有生無死。只有出家修行,才可拋卻煩惱、脫離苦海。達到“自我與他人融合”的涅槃境地,才算實現了人生價值。
二
佛教所宣揚的棄家離親、絕妻斷嗣等教義跟漢代所彰顯的倫理綱常產生著尖銳的對立,受到了那些恪守夏夷關防的文人士夫們的竭力反對。對于抵拒的情由,漢末歸化佛門的牟融在其所著《理惑論》中有過詳細追述。他寫道:“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廊落難用,虛無難信。”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古人對家庭綱紀倫常的堅守,不僅成為否定佛教合理性的重要依據,而且成為佛教走進民間的最大障礙。牟子承認,“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因此,“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
從宗教在專制帝國的傳播規律來看,弘道的最大阻力并不在于民眾中哪些人會抵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它的教理教義。在漢代,君臣父子倫理體系賦予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影響力,一位皇帝的進退不僅關乎著一種宗教的興衰,其興趣和偏好還可能創造新的信仰。佛像崇拜為佛教三寶之一,修持此寶可拔除邪知惡念而得生善途。東漢形成的佛像葬俗,與明帝個人的佛教偏好不無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說,佛教畫像之所以能夠彌漫杏壇、流布民間,其實是以明帝感法為肇端的,明帝對佛像走進家庭倫理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永平以來,中國始傳其法,圖其像。而至王公貴人,皆遵奉之。”民間仿習明帝陵墓樹佛像的做法,也在墓葬中刻畫佛像。“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明帝至順帝年間所刻繪的佛像漢畫,造型一般為立像或坐像,表現的是單純的佛法崇拜,山東、重慶、四川、陜西等地漢畫墓中均有出土,印證了文獻的相關記載。皇帝的喜好和恩準雖然是獲得傳教通途的重要一步,但一種宗教的被接受程度最終還是取決于它滿足民眾需要的程度。初傳時期的佛教要想在濃郁的儒家文化氛圍中站穩腳跟,就不能無視民眾的這種精神需求。中國素以家庭為重,具有重人倫和重現世的特征,渴望人丁興旺。在這種文化的浸淫中,世人十分崇拜深潛送子賜福隱德的西王母。此一信仰其久,闕疑成信,在漢代更為大闡,其形象在陽宅、陰宅中有著廣泛刻繪。此類精神偶像自然就成了佛教最佳的模仿對象。從目前出土的佛教漢畫來看,對西王母畫像的模仿,明顯經歷了這樣3個階段:第一階段,造像的品格和出現的位置均模仿西王母,時間在章帝時期。如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出土的八角擎天石柱上所刻的佛像和西王母像就是如此。西王母像居于石柱西面頂端,戴勝,其座由巨鰲相托.座下為白虎、麒麟。石柱東面為東王公像,格局與此相似。佛像位于南北二面,與西王母像相鄰,亦處于石柱頂端,其下為人面鳥身雙首神像和蒼龍圖像。原發掘報告稱這是“佛教傳到中國不久,其藝術在中土開始萌芽的現象。”這種小心翼翼模山范水的情形在四川成都漢代崖墓中也有出現,表現出民間以西王母形式處理佛像信仰的普遍性。第二階段為佛教借用西王母圖像特征而成像,或者說是在西王母像的傳法系統中用佛像對西王母像實施置換,時間約在和帝時期。這類圖像的出土以西南地區為最多,幾乎成了具有時代共性的刻繪法則。如四川西昌崖墓所出佛像搖錢樹座上,佛像就被刻繪在西王母常坐的龍虎座之上。在四川新都出土和帝永元元年漢畫磚中,佛像亦居于龍虎座上。龍虎座為西南地區西王母畫像的重要標志,佛像對于西王母法流的刻意借用,可見出初傳時期佛教的生存策略,有著佛門自家宗義的鮮明圓擇。第三個階段為完全具備佛教性質和內涵的獨立佛像。這類佛像從重慶豐都出土東漢延光四年搖錢樹佛像推斷,時間可能已下延到東漢中期。正面端坐,隨從簇擁,像西王母一樣,或居于墓額正中,或居于搖錢樹干和樹座的中央,標準的偶像崇拜布局模式。樂山麻浩墓和柿子灣崖墓所刻佛像,均居于中央重要位置,顯得極為尊崇,隱含著濃重的意識形態修辭。現藏南京博物館的一座彭山東漢中期搖錢樹陶座,其中央刻繪正面端坐的佛像,胡僧胡人配侍兩側,清晰的佛門話語透析著佛教的正法宗義。這樣的構圖還可見于新疆民豐縣尼雅出土的臘纈棉布上的佛像。在佛教的教義中,以佛陀為偶像表明佛在心中,通過瞻仰圣像可修行證道、攝心正念。對佛像頂禮膜拜,便可與佛交流而獲得感應,不僅可得智慧之男和端正之女,而且還可永保佛種不斷。古人將佛像納入到民間信仰系統重新融攝,借像表法,實屬十分典型的合儒釋理念為一體的哲學圖式。
從這一過程來看,佛教并沒有沐浴在中國偶像的榮光里無所作為,而是在積儲經驗,勇敢邁步,不斷設計著新的藍圖,以非常態表征所蘊涵的知識體系與信仰結構來喚起世人對佛教大義的認知。之所以這樣說,乃出于以下3個理由。
第一是這一時期的佛像中有些已經刻繪上了白毫相和項光,給了人在寒峭與肅殺并未退盡的殘冬佛教以急于造船出海的證詞。例如,四川忠縣涂井5號崖墓搖錢樹佛像和何家山1號崖墓佛像均帶有白毫相。白毫相為佛陀三十二相中最殊勝者,具有消除業障、安樂身心的效用,刻繪此相,表示除卻百億那由佗恒河沙劫生死罪之福德。項光為非常難得的殊勝法緣,是自性中的光明,佛示現于你,則表示佛已開啟你的智慧之光和給予了你多生多劫的法緣。擁有項光的佛像現在出土較多,除上述麻浩墓、柿子灣墓、新疆民豐尼雅墓出土的佛像有項光外,四川綿縣、安縣、三臺,重慶豐都、忠縣,陜西城固、漢中和貴州清鎮出土的搖錢樹佛像凡56尊,無不刻有項光。這些畫像或可透露佛門宏通的立身旨歸和潛藏的弘法雄心。這里邊雖然帶有佛教向儒家倫理妥協、調和的痕跡和某種形義串通的借鑒成分,但正是這種義不遠宗、言不乖實的妥協調和,奠基了中國佛教與傳統家庭觀念的相適應的“資道”特色和法緣傳承精神。
第二是此時的漢畫中已有了佛教專有的膜拜儀式。憑借這種傳教方式,佛教在逐漸為漢代民眾所接納的同時,佛教漢畫的內容也在朝著專有化的方向發展,顯示出了不同于儒家文化的家庭倫理。最為典型的,要數漢畫對祭祖時焚香儀式的表現。焚香乃佛門五種供養之一,其裊裊香氣不僅能夠流芳解穢,而且還能飛向祗洹援佛臨顧演說妙法,故佛門以焚香為“佛使”,視作菩薩境界。山東臨沂吳白莊東漢中期偏后漢畫墓出土的祭祀圖上,祭主形象高大,憑幾跪坐,面前幾案上陳放香爐、祭品,祭眾由界欄分成兩排執笏面向祭主跪拜。徐州十里鋪的漢畫墓后室東支柱上刻繪畫像兩層,祭祀場面位于上層,畫面中刻屋宇1棟,屋內祭主2人對坐,面前置香爐祭品等物。除此之外,以香爐為內容的祭祖漢畫,在南陽縣英莊東漢早期畫像墓和山東沂南東漢中期畫像石墓中也有出土。儒家雖重祭祖孝親,但漢代沒有焚香儀式。香爐進入世俗的倫理生活,為我們判斷漢代民間影附風靡地接受佛教法義和質疑學界漢代佛教只在上層人士間傳播的通說提供了客觀依據。
第三是歷史文獻的佐證。佛教從四諦出發而推出的森羅萬象俱空和世間一切皆苦的命題確實比儒家學說顯得圓通、深刻,因此,漢代的一些貴族士夫也愿意把佛教的空無妙旨當作慰藉心脾的良藥。如果說明帝永平感法之后人們在壽陵做佛像還只是表明東漢中期以前漢地已有佛教傳播的話,那么史書對楚王英的有關記載所透露的則已不只是個佛教的簡單傳播問題,而是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了。《后漢書》記載,英晚節“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黃縑白紈三十匹。國相以聞,詔報日:“楚王頌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絮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咎?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這則為學界一再引用的史料,細覆之可見片言之間所綴的兩個重要信息:一乃東漢中期以前貴族禮佛供齋場面宏大、態度虔誠。二乃佛教在永平年間即發展有出家和不出家的信徒。“絮齋三月”,就是佛典中所謂的三長齋月,它意味著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從初一到十五都要舉行守戒、持齋、拜、懺悔、焚香、散華、懸雜幡蓋、供事三寶等佛陀救贖儀式,每項儀式的儀軌相當繁雜,加在一處的文字量絕非一篇論文所能涵蓋。作為一種顯示“大善”的宗教儀式,將其科目按規定做下來也非一天所能輕松完成,這從漢代及其以后翻譯過來的相關經典和古往今來學者的研究著作中都可得到證明。史料中所說的“伊蒲塞”,指佛門俗家弟子,亦稱居士。“桑門”即沙門,指出家的佛家弟子。從《后漢書》的這條記載中可以感受到當時貴族階層深溺佛法奧義的情況。佛教漢畫作為特定人群在特定時空宗教情緒、宗教態度和宗教期望的真實流露,它雖然因條件限制沒能夠用宏富的篇幅寫下三長齋月的專論,但是用精妙的圖像闡釋和抒發了人們心底那種寄望佛陀救贖死去親人靈魂并保佑生人的思想情感。在陜西城固和安縣東漢中期畫像墓出土的搖錢樹上,刻有佛陀手持表示六道輪回的輪盤的畫像。此輪盤象征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和阿修羅、天道、人道的三善道,為佛教地獄救贖的主要內容。這類材料和畫像出現在歷史文獻與民間的喪葬生活中,表明在東漢中期以前,佛教義理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貴族和普通民眾的家庭倫理觀念。
佛教在傳人初期,雖然主要通過靠攏儒家文化的方式來求得生存,但當東漢晚期外部形勢發生變化,儒學信仰危機暴發之后,這種情形便漸漸地消失了。佛教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漢代的家庭觀念和倫理道德受到了深刻影響。
由于儒家的仁義之學及其所勾畫的內圣外王的倫理體系是以宗法制的支持和保障為前提的,所以,盡管它在大一統的統治格局中能夠較好地發揮維護倫理秩序的功能,人們對其所確立的倫理道德準則也會表現出一種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誠而“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但是,當漢王朝大一統的統治局面遭到破壞,天災人禍所孽乳的冷漠情感侵襲到宗法制度下家庭組織的每一個細胞時,儒家的忠孝觀念和人格教條便不能為社會大變局中那些深受憂患煎熬的人們提供有效的回應策略了,有道是“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另外,東漢晚期,外戚秉權,宦豎充朝,奸佞橫行,統亂莫稽,政治敗壞到了極點。統治集團內部為了各自的利益進行著無休止的傾軋,稍有不慎,便有朝榮夕哀之虞。在這種飄風終朝、驟雨終日的環境中,人們心間總是籠罩著一股悲涼、苦悶、怨憤的情緒,精神也經常處于壓抑、焦慮、頹廢的狀態,相當一部分人在社會險惡的沖擊波中對儒家修齊治平的工具理性產生了幻滅感。特別是桓靈之世兵戎四起,世家平民處在生命涂炭這樣一種“厄運之會”,內修圣德、外務事功的體證實踐在他們的心中也因為黑暗世事的遮蔽而沒有了昔日耀眼的光芒,儒家家庭倫理的精神靈氣漸漸窒息。在這不堪回首的歲月里,佛教盡管在治國方面沒有大的作為,但教義中那種佛性人人皆有,成佛人人可能的言說,對于飽受痛苦的民眾而言,卻不能說不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它的輪回說、業極說、因緣說、三世說、彼岸說,為流離失所、身處絕境邊緣而無力解脫的民眾提供了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對于彼岸的殷切期待,招致人們在佛教面前靡不刳心。桓帝為坐致太平和福壽雙全,不僅于宮中立浮屠之祠,而且還“數祀浮圖”。嚴佛調于桓靈之際率先出家,譯經多部,罕不承緒。于譯經之余,還博覽精思,對《十慧經》分章句疏釋,開漢人注述佛經之先河。督管廣陵、下邳、彭城三郡漕運的下邳相笮融舉辦了有漢一朝規模最大的事佛活動,在這一活動中,笮融“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悉課誦佛經。”“課誦佛經”不僅說明佛教已從早期黃老浮屠并祠的信仰模式中撤出而單獨接受崇拜,而且也說明已經有大批民眾皈依佛門開始聞誦佛經了。牟子在《理惑論》中,明確指出佛門戒律的作用等同于傳統禮制,佛教教義是合理的。這些人物對佛法的弘揚和肯定,擴大了佛教在漢代的影響。
社會對佛教的敬仰與渴盼,也鼓舞了傳教士們傳教弘法的信心和熱情。安息佛徒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年來到京師,筆耕不輟,二十余年的時間里,翻譯《陰持入經》、《十二門經》、《人本欲生經》等佛教經典35部41卷。支讖為月氏國人,在華四十余年,翻譯《寶積經》、《首楞嚴經》、《般若道行品經》等佛教經典14部27卷。安息居士安玄,于靈帝末年游賈雒陽,一邊與沙門研論佛教經義一邊翻譯《法鏡經》,從居士的視閾論析居士修持的各種戒律,闡揚佛門倫理在黑暗、冷酷生活中的價值。傳教士對于佛教教義大張旗鼓的翻譯和廣泛宣傳,從根本上增強了中土信徒信奉佛教的勇氣。一時間,把弘揚佛法當成了他們的共同使命。特別是洛陽人孟福,南陽人張蓮、韓林,穎川人皮業等.既是中原的貴族豪佑,也是這一崇佛大潮中涌現出來的忠實信徒。這批人跟傳教士同舟共濟,通力合作,為佛教在中土的發硎新試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這些人的帶動影響下,社會各界,聞風竟會。據史載,安世高于京都講經,“聽者云集”。笮融在彭城浴佛,“來觀及就食且萬人”。這些都充分說明,時移世易,佛教的家庭倫理思想已以一種不可違逆的力量浸漫到了全國各地。
東漢后期佛經傳譯的重點在禪數之學,五蘊有為法深刻地影響著整個社會之于佛教的理解與接受,它的地獄救贖說和業報輪回說給水深火熱之中汲汲顧影、旦不保夕的民眾帶來極大的寬慰。“聞有佛如來能救苦難,誰不愿托以自庇。”時代對佛教的需要,必然鑄成超脫化的審美風習和信仰情結。佛界不僅成了顛沛流離艱難困苦之際民眾心靈中的一塊樂土,其所宣揚的精神解脫觀念也深存人心,表現佛陀保佑的佛祖降身故事和象征解脫大義的佛塔、蓮花、舍利等也因此成了東漢晚期佛教畫像的主要內容。
在佛教的教義中,釋迦戒行高潔,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達到了修行的最高果位。他了悟自性、人生和宇宙諸法,超越了閻浮提和出世間,至真至善,至知至能,法身化身報身聚合為一,能幫助眾生獲得徹底解脫。由于他把引導眾生遠離諸著作為畢生追求,所以受到民眾廣泛的供奉和祭奠。在東漢后期的漢畫中,表現佛祖故事的圖像刻繪得不少。在和林格爾東漢后期墓的前室壁畫中,畫一人騎白象,左上榜題“仙人騎白象”五字。據俞偉超考證,顯示的是佛祖能仁化騎白象以就母胎的前后因緣。在佛教教義里,端立法身即證得法身,以此像信受佛說,佛悉知悉見,悉知悉見之后必加護念。漢畫對于佛教倫理元素的擷取和運用,其凝重的法理折射了在國亂人苦年代人們祈求佛陀護佑的心愿,這類圖像在東漢后期出現并非出自偶然。六牙白象被佛典視為象中之寶,東漢末年傳教士竺大力共康孟祥譯的《現變品第一》對它的功能有著這樣的描述:“白象寶者,色白紺目,七肢平躊,力過百象。髦尾貫珠,既鮮且潔。口有六牙,牙七寶色。若王乘時,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墓返,不勞不疲。若行渡水,水不動搖,足亦不濡,是故名為白象寶也。”在翻譯人姓名無顯的東漢譯經《雜譬喻經》卷上,對六牙白象也有過這樣的記述:“昔雪山有白象王,身有六牙,生二萬象。”六牙白象為象王,神通無邊,眾梵典在述及佛降身之說時,無不以六牙白象作能仁菩薩的化乘工具。因此,六牙白象實為佛祖法身的代表。在中國出土的漢畫中,有好幾處都發現有這一佛教瑞像因緣故事圖解。山東滕縣出土的六牙白象畫像磚上,刻兩匹白象,每象六牙,其上有人乘坐。同樣構圖又見于四川綿陽何家山2號東漢晚期崖墓出土的銅搖錢樹葉片上所繪的“象與象奴”畫像。以圖像宣說佛法勝義,揭示其隱微道理,在佛教義理的闡釋系統中追溯其知識構成和表現模式的學術淵源,既反映出東漢晚期佛教對民間家庭生活滲透和影響的程度,也顯示出東漢晚期以佛教倫理取代儒家倫理以擺脫歷史意識形態羈縻的思想傾向。漢畫把佛教精神和佛教理念外化為鮮明生動的倫理圖像,讓人們通過相關情景的點化而窮推其源,從而體悟釋尊斷滅三惑、離家棄業的超邁品格,可謂是慧發天真,言約旨遠。
佛塔,漢代稱浮屠,源于印度宰堵坡,為存藏佛祖舍利的建筑,佛門認為是最可尊敬的佛祖慧命。在佛教信仰中,供養佛塔跟供養佛身同義,是諸法因緣和合的顯現和超脫生死的象征,佛經中有很多敬建、禮拜、供養佛塔的文獻。漢代信佛之人,也常將佛塔圖案鑄進磚中。在四川什邡縣出土的東漢佛塔畫像磚上,“中間有一佛塔,兩邊為菩提樹,再往兩邊又各有一佛塔,佛塔與菩提樹相間而刻。佛塔與菩提樹相間,表明佛佛相生不斷。將刻繪佛塔圖案的畫像磚砌進墓室,是為了便于受特閱念,在了然佛法之際,廣結佛緣,達到開菩提路、超脫生死輪回的目的。與佛塔寓意相同的事像,還有漢畫中的蓮花圖像。蓮花在佛教里的寓意極為豐富,既比喻純凈,也象征佛法。在佛教看來,世間污濁骯臟,只有佛地才是一片凈土,沐浴蓮花浩蕩青光并廣修四攝六度,才能像純潔的蓮花一樣超脫煩惱不為齷齪所欺。蓮花還常代表佛法,《觀無量壽經》稱眾生臨終時阿彌陀佛和勢至菩薩都要親持蓮臺超脫亡靈。蓮花與佛教的淵源很深,印度阿育王時期弘法獅形石柱的底部就刻繪有蓮花圖案,巽伽王朝建造的巴爾胡特和桑奇塔欄桿上也刻有很多蓮花。正因為蓮花與佛教具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常用蓮寺、蓮經、蓮臺來分別稱呼佛寺、佛經、佛座。東漢后期漢畫中的蓮花也多與佛像連在一起。四川安縣文管所收藏的佛像搖錢樹上,佛像項光之上有蓮花,佛像兩側有八瓣蓮花。1984年河南孟津縣朝陽鄉出土的一面東漢晚期佛像銅鏡,收藏于洛陽市博物館。2009年初筆者專程到該館考察了這面銅鏡。佛像為銅鏡背面裝飾的主要內容,正面,結跏趺坐.座下也為蓮花圖案。佛蓮一體,既有道德修養的寓意,也有宗教修證的內涵,表達了一種斷除輪回苦海,享受出世解脫歡樂的愿望。在佛教信仰中,舍利乃高僧大德真身,供養舍利就是供養佛身,按《金光明經》的講述,修持這種“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熏”的舍利菩薩之道,并于此殊勝法門朝持暮誦,就能明心見性,得“最上福田”。漢末流行將舍利畫在盤中裝飾墓室的風習,如在和林格爾壁畫墓中,除前室南壁繪有仙人騎白象的畫像之外,東邊墓門上還“繪有一盤狀物內放有四個圓球形的東西,在其左上方題有‘猞猁’二字。”眾緣和合為假有,舍利這一佛教題材的出現,是賅攝佛經要義、覺悟憑借圖示形式的外化,表現了漢代人在命若懸絲之時對佛教去妄歸真旨趣的忠愨和對痛苦艱難狀態實施超脫這一實相境界的體證。漢畫通過佛祖降身故事、佛塔、蓮花、舍利等所張揚的這種解脫心體跟儒家倫理體系中的忠孝相比,盡管都頗富激情,但已有南轅北轍的味道,從中已經看不出儒家的仁義內涵,此岸與彼岸的分隔也使它更難推導出修齊治平的抱負。個人道德完善與社會進步志向的疏離,反映出漢末這個眾生備受諸苦煎熬、翹首切盼佛陀降臨時期人們在家庭倫理的學理認知和哲學判斷上所發生的變化。
漢畫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璀璨明珠,記載了大量佛教內容和漢代民間理解和接受早期佛教的資料,展示了佛教文化初傳的歷程中,該教在家庭倫理上對儒家文化的對抗、靠攏、篡弒的有關情形,這些資料是我們了解佛教文化在漢代的影響及影響方式的重要途徑。在漢代佛教的研究上,本來資料就極為有限,而又多集中于人們已知的所謂歷史文獻范圍之內,民間特色極為濃厚的出土漢畫文獻還沒有得到科學系統的挖掘和梳理,其承載的佛教信息還幾乎未被學界利用,這一點很少為世人所注意。本文在上述方面所做的嘗試和探索,祈愿能夠在拓展早期佛教的資料來源、把握佛教文化被接受的規律、揭示漢代佛教的具體狀態和豐富完善佛教史的研究方面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