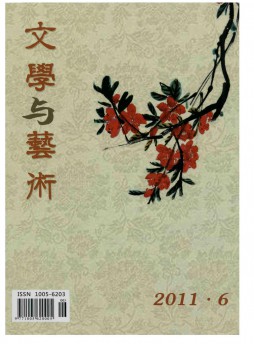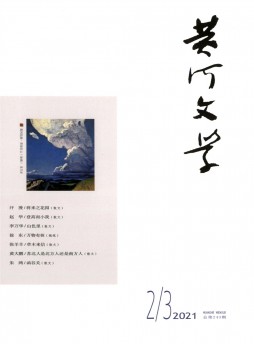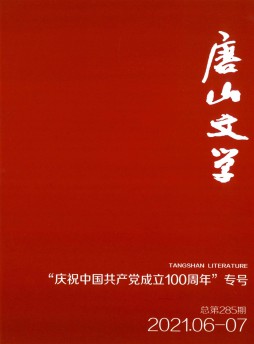文學經典古代文學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經典古代文學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耶穌會的建立和來華意籍耶穌會士
耶穌會于1534年由依納爵·羅耀拉(IgnaziodiLoyola)應當時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羅三世(PapaPaoloIII)批準了其組織形式和會憲。耶穌會士誓愿絕對服從教皇,特別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穌會建立了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并培養了大量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耶穌會士,這些耶穌會士們的學術成就對他們在海外,包括中國的傳教活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歷史中,來自于意大利的傳教士較之其他國籍的人做出的貢獻更為突出。這既包括最早確立和推行適應中國傳統文化傳教路線的耶穌會士范禮安、羅明堅和利瑪竇,也包括利瑪竇之后的郭居靜、艾儒略、衛匡國、高一志、畢方濟、羅雅谷、利類思、潘國光、畢嘉、殷鐸澤、龍華民和熊三拔等著名傳教士。”②這里要著重介紹和評述的是對中國文化及中國儒家文學經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羅明堅、利瑪竇和殷鐸澤三人。
(一)羅明堅與《四書》
羅明堅(MicheleRuggeri)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傳教士,也是歐洲第一位漢學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國,獲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學位。29歲時加入耶穌會,1578年和利瑪竇等人一起離開歐洲前往中國,并于1579年到達澳門。羅明堅刻苦學習中國語文,他創建“經言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教授外國人漢語的學校。為了幫助自己及來華傳教士學習中國語言,羅明堅編寫了《葡華字典》,第一欄是葡萄牙語詞項,第二欄是拉丁拼音,第三欄是漢字,第四欄是意大利文詞項。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誤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節來中國,羅明堅被派遣回到羅馬。但因后來一系列變故導致計劃無法成行,羅明堅便隱居薩萊諾,再沒有回到中國。在薩萊諾,羅明堅完成了將儒家經典《四書》翻譯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學》譯文刊載于1593年波色威諾的《精選文庫》中,這是最早在歐洲出版的介紹中國儒家經典的譯著。意大利漢學家、教授、出版總監弗朗西斯科·達萊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羅馬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國立圖書館中的手稿文獻為基礎,對羅明堅的《四書》譯作做了細致的研究。
(二)利瑪竇及其對中國文學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馬爾凱大區馬切拉塔城的一個貴族家庭。馬切拉塔是教廷國的重要城市,宗教氣氛濃厚,經濟、社會發展也十分活躍。利瑪竇9歲便進入當地由耶穌會士開辦的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16歲時他的父親將他送到羅馬大學法學院讀書,在這里他結識了一些耶穌會神父,并最終成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穌會修士。利瑪竇在羅馬期間積累了豐富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與教會上層人士建立了良好關系,為后來的傳教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瑪竇有著良好的師生關系。1578年3月,利瑪竇和羅明堅等14人乘船繞過好望角向東航行,利瑪竇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達中國澳門。利瑪竇起初作為羅明堅的助手,在羅明堅大體確定的傳教策略基礎上進一步調適和發展,適應中國傳統文化。羅明堅離開中國后,利瑪竇拋棄傳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換中國儒生的服裝,進一步適應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瑪竇一行到達北京,在北京雖幾經波折,但利瑪竇的廣泛交往使他跨越險阻,繼續推動著傳教事業的發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寫和出版了《天主實義》《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利瑪竇很早就開始了解中國文學,這也要得益于范禮安的指點,在中國當時特殊的環境中,必須要很好地了解中國文化和經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寫到的那樣,他認為:“只知道我們的(指西方的)文學而不知道彼國的文學是沒有多大用處的。”③因此,他開始非常努力地學習《四書》,并翻譯成拉丁文,使《四書》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剛來中國的同教會教士閱讀,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書》的內容。利瑪竇還十分了解《五經》,有些人認為他熟記《五經》甚至強過許多中國官員,《四書》《五經》都是選拔政府官員的科舉考試的規定書目。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建立在兩大理由上:1.不了解對話者受教育的典籍就無法恰當地與其交流;2.利瑪竇找到了有利于傳教游說的極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觀點的同時也利用中國經典作品的權威性內容,如果沒有對中國文學的深厚了解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利瑪竇寫道:“用我們堅持并嚴肅探討過的方法,以他們謙恭有禮的舉止,他們自會重視圣賢之名。我希望我們可以堅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為這里有許多優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學家,現在沒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國之文學,因為只知道我們的文學而不了解中國的是沒用的。尊敬的神父,您會看到這一點是多么重要。我認為這一方法比一萬基督徒的功用還大,以此安排才能實現整個國家的皈依。”④利瑪竇認真研讀《四書》《五經》,因此在1595年開始寫作《交友論》時,他也借鑒了孔子關于友誼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論語》中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幫助你成就仁德,友誼是仁的結果,而仁是人類的至善至美,在這方面利瑪竇認為中國的理論與他熟知的基督教教義驚人地相似。利瑪竇在《交友論》中寫道:“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為友之責矣。”⑤“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為仇敵,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為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⑧這種獨特的方法在《天主實義》中也有運用。利瑪竇為了闡釋上帝的真正含義,借用了很多中國古代經典。他寫道:“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為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圣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為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⑨盡管利瑪竇出于傳教策略的需要,對中國古經書有一些誤讀,他也無法完全理解中國哲學的復雜性和文字概念的多義性,但他的力辯卻充分反映了他對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的廣泛而細致的研讀,并通過翻譯《四書》將中國的文化思想介紹和傳播給西方的耶穌會士。
(三)殷鐸澤———中國文學的翻譯者和傳播者
殷鐸澤(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亞,16歲起進入卡塔尼亞的耶穌會學校,后來成為一名耶穌會士。1659年他作為傳教士到達中國,在江西建昌進行傳教活動。殷鐸澤熱愛中國哲學,對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將自己讀《四書》所做的筆記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題目叫作《中國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頁孔子傳記、14頁《大學》譯文和《論語》的部分譯文內容。1667年他在廣州又出版了《中國的政治道德學》(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對《中庸》進行了部分翻譯,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時他又添加了對孔子生平的介紹。盡管這部作品的流傳范圍很有限,但因為1672年被法國作家、旅行家、東方學家戴夫諾(M.Thévenot)收錄在他的《各種獵奇之旅之報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歐洲獲得了一定的關注。目前該作品在世界上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圖書館中。他所譯的《中庸》又與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Couplet)、郭納爵(IgnacedaCosta)的譯作一起合編為《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鐸澤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和翻譯者,他用拉丁文翻譯了許多中國文學經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鐸澤將孔子及其作品介紹到西方,產生了重大影響,萊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爾(Wil-liamTemple)在讀過《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后都對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贊譽,孔子在歐洲因此被稱為道德與政治哲學上最偉大的學者與預言家。自由派人士歡呼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類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國的蘇格拉底。
二、法國漢學的后來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學者對中國文學的譯介
從17世紀中葉起,歐洲漢學的牛耳從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國人手中,有幾方面原因:1.1658年法國從羅馬教廷取得在中國、越南建立主教區的權利,這為在這些教區征招法國傳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國傳教士開始與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觸,在對中國研究的過程中,他們編寫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國學者將對漢學的研究科學化、專門化,特別是在法國本土,改變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學術化的風格。3.在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中法條約簽訂以后,法國人對中國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國幾大漢學家、翻譯家,如儒蓮(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貢獻突出。到19世紀,除了古文經書和科學著作之外,法國學者更注重對中國民間文學作品的翻譯,如元雜劇、詩歌、愛情小說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學者對中國文學的譯介常常受到法國學者的啟發,或從法語譯本中轉譯過來。皮埃特羅·安東尼奧·麥塔斯塔西奧(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詩人、歌劇劇本作家、劇作家、音樂劇改革家,長期為奧地利宮廷創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卻崇尚英雄壯舉。1752年,他將歌頌忠誠正義、舍己為人的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改寫成意大利文歌劇,題為《中國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維也納美泉宮皇家花園劇院上演,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麥塔斯塔西奧對《趙氏孤兒》的翻譯和改編參照的就是收錄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穌會神父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譯的法語版。阿爾豐索·安德萊奧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對近代中國進行研究的意大利學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羅倫薩,早年學習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燒炭黨人的革命活動,作為律師他曾為多梅尼科·圭拉齊(DomenicoGuerrazzi)進行辯護,因此屢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國巴黎期間,他結識了法國漢學家儒蓮并在他的指導下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從此一生致力于漢學研究。他在佛羅倫薩的語史學界教授漢語,尤其致力于閱讀和翻譯中國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為題目翻譯出版了中國著名古典小說《水滸傳》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對中國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寫有《論古中國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譯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時會標注音標,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圖羅·馬薩拉尼(TulloMassarani)所編寫的《玉書:遠東的回聲》(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錄、翻譯了中國古代多個朝代詩人的百余首詩作。全書共176頁,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為25個主題:“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漁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鏡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鴨”(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圖羅·馬薩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學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國第一位猶太議員。他精通藝術,文學創作風格靈活優雅,著述頗豐。他讓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國浪漫派詩人海涅,推廣了歐洲一些不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別是他對于意大利文學家卡洛·譚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為著名。
三、明清時期意大利人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譯介的動機及特點
歷史事實證明,歐洲人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直接解讀甚至轉譯一開始并不是來源于興趣,而是出于宗教需要。歐洲人想要用基督教思想同化中國這個東方的神秘的泱泱大國,可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古羅馬帝國在攻占希臘時曾發生過的同樣的情況:占領者被被占領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征服了。面對中國復雜的歷史政治環境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基督教思想并沒有說服力,如果不能先被中國的思想同化,借用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經典來說理,那么傳教之路必然走不下去,這也正是早期耶穌會士在中國采用適應性傳教策略的根源。因此,從學習語言文字,到研讀古文典籍,耶穌會士一步一步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并有了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愿望,翻譯就從這里開始。當然,這種翻譯是有目的的,是為傳教之方便,而且是片段的、零散的,水平十分有限。翻譯的文字是拉丁文,并不是國別語言(特別是統一的意大利語言形成較晚)。清朝以后,意大利傳教士的地位逐漸被法國人取代。法國人對中國的研究涉及范圍更廣,最重要的是他們將對中國的研究系統化、科學化,翻譯作品的語言也常為法語。再考慮到在歐洲大陸上經歷了啟蒙主義運動、大革命和拿破侖統治的法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優越性,意大利在這一階段往往只能追隨法國的步伐,在對中國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可是意大利人對中國的研究,對中國典籍、經書、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的譯介從沒有間斷過,從最初到現在,可以說他們是歐洲漢學研究的啟蒙者,是中國思想文化在歐洲的最早的傳播者,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學譯介歷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作者:谷倩兮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