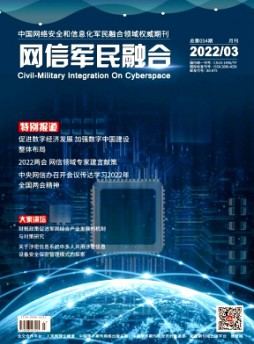玄釋融合與古代文化之成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玄釋融合與古代文化之成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名士與名僧文化特質(zhì)
名士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幽、厲之后,周室微,陪臣執(zhí)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1]1095由此可見,隨著周政權(quán)控制力的降低,過去被中央政權(quán)壟斷的思想權(quán)力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逐漸下降到地方。這種思想權(quán)力的下移成為名士出現(xiàn)的催生動力。由于處于統(tǒng)治階級的底層,自產(chǎn)生之日起名士對政權(quán)就有很強(qiáng)的依附性,他們的成功依賴于王權(quán)的尊重與認(rèn)可,擁有思想權(quán)力的名士只有通過為政權(quán)出謀劃策才能展現(xiàn)自己的存在價值。秦漢時期政權(quán)的統(tǒng)一和王權(quán)的加強(qiáng)帶來的一個后果是學(xué)術(shù)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使曾經(jīng)獨(dú)享思想權(quán)力的名士被政權(quán)邊緣化。名士開始失去對思想權(quán)力的控制權(quán)。感受到威脅之后,名士曾采用多種方式來爭回自己對思想權(quán)力的控制權(quán)。最早的方式是通過在理想主義精神下,以普通人難以達(dá)到的標(biāo)準(zhǔn)來評判現(xiàn)實(shí)。如西漢后期蓋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yùn),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2]但是這種抗?fàn)幨遣粫痪哂袕?qiáng)烈集權(quán)傾向的王權(quán)所容納的。王權(quán)與名士為了爭奪對思想權(quán)力控制權(quán),開始了強(qiáng)烈而又持久的矛盾與沖突。東漢末年連綿不斷的黨錮之禍就是這種矛盾沖突的集中表現(xiàn)。名士在某個具體階段的政治斗爭中或許會占據(jù)上風(fēng),但因為沒有政治權(quán)力的持久保障,其最終失敗之命運(yùn)注定是不可逃避的。這種情況下思想界展開了對終極世界的探尋與解答。這種探尋與解答既可使其逃避政治斗爭的迫害,又可展現(xiàn)自我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回到老莊、在儒家世俗主義基礎(chǔ)上輔以老莊思想對終極問題的探討,進(jìn)而重構(gòu)社會思想,并在重構(gòu)的過程中試圖重新建立自己在思想領(lǐng)域權(quán)力的合法性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的首要選擇。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與秦漢時期名士具有不同的特質(zhì)。關(guān)于這一時期名士的特質(zhì)牟宗三與余英時均有論述。牟宗三認(rèn)為主要特征是清言玄談、生活曠達(dá),“然則‘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不濁,逸則不俗”。
余英時亦持類似認(rèn)識。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與“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fēng)的演變”兩章節(jié)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觀點(diǎn)是,名士是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的承載者;其文化特質(zhì)是建構(gòu)于服膺儒家思想、注重人倫秩序的門閥宗族基礎(chǔ)上的曠達(dá)、玄理以及清逸生活之追求。佛教雖在兩漢之間傳入中國,但魏晉之前佛教在中國影響較小,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幾點(diǎn):一、中國傳統(tǒng)思想強(qiáng)調(diào)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秩序并有積極入世觀念,而佛教強(qiáng)調(diào)從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退隱并展開對終極世界的思考;二、儒道均將自我與王權(quán)相聯(lián)系,力圖在尊重王權(quán)的前提下實(shí)現(xiàn)自我的發(fā)展,而初入中國的佛教依然有很強(qiáng)的印度文化色彩,對王權(quán)的尊重在中國統(tǒng)治者以及儒道學(xué)者看來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三、佛教進(jìn)入中國的文化積淀尚較為淺薄,社會對佛教的教義、教儀認(rèn)識不夠,存在很強(qiáng)的認(rèn)識偏見;四、佛教是一種異域文化,很容易受到中國文化中心主義者的攻擊。基于上述原因兩漢時期中國社會對佛教的興趣點(diǎn)主要落在神仙方術(shù)方面,佛教僅獲得在統(tǒng)治者上層的活動權(quán),故這一時期罕有名僧出現(xiàn)。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在中國高速發(fā)展的時期。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出現(xiàn)主要基于兩種因素的作用:其一,從社會基礎(chǔ)來看,此時期中國戰(zhàn)亂紛爭、政局變化不定,民眾飽受兵亂之苦,以出世為本的教義在這一時期有了傳播的民眾基礎(chǔ);其二,從思想基礎(chǔ)來看,此時期是以簡練語言探討本體論和認(rèn)識論為基本特征的玄學(xué)代替兩漢傳統(tǒng)儒學(xué)的時期,具有強(qiáng)力思辨能力的佛教教義在知識分子中無疑如魚得水,易于引起思想共鳴。上述兩種因素作用下佛教名僧層出不窮。具有豐厚的佛學(xué)素養(yǎng),并對當(dāng)時中國文化有著較為深刻認(rèn)識的名僧層出不窮為其成為一個相對獨(dú)立的文化群奠定了基礎(chǔ)。由此名士與名僧間的交流也就成為可能。
二、名士與名僧:個人層面上的考察
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傳下來有關(guān)名士與名僧間學(xué)術(shù)交流事跡記載的史籍主要為《世說新語》與《高僧傳》。《世說新語》由劉宋劉義慶組織編寫,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xué)、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門,共一千多則,記述自漢末到劉宋時名士貴族的遺聞軼事。南梁慧皎撰《高僧傳》主要記載東漢永平至梁天監(jiān)間名僧事跡。《世說新語》中記載名士與名僧交往的事件敘述如下。發(fā)生在瓦官寺的事件有二:其一,“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shè)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dāng)是逆風(fēng)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鳳!’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其二,“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茍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yùn)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yùn)圣人邪?’茍子不得答而去”;事件地點(diǎn)在白馬寺的是“《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鉆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biāo)新理于二家之表,立異義于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4]260發(fā)生在會稽西寺的有,“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茍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於法師又作林法師)并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yōu)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fù)執(zhí)王理,王執(zhí)許理,更相覆疏,王復(fù)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4]266發(fā)生在東安寺的有,“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gòu)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dāng)對。王敘致數(shù)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jìn)。’王大慚而退”。
發(fā)生在祗洹寺的有,“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兇物。’復(fù)更聽,王又曰:‘自是缽釪后王、何人也’”。[4]568發(fā)生在豫章精舍的有,“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shù)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于軒庭,清流激于堂字。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yùn)用吐納,風(fēng)流轉(zhuǎn)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后不堪,遂出”。[4]775-776個人層面上交往首先表現(xiàn)出的特點(diǎn)是名士的學(xué)術(shù)謙恭。深諧般若學(xué)理的名僧就成為名士接納、學(xué)習(xí)的目標(biāo),此時名士往往以謙虛的態(tài)度接待名僧。“蜜天資高朗,風(fēng)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于物。晉永嘉(公元三零七至三一三年)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dǎo)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5]29-30“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lǐng)軍供養(yǎng)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無論是王導(dǎo)將帛尸梨密引為我輩中人還是王洽停車靜候法汰,這種對名僧的推崇顯然源自于名僧掌握豐富的佛教般若學(xué)知識。名士的學(xué)術(shù)謙恭表明以名士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在當(dāng)時具有很強(qiáng)的學(xué)習(xí)自覺性。這種學(xué)習(xí)自覺性顯然是思想界破除儒家獨(dú)斷式判斷之后以玄學(xué)為出發(fā)點(diǎn)展開認(rèn)識論與邏輯概念的討論之過程中對知識之渴求的外在呈現(xiàn)。這種外在呈現(xiàn)表明處在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中國文化具有較強(qiáng)的進(jìn)取力。如果說名士在交往過程中獲得的是般若學(xué)所隱含的概念體系構(gòu)建和思辨性思維方式的啟發(fā),那么名僧在交往過程中獲取的不僅是名,而且還有利。南渡之前,許多名僧在經(jīng)濟(jì)上處于困難之境。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后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quán)救饑爾,無為遂負(fù)如來也”,“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lǐng)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但是渡江之后,或有帝王襄助,如支遁之隱退或有大臣資助,如康僧淵。名僧很快就積聚了大量財富,以至于能夠買山建寺,過上優(yōu)裕的生活。康僧淵在豫章建寺,支遁買印山,“支道林因人就深公(竺道潛)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堯時隱士)、由買山而隱’”。名利的獲得對名僧有雙重作用:其一,名氣與財力有利于傳教事業(yè)的展開。如帛尸梨密去世后,成帝為表悼念而在其墓旁建高坐寺以及后來謝琨贊助建寺均因密而起。“蜜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fēng),為樹剎冢所。后有關(guān)右沙門來游京師,乃于冢處起寺。陳郡謝琨贊成其業(yè),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世說新語》對此事亦有記載,不過建寺人記為晉元帝,余嘉錫在箋疏中考證因咸康為成帝年號,因此建寺追憶帛尸梨密者應(yīng)為成帝而非元帝。(詳細(xì)論述參見《世說新語》(上),第119-120頁。)再如前文所講康僧淵所建豫章精舍事。其二,過于注重名氣的獲得使名僧往往拘于世俗而不能自拔,這又成為其弘法之障礙。前文所引殷浩求學(xué)《小品》事件。《世說新語》引語林言“浩于佛經(jīng)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fù)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僅因恐懼名聲有損,在王羲之的勸說下,支遁便駐足不前,不敢與殷浩相談。支道林尚且如此,況乎他人。為此,慧皎不再作名僧傳,而作高僧傳,“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shí)之賓也。若實(shí)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記;高而不名,則備今錄”。當(dāng)然在以《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為基點(diǎn)考察名士與名僧的個人交往時我們應(yīng)對這兩部著作不同認(rèn)知視角給予高度關(guān)注。以支遁退隱事件為例,《世說新語》的敘述是,“支道林還東,時賢并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yuǎn)。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fù)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高僧傳》的敘述則是,“詔即許焉,資給發(fā)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并餞離于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萬)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由上述事例可見,《世說新語》通過對這一事件中謝、蔡不計前嫌的敘述來宣揚(yáng)魏晉名士的風(fēng)流,而《高僧傳》則據(jù)此來強(qiáng)調(diào)支遁學(xué)行風(fēng)范對時人的影響。二者相比,《高僧傳》具有較強(qiáng)的護(hù)教性。這是我們需注意的。
三、名士與名僧:文化交往層面上的考察
東晉南朝名士與名僧間文化交往主要圍繞玄學(xué)與般若學(xué)之間的交鋒與融合而展開。玄學(xué)由漢代道家思想、黃老之學(xué)演變發(fā)展而來的,意在以思辨思維探究事關(guān)“本末有無”的終極問題。就本質(zhì)而言,玄學(xué)是漢代道家思想、黃老之學(xué)與儒家經(jīng)義相結(jié)合而成的哲學(xué)思潮。般若學(xué)是依據(jù)《般若經(jīng)》而起,關(guān)于佛教義理的一種佛教哲學(xué)思潮。般若學(xué)的核心是“緣起性空”。“性”指諸法之體性、理性,“空”指諸法皆由眾緣假合,沒有自性。東晉南朝名士與名僧間學(xué)術(shù)交流對中國思想發(fā)展的影響是多重的。總體而言,玄學(xué)與般若學(xué)的互通是名士與名僧溝通的橋梁。名士通過解讀般若來深化建構(gòu)在玄學(xué)基礎(chǔ)上人與自然、社會與宇宙之認(rèn)識;名僧則通過談玄來推進(jìn)以般若學(xué)為代表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潛優(yōu)游講席三十余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nèi)外兼洽”。“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欲與支道林辨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名士與名僧交往首先促進(jìn)了玄學(xué)的發(fā)展。玄學(xué)的發(fā)展經(jīng)歷四階段:一、正始玄學(xué),以何晏、王弼為代表,代表作有《無名論》、《周易注》與《老子注》,“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為其核心思想;二、竹林玄學(xué),以嵇康、阮籍為代表,代表作有《嵇康集》、《阮籍集》,竹林玄學(xué)本質(zhì)在于“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三、元康玄學(xué),以裴頠、郭象為代表,代表作有《崇有論》和《莊子注》,“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郭象)”是其核心思想;四、江左玄學(xué),以張湛、韓康伯為代表,代表作有《系辭注》和《列子注》,“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張湛)”為宗旨。玄學(xué)四階段發(fā)展的共同點(diǎn)在于試圖超越儒學(xué),確立擺脫社會人生束縛、回歸自然,從而獲得身與心的完全自由。為了達(dá)到這種自由,名士們在本體論外需要思考現(xiàn)象與本質(zhì)之間存在何種關(guān)系,肯定與否定之間又有何種聯(lián)系存在。上述問題是儒家判斷式文化所缺少的。但佛教般若學(xué)通過“諸法性空”“中道實(shí)相”解答了現(xiàn)象與本質(zhì)間關(guān)系,通過“假有”“性空”解答了肯定與否定的思辨關(guān)系。這些發(fā)生在名僧間理論的提出與思辨的展開對名士所主倡的玄學(xué)之發(fā)展與成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名士與名僧交往其次促進(jìn)了佛教的中國化,具體表現(xiàn)在佛教般若義理中國化解讀與佛教文化功能中國化兩個方面。般若義理玄學(xué)化我們可以以般若學(xué)“如性”的解讀為例。如性本意為“如實(shí)在那樣”,輾轉(zhuǎn)來自婆羅門教。儒家重現(xiàn)實(shí)傳統(tǒng)影響下的中國文化中概念的表達(dá)均要求有現(xiàn)實(shí)事物的對應(yīng),缺乏對抽象概念的界定,“如性”的翻譯就成為一個難題。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對現(xiàn)實(shí)事物的理解與其本身往往有一定偏差,常常以“不如實(shí)在那樣”的形式出現(xiàn),因此“如性”也具有“空性”的含義。學(xué)者們在翻譯“如性”時首先比對玄學(xué),將其翻譯為“本無”。而玄學(xué)意境中的“本”與“末”相對,“無”與“有”相對,其意義變?yōu)槿f物從無而生,完全脫離了印度佛學(xué)之本意,成為以印度文化為外衣,內(nèi)則為中國本土思想之表達(dá)般若義理中國化之產(chǎn)物。佛教文化功能中國化可以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事件中:道安強(qiáng)調(diào)宗教對社會教化作用,改印度佛教以個人或眾生本位為以國家和社會為本位;道生強(qiáng)調(diào)通過個人內(nèi)心的自我完善而頓悟成佛,摒棄苦修成佛論;慧遠(yuǎn)協(xié)調(diào)佛教與儒家政治倫理、道家出世哲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提出中國佛教神學(xué)基礎(chǔ)三世報應(yīng)說,在民眾間宣揚(yáng)通過念佛、觀佛等手段未來進(jìn)入極樂世界;羅含為佛教業(yè)報輪回注入中國固有宗法觀念。這些思想的提出均可視為佛教文化功能中國化的具體表現(xiàn),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為適應(yīng)中國社會而作出的自身調(diào)整。
四、名士與名僧:哲學(xué)層面上的考察
名士與名僧交往對中國哲學(xué)在本體論、認(rèn)識論以及思維方式等方面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名士與名僧學(xué)術(shù)交往在哲學(xué)層面上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在本體論方面。《道德經(jīng)》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fù)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是對宇宙本體起源的一種探索和認(rèn)識。這種探索與認(rèn)識在阮籍《達(dá)莊論》中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從而成為玄學(xué)本體論的基礎(chǔ)。僧肇在《寶藏論》中解讀《道德經(jīng)》宇宙起源論時將“陽”比附為清,為心,將“陰”比附為濁,為色。僧肇談到,“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yè)因,遂成三界種子”。玄學(xué)從“道”出發(fā),以陰陽認(rèn)識宇宙起源,以此來追求自我意識與客觀精神的同一,而佛教般若學(xué)則通過論述客觀世界的虛妄,宣揚(yáng)通過般若智慧來獲得對宇宙本體起源的真實(shí)認(rèn)識,進(jìn)而達(dá)到覺悟與解脫。但是不論是名士所倡導(dǎo)的對自我意識與客觀精神的同一的追求還是名僧所倡導(dǎo)的通過般若智慧獲得覺悟與解脫其共通之處在于將宇宙本體起源論引申社會生活,將社會人生之道與宇宙精神合為一體。因此,名士與名僧交往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哲學(xué)的本體論。名士與名僧交往豐富與發(fā)展的第二個哲學(xué)領(lǐng)域是認(rèn)識論。儒學(xué)思想指導(dǎo)下,為了維護(hù)一元政治下的宗法制度和社會秩序,所采用的認(rèn)識論是無需嚴(yán)密論證和邏輯推理的直言式判斷。讖緯經(jīng)學(xué)中以天意神授的方式對人與自然、社會與宇宙的關(guān)系進(jìn)行表述就是這種判斷在兩漢時期的具體表現(xiàn)。但是這種直言式判斷只是儒家形而下的、封閉式的認(rèn)識表述,在佛教理論中是不存在的。“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若有不即真,無不夷跡,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也。”僧肇《不空真論》從認(rèn)識與變化總是相對的視角出發(fā),就事物認(rèn)識規(guī)律做了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認(rèn)識角度的闡釋。名士與名僧交往在哲學(xué)層面上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哲學(xué)思維方式的影響上。佛教表詮遮詮式思維(即在正概念、反概念提出的基礎(chǔ)上,闡述中概念,這從本質(zhì)講是一種肯定與否定相結(jié)合來認(rèn)識事物的辯證思維方式。)取代了儒家直斷式思維方式,進(jìn)而豐富了中國思想的哲學(xué)思維。例如對空色關(guān)系的理解上,傳統(tǒng)思維范式下,空為空,色為色,時人在探討“微”這個空與色之間的轉(zhuǎn)換概念時就很難理解。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思維中,“微”要么屬于空,要么屬于色,是不能夠既空又色的。因此而生佛教般若學(xué)發(fā)展史上的六家七宗之爭。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是僧肇。僧肇對空的解釋超越與涵蓋了現(xiàn)象世界的假有與精神世界的真有,通過辯證思維最終解決了人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疑惑。總之,名士與名僧交往既促進(jìn)了玄學(xué)的成熟,也促進(jìn)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名士與名僧的學(xué)術(shù)交流使作為異域文化的佛教及其哲學(xué)思想在中國開始流通。因他們的交往,古代中印文化實(shí)現(xiàn)了初步和平融合。這是人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舉。
作者:劉建華 單位:西北大學(xué) 延安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