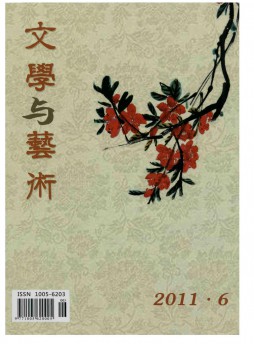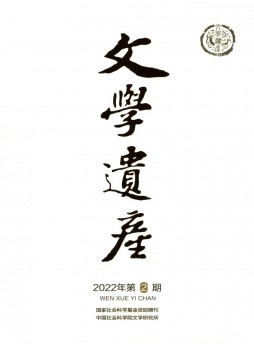漢文學傳播論文:民俗文學對漢文學傳播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漢文學傳播論文:民俗文學對漢文學傳播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汪力娟汪力智單位:云南紅河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云南紅河州國土資源局
哈尼族土司與漢文化傳播
哈尼族世居于大山深處,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他們受中央王朝的影響很小,與漢族社會聯系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哈尼族就被中央王朝所統治,與漢族社會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哈尼族土司一開始是迫于中央王朝的壓力,必須要加強漢文化的學習和教育。如在清初,清政府頒布了云南土司世襲的辦法,其中就明確規定土司的襲位者和其他子弟必須接受漢文化教育。據《云南通志稿•學校志》載:清政府“題準云南土司應襲子弟,令各該學立課教訓,俾知禮儀。
俟父兄謝事之日,回籍襲職。其余子弟,并令課讀。該地方官擇文理稍通者,開送提學考取,入學應試”。就這樣,哈尼族土司在長期接觸、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逐漸被漢族先進的科技和文化所折服,進而使自身學習和接受漢文化成為一種自覺行為,他們從自身做起,積極學習、傳播漢文化,引導哈尼族接受、崇尚漢族文化。
(一)使用漢姓,傳播漢族文化
使用漢姓,是哈尼族土司積極接受、傳播漢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哈尼族傳統社會普遍使用“父子連名”家譜。這是一種特殊的家譜,其實質是父系制家庭結構、血緣及財產繼承關系的體現;其形式是父親名字的后一個字(音節)為長子名字的前一個字。例如:黑嘎(父名)———嘎嘮(子名)———嘮篩(孫名)……長久以后,就會形成一串長長的父子連名譜系。”
天啟《滇志》-《臨安府•土司官志》記載:“各長官司,俱本土羅倮倮、和泥(哈尼)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匯之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從元朝起,哈尼族的首領們,一旦被中央王朝封為土司,他們都有這樣的心態,即:為表明自己的進步,表明自己與漢族官員沒有差異,便紛紛使用漢姓,如王、龍、錢、羅、李、白、張等。據嘉慶《臨安府志》-《土司志》記載:“明初,土司阿英歸附,賜姓錢,授副長官,世襲。于是,一些哈尼族土司開始帶頭使用漢姓,拉開了在哈尼族地區吸納、傳播漢文化的序幕。有資料描述:哈尼族土司龍者寧,在入貢京師時,得以參加明成祖親臨的端午節,景仰了大都的先進文化盛況,深受感染,他返鄉后,每年都在自己的轄地如期舉辦漢族的這一節日慶典。再有哈尼族土司龍上登,曾赴京受職,在京逗留期間,酷愛漢文典籍,回到家鄉后,興建學校,建蓋文廟,還親自撰寫碑文,論述孟子學說等。由于他的親自倡導,漢文化在他所統治的哈尼族地區得以順利傳播,讓當地的哈尼族群眾有機會較早地接觸到漢文典籍。在明朝末年,龍上登土司的女兒便懂漢文典籍,能工描山水、花卉,顯露出深厚的漢族文化功底。土司們開啟了哈尼族使用漢姓的先河,哈尼族群眾緊跟效仿,于是,漢民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間被普遍使用,漢族文化也如春雨潤物,融化于哈尼民族的生活。
(二)啟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高層統治,傳播漢族文化
土司制度設置之初,哈尼族土司因缺乏漢文化知識而深感事業難以順利進行,在不斷的實踐摸索中,哈尼族土司們漸漸意識到,讓那些學問深厚的漢族知識分子來協助自己的統治,才能盡快地改變這種被動的統治局面,于是他們便開始用高薪聘請自己信得過的漢族知識分子為自己謀劃,讓他們參與到自己的統治行列中來。這些受重用的漢族知識分子協助土司出謀劃策,辦理外交事宜以及一些具體統治措施。例如建筑風格、軍事裝備、典章法規、器物、監獄等,都效仿漢文化模式構建和設置。
在這個過程中,漢文化也被潛移默化地注入到哈尼族土司制度機體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文化的影響在哈尼族土司制度中日愈濃厚,同時也直接影響到轄區內平民百姓的思想意識和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他們緊跟效仿,使得漢族文化在哈尼族社會中得到迅速接納和傳播。紅河思陀(地名)土司李呈祥(1900—1977)聘請由武漢大學畢業的漢族知識分子廖伯英為他的參謀,使他在上世紀40年代前后那些飄搖動亂的年代中,各項事業都得到順利發展,其傳奇的人生功業在當地廣為流傳。
興辦教育,傳承漢族文化
哈尼族土司在與漢族長期交往中,感知到漢族不僅有先進的文化,而且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于是,一些開明的土司便積極開辦學校,興辦教育,想讓自己的后輩能更早、更多地學習漢文化知識。
如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當時元江府向中央王朝奏請辦學時說:“時元江府言,土官子弟、編氓多愿讀書,宜設學校以教之。詔從之。”土司們不斷聘請漢族知識分子到自己的轄區當教師,興辦各類學校,傳授漢文化知識。土司和其他富裕家庭弟子得以進入學校讀書,系統地學習漢文化知識。
如哈尼族末代土司李呈祥,堪稱是樂于興辦教育事業的杰出代表。他從小便接受漢文化教育,曾先后到過石屏、昆明及南京求學,獲得了不少新知識和新思想,他的統治較之其父輩開明、進步,不僅對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讓步政策,還大力鼓勵發展手工業和農貿集市,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他創辦“思陀高等小學堂”,聘請文化知識較高的漢族教師講學,為漢文化在哈尼族地區的傳播創造了良好條件。更可貴的是他所倡導的學習漢文化的風氣,還對周邊地區的哈尼族青少年產生極大的影響,吸引他們前來求學,他還對那些家境貧寒而學業優異的學生給予幫助,培養了許多哈尼族知識分子,為上世紀40年代后期共產黨領導下活躍在滇南地區的邊縱十支隊輸送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受到各階層人士的信賴和稱贊。
結語
在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哈尼族土司,曾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方面對轄區內的平民百姓加以嚴酷統治和剝削;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優勢,以啟用漢姓、聘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高層統治、興辦教育等多種形式和渠道,將漢族文化微妙地納入到哈尼族傳統社會機體之中,開創了哈尼族吸納、傳播漢族文化的歷史先河,為哈尼民族的不斷發展壯大做出過積極貢獻。
今天,漢文化對哈尼族的影響已滲透到哈尼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漢文化與哈尼族文化正在哈尼族地區和諧交融,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