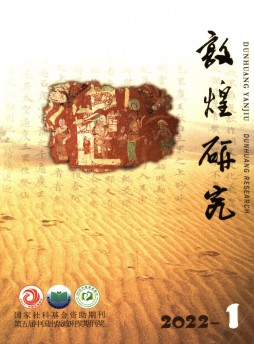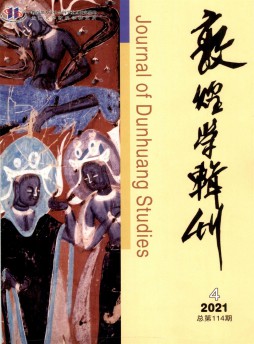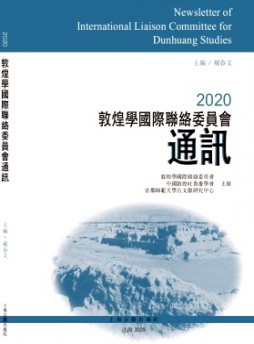敦煌哲學的建構途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敦煌哲學的建構途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哲學”建構的近代路徑及對孕育“敦煌哲學”的啟示
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術體系建構,基本上是跟隨西方近代學科劃分的風氣大勢起舞的。文藝復興前后,隨著科學精神與商業氣息的聯袂趨勢加劇,歐洲社會物質財富開始涌流,“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給精神分工的細致化、精密化提出了要求并創造了可能,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也慢慢蘇醒,但時代風氣已經慢慢被商業化后面的實用主義所主導。與此相對應,作為最古老學科的哲學,自身蹈空臨虛的性質使得其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在不斷興起的學科劃分熱潮中,人們發現必須首先找到這個學科賴以存身的依據,這就不得不和哲學打交道,使得哲學又被學科的建構熱潮推動、拱衛而獲得額外的學術殊榮。因此,哲學在學術界獲得的重視與現實當中遭受的冷遇成了一個奇怪的扭結,這實際上也預示著科學精神與現實生活在形成張力當中成為時代精神的塑造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哲學這個詞開始慢慢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在近代化運動中占得先機的日本人,學術理路上也先行一步。日本翻譯家西周在處理philosophy這個詞匯的時候,一時拿捏不準,幾經討論,大約在1873年左右,最后才定名為“哲學”。由于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極強的親緣性,向中國古代經典借力是日本近代大規模翻譯熱潮的一個普遍做法。西周等人在《爾雅》中發現“哲”具有“聰明睿智(哲,智也)”之義,便創制“哲學”一詞來指稱philosophy。這里有幾個問題應予澄清:其一是哲學一詞在當初日本人的語境中實際上是一個區別性概念,因為他們發現philosophy在當時泛漢語文化語境中(指處在漢語文化籠罩下的中日韓等東南亞地區)并沒有一個對應的詞匯,尤其不同于累世流傳的儒學,因此才有“哲學”一詞的應用而生。其二是當時西周并沒有嚴格遵循philosophy的含義進行翻譯,因為此一詞直譯過來就是“愛智學”,而翻譯成“哲學”就消減了智慧運動的情緒化動力———愛,這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誤譯。這個誤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哲學”在傳入漢語界之后所經歷的悲喜兩重天的命運,被一些人認為是智慧之學而獲得了空前關注,又由于形而上的品性在現實中不適當地被各種權力所借用,產生了所謂的大眾哲學等匪夷所思的現象。其三是西周當時并沒有厘清哲學作為思想的座架對西方運思軌跡的奠基性作用,導致東亞國家基本上在近代性即知性角度理解哲學就成了一個蕭規曹隨的歷史慣性,而不知道哲學本真含義的演變蘊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絕大多數學人在近代意義上理解哲學就不足為怪。其四,中國學術界引入“哲學”一詞,實際上面臨著如何與傳統的學術體系劃分兼容、如何正確理解西方思想核心等問題,而當時的引入者如黃遵憲、梁任公諸君尚未具備那種縝密運思的能力,至少沒有做好哲學般運思的準備。其五,哲學的傳入并在中國學術界立身之后,就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即“哲學在中國”和“中國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被馮友蘭等人敏銳地意識到了,并把哲學當作一種民族生存經驗的自覺理論樣式而予以暫時性解決,這為“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在21世紀初葉成為學界熱點埋下了伏筆。單憑哲學詞匯的創制看,它肯定是一個舶來品,或者作為一個學術范疇,哲學是外來詞,因為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典籍當中,并不能找到一個確然存在的“哲學”,雖然早有“哲人”、“哲夫”等說法。同時,哲學在西方學術分類當中,起著架構性的作用,它是一切學科劃分的最終基座,近代以來的學科建制絕大部分是一個個從哲學當中逐漸分離出來的。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術傳統,確然看不到“哲學”的支撐作用。
近世學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幾乎都認定雖然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之名,但一定有哲學之實。這樣的作法是,最早謝無量等人的《中國哲學史》其內容與中國思想史幾乎沒有區別;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認定哲學就是研究“人生切要問題”的學問,然后幾乎不假思索展開了對“中國哲學史”的寫作;張岱年等人認定哲學內容大致相當于中國傳統中的義理之學。馮友蘭比較清醒地認識到,必須把哲學與科學予以區分,否則就成了哲學在中國。在其名著《中國哲學史》中這一問題雖然并沒有講透徹,但沿著馮先生的思路前推,可以得出的結論似乎是:哲學與特殊民族的特殊運思習慣相關,它不但是運思的經驗與成果的總結,更是一個運思的軌跡反應。這也意味著,哲學實際上反映著一種面對世界的思維架構,它因不同的生活習慣、歷史傳承而具有各自的特點。但如果僅僅這樣推理尚不夠,因為這會把哲學無限泛化,讓每個不同的人或民族都似乎有不同的哲學,這反而失去了“學”的本意。近代以來的“學”意味著有特定概念和研究對象,有著通約化的語言,是可學的,可理解的。由此只有具有群體所遵循的、穩定有效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運思軌跡和經驗,才可能被稱之為哲學。胡適、馮友蘭在“中國哲學”范式建構中居功至偉,但他們共同受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其“哲學觀”屬于新實在論是大家的共識,此看法也構成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主流觀點。這樣,(中國)哲學就具有了“宗教與科學”的性質,但又不同于二者。作為面對世界的運思經驗,哲學實際上擔當著世界觀的作用,但這個世界觀是靠哲學自身內在的演化規則來執行、達到的,因而不同于宗教化不假思索的信仰。也正在世界觀的意義上,哲學也區別于科學,因為,科學要剔除了人的主觀性,達到假設的某種客觀性,而哲學恰恰包含著人的情緒、信仰、運思習慣等,它是一個現實的然而又是歷史的產物,單靠科學的冷靜觀察或客觀實驗無法提供一個完整有效的世界觀。此問題在近代科玄論戰中得以發酵,決定著中國哲學的發展路向,也說明哲學在中國學術語境中的多義性。與其相對應,1930年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言中首倡“敦煌學”,只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其時并沒有對敦煌學的內涵外延予以清晰考察,更多指整理和研究敦煌發現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后來敦煌學的研究內容越來越廣,并逐漸成為國際顯學。可見,一個學術概念在創立之初,其含義的完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敦煌哲學”創立之初當應有此學術雅量。
二、從哲學的分類到“敦煌哲學”成立之可能
如果沿著philosophy所展開的軌跡回眸,那個“物理—后物理”所構成的形式化運思構架附著了幾乎所有哲學的概念,這些概念的核心是“本質—現象”所衍生的。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有清算這個構架的沖動,直到現象學和分析哲學的崛起,前者懸置爭論,后者企圖通過嚴格的語義分析,一勞永逸清除形上學(后物理學)所制造的語詞假相。如果說傳統哲學糾纏于是與存在,哲學就是一門關于“是”的學問,現象學以不“是”什么自居,分析哲學則以語義診斷而存身。這兩大現代哲學思潮在當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詰難,因為現象學作為方法有效并附有啟發性,但其創始人胡塞爾一開始所謂的“本質直觀”就有重蹈傳統形上學的嫌疑,這也是海德格爾后來背離現象學運動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分析哲學在一開始構建嚴格的“邏輯語言”,直到后來維特根斯坦等人意識到語言的“游戲性”,重新回到生活(自然)語言,意味著堅決清理哲學語言已經幾乎不可能了。但無論遭遇怎樣的困境,當代歐美哲學界慢慢意識到,所謂哲學,就是那個決定了西方人運思構架與軌跡的東西,并且這個東西,是古希臘人的一種創造,是遵循嚴格的形式邏輯,沿著“本質—現象”這一構架展開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里達等人認定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民族運思方式都不是哲學化的,也正是類似這一論斷,引爆了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如果把“費羅索菲Philosophy”當成西方人的那個大思,那么沿著這個思路就會對通常的學科劃分造成致命性傷害。它意味著哲學就是一個運思的構架,無法分類且無法修飾,因而由此所謂的管理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科學哲學等等,其合法性都會受到質疑。如果哲學是無法分類的,那也意味著,我們即將討論的敦煌哲學也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分析哲學一個很重要的成果是,語言必須回歸日常生活,它是人們之間的游戲。這也意味著包括學術語義在本性上也并不是嚴格的,因為它的有效性依賴另一方的認同。后現代哲學在解構“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沖動中,無法避免由此而導致的價值虛無。福柯敏銳地洞見到知識與權力具有同構關系,但無法清理掉這個中心。這也意味著,約定俗成的東西仍然具有它的某種合理性。
在近代興起的學術劃分熱潮中,哲學也被一次次附加了許多修飾語,隨著研究重點和實用性的雙重需求,哲學被實用主義、存在主義、新實在論等一次次命名。如果考慮到這個熱潮,意味著當初哲學這個詞在中國學術界誤打誤撞、生根發芽,實際上已經具有了自己的合法性。語言的有限性意味著命名本身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因而哲學可以嚴格意義上理解,也可以在更寬泛意義上看待,即哲學可以狹義化,也可以廣義化。哲學在中國學術界的落地生根,還并不完全由語言的游戲性決定,它實際上牽涉到中國思想經驗與一個被哲學構架決定了的整個西方學術體系如何對話的問題。只有通過共名的哲學,才可能依循現代學術語言對中國傳統運思經驗予以解讀,否則會面臨著無法對傳統進行言說的尷尬。近代中國民族苦難史昭示,完全依照過去本有的漢語學術劃分框架,已經無法在科技主導的時代精神中站住腳,即使中國傳統運思方式持久有效,但必須經過現代化的闡釋,形成一種對話的姿態才能讓其內部的活力得以彰顯。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的成立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我們今天談論敦煌哲學開出了思路。它在源頭上給我們論述敦煌哲學以言語的合法性。對于那些把敦煌與哲學連接起來持有懷疑態度的人來說,至少在近代哲學傳入中國的歷程看,我們的判斷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當敦煌學已然約定俗成進入中國學術界的視野后,就面臨著其自身內涵的理論闡述問題。姜亮夫先生曾說:“……所以我們現在將研究敦煌所有的東西的學科稱之為‘敦煌學’。這個‘學’字是什么意思呢?‘學’就是說一種有系統,有原始發生、發展到衰落的次序的,就叫做學。敦煌就是這種東西,就是學。”[1]但學之為學在嚴格的學科建構中,必然有著哲學的機理,或者,在近代的學科建構中,通常只有把學科的基礎掛靠到形上學(哲學)上,這個學科的成立才就具有了合法性。就敦煌學來說,這一問題至今并未得到解決。在現有的學科分工中,敦煌學在社會、人文科學的序列中排位就處在尷尬的境地。周一良先生認為:“從根本上說,‘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律、成體系、有系統的一門科學。”所以他贊成把“敦煌學”永遠留在引號當中。[2]但這個困難并沒有阻擋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研究范圍日益擴大,從剛開始的敦煌遺書研究擴展到敦煌藝術、敦煌史地、敦煌簡牘、敦煌學理論等等,其中敦煌學理論就必須直面敦煌學內在根據的問題。“從目前看,敦煌學也確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獨特的研究對象”。[3]也有人認為:“敦煌學顯然并非一門單一的學科,它實際上是一門包括許多學科的群體性學問。”[4]概而言之,敦煌哲學在語義的本質上具有成立的可能性,在敦煌學的發展當中更具有找出其內在隱線、為學科之成立找到合法性的迫切需求。
三、敦煌哲學的根本依據:敦煌性
敦煌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立,必然有其內在的根據,這就要求必須對敦煌哲學本身的特質予以揭示。在“敦煌哲學”的構架中,“敦煌”構成了修飾語,人們不僅會心生疑竇:為何是敦煌?假如把敦煌僅僅看作一個地域性概念,馬上會引發人們的質疑:是否能夠把敦煌置換成別的地名?譬如天水,譬如酒泉,甚而甘肅哲學豈不更加顯得地域遼闊?這里首先必須回應敦煌作為飾詞的基本含義。作為地名意義上的敦煌出現,在漢語文獻中最早見于《史記》,當時張騫在給漢武帝的報告中明確提到了敦煌二字。后世論者也曾爭論敦煌地名的由來,有的甚至說敦煌一詞來自于中國古代少數民族。[5]但漢代以后敦煌作為地名,其基本含義以這樣的解釋為準:“敦,大也,煌,盛也”。按我們的理解,弄清一個地名的來歷是必要的,這是文化學上造成蝴蝶效應的初始因子,即文化具有歷史的慣性,初始形式具有決定后世發展的巨大作用,但過分糾纏于詞源學的考察并無法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秘密,有些詞匯在歷史的流變中發生了重大的語義變遷,以訛傳訛、歪打正著的事情大為存在。如果我們僅僅把敦煌當作一個地名,就無法讓其文化含義凸顯,而“偉大輝煌”的本意則透露了“敦煌”的含義,歌頌軍功武力的地名外溢出來,變遷為一個富有精神承載力的重大詞匯,這甚至可以成為理解敦煌哲學的一個入手處。
在西漢初設河西四郡的時候,敦煌作為正式的地名被固定下來,這里成了幾大文明的交匯點,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是各種文化交流的大動脈。20世紀以來,由敦煌學不斷派生出新的學科分支,如敦煌文化、敦煌文學、敦煌藝術等等。這些學科按其學科的建制而言都有各自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和學科特質。顏廷亮先生曾對敦煌文化有過自己的總結:“敦煌文化的獨特的基本精神或者說敦煌文化的靈魂,乃是根深蒂固的中原情結,乃是透骨入髓的鄉土情感,乃是這兩者水乳般的交融為一。”[6]穆紀光先生在對敦煌藝術哲學進行總結的時候,“沒有對敦煌藝術涉及的所有哲學問題進行普遍論述,而是從‘存在論’的觀點出發,對敦煌藝術形式背后所隱含的人的生存狀況進行分析和敘述。”[7]特別是對佛教經典的改造與發揮出發,闡發其蘊涵的藝術哲學的。兩位先生顯然已經觸發到了作為文化構架的敦煌可能附著的精神內涵,顏先生首次討論了敦煌文化精神,穆先生從藝術哲學的角度給予了敦煌哲學一個有益的視角,那就是佛經精神與世俗化生活在敦煌的融合。但依照這些的觀點尚不能讓敦煌自身作為哲學的生發地予以現身。季羨林在多年前對敦煌的文化定位有過精妙的總結,它對于理解敦煌現象乃至發掘敦煌哲學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他斷言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只有在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發生了匯流,“世界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8]接下來一個問題是:為何是敦煌而不是別的地方?作為一個地名的敦煌為何能夠承載起一種精神的囑托?敦煌作為四大文明的匯流處,其重要地位不可替代,百年前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不但見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輝煌,更讓敦煌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集散地逐漸浮現。敦煌哲學的成立當從“希臘性”意義上予以揭示。黑格爾曾說,當歐洲人提到希臘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精神家園感。這源自希臘從一個古代的地域國家名稱走向了文化的飾語。當我們歷經努力,打開敦煌哲學的地形地貌的時候,也許那種久久回蕩在歷史當中的精神家園感也會重現光輝,帶來久違的歷史人文溫度,久沐在敦煌文化中的古代人有著強烈的中原情結,這個情結實際上也是家園感的反映,而近世以來,凡是被敦煌文化所吸引感染的學人,無不在“敦煌”的感召下生發出巨大精神敬畏與心靈震動。由此,敦煌本身就成為一種飾詞,敦煌性恰恰對照敦煌的“偉大輝煌”而生,它沒有脫開敦煌地名的含義,但又超越于具體的地域名稱。如果對照希臘性人的理性精神的覺醒,則敦煌性應當是基于偉大空間的共生性這一特質,所表現出的大氣包容、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也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能說是敦煌哲學而不能輕易妄言酒泉哲學、甘肅哲學等這樣的說法。敦煌哲學存在的內在根據是什么?是人為創制一種哲學還是基于歷史精神的結構發現一種哲學?那是一種精神的暗流,是歷史的隱線,是潛伏在偉大輝煌的敦煌文化下的精氣神,它所需要的是重見天日,需要在歷史的河床中找到它奔騰的力量。因此,敦煌哲學并不是建構,而是一種發現,一種荒蕪的精神地貌的重新耕作,煥發新的思想朝氣。
當我們把哲學從嚴格的證明體系引申過來,讓其接受其他語詞修飾的時候,是否意味著哲學可以隨意接受打扮?如果這樣做,勢必失去哲學作為引導人之所思的嚴格性,或者哲學失去其作為思維構架的基礎性作用,那么,即使敦煌哲學成立,也僅僅是為當前學界假借分科命名的學術圈地運動提供了一個談資,而無法讓作為嚴肅的學科保持久遠的生命力,更無法對敦煌學的研究給出一個方法論的支持。但如果在成果斐然、引世矚目的有關敦煌學的研究中,潛心再潛心,發現那紛繁的敦煌現象后面的精神主線,它不但橫貫敦煌學的始終,而且能夠為未來有關敦煌學的研究提供一個方向性甚至是方法論的支持,那它不是敦煌哲學又能是什么呢?反過來講,敦煌文化在歷史上輝煌了上千年,并且在20世紀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它所涉及的內容不但囊括了中國古代各家各派和所有文化形式,而且成了古代文明的集散地,各種文化、各種文明都在此有著深深的烙印,敦煌曾是世界文明的大舞臺,并能夠保持長久的輝煌,而不是過眼沙塵。這就啟迪后人,一種文化能夠長久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內在理由。敦煌文化龐雜博大而有序不亂,百花競放又不失下自成蹊,這必然有種隱含的精神張力來支撐其繁盛,否則敦煌文化就早已在歷史的風沙中坍塌了。那么,這個精神張力是什么呢?唯有敦煌哲學。嚴格意義上說,敦煌哲學不是建構的問題,而是發現的問題,后人僅僅是發現了敦煌哲學并予以命名。敦煌哲學的成立必須從揭示其自身的特質入手。
四、從中國哲學的核心理念回到敦煌哲學
欲對敦煌哲學的特質予以揭示,就必須對中國哲學的特質予以審察。敦煌哲學概念只能隸屬于中國哲學,這二者的關系是子集與母集的關系。但敦煌哲學也一定不完全等同于中國哲學,它一定是把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質加以張揚、發揮、放大了,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精神特質。以下當我們討論中國哲學特質的時候,實際上是根據敦煌哲學的特殊性,更加強調了中國哲學某一方面的特質。如果我們放棄對“哲學是一個證明體系”的硬性規定,而把哲學當作更加始源性的運思基座,則中國哲學當是中國人運思的軌道及其痕跡。從“物理—后物理”的運思構架出發,在形式邏輯的指引下,具有時空含義的世界,具有邏輯冷硬性的真理,具有存在意義的自我等一系列概念被創制出爐,這種具有幾何性的思的經驗并不為中國古代人熟悉。或者我們更加有把握的說,這種運思經驗沒有成為中國學人的主流方式。中國哲學的特質恰恰是在中外哲學對比中現身的,但對比的前提必然具有某種相似的問題、相同的對象。就中國哲學處理的主題而言,它要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人與神靈的問題予以自我解讀,就此來說,中西方哲學都在“自我—他者”這個主題的框架中來審視人在宇宙當中的地位。無論是后世以恩格斯為代表所謂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是自尼采、海德格爾之后西方人對“存在與存在者”的執著,實際上都是人面對天地萬物、自我神明,要對自我進行一個價值定位,尋訪到心靈歸宿地,由此找到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此來說,范鵬先生關于敦煌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總結甚為恰當,他認為:“‘極高明而道中庸’作為整體的中國哲學的境界和精神當然也就必然是敦煌哲學的精神。”[9]在完成形式化的運思框架后,自亞里士多德以降,哲學就主宰了西方人的運思軌跡。兩千多年來西方人一旦思想,就是哲學的,就是處在“物理—后物理”的張力扭結中,而一旦給出一個不言自明的開端,如公理、概念、假設、條件等,就會在邏輯思維的推力下,呈現出定理、推理、結論等。中國哲學面對天地萬物并不是采取嚴格的形式邏輯,而是一直處在自然思維的要求中,它在開端處把人看作天地萬物的一部分,人是萬物之靈長,但絕非萬物之主宰。換言之,主體意識在中國哲學那里是隱忍的,而不是張揚的。中國人在處理“自我—他者”這個思維扭結的時候,并不是把自我抽離出來,而是首先把自己歸于這個整體,元素寓于關系中,關系的作用遠遠大于單個元素的性質,陰陽五行的生克變化都沒有固定的好壞,而是遵循彼此的平衡。在中國哲人眼里,人是萬物之一種,人的最高境界并非是從萬物當中突出出來,而是如何讓自己化為萬物的一部分。就此來說,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既是古代生活經驗的理性總結,也實際上是一種賴以安撫自身存在的信仰。中國哲學既是有理性的,但又由于在運思的開端處,就把自身看作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所以又十分重情感。后世引申出的辯證思維、整體觀念、實事求是等實際上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發揮。人與萬物的須臾不可分,這既是理性的認識,又是生活的信仰,使得中國哲學在整體中見部分,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講求共贏共生,最后發展出一個基本理念:和。
就此來說,中國哲學并沒有開出嚴格幾何學意義上的世界,沒有原子化的自我,沒有過分的“自我—他者”關系的嚴重緊張,而是給出了具有理性和情感相交織的天下、道理、和合等。后世論者如列維•布留爾等人在人類學的考察中有所謂“原始思維”的說法,把這種比附思維區別于現代人,或者把一切具有比附性質而不符合邏輯分類的思維都歸結為原始思維,帶有明顯的邏輯原教旨主義。從處理矛盾關系的角度看,中國哲學尚和而西方哲學尚斗的路徑是清晰的,且很難說誰高孰低的。也許,從一個局部講,尚斗的理念更加具有戰斗力,更加直接有效,但以道觀之,從萬物并流而不相害的信念出發,尚和恰恰表明了萬物變遷的常態,散發著濃重的溫情主義。以張載為代表提出的所謂“太和”觀念中,中國古人早看到了矛盾雙方斗爭的一面,但更多強調“仇必和而解”,這區別于18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所謂“矛盾的斗爭性是絕對的”。這一運思框架在中國哲學的基本符號即陰陽五行、八卦動靜中已經完全具備。在“陰陽”的運思框架中,世界被中國人早早劃分為可見與不可見的兩部分,而《周易》中強調的“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給出了運思的軌跡與歸宿:道。人之所要做的僅僅是找出不同層面的道,并力爭掙脫“技”的束縛。健康的家庭、社會與個人面對的問題是如何保持陰陽五行的動態平衡,而并非偏于一方去消滅另一方。這就使得和的觀念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理念。和不是沒有原則的和稀泥,不是騎墻的鄉愿,而是堅持中庸之道的包容,是“多樣性的統一”。在中國古人的世界里,關系比單獨的元素更加重要,真正的強大不是征服性的主宰,而是無聲的滲透,保持和的狀態。同時,中國哲學的原始眼界是陰陽,把天地萬物首先劃分為可見與不可見兩部分,這就為泛神靈的存在留下了余地,中國哲學不僅僅是理性的產物,也包含了信仰的對象。
五、敦煌哲學可能的核心觀念:和
欲讓敦煌哲學現身,必須涉及到對敦煌哲學可能的特質之揭示。文明的交匯地為數不少,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明的邊緣地帶都可能是文明的交匯地,為何敦煌能夠占有特殊的位置?季羨林先生臨終前還念念不忘對敦煌以及新疆哈密地區文化豐富性的總結,并一再聲稱敦煌是世界的。把這個問題再清晰化,也即為何敦煌能夠負載起一種精神氣質的囑托?亦即敦煌哲學為何能夠成立?可能的回答是:敦煌哲學將中國哲學的和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敦煌哲學必然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凡是對敦煌哲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對中國哲學的再認識。敦煌哲學的特質將深化人們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反過來,中國哲學的總體特征也必將規定著敦煌哲學的內涵。除過和之外,中國哲學里還有許許多多的價值理念,如重倫理綱常、重天道王權,由此引發對孝道、仁愛等諸范疇的闡發。但我們認為,在敦煌哲學中,和的觀念是根本性的,它起到了統攝敦煌學的作用,也應是敦煌哲學之魂。我們前面從中國哲學的核心觀念“和”入手,對中國哲學進行了初步總結。而我們看到,敦煌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立,恰恰在于其內在構架中時時處處都體現出的和的觀念。首先,從和的表現看,敦煌作為幾乎古代所有文明的交匯地,讓所有的文明形式都留下了痕跡。無論是中國儒家文明,還是古希臘文明,還是印度佛教文明,抑或阿拉伯伊斯蘭文明,都在敦煌有著各自的痕跡,都書寫了自己的特質。甚而慢慢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其他古老文明形式,也都在敦煌留下了深深的足跡。這些足跡通過敦煌石窟以及百年前發現的敦煌藏經洞為載體,每個文明形式甚而是亞文明都能夠在敦煌找到曾經的足跡,這種包容大度沒有“和”的精神支持是無法想象的。
其次,敦煌不是僅僅把各種文明做了簡單的雜糅攪拌,不是簡單的文化集散地,而是創造出了屬于自身的文化形式即敦煌文化,也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在敦煌石窟為代表的藝術形式中,反映的不僅僅是佛家的處世理念,而是常見儒家的圣賢、道家的神仙,凡圣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世俗生活與神圣生活統為一體,甚而希臘文明、伊斯蘭文明的理念、特質也得到了反映。一部經文能夠有多種文字書寫,一個石碑鑲嵌多種文字,這些百川匯流、有容乃大的特質在敦煌隨處可見。換言之,各種文明形式都能夠在敦煌找到自己的根脈,并且都是生長在鮮活的體質上的,敦煌是各種文明之匯流,更是各種文明之融合地、生長地。取百家之長而獨樹一幟,這表明了“和”對各種文明因素的強大的粘合、再生能力。反過來,只有和才能夠把形式迥異的文化母體統攝到一個整體中。再次,應該看到各種文明交匯形成新的文化形式的難能可貴,或者非常萬難。就此來說,世界上唯有敦煌,才能以一個地域來命名一種精神的形式。在敦煌文化生成的時候,四大文明形式都已經各自成熟。文明形式的成熟意味著對文明他者的拒斥,這尤其反映在宗教文化中。由于宗教信仰的絕對性,必然會導致宗教信仰的排他性,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常見的事情,尤其歐洲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戰爭史。而敦煌恰恰包容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明形式。唯有和才讓文明劍拔弩張的對峙柔軟下來,消弭這種張力只有中國做到了,更進一步說,只有敦煌做到了。
最后,我們反過來推理,敦煌之所以能夠形成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藝術形式,必然與一個根本的觀念有關,而融和各種文化的劍鋒,軟化各種文明的張力,唯有和。敦煌的雕塑、舞蹈、繪畫等藝術形式從屬于更大范圍的敦煌文化,而敦煌文化所反映出的海納百川、文明競流的特征,必然有種基本的理念來支撐它,除過中國哲學中的和,無他者可以替代。和在這里不但是一種價值的出發點與歸宿點,而且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種思索軌跡,是處理問題的基本方法。正因為有了和,敦煌成為了自身,正因為有了和,敦煌哲學立起來了,敦煌文化獲得了靈魂,敦煌藝術有了大的依托,敦煌具有了精神家園的意味。和不是簡單的元素堆積,不是原子變量的力量拉扯,而是動變中關系的此消彼長,是指向生的取長補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敵我決斗。敦煌哲學之成立恰恰在于以一種決然而然的特質把中國哲學的和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它向世人昭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和合共處的,是可以實現共贏的,是能夠在相互學習中獲得共生效應的。和不但是價值觀,而且能夠成為一種方法論。從這里出發,敦煌哲學不但躍出隱蔽的精神領地,而且給世人理解敦煌文化給出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附著在“敦煌”身上的一切文化現象都可能變得豁然開朗、別有洞天。敦煌哲學以和為基本內核,它會引導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學理念,“和而不同”表明了萬物的變化的動力,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在差異中找到共同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和而生氣”,氣聚為生,氣散為死,敦煌哲學的和與中國哲學重生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完全一致。有了和,中國哲學講求的生生不息就有了源頭;有了和,處理棘手的重大問題就有了新的思路,這迥異于西方所謂“哲學就是學會死亡”的基本理念。同時,它也給出了日后可能有待深入的重大研究領地,譬如:“和”的自身的依據是什么?“和”如何在敦煌哲學中占有主導地位并在敦煌文化中得到更加細致有序的體現?敦煌哲學為何能夠把尚和的中國哲學基本理念發揮到極致?它對未來的文明對話或者新的文明樣態有何啟發?等等。這將是另外的問題。
作者:成兆文單位:甘肅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