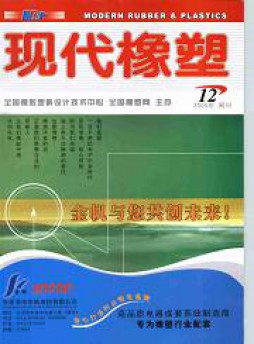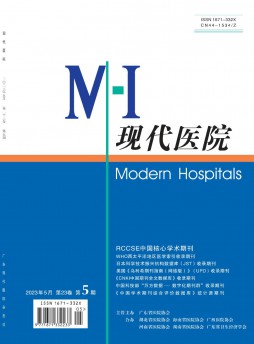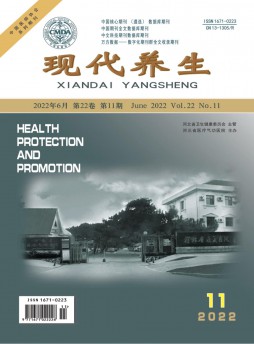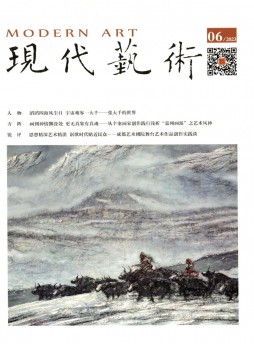華忱之的現代文學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華忱之的現代文學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近年來,王富仁、錢理群等學者在總結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經驗和學術傳統時,都以開闊的學術視野和精準的學術眼光,描繪出了一副“多點共生”、“眾聲喧嘩”的上世紀80年代研究地圖:“以第一代學者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除了北京的李何林、王瑤、唐弢,上海的賈植芳、錢谷融外,還有南京的陳瘦竹,山東的田仲濟、孫昌熙,河南的任訪秋,陜西的單演義和四川的華忱之等。1作為建國后四川大學現代文學學科重要奠基人的華忱之先生,2014年是其誕辰100周年,可我們發現學界不僅關于先生的紀念文章寥寥,甚至連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多不知曉。情勢如此,原因自然不一,但學術研究重“中心”輕“邊緣”的地緣性特征亦難脫其咎。而我們對華先生的深切紀念,對學科偏陋的實際糾正,都離不開對其現代文學研究成果進行認真研究和總結。
華忱之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和四川大學的相遇,有待于新文學史課程的設置和高等院校調整兩個要素的形成。1950年5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并成立課程改革小組。2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將“中國新文學史”設置為各大學中國語文系的必修課程,學科創建之初,專任教師奇缺,許多學者從古典文學研究轉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華忱之與王瑤、單演義等人在不同的地域“順”勢而動,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第一代學者。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開始,華忱之與蒙文通、蒙思明、繆越等學者一道,由華西大學調任四川大學。3此后,他與林如稷、李昌陡、陳思苓、易名善等成為現代文學教研室的第一批成員。綜觀華忱之的現代文學研究,其對象主要集中在魯迅、郭沫若、茅盾和曹禺等幾位經典作家上。如果不為尊者諱,我們很容易發現華忱之的話語體系中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征,比如將魯迅和曹禺等作家的創作道路,描述成逐漸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的歷程。但是如果僅僅滿足于尋找出意識形態的蛛絲馬跡,這是懶惰主義;若以此來否定一位學者的學術造詣,這是虛無主義。實際上,上述類似的話語,很難看作是華忱之獨有的思想結晶,而更宜視作整個學術界不可違抗的權威性解釋。我們如何排除這些廣泛存在的官方定義和宏大命題導致的表面干擾,發現學者本人對現代文學學科的整體性觀照和對文學現象的獨特評斷?首先,他在80年代初即呼吁加強對現代文學研究中薄弱環節——抗戰文藝的研究。華忱之的憂慮不僅是對80年代以前抗戰文藝研究情況的歷史總結,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研究成果偏少的背后,還隱含著“價值估計不足”、“正面戰場關注不夠”等一些深層問題。
他本人在新時期對經典作家抗戰期間創作的研究便是對其呼吁的最佳實踐。比如他發現一些文學史著作對郭沫若抗戰時期的雜文散文語焉不詳甚至只字不提,于是作了《論郭沫若抗戰時期的雜文》,對郭沫若抗戰時期的雜文集《羽書集》《蒲劍集》《今昔集》《沸羹集》進行了細致梳理,認為“《羽書集》所收,大多偏重于動員大眾的抗戰宣傳”,“《蒲劍集》、《今昔集》中收入的則多是關于學術研究,特別是有關屈原研究的一些文章”,并呈現了郭沫若的斗爭精神、人民本位意識和“文化界領袖”的作用。5除此,華忱之還搜集整理了抗戰時期郭沫若的舊體詩文佚作,并對郭沫若的《歸國雜吟》《戰聲集》《蜩螗集》《潮汐集•汐集》等舊體詩進行了知人論世的闡釋,凸顯了郭沫若“愛國抗日的思想感情,以及與積極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革命現實主義創作特色”。華忱之對于曹禺、田漢在抗戰期間的文藝研究更側重在史料的發掘和闡釋上。他以話劇《黑字二十八》和曹禺所作的戲劇講座《編劇術》為中心,記錄了曹禺在抗戰初期的一些創作活動。對于曹禺解放前關于戲劇理論和編劇方法唯一的且“印本不多,流傳不廣”的一篇講話,他詳細介紹了其版本出處,并對其內容進行了撮要簡述。此外他還介紹了1938年重慶舉行的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第一屆戲劇節紀念大會上的《全民總動員》的演出概況,并將曹禺和宋之的合作完成的四幕話劇《黑字二十八》與《全民總動員》的異同進行了重要的辨析。7華忱之對田漢在抗戰期間活動及貢獻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田漢與《抗戰日報》的關系上。他強調了田漢1938年在長沙創辦《抗戰日報》的艱辛勞作,并對“保存不多”、“殘缺不全”的《抗戰日報》的《創刊之詞》、重要作品如田漢的抗戰京劇《新雁門關》等做了重要的史料重述。8其二,他特別強調“繼承傳統,借鑒外國”的治學方法。作為這個學科第一代學者,華忱之“一貫強調立說著書,必須在繼承借鑒,批判吸取中外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別辟蹊徑,獨創新機”
在“融貫中西古今”的理念自覺下,華忱之能迅速洞悉現代文學經典作家作品中的中國民族特色和外國文化影響,并以能否批判性地吸收古今中外文藝經驗,作為評價作家成就的重要標準。當然,華忱之對“中西古今”的強調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在遵行“延安講話精神”,創作“具有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民族的群眾的新文化”的五六十年代,他不得不跟隨“厚今薄古”的時代主調,但依然曲折而執著地表達著他對古典傳統的敬意。在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所作的《繼承民族傳統,發展詩歌創作》上,他強調:“深入生活、向群眾學習是主要的意面;但批判地繼承中國民族、民間的優秀文藝傳統、吸收外國進步的文藝遺產……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并指出現代詩歌要向古典詩歌學習“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形式運用和講求韻律”、“刻畫藝術形象和熔鑄語言”等方面的優點。10到了八九十年代,在一個更加自由的學術空間中,華忱之的魯、郭、茅、曹研究不再局限于強調這些經典作家所受的經典傳統影響,而是直陳他們對外國文學的借鑒。比如《魯迅對中外文化的理論主張與批評實踐》一文從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角度詳述了魯迅對世界優秀文化的借鑒。在《繼承傳統,借鑒外國》一文中,他更將茅盾和郭沫若進行了橫向比較,將二人卓越的文學成就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繼承和西方文藝的借鑒”基礎上。
盡管華忱之一再強調所有的繼承和借鑒,都必須建立在“有分析有批判”的“正確態度和方法”上,這顯然有失牽強。可如果聯系到80年代初整個現代文學學科普遍認為“離開了對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聯系的考察,就不可能弄清現代文學的‘現代化’特點”,那么這種“牽強”的強調則實屬其來有自。它既是學者個人順應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心理趨勢的自然反映,同時也是他們這一代學人壓抑已久的文化多元化和文學現代化思想的集中綻放。其三,他強調文學研究必須關注作品本身的分析解讀。這種似乎并無新意的呼吁其實具有極強的歷史和現實針對性,即反對“單純用思想性分析代替藝術性分析”、“把作品的主題思想與藝術性分析互相割裂開來,孤立開來”,而應該“把思想性藝術性結合在一起來分析”,因此,他在五六十年代的課堂上,就非常注意對作品藝術性的分析。他的學生曾就此批判他“用了很多時間對聞一多臧克家前期的詩作,從題材的選擇到字句的推敲,作了仔細的講解。相反,對張志民的‘死不著’,及柯仲平的一些詩,則寥寥數語,敷衍了事”。中文系召開的檢查批判大會,也將其教學中“偏重作品的藝術技巧,忽視作品的政治內容”作為他“錯誤”文藝思想的重要內容。
在對曹禺劇作的研究上,華忱之可謂最全面深入地貫徹了他的作品的細膩分析和對作家的深切理解。比如評論界曾長期認為《雷雨》“是以蘩漪和周樸園的矛盾沖突為中心的”,他則認為“侍萍與周樸園的矛盾才應該是《雷雨》戲劇沖突的中心和主線”。16此外,有論者常將蘩漪看作“向周樸園進攻的主將”,而他并不認為蘩漪與周萍的“畸形的病態的‘亂倫’之愛”是個人解放的正當之路,對蘩漪的反抗性也持保留態度,認為“她畢竟是一個‘舊式女人’,因此,她既不可能像《傷逝》中子君那樣,也不允許像娜拉那樣,毅然決然沖出封建牢籠,另尋新的出路”17。比如他對《日出》中陳白露“竹均時代”和“白露時代”的矛盾糾葛;對《北京人》中思懿的“虛偽,自私,詭詐,潑辣,口蜜腹劍的戲劇性格”,曾文清的“軟弱,萎靡,空虛而懶散”,愫芳“從夢幻到覺醒,從覺醒到出走的曲折過程”概括得都頗為精當。特別是他對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被認為是失敗之作的《原野》別具慧眼,高度肯定了“《原野》在曹禺的創作道路和美學追求上,別辟蹊徑,獨具一格,表現為曲折的前進,而不是‘前進中的曲折’”20。因為強調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同情,所以華忱之特別反對文學研究的先入之見。這一面體現在批評左翼作品政治訴求影響了藝術性探索,指出抗戰初期的作品“由于政治任務迫切,作家們廉價的熱情的發洩,因而往往寫的不深刻”;另一方面體現為對海外現代文學研究的武斷保持警惕,比如深刻地指出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作品的文學價值為原則”背后的意識形態偏見;比如批評劉紹銘抱著曹禺“作品華而不實”的“藝術偏見”做研究,難免貶抑失當。23這種兩面開弓,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眼光即使在今天也是難得的。二如果要為華忱之從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研究轉向的學術道路和對融貫古今中西的強調、對作家作品充滿理解之同情的學術特色尋找背后的“故事”,那么“清華學風”是其極為重要的學術傳統和學術動力。即使在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北京高校學科體系中,古典文學在大學文學院尤其是文學系的課程體系中仍居正統。清華中文系從1928年起制訂了詳細的課程表,中國文學史、文選、詩、賦、詞、戲曲、小說等各體文學課程成為必修課,此外還開出過《樂府》《歌謠》《詩經》《楚辭》《唐詩》等選修課。1933年課程調整后,諸如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國音韻學概要、國學要籍、中國文學史等國學課程仍是最基礎的必修課內容。更為重要的是主講這些課程的教師都是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楊樹達、陳寅恪、趙元任、俞平伯、王力等知名學者。華忱之肄業清華期間,深受陳寅恪、聞一多、劉文典、錢穆等先生影響,對考證、校勘、考據和唐詩、清代樸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過著“在學問里找到了非常的愉快”的“學生派的生活”。25此后,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孟郊年譜》還因取材廣泛,引用文獻書目達一百二三十種,考證方法不拘一格,深受聞一多先生稱許,認為:“本系歷屆畢業論文,用力之勤,當以此為首屈一指。”26另一方面,楊振聲擔任中文系主任期間(1928—1930),曾提出“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的教學方針。
中文系進入了所謂的“新文學試驗時期”,開始為學生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朱自清主講)、當代比較小說、高級作文等課程。加之,清華大學戲劇教育和戲劇活動相當活躍,華忱之耳濡目染,自然對新文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更何況華忱之欽慕的聞一多、朱自清在將研究的重點和興趣轉向古典文學前,就已經是著名的新文學作家了。所以,如果說朱自清、聞一多一代是在新文學創作和研究中,發現了古典文學的價值,那么華忱之、王瑤這一代更像是從古典文學的趣味中,感念到現代文學的情懷。清華中文系對外國語言和文學的重視也是一貫的。中文系早期規定必修的外文課程達24學分,1933年后改為18—22學分,約占本系必修課程總學分的1/5左右。其中外語方面除必修兩年英文外,還鼓勵選修第二外語。外國文學方面,早期要求必修西洋文學概要和西洋文學專集研究。此外還鼓勵學生選修現代西洋文學、中西詩之比較等英文講授的課程。29華忱之強調借鑒外國文化對于作家創作和學者研究的重要性,一個重要的淵源即在此。實際上,他的清華同學王瑤也特別注重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之間的關系,前后著文《五四新文學所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現代文學中的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等。這再次證實了“清華學風”對一代學者的深沉鐫刻。華忱之強調深入時代和生活、深入人物形象,對作家作品報以理解之同情,也與“清華學風”息息相關。1988年王瑤在《念聞一多先生》一文中,借用了馮友蘭關于近代學術史“信古”、“疑古”、“釋古”的論斷,來概括清華文科的學風——“我們應該在‘釋古’上多用力,無論‘信’與‘疑’必須作出合理的符合當時情況的解釋。”王文雖以聞一多、朱自清的研究為此論表率,但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撰寫的審查報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主張,可視作對“釋古”的回應和發揮,且可視作對“清華學風”的另一種表述:“主張對歷史書寫者或闡釋者的‘主觀’性進行正面的規訓:即通過對古人立說之環境、背景以及對話對象的‘真了解’,而在‘神游冥想’中與古人出于‘同一境界’,從而作出合理的批評與闡釋。”
王富仁曾區分過兩種學者,一種是“實中求是”之人,因為這個“是”是自己“求”出來的,不同于當時世俗的見解,所以“孤傲”——文求“是”,行為“理”,人尚“獨”。還有一種是“是中求實”之人,因為“是”的是別人及其作品,所以不“孤傲”,沒有架子——文求“實”,行為“事”,人尚“真”。前者如陳獨秀,后者如單演義。32其實,后一類也包括華忱之這樣的學者。但華忱之這一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又豈是一個“真”字所能概括?他們曾是這個學科的奠基者,隨后又是這個學科的守護者,之后還是這個學科的傳遞者。他們捍衛經典作家尤其是魯迅的正面意義,同時也為作家們被忽略被貶低的特色和價值辯護;他們強調對作家作品的理解同情,這也構成了80年代的主體性思想萌生的本土性資源;他們還引導著現代文學學科和年輕一代學人始終與優良的學風學統緊緊相連。他們身上的確難以擺脫國家意識形態的某些束縛,也可能缺乏豐富的研究著述,但是他們的許多研究和判斷至今仍然鞭辟入里,他們曾經的許多憂慮和期待至今仍然亟待解決。
作者:康斌 單位:四川大學錦江學院文學與傳媒系
- 上一篇:基礎教育校本培訓探討范文
- 下一篇:抗日救亡文學中的在地意識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