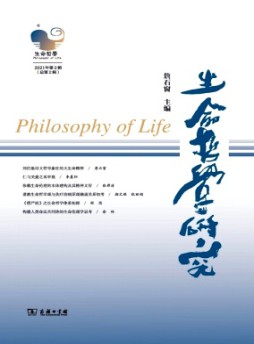方東美對(duì)哲學(xué)發(fā)展的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方東美對(duì)哲學(xué)發(fā)展的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學(xué)術(shù)交流雜志》2015年第七期
一、中國(guó)哲學(xué)的基本精神
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的理解向來(lái)見(jiàn)仁見(jiàn)智。方東美立足于中西印哲學(xué)的比較,概括出他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有機(jī)統(tǒng)一、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等。
(一)有機(jī)統(tǒng)一,廣大和諧。方東美用機(jī)體主義來(lái)概括之。從消極面而言,機(jī)體主義反對(duì)將人與物視為絕對(duì)的孤立系統(tǒng)而互相對(duì)峙,反對(duì)將千差萬(wàn)別的大千世界轉(zhuǎn)化機(jī)械秩序,反對(duì)將變動(dòng)的宇宙看作再無(wú)發(fā)展余地和創(chuàng)進(jìn)可能的封閉系統(tǒng)。從積極面而言,機(jī)體主義“旨在統(tǒng)攝萬(wàn)有,包舉眾類(lèi),而一以貫之……形成一在本質(zhì)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攝、旁通統(tǒng)貫而廣大和諧之系統(tǒng)”[。總之,機(jī)體主義反對(duì)對(duì)立的、機(jī)械的、封閉的宇宙觀,主張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的、圓融的宇宙觀。
(二)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內(nèi)在于有機(jī)統(tǒng)一、廣大和諧的宇宙觀中。方東美指出,西方哲學(xué)在論人的時(shí)候往往把他與上帝、自然疏離開(kāi)來(lái),而中國(guó)哲學(xué)“其論人也,恒謂之德合天地,或性體自然。性天之道,存乎創(chuàng)造化育歷程,萬(wàn)物一切,各正性命,以盡其性。人之天職,厥為參天地,盡物性,據(jù)乎德,發(fā)乎誠(chéng),黽勉以行,盡性而天,精義入神”。中國(guó)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人與天地、性與自然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和交互滲透。“儒家、道家、大乘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等……其崇信‘混化萬(wàn)物,一體同仁’之教,則初無(wú)二致。……此種‘萬(wàn)物一體同仁’之情,存而養(yǎng)之,擴(kuò)而充之,發(fā)揮極致,即為圣智圓滿(mǎn)”,體認(rèn)天人合德不僅是入圣的路徑,甚至可以“當(dāng)下即圣”。
(三)雙回路向。方東美在解釋超越形上學(xué)時(shí)已經(jīng)談到這個(gè)問(wèn)題,認(rèn)為這種形上學(xué)表現(xiàn)為超拔提升和居高回視兩個(gè)方向。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超化的意義,說(shuō):“關(guān)于中國(guó)形上學(xué)之諸體系,有兩大要點(diǎn)首宜注意:第一,討論‘世界’或‘宇宙’,不可執(zhí)著其自然層面而立論,僅視之為實(shí)然狀態(tài),而應(yīng)當(dāng)不斷地予以超化:對(duì)儒家言,超化之,成為道德宇宙;對(duì)道家言,超化之,成為藝術(shù)天地;對(duì)佛家言,超化之,成為宗教境界。自哲學(xué)之眼光觀照宇宙,至少就其理想層面而言,宇宙應(yīng)當(dāng)是一大超化之世界。中國(guó)形上學(xué)之志業(yè),即在于通透種種事實(shí),而蘊(yùn)發(fā)對(duì)命運(yùn)之了悟。超化之世界,是一深具價(jià)值意蘊(yùn)之目的論系統(tǒng)。”方東美認(rèn)為,有事實(shí)世界和價(jià)值世界,有現(xiàn)實(shí)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國(guó)哲學(xué)不是將它們分裂開(kāi)來(lái),而是統(tǒng)一起來(lái),中國(guó)哲學(xué)以事實(shí)世界或現(xiàn)實(shí)世界為起點(diǎn),但絕不執(zhí)著于此,而是通過(guò)超化,把事實(shí)世界和價(jià)值世界、現(xiàn)實(shí)世界和理想世界統(tǒng)一起來(lái),實(shí)現(xiàn)前者向后者的超拔提升。
(四)立乎中道。在談到心物關(guān)系時(shí),方東美認(rèn)為中國(guó)哲學(xué)的特色是立乎中道、心物不隔。他指出,在西方,哲學(xué)系統(tǒng)不建立于物質(zhì),即建立于精神。哲學(xué)思想內(nèi)容,乃游移于精神主義與唯物主義二者之間。在印度,凡超越系統(tǒng)皆尚精神,其俗界觀則從唯物。“然在中國(guó),哲學(xué)家之待人接物也,一本中道。立乎中道,遂自居宇宙之中心,既違天地不遠(yuǎn),復(fù)與心物不隔,借精神物質(zhì)之互滲交融,吾人乃是所以成就生命之資具。率性自然,行乎廣大同情之道,忠恕體仁,推己及物,乃不禁自忖:宇宙在本質(zhì)上元是一大生命之領(lǐng)域,其中精神物質(zhì)兩相結(jié)合,一體融貫。宇宙大全,乃是無(wú)限之生命界。中國(guó)哲學(xué)之悠久傳統(tǒng),皆沿習(xí)‘生命中心主義’之途徑,而向前邁進(jìn)發(fā)展。”立乎中道即是不偏于物亦不偏于心,而以人為中心把二者貫通起來(lái)。
(五)三才合一。方東美說(shuō):“柏拉圖于其《對(duì)話(huà)錄•斐德羅斯》篇中,追述乃師蘇格拉底盛贊依索格拉底(Isocrates)之言曰:‘斯人體內(nèi)有哲學(xué)!’克就典型之中國(guó)形上學(xué)家而論,吾人大可將該句倒轉(zhuǎn),翻作‘其哲學(xué)體系之內(nèi)有個(gè)人’,而呼之欲出者。問(wèn)題之關(guān)鍵是:何等類(lèi)型之人物、始配挺身而出,為中國(guó)哲學(xué)代言?……其人至少必須具備‘先知、詩(shī)人與圣賢’三重才性,集于一身,始足語(yǔ)此。”“蓋先知之最大關(guān)注,恒在于人類(lèi)之命運(yùn)及世界未來(lái)之歸趨;詩(shī)人雖向往未來(lái)幻境之福祉,然卻又往往逆轉(zhuǎn)時(shí)間之向度,回向過(guò)去,于過(guò)去黃金時(shí)代之畫(huà)幔上象其理想夢(mèng)境,而寄托遙深;圣賢既屬道德高尚、力行實(shí)踐之人,恒欲申展時(shí)間之幅度,無(wú)論過(guò)去或未來(lái),俱納諸不朽之現(xiàn)在之內(nèi),期于當(dāng)下履踐,使其崇高理想充分實(shí)現(xiàn),以求致乎其極,或庶幾乎?”能夠?yàn)橹袊?guó)哲學(xué)代言的人應(yīng)該是先知、詩(shī)人與圣賢三才合一的人,這也是方東美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知關(guān)注未來(lái),詩(shī)人關(guān)注過(guò)去,圣賢把未來(lái)和過(guò)去納入現(xiàn)在。中國(guó)哲學(xué)是宗教、哲學(xué)、藝術(shù)、道德的融合體,涵容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只有集宗教、哲學(xué)、藝術(shù)、道德修養(yǎng)于一身者才有資格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的代言人。
(六)思想連續(xù)。方東美指出,有兩點(diǎn)應(yīng)該注意到:一方面,就中國(guó)哲學(xué)的傳統(tǒng)而言,自先秦、兩漢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個(gè)共通點(diǎn),借司馬遷的話(huà)來(lái)說(shuō),就是“究天人之際”。另一方面,無(wú)論是哪一派的中國(guó)哲學(xué),借司馬遷一句話(huà)來(lái)說(shuō),就是“通古今之變”,無(wú)論是個(gè)人的、學(xué)派的或是產(chǎn)生自任一時(shí)代的,都表達(dá)出歷史的持續(xù)性,與其他各派的哲學(xué)思想發(fā)展彼此呼應(yīng),上下連貫,形成時(shí)間上的整體聯(lián)系。這兩個(gè)特點(diǎn)表現(xiàn)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上是有利也有弊。“利”是任何學(xué)術(shù)思想不能孤立于過(guò)去的已知條件之外,要兼顧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性以及未來(lái)的發(fā)展性,產(chǎn)生歷史持續(xù)性的效果。“弊”在道統(tǒng)觀念,思想易受到道統(tǒng)觀念的束縛和支配。比較之,西方哲學(xué)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性不足,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獨(dú)特的思想系統(tǒng),而中國(guó)哲學(xué)“通古今之變”,強(qiáng)調(diào)歷史的連續(xù)性,與其他哲學(xué)思想形成整體聯(lián)系。以上,有機(jī)統(tǒng)一、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三才合一、思想連續(xù)就是方東美所說(shuō)的中國(guó)哲學(xué)的基本精神。
二、中國(guó)哲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
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的研究雖然也有通史性意義,但有論述的重點(diǎn),所以在中國(guó)哲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上每個(gè)階段筆墨不均。總體而言,方東美認(rèn)為中國(guó)哲學(xué)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gè)曲折上升的歷程,持的是一種歷史進(jìn)化論的觀點(diǎn)。
(一)總歷程胡適的《中國(guó)哲學(xué)史大綱》把中國(guó)哲學(xué)史區(qū)分為“古代”(先秦)、“中世”(漢至唐)、“近世”(宋元明清)三大階段,馮友蘭的《中國(guó)哲學(xué)史》把中國(guó)哲學(xué)史分為“子學(xué)時(shí)代”和“經(jīng)學(xué)時(shí)代”兩大階段,勞思光把中國(guó)哲學(xué)史分為“初期”“中期”“晚期”三個(gè)大階段。方東美則以形象的方式勾畫(huà)出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的五大階段,“以一句不規(guī)律、三節(jié)步之詩(shī)行喻表之,現(xiàn)為缺末韻格(catalectic)”。虛線(xiàn)部分為第一階段,時(shí)間漫長(zhǎng),其源起及發(fā)展詳情俱不可考。據(jù)傳約經(jīng)歷四千來(lái)年,無(wú)疑系屬上古洪荒時(shí)代(公元前5042~前1142),隱涵一套“原始本體論”,中國(guó)形上學(xué)之基調(diào)表現(xiàn)為神話(huà)、宗教、詩(shī)歌之三重奏大合唱。第一音步為第二階段,屬“揚(yáng)抑抑”格,其重輕部分分別代表儒、道、墨三家所高度發(fā)展出的理論系統(tǒng)。這是有信史可征的一段神奇?zhèn)ゴ笾统善冢L(zhǎng)達(dá)九個(gè)世紀(jì)(公元前1146~前246),系中國(guó)哲學(xué)創(chuàng)造力之最盛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時(shí)爭(zhēng)鳴,競(jìng)為顯學(xué)。第二音步為第三階段,屬“抑抑揚(yáng)”格,其中足以看出傳統(tǒng)儒、道兩家盈虛消長(zhǎng),終于逐漸讓位于大乘佛學(xué)諸宗。這一階段為中國(guó)哲學(xué)之吸收與再創(chuàng)期(公元前246~公元960)。經(jīng)過(guò)一段漫長(zhǎng)的醞釀、吸收與再創(chuàng),最終形成具有高度創(chuàng)發(fā)性的玄想系統(tǒng)即中國(guó)大乘佛學(xué)。第三音步為第四階段,屬“抑揚(yáng)抑”格,代表公元960年至今,為形上學(xué)之再生期,表現(xiàn)為新儒家三態(tài),而俱受佛、道兩家影響。“吾人先后在新儒學(xué)(性、理、心、命之學(xué))之形式中,次第復(fù)蘇中國(guó)固有之形上學(xué)原創(chuàng)力,而新儒學(xué),亦多少沾染一層道家及佛學(xué)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為產(chǎn)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實(shí)主義型態(tài)、(2)唯心主義型態(tài)與(3)自然主義型態(tài)之新儒學(xué)。”第五階段應(yīng)該是中西哲學(xué)相互碰撞的時(shí)期,“倘音節(jié)排列再更進(jìn)一步,采缺末韻格,則余外之重音節(jié)部分,無(wú)疑顯指針對(duì)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攝納期。今日學(xué)界之中,凡觀察敏銳之士,皆不難處處嗅到此種氣息焉。”以上,總體上把中國(guó)哲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歸納為原始期、定型與最盛期、吸收與再創(chuàng)期、再生期、吸收攝納期。接下來(lái)談一下方東美與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歷程相關(guān)的未曾充分展開(kāi)的一些問(wèn)題。
(二)漢代哲學(xué)以及道教方東美認(rèn)為,秦漢從哲學(xué)方面來(lái)講缺乏創(chuàng)造力,“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風(fēng)浸衰,其號(hào)稱(chēng)一代祭酒者,固學(xué)者輩出,然俱非獨(dú)立之思想家。此段時(shí)期,少數(shù)哲匠不為雜家,即為批評(píng)家:前者如呂不韋、劉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輩中人即或仍談學(xué)論道(形上學(xué)),然其興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論及宇宙發(fā)生論為主題矣。通常雖多依原始萌芽科學(xué)(陰陽(yáng)五行之說(shuō))為基礎(chǔ),間亦訴諸詩(shī)意幻想。”但是,方東美對(duì)漢儒的治學(xué)方法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他指出,無(wú)論是從宋明儒本身的立場(chǎng)或是從以宋明儒“嫡傳”自居之現(xiàn)代學(xué)者的立場(chǎng),一般皆認(rèn)為漢儒之學(xué)一無(wú)是處:在學(xué)術(shù)上面是支離破碎,在方法學(xué)上面也是遠(yuǎn)離正題。然而,今天我們來(lái)談漢儒,在思想史方面,盡管漢儒之“微言大義”不免于以雜家及陰陽(yáng)家的思想栽贓到儒家正統(tǒng)思想之中,去歪曲它、誤解它,但所謂漢儒也不是一個(gè)單純的學(xué)派,無(wú)論是今文經(jīng)學(xué)還是古文經(jīng)學(xué),他們都有一個(gè)嚴(yán)正不茍的工作,就是所謂“解詁”,解詁的用意在于透過(guò)章句訓(xùn)詁而還原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講到孔孟的學(xué)說(shuō),就從文獻(xiàn)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實(shí)講明孔孟的經(jīng)典大義,而還原出那個(gè)時(shí)代的真正意義。從這一方面來(lái)看,漢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漢儒面對(duì)古代流傳下來(lái)的經(jīng)典,從不敢茍順?biāo)揭狻y發(fā)議論,盡可能地有一分證據(jù)說(shuō)一分話(huà),有一分師承做一分文章。這在漢儒而言,叫做“師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講《詩(shī)》,魯詩(shī)有魯詩(shī)的講法,齊詩(shī)有齊詩(shī)的講法;講《周易》,魯學(xué)有魯學(xué)的講法,齊學(xué)有齊學(xué)的講法;其它諸經(jīng),莫不如此,是絕對(duì)不能亂講的。漢儒的這種精神成就是我們不能否認(rèn)的。”
至于道教,方東美否定的地方偏多。他指出,道教的思想本身就是駁雜的東西。戰(zhàn)國(guó)時(shí)它的思想是神仙家言、方士家言。西漢時(shí)再同道家思想的余波結(jié)合起來(lái),后漢時(shí)才變成了一種偽托老莊道家哲學(xué)的道教。以后它又受了佛教的影響,所以它許多經(jīng)典都是模仿佛經(jīng)。這樣一個(gè)駁雜的東西,經(jīng)過(guò)了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的衰世。在佛教盛行于中國(guó)的時(shí)候,儒家無(wú)力反抗,還是道教打起中國(guó)文化的招牌與佛教周旋角力。方東美特別討厭張道陵之流對(duì)老子哲學(xué)的糟蹋,他指出,張道陵事實(shí)上是方士之類(lèi)的人,在宗教方面屬于邪教,在哲學(xué)上打著道家思想的招牌糟蹋道家的哲學(xué)。譬如張道陵說(shuō)“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把“道可道”解釋為早上吃了很美的早餐。這跟“道可道”有什么關(guān)系呢?而底下這句更不成話(huà),“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早上吃了很豐盛的早餐,到了晚上要排泄出來(lái)。這個(gè)打著道教旗號(hào)、推崇太上老君的鬼道,這樣糟蹋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這兩句話(huà)。再說(shuō)“兩者同出而異名”,本來(lái)在老子里面有兩種斷句方法,一方面指有無(wú)同出而異名,有時(shí)讀做“兩者同,出而異名”,但是鬼道的注解卻說(shuō):“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成精也。”這就越發(fā)不像話(huà)了,竟解釋成一方面小便,一方面泄精,就叫做“同出而異名”。而“玄之又玄”,他說(shuō)是“鼻與口也”,這根本是不知所云。張道陵在注釋老子五千言時(shí)如此侮蔑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事情。
(三)魏晉玄學(xué)方東美認(rèn)為,魏晉玄學(xué)的主題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結(jié)合起來(lái),但每位哲學(xué)家的傾向并不完全一致。“何晏、王弼出,玄風(fēng)復(fù)振,其旨則皆在調(diào)和孔老間之歧異,倡‘貴無(wú)論’以釋道。……何晏崇孔,故援道入儒;王弼宗老,乃援儒入道。然兩氏同以‘致一’為其玄學(xué)探究之基本核心,則毫無(wú)二致。”方東美進(jìn)一步解釋說(shuō),從王弼、何晏對(duì)儒家《周易》的詮釋中可以看出,上古以來(lái)兩支分道揚(yáng)鑣的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引者注)到魏晉時(shí)期有了結(jié)合的企圖,比如王弼把儒家的系統(tǒng)落到道家的系統(tǒng)里去,而何晏要把道家的系統(tǒng)落到儒家的系統(tǒng)里去。方東美還談到:裴頠與孫盛,“前者崇有而抑無(wú),蓋以絕對(duì)之無(wú)(至無(wú)),于生命界無(wú)以能生,故為虛而非實(shí),成性之道,無(wú)所用之。始生者,自生也;始有者,自有也,既非生之于無(wú),亦非亡之于無(wú).更非化之于無(wú),而是唯一之本體、真實(shí)無(wú)限,即有顯用者也。后者則另?yè)?jù)邏輯立場(chǎng),推演老氏之主旨,概歸諸剌謬不通、自相矛盾者”;向秀與郭象,“皆基于莊子哲學(xué),一方面,視‘有’、‘無(wú)’二名,乃相待觀成:無(wú)不能生有,有不能還無(wú)。至于二者孰更為根本,實(shí)乃無(wú)謂之爭(zhēng)”。
(四)道家哲學(xué)與佛學(xué)方東美認(rèn)為大乘佛學(xué)與道家思想有相同之處:“大乘佛學(xué),則由其證得之慧境,靈光燭照而展現(xiàn)于吾人之面前者,是為上法界與法滿(mǎn)界;于是,時(shí)間生滅變化界中之生命悲劇感,遂為永恒界中之極樂(lè)所替代。夫惟如是,佛家之解脫精神,乃能無(wú)人而不自得,逍遙遨游于詩(shī)意盎然之空靈妙境。臻此境界,佛家之精神,即能當(dāng)下渾然忘卻時(shí)間生滅變化界中之一切生命悲劇感,而徑與道家,尤其老子之精神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矣。”解脫、逍遙、空靈的精神境界是大乘佛學(xué)和道家所同有的。方東美認(rèn)為道家哲學(xué)對(duì)中國(guó)佛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王弼注《老》對(duì)般若哲學(xué)之影響,其著例也,觀乎道安及其同代諸賢情形,足見(jiàn)一斑。關(guān)于‘有、無(wú)’對(duì)諍,向有‘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之說(shuō)。……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佛學(xué)思潮,七宗競(jìng)秀,然其玄學(xué)主旨,則端在‘本無(wú)’,倡‘貴無(wú)賤有’,與裴頠之‘崇有抑無(wú)’針?shù)h相反,適成對(duì)照。茲以降,佛、道攜手,形成聯(lián)合陣線(xiàn),以對(duì)抗傳統(tǒng)儒家矣。”僧肇的“《般若無(wú)知論》及《答劉遺民問(wèn)》,字里行間,莊子之影響,豈淺泛哉”。“道生在精神上酷似老、莊,主張‘掃相即以顯體;絕言乃所表性。’蓋謂究極本體,既非可得解于權(quán)言之窮,亦不可盡求諸假相之歸。”
三、簡(jiǎn)要分析
綜觀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和發(fā)展歷程的闡釋?zhuān)覀兛梢宰鞒鋈缦聨c(diǎn)分析:
(一)方東美對(duì)形上學(xué)類(lèi)型的劃分基于中西哲學(xué)的比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但也有可以進(jìn)一步厘清的余地。自“西學(xué)東漸”以來(lái),中西文化發(fā)生了激烈碰撞。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群體開(kāi)始并逐步深入地探尋著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學(xué)的差異,梁?jiǎn)⒊?yán)復(fù)、胡適、梁漱溟、馮友蘭、賀麟、錢(qián)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fù)觀、張岱年、任繼愈、馮契、蕭萐父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討了中西哲學(xué)各自的特征,多數(shù)人認(rèn)為中國(guó)哲學(xué)的基本精神是實(shí)用理性,倫理學(xué)發(fā)達(dá),而知識(shí)論、邏輯學(xué)等相對(duì)薄弱。在對(duì)中西形上學(xué)特點(diǎn)的概括上,影響比較大的觀點(diǎn)是:西方哲學(xué)走的是外在超越的道路,把人類(lèi)的價(jià)值源頭歸結(jié)為外在的力量;而中國(guó)哲學(xué)走的是內(nèi)在超越的道路,把人類(lèi)的價(jià)值源頭歸結(jié)為內(nèi)在的心性。與此相關(guān),西方哲學(xué)的思維偏向兩分法,注重分析;中國(guó)哲學(xué)的思維偏向統(tǒng)一性,注重綜合。上述觀點(diǎn)不知何人最早提出,但方東美對(duì)形上學(xué)的分類(lèi)無(wú)疑表達(dá)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他所說(shuō)的超絕形上學(xué)指的是西方哲學(xué)以分裂為特征、尋求外在超越的形上學(xué),而超越形上學(xué)、內(nèi)在形上學(xué)則是典型的中國(guó)形上學(xué),以追求統(tǒng)一和諧為特征。這種宏觀的比較結(jié)論無(wú)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為我們把握哲學(xué)形上學(xué)的差異提供了重要思路。但從方東美對(duì)超越形上學(xué)、內(nèi)在形上學(xué)的論述來(lái)看,二者的界限似乎不甚清晰,前者強(qiáng)調(diào)宇宙與人的統(tǒng)一性,主張超拔和規(guī)范的“即理想即現(xiàn)實(shí)主義”,后者強(qiáng)調(diào)本體內(nèi)在于宇宙以及本體與現(xiàn)象的統(tǒng)一性,在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一性方面二者很難區(qū)分。方東美所說(shuō)的內(nèi)在形上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本體內(nèi)在于宇宙,與通常所說(shuō)的價(jià)值內(nèi)在于人的心性還是有所不同的。
(二)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的理解觀點(diǎn)明確,前后統(tǒng)貫,體現(xiàn)了一種高貴和樂(lè)觀的哲學(xué)精神。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的概括學(xué)界見(jiàn)仁見(jiàn)智,方東美的主要觀點(diǎn)是有機(jī)統(tǒng)一、天人合德、雙回路向、立乎中道等,其邏輯主軸是統(tǒng)一和諧,類(lèi)似于熊十力的“不二”。從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精神的概括中我們可以體會(huì)出一種高貴樂(lè)觀的哲學(xué)精神,這與方東美對(duì)哲學(xué)功能的理解有關(guān),他說(shuō):“偉大的哲學(xué)思想可以改造世界。它不像近代許多存在主義的思想家們,不僅是在那個(gè)地方演悲劇,而且是演雙重悲劇!甚至演三重悲劇!重重悲劇下幕以后,依然是精神局促于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心靈不能超脫解放,埋沒(méi)在這個(gè)‘最煩惱的世界’中。……假使哲學(xué)家要拯救世界,則決不能投身到黑暗罪惡的社會(huì)中去,而同流合污。哲學(xué)沾染了罪惡,那就是宣告它的精神死亡。哲學(xué)精神死亡了,如何能拯救世界?相反的是罪惡的世界征服了它。”[4]89-90方東美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不能沾染罪惡,哲學(xué)要拯救世界、改造世界;哲學(xué)不能總演悲劇,要超拔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方東美不論是對(duì)儒家哲學(xué)、道家哲學(xué)、佛學(xué)、新儒家哲學(xué),總是以一種景仰、欣賞、陶醉的態(tài)度去對(duì)待,極力挖掘其間的寶貴資源,為我們理解中國(guó)哲學(xué)傳統(tǒng)提供了一種樂(lè)觀向上的積極態(tài)度。
(三)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歷程的描述大致符合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的實(shí)際,但也有一定的疏漏。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歷程曲折進(jìn)步的理解是正確的,這是多數(shù)哲學(xué)史家都堅(jiān)持的觀點(diǎn),也是符合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的歷史實(shí)際的。大家通常認(rèn)為先秦時(shí)期、宋明時(shí)期是中國(guó)哲學(xué)的輝煌時(shí)代,但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不盡一致。勞思光強(qiáng)調(diào)的是孔孟和陸王的心性論哲學(xué),方東美強(qiáng)調(diào)的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國(guó)大乘佛學(xué)、新儒家。就此而言,把方東美界定為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確有可疑之處。與此同時(shí),大陸中國(guó)哲學(xué)史家在認(rèn)同先秦是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黃金時(shí)代的同時(shí),也注重其他動(dòng)亂時(shí)代的哲學(xué)成就,如:李澤厚比較看重魏晉時(shí)代,認(rèn)為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了純哲學(xué)、純美學(xué)等;蕭萐父更看重明清之際,認(rèn)為這一時(shí)期的啟蒙哲學(xué)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接合點(diǎn)所在。但無(wú)論怎樣,中國(guó)哲學(xué)都是在曲折發(fā)展中不斷進(jìn)步的,除勞思光的哲學(xué)史退化論之外,多數(shù)哲學(xué)史家如馮友蘭、張岱年、馮契等均持此見(jiàn),方東美亦不例外,這是一種正確的哲學(xué)歷史發(fā)展觀。由于方東美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的研究重點(diǎn)突出,所以難免有所疏漏。在總過(guò)程上,漢代哲學(xué)、魏晉玄學(xué)、唐代儒家哲學(xué)等筆墨較少。在先秦哲學(xué)中,對(duì)名家、法家、荀子等關(guān)注不夠。這恐怕與方東美《中國(guó)哲學(xué)精神及其發(fā)展》不是按照年代而是按照學(xué)派書(shū)寫(xiě)的體例有關(guān),雖不全面但重點(diǎn)突出。
作者:柴文華 谷真研 單位:黑龍江大學(xué) 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哲學(xué)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