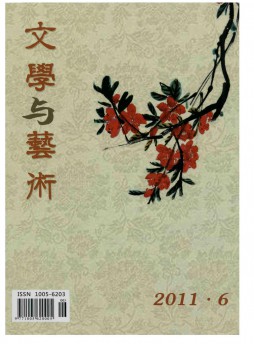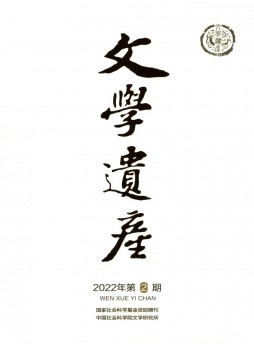文學經(jīng)典化的歷史語境與審美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經(jīng)典化的歷史語境與審美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涼山文學》2017年第4期
日前,由《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編輯部、上海師范大學當代上海文學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的“20世紀中國文學經(jīng)典化高峰論壇”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來自《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編輯部和全國各高校的專家學者40余人出席了論壇。
論壇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詹丹教授主持。《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副總編輯楊海英致辭,她認為“經(jīng)典”就是所強調(diào)的高峰,是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寫照;學術(shù)研究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闡釋新時代新發(fā)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她還介紹了《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的基本情況與“綜合性”“有特色”“專題化”的辦刊理念。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陳恒教授在致辭中從文史相關(guān)的角度談論文學經(jīng)典的問題,指出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jié)合的必要性,他提出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脫離歷史意識就難以產(chǎn)生具有偉大意義的經(jīng)典作品。吉林大學資深教授張福貴代表與會學者致辭,他強調(diào)論壇主題的重要性,認為文學經(jīng)典化是文學史中的重要問題,該問題研討的意義不僅在于今天,更在于未來。在學術(shù)研討中,學者們圍繞文學史觀、經(jīng)典化標準、經(jīng)典化方式、文學批評途徑、文學史家及文學研究者責任、文學語言等問題展開研討。文學史寫作是文學經(jīng)典化的重要途徑,通過文學史家的遴選與評論,對于文學史發(fā)展歷程中的文學作品進行經(jīng)典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張福貴教授指出文學史是由一系列經(jīng)典構(gòu)成,他在梳理了經(jīng)典概念與經(jīng)典的產(chǎn)生后,提出經(jīng)典必須具有人類性和審美性,在蘊含豐富的審美性的同時,應該具有人類意識和人性意識。楊劍龍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文學經(jīng)典化角度回眸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認為雖然此概念企望將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文學發(fā)展置于統(tǒng)一的主題、審美視閾中,用進化式的方式看待文學的發(fā)展與嬗變,但是其貢獻和價值仍然毋庸置疑。劉忠教授(上海師范大學)由“重寫文學史”口號談論文學經(jīng)典化,他指出文學史寫作并不是簡單地捍衛(wèi)一個永恒不變的觀念和秩序,而應將文學置于歷史語境中進行闡釋,凸現(xiàn)它的在場性和鮮活性。
如何對20世紀中國文學進行經(jīng)典化,究竟以怎樣的標準開展經(jīng)典化,學者們對于相關(guān)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李繼凱教授(陜西師范大學)從文化建設(shè)角度理解文學的經(jīng)典化,提出應該在文化磨合歷程中建構(gòu)經(jīng)典,從文化策略角度理解經(jīng)典,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傳揚經(jīng)典。湯哲聲教授(蘇州大學)談論中國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經(jīng)典的認定與批評標準的建構(gòu),指出對于文學作品經(jīng)典性的論定首先應該有通俗文學性質(zhì)的確認,在此基礎(chǔ)上建構(gòu)中國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通俗文學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發(fā)展中具有獨特的價值。郝雨教授(上海大學)分析文學經(jīng)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guān)聯(lián),提出需要深入研究文學經(jīng)典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積極表現(xiàn)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其實文學的經(jīng)典化是對于文學史上作品的遴選與闡釋,這就必須以回到歷史原點的方式仔細閱讀,細心篩選。張中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從抗戰(zhàn)文學史重寫與經(jīng)典文本的確認及闡釋的角度,提出應該回到歷史現(xiàn)場,認真考察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經(jīng)典。欒梅健教授(復旦大學)提出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的經(jīng)典化期待,認為應該大量閱讀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文本,辨認出優(yōu)秀的經(jīng)典化作品,通俗文學才能順理成章地進入文學史行列中。錢文亮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談論文學經(jīng)典,包括經(jīng)典形成的過程和生產(chǎn)機制、社會歷史語境、演變的歷史脈絡(luò)和美學傳統(tǒng)。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是文學經(jīng)典化的工具與方式,只有掌握了切合文學對象的理論,只有進行正確的文學批評,才能真正掌握經(jīng)典化的真諦。殷國明教授(華東師范大學)認為文學理論與文學研究應該為經(jīng)典的產(chǎn)生營造氛圍、為創(chuàng)造經(jīng)典開路,經(jīng)典不是能用金錢堆出來的,我們應該面對歷史、面對人民、面對未來努力創(chuàng)造經(jīng)典。喻大翔教授(同濟大學)由香港“沙田派”看文學經(jīng)典的分層,他將經(jīng)典評判定為語言、文體、主題、題材經(jīng)典等文學的橫向標準,和個人、時代、國家、世界經(jīng)典等時空的縱向標準,提出不同層次的經(jīng)典應該放在特定語境里衡量。李洪華教授(南昌大學)從世界華文文學的角度談論經(jīng)典建構(gòu),指出當下眾多華文文學史敘述中,多以地域為單元建構(gòu)華文文學史版塊,缺乏文學史的經(jīng)典意識和整體觀念。
文學經(jīng)典化說到底是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的一項重要工作,雖然社會讀者與文學市場也參與了文學經(jīng)典化的過程,但是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具有極為重要的話語權(quán)與闡釋作用。張全之教授(重慶師范大學)考察文學研究者在文學經(jīng)典化中的作用,認為文學研究者是文學經(jīng)典化的承擔者,研究者應該反思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文學經(jīng)典化過程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汪娟副教授(嘉興學院)談論中國當代文學經(jīng)典化的可能性及限度,提出經(jīng)典化不僅要將研究對象歷史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歷史化,當代文學的經(jīng)典化離不開研究者的推介、宣傳及傳播,應避免總是以現(xiàn)有的研究為參照。蔣進國副教授(中國計量學院)探究中國現(xiàn)代文化中心的轉(zhuǎn)移與文人京滬遷徙,指出1927年前后大批文人從北京南遷上海,中國現(xiàn)代都市文學得到較大的發(fā)展。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文學的經(jīng)典化與語言有著極為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文貴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從文學語言的角度談論經(jīng)典,指出狂人話語與書面文言、日常白話處在相互包孕和相互搏殺中,作為經(jīng)典的魯迅的《狂人日記》才得以誕生。陳海英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從陌生化語言風格探求角度談論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小說創(chuàng)作,指出穆時英小說對語言陌生化的刻意追求,主要體現(xiàn)在對變異性語言的創(chuàng)造和運用上,語言風格成為其作品走向經(jīng)典化的重要因素。陳蘅瑾副教授(越秀外國語學院)探究劉震云小說的反諷特征,小說呈現(xiàn)出言說的困境與欲望的升騰、矛盾對照中的孤獨凄清、敘述者與讀者雙重視角中的戲劇反諷,作家試圖以反諷者的姿態(tài)去發(fā)現(xiàn)并解開人類本性與被社會和權(quán)力制約了的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
對于文學經(jīng)典性的研討還涉及網(wǎng)絡(luò)文學、海派文學、軍旅文學等。董麗敏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以網(wǎng)絡(luò)小說《慶余年》談論網(wǎng)絡(luò)文學的經(jīng)典化,認為以玄幻文學為代表的網(wǎng)絡(luò)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出了網(wǎng)絡(luò)文學未來經(jīng)典化的空間與可能,必須有效地介入并引領(lǐng)當代青年文學健康良性發(fā)展。劉暢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分析當代網(wǎng)絡(luò)小說中的“志怪”傳統(tǒng)和意義,認為從小說類型、敘事觀念、敘事模式等均可見到網(wǎng)絡(luò)文學的“志怪”傳統(tǒng),但與傳統(tǒng)志怪文學相比,又暴露出思想底色不足等問題。吳智斌副教授(浙江財經(jīng)大學)從“夜”的視角審視《海上花列傳》的頹廢敘事,從“夜”化走向于頹廢語境生成、舊面孔與新生活、現(xiàn)代海派小說頹廢審美的中國經(jīng)驗展開分析。滿建副教授(安徽省宿州學院)談論上海現(xiàn)代消閑刊物與海派散文的新變,指出海派散文更傾向于消閑的審美功能,形成具有新的文體特點的新型都市散文。溫江斌(上海師范大學)研究了1920年代中期上海的“小報型”畫報,認為隨著印刷技術(shù)的革新和攝影技術(shù)的普及,1920年代中期上海興起了一股畫報潮,開啟了中國近現(xiàn)代畫報銅版全盛時期,融新聞時事與文藝小品于一爐,并以一種對話與傾訴的方式,相當寫實地呈現(xiàn)了一般民眾的文化需求和集體心態(tài)。陳彥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小說《鳳子》探究沈從文早期寫作思想特征,指出這篇充滿對話性的作品,將湘西地方苗人生活鑲嵌到復雜的對話中,并以巧妙的思辨線索將其勾連,呈現(xiàn)其早期寫作中的思想演進。王童(上海師范大學)談論當代軍旅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影視化傾向,認為追求畫面感、臺詞化、場景式,導致小說文體特征消解。
20世紀中國文學承擔著中國文學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從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重任,跨越了近代、現(xiàn)代與當代文學三個階段,其具有與中國古典文學截然不同的特色,呈現(xiàn)出多元而駁雜的圖景。改革開放以后,經(jīng)過近四十年的文學史梳理與研究,在文學史料、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的研究中,更多的作品被發(fā)現(xiàn),更多的作家被載入了文學史,形成了文學史越寫越厚的傾向。今天面對20世紀文學經(jīng)典化以及21世紀正在發(fā)生與進行的文學的經(jīng)典化,我們應該以文學史家的宏闊眼光,理論家的高屋建瓴,批評家的敏銳視野,不僅關(guān)注文學的經(jīng)典化歷程,而且關(guān)注如何使文學史發(fā)展真正達到經(jīng)典化。這仍然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切實面對的問題。
作者:楊劍龍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當代上海文學研究中心
擴展閱讀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文學批評論文
- 2文學作品分析論文
- 3文學作品鑒賞論文
- 4文學鑒賞論文
- 5文學教育論文
- 6文學寫作論文
- 7文學專業(yè)論文
- 8文學敘事論文
- 9文學學術(shù)論文
- 10文學的藝術(sh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