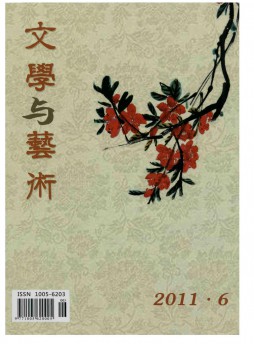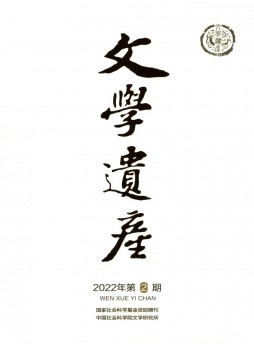文學(xué)譯介中譯者和讀者的互動(dòng)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譯介中譯者和讀者的互動(dòng)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涼山文學(xué)》2017年第4期
摘要:文學(xué)作品經(jīng)由翻譯開(kāi)啟其后續(xù)生命,而讀者通過(guò)對(duì)譯作的閱讀與闡釋參與作品的再創(chuàng)造,譯者與讀者在文學(xué)翻譯與傳播的過(guò)程中建立了不可避免的聯(lián)系。本文以昆德拉作品的漢譯為例,探討譯者與讀者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讀者在昆德拉作品的譯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讀者的期待與審美需求對(duì)翻譯造成影響,其對(duì)譯文的關(guān)注形成讀者與譯者間的多種互動(dòng)的可能。其中,讀者針對(duì)昆德拉作品譯文的批評(píng)對(duì)于開(kāi)拓翻譯的可能性、促進(jìn)對(duì)原文的理解起著積極作用,體現(xiàn)出讀者與譯者之間深刻的互動(dòng)性的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譯者;讀者;互動(dòng)關(guān)系;昆德拉
1.引言
近40年來(lái),翻譯理論探索不斷發(fā)展,不斷深入。較之于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其中有一個(gè)重要的轉(zhuǎn)變,就是在對(duì)翻譯過(guò)程、尤其是對(duì)翻譯傳播的研究中,對(duì)讀者予以了特別的關(guān)注。如果說(shuō)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是以作者為中心,那么當(dāng)代翻譯研究則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將讀者納入了譯介活動(dòng)的考察之內(nèi),且給予其重要的位置。楊武能(1998:227-235)就認(rèn)為:“譯本的讀者也并非處于消極被動(dòng)的無(wú)足輕重的地位,因?yàn)樗麄儗?shí)際上也參與了譯本和原著的價(jià)值的創(chuàng)造。”讀者是與文本相對(duì)而言的。按常理論,讀者面對(duì)的是文本,一般都是與作者發(fā)生或直接或間接的關(guān)系。但就翻譯而言,一般的讀者是面對(duì)譯本,而非原作,讀者是經(jīng)由翻譯而對(duì)文本有了閱讀的可能,于是與譯者便有著不可避免的聯(lián)系。本文以昆德拉作品的漢譯為例,就譯者與讀者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做一探討。
2.文本譯介中讀者的地位
在外國(guó)文學(xué)的譯介中,外國(guó)作家常常有機(jī)會(huì)與中國(guó)讀者建立直接的聯(lián)系。考察外國(guó)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百年史,國(guó)外許多重要的作家都到中國(guó)訪(fǎng)問(wèn)過(guò),與讀者有一定的接觸與交流。如在20世紀(jì)20年代,確切地說(shuō),在1924年與1929年,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印度詩(shī)人泰戈?duì)柧拖群髢纱卧L(fǎng)問(wèn)中國(guó),尤其在其第一次訪(fǎng)問(wèn)中,與中國(guó)文學(xué)界有廣泛的接觸。而在本世紀(jì),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法國(guó)作家勒克萊齊奧多次來(lái)中國(guó),甚至應(yīng)邀到南京大學(xué)講學(xué),在講學(xué)期間,先后到國(guó)內(nèi)近十所大學(xué)以及圖書(shū)館為普通讀者作公開(kāi)演講,在上海讀書(shū)節(jié)期間,還為讀者簽名,與讀者交流,還到中學(xué)去與中學(xué)生交流。這些活動(dòng)對(duì)于促進(jìn)其作品在中國(guó)的閱讀和理解,有著不可忽視的直接作用。然而,就昆德拉而言,由于其個(gè)人原因,他很少與讀者直接打交道,對(duì)于中國(guó)讀者而言,無(wú)緣與他見(jiàn)面和交流。而在他看來(lái),讀者讀他的書(shū)便可,在他的書(shū)上,對(duì)他本人的介紹,他認(rèn)為都是多余的,比如在其作品的中譯本上,經(jīng)他授權(quán),只能看到一行字的介紹:米蘭•昆德拉(1929—),小說(shuō)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guó)定居。除此介紹之外,據(jù)出版者趙武平介紹,昆德拉不允許中文譯本有任何形式的副文本,比如譯序、譯后記、出版者的話(huà)、作品簡(jiǎn)介等等。也許,他要讀者直接面對(duì)他的作品,讓讀者不受影響地獨(dú)立閱讀。因此,排除了與讀者的直接接觸與交流,譯文便成了連接作者昆德拉與廣大讀者的唯一載體。昆德拉之所以對(duì)譯文的要求很高,其原因也許就在于此。而對(duì)于我們的研究而言,由于讀者是經(jīng)由譯文去閱讀昆德拉,理解昆德拉,對(duì)于譯文便也有期待和要求。鑒于昆德拉作品譯介在中國(guó)的具體情況和讀者對(duì)于譯文的特別關(guān)注,我們?cè)诖宋闹校瑢⒅赜懻撟g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
與作者、編者、譯者相比,讀者是一個(gè)很寬泛的概念,有顯性的讀者,也有隱含的讀者。按照接受美學(xué)的觀(guān)點(diǎn),讀者對(duì)于作品的理解與闡釋?zhuān)瑢?shí)際上是參與了作品的再創(chuàng)造。薩特(1998:101)對(duì)此有深刻的論述,在他看來(lái),作家“只有通過(guò)讀者的意識(shí)才能體會(huì)到他對(duì)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學(xué)作品都是一項(xiàng)召喚。寫(xiě)作,這是為了召喚讀者以便讀者把我借助語(yǔ)言著手進(jìn)行的揭示轉(zhuǎn)化為客觀(guān)存在”。著名作家、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陳忠實(shí)對(duì)讀者之于作家的積極作用也有深刻的認(rèn)識(shí),他在討論《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給汪健的回信中說(shuō):“對(duì)于作家來(lái)說(shuō),他是用作品和這個(gè)世界對(duì)話(huà)的,作品其實(shí)就是他的從生活體驗(yàn)進(jìn)而到生命體驗(yàn)的一種展示,而展示的最初的和終極的目的都是為了與讀者進(jìn)行交流和溝通,能與讀者完成這種溝通和交流才是作家勞動(dòng)的全部意義所在。進(jìn)一步說(shuō),文學(xué)溝通古人和當(dāng)代人,溝通著不同膚色操不同語(yǔ)言的人。溝通心靈,這才是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人癡情矢志九死不悔的根本緣由。”(陳忠實(shí)2016:B1)文論家姚斯從文學(xué)作品生命生成的角度,對(duì)讀者的重要性作了這樣的闡述:“文學(xué)作品的生命體現(xiàn)在不同時(shí)代讀者對(duì)其意義的重新闡釋與認(rèn)識(shí)上,”一部有獨(dú)特價(jià)值的文學(xué)作品,總是“渴望讀者閱讀、希求與接受者對(duì)話(huà)”(轉(zhuǎn)引自王岳川1992:54)。在文學(xué)翻譯與傳播的整個(gè)過(guò)程中,讀者也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譯介活動(dòng)中去,有時(shí)還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在我們對(duì)昆德拉的譯介研究中,一方面我們要關(guān)注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國(guó)的翻譯,尤其是接受途徑,另一方面要考察讀者是怎樣參與這個(gè)譯介活動(dòng)的,又呈現(xiàn)出怎么樣的參與性接受姿態(tài),有何積極的價(jià)值。
譯者在翻譯時(shí),不但要考慮篇章詞句、上下文的聯(lián)系以及原作的文化精神,還要考慮譯語(yǔ)的文化背景和讀者的需要(王振平2016:113)。對(duì)于譯者而言,讀者的期待與讀者的審美需求,是一個(gè)在翻譯活動(dòng)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影響因素。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dá),在對(duì)翻譯活動(dòng)進(jìn)行定義時(shí),就把讀者反應(yīng)的因素考慮在內(nèi)。在中國(guó)的翻譯理論研究中,曾虛白對(duì)讀者的作用就有自己的理解,他提出:“我們譯書(shū)的人應(yīng)該認(rèn)清我們的工作之主因,是為著不懂外國(guó)文的讀者,并不是叫懂得外國(guó)文的先生們看的。……所以我們訓(xùn)練的進(jìn)行應(yīng)該就著這一班人的心理來(lái)定我們的方針。”他認(rèn)為,“我們應(yīng)該拿原文所構(gòu)成的映象做一個(gè)不可移易的目標(biāo),再用正確的眼光來(lái)分析它的組織,然后參照著譯本讀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組合成我們自己的文字。”(轉(zhuǎn)引自陳西瀅2009:474-482)在《翻譯中的神韻與達(dá)———西瀅先生<論翻譯>的補(bǔ)充》一文中,曾虛白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至于翻譯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有兩重:一在我自己,一在讀者。為我自己方面,我要問(wèn):‘這樣的表現(xiàn)是不是我在原文里所得的感應(yīng)?’為讀者方面,我要問(wèn):‘這樣的表現(xiàn)是不是能令讀者得到同我一樣的感應(yīng)?’若說(shuō)兩個(gè)問(wèn)句都有了滿(mǎn)意的認(rèn)可,我就得到了‘神韻’,得到了‘達(dá)’,可以對(duì)原文負(fù)責(zé),可以對(duì)我自己負(fù)責(zé),完成了我翻譯的任務(wù)。”(曾虛白2009:483-490)曾虛白的觀(guān)點(diǎn)與理論與奈達(dá)的讀者反應(yīng)觀(guān)有相通之處,值得指出的是,曾虛白是在1929年提出的,比奈達(dá)要早近半個(gè)世紀(jì)。以此讀者觀(guān)為參照,我們?cè)偃z視昆德拉譯介活動(dòng),可以更為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讀者與譯者之間互動(dòng)的重要性。如曾虛白所論,譯者在翻譯活動(dòng)中,讀者的影響是深刻存在的,他的“二為”論,強(qiáng)調(diào)的是譯者對(duì)原文的感應(yīng)與讀者對(duì)譯文的感應(yīng)的一致性。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在當(dāng)今社會(huì),由于教育的發(fā)展,在當(dāng)代中國(guó),昆德拉的讀者中懂英語(yǔ)的大有人在,懂法語(yǔ)的也有,所以譯者面對(duì)的不僅僅如曾虛白所說(shuō),是不懂外文的“讀者”。而且,作為譯者,對(duì)原文的理解與感應(yīng)還存在是否符合作者意圖和文本意義的問(wèn)題,對(duì)此,當(dāng)代中國(guó)的不少懂外文的讀者時(shí)刻都有可能參與到討論中來(lái),提出不同的意見(jiàn),何況有不少昆德拉譯文的讀者是專(zhuān)家,是昆德拉的研究者。此外,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國(guó)還有不同時(shí)期的譯本,對(duì)后來(lái)出版的譯文的閱讀和接受,還有前譯為參照,因此譯者與讀者之間便形成了多種互動(dòng)的可能。
3.讀者批評(píng)之于譯者的作用
與別的作家在中國(guó)的譯介活動(dòng)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昆德拉在中國(guó)的關(guān)注度很高,其主要作品的英文本在中國(guó)又有很大的市場(chǎng),加上網(wǎng)絡(luò)的傳播力,對(duì)昆德拉作品的接受不同于一般情況,除了讀者對(duì)作品的閱讀與闡釋之外,讀者還對(duì)翻譯本身予以了特別的關(guān)注。就譯者而言,對(duì)于讀者的接受心理,尤其是對(duì)前譯的接受習(xí)慣以及廣大讀者在前譯的影響下對(duì)原作的審美期待的緣故,在翻譯活動(dòng)中,都是應(yīng)該關(guān)注和考慮的因素。考察讀者對(duì)于翻譯問(wèn)題的關(guān)注與參與,我們充分注意到了文本的批評(píng)對(duì)于開(kāi)拓翻譯的可能性、促進(jìn)對(duì)原文的理解的重要作用。
就我們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從翻譯的角度對(duì)昆德拉譯本的批評(píng),與對(duì)昆德拉作品的理解與闡釋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就文本批評(píng)對(duì)翻譯的作用而言,專(zhuān)家型讀者對(duì)于譯本的批評(píng)和商榷有著獨(dú)特的價(jià)值。劉云虹對(duì)翻譯批評(píng)的功能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她認(rèn)為,翻譯批評(píng)一方面有對(duì)“譯者”的指導(dǎo)功能,認(rèn)為“翻譯作品不僅體現(xiàn)譯者的技巧、能力,更包含著他對(duì)翻譯的態(tài)度和立場(chǎng)。譯者具備了相當(dāng)?shù)恼Z(yǔ)言能力和審美情趣,這并不意味著他一定能夠奉獻(xiàn)出令人稱(chēng)贊的譯作。因此,鼓勵(lì)譯者在翻譯過(guò)程中進(jìn)行能動(dòng)的再創(chuàng)造并使之保持在適度的范圍內(nèi),避免一切因主觀(guān)性而可能導(dǎo)致的理解、詮釋的過(guò)度自由或盲目,這些都是翻譯批評(píng)必須承擔(dān)的重任,翻譯批評(píng)責(zé)無(wú)旁貸地應(yīng)當(dāng)給予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更為深切的關(guān)注,引導(dǎo)翻譯行為走向成熟與自律。”(劉云虹2015:216)另一方面,翻譯批評(píng)也有對(duì)“讀者”的引導(dǎo)功能,她指出“批評(píng)者憑借自身的審美感悟能力和翻譯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向讀者傳達(dá)自身的閱讀感受和審美體驗(yàn),為讀者提供一種或幾種理解原文意義和譯文意義的可能性,并鼓勵(lì)和引導(dǎo)讀者積極發(fā)揮其主觀(guān)能動(dòng)性,對(duì)譯作進(jìn)行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以吸引讀者充分享受閱讀的樂(lè)趣,進(jìn)而促使更多的人喜愛(ài)翻譯作品,關(guān)注翻譯事業(yè)。”(同上:218)劉云虹指出的翻譯批評(píng)之于譯者與讀者的作用,為我們考察昆德拉作品的翻譯提供了可能的路徑。對(duì)于韓少功來(lái)說(shuō),他和韓剛合作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發(fā)表之后,在大陸和臺(tái)灣有廣泛的傳播。就翻譯本身而言,學(xué)界有一些批評(píng)和商榷,高方對(duì)此有所關(guān)注,在她簡(jiǎn)評(píng)《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兩個(gè)版本的翻譯時(shí),特別注意到蕭寶森和林茂松兩人合作,從“文法、語(yǔ)序、字詞、語(yǔ)言、隱喻、注釋”等六個(gè)方面對(duì)韓少功的譯本與其依據(jù)的英文本進(jìn)行的對(duì)比與分析,這篇批評(píng)文章針對(duì)的就是韓少功譯本所存在的問(wèn)題,而且提出了比較嚴(yán)肅的批評(píng):“譯文文筆優(yōu)美生動(dòng)、簡(jiǎn)潔流利,這或許與兩位譯者本身皆從事寫(xiě)作工作,駕馭文字的功夫純熟有關(guān)。然而書(shū)中的錯(cuò)誤卻也不可勝數(shù)。本書(shū)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中,韓本明顯誤譯之處居然達(dá)40處之多,其他值得商榷之處更是不勝枚舉。這些謬誤雖然部分可能是因匆匆趕譯、忙中有錯(cuò)所致,但比例仍然偏高。由錯(cuò)誤的性質(zhì)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以從事翻譯工作者應(yīng)具有文字素養(yǎng)而言,韓本譯者對(duì)英文的理解程度實(shí)顯不足,時(shí)常發(fā)生誤解原意的現(xiàn)象,形成讀者在了解原作過(guò)程中的嚴(yán)重障礙。”(蕭寶森、林茂松1999:720-734)對(duì)于如此嚴(yán)峻的批評(píng),作為譯者的韓少功沒(méi)有抵觸,而是從積極的方面予以肯定。他還根據(jù)讀者的一些批評(píng)和建議,對(duì)譯文作了修訂。在與許鈞的對(duì)談中,他誠(chéng)懇地表示:“修訂版也在臺(tái)灣出版10來(lái)年了,我這些年忙著一些別的事,說(shuō)實(shí)話(huà),沒(méi)有功夫考慮這本舊書(shū)。如果還有人指正,再版時(shí)還樂(lè)意繼續(xù)吸納正確的意見(jiàn),力求好一點(diǎn)。”(許鈞、韓少功2003:202-205)這是文本的批評(píng)之于譯者的作用而言。而翻譯批評(píng)對(duì)讀者的引導(dǎo)作用,在高方的批評(píng)中有明確的體現(xiàn)。比如,她在評(píng)論中就昆德拉作品中一些有著深刻的“哲理意味”的詞語(yǔ)的翻譯作一認(rèn)真的對(duì)比分析,指出:
在全書(shū)的翻譯中,韓少功對(duì)“輕”這個(gè)具有統(tǒng)領(lǐng)全書(shū)精神作用的關(guān)鍵性的哲學(xué)詞語(yǔ),在處理上顯得比較隨意,常用“輕松”輕易替換“輕”,失去了原文表達(dá)中那種凝重而深刻的哲學(xué)意味。在書(shū)中,除了生命之“輕”與“重”的對(duì)立之外,還有與之相聯(lián)系的生命的“偶然”與“必然”的對(duì)立。輕為偶然,重為必然。書(shū)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那個(gè)“非如此不可”(Mussessein)的音樂(lè)動(dòng)機(jī),便是對(duì)生命之必然的一種拷問(wèn)與質(zhì)疑。在該書(shū)的第一部分的第17章,小說(shuō)以富有哲理的語(yǔ)言談?wù)搻?ài)情的偶然與必然,在不足一千字的敘述中,我們發(fā)現(xiàn)“偶然”一詞在許鈞的譯本中先后“十次”出現(xiàn),并圍繞著“偶然”一詞,用了“突然”、“自然而然”等詞加以鋪墊,將“突然”、“偶然”與“自然而然”和“必然”聯(lián)成了一條線(xiàn),以傳達(dá)原文“偶然”與“必然”之間的聯(lián)系。而在韓少功的譯本中,我們看到了“機(jī)緣”、“機(jī)會(huì)”、“碰巧”與“偶然”等多種表達(dá),明顯重表達(dá)的文學(xué)性,哲學(xué)的意味并不像許鈞的譯本濃重,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這種差異在前文提及的關(guān)于兩元對(duì)立的詞語(yǔ)表述中也同樣可見(jiàn),對(duì)比韓少功筆下的“光明/黑暗,優(yōu)雅/粗俗,溫暖/寒冷”,與許鈞筆下的“明與暗、厚與薄、熱與冷”,意義上的差別暫且不論,單從詞語(yǔ)含義而言,韓譯多色彩,導(dǎo)向“感性世界”,而許譯冷峻,導(dǎo)向“理性世界”。
細(xì)讀這段評(píng)論文字,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批評(píng)不僅僅對(duì)于譯者的翻譯與詞語(yǔ)處理有參照作用,而且對(duì)引導(dǎo)讀者從詞語(yǔ)層面去加深對(duì)原文的理解,也不無(wú)積極的作用。
讀者對(duì)于翻譯的關(guān)注,在昆德拉作品漢譯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這在其他作家的翻譯中比較少見(jiàn)。究其原因,應(yīng)該說(shuō)有兩個(gè)方面值得考慮:一是翻譯是一個(gè)不斷深入不斷發(fā)展的過(guò)程,如我們?cè)谏衔乃懻摰哪菢樱白g與后譯之間形成一種互動(dòng)的關(guān)系,前譯如果在讀者中產(chǎn)生過(guò)廣泛的影響,后譯便要經(jīng)受考驗(yàn),經(jīng)受來(lái)自于讀者的批評(píng)。這樣的批評(píng)往往是以前譯為參照,對(duì)后譯提出批評(píng)。其二,昆德拉在中國(guó)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在中國(guó)有了譯介后,國(guó)內(nèi)有很多讀者成了他的“粉絲”,加上昆德拉的作品的英譯本在國(guó)內(nèi)流傳,許多讀者可以根據(jù)英譯本和前譯本對(duì)后來(lái)問(wèn)世的譯文進(jìn)行批評(píng)。我們特別注意到,在文學(xué)翻譯的接受過(guò)程中,前譯一旦形成影響,在讀者的接受中便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力量,后來(lái)譯者的相關(guān)改動(dòng),哪怕在意義的傳達(dá)上更準(zhǔn)確,更符合原意,都有可能受到讀者的批評(píng),乃至抵制。瀏覽網(wǎng)絡(luò)上有關(guān)昆德拉在中國(guó)譯介的一些報(bào)道或材料。因?yàn)轫n少功與韓剛的譯本在前,其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廣大讀者所接受,而且這一句式被媒體所喜愛(ài),很多文章的題目都借助這一句式,已經(jīng)沉淀為接受者的“昆德拉記憶”。關(guān)于書(shū)名的翻譯,韓少功與許鈞的對(duì)話(huà)中有討論,這里不再贅述。問(wèn)題是當(dāng)許鈞根據(jù)法文版書(shū)名,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后,昆德拉的一批老讀者便予以反對(duì),有的讀者在網(wǎng)絡(luò)討論版留言,說(shuō)憑許鈞改了書(shū)名,就不接受新版。但是作為譯者,對(duì)于讀者的意見(jiàn)自然會(huì)考慮,但譯者也有其遵循的原則。許鈞的翻譯有著明確的原則:翻譯以信為本,求真尚美。他堅(jiān)持自己的原則,在不同場(chǎng)合多次與讀者交流,闡述他修改書(shū)名的原因:
翻譯昆德拉的困難絕對(duì)不僅僅限于文字轉(zhuǎn)換的困難。作為復(fù)譯者,我充分認(rèn)識(shí)到,文學(xué)復(fù)譯是一個(gè)文化積累的過(guò)程,韓少功的翻譯為昆德拉在中國(guó)的被接受與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本經(jīng)由廣大讀者的接受而融合了中國(guó)文化的語(yǔ)境。作品的譯名,有些關(guān)鍵詞的處理,一旦被讀者接受,就難以改變,哪怕當(dāng)初譯得并不貼切。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在翻譯中,應(yīng)該說(shuō)是充分尊重讀者的選擇的,像書(shū)名,盡管就意義與精神的傳達(dá)而言,用“存在”遠(yuǎn)比用“生命”準(zhǔn)確,但我還是保留了“生命”的譯法。但由于“生命中……輕”與“生命之輕”在意義上有著巨大的差異,就如“生命的長(zhǎng)與短”,并不能等同于“生命中的長(zhǎng)與短”一樣,我還是冒著對(duì)“讀者不敬”的危險(xiǎn),作了改動(dòng),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譯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傳達(dá)昆德拉直面生命的拷問(wèn),但愿廣大讀者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許鈞2007:66-67)作為復(fù)譯者,面對(duì)前譯在讀者中間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許鈞既考慮讀者的接受心理與漢語(yǔ)的表達(dá)習(xí)慣,但同時(shí)又堅(jiān)持原則,將自己改譯書(shū)名的“用心”袒露給廣大讀者,與他們一次次交流。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許鈞翻譯的新書(shū)名因更切合昆德拉作品的原義,逐漸被學(xué)界和廣大讀者接受。這樣的一個(gè)過(guò)程,充分地說(shuō)明了翻譯是一項(xiàng)具有“歷史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動(dòng),讀者與譯者之間的交流互動(dòng),有助于深化對(duì)原作的理解,也有助于提升翻譯的質(zhì)量。
4.譯者的求真與面對(duì)批評(píng)的積極回應(yīng)
讀者與譯者的交流的互動(dòng)性,并不表現(xiàn)在兩種觀(guān)點(diǎn)的一致。不同觀(guān)點(diǎn)的交流或交鋒,都是一種互動(dòng)性的體現(xiàn)。就昆德拉作品的翻譯本身而言,我們發(fā)現(xiàn)有的讀者的觀(guān)點(diǎn)非常犀利,批評(píng)也很尖刻。比如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的新譯文本問(wèn)世后不久,讀者反應(yīng)強(qiáng)烈,在國(guó)內(nèi)新聞界很有影響力的《新京報(bào)》于2004年8月6日與8月14日連續(xù)發(fā)表讀者評(píng)論文章,第一篇的題目為《對(duì)米蘭•昆德拉的強(qiáng)暴》。單就批評(píng)文章的題目,便可見(jiàn)評(píng)論者的尖刻。該文署名卡爾文,在文中,作者對(duì)《被背叛的遺囑》的前后兩個(gè)譯本進(jìn)行了比較,挑選了有關(guān)段落,對(duì)新譯本的譯者余中先的譯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píng)。該文首先認(rèn)定昆德拉的這部書(shū)已經(jīng)“有著令人百看不厭的出色譯本,翻譯者孟湄。”然后寫(xiě)道:我們先來(lái)欣賞一段由孟湄所作的譯文:“……今日小說(shuō)生產(chǎn)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說(shuō)歷史之外的小說(shuō)組成的:小說(shuō)化的懺悔,小說(shuō)化的報(bào)道,小說(shuō)化的清算,小說(shuō)化的自傳,小說(shuō)化的披露隱私,小說(shuō)化的告發(fā),小說(shuō)化的政治課,小說(shuō)化的丈夫臨終之際,小說(shuō)化的父親臨終之際,小說(shuō)化的母親臨終之際,小說(shuō)化的失去童貞,小說(shuō)化的分娩,沒(méi)完沒(méi)了的小說(shuō),直至?xí)r間的終結(jié),說(shuō)不出任何新的東西,沒(méi)有任何美學(xué)的雄心,為我們對(duì)人的理解和為小說(shuō)的形式不帶來(lái)任何變化,一個(gè)個(gè)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費(fèi),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重復(fù)的精心設(shè)計(jì)與順暢的節(jié)奏相結(jié)合,使得敘述的形式與內(nèi)容充分融合為血與肉的關(guān)系。而譯文正是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出了這一關(guān)系,使我們非常清晰地把握住作品的思路與表達(dá)方式。我們?cè)賮?lái)看看新版余中先先生的譯文:“……今天絕大部分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都是在小說(shuō)史之外的作品:懺悔小說(shuō)、報(bào)道小說(shuō)、付賬小說(shuō)、自傳小說(shuō)、秘聞小說(shuō)、揭內(nèi)幕小說(shuō)、政治課小說(shuō)、末日丈夫小說(shuō)、末日父親小說(shuō)、末日母親小說(shuō)、破貞操小說(shuō)、分娩小說(shuō),沒(méi)完沒(méi)了的各類(lèi)小說(shuō),一直到時(shí)間的盡頭,它們講不出什么新東西,沒(méi)有任何美學(xué)抱負(fù),沒(méi)有為小說(shuō)形式和我們對(duì)人的理解帶來(lái)任何的改變,它們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種早上拿來(lái)可一讀,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貨色。”這位余先生竟能在彈指之間將一支樂(lè)曲的美剝得精光,卻又洋洋灑灑不動(dòng)聲色地從頭翻到尾。我想請(qǐng)問(wèn)余先生,什么叫做“末日丈夫”?“末日父親”?“付賬小說(shuō)”?“末日母親”……?有哪個(gè)瘋子能理解這些詞匯的確切含義?(卡爾文2004)批評(píng)者的口氣看去十分激烈,而且在批評(píng)中還用了“強(qiáng)暴”昆德拉的語(yǔ)句。在這篇文章見(jiàn)報(bào)一個(gè)星期之后,又見(jiàn)另一篇署名魯平原的文章,題目叫《“分娩小說(shuō)”與翻譯怪胎》,文章還是就卡爾文列舉的那一段,對(duì)翻譯提出批評(píng),繼而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優(yōu)秀翻譯的懷念:“這不得不讓我又一次念想到那些名字:傅雷、戈寶權(quán)、田德望、周煦良、卞之琳、羅大岡,還有郝運(yùn)、草嬰、王了一……那些曾經(jīng)給我最美好的異域夢(mèng)幻的翻譯家,那些給害怕外國(guó)文學(xué)的人以閱讀信心和美好體驗(yàn)的翻譯家,那些不僅熟通外文更能精通異域文化、文學(xué)造詣?lì)H高的翻譯家。只是,他們或已逝去,或已蒼老,筆墨久擱,讓我們徒留空洞的悲哀。”(魯平原2004)讀了這樣的文字,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兩位批評(píng)者都是外國(guó)文學(xué)的忠實(shí)讀者,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有著發(fā)自?xún)?nèi)心的喜愛(ài),對(duì)優(yōu)秀的翻譯家有著難得的崇敬之情。卡爾文對(duì)孟湄的譯文是“百看不厭”,認(rèn)為是“出色”的,他表達(dá)的是“欣賞”。作為一位有責(zé)任感、不斷求真的譯者,面對(duì)讀者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的這份熱愛(ài),譯者余中先沒(méi)有計(jì)較文章尖刻的語(yǔ)氣、尖銳的批評(píng),而是以求真的態(tài)度,作出了積極的回應(yīng)。又是相隔一個(gè)星期,同樣在《新京報(bào)》上,我們讀到了余中先的回應(yīng)文章,題目也很醒目:《余中先:更正我的一段翻譯》。余中先是我國(guó)著名的法語(yǔ)翻譯家,在國(guó)內(nèi)讀書(shū)界具有很大的影響。《被背叛的遺囑》是昆德拉很重要的作品,譯者又是翻譯界的著名譯家,有關(guān)翻譯的批評(píng),自然也引起了比一般的作品或譯者要強(qiáng)烈得多的關(guān)注度。余中先從尊重讀者、理解讀者的態(tài)度出發(fā),直面自己的翻譯,歡迎讀者的批評(píng):“從《新京報(bào)》上讀到了卡爾文和魯平原對(duì)我所翻譯的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的批評(píng)意見(jiàn),我覺(jué)得很高興,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就應(yīng)該如此一針見(jiàn)血。”基于對(duì)批評(píng)的這一態(tài)度,余中先坦誠(chéng)地承認(rèn)了自己譯文出現(xiàn)的問(wèn)題:“見(jiàn)到批評(píng)文章后,我又翻閱了一下原著,發(fā)現(xiàn)我的這一段譯文確實(shí)大有問(wèn)題。”然后,他又認(rèn)真分析了出現(xiàn)錯(cuò)誤的原因:關(guān)鍵的問(wèn)題是對(duì)“romancé”一詞的理解和轉(zhuǎn)達(dá)。這個(gè)詞來(lái)源于“小說(shuō)”(roman),可以理解為“把……寫(xiě)成小說(shuō)體裁”、“使之小說(shuō)化”。孟湄女士的譯本對(duì)這一段的處理很好,把這個(gè)詞譯為“小說(shuō)化的”;當(dāng)然也可以譯成“小說(shuō)式的”或“寫(xiě)成小說(shuō)模樣的”;而我的譯本把它們譯成“××小說(shuō)”,則十分生硬,尤其妨礙理解。而且,僅只這一個(gè)詞,在原文中重復(fù)了十二次,于是在譯文中形成了十二次別扭。(余中先2004)余中先分析了原因之后,又謙遜地參考了孟湄的翻譯,對(duì)譯文作出了更正:卡爾文的文章中批評(píng)我“洋洋灑灑不動(dòng)聲色地從頭翻到尾”,而竟然沒(méi)有覺(jué)察到譯文中完全沒(méi)有了美感。這種說(shuō)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就這一段譯文而言。在借鑒了孟湄女士的譯文后,我認(rèn)為,這一段應(yīng)該翻譯成這樣:“今天絕大部分的小說(shuō)生產(chǎn)都是在文學(xué)史之外的作品:小說(shuō)化的懺悔、小說(shuō)化的報(bào)道、小說(shuō)化的清賬、小說(shuō)化的自傳、小說(shuō)化的透露秘聞、小說(shuō)化的揭發(fā)、小說(shuō)化的政治課、小說(shuō)化的丈夫臨終、小說(shuō)化的父親臨終、小說(shuō)化的母親臨終、小說(shuō)化的破貞操、小說(shuō)化的分娩,沒(méi)完沒(méi)了的各類(lèi)小說(shuō)……”(同上)余中先還明確表示:“我要感謝卡爾文和魯平原等批評(píng)者。如有再版,以上這一段文字一定會(huì)改過(guò)來(lái)的。當(dāng)然,在今后的翻譯工作中,我會(huì)做得更加認(rèn)真些,力求對(duì)得起讀者。”(同上)在上面,我們不厭其詳?shù)亟榻B有關(guān)《被背叛的遺囑》中譯的批評(píng),大段地引用兩位讀者和譯者的文章,目的在于忠實(shí)地再現(xiàn)讀者與譯者之間的關(guān)系,凸顯批評(píng)與被批評(píng)之間那種深刻的互動(dòng)性的價(jià)值。譯者余中先從批評(píng)中想到的是“力求對(duì)得起讀者”,是在作品再版時(shí)“更正”譯文。這樣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開(kāi)拓了翻譯的可能性,也為讀者能夠讀到更符合原作精神、“神韻”的譯文提供了可能性。尤其余中先作為在國(guó)內(nèi)翻譯界享有盛名的翻譯家,面對(duì)讀者的批評(píng)所表現(xiàn)出的大度與求真的勇氣,對(duì)中國(guó)翻譯界,具有典范性的意義。
5.結(jié)語(yǔ)
譯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是多方面的。我們?cè)谏衔闹赜懻摿俗g者與讀者圍繞翻譯本身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其中凸顯的價(jià)值,對(duì)我們國(guó)內(nèi)有關(guān)翻譯的討論有著重要的參照性,比如前些年圍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dú)》的新舊譯本的爭(zhēng)論、村上春樹(shù)作品的不同譯者的翻譯的討論等,或許可以從中獲得某些啟示,有進(jìn)一步加以檢視和思考的必要。
參考文獻(xiàn)
[1]陳西瀅.論翻譯[A].羅新璋,陳應(yīng)年.翻譯論集(修訂本)[C].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474-482.
[2]陳忠實(shí).關(guān)于《白鹿原》的通信[N].深圳特區(qū)報(bào),2016-05-05-B1.
[3]高方.文學(xué)生命的繼承與拓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漢譯簡(jiǎn)評(píng)[J].中國(guó)翻譯,2004(2):50-55.
[4]卡爾文.對(duì)米蘭•昆德拉的強(qiáng)暴[N].新京報(bào),2004-08-06.
[5]劉云虹.翻譯批評(píng)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6]魯平原.“分娩小說(shuō)”與翻譯怪胎[N].新京報(bào),2004-08-13.
[7]讓-保爾•薩特.薩特文學(xué)論文集[C].施康強(qiáng),等,譯.李瑜青,凡人,主編.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01.
[8]王岳川.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2:54.
[9]王振平.論文學(xué)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與叛逆[J].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1):113-116.
[10]蕭寶森,林茂松.兩個(gè)中譯本的比較分析[A].李鳳亮,李艷.對(duì)話(huà)的靈光———米蘭•昆德拉研究資料輯要(1986-1996)[C].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1999:720-734.
[11]許鈞,韓少功.關(guān)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新老版本譯者之間的對(duì)話(huà)[J].譯林,2003(3):202-205.
[12]許鈞.生命之輕與翻譯之重[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7:66-67.
[13]楊武能.翻譯、接受與再創(chuàng)造的循環(huán)———文學(xué)翻譯斷想之一[A].許鈞.翻譯思考錄[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27-235.
[14]余中先.余中先:更正我的一段翻譯[N].新京報(bào),2004-08-20.
[15]曾虛白.翻譯中的神韻與達(dá)———西瀅先生《論翻譯》的補(bǔ)充[A].羅新璋,陳應(yīng)年.翻譯論集(修訂本)[C].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483-490.
作者:許方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