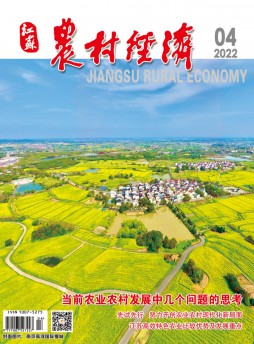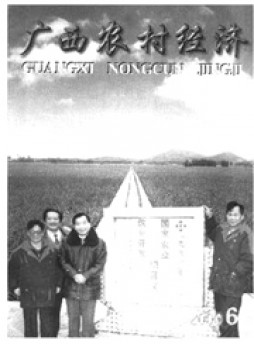農村經濟分化與政治穩定的流動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村經濟分化與政治穩定的流動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勉強維生”的村莊集體經濟與經濟能人的共生
1978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在提高村民勞動積極性、激發農村經濟活力的同時,也使農村集體經濟逐漸的解體,農村的村莊政治與經濟開始逐漸分離,村莊的政治發展失去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雖然成就了村民收入水平的成倍遞增,但是也使得農村集體收入進一步縮減,造成村莊集體經濟的“空殼化”。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缺乏有效的經濟支撐下,村莊的各項事業陷入停滯狀態,村莊政治難以正常的運轉、不穩定因素不斷積聚。然而,在筆者J村的調研中卻發現,盡管J村集體經濟陷入空殼,集體收入十分微薄,但是村莊的各項公共事業還能夠“基本”運轉,村莊政治并未出現較為大的波動。2010年J村年收入是12300元。主要分為來自于發包租賃的8300元和上級撥款4000元。J村會計及村支書稱稅費改革后J村的收入主要來源就是村里的幾間房子的出租。J村的全部用收入剛剛滿足給村組干部發放誤工補貼。通過對J村十五戶村民的調研,發現J村村民打工收入大致在每月1500元左右,而J村村干部月收入即誤工補貼僅為400-500元。在J村全體村民中,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及以上的僅有1戶,其家庭住房、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在處于顯赫地位。J村政治能人工作收入上的“捉襟見肘”與J村經濟能人的顯赫一方形成鮮明對比。因此,J村內政治能人與經濟能人在村中政治事務、經濟事務及社會事務上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就很值得去探究。事實上,J村政治能人手中掌握著很多政策性信息,如小額信貸、良種補貼等,而這些信息不是普通村民所能夠掌握的。正是這些灰色信息給予政治能人以政治資本,進而轉化為其人際處理的資本之一。如J村獲得小額信貸的村民主是村干部的親朋好友。對于J村中的經濟能人而言,伴隨其經濟地位的提升還有其受關注度,二者的勾連源于J村穩定和J村發展的需要。如J村公共服務的構建需要村民集資,做好村莊經濟能人的工作則能對其他村民的起到良好的帶動效應,而經濟能人也會借助村干部所提供的信息得以更好的營生。當然,二者并不是完全相融,決定其融合度的關鍵因素是雙方給予對方信息的經濟價值或政治價值的大小,即以“理性人”的角色來思考各自的利益。
(二)“小打小鬧”的散戶與“有序合作”的并立
就土地收益而言,J村淮山年產量約為4000斤,按照市場均價5元每斤計算,一畝淮山的經濟產值約為20000元,除去農藥、化肥、電力和種子等生產成本,普通村民種植一畝淮山的年收入為5000-8000元。J村村民W某于2009年耗資120多萬成立特色淮山經濟合作組織。該組織的分工是1人負責搜集信息,1人負責尋找銷路,另三人負責產量的達標及其他協助工作。由于該組織分工與合作進行的比較隱蔽,以致除J村村委成員外其他村民對此毫不知情。而該組織所生產的特色淮山的市場均價高達6元左右,其年經濟產值比一般淮山高出4000元。此處對比僅是在一般淮山暢銷的情況下,若市場不景氣其他村民只能望“市”興嘆,而合作組織卻可以運用市場上的信息進行優化處理。因此,合作組織的村民與分散化的其他村民之間的經濟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J村人均耕地僅為0.5畝,有限的土地導致依靠土地所獲取的經濟收入并不大,加上外出務工潮流的沖擊,部分村民為了專心務工便將土地轉包給合作組織成員,擁有土地的基數因此拉大,土地的經濟收入也與此劇增,而且合作組織成員對其內部信息的隱性化處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隱蔽了他人的注意,因此,土地造就的經濟收入差異得以認可。
(三)“分化懸殊”的家庭收入與心理平衡的融生
J村貧富分化顯著,受訪的15戶村民平均務農年收入約為20017.89元,平均務工年收入約為34109.09元,每戶平均年總收入約是60896.67元。務農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于耕地面積的多少而造成,務工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勞動力的多少而造成。筆者對J村村民年總收入進行分層統計,發現年總收入在15戶村民均值年總收入以下的有8戶,占總樣本量的53.3%;村民年總收入在15戶村民均值年總收入以上的有7戶,占總樣本量的46.7%。總之,超五成村民年總收入處于平均值以下。此外,村民年總收入最低為20000元,最高為138000元,差值為118000元。由此可見,J村貧富分化傾向很嚴重。此外,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年總收入高且不是靠外出務工所得的村民收入來源主要是搞養殖以及規模化種植。在走訪村民時,筆者注意到,有的村民一家幾口人蝸居在兩小間平房中,而有的家庭則至少蓋三層樓,有的還添置現代化的室內設備。但是,這種經濟差距并未造成村民之間的不平衡心理。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務工收入對于家庭收入的重大貢獻使得村民認為,只要家里勞動力多,經濟條件自然會好;二是只要自己有能力,經濟條件也會提升。因此,經濟差的村民將自身的狀況歸結為自己家庭勞動力不足或者自身能力不強等自身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發現,村民交往的原則是親朋好友的聯系機制,即有困難或者有致富之路等等問題或信息均以自身為中心,然后以親朋好友的圈層往外擴散,這種無意識的交往原則所產生的重要后果是村莊貧富分化呈現圈狀發展,即經濟實力強的村民其關聯度高的人的經濟實力也相對較高,如上文中的合作組織實際上是一個家族組織,村中的養殖大戶也是家族組織。這種互助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同圈層村民之間的好感。而外圈層的村民也會以自己對自身所處圈層的經濟能人的了解及尊重來看待其他圈層的經濟能人,進而不同圈層之間的分化狀況并未引起處于邊緣地帶的貧困村民的仇富心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雖然J村貧富的分化在不斷擴大,但是J村的政治運行是穩定的。而這就與我們所熟知的貧富分化會造成政治不穩定的觀點不同。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傳統關于農村政治穩定與經濟分化的關系研究,其主流觀點要求我們從村莊外部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認識兩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所在,并將這種矛盾與沖突的解決機制定位在村莊民主機制的建構上。事實上,這種研究思路導致我們忽視了農村內部固有結構的韌性以及對相應矛盾與沖突的吸納與處理能力。撇開民主與自治,筆者發現在經濟分化的J村內部存在另一套內在的利益平衡與消化機制。這種機制一定程度上可能與民主相悖,一定程度上可能與理論常識相左,但是這樣一套機制或者說一套生活與內在治理邏輯確實存在著。
二、農村經濟分化與政治穩定的內在平衡機制
J村經濟分化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并沒有對政治運行帶來挑戰,與我們的理論常識相反。J村的政治運行相對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建立在良好的民主調節機制上,也不是建立在均衡的利益協調與分配機制上,更不是建立在外部政府與嚴密管控與政治精英的威權治理上。那么經濟分化與政治穩定之間是如何在實現平衡與共生的呢?筆者通過對J村的研究發現經濟分化與政治穩定的內在平衡機制包括層面:
(一)村莊政治的“神秘性”
對于80%的J村村民而言,村莊政治生活離他們是遙遠的。村莊政治情況的信息的不透明、信息傳播的有限性,使得村民對于政治生活的真實情況既充滿困惑,又不想介入,于是這種帶有神秘性的村莊政治色彩使得村莊政治的情況基本上掌握于村委干部手中,其基本運行的狀態取決于村委會干部的上下連接能力。而村民作為直接利益的追求者往往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獲取可觀的貨幣收入上。正式的政治過程與運行村民并不想直接接入,除非有直接的利益沖突,這就給村委會政治創造了“神秘”的可能性。也正式這種村民自己不愿揭開的“神秘”,使得村莊政治與村民經濟生活之間劃清了界限。關鍵是村委會干部如何對上與對下,以及村民自身如何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
1、村委政治“上”與“下”的勾連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村委會職權來源于村民的授權,因此村委會干部必須對村民負責,代表村民的利益。而在現實中,村委會干部的權力不僅僅來源于村民民主化的授權,同時還來源于鄉鎮的授權。村干部的行為動機同樣來源于經濟利益的結構安排,并受政治關系結構的限制。經濟利益最明顯的來源于工資結構,而政治關系結構則要一方面服從上級的任務安排,另一方面又不能碰觸村民的現實利益結構。正如J村村支書坦言,由于自己的工作收入一部分來源于鄉鎮,一部分來源于村莊,因此,在工作中不得不雙方面考慮,而不是單純的“唯上”或者“唯下”。具體而言,在處理上級布置的任務時,村委可以權變處理,而其如此做的思維邏輯就是“我還有部分收入是村集體給的”;在協調村民之間矛盾受挫時,村干部有上級做后盾的形象也源于績效工資的發放。可見,雙層的經濟利益來源構成是村兩委角色尷尬的主要原因。但是,正是這種尷尬的角色,使其既不能盲目的跟“上”,也不能隨意的待“下”,而是綜合考慮,盡量做到“上”與“下”的合理勾連。而正是這種合理勾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下不一致的政治壓力,使得J村政治呈現穩定趨勢。而另一方面,在J村村干部的政治生活中還存在兩種相對獨立的利益結構:一是鄉鎮政府的管控政治利益結構,二是村民的家戶利益結構。在J村,村干部作為這兩種利益結構的協調人與中間人,一方面盡量保持鄉鎮政治利益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另一方面又不碰觸村民切身的家戶利益,并在家戶利益結構之外尋在上下之間的利益平衡點。
2、村民政治“無利可圖”的冷淡相對于村莊政治,村民政治顯得相對簡單。對于村民來說,其主要的行為動機是如何獲得較多的貨幣收入,村民的更多的是追求一種行為發生或者事件的參與能夠給自身或者這個家庭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他們對于村莊政治或者村級民主并不是十分熱情,他們將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投入到賺取貨幣的實踐中。政治對于他們而言是無利可圖的,因此對于日常村莊政治而言他們是冷淡的,甚至是不愿意參與,覺得浪費時間。在調查中發現,80%的J村村民對村級事務并不知曉也不愿意知曉。村民這種政治冷淡,一方面為村干部協調上下級關系留足了空間,另一方面也從靜止而非發展的層面促進了村莊內部政治的穩定。與此相伴隨的更為重要的層面,村民將經濟生活剝離于政治生活之外,村莊政治與村民經濟生活之間不存在利益上與結構上的硬性關系。在大多數村民看來,村里的事實村里的事,他們說不上也管不上。而自家經濟上事情,那也是村里管不了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相對獨立,也使得村莊內部經濟分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不至于從家庭層面上升到村莊治理層面。當然,村民并不是無法參與村莊政治,更不是對村莊政治一無所知,相對而言,村民對于村莊政治的運行規則比較清楚,只是不想越界,正如有些村民所言“不想管那個閑事”。可以說,村莊政治的神秘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村民冷淡的一種表現,而不是真正的神秘。
(二)村民生存的可流動性
傳統村民的生存主要是以村落空間為范圍,村民生存與生活依附在土地和農業上。這種靜止的生存模式將村民主要的視野和關系網絡集中在村落空間內部,因此,農業、村民與村落政治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在廢除農業稅以前,農村政治主要是和農村經濟掛鉤的,村民的家庭利益與村落的政治利益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村民的生存狀態與村落的政治生態是密切關聯的。伴隨著大規模村民流動的出現,村民的生存視野與經濟活動范圍發生了變化,生存具有了可流動性,生存的壓力與矛盾也開始從村落空間轉移到村落以外的空間,尤其是農業稅的廢除,使得村民的經濟生活與村莊的政治結構逐漸劃清了界限。
1、土地經營思維的轉變“三農”問題的核心是村民問題,村民問題的核心又是土地制度。村民承包的土地,具有生產資料、家庭財產、生活保障三種功能。村民這一頭,因為土地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村民有了這塊地就會天下太平了。正因如此,土地矛盾曾是J村村民爆發起義的重要原因。時隔一個世紀之后,土地的生存保障作用是否依舊為村民經營土地的首選呢?土地的運用邏輯是否發生變化了呢?土地矛盾是否依舊是社會隱患的重大因素呢?是否會再次引燃社會矛盾呢?事實上,在沒有涉及到外部開放的條件下,土地矛盾在J村已經無法構成村莊政治的威脅,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村民土地經營思維的轉變。以往在J村,土地的規模以及土地經營的好壞是決定村民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在土地經營過程中,圍繞分地、土地邊界、水利灌溉、交公糧等產生過一系列的糾紛與矛盾,村莊政治穩定的也主要圍繞這些問題形成自身的結構與狀態。伴隨著農業稅的廢除,以及外出務工經濟的出現,傳統農業已經不再是J村村民年總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通過對15戶村民的調查,發現除一戶未從事農業生產外,其他14戶均種植一季水稻,且無出售糧食的現象。J村村民將經營視野集中在經濟作物上,在J村一畝水稻除去成本以后的年收入約為400-500元,而一畝普通淮山的年收入約為5000-8000元,由此村民的種植習慣由傳統的兩季水稻變為一季水稻一季淮山。同時種植思維轉移到家庭內部,即家庭成員如何管理與經營的過程,在土地經營層面家庭與家庭之間也劃分了界限,經濟分化結果具有內向化的過程,由此產生的貧富分化與村落和其他家庭之間沒有關系,而是家庭內部經營的結構,進而將經濟分化的矛盾與沖突化解了。
2、非農產業的吸納從調查的情況來看,J村村民經濟收入的主要部分,并非來源于傳統農業,剔除依靠種植淮山的村民,J村村民的經濟收入與經濟分化主要來源于外出務工。調查數據顯示89%村民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非務農收入,而這部分村民家庭經濟收入大部分來源于外出務工,也就是說村民的生存狀態不再局限于村莊內部,其生存的矛盾和沖突也主要不是由村莊治理造成的。生存的流動性主要來源于外部市場經濟的繁榮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而在外部生存經營中,村民的經營狀態主要依賴于自身,而不是村莊的關系結構和政治結構。由此改變了村民對于自身經濟能力與家庭經濟狀態的認識,如村民訪談中所言“誰有本事,誰就可以過上好日子,自己沒本事,也就不能怪別人,哪還能嫉妒那些富人。”這也是大多數村民對待村莊貧富分化的態度。而村民之所以有著這樣的態度,其進一步的原因是在于“只要能動,出去打工也餓不死的”。可見,非農產業的吸納并非單純的提高了村民的經濟收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舒緩了村民的生存之憂,即沒有土地了,只要有勞動力他們依舊可以很好的生存。所以,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可流動性在疏導著的經濟利益矛盾以及村莊內部的治理矛盾。所以,非農產業的吸納機制是經濟利益矛盾疏導的關鍵點。它是村民心理自我調節、尋求新出路的重要標桿。這也是,J村經濟分化未能導致政治不穩定運行的主要原因。
(三)村民聯絡的圈層性
在分析J村村民家庭收入差距顯著的現狀時,筆者發現村民無意識形成的交往原則在消解不平衡心理有著重要作用。而這種交往原則呈現出明顯的圈層性。圈層內部的輻射與帶動效應一方面平衡者經濟分化帶來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也通過關系輻射與帶動逐漸改善經濟條件相對價差的村民的生存狀態。同時,不同圈層內部由于圈層的相對穩定以及界限的相對清晰,使得不同圈層內部的村民有著自身的不同打算和生活。圈層彼此之間是相對獨立的,其利益結構也是相對獨立的,這就形成一個圈層內部的經濟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不會對其他圈層的經濟利益或者政治利益產生威脅。而圈層內部的經濟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會通過圈層內部的關系互動得到逐步的改善。
1、圈層的外部化傳統J村的圈層結構是內部化的,具體表現為不同的圈層往往被局限于村落空間內部,而村落空間內部的資源又是有限的。如為獲取較多的政治資源與土地資源,導致村落之間不同圈層之間矛盾與沖突的不斷升級。伴隨著農業稅的廢除以及外出務工經濟的發達,圈層之間的資源爭奪逐漸消失了。相對而言,圈層內部的家庭與村民將經濟資源的獲取外部化了,通過外出務工、自身創業以及技能提升等在村落的外部空間尋找新的生存出路。由此,圈層之間的利益爭奪也慢慢消失,村莊政治也越來越趨于穩定。同時,圈層的外部化,使得圈層內部不同家庭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經濟收入逐漸提高,圈層內部的經濟分化逐漸加劇。但是,由于圈層內部是一個小的關系網絡與互助團體,圈層內部之間的帶動效應也逐漸形成,這就形成了圈層內部經濟分化的平衡機制。這種平衡機制:一方面使得被幫助者易產生對給予幫助者的感激心理及對對方的能力的認可心理;另一方面,在貧富互助下,被幫助者的經濟狀況一般也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這會使得同一勾連網絡的貧富分化不是特別明顯。同時,對于同一網絡中富有者的感激及敬佩心理,使得處于經濟劣勢的村民將原因更多的歸結為自身,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對其他網絡中比自己經濟條件好的村民的不平衡心理。
2、圈層界限的清晰化伴隨著J村圈層外部化同時出現的是圈層界限的清晰化,這種清晰化集中表現為不同圈層的利益結構是不同的,他們分別具有自身得以存在的圈層內核,如淮山種植、卡車運輸、衣服銷售等。這些圈層之間的利益結構也是不沖突的,他們分別從事著不同的行業。行業的不同由此造成經濟收入的不同,也就形成了我們明面上所看到的經濟分化。但是這種經濟分化之所以沒有產生對村落政治運行穩定的沖擊,關鍵就在于這些經濟分化的出發點不同,產生的空間不同,利益結構不同,由此形成了清晰的圈層利益界限。如J村的調查中,從事淮山種植的往往以經濟合作社的幾個大戶形成的圈層為主。還有幾家從事火車運輸的,而他們之間又是親戚關系。在外務工的有分別呈現出不同的城市,如去上海務工的多是親戚關系或者熟人關系,某一個人立足腳之后逐漸帶出來關系鏈上其他成員進入。在無錫從事衣服銷售的三家人,也是親戚關系。總的來說,圈層界限的清晰化以及異質化,使得村莊內部的經濟分化不至于形成治理危機。而那些留守在村莊的傳統種植村民則成為經濟分化的最底層鏈條,但是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自己沒有本事,與他人無關。同時,圈層界限的清晰化與異質化也是的圈層之間的經濟分化與貧富分化不至于產生矛盾與沖突,因為彼此之間所消耗和使用的不是同一空間內部的同一資源。而圈層內部的經濟分化在圈層關系的約束下和圈層的帶動作用下,也不會形成治理危機以至于對村莊的政治運行產生威脅。
三、結語
筆者通過對J村的調查,分析其村莊政治運行和村莊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和平衡機制的。發現隨著我國經濟建設不斷推進,要想協調好農村的經濟分化以及農村政治穩定二者的關系,必須要把村莊內部以及更主要的外部環境影響因素納入到考慮范圍之中。村莊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已經不再取決于一個圈層或者某個領域的單個影響。影響因素的多元和發展空間的拓展,對于村莊的治理需要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撐或者法律保障,因而,村莊治理已經變成了國家治理,現有的農村經濟分化產生的矛盾也需要國家從更廣闊的公共政策層面加以消弭。從這一層面來看,未來中國農村治理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村落治理,而是更高層次的國家治理。村民的政治視野不再是村落政治,而是國家政治。(本文來自于《社會主義研究》雜志。《社會主義研究》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唐鳴李哲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