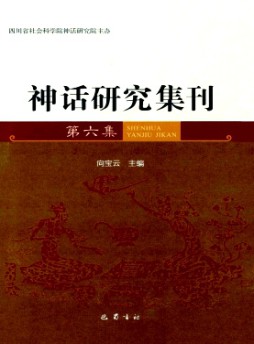神話學到民俗藝術(shù)學的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神話學到民俗藝術(shù)學的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民族藝術(shù)雜志》2014年第三期
1987年我和郭于華作為首批民俗學博士生入學北京師范大學師從張紫晨先生之后,民俗學的研究成為我專攻的方向。20余年來,我在民俗學的研究中,主要對民俗學的基本理論和民俗文化的一些專題進行了研究,也部分涉及了比較民俗研究等領(lǐng)域。在民俗學的理論研究方面,我曾出版了《應(yīng)用民俗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國都市民俗學》(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作為開創(chuàng)性的選題,它們豐富了民俗學的學科體系,開辟了我國民俗學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應(yīng)用民俗學》包括“概論”、“應(yīng)用對象論”、“應(yīng)用功能論”、“應(yīng)用資源論”、“移風易俗論”、“當代應(yīng)用概說”、“應(yīng)用前景論”和“結(jié)語”八章,初步建構(gòu)了應(yīng)用民俗學的研究體系。該書指出,“應(yīng)用民俗學是以民俗為教育手段,干預(yù)生活、改造社會的學科,同時也是以民俗為開發(fā)對象,對其加以勘察、利用、保護及管理的學科”。其理論構(gòu)架主要是“移風易俗論”、“民俗資源論”和“民俗工程學”。與一般文章提及“應(yīng)用”就是講“開發(fā)”和“產(chǎn)業(yè)”不同,《應(yīng)用民俗學》在辨析“迷信”與“俗信”的異同時,強調(diào)它還有對陋俗加以移易、批判、勸誡的任務(wù)。該書還提出,民俗應(yīng)用的三個要素是“應(yīng)用者”、“應(yīng)用源”和“應(yīng)用場”,它們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制約;應(yīng)用的基本建設(shè)應(yīng)包括市場建設(shè)、基地建設(shè)、社區(qū)建設(shè)和隊伍建設(shè);民俗應(yīng)用的實質(zhì)可判斷為“文化的選擇”、“文化的保護”、“資源的開掘”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中國都市民俗學》系我國第一部有關(guān)都市民俗學的研究著作,它在對中國古代都市民俗的梳理,以及對當代民俗生活的變遷和城鄉(xiāng)民俗整合趨向的分析基礎(chǔ)上,提出以“主體與時空流動論”、“民俗中心轉(zhuǎn)移論”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磨合論”三個新的理論研究當代中國的都市民俗。直到本世紀初,還有人認為,中國民俗在農(nóng)村,都市里沒有民俗,該書以大量古代都市民俗資料和當代都市職能及都市民俗特征的歸納對此做出了回應(yīng)。該書針對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指出,由于都市與鄉(xiāng)村空間分野的客觀存在,“田野作業(yè)”已不適合作為都市民俗的研究術(shù)語,可用“社區(qū)作業(yè)”或“街區(qū)作業(yè)”等新詞來替代,以符合都市民俗采集的環(huán)境特點和研究工作的實際。在民俗文化的專題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中國魚文化》(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祈禳:求福•除殃》(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風俗探幽》(東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國鎮(zhèn)物》(臺北東大出版公司1998年)、《中國祥物》(臺北東大出版公司2003年)等專著。
《中國魚文化》是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chǔ)的研究著作,也是我國第一部有關(guān)魚文化的民俗專題論著。014它以歷史上的各類魚圖、魚物、魚俗、魚信、魚話為研究對象,選取多學科的視角,通過內(nèi)涵闡釋、功能探究、魚謎揭解和演進分析,以展現(xiàn)魚的大千世界和人的精神宇宙。作為超學科、多層次的復合研究,它把民俗學、人類學、藝術(shù)學、考古學、文化學等學科統(tǒng)合起來,提出重申了一些創(chuàng)見,如金魚獻寶故事的源頭在中國,魚為星精獸體的象征,孟姜女的原型為善哭善織的海人魚,和合二仙的象征形象來自波斯女神阿娜希塔,河姆渡文化時期魚與小兒同食的野蠻風俗是中古西南地區(qū)殺食頭胎為“宜弟”的先型,等等。對我來說,該書的寫作開始形成注重理論闡發(fā)與實證研究、古籍文獻與藝術(shù)圖像、行為信仰與口承資料互證互補的研究風格。《中國鎮(zhèn)物》作為我國第一部鎮(zhèn)物文化研究的專著,包括“導論”、“歲時鎮(zhèn)物”、“護身鎮(zhèn)物”、“家宅鎮(zhèn)物”、“路道鎮(zhèn)物”、“婚喪鎮(zhèn)物”、“御兇鎮(zhèn)物”、“結(jié)語”等部分。所謂“鎮(zhèn)物”,又稱作“禳鎮(zhèn)物”、“辟邪物”或“壓勝物”,它以有形的器物表達無形的觀念,在心理與風俗的層面幫助人們面對各種實際的災(zāi)害、危險、兇殃、禍患,以及虛妄的神怪鬼祟,克服各種莫名的恐懼與困惑。作為文化象征的產(chǎn)物,鎮(zhèn)物以非實驗的方式,用加工過的自然物或人工物來建立自然世界與幻想世界的同一;作為巫術(shù)信仰的物化,它借取虛構(gòu)的“超自然的力量”,以圖對他人、他物或環(huán)境加以控制;作為宗教的通神法物的泛化,隨著民間文化選擇和長期俗用的結(jié)果,它強化了排解種種生活困惑的工具性質(zhì);作為風俗探秘的符號,它往往表現(xiàn)為心象與事象的疊合,并在各種裝飾性的外觀下隱含著風俗生活的秘密,也展現(xiàn)著人類的多彩思維和奇妙創(chuàng)造。對源頭悠遠、形制龐雜的鎮(zhèn)物,我做了“四不”的概括,即:無時不有的文化載體,無處不在的象征符號,無物不用的生成方式,無人不與的民俗情境。在民俗學的專題研究方面,我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過論文數(shù)十篇,包括《論先秦諸子的鬼神觀》、《論民間信仰的研究體系》、《祖道軷祭與入山鎮(zhèn)物》、《石敢當與山神信仰》、《論佛學的俗用》、《試論鄉(xiāng)野道教》、《魂瓶錢樹與釋道融合》、《南京郊外的儺文化傳承》、《中國園林建筑中的民俗觀》、《薺菜花與上巳節(jié)》、《春節(jié)文化符號的釋讀》等,涉及多個研究領(lǐng)域。在域外民俗和比較民俗的調(diào)查研究方面,我出版了《問俗東瀛》一書(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發(fā)表了《東方魚文化三題》、《中日民間信仰研究的歷史回顧》、《中韓元夕民俗三題》、《中國紙馬與日本繪馬略論》、《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隱義》等論文。
1996年底我獲得了日本學術(shù)振興會的長期項目,于1997年3月至1998年1月在日本東北大學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合作研究,其間我在日本東北地區(qū)的宮城、山形、福島、巖手、青森等縣多次開展民俗調(diào)查,后利用搜集到的資料和考察筆記寫成《問俗東瀛》一書。該書包括“墓地調(diào)查”、“船岡賞櫻”、“鄉(xiāng)村做客”、“恐山之行”、“山形采風”、“原野探舊”、“仙臺節(jié)日”、“民俗藝術(shù)”八個部分,以田野作業(yè)中的所見所感為主,記錄了日本的風俗與信仰,以及考察過程,同時對中日的當代墓制、蠶神信仰、七夕民俗等進行了比較研究。該書指出日本的神異動物河童可能來自中國的猴、馬傳說,而在寺廟、商店和情人旅館中常見的貍的塑像,則來自羅馬人用以結(jié)緣的信仰風俗。這些觀點均有創(chuàng)新的意義。2009年我應(yīng)邀參加了日本的國際研究項目“東亞的祭祀藝能研究”,項目的周期為4年,第一年在日本愛知縣東榮町中在家對“花祭”儺儀做實地考察,之后我分別在中國和日本發(fā)表了《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隱義》一文。日本學者從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關(guān)注和考察“花祭”活動,認為它與中、韓文化有聯(lián)系,但其中很多東西還看不出它的真正意義。我的文章著重對“花祭”中的一些象征元素做出解說,指出與中國文化的承繼關(guān)系。文章的“結(jié)語”作了這樣的概括:“日本東榮町中在家的‘花祭’名稱與‘花樹’相聯(lián)系,是‘花樹’迎神、送神意義的概括。‘花祭’儀式的信仰中心是山神崇拜,‘花祭’中的神鬼都是‘山神’的形象。‘花祭’作為帶有巫儺風氣的民間信仰活動,其中有宗教哲學的因素,即主要來自中國的兩儀五行觀。‘花祭’中的日月切紙、庭火與山泉、山神與水神、煮沸的開水等,包涵著‘陰陽兩儀’的隱義;而‘金、木、水、火、土’切紙,拜五方,五遍舞歩等,則透露出‘五行’觀的哲學影響。”《中日民間信仰研究的歷史回顧》系與日本學者鈴木巖弓教授合作由我執(zhí)筆的文章,旨在對百年來中日民間信仰的研究做學術(shù)史的總結(jié),并歸納它們之間的異同。文章指出,中日一百年來有關(guān)民間信仰的研究具有學術(shù)的與社會的雙重意義,是近現(xiàn)代文化思潮與社會生活的曲折反映。文章歸納中日民間信仰研究有著以漢字作為概念名稱、早期都譯介并借鑒西方學者相關(guān)理論、都以采集整理和理論概括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均以本國的為主等共同點,同時著重指出它們的相異方面:中國將貧弱之根歸于“迷信”,視其為“種滅國亡”之禍,而日本視民間信仰為“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并欲發(fā)揚其中潛含的“文化創(chuàng)造的因子”;中國由民間信仰而強調(diào)啟蒙的任務(wù),并以倡導科學與教育作為革除迷信的手段;日本的民間信仰在國內(nèi)是為了認知和保護自身的傳統(tǒng),在殖民地則為了對異文化加以把握。
我對民俗藝術(shù)的研究經(jīng)歷了從專題探究到理論建構(gòu)的過程,并逐步從民俗與藝術(shù)的交叉研究過渡到對“民俗藝術(shù)學”這一學科的建設(shè)。我從1999年開始在“藝術(shù)學”學科內(nèi)招收民俗藝術(shù)學方向的碩士生,從2003年開始招收民俗藝術(shù)學方向的博士生,這一方向目前在我國研究生教育中仍然是唯一的。至今,我已培養(yǎng)獲得學位的民俗藝術(shù)學碩士23人,民俗藝術(shù)學博士18人,另有專攻這一方向的3名博士后人員出站。我曾發(fā)表過《<八寶圖>與建筑裝飾》、《民間小戲略論》、《中國紙馬與佛教藝術(shù)》、《祈年禮俗與神馬地畫》、《虎圖虎俗的文化探秘》、《鐘鼓•琴•琵琶———中國吉祥樂器摭談》、《沉醉于民俗藝術(shù)的園田》、《靈巖寺泥塑羅漢吉祥衣飾探究》、《切紙•面具•神像———日本民俗藝術(shù)三題》、《高淳花臺會與鄉(xiāng)野戲劇教育》、《論民俗藝術(shù)學研究》、《南京高淳水陸畫略論》、《山西常家莊園影壁花墻磚雕的文化功能》、《民俗藝術(shù)研究的歷史回顧》、《論民俗藝術(shù)學體系形成的理論與實踐基礎(chǔ)》、《論民俗藝術(shù)傳承的要素》、《略談書法與民俗藝術(shù)》、《民俗藝術(shù)傳承的結(jié)構(gòu)與層次》、《論民俗藝術(shù)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等研究文章。在民俗藝術(shù)研究的著作方面,我出版了《中國紙馬》(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江蘇紙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民俗藝術(shù)學》(南京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
《民俗藝術(shù)學》一書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shù)學)項目的最終成果,由我及我培養(yǎng)的已獲得博士學位的幾位課題組成員共同完成,我制定了全書的寫作框架和理論基調(diào),寫作了其中的4章,并通改了全稿。作為第一部民俗藝術(shù)學理論著作,它構(gòu)建起學科的理論框架,開辟了藝術(shù)學的分支學科。該書包括“緒論”、“民俗藝術(shù)學體系論”、“民俗藝術(shù)學方法論”、“民俗藝術(shù)類型論”、“民俗藝術(shù)特征論”、“民俗藝術(shù)功能論”、“民俗藝術(shù)傳承論”、“民俗藝術(shù)審美論”、“民俗藝術(shù)作品論”、“民俗藝術(shù)應(yīng)用論”、“民俗藝術(shù)傳播論”“、民俗藝術(shù)保護論”共12章。《民俗藝術(shù)學》首先進行了概念界定,對“民俗藝術(shù)”、“民間藝術(shù)”、“民藝”等做了辨析,指出:民俗藝術(shù),系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種藝術(shù)形態(tài),作為傳承性的下層藝術(shù)現(xiàn)象,它又指民間藝術(shù)中能融入傳統(tǒng)風俗的部分。從主導方面說,“民俗藝術(shù)”的概念是以傳承性、風俗性對下層社會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所做出的文化判斷;而“民間藝術(shù)”的概念乃基于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的分野,強調(diào)其下層性的特征;至于“民藝”一詞,則出于對某些藝術(shù)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與應(yīng)用主體所做出的身份認定和類型劃分。民俗藝術(shù)學的理論基點為“傳承論”、“社會論”、“象征論”,它們分別從存在特征、屬性風格和表現(xiàn)方式三個方面構(gòu)成了民俗藝術(shù)學的理論基礎(chǔ)。民俗藝術(shù)學的研究體系包括民俗藝術(shù)志、民俗藝術(shù)論、民俗藝術(shù)史、民俗藝術(shù)批評、民俗藝術(shù)應(yīng)用研究、民俗藝術(shù)專題研究等基本范疇,其體系隨學科的發(fā)展和研究的深化而不斷地充實和嚴整。
該書還對中國的民俗藝術(shù)研究做了綜述和小結(jié),指出其以下階段性的特點:1.1949年以前,我國的民俗藝術(shù)研究以常任俠、岑家梧等為代表,他們主要從藝術(shù)史的研究出發(fā),較集中在民俗藝術(shù)文物的調(diào)查與研究方面,而較少涉及民俗藝術(shù)的基本理論問題。他們在自己的論著中提出了“民俗藝術(shù)”的概念,但對“民俗藝術(shù)”、“民間藝術(shù)”等又未從理論上加以厘清,概念的混用正反映了民俗藝術(shù)研究在初始階段的學術(shù)狀況。2.臺灣的民俗藝術(shù)研究,在30年前基本沿襲常任俠、岑家梧、凌純聲等學者的治學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民俗藝術(shù)的研究中同時注意田野調(diào)查、宗教藝術(shù)、山地文化等方面,對“民俗藝術(shù)”開始思考并提出“善加保護”和“維護”的問題。近10余年來,臺灣開始在高等院校設(shè)立民俗藝術(shù)的研究機構(gòu),注意“以民俗藝術(shù)為核心”,匯集眾多相關(guān)學科,同時強調(diào)本地民俗藝術(shù)的調(diào)查和理論基礎(chǔ)的建立。3.近20年來,中國大陸的民俗藝術(shù)研究和民俗藝術(shù)學教育取得了突出的進展,相關(guān)論著的出版、民俗藝術(shù)學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yǎng)、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設(shè)立、民俗藝術(shù)相應(yīng)機構(gòu)的建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程的開展等,都反映了中國民俗藝術(shù)研究的拓展和繁榮。四早在20多年前我就寫過一篇短文,與青年學生們談治學的感悟,當時我說了三點,現(xiàn)在我愿在此重提:1.敏而好學,鍥而不舍。所謂“敏而好學”,就是要以創(chuàng)造性思維引導自己,善于在學習中總結(jié)規(guī)律、發(fā)現(xiàn)問題,在攝取各類知識的時候,不是生吞活剝,而是力求理解、消化,并做出取舍。同時,要廣開知識的信息源,培養(yǎng)多種興趣,在治學中始終保持一個或幾個“焦點”,把接受與求索統(tǒng)一起來。所謂“鍥而不舍”,主要指恒心與毅力,要經(jīng)得起失敗學界名家的痛苦和成功的歡樂,不因挫折而氣餒,也不因一時的成功而固步自封。所選擇的課題最好要有系列性或遞進性,不滿足于“滿天星”,而力求“眾星拱月”。2.另辟蹊徑,獨上高樓。治學中應(yīng)注意選擇并調(diào)整自己的專攻方向,盡可能走前人沒走過的道路,努力開辟新的學術(shù)空間。這除了要多閱覽,了解學科的研究狀況之外,也要有開辟新視角的意識和勇氣。治學者在認定開拓路徑之后,還要有“獨上高樓”的志氣,向最高水準進發(fā)。盡管并非人人皆做得“一流”,但樹立一個較高的目標能成為自己不懈努力的動力。3.博采精研,融會貫通。任何學術(shù)成就都是在前人成果基礎(chǔ)上的新的開拓,因此,“另辟蹊徑”也要博采眾長。同時,知識與真理并非出于書本一途,更應(yīng)注意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從現(xiàn)實的生產(chǎn)與生活中尋找資料和問題,加以思考和取舍,并力求嚴謹、扎實。所謂“融會貫通”,除了知識層面的應(yīng)用外,也包括研究方法的選擇。對具體問題的探究不囿于人為的學科分類,可以超學科多層次的復合研究取代單學科的孤立研究。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是豐富復雜并不斷變化發(fā)展的,因此,只有多維視角與交叉研究才有助于洞察對象的實際,從而引出科學的結(jié)論。
作者:陶思炎單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