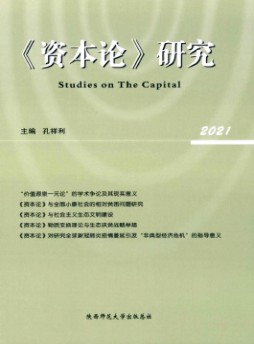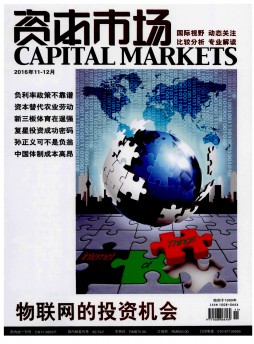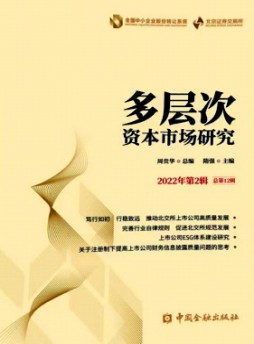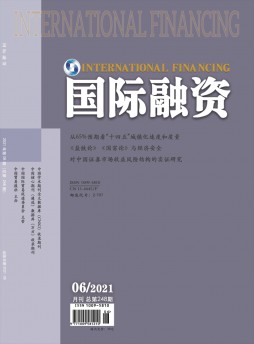資本主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資本主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guān)鍵詞]資本主義;解讀;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dòng)力》
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今天,已經(jīng)走過(guò)了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動(dòng)力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性質(zhì)是否已經(jīng)改變?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就這些問(wèn)題進(jìn)行探討,對(duì)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特征,把握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FeranandBraudel)是法國(guó)年鑒歷史學(xué)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時(shí)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jì)的物質(zhì)文明、經(jīng)濟(jì)和資本主義》和《法蘭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長(zhǎng)時(shí)段理論”連同年鑒學(xué)派一起,對(duì)20世紀(jì)末的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有較大影響。本文主要是對(duì)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dòng)力》一書(shū)進(jìn)行解讀。該書(shū)是1976年布羅代爾應(yīng)美國(guó)霍普金斯大學(xué)邀請(qǐng)所作的三次學(xué)術(shù)報(bào)告演講,并附錄了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討會(huì)上的言談。布羅代爾在他的這本小冊(cè)子中既給讀者提供了一些關(guān)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動(dòng)因的新解釋,對(duì)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范疇作了不同于其他學(xué)者的新界說(shuō),例如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競(jìng)爭(zhēng)與壟斷、中心與之間的關(guān)系等都提出了其獨(dú)特的見(jiàn)解。布羅代爾重視從生活世界人手進(jìn)行觀察和研究,他的這些見(jiàn)解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生活世界的范圍之內(nèi)對(duì)資本主義所作歷史考察和現(xiàn)實(shí)分析的結(jié)果,從而為我們這些外部讀者深入了解資本主義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視角。作為20世紀(jì)西方史學(xué)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布羅代爾是一位追求真實(shí)歷史并對(duì)于人類前途有著熱忱企盼的學(xué)者。他對(duì)資本主義的剝削特質(zhì)持有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并期盼實(shí)現(xiàn)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博愛(ài)。然而,布羅代爾在闡述資本主義的動(dòng)力、本質(zhì)與特征時(shí)有不少觀點(diǎn)是經(jīng)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的,對(duì)這些觀點(diǎn)的批判與反思能夠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與困惑。
在該書(shū)中,布羅代爾首先對(duì)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動(dòng)力源泉進(jìn)行了探索。布羅代爾關(guān)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來(lái),“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dāng)今的時(shí)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渾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對(duì)于人來(lái)說(shuō),過(guò)去獲得的經(jīng)驗(yàn)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duì)于這些東西,沒(méi)有人去細(xì)心觀察”。布羅代爾堅(jiān)持認(rèn)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著推動(dòng)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術(shù)與市場(chǎng)。在對(duì)資本主義發(fā)展動(dòng)力的分析方面,布羅代爾與馬克斯·舍勒以及馬克斯·韋伯存在著根本的歧異。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的動(dòng)力歸因于物質(zhì)生活中的人口、技術(shù)與市場(chǎng)等客觀因素,而馬克斯·舍勒與馬克斯·韋伯均把資本主義的動(dòng)力在本質(zhì)上歸因于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其中馬克斯·舍勒把資本主義精神歸結(jié)為一種“怨恨”,而馬克斯·韋伯則認(rèn)為資本主義動(dòng)力根源于新教倫理精神。
布羅代爾對(duì)資本主義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之間的聯(lián)系給出了自己獨(dú)特的判斷,并對(duì)資本主義的特征與本質(zhì)進(jìn)行了分析。布羅代爾認(rèn)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gè)領(lǐng)域區(qū)別開(kāi)來(lái),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是由商品交換引發(fā)的,是資本主義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他堅(jiān)持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作出某種區(qū)分,“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關(guān)系來(lái)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shí)別”。在他看來(lái),第一種形式的交換包括市場(chǎng)的每日交換、當(dāng)?shù)氐幕蛘呓嚯x的貿(mào)易。這種形式的交換沒(méi)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種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遠(yuǎn)程貿(mào)易。這種形式的交換容易避開(kāi)規(guī)則和慣常的控制。布羅代爾總結(jié)道,兩種形式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jìng)爭(zhēng)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jí)的、復(fù)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dòng)的機(jī)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lǐng)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dòng),而是第二類活動(dòng)”。在物質(zhì)生活、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與發(fā)展歷程方面,布羅代爾正確地指出物質(zhì)生活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的共同基礎(chǔ),他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方式認(rèn)為,“其實(shí),一切都駝在物質(zhì)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zhì)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jìn)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來(lái),擴(kuò)張其關(guān)系網(wǎng)。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kuò)充的受益者”。這種觀點(diǎn)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程是相符合的,與的唯物史觀也有著很好的吻合。
二
與以往的資本主義研究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義末期的傳統(tǒng)不同,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gè)長(zhǎng)時(shí)期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資本主義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離不開(kāi)穩(wěn)定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資本主義也不是在舊的封建土地貴族階級(jí)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新的社會(h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級(jí)制內(nèi),利用它的奢侈、閑散和缺乏遠(yuǎn)見(jiàn),攫取它的財(cái)產(chǎn)。在論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時(shí),他指出:“資本主義的推進(jìn)與成功需要一定的社會(huì)條件。它要求社會(huì)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并且,他以歐洲、中國(guó)與伊斯蘭國(guó)家的不同社會(huì)條件令人信服地說(shuō)明了資本主義發(fā)展命運(yùn)迥異的原因。與我們傳統(tǒng)認(rèn)為東方社會(huì)的高度封閉性與穩(wěn)定性不同,布羅代爾認(rèn)為中國(guó)與伊斯蘭社會(huì)的構(gòu)成遠(yuǎn)遠(yuǎn)不如歐洲封閉與穩(wěn)定。在布羅代爾眼中,中國(guó)的科舉是敞開(kāi)的大門(mén)、開(kāi)放的等級(jí);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lái)都是暫時(shí)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guò)是終生受用。布羅代爾對(duì)傳統(tǒng)中國(guó)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洞察,覺(jué)察到了那些過(guò)分富有、勢(shì)力過(guò)大的家族將受到國(guó)家的懷疑,而在法律上國(guó)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guó)家有權(quán)向農(nóng)民征稅,對(duì)于礦、工、商、企業(yè)看得很緊。這就使得在中國(guó),“每當(dāng)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zhǎng)之時(shí),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quán)的國(guó)家所制服”。在廣闊的伊斯蘭國(guó)家,尤其在18世紀(jì)之前,土地的擁有是臨時(shí)的,領(lǐng)由國(guó)家分配。因此,社會(huì)的頂峰經(jīng)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dòng)。而大家族正是布羅代爾所相信的初始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并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的地方。通過(guò)比較,布羅代爾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古代中國(guó)與伊斯蘭國(guó)家的社會(huì)等級(jí)是開(kāi)放的、流動(dòng)的,而歐洲的社會(huì)構(gòu)成顯得遠(yuǎn)為封閉與穩(wěn)定。這樣,他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論證。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歐洲,“財(cái)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zhǎng)與維持。在貨幣經(jīng)濟(jì)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xiàn),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duì)平靜的社會(huì)之水”。資本主義并沒(méi)有從根本上觸動(dòng)舊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財(cái)產(chǎn)和社會(huì)特權(quán)相對(duì)地受到保護(hù),名門(mén)世家還能相對(duì)平靜地坐享其成。由于財(cái)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來(lái)的位置上,……必須確立這種平靜或相對(duì)平靜的局面,才能使資本得以積累,使名門(mén)世家得以綿延長(zhǎng)存,使資本主義在貨幣經(jīng)濟(jì)的幫助下降臨人間。”過(guò)去流傳下來(lái)的財(cái)產(chǎn)繼承制度、封建地產(chǎn)、世襲家族的財(cái)富,為資本主義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提供了基礎(chǔ)。盡管布羅代爾是在全面考察資本主義長(zhǎng)時(shí)段歷史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論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論探索意義。但對(duì)他的某些觀點(diǎn)還是應(yīng)該作具體的分析、辯證的對(duì)待。例如,布羅代爾此處論證的符合邏輯并不能消除與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與他對(duì)壟斷與資本主義關(guān)系看法之間的矛盾。他認(rèn)為,資本主義從來(lái)都是壟斷的,一切壟斷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說(shuō),在伊斯蘭國(guó)家也好,在基督教國(guó)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guó)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guó)家的人。”沃勒斯坦在總結(jié)布羅代爾的思想時(shí)也指出:“如果沒(méi)有一種政治保證你就永遠(yuǎn)不能支配經(jīng)濟(jì),永遠(yuǎn)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chǎng)的力量,要想設(shè)立非經(jīng)濟(jì)性的壁壘,不讓人家涉足經(jīng)濟(jì)交易,要想將非分的價(jià)格強(qiáng)加于人,要想保證非優(yōu)先性的采購(gòu),不依靠某個(gè)政治當(dāng)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認(rèn)為沒(méi)有國(guó)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對(duì)國(guó)家的情況下也能成為一個(gè)(布羅代爾定義下的)資本家,那簡(jiǎn)直是一個(gè)荒誕的想法。”但是,即使我們承認(rèn)上述說(shuō)法,也不能消除布羅代爾的一個(gè)悖論。因?yàn)椋绻麌?guó)家對(duì)資本家是支持的話,那么顯然國(guó)家就不是處于中立的狀態(tài)之中,這與布羅代爾關(guān)于資本主義發(fā)展所需要的社會(huì)條件的判斷是矛盾的。
另外,在闡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的關(guān)系時(shí),布羅代爾指出資本主義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是兩種不同的層面,競(jìng)爭(zhēng)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特征,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誠(chéng)然,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中,壟斷的程度越來(lái)越高,由私人壟斷發(fā)展到國(guó)家壟斷,再發(fā)展到跨國(guó)壟斷,但是,競(jìng)爭(zhēng)始終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否認(rèn)了競(jìng)爭(zhēng),也就等于取消了資本主義。
最后,在關(guān)于專業(yè)化即勞動(dòng)分工問(wèn)題的闡述上,布羅代爾的觀點(diǎn)也容易引起爭(zhēng)論。布羅代爾認(rèn)為:“勞動(dòng)分工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進(jìn)展,迅速增強(qiáng),波及整個(gè)商業(yè)社會(huì),但處于頂層的批發(fā)商——資本家卻是例外。”對(duì)此,布羅代爾作出了三項(xiàng)判斷:(1)商人不實(shí)行專業(yè)化,因?yàn)樵谒苡|及的范圍內(nèi)沒(méi)有一個(gè)行當(dāng)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全部的活動(dòng)攏固;(2)大商人經(jīng)常要更換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因?yàn)楦呃麧?rùn)不斷地從一部門(mén)向另一部門(mén)轉(zhuǎn)移;(3)大商人的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只有一種有時(shí)具有專業(yè)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qián)交易。但是,對(duì)他的三項(xiàng)判斷都不難予以駁斥:第一,他所謂的商人即資本家在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由于競(jìng)爭(zhēng)的存在以及市場(chǎng)規(guī)律的作用確實(shí)沒(méi)有一個(gè)行當(dāng)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傾向于將各行當(dāng)?shù)睦麧?rùn)平均化,然而,由于競(jìng)爭(zhēng)與市場(chǎng)規(guī)律的作用,資本家要在部門(mén)利潤(rùn)趨向平均化的市場(chǎng)中生存或取勝,就必須實(shí)行專業(yè)化,取得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第二,高利潤(rùn)確實(shí)不斷地從一個(gè)部門(mén)向另一個(gè)部門(mén)轉(zhuǎn)移,直至競(jìng)爭(zhēng)使得其利潤(rùn)向社會(huì)平均利潤(rùn)靠近。然而,如果布羅代爾承認(rèn)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的話,則大資本家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jìn)入已為別的資本家所壟斷的高利潤(rùn)部門(mén);如果壟斷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而競(jìng)爭(zhēng)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的話,那么大資本家還是會(huì)選擇自己具有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產(chǎn)業(yè)部門(mén),則專業(yè)化乃是其必然的結(jié)果。布羅代爾的第三個(gè)判斷,事實(shí)上是對(duì)其關(guān)于專業(yè)化問(wèn)題的自我反駁。金錢(qián)交易即金融產(chǎn)業(yè)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一個(gè)部門(mén),其走向?qū)I(yè)化與其他資本主義部門(mén)的專業(yè)化一樣,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質(zhì)疑不僅了布羅代爾關(guān)于資本家專業(yè)化的命題,并且又一次對(duì)其關(guān)于資本主義社會(huì)競(jìng)爭(zhēng)與壟斷關(guān)系的觀點(diǎn)作出了有力的反駁。
三
布羅代爾對(duì)資本主義及其進(jìn)程的認(rèn)識(shí)是與世界總體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通過(guò)區(qū)分世界經(jīng)濟(jì)與經(jīng)濟(jì)世界兩個(gè)概念,布羅代爾詳細(xì)地闡述了經(jīng)濟(jì)世界、經(jīng)濟(jì)世界的中心與的關(guān)系以及經(jīng)濟(jì)世界中心轉(zhuǎn)移的規(guī)律。布羅代爾將世界經(jīng)濟(jì)界定為整個(gè)世界的經(jīng)濟(jì),即西第蒙斯所說(shuō)的“全球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世界則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個(gè)經(jīng)濟(jì)整體的情況下,地球上一個(gè)部分的經(jīng)濟(jì)。一個(gè)經(jīng)濟(jì)世界總要有一個(gè)極,一個(gè)中心,并且分解為中心地區(qū)、中間地區(qū)和地區(qū)。與沃勒斯坦提出的在從16世紀(jì)才建立起來(lái)的歐洲經(jīng)濟(jì)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經(jīng)濟(jì)世界的觀點(diǎn)不同,布羅代爾認(rèn)為遠(yuǎn)在歐洲認(rèn)識(shí)整個(gè)世界之前,自中世紀(jì),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經(jīng)分成幾個(gè)經(jīng)濟(jì)世界。這種觀點(diǎn)現(xiàn)在基本上得到學(xué)界的認(rèn)同。在闡述各經(jīng)濟(jì)世界中心變換即中心偏移規(guī)律的時(shí)候,布羅代爾也不自覺(jué)地流露出了一種“霸權(quán)穩(wěn)定論”的觀點(diǎn)傾向。他認(rèn)為,每當(dāng)出現(xiàn)一個(gè)中心失落的情況時(shí),一個(gè)新中心的重組過(guò)程就開(kāi)始了。一個(gè)經(jīng)濟(jì)世界若沒(méi)有一個(gè)重心,若沒(méi)有一個(gè)極,就不能生存下去。這種傾向隨著他將歐洲的經(jīng)濟(jì)世界歸結(jié)為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顯示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特征。這也是西方學(xué)者慣常流露出來(lái)的一種神態(tài)。然而,布羅代爾畢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義傾向,追求歷史真實(shí),關(guān)心人類前途的學(xué)者,在指出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世界中心變換規(guī)律之后,布羅代爾認(rèn)為資本主義性質(zhì)并未發(fā)生改變,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削國(guó)際資源、利用國(guó)際機(jī)遇的基礎(chǔ)之上;并且,它一貫地、頑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實(shí)上的壟斷,不顧在這方面反對(duì)它的激勵(lì)行動(dòng)。這實(shí)際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世界中心國(guó)家對(duì)國(guó)家的剝削以及國(guó)際經(jīng)濟(jì)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從布羅代爾把這兩方面看作是資本主義性質(zhì)并未改變的證據(jù)可以認(rèn)為,布羅代爾正是把剝削當(dāng)作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總結(jié)布羅代爾的思想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在我看來(lái),參與布羅代爾所理解的市場(chǎng)世界就是意味著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爭(zhēng),即為人類的自由與博愛(ài)而斗爭(zhēng),因?yàn)椋@樣一場(chǎng)斗爭(zhēng)的邏輯不允許世界上存在著人下人。這是一個(gè)(對(duì)于傳統(tǒng)觀念的)扭曲:布羅代爾定義下的市場(chǎng)所取得的勝利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會(huì)主義的表征。”布羅代爾的上述觀點(diǎn)不僅說(shuō)明了其作為一名史學(xué)家治學(xué)的科學(xué)性,也說(shuō)明了他對(duì)人類前途的關(guān)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觀相呼應(yīng)。
第2篇
恩格斯在批判英國(guó)曼徹斯特的艾爾克河時(shí)又指出:“在這里的一個(gè)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頂?shù)倪^(guò)道的盡頭,就是一個(gè)沒(méi)有門(mén)的廁所,非常臟,住戶們出入都只有跨過(guò)一片滿是大小便的臭氣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爾克河“下面緊靠河的地方有幾個(gè)制革廠,四周充滿了動(dòng)物腐爛的臭氣”。“橋底下流著,或者更確切地說(shuō),停滯著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fā)臭的小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通通匯集在艾爾克河里。”從恩格斯對(duì)艾爾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徹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環(huán)境特別骯臟。艾爾克河附近有多個(gè)工廠,特別是制革廠四周彌漫著動(dòng)物尸體腐爛的臭氣味。人們的排泄物、工廠的廢棄物以及廢水都直接排到艾爾克河里,使得艾爾克河發(fā)黑、發(fā)臭,嚴(yán)重地污染著曼徹斯特城市的環(huán)境,這些污染主要來(lái)自于工業(yè)生產(chǎn)。這還只是曼徹斯特舊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爾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這遠(yuǎn)遠(yuǎn)不是環(huán)境污染最嚴(yán)重的地方。恩格斯還對(duì)英國(guó)曼徹斯特的杜西橋以上的朗密爾特街空氣進(jìn)行了這樣的批判:“成群的豬在街上到處亂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亂拱,或者在大雜院內(nèi)的小棚子里關(guān)著……結(jié)果豬是養(yǎng)肥了,而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雜院里本來(lái)就不新鮮的空氣卻由于動(dòng)植物體的腐爛而完全變壞了。”恩格斯認(rèn)為,只有工業(yè)才使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為了自己發(fā)財(cái)致富,而把大雜院當(dāng)作住宅以高價(jià)租給工人,剝削貧窮的工人,制造廢棄物污染空氣、破壞生態(tài),造成生態(tài)危機(jī),毀壞成千上萬(wàn)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確地指出“:所有這些都是工業(yè)造成的。”
二、對(duì)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污染的現(xiàn)實(shí)批判
人類從石器時(shí)代過(guò)渡到銅器時(shí)代和鐵器時(shí)代起,農(nóng)業(yè)就在逐步發(fā)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huì),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與生態(tài)保護(hù)基本處于平衡狀態(tài),人與自然界相處較為和諧,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沒(méi)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壞。恩格斯在《英國(guó)工人階級(jí)狀況》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機(jī)器之前,紡紗織布都是在工人家里進(jìn)行的。妻子和女兒紡紗,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把紗織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紗賣(mài)掉。”但是產(chǎn)業(yè)革命使這種“田園詩(shī)”般的生活成為歷史,工人們不得不舍棄這種基本處于自給自足的美好田園生活,被卷進(jìn)了資本主義這架加速運(yùn)轉(zhuǎn)的龐大機(jī)器。馬克思通過(guò)考察發(fā)現(xiàn),“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的任何進(jìn)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dòng)者的技巧的進(jìn)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jìn)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chǎn)發(fā)展了社會(huì)生產(chǎn)過(guò)程的技術(shù)和結(jié)合,只是由于它同時(shí)破壞了一切財(cái)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業(yè)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農(nóng)業(yè)機(jī)器的技術(shù)不斷更新,農(nóng)業(yè)機(jī)器的技術(shù)不斷的發(fā)展更新就會(huì)生產(chǎn)出更多的產(chǎn)品,破壞更多的土地,出現(xiàn)更多新陳代謝斷裂,最終造成了生態(tài)危機(jī)的發(fā)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經(jīng)或者正在經(jīng)歷這種過(guò)程的國(guó)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guó);森林消失,如在英國(guó)和法國(guó),目前在德國(guó)和美國(guó)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淤淺在俄國(guó)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恩格斯認(rèn)為,無(wú)論是大工業(yè)已形成的資本主義國(guó)家還是正在發(fā)展工業(yè)的資本主義國(guó)家,都對(duì)環(huán)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使得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家庭手工業(yè)遭到破壞,牧場(chǎng)及森林逐漸消失,自然經(jīng)濟(jì)向貨幣經(jīng)濟(jì)演變。自然界的新陳代謝本是良性循環(huán)的,人與自然界的新陳代謝也應(yīng)該是良性循環(huán)的。人們所產(chǎn)生的排泄物以及工業(yè)循環(huán)產(chǎn)生的廢棄物,應(yīng)該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陳代謝循環(huán)的一部分,應(yīng)當(dāng)回歸自然界,回歸土壤,投入新一輪的代謝,使得土壤永續(xù)保持良性循環(huán)。馬克思、恩格斯通過(guò)對(duì)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的考察發(fā)現(xiàn)了新陳代謝的斷裂,原本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guò)程中,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出后,農(nóng)場(chǎng)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稈返回土地,進(jìn)入土地的自我循環(huán),加上牲畜糞便等農(nóng)家肥,維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再生產(chǎn)條件”被破壞了,土地的養(yǎng)分在年復(fù)一年的輪作中被帶走了,這種新陳代謝斷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終導(dǎo)致土壤危機(jī)發(fā)生。馬克思認(rèn)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來(lái)越占優(yōu)勢(shì),這樣一來(lái),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huì)的歷史動(dòng)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這樣它同時(shí)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nóng)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資本主義制度使人口大量匯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會(huì)勞動(dòng)力,創(chuàng)造更多的財(cái)富。但是人口過(guò)度集中卻嚴(yán)重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導(dǎo)致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出現(xiàn)新陳代謝斷裂。同時(shí),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對(duì)農(nóng)業(yè)造成的危害時(shí)還指出:“文明和產(chǎn)業(yè)的整個(gè)發(fā)展,對(duì)森林的破壞從來(lái)就起很大的作用,對(duì)比之下,對(duì)森林的護(hù)養(yǎng)和生產(chǎn)簡(jiǎn)直不起作用。”“對(duì)耕作的最初影響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樹(shù)木等,最后會(huì)使土地荒蕪。”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huì)文明和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被破壞,樹(shù)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壞,最后造成土地荒蕪、水土流失,生態(tài)不斷惡化,形成生態(tài)危機(jī)。
三、對(duì)資本主義生活環(huán)境污染的現(xiàn)實(shí)批判
第3篇
伍德不認(rèn)同目前流行的歷史時(shí)期的劃分,認(rèn)為把18世紀(jì)以來(lái)的資本主義歷史劃分為“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兩個(gè)主要階段是錯(cuò)誤的,強(qiáng)調(diào)資本主義的特殊性,質(zhì)疑“現(xiàn)代性”概念。自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人類似乎已經(jīng)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歷史時(shí)期,一些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改變,并將其稱之為后現(xiàn)代主義;另一些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變,將其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多元化資本主義。這些分析的共同點(diǎn)都是關(guān)注新技術(shù)、新交流手段、消費(fèi)主義等。后現(xiàn)代主義的知識(shí)分子都認(rèn)為資本主義高度繁榮,強(qiáng)調(diào)差異和新時(shí)代的到來(lái),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后現(xiàn)代性不是一種歷史時(shí)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屬性。伍德認(rèn)為,文化和經(jīng)濟(jì)的因素產(chǎn)生了后現(xiàn)代性的概念,否認(rèn)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劃分為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兩個(gè)主要階段,認(rèn)為現(xiàn)代性概念是錯(cuò)誤的,而使用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概念能否讓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是一個(gè)值得討論的問(wèn)題。伍德從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通過(guò)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大衛(wèi)·哈維的“后現(xiàn)代性”概念來(lái)論述這個(gè)問(wèn)題。根據(jù)詹姆遜和哈維的理論,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代表了兩個(gè)不同的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從來(lái)就沒(méi)有發(fā)生本質(zhì)的改變,并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從物質(zhì)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轉(zhuǎn)變。伍德指出,對(duì)于詹姆遜而言,后現(xiàn)代性對(duì)應(yīng)著“晚期資本主義”或新的多樣性的“信息化”和“消費(fèi)主義”的資本主義階段。哈維將后現(xiàn)代性描述成一種從福特主義到靈活積累的轉(zhuǎn)變。后現(xiàn)代性對(duì)應(yīng)著資本主義的某個(gè)發(fā)展階段,這個(gè)階段的特征是大規(guī)模的標(biāo)準(zhǔn)化的商品生產(chǎn),而且勞動(dòng)模式已經(jīng)被靈活性所代替:新的生產(chǎn)模式團(tuán)隊(duì)概念、準(zhǔn)時(shí)生產(chǎn)、多樣性的商品市場(chǎng)、流動(dòng)的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的資本等都因新技術(shù)而成為可能。伍德指出,這些改變主要是文化的改變。在哈維的后現(xiàn)代性理論中,時(shí)空壓縮占據(jù)重要地位,依靠新技術(shù),時(shí)間的加速和空間的壓縮成為可能,出現(xiàn)了新的交流模式、生產(chǎn)方法和市場(chǎng)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費(fèi)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現(xiàn)了新的文化資源來(lái)構(gòu)建“后現(xiàn)代主義”。伍德不同意哈維和詹姆遜等人的后現(xiàn)代性的觀點(diǎn),一方面,認(rèn)為當(dāng)今的確有一些像哈維和詹姆遜這樣的知識(shí)分子視“后現(xiàn)代性”為一種歷史態(tài)勢(shì)和當(dāng)代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視其為一種有歷史根源和物質(zhì)基礎(chǔ)、受制于歷史演變和政治力量的社會(huì)、文化形態(tài),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另一方面,她認(rèn)為當(dāng)代西方社會(huì)所謂的“最新”變化并不新,所謂的“后現(xiàn)代性”只不過(guò)是資本主義的晚期形態(tài),是資本主義的進(jìn)一步普遍化,是它的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社會(huì)關(guān)系和矛盾的進(jìn)一步普遍化,商品經(jīng)濟(jì)、資本積累和利潤(rùn)最大化的邏輯滲透到更廣闊的領(lǐng)域中。伍德指出了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以及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他認(rèn)為,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后現(xiàn)代性概念進(jìn)入現(xiàn)代性概念的范圍,后現(xiàn)代性與現(xiàn)代性相聯(lián)系。后現(xiàn)代性代表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以鮮明的經(jīng)濟(jì)和技術(shù)特征為標(biāo)志,被描述為信息時(shí)代、靈活積累、自由資本主義、消費(fèi)主義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組成。后現(xiàn)代性只是一種歷史癥候,不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后現(xiàn)代性”的概念在本質(zhì)上是對(duì)“現(xiàn)代性”概念的倒置。關(guān)于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之間的爭(zhēng)論雖然“剪不斷”、“理還亂”,但都沒(méi)有超越現(xiàn)代性話語(yǔ)的場(chǎng)域。“后現(xiàn)代性”概念從其傳統(tǒng)意義來(lái)說(shuō)與現(xiàn)代性概念相對(duì),后現(xiàn)代性緊隨現(xiàn)代性,而現(xiàn)代性顯示了資本主義與資產(chǎn)階級(jí)的同一性,現(xiàn)代性沒(méi)有使啟蒙理性同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jì)理性區(qū)別開(kāi)來(lái)。后現(xiàn)代主義關(guān)注資本主義的歷史轉(zhuǎn)變,強(qiáng)調(diào)資本主義社會(huì)和非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連續(xù)性,代替了啟蒙工程意義上的現(xiàn)代主義文化和知識(shí)模式。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在歷史的發(fā)展中被遮蔽,資本主義體系被看作一種自然的生成過(guò)程。伍德在批判后時(shí)指出,“后現(xiàn)代主義在它們?nèi)匀槐S械膶?duì)于平等或者某種形式的社會(huì)正義之承諾的范圍內(nèi)并沒(méi)有完全擺脫渴望解放與拒絕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礎(chǔ)的支撐之間的矛盾。后現(xiàn)代主義不能為它自己關(guān)于解放之承諾就此問(wèn)題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義提供一個(gè)可信的基礎(chǔ)。”伍德從當(dāng)代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quán)出發(fā),認(rèn)為正是后現(xiàn)代主義支撐西方帝國(guó)主義實(shí)施霸權(quán),這表現(xiàn)在后現(xiàn)代主義對(duì)歷史的無(wú)知,取消對(duì)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否定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價(jià)值,否定結(jié)構(gòu)和整體性思想,她認(rèn)為,“后現(xiàn)代主義不再是對(duì)疾病進(jìn)行診斷的一種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種疾病。
二、現(xiàn)代性與啟蒙運(yùn)動(dòng)
伍德指出,啟蒙運(yùn)動(dòng)與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性相關(guān),或者是因?yàn)樵缙谫Y本主義在其發(fā)展過(guò)程中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性,或者是因?yàn)楹侠砘陌l(fā)展產(chǎn)生了啟蒙運(yùn)動(dòng),帶來(lái)了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觀念來(lái)源于啟蒙運(yùn)動(dòng)的精神,是啟蒙精神哺育了現(xiàn)代性。伍德認(rèn)為,現(xiàn)代性來(lái)源于啟蒙運(yùn)動(dòng),在19世紀(jì)才得以興起。“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它們的傳統(tǒng)是西方現(xiàn)代性……西方自18世紀(jì)以來(lái)學(xué)術(shù)論戰(zhàn)繼承的遺產(chǎn)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無(wú)論好壞,這些都是西方的現(xiàn)實(shí)。”啟蒙運(yùn)動(dòng)代表了理性主義、技術(shù)中心主義、知識(shí)和生產(chǎn)的標(biāo)準(zhǔn)化、單線進(jìn)步觀以及普遍與絕對(duì)化的真理。這些特點(diǎn)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相聯(lián)系,已經(jīng)成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啟蒙工程。啟蒙運(yùn)動(dòng)誕生于獨(dú)特的非資本主義社會(huì),其許多特點(diǎn)根源于非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所有制關(guān)系。非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所有制關(guān)系不是向資本主義的過(guò)渡,而是脫離封建主義束縛的一種可選擇的道路。伍德認(rèn)為,現(xiàn)代性工程的主要發(fā)源地是農(nóng)村占主導(dǎo)的法國(guó),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在這個(gè)市場(chǎng)中,非資本主義原則仍然在起著作用,不從勞動(dòng)力中榨取剩余價(jià)值,不存在生產(chǎn)價(jià)值的創(chuàng)造,而是古老的商業(yè)行為。”這個(gè)市場(chǎng)崇尚賤買(mǎi)貴賣(mài)的原則,以外地謀利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買(mǎi)賣(mài)為主,農(nóng)業(yè)人口占據(jù)大多數(shù),是潛在的消費(fèi)市場(chǎng)。法國(guó)大革命后,資產(chǎn)階級(jí)包括專家、政府官員、知識(shí)分子與貴族統(tǒng)治者之間的斗爭(zhēng)同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的枷鎖中解放沒(méi)有任何關(guān)系。資產(chǎn)階級(jí)對(duì)專制國(guó)家的態(tài)度是模糊的,對(duì)專制原則的挑戰(zhàn)僅僅是對(duì)專制原則的延伸,完成了專制的集權(quán)化工程,這些同啟蒙精神相悖。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假設(shè)是各種類型的國(guó)家都存在于西方歷史中,“西方國(guó)家”在啟蒙運(yùn)動(dòng)中形成一個(gè)共同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現(xiàn)代性”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學(xué)術(shù)工程共同代表的單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則是理性主義。廣大的歷史學(xué)家和社會(huì)思想家已經(jīng)對(duì)理性主義進(jìn)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支持者還是批評(píng)者(或兩者皆有),從馬克斯·韋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爾到當(dāng)代反啟蒙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幾乎都以“善惡”二元對(duì)立的方式描述現(xiàn)代性。在這種情況下,“啟蒙運(yùn)動(dòng)要么被看做是人類解放的高峰,要么作為在最好情況下已無(wú)法阻止現(xiàn)代悲劇(啟蒙辯證法)和在最壞情況下導(dǎo)致種族滅絕和核毀滅威脅根源的慘敗。”如果現(xiàn)在有一個(gè)普遍的“現(xiàn)代性”概念,那么現(xiàn)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啟蒙運(yùn)動(dòng)“理性主義”的由資本主義市場(chǎng)、形式民主和技術(shù)進(jìn)步組成的一個(gè)復(fù)合物。后現(xiàn)代主義拋棄所有啟蒙運(yùn)動(dòng)中好的東西,特別是對(duì)普遍的人類解放的追求,將資本主義的破壞性歸咎于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價(jià)值。現(xiàn)在應(yīng)該將屬于資本主義而不屬于“現(xiàn)代性工程”的觀點(diǎn)同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方案區(qū)分開(kāi)來(lái)。“這樣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啟蒙運(yùn)動(dòng)思想的后現(xiàn)代主義,也有助于反對(duì)資本主義的歡呼雀躍。”后現(xiàn)代主義根源于現(xiàn)代主義,是對(duì)現(xiàn)代性工程的回應(yīng)。“后現(xiàn)代主義認(rèn)為這個(gè)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決定性的。否認(rèn)任何完整的過(guò)程,任何所謂的‘宏大敘事’,并拒絕對(duì)世界和歷史做出綜合的普遍的理論解釋。”后現(xiàn)代主義也拒絕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認(rèn)為啟蒙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死亡,但仍有價(jià)值,它要借助社會(huì)主義得以復(fù)興。資本主義雖已經(jīng)普遍化,但不妨礙啟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資本主義對(duì)人類的壓迫,才能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性與啟蒙的聯(lián)盟,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理性、科學(xué)和自由的啟蒙精神。
三、簡(jiǎn)評(pí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