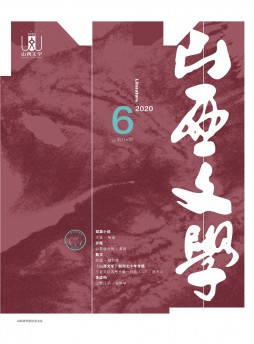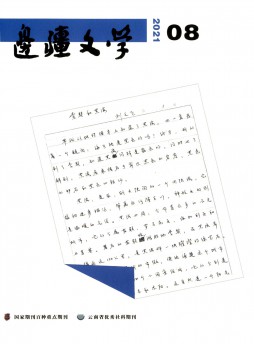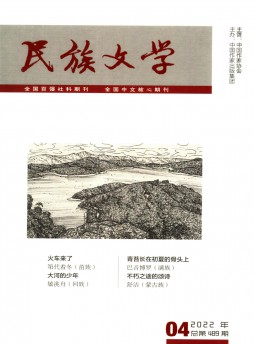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guān)鍵詞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 文學(xué)批評(píng) 傳統(tǒng)文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I20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學(xué)批評(píng)一直以來都是文學(xué)活動(dòng)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漫長的文學(xué)史中,文學(xué)批評(píng)從來沒有缺席,它伴隨著整個(gè)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直至今日。但當(dāng)前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完全顛覆了文學(xué)發(fā)展的土壤,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在興起的初期就受到了眾多的質(zhì)疑,特別是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似乎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環(huán)境中并不具備話語權(quán),也導(dǎo)致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當(dāng)前的發(fā)展極為艱難。當(dāng)然,我們不能夠一味地為了批評(píng)而批評(píng),批評(píng)的目的是進(jìn)步,而不是吹毛求疵。當(dāng)前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發(fā)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們就要剖析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與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關(guān)系,圖探索出二者的平衡點(diǎn),使二者能夠相互促進(jìn),為中國文學(xué)事業(yè)乃至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xiàn)重要的力量。
1文學(xué)批評(píng)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概念
文學(xué)批評(píng)是文學(xué)活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字面上我們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過批評(píng)的方式對(duì)文學(xué)的發(fā)展方向、內(nèi)容和思想等要素進(jìn)行正確的引導(dǎo),使文學(xué)的發(fā)展不致偏離方向。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文學(xué)的發(fā)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的,首先,對(duì)于作家來說,文學(xué)批評(píng)能夠有效地規(guī)范作家的寫作行為,能夠引導(dǎo)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正確方向;其次,對(duì)于讀者來說,通過批評(píng)的角度能夠讓讀者更為深刻地理解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涵,也有助于提升讀者的文學(xué)審美水平;最后,對(duì)于整個(gè)社會(huì)來說,文學(xué)批評(píng)代表的是主流的價(jià)值觀,之所以會(huì)出現(xiàn)公認(rèn)的批評(píng),是因?yàn)槠洳环仙鐣?huì)大多數(shù)人的想法和觀念,這對(duì)于弘揚(yáng)社會(huì)正能量,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也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顧名思義指的就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創(chuàng)作、發(fā)表、供讀者閱讀的文學(xué)作品。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范圍非常廣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參差不齊,這恰恰是因?yàn)榫W(wǎng)絡(luò)的開放性激勵(lì)著“草根”一族開始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舞臺(tái),文學(xué)不再是作家獨(dú)享的瑰寶,而成為了每個(gè)人都可以接觸并實(shí)踐的平民化的產(chǎn)物。
2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對(duì)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挑戰(zhàn)
當(dāng)前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擔(dān)憂的并不是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環(huán)境中沒有文學(xué)批評(píng),恰恰相反,網(wǎng)絡(luò)世界絕對(duì)不缺少“批評(píng)者”,網(wǎng)絡(luò)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對(duì)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而很多觀點(diǎn)非常淺顯,僅僅是自身的直觀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觀性。這才是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們最害怕見到的事情---不怕沒有批評(píng),但是怕沒有邏輯的批評(píng)。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蓬勃發(fā)展的當(dāng)前,文學(xué)批評(píng)越來越大眾化,卻又越來越低俗化。當(dāng)然,這也是一個(gè)文學(xué)批評(píng)發(fā)展的“陣痛”,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話語權(quán)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而現(xiàn)在話語權(quán)回歸大眾,勢必要經(jīng)過一定時(shí)期的混亂和無序,最終終究會(huì)朝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這也是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的“精英”和“平民”之爭,是文學(xué)批評(píng)在當(dāng)前時(shí)代必然要經(jīng)過的過程。
3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如何應(yīng)對(duì)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挑戰(zhàn)
在當(dāng)前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迅猛發(fā)展的情況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應(yīng)當(dāng)適時(shí)地進(jìn)行調(diào)整,以應(yīng)對(duì)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挑戰(zhàn),如此才能夠不負(fù)文學(xué)批評(píng)之名,充分發(fā)揮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文學(xué)發(fā)展的作用。
首先,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應(yīng)當(dāng)走進(jìn)大眾。數(shù)千年來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話語權(quán)都掌握在極少數(shù)人口中,這種自詡為“雅”,卻無法容忍“俗”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狀態(tài)其實(shí)并不是一個(gè)正確的狀態(tài),精英化并不是文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píng)發(fā)展的正確道路。文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píng)是服務(wù)大眾的,大眾都不認(rèn)同,文學(xué)批評(píng)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了。
其次,應(yīng)當(dāng)堅(jiān)守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原則、精神和價(jià)值。文學(xué)批評(píng)是要對(duì)文學(xué)的發(fā)展起到促進(jìn)和引導(dǎo)作用的,無腦地批判并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所以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當(dāng)前文學(xué)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還是應(yīng)當(dāng)堅(jiān)守一些原則、精神和核心價(jià)值的。例如人文主義精神、歌頌真善美、批判假惡丑這都是文學(xué)批評(píng)恒久不變的精神和價(jià)值,無論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如何發(fā)展都不應(yīng)當(dāng)有所改變。
最后,要轉(zhuǎn)變批評(píng)的方式。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太過于艱澀,讓大多數(shù)讀者都無法理解,那么文學(xué)批評(píng)難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嗎?當(dāng)前的時(shí)代中,人們在各個(gè)領(lǐng)域的選擇都更多了,人們更愿意去選擇自己能夠理解和適應(yīng)的事物,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應(yīng)有的發(fā)展方向,沉重的說教已經(jīng)不適合當(dāng)前的時(shí)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結(jié)語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發(fā)展的確給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是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之所以能夠在這數(shù)十年內(nèi)極為蓬勃的發(fā)展,一方面是因?yàn)楫?dāng)前社會(huì)形態(tài)、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巨大變化,另一方面也是因?yàn)樯鐣?huì)意識(shí)隨著社會(huì)物質(zhì)的變化已經(jīng)發(fā)展根本性的變革。很多文學(xué)批評(píng)家都在感嘆和惋惜,因?yàn)槲膶W(xué)批評(píng)已經(jīng)存在了數(shù)千年,但卻在只有數(shù)十年歷史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面前捉襟見肘。筆者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是伴隨著文學(xué)的發(fā)展而誕生的,只要有其價(jià)值,就不會(huì)消亡,只是面臨著當(dāng)前文學(xué)結(jié)構(gòu)發(fā)生巨大變革的背景,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合理的改變,一切從實(shí)際出發(fā)才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真正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原則,才是能夠繼續(xù)發(fā)揮其引導(dǎo)作用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xiàn)
[1] 趙李梅,傅宗洪.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如何應(yīng)對(duì)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挑戰(zhàn)[J].綿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29(7).
第2篇
論文關(guān)鍵詞:印象主義的批評(píng);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批評(píng)的獨(dú)立性;自我;妙悟
很久以來,人們對(duì)李健吾先生的評(píng)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說、散文、翻譯作品和法國文學(xué)研究理論上.即使談他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大多也只是會(huì)談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問因書評(píng)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兩場筆墨“官司”。但是毫無疑問,李健吾還是一個(gè)成就卓著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由于他與法國印象主義的淵源,一直以來,李健吾的批評(píng)都被稱作是印象主義的批評(píng),或者是印象鑒賞的批評(píng),他自己也樂于承認(rèn)這樣的概括。但是近年來,有許多評(píng)論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評(píng)中不僅有法國的印象主義,也有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成分,因而他的批評(píng)又被稱為中國式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但是,在我看來.縱觀李健吾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法國的印象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并不只是份量輕重的問題,而是表里的關(guān)系,即法國的印象主義為表.而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為里,雖然完全中國傳統(tǒng)式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所占的地位與份量不大.卻是他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核心所在.是我們理解他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的一把鑰匙。
一、表面上看來,他深得法國印象主義的精髓
從源流上說,印象主義其實(shí)是唯美主義的余波。而唯美主義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的獨(dú)立,主張“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因而印象主義提出“為批評(píng)而批評(píng)”。此外.印象主義者很看重批評(píng)家的主觀介入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他們非常贊同王爾德提出的唯美主義觀點(diǎn),認(rèn)為批評(píng)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甚至認(rèn)為“最高之批評(píng).比創(chuàng)作之藝術(shù)品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因而印象主義者主張應(yīng)以個(gè)人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從事批評(píng)。而在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本質(zhì)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發(fā)現(xiàn)論”,就是把批評(píng)當(dāng)作是“自我發(fā)現(xiàn)”的一種手段。“猶如書評(píng)家、批評(píng)家的對(duì)象也是書。批評(píng)的成就是自我的發(fā)現(xiàn)和價(jià)值的決定。發(fā)現(xiàn)自我就得周密,決定價(jià)值就得綜合。一個(gè)批評(píng)家是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的化合.有顆創(chuàng)造的心靈去運(yùn)用死的知識(shí)。他的野心在擴(kuò)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認(rèn)識(shí),提高他的鑒賞,完成他的理論。(批評(píng))本身也正是一種藝術(shù)。”可以說,李健吾的獨(dú)特之處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評(píng)本身是一種藝術(shù)。這樣,批評(píng)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東家一樣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臉色,因?yàn)椤白髡叩淖园?以及類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過,是一種經(jīng)驗(yàn);批評(píng)者的探討,根據(jù)作者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果(書),另成一種經(jīng)驗(yàn)”。批評(píng)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píng)者有闡釋的自由。因此,當(dāng)《愛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評(píng)者的“拳頭會(huì)打到空處”的時(shí)候.李健吾并不是臉紅心跳、誠惶誠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見,而是坦然道:“我無從用我的理解鉗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樣不能強(qiáng)我影從。”他捍衛(wèi)了批評(píng)的尊嚴(yán),因?yàn)榕u(píng)“是一種獨(dú)立的,自為完成的.猶如其他文學(xué)的部門.尊嚴(yán)的存在”。在他看來.批評(píng)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尷尬,批評(píng)家不需要同作家“攀親戚”.批評(píng)和作品是兩種互為需要的藝術(shù)。批評(píng)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píng)者有闡釋的自由。維護(hù)批評(píng)的尊嚴(yán)當(dāng)然不以貶低創(chuàng)作的地位為代價(jià),批評(píng)者和創(chuàng)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謙遜的、取對(duì)話的態(tài)度。批評(píng)者的謙遜并非意味著批評(píng)主體的喪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評(píng)主體的確立不表現(xiàn)為教訓(xùn)、裁斷,甚至判決的冰冷的鐵面.而是以“泯滅自我”為條件.并且在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交流融匯中得到豐富和加強(qiáng)。因此,對(duì)于批評(píng)者來說,作品并非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而是經(jīng)驗(yàn)的對(duì)象;批評(píng)主體在經(jīng)驗(yàn)中建立和強(qiáng)化.并由此確立批評(píng)的獨(dú)立性。
倘若批評(píng)是一種獨(dú)立的藝術(shù).那么批評(píng)也就是一種“表現(xiàn)”,表現(xiàn)“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謂的風(fēng)格,或者文筆”。風(fēng)格即是“人自己”,表現(xiàn)自我,同時(shí)就“區(qū)別這自我”.“證明我之所以為我”。其難在于一個(gè)“誠”字。近年來,批評(píng)界不時(shí)冒出一兩聲對(duì)文采的呼喚.李健吾的議論可以使我們豁然開朗:批評(píng)要有文采,但這文采決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潤色”,它“是內(nèi)心壓力之下的一種必然的結(jié)果”。
由此出發(fā),李健吾把“自我”作為批評(píng)的“根據(jù)”。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張揚(yáng)自我”雖然不是新鮮事,但在批評(píng)中。“自我”卻一直被忽略。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種批評(píng)的自我意識(shí),他認(rèn)為強(qiáng)調(diào)“自我的發(fā)現(xiàn)”的結(jié)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評(píng)的獨(dú)立”,批評(píng)也就由充當(dāng)文學(xué)的附庸而轉(zhuǎn)為一種獨(dú)立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
印象主義的哲學(xué)基礎(chǔ)是相對(duì)主義和懷疑論,認(rèn)為宇宙萬物永遠(yuǎn)都處于變動(dòng)的狀態(tài),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觀真實(shí),一切所謂“真實(shí)”都無非是一種感覺,是相對(duì)的、主觀的。這樣,印象主義者就特別強(qiáng)調(diào)以個(gè)人的感覺與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或者說,干脆否定任何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
由此出發(fā)。李健吾也否定批評(píng)中存在任何客觀的固定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于許多批評(píng)家都特別關(guān)注作品的所謂“客觀意圖”。他認(rèn)為是不存在的,因?yàn)榧词故亲髡弑救艘膊灰欢ň湍苷f得清楚,那么批評(píng)家就更加無從解釋了。更何況人與人的差異極大。同樣的事物也會(huì)有不同的解釋。所以任何解釋也都無所謂是否合乎標(biāo)準(zhǔn)。所以,李健吾的批評(píng)重在對(duì)于作品的整體的審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閱讀,首先是體味。“批評(píng)的對(duì)象也是書”,“凡落在書以外的條件。他盡可置諸不問”。首先“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shù)、文學(xué)等武裝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準(zhǔn)他們的態(tài)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來看一個(gè)人潛在的活動(dòng),和聚在這深處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漿,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則,“缺乏應(yīng)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執(zhí)誤”。他強(qiáng)調(diào)直覺,強(qiáng)調(diào)感受,“批評(píng)的成就是自我的發(fā)現(xiàn)和價(jià)值的決定”。據(jù)說如今有的批評(píng)家很少讀作品,或是淺嘗輒止,他們的批評(píng)隔靴搔癢,戳不到痛處,也就難怪了。
二、實(shí)質(zhì)上。他是在將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現(xiàn)代化
正如溫儒敏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史》中所說:“中國傳統(tǒng)批評(píng)思維方法不無精微之處,在和世界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評(píng)理論的比較中。中國古典形態(tài)的批評(píng)確能獨(dú)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國傳統(tǒng)批評(píng)多采用的詩話、詞話、小說評(píng)點(diǎn)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覺與經(jīng)驗(yàn),習(xí)慣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鑒賞。以詩意簡潔的文字,點(diǎn)悟與傳達(dá)作品的精神或閱讀體驗(yàn);另有一種傳統(tǒng)批評(píng)的路數(shù)則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純粹實(shí)證式的考據(jù)、注疏和索隱。但是不管哪一種,都不太注意語言抽象分析和邏輯思辨,缺少理論系統(tǒng)性。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所依賴的不是固定的理論和標(biāo)準(zhǔn),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閱讀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賞力和判斷力,這些都是溝通批評(píng)家與作者、讀者感受體驗(yàn)的橋梁。”
如果我們拋開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主義與術(shù)語.仔細(xì)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許多評(píng)論,用心體會(huì)一下的話,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李健吾雖然被冠以印象主義,但他對(duì)許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議論卻更令人想起中國古典的文學(xué)評(píng)論,如《文心雕龍》、《人間詞話》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義,是因?yàn)樗鼜谋举|(zhì)上與中國的古典文學(xué)批評(píng)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義的理論來收束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現(xiàn)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體的方法.就是“把他獨(dú)有的印象形成條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而是他獨(dú)有的。基于他全部個(gè)人的修養(yǎng)、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和人格的印象,“條例”即規(guī)則,即綜合。要通過理性分析來完成。不妨說。李健吾的批評(píng)是一種以個(gè)人的體驗(yàn)為基礎(chǔ),以普遍的人性為指歸。以淵博的學(xué)識(shí)為范圍的瀟灑自由的批評(píng)。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賞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家法郎士的話說:“好批評(píng)家是這樣一個(gè)人:敘述他的靈魂在杰作之間的奇遇。”
第3篇
論文關(guān)鍵詞:新歷史主義;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歷史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是舶來品,它產(chǎn)生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學(xué)界。20世紀(jì)80年代,在渡過了西方“歷史主義危機(jī)”之后,人們又重新追問文學(xué)與歷史的關(guān)系。在這種情況之下,新歷史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以反抗形式主義的姿態(tài),登上了歷史舞臺(tái),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征。
一、歷史與文學(xué)
(一)歷史是什么。從歷史理論來說,新歷史主義的“新”是相對(duì)于傳統(tǒng)歷史觀而言的,這最主要表現(xiàn)在它對(duì)歷史的性質(zhì)的再認(rèn)識(shí)上。而對(duì)“歷史是什么”的回答,構(gòu)成了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chǔ)。傳統(tǒng)的歷史觀把歷史看成是一個(gè)可供客觀認(rèn)識(shí)的領(lǐng)域,歷史是獨(dú)立于歷史研究者認(rèn)識(shí)主體的、獨(dú)立于他的研究手段(“發(fā)現(xiàn)”)和工具(“語言”)的實(shí)際存在。如果歷史研究者在把握歷史的過程中能夠克服和排除主觀因素,透明地運(yùn)用其語言工具,他就能夠再現(xiàn)般發(fā)掘出埋藏在時(shí)間風(fēng)塵下的“史實(shí)”,并由此獲得關(guān)于歷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發(fā)現(xiàn)。在新歷史主義看來,上述的歷史觀是實(shí)證主義和科學(xué)主義在歷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歷史研究者的主體(“人”)和他的工具(“語言”)本身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任何具體的人在借助語言而把目光投向過去的時(shí)候,他的視點(diǎn)和視野都已經(jīng)被限制在某一現(xiàn)刻歷史、語言的歷史沉淀以及它們錯(cuò)綜的復(fù)合影響之中。
展現(xiàn)在他眼前的不過是他所看見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因此,新歷史主義認(rèn)為歷史是現(xiàn)時(shí)的人對(duì)過去的一種“知識(shí)”,這種知識(shí)以話語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寫出來的。至于歷史上究竟發(fā)生過什么,他們則不管,他們認(rèn)為歷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種閱讀、闡釋這些文本的策略組成。
對(duì)此美國文藝?yán)碚摷液5恰烟卣f:“從這種觀點(diǎn)看,‘歷史’不僅是指我們能夠研究的對(duì)象以及我們對(duì)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類特別的寫作出來的話語而達(dá)到的與‘過去’的某種關(guān)系。”在這里,歷史是對(duì)過去事件的描述,而這種描述并非純粹的客觀再現(xiàn),而是語言對(duì)事件的再度構(gòu)成,其中必然滲透著語言運(yùn)用者對(duì)事件的解釋。
因此,歷史被看作一個(gè)文本。海登·懷特還進(jìn)一步論證道:“不論歷史事件還可能是別的什么,它們都是實(shí)際上發(fā)生過的事件,或者被認(rèn)為實(shí)際上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這樣的事件,為了構(gòu)成反映的客體,它們必須被描述出來,并且以某種自然或?qū)iT的語言描述出來。后來對(duì)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釋,不論是自然邏輯推理的還是敘事主義的,永遠(yuǎn)都是對(duì)先前描述出來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釋。描述是語言的凝聚、置換、象征和對(duì)這些作兩度修改并宣告文本產(chǎn)生的一些過程的產(chǎn)物。單憑這一點(diǎn),人們就有理由說歷史是一個(gè)文本。”
歷史是一種話語,或一種文本。這種歷史觀帶有明顯的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色彩,是后結(jié)構(gòu)主義者歷史觀的延續(xù)。福柯等后結(jié)構(gòu)主義者,把歷史稱為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正是突出了歷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話說就是,原先的一個(gè)大寫的單數(shù)的“歷史”(History)被小寫的復(fù)數(shù)的“歷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歷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歷史。福柯的這種歷史觀正應(yīng)和了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一種信念,即人們只有通過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對(duì)于人的思想來說是不存在的,沒有意義的。
作為話語或文本而存在的歷史,帶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虛構(gòu)因此而成為歷史文本無法擺脫的特質(zhì)。海登·懷特曾說歷史的深層結(jié)構(gòu)是詩性的,便是基于對(duì)歷史文本的想象與虛構(gòu)特質(zhì)的理解而作的評(píng)論。這也就是說,歷史從來就不能脫離想象而存在,歷史在本質(zhì)上仍是一種語言闡釋,它不能不帶有一切語言構(gòu)成物所共有的虛構(gòu)性。與此相關(guān),所謂歷史真實(shí)并不等于事實(shí),它是事實(shí)與一個(gè)觀念構(gòu)造的結(jié)合,也就是說,沒有一種絕對(duì)的真實(shí),一種離開具體觀念和闡釋語境的真實(shí)。歷史話語中的真實(shí)總是存在于一定的觀念構(gòu)造之中。
(二)歷史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當(dāng)海登·懷特把歷史的深層結(jié)構(gòu)解釋為“詩性”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在歷史與文學(xué)之間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時(shí)候都更加密切的聯(lián)系。新歷史主義者認(rèn)為,歷史和文學(xué)同屬一個(gè)符號(hào)系統(tǒng),歷史的虛構(gòu)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xué)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傳統(tǒng)歷史學(xué)家那里,歷史的特質(zhì)是“真實(shí)”,它記錄的是真實(shí)的事件,而這種“真實(shí)”與文學(xué)的特質(zhì)“虛構(gòu)”恰成對(duì)比,兩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歷史主義者打破了歷史的“真實(shí)”假象,他們認(rèn)為,歷史文本的運(yùn)作方式是“編織情節(jié)”,即從時(shí)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shí),然后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而進(jìn)行編碼,這種編織情節(jié)的方式與文學(xué)話語的虛構(gòu)方式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在舊歷史主義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中,文學(xué)文本被看作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認(rèn)為它產(chǎn)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是對(duì)歷史的一種反映。那么,舊歷史主義批評(píng)家所從事的文學(xué)研究和文學(xué)評(píng)論的任務(wù)就是一種“還原”歷史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通過把文學(xué)作品放到它所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試圖再現(xiàn)出作者的原來的意義,從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舊歷史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關(guān)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因?yàn)樗J(rèn)為在文學(xué)作品之外,有一個(gè)真實(shí)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xué)作品只是對(duì)這個(gè)真實(shí)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是,歷史是第一性的,文學(xué)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說歷史是背景,文學(xué)作品是前景。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真實(shí)決定了文學(xué)的存在和文學(xué)的內(nèi)容。而新歷史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不再把歷史看成是由客觀規(guī)律所控制的過程,看成是文學(xué)的“背景”或“反映對(duì)象”,而是把歷史和文學(xué)兩者同時(shí)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構(gòu)成。在他們看來,歷史和文學(xué)同屬一個(gè)符號(hào)系統(tǒng),歷史的虛構(gòu)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xué)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因此兩者之間不是誰決定誰、誰反映誰的關(guān)系,而是相互證明、相互印證的“互文性”關(guān)系。在新歷史主義者眼里,文學(xué)與歷史并無明顯的界限,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以一種復(fù)雜的相互糾纏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他們所關(guān)注的,并非通常人們理解的那種虛構(gòu)的、想象的、狹義的文學(xué),而是包括文學(xué)在內(nèi)的整個(gè)文化。換句話說,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從事的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體批評(píng)行為的實(shí)施過程中,我們既能看到“用文學(xué)的方法研究歷史”,也能看到“用歷史的方法研究文學(xué)”。
二、文學(xué)與政治
當(dāng)新歷史主義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歷史文本與非歷史文本間的鴻溝,拉近了歷史客體與當(dāng)代主體間的距離時(shí),并不意味著要把歷史文本理解成憑空捏造,新歷史主義的目的是揭開作為教科書或史書的“歷史”的神秘的面紗,讓人看到其形成軌跡,發(fā)現(xiàn)文本的“歷史性”。在這方面,它對(duì)福柯的“話語——權(quán)力”理論多有借鑒。福柯用“話語”連接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huì)中的整個(gè)社會(huì)機(jī)制、慣例、習(xí)俗等,這就使文本作為一種“話語實(shí)踐”指向社會(huì)歷史。話語實(shí)踐植根于社會(huì)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約,總是體現(xiàn)著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由此,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論歷史或文學(xué),作為文本,它們都是一種權(quán)力運(yùn)作的場所,不同意見和興趣的交鋒場所,傳統(tǒng)和反傳統(tǒng)的勢力發(fā)生碰撞的地方。
同時(shí),福柯挑戰(zhàn)現(xiàn)存歷史定論的勇氣也給了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說,在任何一個(gè)看似處于某種統(tǒng)一意識(shí)形態(tài)統(tǒng)治下的歷史時(shí)期中,都充滿了被壓抑的它異因素,歷史學(xué)家必須在他的譜系研究中對(duì)它異和斷裂給予格外的關(guān)注。研究斷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話語、社會(huì)形態(tài)的形成條件,并由此對(duì)它進(jìn)行批判,而不是認(rèn)可;昭彰它異不僅否定了統(tǒng)一意識(shí)形態(tài)的神話,而且通過歷史定論對(duì)它異因素的壓制過程和方式可以透視出社會(huì)、政治、文化的復(fù)雜的機(jī)制運(yùn)作情況。
因此,新歷史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對(duì)歷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著對(duì)現(xiàn)今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馬上顛覆現(xiàn)存的社會(huì)制度,而在于對(duì)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則進(jìn)行質(zhì)疑。新歷史主義批評(píng)所關(guān)心的不只是主導(dǎo)意識(shí)形態(tài)所維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這表象下被壓抑的它異和破壞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