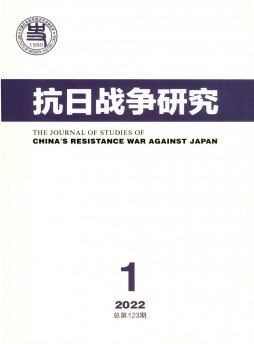戰爭時期的音樂理論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戰爭時期的音樂理論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張雪艷單位:西安工業大學
在中國近現代音樂批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音樂理論批評也許并不像同時代的某些理論批評(諸如文學批評)那樣成果豐碩,但是在百余年的音樂文化建設中,對于音樂創作和音樂建設的努力從未停止過,即使在中國民族危亡時刻,音樂的理論建設也同樣在積極地進行著。發生在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時期的延安音樂理論建設,是中國音樂理論建設中不可獲缺,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它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新音樂理論的重要思想和左翼音樂運動中的音樂理論批評的傳統,成為中國新音樂理論建設的新階段。本文試圖將延安時期音樂理論建設作為考察對象,對這一階段的音樂理論的求索過程和主要理論成就進行初步的梳理。延安時期的音樂理論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有著久遠的歷史文化淵源。它的形成和發展深受中國近代革命思潮和五四新音樂的影響,是在黨的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總結中央蘇區的音樂實踐和左翼音樂運動理論成果基礎上所進行新的理論創造和新的音樂建設。這一時期,民族化、大眾化是音樂理論持續關注和努力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延安時期音樂運動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這一時期音樂理論建設的核心。
音樂大眾化思想并非肇始于延安時期。其萌芽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新音樂理論,當時的音樂界就提出了“以‘平民文學’為鑒,主張通過藝術、音樂來發展個性自由,培養高尚情操,以達到改善人生,改善社會的功效,以‘啟蒙’為中心,以美育為形式,強調藝術與生活之關系,重視藝術的社會功能。”(劉曲雁.“五四”與“新音樂”理論[J].齊魯藝苑,1995,(1).)此時的“平民文學”也就是大眾文學,以“‘平民文學’為鑒”的新音樂也就是民眾全體的音樂,而且也初步強調了藝術的社會功能。在1927年至1934年中央蘇區領導的革命文藝發展中,音樂大眾化雖然并沒有形成相應的音樂理論,但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大眾化是作為一種音樂實踐而存在的。因為蘇區文藝還處在革命文藝的萌發期,而革命音樂活動是為了在音樂上尋求與群眾溝通的語言,團結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為革命斗爭服務。蘇區的音樂大眾化主要是從民間文藝中吸取營養,對當地流行的歌曲進行重新填詞改造以便于傳唱。這種方法為后來延安時期的民間音樂采集研究所繼承和采用。
大眾化概念的明確提出首先發生在文學領域。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為了更大范圍地爭取廣大群眾投入到民族解放斗爭中去,左聯成立后十分重視文藝大眾化問題,不僅成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而且還專門開展過三次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討論涉及大眾化的必要性、目的、方法和途徑等問題。1931年11月的“左聯”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還特別強調了大眾化問題的意見:“為完成當前迫切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確定新的路線。首先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大眾化。……今后的文學必須以‘屬于大眾,為大眾理解,所愛好’為原則。”(文學導報,第一卷,1931年11月15日)這里的“大眾”已經從民眾全體的“大眾”,衍變為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的代名詞。“左翼文藝運動提出的‘大眾化’的主張,意味著文藝家要走向農工大眾,發展大眾文藝,使文藝成為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姜昕.延安解放區音樂大眾化思潮研究[D].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7)從文學界開始的大眾化要求繼而影響到了包括音樂在內的整個藝術界。1932年至1934年間,一些進步音樂工作者如聶耳、王旦東、李元慶、田漢、任光、張署、安娥、呂驥等人先后組織成立了“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1932年)、“中蘇音樂學會”(1933年)、“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1934年)等左翼音樂組織,開展了革命音樂活動。從1936年初起,為了與當時政治上的抗日統一戰線相呼應,左翼音樂界提出了音樂大眾化的問題,并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大量有關大眾音樂的批評文章。其中周巍峙的《國防音樂大眾化》、呂驥的《論國防音樂》、劉良模的《高唱吧!中國》、陶行知的《從大眾歌曲講到民眾歌詠》、周鋼鳴的《論聶耳和新音樂運動》、麥新、孟波的《大眾歌聲》第一集前記等文,從理論上闡述了左翼音樂運動的根本任務和性質。他們認為,應該“把國防音樂迅速建立起來”,以喚醒民眾,同時指出“建設國防音樂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大眾化”。為實現大眾化,“國防音樂應當以歌曲為中心”,因為歌曲較容易為群眾所接受,“要用唱歌的方法來喚醒民眾,訓練民眾,組織民眾,使他們有參加集團生活的習慣和紀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集團”。這些音樂思想為延安時期的音樂大眾化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左翼時期的音樂大眾化追求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并沒有很好的得到落實,但在延安時期這種理論訴求卻得到了最好的實現。延安時期的音樂理論建設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政治性。
它對于中國音樂發展最大的貢獻在于: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熱潮的激勵下,確立了中國音樂民族化、大眾化的發展方向。音樂大眾化在這一時期最終得以確立,主要依賴于當時的音樂創作實踐和豐富多彩的音樂活動,同時又離不開文藝方針政策的指導。自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陜北后,延安便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本營。此時,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使延安成為中國革命以及新文藝運動的中心。當時延安匯集了大量的進步音樂家,其中有許多人如呂驥、向隅、唐榮枚、張貞黻等都是具備相當專業音樂水平的音樂家,他們在救亡圖存精神的號召下,走上前線和走進敵后宣傳抗戰,在體驗現實生活與深入群眾的過程中轉變了自身的世界觀和創作觀念。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音樂事業中,掀起了群眾歌曲創作的藝術高潮,并將創作經驗提煉升華為創作心得和音樂理論。此外,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的音樂教育理論以及對于民間音樂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在培養延安解放區的音樂人才以及推動音樂民族化大眾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音樂大眾化成為這一時期文藝界的普遍的追求,音樂大眾化在延安解放區最終確立。
這一時期的音樂大眾化既有前期音樂大眾化的一些共性,同時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即黨對于文藝發展的干預指導性前所未有的加強了。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進一步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強調文藝的改造與服務,不僅要改造某些左翼藝術家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從而使其向工農兵方向轉變;同時還強調要用中國傳統的民族民間藝術形式風格來影響和改變他們原來的西化風格,從而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講話”指明了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提出并解決了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擺正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比較徹底地解決了音樂大眾化的路線、方針問題,成為延安音樂理論建設的重要一面。延安時期的音樂理論建設與音樂實踐緊密結合,大多數革命音樂家身兼創作、教學、戰地宣傳等多重工作,他們在實踐基礎上對音樂評論、音樂理論研究進行了新的探索,提出、討論了許多問題,如音樂與現實生活的關系、音樂的繼承發展,中西文化關系,民族化、大眾化等問題都得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就。其中音樂的民族形式問題、民間音樂研究、民族音樂理論期刊的建設等成為我國音樂理論建設中極其光輝的一頁,是社會主義時期音樂理論建設的雛形,為現代音樂建設譜寫了令人驕傲的篇章。
延安時期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是這一時期音樂理論探索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這一問題的提出和討論,既有現實的也有歷史原因,其出發點在于使文藝能夠爭取更多的群眾,從而使文藝能夠更好更有效地為民族解放戰爭服務。這些討論的中心議題,主要是如何理解和對待西方音樂對中國音樂的影響,如何使音樂創作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樂于接受,與此相聯,就不可避免涉及到音樂上的中西關系、傳統繼承等問題。
事實上,音樂“民族形式”的探討早在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展開時就已提出。當時僅僅認為文藝內容應盡力反映群眾的現實生活,在形式和語言上要盡可能考慮到群眾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來,音樂工作者為迎合群眾對于民間音樂的喜愛,提出了采用“利用舊形式、反映新內容”的看法。盡管這樣的觀點在理論深度上還比較單薄,但這些看法對當時抗戰音樂創作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40年代初,“民間研究會”的成立之后,音樂家們在經歷了對民間音樂的采集、整理、研究之后,才達到了“文藝工作者應該重視對民族傳統的繼承”和“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群眾,先當群眾的學生,后當群眾的老師”這樣的認識高度。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冼星海和賀綠汀的文章較有代表性。冼星海《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音樂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立足點應該是現實生活,創作新的民族形式,關鍵還是要向人民大眾的生活學習。對于如何更好地解決音樂的民族形式問題,冼星海指出,應該“廣泛地收集民間小調、歌謠,深刻地研究中國的音樂史。另外還要注意呼吸西洋音樂高深的技術與理論修養。”這也就是他說的:“以民間音樂做基礎,參考西洋音樂進步成果,創造一個新的中國音樂形式”(在《生產大合唱》座談會上的發言)。賀綠汀在《抗戰音樂的歷程及音樂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在抗戰時期,我們要用音樂來動員民眾,當然我們更需要民間歌謠形式。利用民歌,創造為民眾所喜愛的新民歌,我們的目的是在動員民眾、教育民眾、提高民眾的音樂水平。不過這不能算是新中國音樂的全部,至多也只能是中國新音樂的一部分。在這偉大的時代,我們更可以創作出比較高深些的大型作品,如交響曲、管弦樂曲、歌劇等等,以反映我們的偉大的時代。”
此外,延安時期的音樂理論建設還圍繞音樂與政治的關系、民間音樂研究以及音樂理論期刊建設等進行了探索。音樂家除了通過言論闡明理論觀點之外,還論述了音樂批評標準問題。冼星海就認為音樂的標準就是社會功利價值標準,在這一標準下,力求藝術性與黨性的統一,他說,“音樂不獨是一種斗爭的武器,他還能給人們一種高尚娛樂,不單是鼓勵沖鋒殺敵,還能慰藉許多在長年抗戰中的英勇戰士”《(民歌研究》)。他認為首先要把音樂當作藝術看,作為“反映大眾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種手段”,然后才是音樂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20世紀40年代,延安的民族音樂研究工作是第一次系統的、有目的的中國現代民族音樂研究,開展了民族音樂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績。其中冼星海的《民歌研究》和呂驥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成就最高。冼星海認為:中國民歌“有它自己活潑的規律,我們應該辯證地去了解它,我們不能拿別人的尺死板地來判斷。”關于研究民歌的方法,冼星海則主張到民間去向民間藝術家學習。呂驥于1946年完成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一文則從民族音樂學的理論高度系統性提出了民間音樂研究的理論框架,他首先指出研究的目的:“應該是了解現在中國各民族、各地區流行的各種民間音樂的狀況,進而研究其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演變過程的歷史,從而獲得中國民間音樂的一些規律性的知識,作為接受中國民間音樂優秀遺產,建設現代中國新音樂的參考。”進而又提出了研究的原則和方法等問題,即“首先了解中國各民族音樂形式的社會條件,即中國各民族人民的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的實際情況,甚至于還要研究各民族的發展史,……僅僅著眼于民間音樂的形式(如音階、調式、節奏式樣、樂曲組織等)與技術性的研究,并不能深刻了解民間音樂,只有從民間音樂的內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現這些內容的音樂語言)出發,才能真正了解民間音樂這些形式與技術在他們生活中具有什么意義”。呂驥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既是對延安當時展開中國民間音樂的學習、運用和研究的理論總結,又為后來人們研究中國民間音樂指出了正確的原則和方法。(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341.)音樂期刊建設是延安時期音樂理論建設的開拓性舉措。
音樂刊物是開展音樂理論建設、推動音樂創作向前發展的重要平臺。1942年4月,由延安邊區音協和邊區作曲者協會編寫的《民族音樂》創刊。刊物主要刊載論文、創作歌曲、介紹蘇聯音樂和西方音樂家,到同年12月共刊行8期。其中,李煥之的《歌曲中國化底實踐》、麥新的《略論聶耳的群眾歌曲》、民歌聯唱《七月里在邊區》、張魯執筆的《怎樣采集民間音樂》、呂驥的《民歌的節拍形式•民間音樂研究筆記之一》等論文,都是民間音樂研究的豐碩成果。1942年11月,由中國民間研究會編印的《民間音樂研究》雖然只刊出一期,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第五次全體大會告全體會友書》(刊詞)、呂驥的《三年來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如何研究民間音樂》,陳沖的《評劇敲擊樂器演奏法》等文都表現出了較高的理論境界和水平。1947年6月,呂驥在東北佳木斯創辦了以刊載創作歌曲和評論性短文為主的綜合性音樂刊物《人民音樂》,除刊發音樂新作之外,還發表歌曲創作及群眾音樂活動的指導性文章,同時還開設了音樂基本知識講座和民間音樂研究專欄,有利推動了東北群眾音樂的發展。解放后呂驥領導中國音協時期,最先創辦的音樂刊物也定名為《人民音樂》,由此可見《人民音樂》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創刊的開拓性意義。
延安時期的音樂理論建設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雖然它與政治關系過于緊密,在音樂創作技法和音樂史學等專業音樂理論上的建樹不夠豐厚甚至有明顯的不足,但的確為后來新中國的音樂文化事業培養了人才、提供了經驗。特別是延安文藝確立的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方向,成了新中國音樂文化事業健康發展的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