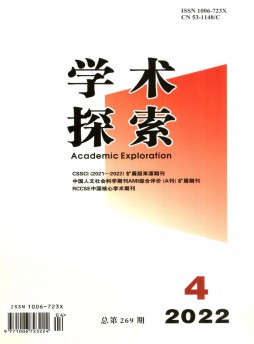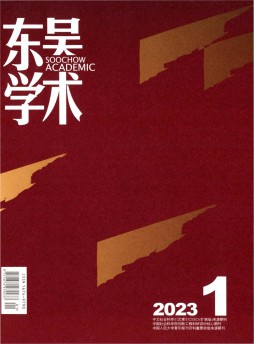衛禮賢的學術網絡和漢學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衛禮賢的學術網絡和漢學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德國研究雜志》2015年第三期
衛禮賢(RichardWilhelm,1873-1930)曾是德屬青島殖民區的一名傳教士,后任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成為德國學界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19世紀20年代,他作為學者和記者,將大量的中國傳統經典文本翻譯成德語,并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①在這些活動過程中,衛禮賢接觸了大批中國官員和學者,形成了他的中國人際學術網絡。衛禮賢的中國學術網絡和漢學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青島時期(1899-1920年)②、北京時期(1922-1924年)、法蘭克福時期(1924-1930年)。在不同的時期,衛禮賢的中國學術網絡呈現出不同的特點。19世紀初,中國的青島是德國的殖民地;19世紀20年代,中德兩國逐漸成為平等的國家。在工作關系中,衛禮賢的地位由殖民特權走向相對平等。對于中國,他逐漸拋棄了“學術”或“文化霸權”①。本文試圖從這一視角,分析衛禮賢的中國學術網絡及其對漢學研究帶來的影響。
一、青島時期(18991920年):在殖民地努力通過建立新工作關系成為“內行人”
衛禮賢的青島時期有兩方面特征。一方面是被租借地的殖民特征深深影響,衛禮賢身處德國殖民強權的社交和知識精英圈子里,享有一系列的特權和隔離政策,同時有仆人侍奉,并且奉行西方至上的理念和基督教的意識形態,②這使他與中國人區別開來。另一方面是衛禮賢不斷探索發現中國精英所秉持的高標準的中國道德和哲學方面的傳統和文化,這方面的意識顯然與殖民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等級制度背道而馳。從高密的非殖民區到尊孔文社,衛禮賢與那些逃到青島的前清代官員建立松散的聯系,受到了中國道德和哲學的熏陶,而且最終在他的生活方式和作品中都有體現。除了在德國殖民地內經營的人際網絡,衛禮賢還建立了多層次的學術工作網絡,有的工作建立在外國人和當地語料提供人之間的等級關系之上,有的工作建立在學者間知識交換、不同個體間密切合作的平等的關系之上。在德國殖民區,衛禮賢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中國學者提供各種條件,并為他們提供資助,反過來,衛禮賢的中國同事則為他提供構建知識和完成工作計劃所需要的內部信息。在這種網絡中,雙方都握有權力和知識。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削弱了殖民關系帶來的權力分配不均,但也未能使雙方完全平等。其后的一些年,德國殖民政權被取代,殖民區也被接管。在最開始的幾年,衛禮賢研究漢學的目標是證明中國的倫理體系(儒學)和西方哲學(康德)、倫理體系(基督教)具有同等價值(和相通之處),并想借助翻譯來消除二者之間的鴻溝。衛禮賢認為儒學對西方世界同樣有價值。此外,這一時期他大量接觸到東西方觀念,這使其對二者間聯系的理解得到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因為東西方那時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③當時,衛禮賢和他的中國翻譯兼助手李本靖的工作關系依然深受殖民等級關系的影響,但1900年,衛禮賢開始主動與高密當地的儒學精英建立非正式合作關系,一種新的工作關系在那里開始逐漸成型。后來,衛禮賢受到聘請,這種關系也由非正式轉為正式。衛禮賢擔任的是高密非租借區一所學校的法定校長,當地的上流人士為其開展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除了負責交換邀請函和禮物,這個職位一方面建立了互惠系統,另一方面為他搭建了實地研究的平臺。衛禮賢可以在當地語料提供者那里收集信息,這有助于完成他的學術追求,也就是翻譯經典。在這樣的關系中,人們認識中和現實中在社會關系和知識上的平等才真正初步實現。1901年衛禮賢創辦德華神學校,為中國人設置副校長一職,實際上是把設置課程的職責交給了中國人,這些都證明了他觀念上在向平等轉變。衛禮賢建立的新工作關系一方面包括接受內行人的幫助,比如他在翻譯內容艱深的文本時會向通曉道家學說的人尋求幫助,但這些人的名字在其翻譯作品中鮮有提及;其他非正式合作包括在他創辦的尊孔文社與一批知識分子和前清代官員的聯系,1911年以后,這種聯系愈益頻繁深入。在眾多合作項目中,他與辜鴻銘(1857-1928年)的關系至關重要。辜鴻銘是一位在愛丁堡成長、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信仰儒教。他秉持文化保守觀念,主張重建君主制,并在東西二元說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辜鴻銘多次探訪青島以及他和衛禮賢之間的頻繁通信不僅僅限于交流想法,他想用“中國文化的概要、對鬼神智慧的洞悉、知識運動的奇妙景象以及古時的文學作品”①來震撼和打動衛禮賢。雖然辜鴻銘在財務上要依靠衛禮賢,但在信中依然將自己視為衛禮賢的老師,甚至在倫理道德問題上給予建議,這已經超越了工作關系的界限。
從衛禮賢的角度講,他對辜鴻銘的想法和解讀印象深刻。在他看來,辜鴻銘的講演“當屬最有趣的講演之類,他舉的所有事例均正確無誤”②。衛禮賢將辜鴻銘的講演和其他作品翻譯為德文,包括著名的《中國的牛津運動》,對歐洲產生巨大影響。在兩人關系的發展過程中,辜鴻銘非常鼓勵衛禮賢通過翻譯經典來使歐洲了解中國文明。同時,衛禮賢為自己對中歐看法的不同找到了支持依據,也確定自己對“中國精神”這一模糊概念有著與內行人較為接近的把握。在翻譯《易經》過程中,從1913年至1920年(由于一戰,1914年8月至1917年間中斷),衛禮賢與前清代官員、德高望重的儒家學者勞乃宣保持著非常親密的工作關系,這種關系超越了那些非正式的工作關系。在衛禮賢看來,他和勞乃宣之間是師生關系,這種關系首先可以作為證明自己是研究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內行人”的機會。二人共同的作品在德國出版,署名衛禮賢。之后,勞乃宣又將作品重新出版。衛禮賢第一次用“我們”這個字眼來描述工作過程,這體現了勞乃宣對于衛禮賢解讀和翻譯《易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勞乃宣傾向于使用“上課”的說法來描述他們間的合作,而沒有強調參與了“工作”。衛禮賢寫到:“我們做了非常細致的工作。他(勞乃宣)用中文解釋文義,我做筆記,然后完成德文翻譯,再將之回譯成中文,過程中不查閱參考資料,然后由勞乃宣進行比較,看我是否理解到位。接下來是對德文翻譯完成風格上的統一,以及討論細節。最后我還要對翻譯進行三到四遍的修訂,并給重要的點加注。翻譯的質量就這樣提上去了。”
①對衛禮賢來說,勞乃宣是令人敬佩的老師,也是為他打開《易經》之門的“大師”。勞乃宣在學術上給衛禮賢的指導,令他著迷:“在他(勞乃宣)的循循善誘下,我在他有些古怪卻又熟悉異常的世界里游走,仿佛被他迷住了。”衛禮賢稱他們共同的作品為勞乃宣的“遺產”②,他不但在描述勞乃宣本人時不吝溢美之詞,對他們工作的描述也是如此:“與這位年長的大師一起工作的幾個小時里,我內心有所超升。”衛禮賢的同代人覺得這種合作形式非同尋常。如果把這種評價往好處看,意為這樣的合作啟發他們重視內行人的知識,衛禮賢的卓越才能也因此體現出來。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G.Jung)這樣夸獎他們的合作:“這樣的合作理應受到贊揚,因為它使《易經》得以出版,注釋也非常優秀。”③但把這種評價往壞處看,就是在質疑衛禮賢作為一個學者的獨立性以及他是否有做出客觀判斷的能力。④在勞乃宣看來,與衛禮賢的合作是一種工作關系,同時也是其完成政治撤退的機會。勞乃宣視自己為“流動難民”⑤,多次談起過“逃亡”⑥。衛禮賢邀請他留在禮賢書院,勞乃宣把這里當作戰爭期間的庇護所,他擔心共和政府會因為他對1916年復辟運動的支持而對他進行報復。⑦勞乃宣在他的作品中特別強調衛禮賢是尊孔學社的社長,并說衛禮賢是一位研究員,“他讀圣人之書、學圣人之道”⑧。在1917年,勞乃宣又著重描述了他們之間的工作關系:“尉(衛)禮賢篤志中國孔孟之道,請求經學。”⑨衛禮賢在青島時期與辜鴻銘非正式的工作關系及與勞乃宣正式的工作關系標志著平等的新型工作關系的實現,在之后的幾個時期里,中德之間平等的政治關系也得以實現。這些平等的工作關系反映了在樹立“中國”這一概念過程中的學術互動。“中國”這一概念與儒學、信仰、帝國以及永恒不變的價值觀是平級的,是堅不可摧的一塊錚錚鐵板,也是與西方相對的模式。之后,張君勱從這個意義上出發把衛禮賢說成是一位“透徹了解中國精神”的“儒生”。①這些緊密的合作關系使衛禮賢成為“內行人”,并塑造了他對于中國的概念,并為他成功進入德國學術界鋪平了道路。
二、北京時期(19201922年):利用雙重角色擴大學術網絡
在北京時期,衛禮賢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學術網絡,并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他是德國駐華大使館的學術顧問,受委托成立東方學社。另一方面,他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主動接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杰出人物。這些杰出人物積極倡導社會改革的理念,呼吁建設一個新的共和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廣泛吸收了西方政治理念和哲學思想。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這段時間人們內心充斥著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懼。1911年辛亥革命已經打碎了“孔子權威”,衛禮賢感覺“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力量可能撤出人類歷史的舞臺”②。然而,世界大戰把歐洲文化推向了類似中國文化這樣的危機,使得實現“中西文化融合”成為了可能。衛禮賢不再像青島時期那樣優先傳播西方文化,而是意在“混合”中西文化,實現東西方文化中最有價值方面的接觸和交流。五四時期的辯論主題不是“是否混合中西文化”,而是“如何混合中西文化”。這深刻影響著衛禮賢,促進了他關于中西文化觀念的轉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杰出人物的相互支持和工作關系反映了這一點。在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例如蔡元培、胡適、徐志摩,構成了衛禮賢第一個學術網絡。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衛禮賢在北京大學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1920年和1922年,衛禮賢曾多次在北京大學作講座。1923年11月③,由于德國財政危機,衛禮賢丟掉了在大使館的工作。時任北京大學德語系主任的楊斌晨曾是衛禮賢的學生,衛禮賢通過他成為了北京大學全職教授,進一步被納入一個更大的知識分子學術網絡。
④衛禮賢第二個重要的學術網絡是指東方學會的儒家傳統主義者,例如王國維、羅振玉、沈曾植、辜鴻銘,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團結一切社會的建設者。衛禮賢在青島時期著重思考的新儒家觀念,在東方學會的章程中占有主導地位。這個章程反映了帝國及其文化衰落的情況,揭示了中國保持儒家主導地位的必要性。衛禮賢還有第三個學術網絡,主要是張君勱,其次是梁啟超。衛禮賢和張、梁二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他們意圖打通新儒家思想、(西方)人生哲學以及中西方相關概念。此外,衛禮賢還建立了一些較小的學術網絡,例如留德歸來的中國學生校友組織,在德留學的中國學生福利協會,中西音樂會“北京的夜晚”。為了闡明衛禮賢在北京時期學術網絡的新狀態,需要引證兩個典型的例子,即衛禮賢和張君勱、蔡元培的關系。張、蔡二人都曾在德國生活過,深受德國哲學和思念觀念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和衛禮賢一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衛禮賢與張君勱之間的合作是基于良好的個人關系。他們互相交流思想,在寫作《德英中哲學詞典》的過程中開始產生了工作關系。1922年10月,當衛禮賢和張君勱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們二人思想的相似性就已十分明了。張君勱在上海代表哲學和科學界歡迎德國哲學家漢斯•杜里舒(HansDriesch)時,衛禮賢也在現場。對于中德間的關系,張君勱表示反對軍事同盟,支持學術聯盟。
1923年,杜里舒和高度重視儒學的衛禮賢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同年,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講座,倡導“科學和玄學之爭”大討論。每兩周召開一次字典談論會,澄清主要的哲學和心理學概念。張君勱曾在德國留學三年,把德國人生哲學定義為“玄學”①。他認為科學并非萬能,對“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在這次學術爭論中,衛禮賢堅決地支持張君勱。1924年7月,衛禮賢在離開中國時高度評價中國的朋友和同事:“我和他(張君勱)成立了由中西學人參加的圓桌會議,我們談論了現在、未來以及時代需要。”②他認為,以張君勱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心系中國的未來,他們在政治和思想領域的努力將會成功。1930年,張君勱盛贊衛禮賢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學者,促進了“新世界文化”的產生。③衛禮賢和蔡元培之間從嚴格意義上講不存在工作關系,但他們二人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和共同的目標,即通過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并非僅是如此)發掘儒家文化的優秀成分。早在1912年,蔡元培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曾要求高校開設中國經典古籍的學術研究。對此,衛禮賢十分認同。1907-1911年,蔡元培曾在萊比錫求學,他非常了解德國對中國的看法。蔡元培任職于教育部期間(直到1912年7月2日),他的老師、世界歷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克特(KarlLamprecht)委托他派遣中國學者前往德國從事學術研究。蔡元培反對“全盤西化”或者“同化西方”,他主張有選擇地接受外來思想、理論、科學,通過“消化”吸收,使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反復強調,中國學者不應該簡單照搬歐洲的東西,必須在歐洲東西的基礎上有新發現;不應該僅僅保護國粹,必須用科學的方法發展國粹。此外,蔡元培認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中西雙方互相交流,即把西方文化引進到東方、把東方文化介紹到西方。衛禮賢和蔡元培一方面主張“進一步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重建固有的精神”①;另一方面強調采用系統的方法調適中西文化,拒絕“簡單拼湊”兩種文化。衛禮賢明確表示,創造一種新文化需要把中西文化結合起來,但不是只言片語的組合。衛、蔡二人都主張從自己文化背景出發調適中西文化,衛禮賢希望通過一定的重構讓德國人理解中國的概念,蔡元培想要從中國人的角度重新闡發自由、民主和平等。在確保中西文化各自獨立的基礎上,如何彌合二者的差異,這是衛禮賢和蔡元培共同面對的難題。
三、法蘭克福時期(1924-1930年):把中德學術合作作為議題之一
衛禮賢離開中國后,開始了他在法蘭克福大學的工作。作為法蘭克福大學的教授,衛禮賢充分利用自己的學術網絡與中國同事建立了多樣的合作方式,創建了一個包括中國同事在內的中國研究所。中德之間的這種學術合作,符合衛禮賢的理念,即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是平等的。衛禮賢認為,人類的新文化需要不斷積累,但絕不是某一種文化的轉化,而是多種文化不斷調適的結果。他不僅從思想上,而且還是從制度上,遠離西方所固有的“文化霸權”。當時,研究中國問題的“知識話語權”是由歐洲/德國的學人掌握著的,但衛禮賢一改舊有的觀念,對此表示反對。衛禮賢認為,中國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研究對象,不可以簡單借助中國人的幫助、而主要運用西方專業知識加以研究,應該把研究中國問題的“知識話語權”交給中國人。由此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是,中國研究所把加強與中國學人的學術合作作為重要議題。北京的相關學術組織認為,為了復興國粹,必須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在衛禮賢看來,之前的歐洲漢學研究缺乏對中國歷史的觀照,這導致漢學理論存在嚴重的偏見。因此,要克服這些障礙,漢學研究必須與中國學人合作。衛禮賢強調,理論分析和歷史事實密不可分,西方漢學家不能脫離中國學人。②具體而言,衛禮賢在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的學術網絡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從中德兩國的國際關系上,合作表現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和中國學人都居于領導地位。合作所需要的資金最初由德國基金會提供,后來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主要用于出版《漢學》(Sinica)雜志。此外,中國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中還有中國政府駐外正式代表。第二,邀請一些中國學者前來訪問,作講座,參加研究所的會議。因此,他們可以充分地討論中國問題。在這方面,衛禮賢主要借助了自己在北京的學術網絡。曾前來作講座的有蔡元培(1925年)、胡適(1926年)、徐志摩(1928年)以及在德國居住的年輕學者。與其他漢學研究所相比,中國學者在這里不僅是教學助理,還是講座教師。1925年,蔡元培把中國駐漢堡領事、學者俞大維推薦給衛禮賢作中國研究所的成員。1927年6月12-16日,中國學者舉辦了一次大型的音樂會,激起了德國廣大民眾的興趣。第三,衛禮賢在《漢學》雜志上發表中國學者的文章,提高中國的學術影響力。開始,他主要是翻譯已經在中國發表的文章。例如,衛禮賢通過介紹梁啟超和他的文章,使德國學者認可中國文章的質量。后來,一些原創性的文章也刊登在《漢學》雜志上。這些文章的撰稿人有胡適(1927年)、生活在德國的年輕學者許道臨(1928年)、中國音樂專家王光祈(1927年、1928年)和中國研究所的外語助理丁文淵。第四,中國研究所章程明確規定加強中德青少年之間的交流。在具體實施上,主要是擴大中國留學生和德國學生的學術網絡。基于此,衛禮賢積極創立中國留德學生會。第五,衛禮賢極力提高中國學人在德國學術界的地位。他高度評價王國維在古代史領域的重要地位,認為王國維的死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衛禮賢回到德國后,曾幫助蔡元培申請法蘭克福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但受到學校教授會的抵制,最終沒有成功。第六,衛禮賢始終和中國學人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1925年,衛禮賢收到蔡元培的兩封來信。第一封信寫于7月23日,蔡元培感謝衛禮賢贈送他《新水星》(DerneueMerkur)雜志的復印件,這份雜志上有一篇衛禮賢的文章《中國和力量》。蔡元培感謝衛禮賢對中國的支持和幫助。第二封信寫于11月12日,蔡元培感謝衛禮賢邀請他參加會議,并解釋了自己不能與會的原因。蔡元培向衛禮賢推薦他的朋友傅斯年和俞大維。此外,衛禮賢曾把自己的著作《中國的精神》贈送給蔡元培。
縱觀上述三個時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衛禮賢的中國學術網絡是如何影響他的漢學研究。衛禮賢與長期以來受到歧視的中國學人建立了豐富的學術網絡,打破了殖民時期遺留的政治與學術研究范式。作為新型的學者,衛禮賢超越了漢學界長期存在的個人主義,把知識生產看作是集體知識收集的過程。在開展學術活動的過程中,衛禮賢逐步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和價值,把漢學“知識話語權”①交給了中國學人。當然,這種“知識話語權”只限于學術工作的具體方面。
作者:羅梅君 單位:柏林自由大學 東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