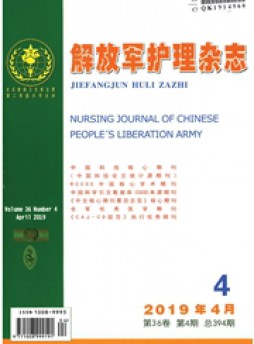解放當代文學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解放當代文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意思,是說,要將“當代文學”從目前的“學科”框制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個特定的中國文學概念,一個表達了當下的、鮮活形態的時間性文學意涵的概念,“當代文學”需要一種“解放”。
十多年前,《文藝爭鳴》雜志曾組織開展過一次主題為“當代文學研究的危機”的討論,就是討論“當代文學”作為一種學科概念的危機。如果說比較文學界常常討論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是對跨國、跨文化的“比較”是否可能的一種不自信的學科自我意識危機,那么,當代文學研究的危機,則是一種人為性的,是一種學術社會學博弈的現實結果,是一種表現為現實的學科體制現象,甚至是一種在“當代文學”作為一種學科在興起建立之初似乎說得過去,但已有權威學者嚴重質疑,并且隨著時間流逝語言命名包袱越來越重、越來越尷尬的社會語言學現象。
什么是當代文學?我的理解很簡單,即當代文學是今人的文學,是活著的文學生活、文學參與者創造的不斷發展前行的文學。在具體理解上,我們要把當代文學作為一種生命時間現象,體現著生命倫理和生命歷史的意味,即如果一個作家還活著,那么他就在當代文學的視野之內,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應在“當代文學”之內了,他成為了“歷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當代文學》中說過,作為一種時間性文學概念,“當代文學永遠處于從過去的文學向將來的文學生長的過程當中,它是變動不居的,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為它設定一個固定不變的起點。當代文學應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從事創作的作家及其作品為主,或者說當代文學就是批評家的天地。研究過去文學的人,我們稱其為文學史家或者學者,而研究當代文壇當代作家當代作品的人,他們直接就是文學批評家。批評家從不滿足于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和學者,他們要成為歷史本身,要與文學的歷史融為一體,他們本身就是當代文學的一部分”。我覺得,當代文學就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時間和進化中的動態概念。一方面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理解“當代”的性質和“當代文學”的性質,不應將其固定化地用一個“起點”來將其學院化、學科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其變動不居的類似生命生活的發展、成長特質,而忽視它,不將它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來看待,仿佛一個“歷史時間性”意義上的學科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起訖點,那就會不符合實際而形成一種語言和觀念的教條和僵化。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其《文學原理》一書中為那種只有“少數堅毅的學者捍衛并研究”的當代文學辯護說:
反對研究現存作家的人只有一個理由,即研究者無法預示現有作家畢生的著作,因為他的創作生涯尚未結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釋;可是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發展前進的作家;但是我們能夠認識現在作家的環境、時代,有機會與他們結識并討論,或者至少可以與他們通訊,這些優越性大大壓倒那一點不利因素。如果過去許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們研究,那么與我們同時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這段話為當代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辯護。但這個辯護卻無法成為將當代文學視為我們理解中的“學科”的辯護詞。因為我們的“學科”對“當代文學”的理解與韋勒克和沃倫對“當代文學”的理解根本不一樣。在韋勒克和沃倫那里,當代文學研究或許有天生的局限,卻沒有我們的“學科”的研究“危機”。
當代文學研究的“危機”(說危機也許過于嚴重,它不過是比照“比較文學危機”的一個說法)在于我們給它設定了一個固定的,仿佛不變的起點(1949年)。而這個起點的固化與“當代”這個富有生命動態的詞匯發生了名實不符的矛盾。屈指算來,我們困在這種“學科”意義上的“當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說是“陳年往事”的越來越遠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還是“當代”嗎?現代性是個好東西。但現代性也有畫地為牢的技術性樊籬及其狹窄,也有“斷裂性”的仿佛永遠要確定一個告別過去的“起點”的嗜好。“當代文學”的“學科”尷尬在這里不能不說是由現代性的觀念局限所造成的。
當然,對當代文學的這種學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許還是現實的、物質性的“學科體制”層面的因素所使然。我們應該將“學科”視為一個現代性的更靠近物質層面的制度化、體制化的東西,它建立在現代大學教育的學術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術性的明晰化和穩固化是它帶給學者和教師的便利,是將歷史和現實事物、將學術對象加以邏輯化知識化的需求結果。是一種非常必要的學術秩序化動機和訴求。作為學術研究人員,我們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學科”之上。盡管我們有時用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似乎表面掩蓋了“當代文學”的學科化,但實際運作中,“當代文學”完全是一個“學科”化的客觀而實在的學術存在形態,從學會、教育、專業等區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的界限是極為明確的。當然,我們應該理解現在這種將當代文學學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當代文學”“學科”以來,它大大推動了當代文學的研究,培養了持續成長的學術力量,取得不斷超越的學術成果。但所有這些積極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決將“當代文學”作為一種有著固定起點的“學科”,與將“當代文學”視為一種不斷發展變化、意指當下文學及其現時生活的“領域”,這兩種理解之間的矛盾。就現實狀況,從小處說,這只是一個學科的命名問題;從大處說,則是中國文學“學科”如何整合的現實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有關“當代文學”的說法,也許就不僅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學術現實操作的難題。但是,既然為“學術”,為由學術而形成的“學科”,就總要科學和名正言順吧,這是學術和學科起碼的倫理要求。我知道,這并不是我們坐在這里,或寫寫文章就能解決的。說“解放”,談何容易!
怎么“解放”?這不是我能夠說的。
我只想指出,現在是應該說要將真正的“當代文學”從學科中解放出來的時候了。“解放”是一種更明確的表達和訴求。無論如何,是一個“學科”也好,是一個學術“領域”也好,“當代文學”不能這樣地成為一種異化語言概念而存在下去,“當代文學”需要恢復其僅指當下的鮮活的文學的本來含義。當代文學的“歷史性”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它的“歷史性”應建立在“當代”作為一種人的生命生活的現世時間基礎之上。
《文藝爭鳴》雜志2007年推出了“當代文學版”,我在前面寫了一個題為《當代的意義》的發刊詞,并無意挑戰“當代文學”概念的現有秩序,但實在有將“當代文學版”辦成體現當代性、當代精神的切近文學現實、參與當代文學發展的刊物。但一年下來,十二期,反思一下,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還是太學院,太“文學史化”了。對如此豐富的前衛的“當代”,刊物體現得非常不夠。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這不能不說是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化、學院化,以文學史為重的風氣有關。我們有些無能為力。這也促使我們下決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紀新生代文學寫作評論大展”,努力體現真實的當代性,增強現場感,或叫與時俱進。新晨
應該談一談有關“當代文學”使用的語言問題。我們實在應該對語言的使用持有一種敬畏的心理和態度。這么多年來,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學科化、固定起點化,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沒有認真對待過像唐弢、施蜇存、王瑤這些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前輩和權威的反對、告誡。唐弢先生甚至說出了“現在出版了許多《當代文學史》,實在是對概念的一種嘲弄”這樣的重話。可是我們依然故我。可見世俗中的學術潮流,學科化的現代物質訴求,其勢力是多么強大。老一輩學術權威“威”而無“權”,這是對“文學史”學術史進行“文化研究”的絕好案例,是一個社會語言學視角的絕妙案例。這些學術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學術時尚而動,發表了使我們不去正視其實越來越無法不正視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們的心中懷有對語言對學術概念的可貴的敬畏之心。從社會語言學的認知角度,我們相信一切語言都是約定俗成的,如果我們約定“當代文學”是指稱我們任意或一定要指稱的對象,那么誰也無可奈何。這固然有理,詞典上有多少這樣的南轅北轍的“約定”俗“成”的詞匯,時勢造語言,語言造時勢。更有甚者,時下當代文學界的部分學者又似乎有意將“當代文學”僅僅限定在他們用意識形態歷史變遷框定的“十七年”文學加上“”文學這樣一種更為狹窄的時間概念內含上,用一種置身于我們身后的意識形態化理解的特殊的“當代文學”概念來表明它與所謂“現代文學”的對立,以及與當下的“新時期文學”對立,由此“當下”的“新時期文學”也并不充分具有“當代文學”的合法性。語言被“文化研究”所顛覆、扭曲、顛倒,造成語言奇觀,如果此時你說“當代文學”是當下形態的,他們反而會嘲笑你是在“望文生義”了。人們對“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現為語言的誠實。無論你怎樣試圖“約定俗成”,不幸的是“當代”這個詞都并不可以任意隨便“約定”,你遇到了一個很麻煩的不肯訓服的詞匯。它似乎在頑強地表明,一些語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帶有某種神性,你必須真誠地面對它,你必須對它有所敬畏,有所規束,有所遵依,畢竟“當代”一詞要比“當代文學”來得更早、更具有意義權威,你用具體“學科”來固化“當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顧一切地強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無濟于事。在我們寫下“當代”二字的時候,你不怕它會像一條泥鰍一樣從指縫間溜之大吉嗎?你會變得可笑,變得尷尬,變得慌恐,變得不自信。
處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說,還是解放了吧。
我們將失去一個“當代文學”,還將獲得一個生機勃勃的“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