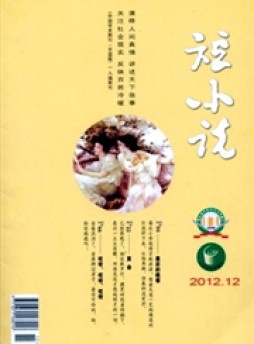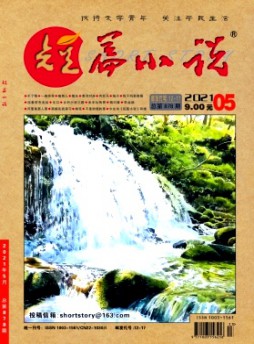施蜇存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特征淺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施蜇存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特征淺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為一名小說(shuō)家,施蜇存一直是被放到海派文學(xué)中的新感覺(jué)派里來(lái)論述的,他和穆時(shí)英、劉吶鷗都是新感覺(jué)派的代表人物,成為20世紀(jì)20-30年代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代表作家,但是一旦對(duì)他們的小說(shuō)進(jìn)行比較分析,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施蜇存的小說(shuō)其實(shí)和穆時(shí)英、劉吶鷗小說(shuō)的區(qū)別是非常明顯的。作為一個(gè)出生于杭州、成長(zhǎng)于松江的現(xiàn)代作家,施蜇存的童年世界主要接受了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的浸染,江南城鎮(zhèn)的生長(zhǎng)背景和相對(duì)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使得他在與城市摩登生活的關(guān)系上沒(méi)有像都市新潮流的引領(lǐng)者穆時(shí)英、劉吶鷗那樣能夠入乎其里而出乎其外,其小說(shuō)不可能像《夜總會(huì)里的五個(gè)人》、《上海的狐步舞》、《熱情之骨》、《禮儀與衛(wèi)生》等小說(shuō)那樣淋漓盡致地描繪現(xiàn)代都市的金錢(qián)、色情、繁華、罪惡交織混淆的現(xiàn)代生活,用夜總會(huì)的瘋狂、爵士樂(lè)的節(jié)奏、狐步舞的體態(tài)、街景的喧鬧繁華來(lái)鋪寫(xiě)現(xiàn)代都市驕奢淫逸的人生病態(tài)和感官印象。因此在對(duì)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感受力上,對(duì)摩登男女交往的敏感程度上,對(duì)語(yǔ)言修辭上的“感覺(jué)化”駕馭程度上,施蟄存的小說(shuō)都沒(méi)有穆時(shí)英、劉吶鷗的小說(shuō)那么強(qiáng)烈。他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位城市之子,文學(xué)史將他劃入新感覺(jué)派的行列幾乎本身就是一種誤會(huì)。難怪施蜇存本人對(duì)樓適夷在《施蜇存的新感覺(jué)主義———讀了<在巴黎大劇院>與<魔道>之后》一文中給他戴上新感覺(jué)派的頭銜深表不滿,認(rèn)為“這是不十分確實(shí)的”[1][p.4]。所以,施蜇存的小說(shuō)在新感覺(jué)派中因其鮮明的個(gè)性而成為一個(gè)“另類”,它在汲取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精華的同時(shí)又印上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的本土特色,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過(guò)分歐化和過(guò)分本土化的不良傾向,應(yīng)和著東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時(shí)代潮流,成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中國(guó)化的典型樣本。
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概述
如果從施蜇存最早向鴛鴦蝴蝶派刊物《禮拜六》、《星期》、《半月》等投稿的小說(shuō)開(kāi)始算起,他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大致經(jīng)歷了由現(xiàn)實(shí)主義到現(xiàn)代主義再向現(xiàn)實(shí)主義回歸的創(chuàng)作歷程,早期的小說(shuō)明顯帶有鴛鴦蝴蝶派世情小說(shuō)的影子,而中期小說(shuō)現(xiàn)代主義傾向最明顯的是小說(shuō)集《將軍底頭》,小說(shuō)集《梅雨之夕》則有向現(xiàn)實(shí)主義回歸的印痕,而到了后期的小說(shuō)集《善女人行品》中,那種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則趨于平實(shí)恬淡,帶上了濃郁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從總體上看,施蜇存的小說(shuō)主要是沿著兩個(gè)方向行進(jìn)的。一條是變態(tài)、怪異的心理小說(shuō),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式描繪男性主人公復(fù)雜、怪異的心理世界,帶上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鮮明印痕。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最早體現(xiàn)在1929年發(fā)表于《新文藝》第3期的《鳳陽(yáng)女》中,到了《將軍底頭》、《梅雨之夕》等集子中的《魔道》、《夜叉》、《旅社》、《鳩摩羅什》、《石秀》、《將軍底頭》、《黃心大師》等小說(shuō)中,這種傾向則表現(xiàn)得更為典型。一條是寫(xiě)實(shí)的、私人生活范圍內(nèi)的日常心理分析敘事,中國(guó)化色彩較為鮮明。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在1926年發(fā)表于《瓔珞旬刊》的《上元燈》、《周夫人》中有所表現(xiàn),集中典型地表現(xiàn)在小說(shuō)集《善女人行品》中。雖然它們所采用的魔幻抑或現(xiàn)實(shí)的筆法不同,但是這兩種敘事都屬心理分析敘事,都圍繞著性和欲望的現(xiàn)代主義主題來(lái)展開(kāi),都體現(xiàn)著一個(gè)現(xiàn)代作家對(duì)中西方文學(xué)吸收與選擇的個(gè)人喜好和審美趨向。雖然“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不但不同于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古典文學(xué),而且有別于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2][p.18],但是在大批的具有現(xiàn)代主義特色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中,食洋不化與中西兼容的現(xiàn)象比較明顯。相對(duì)于穆時(shí)英、劉吶鷗等“洋場(chǎng)之子”感興趣于都市生活漂浮不定的焦慮情感體驗(yàn)、攝取光怪陸離的大都市洋場(chǎng)符號(hào)的小說(shuō)描寫(xiě)不同,施蜇存的小說(shuō)則主要聚焦于都市邊緣人的心理描寫(xiě)或者以故事新編的形式透視古代英雄、高僧的靈魂世界進(jìn)行心理“祛魅”的形式還原他們的世俗情懷。這種獨(dú)異的觀察視域與作家個(gè)人的城市邊緣人身份密不可分,步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生涯的施蜇存一方面在上海幫劉吶鷗辦第一線書(shū)店、水沫書(shū)店,協(xié)辦《無(wú)軌列車》、《新文藝》雜志,還同時(shí)在上海松江中學(xué)任教,上海與松江兩地的來(lái)回奔走,使他不論與大都市還是小城鎮(zhèn)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導(dǎo)致了他的創(chuàng)作在城鄉(xiāng)兩種題材間展開(kāi),并且他巧妙地用表現(xiàn)人的分裂、壓抑心理這一主題巧妙地貫穿于這兩種題材中,使得他的小說(shuō)既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又印上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影子,成為中西文化背景下誕生的“寧馨兒”。
二、變態(tài)、怪異的心理分析小說(shuō)
先看施蜇存的第一類小說(shuō),即采用魔幻的手法描寫(xiě)變態(tài)、怪異心理的小說(shuō)。這是施蜇存小說(shuō)西化色彩比較明顯的一類小說(shuō),他是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剖析筆下人物變態(tài)、怪異的心理世界,使得這一類小說(shuō)帶有泛弗洛伊德式的傾向。不過(guò),在對(du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運(yùn)用上,施蜇存采取的是“旨在以人的心理動(dòng)機(jī)去消解歷史對(duì)象的光環(huán)的策略”,而不同于“劉吶鷗、穆時(shí)英等以人的生物性去解釋人的傾向”[3][P.165],因?yàn)椤八麄冋J(rèn)定的都是以財(cái)色為其根性的人的世俗性質(zhì)”,其實(shí)和弗氏的理論世界還是隔了一層,雖然施蜇存筆下的性心理描寫(xiě)還僅僅停留在人的本能欲望存在的淺層層面上,沒(méi)有發(fā)展升華成一種非理性的激情和價(jià)值,但是已經(jīng)超越了劉吶鷗他們對(duì)欲望都市的浮光掠影式的外在刻畫(huà)層面,而開(kāi)始向人的精神心靈世界掘入,試圖通過(guò)對(duì)人的心理世界的透視來(lái)揭示外在行為怪異的動(dòng)因來(lái)。因此,雖然施蜇存這一類小說(shuō)中的人物可能是現(xiàn)代都市里的享樂(lè)者,也可能是鄉(xiāng)下世界的奇遇者,還可能是古代文學(xué)世界里的英雄、名人或高僧,但他們此時(shí)已經(jīng)變成精神分析世界里的魔幻人物,帶著獨(dú)異的眼睛和另類的心理來(lái)觀察和體驗(yàn)外在世界。在這一類小說(shuō)中,心理體驗(yàn)的主體往往是男性人物,即用男性主人公的心靈感知去揭示外在世界的神秘怪誕。小說(shuō)《魔道》、《施舍》、《宵行》、《夜叉》、《兇宅》等是以現(xiàn)實(shí)幻覺(jué)的形式通過(guò)現(xiàn)實(shí)男性主人公自閉式的“妄想”來(lái)展開(kāi)小說(shuō)情節(jié)的,而《鳩摩羅什》、《石秀》、《將軍底頭》、《阿襤公主》等小說(shuō)是以歷史魔幻的形式通過(guò)歷史人物的心理妄想來(lái)展開(kāi)情節(jié)的。比如《魔道》寫(xiě)的是上海大城市里一位周末外出郊游的男子一連串夢(mèng)魘式的奇遇。這位男子一直處于狂亂的幻覺(jué)狀態(tài)之中,火車上的黑衣老婦,他懷疑是“西洋的妖怪老婦人”[4][p.75]和“《聊齋志異》中的隔著窗欞在月下噴水的黃臉老婦人”[4][p.75]幻像;朋友陳君的太太開(kāi)始穿著淡紅綢的洋裝、描著纖細(xì)的朱唇、以永遠(yuǎn)微笑著的眼睛讓他產(chǎn)生愛(ài)欲,感覺(jué)處處被挑逗,而第二天再抱著黑貓出現(xiàn)的時(shí)候則在他的眼中成了妖婦。在《夜叉》中的男性講述者就是一位早期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他在西湖劃船時(shí)看到的另一只船后艙里的一個(gè)白衣女子的背影被他認(rèn)為是妖淫之?huà)D,自此以后這個(gè)妖媚之影如鬼魂般追隨著他,直至把他逼瘋。在《鳩摩羅什》中,這位高僧的宗教信念和性欲之間的沖突被拿到顯微鏡下放大顯形,顯示了他痛苦而漫長(zhǎng)的靈魂煎熬過(guò)程。他一方面是一個(gè)剃度的、努力把自己修成正果的僧人,還是一個(gè)擁有妻室的日常生活正常的凡人,他一直生活在兩幅無(wú)法統(tǒng)一的形象軀體之中,“日間講譯經(jīng)典,夜間與妓女睡覺(jué)”[5][p.83]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無(wú)法維護(hù)他那幅“高僧”的嘴臉,只能靠“吞針”邪術(shù)來(lái)欺世盜名。在《石秀》中,梁山好漢之一的石秀在上山之前造成楊雄殺妻血案的心理動(dòng)因竟然是對(duì)由義嫂愛(ài)而不得的恨意轉(zhuǎn)化為嗜血的快感沖動(dòng)造成的,當(dāng)楊雄把潘巧云的四肢和兩個(gè)乳房都割下來(lái)之后“,看著這些泛著最后的桃紅色的肢體,石秀重又覺(jué)得一陣的滿足的愉快了”[5][p.121],但隨之以后又是好像欺騙楊雄做了什么上當(dāng)?shù)氖虑榈那妇危瑫r(shí),看到古樹(shù)上許多饑餓的烏鴉在啄食潘巧云的心臟,又不禁想到“: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5][p.121]因此,歷史正統(tǒng)文化典籍中的正面男性形象被徹底顛覆,男性人物的食色本性被彰顯出來(lái),強(qiáng)烈地制約和困擾著人二律背反的精神世界,還原他們俗人為食色而蠅營(yíng)狗茍的生存本相,導(dǎo)致了他們體現(xiàn)社會(huì)正面價(jià)值的“將軍”“、高僧”“、江湖好漢”身份與好色男人身份發(fā)生裂變,并且后一種身份不斷地蠶食著前一種身份并使男性人物陷入躁亂、迷失的境地。因此,上述小說(shuō)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出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孤獨(dú)、漂流等主題,它通過(guò)對(duì)人內(nèi)心世界的揭示來(lái)展示現(xiàn)代主體內(nèi)在分裂的事實(shí),描繪出他們?cè)趧?dòng)感、媚惑的生存世界里的心靈焦灼與不安,這種泛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方式顯然借鑒了西方先進(jìn)的理論和文學(xué)成果,這是一位深處大時(shí)代的東方作家對(duì)西方文明成果的自覺(jué)借鑒與吸收。但是,施蜇存的這種借鑒與吸收并不是對(duì)西方成果的生吞活剝,而是自覺(jué)把其放置到東方式的文化語(yǔ)境中,并對(duì)其進(jìn)行修改與變通,因此他又是充分中國(guó)化的。這些被男性主人公心靈感知到的女性形象不是現(xiàn)代都市培育出來(lái)的現(xiàn)代精神幻像,而是來(lái)自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或民間,《鳳陽(yáng)女》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個(gè)玩雜耍的風(fēng)騷女人,《魔道》和《夜叉》中的女人則來(lái)自鄉(xiāng)下,《石秀》中的潘巧云、《鳩摩羅什》中的孟嬌娘、《黃心大師》中的惱娘、《將軍底頭》中的漢家女子都來(lái)自民間世界,帶有聊齋式妖女的原型演變印痕。并且,這些女子僅僅是作為符號(hào)而出現(xiàn)在小說(shuō)中,很少對(duì)其作正面描繪,她們是一個(gè)個(gè)被魔化、幻化的、簡(jiǎn)單的、虛幻的象征性符號(hào),被“他視”而遮蔽了復(fù)雜豐實(shí)的心靈世界,這種揭示既顯示了施蜇存無(wú)法進(jìn)入都市女性、與現(xiàn)代都市相隔膜的邊緣人心理,也展示了一種傳統(tǒng)式的男權(quán)中心主義意識(shí)依然在發(fā)揮作用,使得具有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的施蜇存小說(shuō)在性別視點(diǎn)上依然不能免俗。
三、寫(xiě)實(shí)的日常心理分析小說(shuō)
再來(lái)看施蜇存的第二類小說(shuō),即寫(xiě)實(shí)的、私人生活范圍內(nèi)的日常心理分析敘事的小說(shuō)。這類小說(shuō)城市主體形象主要由地位卑微的普通男子和日常的“善女人”兩組形象組成。男子多是無(wú)力周旋于城市摩登生活的更傳統(tǒng)、更卑微的邊緣人物,他們和《鷗》中的銀行記賬員小陸一樣私心羨慕著大光明劇院富麗的外表、聲色齊備的娛樂(lè)、叢集著的仕女群,心中自慚形穢而一籌莫展。女子則改變了魔化的妖婦形象,也不同于穆時(shí)英、劉吶鷗筆下摩登女形象,而成為信奉禮法、循規(guī)蹈矩的良家女性,她們作為中國(guó)家庭中的妻子或母親的形象存在,生活在規(guī)格化的道德倫理框架里,是中國(guó)最普通最常見(jiàn)的女性。這一類小說(shuō)改變了前一類小說(shuō)過(guò)度困惑感、魔幻感的現(xiàn)代面具,而轉(zhuǎn)入日常化的生活場(chǎng)景敘事中,那種現(xiàn)代妖媚女性的不可知感、符號(hào)化傾向不見(jiàn)了,而成了感受現(xiàn)代都市之風(fēng)的家庭婦女或鄉(xiāng)下女人。《春陽(yáng)》中,鄉(xiāng)下的嬋阿姨來(lái)到了上海,沐浴在大都會(huì)的春陽(yáng)中:“眼前的一切都呈著明亮和活躍的氣象。每一輛汽車刷過(guò)一道嶄新的噴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櫥上閃耀著各方面投射來(lái)的晶瑩的光,遠(yuǎn)處摩天大廈的圓甌形的屋頂上輝煌著金碧的光……”[4][p.84]正是這些大都市的光鮮風(fēng)景令善女人無(wú)法安寧,喚醒了這些女人心中蟄伏已久的情欲,令她們深受精神和肉體的煎熬:“想起那年輕的行員,嬋阿姨就特別清晰地看到了他站在保管庫(kù)邊凝看她的神情。那是一道好像要說(shuō)出話來(lái)的眼光,一個(gè)躍躍欲動(dòng)的嘴唇,一幅充滿熱情的臉。”[4][p.84]而善女人偶爾的“不善”即出軌,正是施蜇存進(jìn)行精神心理分析敘事的重點(diǎn)。《霧》講了一個(gè)老處女的故事。28歲的素貞小姐是一個(gè)年邁的神父的女兒,生活在上海附近的一個(gè)島上,主要靠?jī)商煲环荨⒂婶~(yú)販帶來(lái)的上海報(bào)紙及偶爾從上海來(lái)的客人的時(shí)髦衣著而感受著世風(fēng)的變化和時(shí)尚的誘惑,自我囚禁導(dǎo)致了力比多情欲的畸形積聚,她固守著一個(gè)信仰,幻想著傳統(tǒng)言情小說(shuō)的“白面狀元郎”出現(xiàn),他“能作詩(shī),做文章,能說(shuō)體己的諧話,還能夠賞月和飲酒”[4][p.96],這種古典式的守候與表妹對(duì)男影星的狂熱追求形成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一旦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施行便不免產(chǎn)生笑話,所以他的初戀故事尚未展開(kāi)便遭遇破滅。在此,一個(gè)傳統(tǒng)中國(guó)文學(xué)里無(wú)數(shù)貞節(jié)寡婦守節(jié)的現(xiàn)代版本再一次上演,一個(gè)有關(guān)性壓抑的傳統(tǒng)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故事又一次被演繹。這些在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生存的善女人生活在故舊的生活模式中,一旦遇到新鮮的現(xiàn)代空氣,那腐朽的封建教條或風(fēng)化破碎,或被激起蟄伏已久的欲望,化為一種溫和的、不激烈的、由性覺(jué)醒帶來(lái)的心理躁動(dòng),雖然這種偶爾發(fā)生的情欲騷動(dòng)以及由之而喚起的對(duì)新生活的追求與外部世界并不協(xié)調(diào),從運(yùn)作方式到價(jià)值邏輯都形成錯(cuò)位關(guān)系,但這種曇花一現(xiàn)式的情欲覺(jué)醒卻體現(xiàn)著女性個(gè)體心理的壓抑和缺失真相。更重要的是,施蜇存對(duì)善女人的心理描寫(xiě)逃避了前期小說(shuō)意識(shí)形態(tài)式的欲望化、符號(hào)化的敘事方程式,采用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心理分析手法,以間接引語(yǔ)的自由運(yùn)用而確立了一種敘事人視角與人物視角靈活置換的修辭方式,不再是純粹內(nèi)視角的心理獨(dú)白,而是讓敘事人與人物共同參與敘述,那些夾敘夾議的分析性話語(yǔ)似乎是人物的心理活動(dòng)又似乎是敘事者的分析,似乎是第一人稱敘述又似乎是第三人稱敘述。這種模棱兩可的敘述方式能夠更加自由地從內(nèi)外兩重角度把握人物心理,既能以心理分析的方式完成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主題承擔(dān),又把這種主題的傳達(dá)變得更富于中國(guó)化,有效地阻隔了前期小說(shuō)“去中國(guó)化”的步伐,在一種日常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中完成了現(xiàn)代主義命題的闡釋。《殘秋下的下弦月》、《蝴蝶夫人》、《阿秀》、《雄雞》等篇目即為這種敘事的代表作品。所以,這些在食色本性的控制下試圖越軌而又越不了軌的善女人并沒(méi)有被他者化或神秘化,而在日常生活固有的邏輯里展開(kāi)了自己的故事。她們的日常性身份被確認(rèn)的過(guò)程,就是女性形象獲得主體性的開(kāi)始,在生活允許的范圍內(nèi)她們成了欲望的表達(dá)者甚至主動(dòng)闡釋者,成了“城市新舊交替時(shí)期人的欲望際遇的一種呈現(xiàn)”[6][p.201],變成了人生的一個(gè)有機(jī)組成部分,而不再是作為欲望的色情符號(hào)點(diǎn)綴在都市男人身邊。從這個(gè)角度看,由施蜇存在20世紀(jì)30年代所展開(kāi)善女人形象系列敘事不僅開(kāi)掘了現(xiàn)代都市敘事的日常領(lǐng)域,而且成為下一個(gè)十年以張愛(ài)玲等人為代表的海派平民敘事打下了基礎(chǔ),拉開(kāi)了序幕,這無(wú)疑使之成為一個(gè)巧妙的界碑,一個(gè)不能忽視的中轉(zhuǎn)站。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由于施蟄存小說(shuō)在兩個(gè)系列里都呈現(xiàn)出鮮明的個(gè)性化特色,所以他的小說(shuō)文本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具有重要的存在價(jià)值和意義。它們并沒(méi)有片面追求所謂的“歐化”風(fēng)格,而遠(yuǎn)離了時(shí)代地域特色下的中國(guó)文化語(yǔ)境,反而在貼近中國(guó)接受語(yǔ)境的基礎(chǔ)上呈現(xiàn)出審美和思想意蘊(yùn)上的先鋒色彩,把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風(fēng)貌與中國(guó)現(xiàn)代甚至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因子結(jié)合在一起。這種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對(duì)于思考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世界化與民族化相互交織的生存環(huán)境和發(fā)展方向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